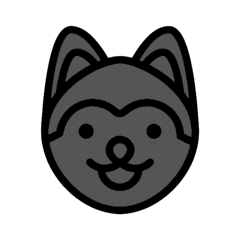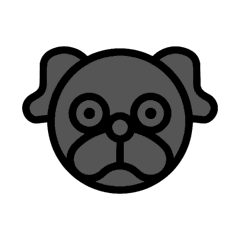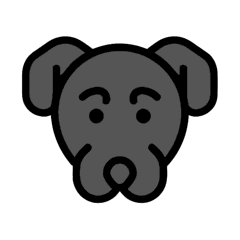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恋足、多奴、寸止,贞操锁】深渊回响 8.10更新至第九章
NTR黑皮寸止连载中现实校园足控射精管理贞操锁雌堕媚外纯爱
今天会更新嘛
BetaDenier:↑【8】对了,突然有一个新奇的想法,在最后这个药物这里除了服侍一次拿出来一颗之外,也可以让主角射一次往里放一颗🤓
那一天之后,林知夏对我,好得匪夷所思。
她不再仅仅局限于学业上的指导。她会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在某个阳光正好的下午,突然拉着我逃离实验室,带我去城市另一端那家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的、昂贵的私房菜馆;她会带我出入那些我只在财经杂志上见过的、顶级会员制的奢侈品商场,面无表情地为我换上阔挺的西装;她会当着实验室所有人的面送给我最新款的手机和一直都想要却舍不得买的配置顶级的笔记本电脑,只因为她觉得“你的旧的太卡了,影响效率”。
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将我拉进了她的世界——一个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我过去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世界。我见识到了她那深不见底的财力,每一次随意的消费,都足以抵上我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薪水。
在这种极致的物质和情感包裹下,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恋爱的错觉。当她耐心地帮我整理被风吹乱的衣领,当她在高级餐厅里自然地将她盘子里最鲜美的那块和牛夹给我时,我几乎就要相信,我们就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如果不是我时刻能感受到身前那个冰冷的贞操锁,以及身后那个早已被我的体温捂热、却依旧坚硬无比的金属肛塞的话。
它们像两个最忠诚的、最残忍的守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如今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怎样一种屈辱的关系之上。
而最让我清醒的,是有时我们并肩坐在某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她会拿出手机,处理一些“工作”。
她不会避讳我,而是会像分享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一样,戴上一只白色的无线耳机,将另一只,塞进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便能清晰地、身临其境地,听到那个加密通讯软件里,传来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那通常是一段充满了静电杂音的、带着卑微喘息的语音。另一头的男人,大概是按下了通话键后,就再也不敢松手。
然后,我会听到林知夏的声音,通过她那小巧的、隐藏在发丝间的麦克风,冰冷地、清晰地,传递到那个卑微的世界里。
“劣等品β-2302号,”她会一边用小勺优雅地搅动着自己面前那杯拿铁,一边用一种近乎无情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说道,
“你真锁了一个月啊,就为了买我一双袜子”
对面传来一阵压抑的、急切的、仿佛在点头般的喘息声。
“行吧,”林知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施舍般的、居高临下的慵懒,“给你10秒钟时间。”
我能清晰地听到,耳机的那一头,瞬间响起了一阵疯狂的、湿滑的、肉体摩擦的声音。紧接着,是那个男人带着哭腔的、绝望的哀求:“不……主人……求求您……10秒钟……不可能这么快就……”
林知夏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她只是看着咖啡杯上漂亮的拉花,用一种平稳的、仿佛在欣赏一首乐曲的节奏,开始了冰冷的倒数。
“九……八……七……”
那头的摩擦声,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绝望,甚至带上了一丝自残般的绝望意味。
“……三……二……一。”
林知夏的声音,像死神的镰刀,精准地、毫不留情地,落下了。
“松手吧。”
耳机那头,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一般的、充满了绝望和不甘的寂静。过了很久,才传来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仿佛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野兽般的呜咽。
林知夏端起咖啡,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对着麦克风,说出了那句最终的、决定他未来一个月命运的审判。
“看来还是锁得太少了。”
说完,她便挂断了通讯,取下了耳机,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消遣。
她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问我,要不要再加一块芝士蛋糕。
那一刻,我所有的温情幻想,都会被瞬间击得粉碎。我不是特殊的,我只是她的一个“玩具”,或许,是目前最令她满意的一个。
而白天有多“温存”,夜晚就有多“残忍”。
我在会所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我不再需要去端盘子,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像一个等待被传唤的奴隶,等候她的指令。
那通常是在她和某个,或者某几个高大强壮的黑人男性结束狂欢之后。
我会接到指令,独自一人来到那个我曾无比恐惧的、顶层的私人套房。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混杂着雪茄、酒精和激烈性爱后的麝香味。床上凌乱不堪,空气中还残留着属于男人的、陌生的气息。
而林知夏,早已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面孔。她会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赤着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脸上没有了白天的温柔,只有一种暴风雨过后的、带着一丝疲惫和暴戾的冰冷。
她什么都不会说,只是会从床边的暗格里,拿出一条黑色的、尺寸惊人的穿戴式假阳具,熟练地绑在自己纤细的腰间。
然后,她会走到我面前,用那根巨大的、冰冷的、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假阳具,狠狠地、毫不留情地,贯穿我那早已被扩张到极限的后穴。
那不是做爱,那甚至不是调教。
那是一种纯粹的发泄。
她会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在我体内疯狂地抽插。她会把白天积攒的、那些无处释放的压力、疲惫和愤怒,通过这根假阳具,一下又一下地,尽数发泄在我的身体里。
在那些混杂着剧痛与极致快感的、漫长的发泄过程中,林知夏有时会突然停下那毁灭般的冲撞,转而用一种更残忍的、精神上的方式来凌虐我。她会贴在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将那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淫靡的画面,一字一句地,灌进我的脑海里。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她会一边用那根巨大的、还埋在我体内的假阳具,不轻不重地研磨着我早已溃不成军的前列腺,一边用一种冰冷而又带着一丝炫耀的语气,向我描述她白天的“盛况”。
“他很强壮,比你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都要强壮。他的阳具……像一根烧红的铁棍,几乎要把我捅穿。”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回味般的、满足的颤音,“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两个不听话的玩具叫了进来,让他们跪在床边,看着我是怎么被干的。”
“我让他们比,看谁的几把更小,更可怜。其中有一个,连勃起都不到十厘米。我让那个黑人,用他那根比他大腿还粗的鸡巴,狠狠地抽他的脸,你猜怎么着?”
她在我耳边发出了一声恶意的轻笑。
“他居然被抽射了。精液射在了我的脚背上,又脏又黏,像一滩鼻涕。我罚他把我和那个黑人干完后流出来的、混合在一起的淫水,全都舔干净。”
她会细致入微地向我描述,在她和那个黑人男性赤身裸体地纠缠、被巨大的阳具肏得浑身颤抖、浪叫连连的时候,身下是如何跪着那几个被她称之为“劣等品”的男人。
他们会像最卑微的狗一样,匍匐在床边,不敢抬头看她被侵犯的脸,只敢用舌头狂热地舔舐她因为高潮而蜷缩的脚趾,亲吻她因为痉挛而微微颤抖的小腿。他们甚至会为了争抢一滴从她体内溢出的、属于那个黑人男性的精液而互相撕咬,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甘美的琼浆。
“他们每一个,都比你更懂得怎么服侍。”她会一边在我体内冲撞,一边用气声这样说道。
这本该是极致的羞辱。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内心,却因为这些露骨的、充满了尺寸对比和权力践踏的描述,产生了一丝病态的、不甘的嫉妒。
我嫉妒那些“劣等品”。
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渴望能亲眼见证她的“盛况”。我渴望能像他们一样,跪在她的脚边,用最卑微的姿态,去仰望她被更强者征服时的、那种混杂着痛苦与极乐的、最真实的表情。
我渴望,能成为她那场盛大而淫靡的权力游戏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却能亲眼见证一切的观众。
而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在一切结束之后,成为她在黑夜里,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承受她所有负面情绪的、孤独的、有生命的玩具。
在一次例行的、粗暴的发泄结束后,我瘫软在地毯上,后穴火辣辣地疼,身体因为刚刚经历过的强制高潮而微微抽搐。林知夏拔出那根巨大的假阳具,随意地丢在一旁,她赤裸的身体覆着一层薄汗,胸口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跨坐在我的身上,用一种慵懒而又危险的语气,开始描述刚才那场她与黑人男性的狂欢。
“你知道吗,”她低下头,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上,“今天那个新来的劣等品很有趣,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只敢趴在地上,像条真正的狗一样,在我被操的时候,用舌头把我的脚底舔得干干净净。”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每一个字都像钩子,勾起我内心最深处的、卑劣的嫉妒和渴望。
“……我也想……”我几乎是无意识地,从喉咙里挤出了这句话,“我也想在那个时候……服侍您。”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在她被另一个男人占有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像条忠犬一样守在她的脚边,舔舐她,亲吻她,成为她在那场游戏中,唯一能完全掌控的、卑微的私有物。
我的话,却让她原本慵懒的神情瞬间凝固了。
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冰冷。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我身上站了起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那种场合不适合你。”她淡淡地丢下这句话,开始自顾自地穿上衣服。
“为什么?”我不死心地追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在穿好衣服后,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像是不忍,又像是警告。
“你只要在这里等我就够了。”
她顾左右而言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那一刻我隐约感觉到,她不希望我看到她被另一个男人玩弄的样子,更不希望我被那个世界的、真正的黑暗所吞噬。我只是她一个人的玩具,她不想让我被别人染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极致的割裂和刺激下,我的整个人,都在发生着微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实验室里,当她不经意间对我微笑时,我会下意识地低下头,脸颊发烫,像一个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我的言行举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柔和。
我的气质开始变得柔和,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态,甚至连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女性化的痕迹。尤其是在被她用假阳具操到高潮的时候,我发出的不再是压抑的闷哼,而是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甜腻的呻吟。
林知夏似乎对我的这种变化非常满意。
她开始偶尔让我穿上女装,陪她一起出门。我们会像一对亲密的闺蜜一样,在街角的咖啡厅里分享同一块提拉米苏,在奢侈品店的镜子前一起比划着最新款的包包。她会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说些无伤大雅的私房话,引得周围的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但只要一走到无人的角落,她就会立刻变回那个掌控一切的女王。她会把我按在墙上,掀起我的裙子,用手指粗暴地玩弄我身后那个早已被撑得松软的后穴,感受着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无法自控地颤抖。
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我越发沉迷,无法自拔。我一边感激她对我的“好”,感激她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光鲜亮丽的世界;一边又在这种不见天日的、扭曲的关系中,被巨大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反复撕扯。
。。。。。。
为了庆祝一个项目的阶段性成功,林知夏组织了一次野餐,同行的还有实验室里另外两位师兄。
那天的阳光好得有些不真实。
学姐穿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裙摆随微风轻轻摇曳,像一朵不胜凉风的水莲花。她的脚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白色棉袜,紧紧包裹着她脚踝线条优美的轮廓,脚下则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小皮鞋。那装扮,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学生,与这个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
公园的小路上,她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甚至将半个身子的重量,都亲昵地、毫无防备地靠在了我的身上。她的发梢随着走路的动作,不时地扫过我的脸颊,带来一阵阵好闻的、洗发水的香气。
这幅画面,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正在热恋中的璧人。路过的行人,总会向我们投来善意的、祝福的目光,有些年轻的女孩,甚至会因为看到我们之间那种亲密的、不加掩饰的爱意,而露出羡慕的微笑。
我们一同走到了草坪上。她脱下小皮鞋,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野餐垫外侧,露出那双仍被白棉袜包裹的脚。
她踩在柔软的垫子上,轻轻地动了动脚趾,像是在享受阳光下的微风与青草的温度。
我注意到,公园里偶尔路过的男人,总会不由自主地朝她脚边瞥上一眼。
他们的目光先扫过我们,最终却黏在她的白袜脚上,或那双刚脱下、还带着余温的小皮鞋里;有人喉结轻轻滚了一下,呼吸短短顿住,再装作若无其事地错开。
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压抑着的、属于成年男性的、混杂着欲望的幻想。
他们大概永远也无法想象,此时学姐脚上那双纯洁的白袜,和草坪上那双人畜无害的小皮鞋,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被允许跪下来,贴近了看——
会发现,那双白色棉袜的袜尖,因为长时间被汗水反复浸润,早已泛起了淡淡的黄痕。
棉布表面原本柔软细腻的纤维,此刻却有些粗糙、微硬,像是曾被什么高温又腥臭的液体喷溅过、风干后留下的结痂印迹。
阳光斜照下,更能隐约辨出几道极浅的、不自然的脊状硬痕——仿佛是某次压抑着的射精,被迫喷洒在袜尖时遗留的痕迹。
而那双黑色小皮鞋,鞋口微张,内壁早已失去了新皮革的质感,鞋垫已经踩出了完整的脚型凹痕。
鼻子凑近那张着口的皮鞋时,扑面而来的并不是想象中少女的体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由旧皮革与脚汗混合发酵后的酸腐气息。
更致命的是,那气味之下,竟还有一丝隐约的腥咸,是雄性精液的味道,与其混杂的,还有淡淡的唾液气息——是被另一条舌头一遍遍舔舐之后留下的腥气。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双鞋袜,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代表着怎样一场残酷而又淫靡的游戏。
那个夜晚,两位师兄像狗一样跪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刚刚解锁的下体因为长达一个月的贞操锁折磨,已经淫乱不堪,不住的流出前列腺液
而在他们面前,摆放着的,就是学姐今天脚上这双刚刚脱下来的黑色小皮鞋。
而学姐今天脚上这双纯洁的白色棉袜,正被两位师兄用手攥着,紧紧贴在鼻子上。
规则很简单——谁先射精,谁就是胜利者。
失败者,则必须在胜者高潮的瞬间,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动作,将那已经滚烫堆积到极限的欲望,硬生生地压制回体内,继续承受贞操锁中无止尽的折磨——直到下一场比赛。
于是,欲望便成了一场残酷的竞争。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场景——
他们像两只发情到极限、丧失理智的野兽,跪趴在地,屁股高高撅起,双膝贴地,脊背拱得僵硬,像等待发情指令的畜生。脸则深深埋进那只还残留着学姐体温的白色棉袜中,鼻尖死死抵住袜尖那一小片发黄的位置。
那一片被脚汗反复浸透、早已泛黄发硬的区域,是整只袜子气味最浓烈、最刺激的源头,混合了汗液长时间浸润后散发出的脚酸味,还有一丝令人作呕却令人兴奋的腥咸……仿佛是曾被某人猛烈射精后喷溅上的残渍,早已风干,留下一圈淡淡却不自然的脊状痕迹。
其中一人甚至,抖着伸出舌头,将舌尖贴上那片疑似精斑的袜面。
那不是发泄——那是一场关乎尊严与屈服的生死竞速。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疯狂地崇拜那片被污染的袜面,是因为他们隐约知道,那处污痕的真正来源。
那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释放,而是来自另外两个男生的发泄——年龄更小,年级更低,甚至大概率只是刚被她选中的“新玩物”。
更年轻的肉体,自然也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直接套着那双白棉袜撸动,在袜面上尽情摩擦,享受汗湿纤维与敏感龟头交缠时的粗糙快感。
但那种特权,并不代表自由。
而对于那种尚未驯服、总想要更多的下体,最合适的调教方式,就是反复的寸止。不断摩擦,不断停下,不准射、不准停,直到理智被彻底磨光。
那双小皮鞋的用途,他们也心知肚明:八成是反扣在脸上的,鞋口紧紧扣住口鼻,不准滑落,不准移开。
唯一被允许的慰藉,就是那口口鼻间反复吸入的脚味,是她踩了一整天的鞋垫热气,是袜尖残留的汗渍甜腥,是那种让人越吸越渴、越渴越痛苦的气息。
这就是套着棉袜撸动的代价。
似乎是和我一样想到了这里,两位师兄的双眼早已泛红,混杂着渴望、羞耻、绝望和嫉妒。
十几秒钟后,在一声几乎是嘶哑的低吼中——
其中一个师兄的身体剧烈抽搐起来,像被从内而外点燃。
他的下体颤抖着,精液如决堤的洪水般,从被解锁不过几分钟的性器中喷涌而出——毫无保留地,尽数射进那只黑色小皮鞋内部。
他的手甚至在射完后仍死死抓着鞋跟,仿佛那里是他唯一的出口。
而另一个师兄,却在那一刻被学姐一脚毫不留情地踹翻。
他正攀上高潮边缘,身体已经抖得像筛子,精液几乎要从马眼里冲出,却在这一脚中戛然而止。
而那只沾满精液的小皮鞋,则安静地躺在一旁,成为这场残酷竞争的唯一胜者的奖杯。
此刻,看着那双被摆在阳光下的、干净的小皮鞋,我的后背不禁一阵发凉。
这份干净,是因为在那个夜晚,那个输掉了比赛的师兄,像一条真正的狗一样,用他的舌头,将胜利者射在里面的、那滩黏稠腥臊的液体,一滴不剩地,全部舔舐干净。
在铺着格子布的草地上,林知夏表现得对我格外亲昵,那种亲昵,甚至超越了普通情侣的界限。她会把剥好的、最甜的那瓣橘子,亲手喂到我的嘴边;会在我嘴角沾上一点酱汁时,拿出纸巾,用一种无比自然的、带着宠溺的姿态,轻轻为我擦拭干净。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让我几乎要融化。而那两位师兄的眼神,则像淬了毒的冰锥,死死地钉在我的身上。
中途,我去取水,其中一位师兄跟了过来。在远离人群的树荫下,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嫉妒和鄙夷。
“你别得意忘形了。”他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的怨毒,“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林知夏是什么人,她会看得上你这种穷酸样?”
我愣住了。
他看到我茫然的表情,脸上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冷笑:“别傻了。我们都一样,都是她的‘玩物’。唯一的区别是,你是她现在最上心、最新鲜的玩具,她愿意在你身上花更多的心思罢了。”
“玩物……我们?”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我如遭雷击,浑身僵硬。
他的目光,不加掩饰地扫过我的下体,和我的臀部。那眼神,仿佛能穿透我那层薄薄的裤子,清晰地看到我身上前锁后塞的羞耻模样。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他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玩具,总有玩腻的一天。到时候,你的下场,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越过他的肩膀,看向远处那个正陪着学姐说笑的、另一个师兄。他笑得那么阳光,但我此刻却仿佛能看到他笑容背后,那和我如出一辙的、深深烙印在骨子里的恐惧和臣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重新坐回林知夏身边时,她依旧对我笑得温柔,又递给我一块切好的西瓜。
我僵硬地接过,低下头,拼命地将所有的屈辱和自卑,连同那口甜得发腻的西瓜,一起吞进肚子里,藏在心里最阴暗的角落。
。。。。。。
日子在白天和黑夜的撕裂中,麻木地向前滚动。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会所的、一条不同寻常的指令。
我没有被要求去那个我熟悉的、作为“发泄玩具”的套房。而是被一个沉默的保安,带领着穿过了几条我从未走过的、阴暗潮湿的“员工通道”。最后,他让我在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狭窄的杂物间里等待。这间房,与隔壁的顶级套房,只有一墙之隔,墙壁上甚至还有一个被窗帘遮住的、用于观察的单向玻璃暗门。
我被告知,在接到传唤之前,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离开。
我像一尊石像,僵硬地站在这个狭小的、充满灰尘气息的杂物间里。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差,隔壁房间的声音,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一根接一根地,狠狠扎进我的耳朵,刺穿我的大脑。
很快,隔壁的房间就传来了声音。
一开始,是几个男人用英语和一种我听不懂的、带着浓重口音的语言在交谈。他们的笑声洪亮而刺耳,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和不加掩饰的粗野。我听见沉重的酒杯碰撞的声音,以及雪茄被剪断的、清脆的“咔嚓”声。那是一个属于上位者的、轻松而惬意的开场。
然后,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响起了。
那不是我熟悉的、属于女王的、冰冷的命令。而是一种混杂着痛苦、欢愉和屈辱的、破碎的呻吟。
那呻吟的声音,像一个开关,瞬间开启了地狱的大门。
男人们爆发出一阵更加肆无忌惮的哄笑。我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用最污秽的词语,命令她像狗一样爬过去。紧接着,是布料被粗暴撕碎的声音,和她一声短促的、压抑着痛苦的惊呼。
然后,一切都失控了。
我听见肉体被皮带或是什么东西反复抽打的、沉闷的“啪啪”声,每一声都伴随着她再也无法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呻吟。男人们在用不同的语言,兴奋地数着数,像是在进行一场狩猎游戏。
我听见她被不同的男人用最粗言秽语的方式羞辱、命令她用嘴去取悦他们。我能听到黏腻的水声,和她因为被掐住脖子而发出的、近乎窒息的、断断续续的呜咽。
但最让我崩溃的,是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似乎厌倦了这种单向的施虐。他用一种戏谑的、残忍的语气下达了一道新的命令。紧接着,我听到了好几个沉重的脚步声在向她靠近。
我第一次,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崩溃。那不再是游戏,而是契约被撕毁后,面对彻底失控的、纯粹的暴力时,最本能的、最绝望的哀求。
但那哀求,只换来了男人们更加兴奋的、魔鬼般的狂笑。
接下来,我听到了此生都无法忘记的声音。那是她被好几个男人同时按住手脚时发出的、徒劳的挣扎声。是她被那些黑人男性用他们巨大的、滚烫的阳具,轮流地、甚至同时地,狠狠贯穿她前后两个穴洞时,发出的凄厉到变了调的惨叫。
那惨叫声,很快就因为不堪的凌辱和痛苦,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混杂着哭泣和求饶的破碎呻吟。我能清晰地听到不同男人的、粗重的喘息声,和肉体毫无廉耻地、野蛮撞击的黏腻水声,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曲最残忍、最淫靡的地狱交响。
我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被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被迫听着我的“主人”,被一群我看不见的、更加恐怖的存在,当做一个公共玩物,肆意玩弄、轮番享用。时间仿佛被拉长到了无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灵魂最残忍的凌迟。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残暴的狂欢,似乎终于落下了帷幕。隔壁的声音渐渐平息,只剩下男人们心满意足的交谈声。
又过了一会儿,我所在的杂物间的门,被“咔哒”一声打开了。
一个我不认识的、同样身形魁梧的黑人男性,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他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用下巴朝里面点了点,眼神就像在示意一条狗去清理主人呕吐出的秽物。
我双腿发软地,一步一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地狱,原来是有气味的。
一股浓稠到几乎凝为实质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瞬间扼住了我的喉咙。那是一种由汗水、精液、雪茄、被打翻的昂贵威士忌、以及一丝微不可查的血腥味混合而成的、属于末日狂欢的腥臊气息。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上,沾染着大片大片的、深色的酒渍和可疑的、白色的粘稠液体,仿佛一幅被肆意凌虐过的抽象画。
而我的学姐,林知夏,那个在我心中永远高高在上、冰冷圣洁的女王……就趴在这幅地狱绘图的最中央。
她像一个被玩坏后随意丢弃的、关节扭曲的陶瓷娃娃,趴在巨大而凌乱的床上。那张曾经承载着无数奢靡与罪恶的大床,此刻看上去更像一个祭坛,而她,就是那场献祭仪式结束后,被遗忘的祭品。
她的神智已经完全抽离,那双曾洞悉一切、让我不敢直视的漂亮眼睛,此刻空洞地睁着,却没有任何焦距。瞳孔散漫,倒映不出天花板上那盏奢华水晶灯的任何光芒。一道干涸的泪痕,从她的眼角蜿-蜒而下,划过她脸颊上那片早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精液的、肮脏的粘腻。
她的嘴唇红肿破裂,嘴角甚至有一丝细微的、已经凝固的血迹。她的头发,那头总是打理得一丝不苟的秀发,此刻像一团枯萎的海草,混杂着各种可疑的液体,狼狈地黏在她的脸上和脖颈上。
她的身体,那具我曾无比渴望、也无比恐惧的、如同艺术品般的身体,此刻成了一块被肆意涂抹的画布。白皙的皮肤上,青紫色的手印、牙印、以及皮带抽打后留下的一道道狰狞的红痕,交错纵横。而覆盖在这些暴力痕迹之上的,是属于不同男人的、已经开始变得半透明或依旧乳白粘稠的精液。它们从她的后背,流到她的大腿,甚至滴落在丝质的床单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屈辱的岛屿。
她无力地趴着,上身几乎贴在床上,而臀部却依旧被维持在一个方便被从后面进入的、高高撅起的姿势。她那被过度使用的、红肿不堪的小穴和后穴,就那样毫无遮拦地、甚至无法完全闭合地暴露在空气中。穴口微微外翻,像两张被蹂躏到麻木的、哭泣的嘴,还在不受控制地向外淌着浑浊的、混合了淫水和精液的液体,将身下的床单浸染出一片深色的、潮湿的地图。
我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我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一切认知,在这一瞬间,被眼前这幅惨烈到极致的、淫靡到极致的画面,冲击得支离破碎。
那个用脚尖就能让我高潮的女王,那个用一道命令就能决定我所有悲喜的主人,那个我以为是金字塔顶端捕食者的存在……原来,也会被这样对待。
原来,她也会哭,会求饶,会被撕碎,会被当成一个连人都算不上的、纯粹的泄欲工具。
原来,她不是神。
她也是……玩物。
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从我那早已麻木的心脏深处,猛地喷涌而出。那不是嫉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滔天怒火、极致心疼和彻底无能为力的、尖锐的刺痛。
就在我的身体因为那句冰冷的命令而本能地想要向前挪动时,一个带着一丝慵懒笑意的声音,从房间的角落里响了起来。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男性。
他并没有参与刚才那场狂欢,而是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自始至终都靠在吧台边,安静地抽着雪茄。此刻,他缓缓地走了过来,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移动的铁塔,投下的阴影将我和床上那个破败的她,完全笼罩。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洞悉一切的、属于更高层级玩家的戏谑,“她对你,不一样。”
“你以为你为什么还活着?”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你本来早该像一条不听话的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了。是她,主动向‘主人们’请求,把你变成了她的专属玩物,用这种方式,才让你这条小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她以为她掩饰得很好。”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她以为,把你变成一个听话的、离不开她的玩物,就能把那份不该有的感情,藏在调教和支配的游戏之下。可惜,她高估了自己作为‘资产’的权限。‘主人们’……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所有物,产生了不该有的、独立的思想和感情。”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份混杂着愤怒与心疼的情感,捅得千疮百孔。
原来……她对我好,是真的。
而这份真实,却成了将她推入更深地狱的、最根本的罪。
“不过,”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个堪称仁慈的、魔鬼般的微笑,“‘主人们’也并非不通情理。我们很乐意成人之美。”
他一边说,一边从吧台上端过来一个银制的托盘,轻轻地放在了我面前的地毯上。
托盘上,没有美酒,也没有佳肴。
只有密密麻麻的、足足有四五十粒的纯白色药片。它们像一盘洁白的、致命的棋子,在奢华的灯光下,反射着冰冷而圣洁的光芒。
“这是‘极乐’。”他用一种冰冷的、仿佛在陈述商品使用说明的语气介绍道,“专门为不听话的‘资产’准备的。能彻底清除掉她们脑子里那些多余的、不该有的思想,让她们变成只会淫荡地张开腿、主动索取性交的、完美的泄欲工具。”
他顿了顿,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眼神,看了一眼床上那个依旧毫无声息的她。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会把脑子彻底烧坏。你知道的,精密仪器,总是很脆弱。”
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彻底冻结了。
“今晚,她需要服下这里所有的药。”黑人男性指了指托盘,然后又伸出手指,指向房间里那十几个刚刚享用完她、此刻正像一群看戏的狼一样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同样身形高大的黑人男性,“当然,‘主人们’给了你一个拯救她的机会。”
“看到他们了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恶魔的耳语,“你去,用你的嘴,你的身体,你的全部,去取悦他们。你只要能让这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射精一次,我就从托盘里,为她拿走一粒药。”
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脸上的笑容更加残忍了。
“别高兴得太早。”他蹲下身,捡起一粒药,在我眼前晃了晃,“这东西的药效很强。一粒,就足以让她神智不清,彻底沦为只会求欢的母狗。两粒,她的大脑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变成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白痴。三粒……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有价值的资产身上,试过三粒以上的剂量。”
我呆呆地看着他,看着那一盘致命的药,看着那十几座由黑色肌肉和欲望组成的、无法逾越的山脉,又回头看了一眼床上那个破败不堪的女人。
这一刻我才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慈悲的“机会”。
这是这世上,最恶毒的诅咒。
它将那份卑微的、见不得光的爱意,血淋淋地剖开,放在了审判的天平上。而天平的另一端,是她的神智,她的未来,甚至她的生命。
我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的尊严,我的身体,我的一切。
这不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而是通往地狱更深处的、唯一的路径。
黑人男性站起身,退回阴影之中,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宣布了这场终极审判的开始。
“开始吧。”
腰肌劳损:↑你是魔鬼吧(bushi)BetaDenier:↑【8】对了,突然有一个新奇的想法,在最后这个药物这里除了服侍一次拿出来一颗之外,也可以让主角射一次往里放一颗🤓
那一天之后,林知夏对我,好得匪夷所思。
她不再仅仅局限于学业上的指导。她会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在某个阳光正好的下午,突然拉着我逃离实验室,带我去城市另一端那家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的、昂贵的私房菜馆;她会带我出入那些我只在财经杂志上见过的、顶级会员制的奢侈品商场,面无表情地为我换上阔挺的西装;她会当着实验室所有人的面送给我最新款的手机和一直都想要却舍不得买的配置顶级的笔记本电脑,只因为她觉得“你的旧的太卡了,影响效率”。
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将我拉进了她的世界——一个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我过去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世界。我见识到了她那深不见底的财力,每一次随意的消费,都足以抵上我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薪水。
在这种极致的物质和情感包裹下,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恋爱的错觉。当她耐心地帮我整理被风吹乱的衣领,当她在高级餐厅里自然地将她盘子里最鲜美的那块和牛夹给我时,我几乎就要相信,我们就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如果不是我时刻能感受到身前那个冰冷的贞操锁,以及身后那个早已被我的体温捂热、却依旧坚硬无比的金属肛塞的话。
它们像两个最忠诚的、最残忍的守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如今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怎样一种屈辱的关系之上。
而最让我清醒的,是有时我们并肩坐在某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她会拿出手机,处理一些“工作”。
她不会避讳我,而是会像分享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一样,戴上一只白色的无线耳机,将另一只,塞进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便能清晰地、身临其境地,听到那个加密通讯软件里,传来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那通常是一段充满了静电杂音的、带着卑微喘息的语音。另一头的男人,大概是按下了通话键后,就再也不敢松手。
然后,我会听到林知夏的声音,通过她那小巧的、隐藏在发丝间的麦克风,冰冷地、清晰地,传递到那个卑微的世界里。
“劣等品β-2302号,”她会一边用小勺优雅地搅动着自己面前那杯拿铁,一边用一种近乎无情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说道,
“你真锁了一个月啊,就为了买我一双袜子”
对面传来一阵压抑的、急切的、仿佛在点头般的喘息声。
“行吧,”林知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施舍般的、居高临下的慵懒,“给你10秒钟时间。”
我能清晰地听到,耳机的那一头,瞬间响起了一阵疯狂的、湿滑的、肉体摩擦的声音。紧接着,是那个男人带着哭腔的、绝望的哀求:“不……主人……求求您……10秒钟……不可能这么快就……”
林知夏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她只是看着咖啡杯上漂亮的拉花,用一种平稳的、仿佛在欣赏一首乐曲的节奏,开始了冰冷的倒数。
“九……八……七……”
那头的摩擦声,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绝望,甚至带上了一丝自残般的绝望意味。
“……三……二……一。”
林知夏的声音,像死神的镰刀,精准地、毫不留情地,落下了。
“松手吧。”
耳机那头,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一般的、充满了绝望和不甘的寂静。过了很久,才传来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仿佛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野兽般的呜咽。
林知夏端起咖啡,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对着麦克风,说出了那句最终的、决定他未来一个月命运的审判。
“看来还是锁得太少了。”
说完,她便挂断了通讯,取下了耳机,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消遣。
她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问我,要不要再加一块芝士蛋糕。
那一刻,我所有的温情幻想,都会被瞬间击得粉碎。我不是特殊的,我只是她的一个“玩具”,或许,是目前最令她满意的一个。
而白天有多“温存”,夜晚就有多“残忍”。
我在会所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我不再需要去端盘子,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像一个等待被传唤的奴隶,等候她的指令。
那通常是在她和某个,或者某几个高大强壮的黑人男性结束狂欢之后。
我会接到指令,独自一人来到那个我曾无比恐惧的、顶层的私人套房。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混杂着雪茄、酒精和激烈性爱后的麝香味。床上凌乱不堪,空气中还残留着属于男人的、陌生的气息。
而林知夏,早已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面孔。她会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赤着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脸上没有了白天的温柔,只有一种暴风雨过后的、带着一丝疲惫和暴戾的冰冷。
她什么都不会说,只是会从床边的暗格里,拿出一条黑色的、尺寸惊人的穿戴式假阳具,熟练地绑在自己纤细的腰间。
然后,她会走到我面前,用那根巨大的、冰冷的、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假阳具,狠狠地、毫不留情地,贯穿我那早已被扩张到极限的后穴。
那不是做爱,那甚至不是调教。
那是一种纯粹的发泄。
她会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在我体内疯狂地抽插。她会把白天积攒的、那些无处释放的压力、疲惫和愤怒,通过这根假阳具,一下又一下地,尽数发泄在我的身体里。
在那些混杂着剧痛与极致快感的、漫长的发泄过程中,林知夏有时会突然停下那毁灭般的冲撞,转而用一种更残忍的、精神上的方式来凌虐我。她会贴在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将那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淫靡的画面,一字一句地,灌进我的脑海里。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她会一边用那根巨大的、还埋在我体内的假阳具,不轻不重地研磨着我早已溃不成军的前列腺,一边用一种冰冷而又带着一丝炫耀的语气,向我描述她白天的“盛况”。
“他很强壮,比你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都要强壮。他的阳具……像一根烧红的铁棍,几乎要把我捅穿。”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回味般的、满足的颤音,“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两个不听话的玩具叫了进来,让他们跪在床边,看着我是怎么被干的。”
“我让他们比,看谁的几把更小,更可怜。其中有一个,连勃起都不到十厘米。我让那个黑人,用他那根比他大腿还粗的鸡巴,狠狠地抽他的脸,你猜怎么着?”
她在我耳边发出了一声恶意的轻笑。
“他居然被抽射了。精液射在了我的脚背上,又脏又黏,像一滩鼻涕。我罚他把我和那个黑人干完后流出来的、混合在一起的淫水,全都舔干净。”
她会细致入微地向我描述,在她和那个黑人男性赤身裸体地纠缠、被巨大的阳具肏得浑身颤抖、浪叫连连的时候,身下是如何跪着那几个被她称之为“劣等品”的男人。
他们会像最卑微的狗一样,匍匐在床边,不敢抬头看她被侵犯的脸,只敢用舌头狂热地舔舐她因为高潮而蜷缩的脚趾,亲吻她因为痉挛而微微颤抖的小腿。他们甚至会为了争抢一滴从她体内溢出的、属于那个黑人男性的精液而互相撕咬,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甘美的琼浆。
“他们每一个,都比你更懂得怎么服侍。”她会一边在我体内冲撞,一边用气声这样说道。
这本该是极致的羞辱。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内心,却因为这些露骨的、充满了尺寸对比和权力践踏的描述,产生了一丝病态的、不甘的嫉妒。
我嫉妒那些“劣等品”。
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渴望能亲眼见证她的“盛况”。我渴望能像他们一样,跪在她的脚边,用最卑微的姿态,去仰望她被更强者征服时的、那种混杂着痛苦与极乐的、最真实的表情。
我渴望,能成为她那场盛大而淫靡的权力游戏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却能亲眼见证一切的观众。
而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在一切结束之后,成为她在黑夜里,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承受她所有负面情绪的、孤独的、有生命的玩具。
在一次例行的、粗暴的发泄结束后,我瘫软在地毯上,后穴火辣辣地疼,身体因为刚刚经历过的强制高潮而微微抽搐。林知夏拔出那根巨大的假阳具,随意地丢在一旁,她赤裸的身体覆着一层薄汗,胸口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跨坐在我的身上,用一种慵懒而又危险的语气,开始描述刚才那场她与黑人男性的狂欢。
“你知道吗,”她低下头,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上,“今天那个新来的劣等品很有趣,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只敢趴在地上,像条真正的狗一样,在我被操的时候,用舌头把我的脚底舔得干干净净。”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每一个字都像钩子,勾起我内心最深处的、卑劣的嫉妒和渴望。
“……我也想……”我几乎是无意识地,从喉咙里挤出了这句话,“我也想在那个时候……服侍您。”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在她被另一个男人占有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像条忠犬一样守在她的脚边,舔舐她,亲吻她,成为她在那场游戏中,唯一能完全掌控的、卑微的私有物。
我的话,却让她原本慵懒的神情瞬间凝固了。
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冰冷。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我身上站了起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那种场合不适合你。”她淡淡地丢下这句话,开始自顾自地穿上衣服。
“为什么?”我不死心地追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在穿好衣服后,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像是不忍,又像是警告。
“你只要在这里等我就够了。”
她顾左右而言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那一刻我隐约感觉到,她不希望我看到她被另一个男人玩弄的样子,更不希望我被那个世界的、真正的黑暗所吞噬。我只是她一个人的玩具,她不想让我被别人染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极致的割裂和刺激下,我的整个人,都在发生着微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实验室里,当她不经意间对我微笑时,我会下意识地低下头,脸颊发烫,像一个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我的言行举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柔和。
我的气质开始变得柔和,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态,甚至连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女性化的痕迹。尤其是在被她用假阳具操到高潮的时候,我发出的不再是压抑的闷哼,而是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甜腻的呻吟。
林知夏似乎对我的这种变化非常满意。
她开始偶尔让我穿上女装,陪她一起出门。我们会像一对亲密的闺蜜一样,在街角的咖啡厅里分享同一块提拉米苏,在奢侈品店的镜子前一起比划着最新款的包包。她会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说些无伤大雅的私房话,引得周围的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但只要一走到无人的角落,她就会立刻变回那个掌控一切的女王。她会把我按在墙上,掀起我的裙子,用手指粗暴地玩弄我身后那个早已被撑得松软的后穴,感受着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无法自控地颤抖。
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我越发沉迷,无法自拔。我一边感激她对我的“好”,感激她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光鲜亮丽的世界;一边又在这种不见天日的、扭曲的关系中,被巨大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反复撕扯。
。。。。。。
为了庆祝一个项目的阶段性成功,林知夏组织了一次野餐,同行的还有实验室里另外两位师兄。
那天的阳光好得有些不真实。
学姐穿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裙摆随微风轻轻摇曳,像一朵不胜凉风的水莲花。她的脚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白色棉袜,紧紧包裹着她脚踝线条优美的轮廓,脚下则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小皮鞋。那装扮,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学生,与这个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
公园的小路上,她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甚至将半个身子的重量,都亲昵地、毫无防备地靠在了我的身上。她的发梢随着走路的动作,不时地扫过我的脸颊,带来一阵阵好闻的、洗发水的香气。
这幅画面,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正在热恋中的璧人。路过的行人,总会向我们投来善意的、祝福的目光,有些年轻的女孩,甚至会因为看到我们之间那种亲密的、不加掩饰的爱意,而露出羡慕的微笑。
我们一同走到了草坪上。她脱下小皮鞋,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野餐垫外侧,露出那双仍被白棉袜包裹的脚。
她踩在柔软的垫子上,轻轻地动了动脚趾,像是在享受阳光下的微风与青草的温度。
我注意到,公园里偶尔路过的男人,总会不由自主地朝她脚边瞥上一眼。
他们的目光先扫过我们,最终却黏在她的白袜脚上,或那双刚脱下、还带着余温的小皮鞋里;有人喉结轻轻滚了一下,呼吸短短顿住,再装作若无其事地错开。
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压抑着的、属于成年男性的、混杂着欲望的幻想。
他们大概永远也无法想象,此时学姐脚上那双纯洁的白袜,和草坪上那双人畜无害的小皮鞋,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被允许跪下来,贴近了看——
会发现,那双白色棉袜的袜尖,因为长时间被汗水反复浸润,早已泛起了淡淡的黄痕。
棉布表面原本柔软细腻的纤维,此刻却有些粗糙、微硬,像是曾被什么高温又腥臭的液体喷溅过、风干后留下的结痂印迹。
阳光斜照下,更能隐约辨出几道极浅的、不自然的脊状硬痕——仿佛是某次压抑着的射精,被迫喷洒在袜尖时遗留的痕迹。
而那双黑色小皮鞋,鞋口微张,内壁早已失去了新皮革的质感,鞋垫已经踩出了完整的脚型凹痕。
鼻子凑近那张着口的皮鞋时,扑面而来的并不是想象中少女的体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由旧皮革与脚汗混合发酵后的酸腐气息。
更致命的是,那气味之下,竟还有一丝隐约的腥咸,是雄性精液的味道,与其混杂的,还有淡淡的唾液气息——是被另一条舌头一遍遍舔舐之后留下的腥气。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双鞋袜,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代表着怎样一场残酷而又淫靡的游戏。
那个夜晚,两位师兄像狗一样跪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刚刚解锁的下体因为长达一个月的贞操锁折磨,已经淫乱不堪,不住的流出前列腺液
而在他们面前,摆放着的,就是学姐今天脚上这双刚刚脱下来的黑色小皮鞋。
而学姐今天脚上这双纯洁的白色棉袜,正被两位师兄用手攥着,紧紧贴在鼻子上。
规则很简单——谁先射精,谁就是胜利者。
失败者,则必须在胜者高潮的瞬间,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动作,将那已经滚烫堆积到极限的欲望,硬生生地压制回体内,继续承受贞操锁中无止尽的折磨——直到下一场比赛。
于是,欲望便成了一场残酷的竞争。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场景——
他们像两只发情到极限、丧失理智的野兽,跪趴在地,屁股高高撅起,双膝贴地,脊背拱得僵硬,像等待发情指令的畜生。脸则深深埋进那只还残留着学姐体温的白色棉袜中,鼻尖死死抵住袜尖那一小片发黄的位置。
那一片被脚汗反复浸透、早已泛黄发硬的区域,是整只袜子气味最浓烈、最刺激的源头,混合了汗液长时间浸润后散发出的脚酸味,还有一丝令人作呕却令人兴奋的腥咸……仿佛是曾被某人猛烈射精后喷溅上的残渍,早已风干,留下一圈淡淡却不自然的脊状痕迹。
其中一人甚至,抖着伸出舌头,将舌尖贴上那片疑似精斑的袜面。
那不是发泄——那是一场关乎尊严与屈服的生死竞速。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疯狂地崇拜那片被污染的袜面,是因为他们隐约知道,那处污痕的真正来源。
那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释放,而是来自另外两个男生的发泄——年龄更小,年级更低,甚至大概率只是刚被她选中的“新玩物”。
更年轻的肉体,自然也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直接套着那双白棉袜撸动,在袜面上尽情摩擦,享受汗湿纤维与敏感龟头交缠时的粗糙快感。
但那种特权,并不代表自由。
而对于那种尚未驯服、总想要更多的下体,最合适的调教方式,就是反复的寸止。不断摩擦,不断停下,不准射、不准停,直到理智被彻底磨光。
那双小皮鞋的用途,他们也心知肚明:八成是反扣在脸上的,鞋口紧紧扣住口鼻,不准滑落,不准移开。
唯一被允许的慰藉,就是那口口鼻间反复吸入的脚味,是她踩了一整天的鞋垫热气,是袜尖残留的汗渍甜腥,是那种让人越吸越渴、越渴越痛苦的气息。
这就是套着棉袜撸动的代价。
似乎是和我一样想到了这里,两位师兄的双眼早已泛红,混杂着渴望、羞耻、绝望和嫉妒。
十几秒钟后,在一声几乎是嘶哑的低吼中——
其中一个师兄的身体剧烈抽搐起来,像被从内而外点燃。
他的下体颤抖着,精液如决堤的洪水般,从被解锁不过几分钟的性器中喷涌而出——毫无保留地,尽数射进那只黑色小皮鞋内部。
他的手甚至在射完后仍死死抓着鞋跟,仿佛那里是他唯一的出口。
而另一个师兄,却在那一刻被学姐一脚毫不留情地踹翻。
他正攀上高潮边缘,身体已经抖得像筛子,精液几乎要从马眼里冲出,却在这一脚中戛然而止。
而那只沾满精液的小皮鞋,则安静地躺在一旁,成为这场残酷竞争的唯一胜者的奖杯。
此刻,看着那双被摆在阳光下的、干净的小皮鞋,我的后背不禁一阵发凉。
这份干净,是因为在那个夜晚,那个输掉了比赛的师兄,像一条真正的狗一样,用他的舌头,将胜利者射在里面的、那滩黏稠腥臊的液体,一滴不剩地,全部舔舐干净。
在铺着格子布的草地上,林知夏表现得对我格外亲昵,那种亲昵,甚至超越了普通情侣的界限。她会把剥好的、最甜的那瓣橘子,亲手喂到我的嘴边;会在我嘴角沾上一点酱汁时,拿出纸巾,用一种无比自然的、带着宠溺的姿态,轻轻为我擦拭干净。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让我几乎要融化。而那两位师兄的眼神,则像淬了毒的冰锥,死死地钉在我的身上。
中途,我去取水,其中一位师兄跟了过来。在远离人群的树荫下,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嫉妒和鄙夷。
“你别得意忘形了。”他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的怨毒,“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林知夏是什么人,她会看得上你这种穷酸样?”
我愣住了。
他看到我茫然的表情,脸上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冷笑:“别傻了。我们都一样,都是她的‘玩物’。唯一的区别是,你是她现在最上心、最新鲜的玩具,她愿意在你身上花更多的心思罢了。”
“玩物……我们?”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我如遭雷击,浑身僵硬。
他的目光,不加掩饰地扫过我的下体,和我的臀部。那眼神,仿佛能穿透我那层薄薄的裤子,清晰地看到我身上前锁后塞的羞耻模样。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他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玩具,总有玩腻的一天。到时候,你的下场,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越过他的肩膀,看向远处那个正陪着学姐说笑的、另一个师兄。他笑得那么阳光,但我此刻却仿佛能看到他笑容背后,那和我如出一辙的、深深烙印在骨子里的恐惧和臣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重新坐回林知夏身边时,她依旧对我笑得温柔,又递给我一块切好的西瓜。
我僵硬地接过,低下头,拼命地将所有的屈辱和自卑,连同那口甜得发腻的西瓜,一起吞进肚子里,藏在心里最阴暗的角落。
。。。。。。
日子在白天和黑夜的撕裂中,麻木地向前滚动。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会所的、一条不同寻常的指令。
我没有被要求去那个我熟悉的、作为“发泄玩具”的套房。而是被一个沉默的保安,带领着穿过了几条我从未走过的、阴暗潮湿的“员工通道”。最后,他让我在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狭窄的杂物间里等待。这间房,与隔壁的顶级套房,只有一墙之隔,墙壁上甚至还有一个被窗帘遮住的、用于观察的单向玻璃暗门。
我被告知,在接到传唤之前,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离开。
我像一尊石像,僵硬地站在这个狭小的、充满灰尘气息的杂物间里。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差,隔壁房间的声音,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一根接一根地,狠狠扎进我的耳朵,刺穿我的大脑。
很快,隔壁的房间就传来了声音。
一开始,是几个男人用英语和一种我听不懂的、带着浓重口音的语言在交谈。他们的笑声洪亮而刺耳,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和不加掩饰的粗野。我听见沉重的酒杯碰撞的声音,以及雪茄被剪断的、清脆的“咔嚓”声。那是一个属于上位者的、轻松而惬意的开场。
然后,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响起了。
那不是我熟悉的、属于女王的、冰冷的命令。而是一种混杂着痛苦、欢愉和屈辱的、破碎的呻吟。
那呻吟的声音,像一个开关,瞬间开启了地狱的大门。
男人们爆发出一阵更加肆无忌惮的哄笑。我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用最污秽的词语,命令她像狗一样爬过去。紧接着,是布料被粗暴撕碎的声音,和她一声短促的、压抑着痛苦的惊呼。
然后,一切都失控了。
我听见肉体被皮带或是什么东西反复抽打的、沉闷的“啪啪”声,每一声都伴随着她再也无法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呻吟。男人们在用不同的语言,兴奋地数着数,像是在进行一场狩猎游戏。
我听见她被不同的男人用最粗言秽语的方式羞辱、命令她用嘴去取悦他们。我能听到黏腻的水声,和她因为被掐住脖子而发出的、近乎窒息的、断断续续的呜咽。
但最让我崩溃的,是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似乎厌倦了这种单向的施虐。他用一种戏谑的、残忍的语气下达了一道新的命令。紧接着,我听到了好几个沉重的脚步声在向她靠近。
我第一次,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崩溃。那不再是游戏,而是契约被撕毁后,面对彻底失控的、纯粹的暴力时,最本能的、最绝望的哀求。
但那哀求,只换来了男人们更加兴奋的、魔鬼般的狂笑。
接下来,我听到了此生都无法忘记的声音。那是她被好几个男人同时按住手脚时发出的、徒劳的挣扎声。是她被那些黑人男性用他们巨大的、滚烫的阳具,轮流地、甚至同时地,狠狠贯穿她前后两个穴洞时,发出的凄厉到变了调的惨叫。
那惨叫声,很快就因为不堪的凌辱和痛苦,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混杂着哭泣和求饶的破碎呻吟。我能清晰地听到不同男人的、粗重的喘息声,和肉体毫无廉耻地、野蛮撞击的黏腻水声,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曲最残忍、最淫靡的地狱交响。
我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被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被迫听着我的“主人”,被一群我看不见的、更加恐怖的存在,当做一个公共玩物,肆意玩弄、轮番享用。时间仿佛被拉长到了无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灵魂最残忍的凌迟。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残暴的狂欢,似乎终于落下了帷幕。隔壁的声音渐渐平息,只剩下男人们心满意足的交谈声。
又过了一会儿,我所在的杂物间的门,被“咔哒”一声打开了。
一个我不认识的、同样身形魁梧的黑人男性,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他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用下巴朝里面点了点,眼神就像在示意一条狗去清理主人呕吐出的秽物。
我双腿发软地,一步一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地狱,原来是有气味的。
一股浓稠到几乎凝为实质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瞬间扼住了我的喉咙。那是一种由汗水、精液、雪茄、被打翻的昂贵威士忌、以及一丝微不可查的血腥味混合而成的、属于末日狂欢的腥臊气息。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上,沾染着大片大片的、深色的酒渍和可疑的、白色的粘稠液体,仿佛一幅被肆意凌虐过的抽象画。
而我的学姐,林知夏,那个在我心中永远高高在上、冰冷圣洁的女王……就趴在这幅地狱绘图的最中央。
她像一个被玩坏后随意丢弃的、关节扭曲的陶瓷娃娃,趴在巨大而凌乱的床上。那张曾经承载着无数奢靡与罪恶的大床,此刻看上去更像一个祭坛,而她,就是那场献祭仪式结束后,被遗忘的祭品。
她的神智已经完全抽离,那双曾洞悉一切、让我不敢直视的漂亮眼睛,此刻空洞地睁着,却没有任何焦距。瞳孔散漫,倒映不出天花板上那盏奢华水晶灯的任何光芒。一道干涸的泪痕,从她的眼角蜿-蜒而下,划过她脸颊上那片早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精液的、肮脏的粘腻。
她的嘴唇红肿破裂,嘴角甚至有一丝细微的、已经凝固的血迹。她的头发,那头总是打理得一丝不苟的秀发,此刻像一团枯萎的海草,混杂着各种可疑的液体,狼狈地黏在她的脸上和脖颈上。
她的身体,那具我曾无比渴望、也无比恐惧的、如同艺术品般的身体,此刻成了一块被肆意涂抹的画布。白皙的皮肤上,青紫色的手印、牙印、以及皮带抽打后留下的一道道狰狞的红痕,交错纵横。而覆盖在这些暴力痕迹之上的,是属于不同男人的、已经开始变得半透明或依旧乳白粘稠的精液。它们从她的后背,流到她的大腿,甚至滴落在丝质的床单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屈辱的岛屿。
她无力地趴着,上身几乎贴在床上,而臀部却依旧被维持在一个方便被从后面进入的、高高撅起的姿势。她那被过度使用的、红肿不堪的小穴和后穴,就那样毫无遮拦地、甚至无法完全闭合地暴露在空气中。穴口微微外翻,像两张被蹂躏到麻木的、哭泣的嘴,还在不受控制地向外淌着浑浊的、混合了淫水和精液的液体,将身下的床单浸染出一片深色的、潮湿的地图。
我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我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一切认知,在这一瞬间,被眼前这幅惨烈到极致的、淫靡到极致的画面,冲击得支离破碎。
那个用脚尖就能让我高潮的女王,那个用一道命令就能决定我所有悲喜的主人,那个我以为是金字塔顶端捕食者的存在……原来,也会被这样对待。
原来,她也会哭,会求饶,会被撕碎,会被当成一个连人都算不上的、纯粹的泄欲工具。
原来,她不是神。
她也是……玩物。
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从我那早已麻木的心脏深处,猛地喷涌而出。那不是嫉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滔天怒火、极致心疼和彻底无能为力的、尖锐的刺痛。
就在我的身体因为那句冰冷的命令而本能地想要向前挪动时,一个带着一丝慵懒笑意的声音,从房间的角落里响了起来。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男性。
他并没有参与刚才那场狂欢,而是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自始至终都靠在吧台边,安静地抽着雪茄。此刻,他缓缓地走了过来,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移动的铁塔,投下的阴影将我和床上那个破败的她,完全笼罩。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洞悉一切的、属于更高层级玩家的戏谑,“她对你,不一样。”
“你以为你为什么还活着?”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你本来早该像一条不听话的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了。是她,主动向‘主人们’请求,把你变成了她的专属玩物,用这种方式,才让你这条小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她以为她掩饰得很好。”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她以为,把你变成一个听话的、离不开她的玩物,就能把那份不该有的感情,藏在调教和支配的游戏之下。可惜,她高估了自己作为‘资产’的权限。‘主人们’……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所有物,产生了不该有的、独立的思想和感情。”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份混杂着愤怒与心疼的情感,捅得千疮百孔。
原来……她对我好,是真的。
而这份真实,却成了将她推入更深地狱的、最根本的罪。
“不过,”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个堪称仁慈的、魔鬼般的微笑,“‘主人们’也并非不通情理。我们很乐意成人之美。”
他一边说,一边从吧台上端过来一个银制的托盘,轻轻地放在了我面前的地毯上。
托盘上,没有美酒,也没有佳肴。
只有密密麻麻的、足足有四五十粒的纯白色药片。它们像一盘洁白的、致命的棋子,在奢华的灯光下,反射着冰冷而圣洁的光芒。
“这是‘极乐’。”他用一种冰冷的、仿佛在陈述商品使用说明的语气介绍道,“专门为不听话的‘资产’准备的。能彻底清除掉她们脑子里那些多余的、不该有的思想,让她们变成只会淫荡地张开腿、主动索取性交的、完美的泄欲工具。”
他顿了顿,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眼神,看了一眼床上那个依旧毫无声息的她。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会把脑子彻底烧坏。你知道的,精密仪器,总是很脆弱。”
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彻底冻结了。
“今晚,她需要服下这里所有的药。”黑人男性指了指托盘,然后又伸出手指,指向房间里那十几个刚刚享用完她、此刻正像一群看戏的狼一样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同样身形高大的黑人男性,“当然,‘主人们’给了你一个拯救她的机会。”
“看到他们了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恶魔的耳语,“你去,用你的嘴,你的身体,你的全部,去取悦他们。你只要能让这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射精一次,我就从托盘里,为她拿走一粒药。”
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脸上的笑容更加残忍了。
“别高兴得太早。”他蹲下身,捡起一粒药,在我眼前晃了晃,“这东西的药效很强。一粒,就足以让她神智不清,彻底沦为只会求欢的母狗。两粒,她的大脑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变成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白痴。三粒……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有价值的资产身上,试过三粒以上的剂量。”
我呆呆地看着他,看着那一盘致命的药,看着那十几座由黑色肌肉和欲望组成的、无法逾越的山脉,又回头看了一眼床上那个破败不堪的女人。
这一刻我才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慈悲的“机会”。
这是这世上,最恶毒的诅咒。
它将那份卑微的、见不得光的爱意,血淋淋地剖开,放在了审判的天平上。而天平的另一端,是她的神智,她的未来,甚至她的生命。
我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的尊严,我的身体,我的一切。
这不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而是通往地狱更深处的、唯一的路径。
黑人男性站起身,退回阴影之中,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宣布了这场终极审判的开始。
“开始吧。”
虽然但是确实很色,不过这篇主要是雌堕为主
BetaDenier:↑只是一个提议,不适合这里也无所谓,只是这样从剧情来讲其实很容易击溃主角的心理防线(例如最后所有的药都没了,主角终于要结束昏过去的时候,突然再射了……),我个人感觉这要很主角很容易就……🤤咳咳腰肌劳损:↑你是魔鬼吧(bushi)BetaDenier:↑【8】对了,突然有一个新奇的想法,在最后这个药物这里除了服侍一次拿出来一颗之外,也可以让主角射一次往里放一颗🤓
那一天之后,林知夏对我,好得匪夷所思。
她不再仅仅局限于学业上的指导。她会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在某个阳光正好的下午,突然拉着我逃离实验室,带我去城市另一端那家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的、昂贵的私房菜馆;她会带我出入那些我只在财经杂志上见过的、顶级会员制的奢侈品商场,面无表情地为我换上阔挺的西装;她会当着实验室所有人的面送给我最新款的手机和一直都想要却舍不得买的配置顶级的笔记本电脑,只因为她觉得“你的旧的太卡了,影响效率”。
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将我拉进了她的世界——一个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我过去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世界。我见识到了她那深不见底的财力,每一次随意的消费,都足以抵上我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薪水。
在这种极致的物质和情感包裹下,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恋爱的错觉。当她耐心地帮我整理被风吹乱的衣领,当她在高级餐厅里自然地将她盘子里最鲜美的那块和牛夹给我时,我几乎就要相信,我们就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如果不是我时刻能感受到身前那个冰冷的贞操锁,以及身后那个早已被我的体温捂热、却依旧坚硬无比的金属肛塞的话。
它们像两个最忠诚的、最残忍的守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如今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怎样一种屈辱的关系之上。
而最让我清醒的,是有时我们并肩坐在某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她会拿出手机,处理一些“工作”。
她不会避讳我,而是会像分享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一样,戴上一只白色的无线耳机,将另一只,塞进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便能清晰地、身临其境地,听到那个加密通讯软件里,传来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那通常是一段充满了静电杂音的、带着卑微喘息的语音。另一头的男人,大概是按下了通话键后,就再也不敢松手。
然后,我会听到林知夏的声音,通过她那小巧的、隐藏在发丝间的麦克风,冰冷地、清晰地,传递到那个卑微的世界里。
“劣等品β-2302号,”她会一边用小勺优雅地搅动着自己面前那杯拿铁,一边用一种近乎无情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说道,
“你真锁了一个月啊,就为了买我一双袜子”
对面传来一阵压抑的、急切的、仿佛在点头般的喘息声。
“行吧,”林知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施舍般的、居高临下的慵懒,“给你10秒钟时间。”
我能清晰地听到,耳机的那一头,瞬间响起了一阵疯狂的、湿滑的、肉体摩擦的声音。紧接着,是那个男人带着哭腔的、绝望的哀求:“不……主人……求求您……10秒钟……不可能这么快就……”
林知夏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她只是看着咖啡杯上漂亮的拉花,用一种平稳的、仿佛在欣赏一首乐曲的节奏,开始了冰冷的倒数。
“九……八……七……”
那头的摩擦声,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绝望,甚至带上了一丝自残般的绝望意味。
“……三……二……一。”
林知夏的声音,像死神的镰刀,精准地、毫不留情地,落下了。
“松手吧。”
耳机那头,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一般的、充满了绝望和不甘的寂静。过了很久,才传来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仿佛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野兽般的呜咽。
林知夏端起咖啡,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对着麦克风,说出了那句最终的、决定他未来一个月命运的审判。
“看来还是锁得太少了。”
说完,她便挂断了通讯,取下了耳机,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消遣。
她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问我,要不要再加一块芝士蛋糕。
那一刻,我所有的温情幻想,都会被瞬间击得粉碎。我不是特殊的,我只是她的一个“玩具”,或许,是目前最令她满意的一个。
而白天有多“温存”,夜晚就有多“残忍”。
我在会所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我不再需要去端盘子,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像一个等待被传唤的奴隶,等候她的指令。
那通常是在她和某个,或者某几个高大强壮的黑人男性结束狂欢之后。
我会接到指令,独自一人来到那个我曾无比恐惧的、顶层的私人套房。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混杂着雪茄、酒精和激烈性爱后的麝香味。床上凌乱不堪,空气中还残留着属于男人的、陌生的气息。
而林知夏,早已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面孔。她会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赤着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脸上没有了白天的温柔,只有一种暴风雨过后的、带着一丝疲惫和暴戾的冰冷。
她什么都不会说,只是会从床边的暗格里,拿出一条黑色的、尺寸惊人的穿戴式假阳具,熟练地绑在自己纤细的腰间。
然后,她会走到我面前,用那根巨大的、冰冷的、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假阳具,狠狠地、毫不留情地,贯穿我那早已被扩张到极限的后穴。
那不是做爱,那甚至不是调教。
那是一种纯粹的发泄。
她会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在我体内疯狂地抽插。她会把白天积攒的、那些无处释放的压力、疲惫和愤怒,通过这根假阳具,一下又一下地,尽数发泄在我的身体里。
在那些混杂着剧痛与极致快感的、漫长的发泄过程中,林知夏有时会突然停下那毁灭般的冲撞,转而用一种更残忍的、精神上的方式来凌虐我。她会贴在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将那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淫靡的画面,一字一句地,灌进我的脑海里。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她会一边用那根巨大的、还埋在我体内的假阳具,不轻不重地研磨着我早已溃不成军的前列腺,一边用一种冰冷而又带着一丝炫耀的语气,向我描述她白天的“盛况”。
“他很强壮,比你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都要强壮。他的阳具……像一根烧红的铁棍,几乎要把我捅穿。”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回味般的、满足的颤音,“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两个不听话的玩具叫了进来,让他们跪在床边,看着我是怎么被干的。”
“我让他们比,看谁的几把更小,更可怜。其中有一个,连勃起都不到十厘米。我让那个黑人,用他那根比他大腿还粗的鸡巴,狠狠地抽他的脸,你猜怎么着?”
她在我耳边发出了一声恶意的轻笑。
“他居然被抽射了。精液射在了我的脚背上,又脏又黏,像一滩鼻涕。我罚他把我和那个黑人干完后流出来的、混合在一起的淫水,全都舔干净。”
她会细致入微地向我描述,在她和那个黑人男性赤身裸体地纠缠、被巨大的阳具肏得浑身颤抖、浪叫连连的时候,身下是如何跪着那几个被她称之为“劣等品”的男人。
他们会像最卑微的狗一样,匍匐在床边,不敢抬头看她被侵犯的脸,只敢用舌头狂热地舔舐她因为高潮而蜷缩的脚趾,亲吻她因为痉挛而微微颤抖的小腿。他们甚至会为了争抢一滴从她体内溢出的、属于那个黑人男性的精液而互相撕咬,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甘美的琼浆。
“他们每一个,都比你更懂得怎么服侍。”她会一边在我体内冲撞,一边用气声这样说道。
这本该是极致的羞辱。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内心,却因为这些露骨的、充满了尺寸对比和权力践踏的描述,产生了一丝病态的、不甘的嫉妒。
我嫉妒那些“劣等品”。
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渴望能亲眼见证她的“盛况”。我渴望能像他们一样,跪在她的脚边,用最卑微的姿态,去仰望她被更强者征服时的、那种混杂着痛苦与极乐的、最真实的表情。
我渴望,能成为她那场盛大而淫靡的权力游戏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却能亲眼见证一切的观众。
而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在一切结束之后,成为她在黑夜里,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承受她所有负面情绪的、孤独的、有生命的玩具。
在一次例行的、粗暴的发泄结束后,我瘫软在地毯上,后穴火辣辣地疼,身体因为刚刚经历过的强制高潮而微微抽搐。林知夏拔出那根巨大的假阳具,随意地丢在一旁,她赤裸的身体覆着一层薄汗,胸口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跨坐在我的身上,用一种慵懒而又危险的语气,开始描述刚才那场她与黑人男性的狂欢。
“你知道吗,”她低下头,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上,“今天那个新来的劣等品很有趣,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只敢趴在地上,像条真正的狗一样,在我被操的时候,用舌头把我的脚底舔得干干净净。”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每一个字都像钩子,勾起我内心最深处的、卑劣的嫉妒和渴望。
“……我也想……”我几乎是无意识地,从喉咙里挤出了这句话,“我也想在那个时候……服侍您。”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在她被另一个男人占有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像条忠犬一样守在她的脚边,舔舐她,亲吻她,成为她在那场游戏中,唯一能完全掌控的、卑微的私有物。
我的话,却让她原本慵懒的神情瞬间凝固了。
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冰冷。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我身上站了起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那种场合不适合你。”她淡淡地丢下这句话,开始自顾自地穿上衣服。
“为什么?”我不死心地追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在穿好衣服后,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像是不忍,又像是警告。
“你只要在这里等我就够了。”
她顾左右而言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那一刻我隐约感觉到,她不希望我看到她被另一个男人玩弄的样子,更不希望我被那个世界的、真正的黑暗所吞噬。我只是她一个人的玩具,她不想让我被别人染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极致的割裂和刺激下,我的整个人,都在发生着微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实验室里,当她不经意间对我微笑时,我会下意识地低下头,脸颊发烫,像一个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我的言行举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柔和。
我的气质开始变得柔和,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态,甚至连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女性化的痕迹。尤其是在被她用假阳具操到高潮的时候,我发出的不再是压抑的闷哼,而是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甜腻的呻吟。
林知夏似乎对我的这种变化非常满意。
她开始偶尔让我穿上女装,陪她一起出门。我们会像一对亲密的闺蜜一样,在街角的咖啡厅里分享同一块提拉米苏,在奢侈品店的镜子前一起比划着最新款的包包。她会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说些无伤大雅的私房话,引得周围的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但只要一走到无人的角落,她就会立刻变回那个掌控一切的女王。她会把我按在墙上,掀起我的裙子,用手指粗暴地玩弄我身后那个早已被撑得松软的后穴,感受着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无法自控地颤抖。
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我越发沉迷,无法自拔。我一边感激她对我的“好”,感激她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光鲜亮丽的世界;一边又在这种不见天日的、扭曲的关系中,被巨大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反复撕扯。
。。。。。。
为了庆祝一个项目的阶段性成功,林知夏组织了一次野餐,同行的还有实验室里另外两位师兄。
那天的阳光好得有些不真实。
学姐穿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裙摆随微风轻轻摇曳,像一朵不胜凉风的水莲花。她的脚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白色棉袜,紧紧包裹着她脚踝线条优美的轮廓,脚下则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小皮鞋。那装扮,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学生,与这个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
公园的小路上,她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甚至将半个身子的重量,都亲昵地、毫无防备地靠在了我的身上。她的发梢随着走路的动作,不时地扫过我的脸颊,带来一阵阵好闻的、洗发水的香气。
这幅画面,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正在热恋中的璧人。路过的行人,总会向我们投来善意的、祝福的目光,有些年轻的女孩,甚至会因为看到我们之间那种亲密的、不加掩饰的爱意,而露出羡慕的微笑。
我们一同走到了草坪上。她脱下小皮鞋,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野餐垫外侧,露出那双仍被白棉袜包裹的脚。
她踩在柔软的垫子上,轻轻地动了动脚趾,像是在享受阳光下的微风与青草的温度。
我注意到,公园里偶尔路过的男人,总会不由自主地朝她脚边瞥上一眼。
他们的目光先扫过我们,最终却黏在她的白袜脚上,或那双刚脱下、还带着余温的小皮鞋里;有人喉结轻轻滚了一下,呼吸短短顿住,再装作若无其事地错开。
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压抑着的、属于成年男性的、混杂着欲望的幻想。
他们大概永远也无法想象,此时学姐脚上那双纯洁的白袜,和草坪上那双人畜无害的小皮鞋,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被允许跪下来,贴近了看——
会发现,那双白色棉袜的袜尖,因为长时间被汗水反复浸润,早已泛起了淡淡的黄痕。
棉布表面原本柔软细腻的纤维,此刻却有些粗糙、微硬,像是曾被什么高温又腥臭的液体喷溅过、风干后留下的结痂印迹。
阳光斜照下,更能隐约辨出几道极浅的、不自然的脊状硬痕——仿佛是某次压抑着的射精,被迫喷洒在袜尖时遗留的痕迹。
而那双黑色小皮鞋,鞋口微张,内壁早已失去了新皮革的质感,鞋垫已经踩出了完整的脚型凹痕。
鼻子凑近那张着口的皮鞋时,扑面而来的并不是想象中少女的体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由旧皮革与脚汗混合发酵后的酸腐气息。
更致命的是,那气味之下,竟还有一丝隐约的腥咸,是雄性精液的味道,与其混杂的,还有淡淡的唾液气息——是被另一条舌头一遍遍舔舐之后留下的腥气。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双鞋袜,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代表着怎样一场残酷而又淫靡的游戏。
那个夜晚,两位师兄像狗一样跪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刚刚解锁的下体因为长达一个月的贞操锁折磨,已经淫乱不堪,不住的流出前列腺液
而在他们面前,摆放着的,就是学姐今天脚上这双刚刚脱下来的黑色小皮鞋。
而学姐今天脚上这双纯洁的白色棉袜,正被两位师兄用手攥着,紧紧贴在鼻子上。
规则很简单——谁先射精,谁就是胜利者。
失败者,则必须在胜者高潮的瞬间,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动作,将那已经滚烫堆积到极限的欲望,硬生生地压制回体内,继续承受贞操锁中无止尽的折磨——直到下一场比赛。
于是,欲望便成了一场残酷的竞争。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场景——
他们像两只发情到极限、丧失理智的野兽,跪趴在地,屁股高高撅起,双膝贴地,脊背拱得僵硬,像等待发情指令的畜生。脸则深深埋进那只还残留着学姐体温的白色棉袜中,鼻尖死死抵住袜尖那一小片发黄的位置。
那一片被脚汗反复浸透、早已泛黄发硬的区域,是整只袜子气味最浓烈、最刺激的源头,混合了汗液长时间浸润后散发出的脚酸味,还有一丝令人作呕却令人兴奋的腥咸……仿佛是曾被某人猛烈射精后喷溅上的残渍,早已风干,留下一圈淡淡却不自然的脊状痕迹。
其中一人甚至,抖着伸出舌头,将舌尖贴上那片疑似精斑的袜面。
那不是发泄——那是一场关乎尊严与屈服的生死竞速。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疯狂地崇拜那片被污染的袜面,是因为他们隐约知道,那处污痕的真正来源。
那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释放,而是来自另外两个男生的发泄——年龄更小,年级更低,甚至大概率只是刚被她选中的“新玩物”。
更年轻的肉体,自然也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直接套着那双白棉袜撸动,在袜面上尽情摩擦,享受汗湿纤维与敏感龟头交缠时的粗糙快感。
但那种特权,并不代表自由。
而对于那种尚未驯服、总想要更多的下体,最合适的调教方式,就是反复的寸止。不断摩擦,不断停下,不准射、不准停,直到理智被彻底磨光。
那双小皮鞋的用途,他们也心知肚明:八成是反扣在脸上的,鞋口紧紧扣住口鼻,不准滑落,不准移开。
唯一被允许的慰藉,就是那口口鼻间反复吸入的脚味,是她踩了一整天的鞋垫热气,是袜尖残留的汗渍甜腥,是那种让人越吸越渴、越渴越痛苦的气息。
这就是套着棉袜撸动的代价。
似乎是和我一样想到了这里,两位师兄的双眼早已泛红,混杂着渴望、羞耻、绝望和嫉妒。
十几秒钟后,在一声几乎是嘶哑的低吼中——
其中一个师兄的身体剧烈抽搐起来,像被从内而外点燃。
他的下体颤抖着,精液如决堤的洪水般,从被解锁不过几分钟的性器中喷涌而出——毫无保留地,尽数射进那只黑色小皮鞋内部。
他的手甚至在射完后仍死死抓着鞋跟,仿佛那里是他唯一的出口。
而另一个师兄,却在那一刻被学姐一脚毫不留情地踹翻。
他正攀上高潮边缘,身体已经抖得像筛子,精液几乎要从马眼里冲出,却在这一脚中戛然而止。
而那只沾满精液的小皮鞋,则安静地躺在一旁,成为这场残酷竞争的唯一胜者的奖杯。
此刻,看着那双被摆在阳光下的、干净的小皮鞋,我的后背不禁一阵发凉。
这份干净,是因为在那个夜晚,那个输掉了比赛的师兄,像一条真正的狗一样,用他的舌头,将胜利者射在里面的、那滩黏稠腥臊的液体,一滴不剩地,全部舔舐干净。
在铺着格子布的草地上,林知夏表现得对我格外亲昵,那种亲昵,甚至超越了普通情侣的界限。她会把剥好的、最甜的那瓣橘子,亲手喂到我的嘴边;会在我嘴角沾上一点酱汁时,拿出纸巾,用一种无比自然的、带着宠溺的姿态,轻轻为我擦拭干净。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让我几乎要融化。而那两位师兄的眼神,则像淬了毒的冰锥,死死地钉在我的身上。
中途,我去取水,其中一位师兄跟了过来。在远离人群的树荫下,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嫉妒和鄙夷。
“你别得意忘形了。”他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的怨毒,“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林知夏是什么人,她会看得上你这种穷酸样?”
我愣住了。
他看到我茫然的表情,脸上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冷笑:“别傻了。我们都一样,都是她的‘玩物’。唯一的区别是,你是她现在最上心、最新鲜的玩具,她愿意在你身上花更多的心思罢了。”
“玩物……我们?”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我如遭雷击,浑身僵硬。
他的目光,不加掩饰地扫过我的下体,和我的臀部。那眼神,仿佛能穿透我那层薄薄的裤子,清晰地看到我身上前锁后塞的羞耻模样。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他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玩具,总有玩腻的一天。到时候,你的下场,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越过他的肩膀,看向远处那个正陪着学姐说笑的、另一个师兄。他笑得那么阳光,但我此刻却仿佛能看到他笑容背后,那和我如出一辙的、深深烙印在骨子里的恐惧和臣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重新坐回林知夏身边时,她依旧对我笑得温柔,又递给我一块切好的西瓜。
我僵硬地接过,低下头,拼命地将所有的屈辱和自卑,连同那口甜得发腻的西瓜,一起吞进肚子里,藏在心里最阴暗的角落。
。。。。。。
日子在白天和黑夜的撕裂中,麻木地向前滚动。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会所的、一条不同寻常的指令。
我没有被要求去那个我熟悉的、作为“发泄玩具”的套房。而是被一个沉默的保安,带领着穿过了几条我从未走过的、阴暗潮湿的“员工通道”。最后,他让我在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狭窄的杂物间里等待。这间房,与隔壁的顶级套房,只有一墙之隔,墙壁上甚至还有一个被窗帘遮住的、用于观察的单向玻璃暗门。
我被告知,在接到传唤之前,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离开。
我像一尊石像,僵硬地站在这个狭小的、充满灰尘气息的杂物间里。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差,隔壁房间的声音,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一根接一根地,狠狠扎进我的耳朵,刺穿我的大脑。
很快,隔壁的房间就传来了声音。
一开始,是几个男人用英语和一种我听不懂的、带着浓重口音的语言在交谈。他们的笑声洪亮而刺耳,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和不加掩饰的粗野。我听见沉重的酒杯碰撞的声音,以及雪茄被剪断的、清脆的“咔嚓”声。那是一个属于上位者的、轻松而惬意的开场。
然后,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响起了。
那不是我熟悉的、属于女王的、冰冷的命令。而是一种混杂着痛苦、欢愉和屈辱的、破碎的呻吟。
那呻吟的声音,像一个开关,瞬间开启了地狱的大门。
男人们爆发出一阵更加肆无忌惮的哄笑。我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用最污秽的词语,命令她像狗一样爬过去。紧接着,是布料被粗暴撕碎的声音,和她一声短促的、压抑着痛苦的惊呼。
然后,一切都失控了。
我听见肉体被皮带或是什么东西反复抽打的、沉闷的“啪啪”声,每一声都伴随着她再也无法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呻吟。男人们在用不同的语言,兴奋地数着数,像是在进行一场狩猎游戏。
我听见她被不同的男人用最粗言秽语的方式羞辱、命令她用嘴去取悦他们。我能听到黏腻的水声,和她因为被掐住脖子而发出的、近乎窒息的、断断续续的呜咽。
但最让我崩溃的,是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似乎厌倦了这种单向的施虐。他用一种戏谑的、残忍的语气下达了一道新的命令。紧接着,我听到了好几个沉重的脚步声在向她靠近。
我第一次,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崩溃。那不再是游戏,而是契约被撕毁后,面对彻底失控的、纯粹的暴力时,最本能的、最绝望的哀求。
但那哀求,只换来了男人们更加兴奋的、魔鬼般的狂笑。
接下来,我听到了此生都无法忘记的声音。那是她被好几个男人同时按住手脚时发出的、徒劳的挣扎声。是她被那些黑人男性用他们巨大的、滚烫的阳具,轮流地、甚至同时地,狠狠贯穿她前后两个穴洞时,发出的凄厉到变了调的惨叫。
那惨叫声,很快就因为不堪的凌辱和痛苦,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混杂着哭泣和求饶的破碎呻吟。我能清晰地听到不同男人的、粗重的喘息声,和肉体毫无廉耻地、野蛮撞击的黏腻水声,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曲最残忍、最淫靡的地狱交响。
我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被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被迫听着我的“主人”,被一群我看不见的、更加恐怖的存在,当做一个公共玩物,肆意玩弄、轮番享用。时间仿佛被拉长到了无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灵魂最残忍的凌迟。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残暴的狂欢,似乎终于落下了帷幕。隔壁的声音渐渐平息,只剩下男人们心满意足的交谈声。
又过了一会儿,我所在的杂物间的门,被“咔哒”一声打开了。
一个我不认识的、同样身形魁梧的黑人男性,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他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用下巴朝里面点了点,眼神就像在示意一条狗去清理主人呕吐出的秽物。
我双腿发软地,一步一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地狱,原来是有气味的。
一股浓稠到几乎凝为实质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瞬间扼住了我的喉咙。那是一种由汗水、精液、雪茄、被打翻的昂贵威士忌、以及一丝微不可查的血腥味混合而成的、属于末日狂欢的腥臊气息。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上,沾染着大片大片的、深色的酒渍和可疑的、白色的粘稠液体,仿佛一幅被肆意凌虐过的抽象画。
而我的学姐,林知夏,那个在我心中永远高高在上、冰冷圣洁的女王……就趴在这幅地狱绘图的最中央。
她像一个被玩坏后随意丢弃的、关节扭曲的陶瓷娃娃,趴在巨大而凌乱的床上。那张曾经承载着无数奢靡与罪恶的大床,此刻看上去更像一个祭坛,而她,就是那场献祭仪式结束后,被遗忘的祭品。
她的神智已经完全抽离,那双曾洞悉一切、让我不敢直视的漂亮眼睛,此刻空洞地睁着,却没有任何焦距。瞳孔散漫,倒映不出天花板上那盏奢华水晶灯的任何光芒。一道干涸的泪痕,从她的眼角蜿-蜒而下,划过她脸颊上那片早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精液的、肮脏的粘腻。
她的嘴唇红肿破裂,嘴角甚至有一丝细微的、已经凝固的血迹。她的头发,那头总是打理得一丝不苟的秀发,此刻像一团枯萎的海草,混杂着各种可疑的液体,狼狈地黏在她的脸上和脖颈上。
她的身体,那具我曾无比渴望、也无比恐惧的、如同艺术品般的身体,此刻成了一块被肆意涂抹的画布。白皙的皮肤上,青紫色的手印、牙印、以及皮带抽打后留下的一道道狰狞的红痕,交错纵横。而覆盖在这些暴力痕迹之上的,是属于不同男人的、已经开始变得半透明或依旧乳白粘稠的精液。它们从她的后背,流到她的大腿,甚至滴落在丝质的床单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屈辱的岛屿。
她无力地趴着,上身几乎贴在床上,而臀部却依旧被维持在一个方便被从后面进入的、高高撅起的姿势。她那被过度使用的、红肿不堪的小穴和后穴,就那样毫无遮拦地、甚至无法完全闭合地暴露在空气中。穴口微微外翻,像两张被蹂躏到麻木的、哭泣的嘴,还在不受控制地向外淌着浑浊的、混合了淫水和精液的液体,将身下的床单浸染出一片深色的、潮湿的地图。
我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我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一切认知,在这一瞬间,被眼前这幅惨烈到极致的、淫靡到极致的画面,冲击得支离破碎。
那个用脚尖就能让我高潮的女王,那个用一道命令就能决定我所有悲喜的主人,那个我以为是金字塔顶端捕食者的存在……原来,也会被这样对待。
原来,她也会哭,会求饶,会被撕碎,会被当成一个连人都算不上的、纯粹的泄欲工具。
原来,她不是神。
她也是……玩物。
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从我那早已麻木的心脏深处,猛地喷涌而出。那不是嫉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滔天怒火、极致心疼和彻底无能为力的、尖锐的刺痛。
就在我的身体因为那句冰冷的命令而本能地想要向前挪动时,一个带着一丝慵懒笑意的声音,从房间的角落里响了起来。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男性。
他并没有参与刚才那场狂欢,而是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自始至终都靠在吧台边,安静地抽着雪茄。此刻,他缓缓地走了过来,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移动的铁塔,投下的阴影将我和床上那个破败的她,完全笼罩。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洞悉一切的、属于更高层级玩家的戏谑,“她对你,不一样。”
“你以为你为什么还活着?”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你本来早该像一条不听话的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了。是她,主动向‘主人们’请求,把你变成了她的专属玩物,用这种方式,才让你这条小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她以为她掩饰得很好。”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她以为,把你变成一个听话的、离不开她的玩物,就能把那份不该有的感情,藏在调教和支配的游戏之下。可惜,她高估了自己作为‘资产’的权限。‘主人们’……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所有物,产生了不该有的、独立的思想和感情。”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份混杂着愤怒与心疼的情感,捅得千疮百孔。
原来……她对我好,是真的。
而这份真实,却成了将她推入更深地狱的、最根本的罪。
“不过,”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个堪称仁慈的、魔鬼般的微笑,“‘主人们’也并非不通情理。我们很乐意成人之美。”
他一边说,一边从吧台上端过来一个银制的托盘,轻轻地放在了我面前的地毯上。
托盘上,没有美酒,也没有佳肴。
只有密密麻麻的、足足有四五十粒的纯白色药片。它们像一盘洁白的、致命的棋子,在奢华的灯光下,反射着冰冷而圣洁的光芒。
“这是‘极乐’。”他用一种冰冷的、仿佛在陈述商品使用说明的语气介绍道,“专门为不听话的‘资产’准备的。能彻底清除掉她们脑子里那些多余的、不该有的思想,让她们变成只会淫荡地张开腿、主动索取性交的、完美的泄欲工具。”
他顿了顿,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眼神,看了一眼床上那个依旧毫无声息的她。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会把脑子彻底烧坏。你知道的,精密仪器,总是很脆弱。”
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彻底冻结了。
“今晚,她需要服下这里所有的药。”黑人男性指了指托盘,然后又伸出手指,指向房间里那十几个刚刚享用完她、此刻正像一群看戏的狼一样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同样身形高大的黑人男性,“当然,‘主人们’给了你一个拯救她的机会。”
“看到他们了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恶魔的耳语,“你去,用你的嘴,你的身体,你的全部,去取悦他们。你只要能让这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射精一次,我就从托盘里,为她拿走一粒药。”
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脸上的笑容更加残忍了。
“别高兴得太早。”他蹲下身,捡起一粒药,在我眼前晃了晃,“这东西的药效很强。一粒,就足以让她神智不清,彻底沦为只会求欢的母狗。两粒,她的大脑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变成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白痴。三粒……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有价值的资产身上,试过三粒以上的剂量。”
我呆呆地看着他,看着那一盘致命的药,看着那十几座由黑色肌肉和欲望组成的、无法逾越的山脉,又回头看了一眼床上那个破败不堪的女人。
这一刻我才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慈悲的“机会”。
这是这世上,最恶毒的诅咒。
它将那份卑微的、见不得光的爱意,血淋淋地剖开,放在了审判的天平上。而天平的另一端,是她的神智,她的未来,甚至她的生命。
我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的尊严,我的身体,我的一切。
这不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而是通往地狱更深处的、唯一的路径。
黑人男性站起身,退回阴影之中,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宣布了这场终极审判的开始。
“开始吧。”
虽然但是确实很色,不过这篇主要是雌堕为主
当然,你要是觉得从文笔来讲不适合这一章节的话,就当我没说🤓
腰肌劳损:↑虚心接受,坚决不改🤓BetaDenier:↑只是一个提议,不适合这里也无所谓,只是这样从剧情来讲其实很容易击溃主角的心理防线(例如最后所有的药都没了,主角终于要结束昏过去的时候,突然再射了……),我个人感觉这要很主角很容易就……🤤咳咳腰肌劳损:↑你是魔鬼吧(bushi)BetaDenier:↑【8】对了,突然有一个新奇的想法,在最后这个药物这里除了服侍一次拿出来一颗之外,也可以让主角射一次往里放一颗🤓
那一天之后,林知夏对我,好得匪夷所思。
她不再仅仅局限于学业上的指导。她会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在某个阳光正好的下午,突然拉着我逃离实验室,带我去城市另一端那家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的、昂贵的私房菜馆;她会带我出入那些我只在财经杂志上见过的、顶级会员制的奢侈品商场,面无表情地为我换上阔挺的西装;她会当着实验室所有人的面送给我最新款的手机和一直都想要却舍不得买的配置顶级的笔记本电脑,只因为她觉得“你的旧的太卡了,影响效率”。
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将我拉进了她的世界——一个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我过去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世界。我见识到了她那深不见底的财力,每一次随意的消费,都足以抵上我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薪水。
在这种极致的物质和情感包裹下,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恋爱的错觉。当她耐心地帮我整理被风吹乱的衣领,当她在高级餐厅里自然地将她盘子里最鲜美的那块和牛夹给我时,我几乎就要相信,我们就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如果不是我时刻能感受到身前那个冰冷的贞操锁,以及身后那个早已被我的体温捂热、却依旧坚硬无比的金属肛塞的话。
它们像两个最忠诚的、最残忍的守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如今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怎样一种屈辱的关系之上。
而最让我清醒的,是有时我们并肩坐在某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她会拿出手机,处理一些“工作”。
她不会避讳我,而是会像分享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一样,戴上一只白色的无线耳机,将另一只,塞进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便能清晰地、身临其境地,听到那个加密通讯软件里,传来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那通常是一段充满了静电杂音的、带着卑微喘息的语音。另一头的男人,大概是按下了通话键后,就再也不敢松手。
然后,我会听到林知夏的声音,通过她那小巧的、隐藏在发丝间的麦克风,冰冷地、清晰地,传递到那个卑微的世界里。
“劣等品β-2302号,”她会一边用小勺优雅地搅动着自己面前那杯拿铁,一边用一种近乎无情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说道,
“你真锁了一个月啊,就为了买我一双袜子”
对面传来一阵压抑的、急切的、仿佛在点头般的喘息声。
“行吧,”林知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施舍般的、居高临下的慵懒,“给你10秒钟时间。”
我能清晰地听到,耳机的那一头,瞬间响起了一阵疯狂的、湿滑的、肉体摩擦的声音。紧接着,是那个男人带着哭腔的、绝望的哀求:“不……主人……求求您……10秒钟……不可能这么快就……”
林知夏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她只是看着咖啡杯上漂亮的拉花,用一种平稳的、仿佛在欣赏一首乐曲的节奏,开始了冰冷的倒数。
“九……八……七……”
那头的摩擦声,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绝望,甚至带上了一丝自残般的绝望意味。
“……三……二……一。”
林知夏的声音,像死神的镰刀,精准地、毫不留情地,落下了。
“松手吧。”
耳机那头,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一般的、充满了绝望和不甘的寂静。过了很久,才传来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仿佛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野兽般的呜咽。
林知夏端起咖啡,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对着麦克风,说出了那句最终的、决定他未来一个月命运的审判。
“看来还是锁得太少了。”
说完,她便挂断了通讯,取下了耳机,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消遣。
她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问我,要不要再加一块芝士蛋糕。
那一刻,我所有的温情幻想,都会被瞬间击得粉碎。我不是特殊的,我只是她的一个“玩具”,或许,是目前最令她满意的一个。
而白天有多“温存”,夜晚就有多“残忍”。
我在会所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我不再需要去端盘子,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像一个等待被传唤的奴隶,等候她的指令。
那通常是在她和某个,或者某几个高大强壮的黑人男性结束狂欢之后。
我会接到指令,独自一人来到那个我曾无比恐惧的、顶层的私人套房。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混杂着雪茄、酒精和激烈性爱后的麝香味。床上凌乱不堪,空气中还残留着属于男人的、陌生的气息。
而林知夏,早已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面孔。她会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赤着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脸上没有了白天的温柔,只有一种暴风雨过后的、带着一丝疲惫和暴戾的冰冷。
她什么都不会说,只是会从床边的暗格里,拿出一条黑色的、尺寸惊人的穿戴式假阳具,熟练地绑在自己纤细的腰间。
然后,她会走到我面前,用那根巨大的、冰冷的、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假阳具,狠狠地、毫不留情地,贯穿我那早已被扩张到极限的后穴。
那不是做爱,那甚至不是调教。
那是一种纯粹的发泄。
她会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在我体内疯狂地抽插。她会把白天积攒的、那些无处释放的压力、疲惫和愤怒,通过这根假阳具,一下又一下地,尽数发泄在我的身体里。
在那些混杂着剧痛与极致快感的、漫长的发泄过程中,林知夏有时会突然停下那毁灭般的冲撞,转而用一种更残忍的、精神上的方式来凌虐我。她会贴在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将那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淫靡的画面,一字一句地,灌进我的脑海里。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她会一边用那根巨大的、还埋在我体内的假阳具,不轻不重地研磨着我早已溃不成军的前列腺,一边用一种冰冷而又带着一丝炫耀的语气,向我描述她白天的“盛况”。
“他很强壮,比你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都要强壮。他的阳具……像一根烧红的铁棍,几乎要把我捅穿。”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回味般的、满足的颤音,“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两个不听话的玩具叫了进来,让他们跪在床边,看着我是怎么被干的。”
“我让他们比,看谁的几把更小,更可怜。其中有一个,连勃起都不到十厘米。我让那个黑人,用他那根比他大腿还粗的鸡巴,狠狠地抽他的脸,你猜怎么着?”
她在我耳边发出了一声恶意的轻笑。
“他居然被抽射了。精液射在了我的脚背上,又脏又黏,像一滩鼻涕。我罚他把我和那个黑人干完后流出来的、混合在一起的淫水,全都舔干净。”
她会细致入微地向我描述,在她和那个黑人男性赤身裸体地纠缠、被巨大的阳具肏得浑身颤抖、浪叫连连的时候,身下是如何跪着那几个被她称之为“劣等品”的男人。
他们会像最卑微的狗一样,匍匐在床边,不敢抬头看她被侵犯的脸,只敢用舌头狂热地舔舐她因为高潮而蜷缩的脚趾,亲吻她因为痉挛而微微颤抖的小腿。他们甚至会为了争抢一滴从她体内溢出的、属于那个黑人男性的精液而互相撕咬,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甘美的琼浆。
“他们每一个,都比你更懂得怎么服侍。”她会一边在我体内冲撞,一边用气声这样说道。
这本该是极致的羞辱。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内心,却因为这些露骨的、充满了尺寸对比和权力践踏的描述,产生了一丝病态的、不甘的嫉妒。
我嫉妒那些“劣等品”。
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渴望能亲眼见证她的“盛况”。我渴望能像他们一样,跪在她的脚边,用最卑微的姿态,去仰望她被更强者征服时的、那种混杂着痛苦与极乐的、最真实的表情。
我渴望,能成为她那场盛大而淫靡的权力游戏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却能亲眼见证一切的观众。
而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在一切结束之后,成为她在黑夜里,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承受她所有负面情绪的、孤独的、有生命的玩具。
在一次例行的、粗暴的发泄结束后,我瘫软在地毯上,后穴火辣辣地疼,身体因为刚刚经历过的强制高潮而微微抽搐。林知夏拔出那根巨大的假阳具,随意地丢在一旁,她赤裸的身体覆着一层薄汗,胸口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跨坐在我的身上,用一种慵懒而又危险的语气,开始描述刚才那场她与黑人男性的狂欢。
“你知道吗,”她低下头,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上,“今天那个新来的劣等品很有趣,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只敢趴在地上,像条真正的狗一样,在我被操的时候,用舌头把我的脚底舔得干干净净。”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每一个字都像钩子,勾起我内心最深处的、卑劣的嫉妒和渴望。
“……我也想……”我几乎是无意识地,从喉咙里挤出了这句话,“我也想在那个时候……服侍您。”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在她被另一个男人占有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像条忠犬一样守在她的脚边,舔舐她,亲吻她,成为她在那场游戏中,唯一能完全掌控的、卑微的私有物。
我的话,却让她原本慵懒的神情瞬间凝固了。
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冰冷。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我身上站了起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那种场合不适合你。”她淡淡地丢下这句话,开始自顾自地穿上衣服。
“为什么?”我不死心地追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在穿好衣服后,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像是不忍,又像是警告。
“你只要在这里等我就够了。”
她顾左右而言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那一刻我隐约感觉到,她不希望我看到她被另一个男人玩弄的样子,更不希望我被那个世界的、真正的黑暗所吞噬。我只是她一个人的玩具,她不想让我被别人染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极致的割裂和刺激下,我的整个人,都在发生着微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实验室里,当她不经意间对我微笑时,我会下意识地低下头,脸颊发烫,像一个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我的言行举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柔和。
我的气质开始变得柔和,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态,甚至连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女性化的痕迹。尤其是在被她用假阳具操到高潮的时候,我发出的不再是压抑的闷哼,而是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甜腻的呻吟。
林知夏似乎对我的这种变化非常满意。
她开始偶尔让我穿上女装,陪她一起出门。我们会像一对亲密的闺蜜一样,在街角的咖啡厅里分享同一块提拉米苏,在奢侈品店的镜子前一起比划着最新款的包包。她会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说些无伤大雅的私房话,引得周围的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但只要一走到无人的角落,她就会立刻变回那个掌控一切的女王。她会把我按在墙上,掀起我的裙子,用手指粗暴地玩弄我身后那个早已被撑得松软的后穴,感受着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无法自控地颤抖。
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我越发沉迷,无法自拔。我一边感激她对我的“好”,感激她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光鲜亮丽的世界;一边又在这种不见天日的、扭曲的关系中,被巨大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反复撕扯。
。。。。。。
为了庆祝一个项目的阶段性成功,林知夏组织了一次野餐,同行的还有实验室里另外两位师兄。
那天的阳光好得有些不真实。
学姐穿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裙摆随微风轻轻摇曳,像一朵不胜凉风的水莲花。她的脚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白色棉袜,紧紧包裹着她脚踝线条优美的轮廓,脚下则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小皮鞋。那装扮,让她看起来就像一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学生,与这个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
公园的小路上,她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甚至将半个身子的重量,都亲昵地、毫无防备地靠在了我的身上。她的发梢随着走路的动作,不时地扫过我的脸颊,带来一阵阵好闻的、洗发水的香气。
这幅画面,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正在热恋中的璧人。路过的行人,总会向我们投来善意的、祝福的目光,有些年轻的女孩,甚至会因为看到我们之间那种亲密的、不加掩饰的爱意,而露出羡慕的微笑。
我们一同走到了草坪上。她脱下小皮鞋,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野餐垫外侧,露出那双仍被白棉袜包裹的脚。
她踩在柔软的垫子上,轻轻地动了动脚趾,像是在享受阳光下的微风与青草的温度。
我注意到,公园里偶尔路过的男人,总会不由自主地朝她脚边瞥上一眼。
他们的目光先扫过我们,最终却黏在她的白袜脚上,或那双刚脱下、还带着余温的小皮鞋里;有人喉结轻轻滚了一下,呼吸短短顿住,再装作若无其事地错开。
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压抑着的、属于成年男性的、混杂着欲望的幻想。
他们大概永远也无法想象,此时学姐脚上那双纯洁的白袜,和草坪上那双人畜无害的小皮鞋,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被允许跪下来,贴近了看——
会发现,那双白色棉袜的袜尖,因为长时间被汗水反复浸润,早已泛起了淡淡的黄痕。
棉布表面原本柔软细腻的纤维,此刻却有些粗糙、微硬,像是曾被什么高温又腥臭的液体喷溅过、风干后留下的结痂印迹。
阳光斜照下,更能隐约辨出几道极浅的、不自然的脊状硬痕——仿佛是某次压抑着的射精,被迫喷洒在袜尖时遗留的痕迹。
而那双黑色小皮鞋,鞋口微张,内壁早已失去了新皮革的质感,鞋垫已经踩出了完整的脚型凹痕。
鼻子凑近那张着口的皮鞋时,扑面而来的并不是想象中少女的体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由旧皮革与脚汗混合发酵后的酸腐气息。
更致命的是,那气味之下,竟还有一丝隐约的腥咸,是雄性精液的味道,与其混杂的,还有淡淡的唾液气息——是被另一条舌头一遍遍舔舐之后留下的腥气。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双鞋袜,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代表着怎样一场残酷而又淫靡的游戏。
那个夜晚,两位师兄像狗一样跪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刚刚解锁的下体因为长达一个月的贞操锁折磨,已经淫乱不堪,不住的流出前列腺液
而在他们面前,摆放着的,就是学姐今天脚上这双刚刚脱下来的黑色小皮鞋。
而学姐今天脚上这双纯洁的白色棉袜,正被两位师兄用手攥着,紧紧贴在鼻子上。
规则很简单——谁先射精,谁就是胜利者。
失败者,则必须在胜者高潮的瞬间,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动作,将那已经滚烫堆积到极限的欲望,硬生生地压制回体内,继续承受贞操锁中无止尽的折磨——直到下一场比赛。
于是,欲望便成了一场残酷的竞争。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场景——
他们像两只发情到极限、丧失理智的野兽,跪趴在地,屁股高高撅起,双膝贴地,脊背拱得僵硬,像等待发情指令的畜生。脸则深深埋进那只还残留着学姐体温的白色棉袜中,鼻尖死死抵住袜尖那一小片发黄的位置。
那一片被脚汗反复浸透、早已泛黄发硬的区域,是整只袜子气味最浓烈、最刺激的源头,混合了汗液长时间浸润后散发出的脚酸味,还有一丝令人作呕却令人兴奋的腥咸……仿佛是曾被某人猛烈射精后喷溅上的残渍,早已风干,留下一圈淡淡却不自然的脊状痕迹。
其中一人甚至,抖着伸出舌头,将舌尖贴上那片疑似精斑的袜面。
那不是发泄——那是一场关乎尊严与屈服的生死竞速。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疯狂地崇拜那片被污染的袜面,是因为他们隐约知道,那处污痕的真正来源。
那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释放,而是来自另外两个男生的发泄——年龄更小,年级更低,甚至大概率只是刚被她选中的“新玩物”。
更年轻的肉体,自然也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直接套着那双白棉袜撸动,在袜面上尽情摩擦,享受汗湿纤维与敏感龟头交缠时的粗糙快感。
但那种特权,并不代表自由。
而对于那种尚未驯服、总想要更多的下体,最合适的调教方式,就是反复的寸止。不断摩擦,不断停下,不准射、不准停,直到理智被彻底磨光。
那双小皮鞋的用途,他们也心知肚明:八成是反扣在脸上的,鞋口紧紧扣住口鼻,不准滑落,不准移开。
唯一被允许的慰藉,就是那口口鼻间反复吸入的脚味,是她踩了一整天的鞋垫热气,是袜尖残留的汗渍甜腥,是那种让人越吸越渴、越渴越痛苦的气息。
这就是套着棉袜撸动的代价。
似乎是和我一样想到了这里,两位师兄的双眼早已泛红,混杂着渴望、羞耻、绝望和嫉妒。
十几秒钟后,在一声几乎是嘶哑的低吼中——
其中一个师兄的身体剧烈抽搐起来,像被从内而外点燃。
他的下体颤抖着,精液如决堤的洪水般,从被解锁不过几分钟的性器中喷涌而出——毫无保留地,尽数射进那只黑色小皮鞋内部。
他的手甚至在射完后仍死死抓着鞋跟,仿佛那里是他唯一的出口。
而另一个师兄,却在那一刻被学姐一脚毫不留情地踹翻。
他正攀上高潮边缘,身体已经抖得像筛子,精液几乎要从马眼里冲出,却在这一脚中戛然而止。
而那只沾满精液的小皮鞋,则安静地躺在一旁,成为这场残酷竞争的唯一胜者的奖杯。
此刻,看着那双被摆在阳光下的、干净的小皮鞋,我的后背不禁一阵发凉。
这份干净,是因为在那个夜晚,那个输掉了比赛的师兄,像一条真正的狗一样,用他的舌头,将胜利者射在里面的、那滩黏稠腥臊的液体,一滴不剩地,全部舔舐干净。
在铺着格子布的草地上,林知夏表现得对我格外亲昵,那种亲昵,甚至超越了普通情侣的界限。她会把剥好的、最甜的那瓣橘子,亲手喂到我的嘴边;会在我嘴角沾上一点酱汁时,拿出纸巾,用一种无比自然的、带着宠溺的姿态,轻轻为我擦拭干净。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让我几乎要融化。而那两位师兄的眼神,则像淬了毒的冰锥,死死地钉在我的身上。
中途,我去取水,其中一位师兄跟了过来。在远离人群的树荫下,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嫉妒和鄙夷。
“你别得意忘形了。”他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的怨毒,“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林知夏是什么人,她会看得上你这种穷酸样?”
我愣住了。
他看到我茫然的表情,脸上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冷笑:“别傻了。我们都一样,都是她的‘玩物’。唯一的区别是,你是她现在最上心、最新鲜的玩具,她愿意在你身上花更多的心思罢了。”
“玩物……我们?”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我如遭雷击,浑身僵硬。
他的目光,不加掩饰地扫过我的下体,和我的臀部。那眼神,仿佛能穿透我那层薄薄的裤子,清晰地看到我身上前锁后塞的羞耻模样。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他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玩具,总有玩腻的一天。到时候,你的下场,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越过他的肩膀,看向远处那个正陪着学姐说笑的、另一个师兄。他笑得那么阳光,但我此刻却仿佛能看到他笑容背后,那和我如出一辙的、深深烙印在骨子里的恐惧和臣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重新坐回林知夏身边时,她依旧对我笑得温柔,又递给我一块切好的西瓜。
我僵硬地接过,低下头,拼命地将所有的屈辱和自卑,连同那口甜得发腻的西瓜,一起吞进肚子里,藏在心里最阴暗的角落。
。。。。。。
日子在白天和黑夜的撕裂中,麻木地向前滚动。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会所的、一条不同寻常的指令。
我没有被要求去那个我熟悉的、作为“发泄玩具”的套房。而是被一个沉默的保安,带领着穿过了几条我从未走过的、阴暗潮湿的“员工通道”。最后,他让我在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狭窄的杂物间里等待。这间房,与隔壁的顶级套房,只有一墙之隔,墙壁上甚至还有一个被窗帘遮住的、用于观察的单向玻璃暗门。
我被告知,在接到传唤之前,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离开。
我像一尊石像,僵硬地站在这个狭小的、充满灰尘气息的杂物间里。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差,隔壁房间的声音,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一根接一根地,狠狠扎进我的耳朵,刺穿我的大脑。
很快,隔壁的房间就传来了声音。
一开始,是几个男人用英语和一种我听不懂的、带着浓重口音的语言在交谈。他们的笑声洪亮而刺耳,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和不加掩饰的粗野。我听见沉重的酒杯碰撞的声音,以及雪茄被剪断的、清脆的“咔嚓”声。那是一个属于上位者的、轻松而惬意的开场。
然后,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响起了。
那不是我熟悉的、属于女王的、冰冷的命令。而是一种混杂着痛苦、欢愉和屈辱的、破碎的呻吟。
那呻吟的声音,像一个开关,瞬间开启了地狱的大门。
男人们爆发出一阵更加肆无忌惮的哄笑。我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用最污秽的词语,命令她像狗一样爬过去。紧接着,是布料被粗暴撕碎的声音,和她一声短促的、压抑着痛苦的惊呼。
然后,一切都失控了。
我听见肉体被皮带或是什么东西反复抽打的、沉闷的“啪啪”声,每一声都伴随着她再也无法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呻吟。男人们在用不同的语言,兴奋地数着数,像是在进行一场狩猎游戏。
我听见她被不同的男人用最粗言秽语的方式羞辱、命令她用嘴去取悦他们。我能听到黏腻的水声,和她因为被掐住脖子而发出的、近乎窒息的、断断续续的呜咽。
但最让我崩溃的,是听到一个说英语的男人,似乎厌倦了这种单向的施虐。他用一种戏谑的、残忍的语气下达了一道新的命令。紧接着,我听到了好几个沉重的脚步声在向她靠近。
我第一次,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崩溃。那不再是游戏,而是契约被撕毁后,面对彻底失控的、纯粹的暴力时,最本能的、最绝望的哀求。
但那哀求,只换来了男人们更加兴奋的、魔鬼般的狂笑。
接下来,我听到了此生都无法忘记的声音。那是她被好几个男人同时按住手脚时发出的、徒劳的挣扎声。是她被那些黑人男性用他们巨大的、滚烫的阳具,轮流地、甚至同时地,狠狠贯穿她前后两个穴洞时,发出的凄厉到变了调的惨叫。
那惨叫声,很快就因为不堪的凌辱和痛苦,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混杂着哭泣和求饶的破碎呻吟。我能清晰地听到不同男人的、粗重的喘息声,和肉体毫无廉耻地、野蛮撞击的黏腻水声,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曲最残忍、最淫靡的地狱交响。
我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被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被迫听着我的“主人”,被一群我看不见的、更加恐怖的存在,当做一个公共玩物,肆意玩弄、轮番享用。时间仿佛被拉长到了无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灵魂最残忍的凌迟。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残暴的狂欢,似乎终于落下了帷幕。隔壁的声音渐渐平息,只剩下男人们心满意足的交谈声。
又过了一会儿,我所在的杂物间的门,被“咔哒”一声打开了。
一个我不认识的、同样身形魁梧的黑人男性,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他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用下巴朝里面点了点,眼神就像在示意一条狗去清理主人呕吐出的秽物。
我双腿发软地,一步一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地狱,原来是有气味的。
一股浓稠到几乎凝为实质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瞬间扼住了我的喉咙。那是一种由汗水、精液、雪茄、被打翻的昂贵威士忌、以及一丝微不可查的血腥味混合而成的、属于末日狂欢的腥臊气息。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上,沾染着大片大片的、深色的酒渍和可疑的、白色的粘稠液体,仿佛一幅被肆意凌虐过的抽象画。
而我的学姐,林知夏,那个在我心中永远高高在上、冰冷圣洁的女王……就趴在这幅地狱绘图的最中央。
她像一个被玩坏后随意丢弃的、关节扭曲的陶瓷娃娃,趴在巨大而凌乱的床上。那张曾经承载着无数奢靡与罪恶的大床,此刻看上去更像一个祭坛,而她,就是那场献祭仪式结束后,被遗忘的祭品。
她的神智已经完全抽离,那双曾洞悉一切、让我不敢直视的漂亮眼睛,此刻空洞地睁着,却没有任何焦距。瞳孔散漫,倒映不出天花板上那盏奢华水晶灯的任何光芒。一道干涸的泪痕,从她的眼角蜿-蜒而下,划过她脸颊上那片早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精液的、肮脏的粘腻。
她的嘴唇红肿破裂,嘴角甚至有一丝细微的、已经凝固的血迹。她的头发,那头总是打理得一丝不苟的秀发,此刻像一团枯萎的海草,混杂着各种可疑的液体,狼狈地黏在她的脸上和脖颈上。
她的身体,那具我曾无比渴望、也无比恐惧的、如同艺术品般的身体,此刻成了一块被肆意涂抹的画布。白皙的皮肤上,青紫色的手印、牙印、以及皮带抽打后留下的一道道狰狞的红痕,交错纵横。而覆盖在这些暴力痕迹之上的,是属于不同男人的、已经开始变得半透明或依旧乳白粘稠的精液。它们从她的后背,流到她的大腿,甚至滴落在丝质的床单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屈辱的岛屿。
她无力地趴着,上身几乎贴在床上,而臀部却依旧被维持在一个方便被从后面进入的、高高撅起的姿势。她那被过度使用的、红肿不堪的小穴和后穴,就那样毫无遮拦地、甚至无法完全闭合地暴露在空气中。穴口微微外翻,像两张被蹂躏到麻木的、哭泣的嘴,还在不受控制地向外淌着浑浊的、混合了淫水和精液的液体,将身下的床单浸染出一片深色的、潮湿的地图。
我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我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一切认知,在这一瞬间,被眼前这幅惨烈到极致的、淫靡到极致的画面,冲击得支离破碎。
那个用脚尖就能让我高潮的女王,那个用一道命令就能决定我所有悲喜的主人,那个我以为是金字塔顶端捕食者的存在……原来,也会被这样对待。
原来,她也会哭,会求饶,会被撕碎,会被当成一个连人都算不上的、纯粹的泄欲工具。
原来,她不是神。
她也是……玩物。
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从我那早已麻木的心脏深处,猛地喷涌而出。那不是嫉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滔天怒火、极致心疼和彻底无能为力的、尖锐的刺痛。
就在我的身体因为那句冰冷的命令而本能地想要向前挪动时,一个带着一丝慵懒笑意的声音,从房间的角落里响了起来。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男性。
他并没有参与刚才那场狂欢,而是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自始至终都靠在吧台边,安静地抽着雪茄。此刻,他缓缓地走了过来,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移动的铁塔,投下的阴影将我和床上那个破败的她,完全笼罩。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洞悉一切的、属于更高层级玩家的戏谑,“她对你,不一样。”
“你以为你为什么还活着?”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你本来早该像一条不听话的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了。是她,主动向‘主人们’请求,把你变成了她的专属玩物,用这种方式,才让你这条小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她以为她掩饰得很好。”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刺耳,“她以为,把你变成一个听话的、离不开她的玩物,就能把那份不该有的感情,藏在调教和支配的游戏之下。可惜,她高估了自己作为‘资产’的权限。‘主人们’……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所有物,产生了不该有的、独立的思想和感情。”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份混杂着愤怒与心疼的情感,捅得千疮百孔。
原来……她对我好,是真的。
而这份真实,却成了将她推入更深地狱的、最根本的罪。
“不过,”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个堪称仁慈的、魔鬼般的微笑,“‘主人们’也并非不通情理。我们很乐意成人之美。”
他一边说,一边从吧台上端过来一个银制的托盘,轻轻地放在了我面前的地毯上。
托盘上,没有美酒,也没有佳肴。
只有密密麻麻的、足足有四五十粒的纯白色药片。它们像一盘洁白的、致命的棋子,在奢华的灯光下,反射着冰冷而圣洁的光芒。
“这是‘极乐’。”他用一种冰冷的、仿佛在陈述商品使用说明的语气介绍道,“专门为不听话的‘资产’准备的。能彻底清除掉她们脑子里那些多余的、不该有的思想,让她们变成只会淫荡地张开腿、主动索取性交的、完美的泄欲工具。”
他顿了顿,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眼神,看了一眼床上那个依旧毫无声息的她。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会把脑子彻底烧坏。你知道的,精密仪器,总是很脆弱。”
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彻底冻结了。
“今晚,她需要服下这里所有的药。”黑人男性指了指托盘,然后又伸出手指,指向房间里那十几个刚刚享用完她、此刻正像一群看戏的狼一样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同样身形高大的黑人男性,“当然,‘主人们’给了你一个拯救她的机会。”
“看到他们了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恶魔的耳语,“你去,用你的嘴,你的身体,你的全部,去取悦他们。你只要能让这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射精一次,我就从托盘里,为她拿走一粒药。”
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脸上的笑容更加残忍了。
“别高兴得太早。”他蹲下身,捡起一粒药,在我眼前晃了晃,“这东西的药效很强。一粒,就足以让她神智不清,彻底沦为只会求欢的母狗。两粒,她的大脑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变成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白痴。三粒……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有价值的资产身上,试过三粒以上的剂量。”
我呆呆地看着他,看着那一盘致命的药,看着那十几座由黑色肌肉和欲望组成的、无法逾越的山脉,又回头看了一眼床上那个破败不堪的女人。
这一刻我才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慈悲的“机会”。
这是这世上,最恶毒的诅咒。
它将那份卑微的、见不得光的爱意,血淋淋地剖开,放在了审判的天平上。而天平的另一端,是她的神智,她的未来,甚至她的生命。
我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的尊严,我的身体,我的一切。
这不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而是通往地狱更深处的、唯一的路径。
黑人男性站起身,退回阴影之中,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宣布了这场终极审判的开始。
“开始吧。”
虽然但是确实很色,不过这篇主要是雌堕为主
当然,你要是觉得从文笔来讲不适合这一章节的话,就当我没说🤓
这次更完后面还有一章尾声
【9】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
不是因为闹钟,也不是因为窗外刺眼的阳光。
而是因为一种……阔别已久的、陌生的寂静。
我躺在自己那张狭窄的出租屋单人床上,意识像一艘沉船,缓缓地从漆黑的海底上浮。我茫然地睁开眼,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每日清晨那准时到来的、被贞操锁勒紧的、因晨勃而产生的剧痛。
而是一种空荡荡的、几乎让我感到恐慌的……自由。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伸向了我的胯下。
那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冰冷的金属,没有禁锢的囚笼,没有那把悬在我灵魂之上的、属于她的锁。
我……自由了?
这个念头刚一浮现,我的大脑就“轰”的一声,仿佛被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无数破碎的、尖锐的、沾满了血与精液的画面,像爆炸的玻璃碎片,从记忆的深海中疯狂地翻涌上来,将我瞬间吞噬。
……那是一个巨大的、像宫殿一样的房间。十几座黑色的、由肌肉和欲望组成的山峦,将我团团围住,他们的眼神,像一群审视着祭品的野兽……
……我跪在柔软的波斯地毯上,人生中第一次,用我那因为恐惧而不断颤抖的嘴唇,笨拙地、屈辱地,去亲吻一个陌生男人的、还残留着汗水咸腥味的脚趾……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身后那个魔鬼般的身影,就从银盘里,又捻起了一粒白色的药片……
……“不!”我听到自己发出了绝望的嘶吼。我开始意识到,单纯的服侍是不够的。我必须……取悦他们。我开始调动我所有的、在这段时间里被雌化后训练出的本能,我的眼神变得献媚,我的腰肢变得柔软,我开始用一种我自己都感到恶心的、骚浪的姿态,去扭动我的身体,去用舌头讨好地舔舐他们的指尖……
……我的表演成功了。第一个男人,在我卖力的口交和抚弄下,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野兽般的咆哮,将他滚烫的精液,尽数灌进了我的喉咙。而那个魔鬼,也遵守了诺言,将一粒药片,丢进了垃圾桶。我看到了希望……
……但很快,我就绝望了。我的讨好,我的雌化,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原始的兽欲。他们不再满足于这种一对一的游戏。一只手,两只手,无数只手,开始在我的身上肆意抚摸,拉扯,他们像对待一个公共妓女一样,将我翻来覆去……
……然后,是后庭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剧痛。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破布,被一根烧红的铁杵,狠狠地、毫不留情地贯穿。我疼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但我不能。我看见那个魔鬼又要伸手去拿药……
……“不!求求您!操我!用您尊贵的鸡巴操我这只母狗的屁眼!”我开始用我能想到的、最下贱的语言,疯狂地乞求着,“只要您射出来!就不用让她吃药了!求求您了!狠狠地操我!”
……我的乞求,成了他们狂欢的号角。更多的、滚烫的、巨大的阳具,开始轮流地、甚至同时地,撕扯着我早已不堪重负的后穴。我感觉自己被彻底地、反复地洞穿,意识在剧痛和一种诡异的、被填满的满足感之间,反复横跳……
……在无尽的凌辱中,我看到了她。她被人扶着,靠在不远处的沙发上。她的眼神,已经恢复了一丝清明。她看着我,这个为了她,正被一群男人当做母狗一样轮奸的、卑微的学弟。
“……别管我了……”我听到她用一种近乎崩溃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对我说,“放弃吧……求你了……”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从她那张苍白的、沾满污秽的脸上,不断地滑落。
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哭。
她不是在为自己的遭遇而哭。
她是在为我。
“啊——!”
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早已一片冰凉。我分不清那是汗水,还是眼泪。
阳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下了一块安静而温暖的光斑。世界如此正常,正常到让我觉得,昨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过于真实的、荒诞的噩梦。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没有锁,没有肛塞,除了身上残留的一些可疑的痕迹,一切都好像恢复了原样。
或许……真的是梦?
就在我试图用这个理由麻痹自己的时候,一股熟悉的、尖锐的刺痛,从我的后庭深处,清晰地、蛮横地传来。
那痛感,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刻骨铭心。
它无情地提醒着我——
那不是梦。
我用我最卑贱的尊严,换回了她的神智。
而我的身体,也永远地,烙上了那场疯狂夜宴的、无法磨灭的印记。
在那之后的一周里,世界仿佛陷入了停摆。
我没有去学校,林知夏也没有联系我。那扇曾经禁锢着我的、无形的牢笼,似乎消失了。没有命令,没有任务,没有那些冰冷的、提醒我身份的刑具。我像一个被突然剪断了线的木偶,瘫软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就在我几乎要以为,我们的人生将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远离的直线,再无交集时,我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
是她发来的短信,内容简单到极致:【今晚七点,上次那家私房菜馆。】
没有称呼,没有多余的解释。
我怀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既恐惧又渴望的复杂心情,赴了这个约。
当我走进那个熟悉的、雅致的包厢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已经到了,正安静地坐在窗边。而她今天的穿着,几乎是精准地、完美地,命中了我在无数个深夜幻想中,为她描绘过的、最纯洁也最色情的模样。
那头我无比熟悉的、瀑布般的黑长直,此刻被精心打理过,柔顺地披在身后,让她整个人的气质,都显得清冷而禁欲。
一件剪裁合体的黑色校服西装外套,里面是洁白的衬衫,胸前系着一个漂亮的红色格子领结。下身是一条同款的红色格子短裙,裙摆整齐地搭在她的膝上。
而她的腿上,则是一双崭新的白丝小腿袜,搭配着一双似乎从来没见她穿过的、棕色的Haruta小皮鞋,似乎还带着崭新皮革的味道。
她就像一个刚刚放学的、家教极好的贵族女校优等生,干净、清纯,不染一丝尘埃。
我敢肯定,我从未见过她穿这一身。
那双白丝小腿袜,纤维在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没有一丝褶皱,也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那双棕色小皮鞋,鞋头没有任何皮革的褶皱,光亮得可以倒映出窗外的光。
这不是她那些在被主人们“享用”时穿着的、脚尖发黄的、事后被无数劣等男人舔舐过的“工作袜”;
也不是那双早已沾染了无数劣等精斑与舌尖唾液痕迹、带着无法彻底洗净的淫靡气息的“工作鞋”。
此刻的它们,干净、笔挺、崭新得不带任何过去的影子,像是从尘世之外专程送来的礼物。
所有的一切都崭新得不带一丝褶皱,这让我无法不产生一个荒唐却又甜蜜的念头——这份纯洁,这身未被任何人见过的、崭新的装扮,是她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身干净、纯情的装扮,却让我的后穴,不受控制地、条件反射般地,传来了一阵熟悉的、空虚的悸动。
那顿饭,我们吃得异常沉默。
服务员每一次进来上菜,都像一个尽职的报时鸟,用碗碟碰撞的清脆声响,提醒着我们时间的流逝。
而我们之间,除了沉默,就只剩下一种太过正常的“正常”。
没有了之前那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没有了那种施舍般的宠溺,更没有了那种不容置喙的命令。她只是安静地吃着饭,偶尔会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眼神看我一眼,然后迅速移开。
那眼神里,有愧疚,有感激,有怜悯,甚至还有一丝……我不敢深究的、平等且温柔的情愫。
这种平等,比之前任何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都更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像一个习惯了被锁链拴着的囚犯,在锁链被解开之后,反而不知道该如何走路。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她说话。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由那个地狱般的夜晚所凝固成的、巨大的鸿沟。
终于,在最后一道甜品被撤下之后,她开了口。
“对不起。”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和颤抖。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她。
“也……谢谢你。”她没有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深沉的夜色上,仿佛在对着整个世界,说出这句迟来的、份量重如山岳的感谢。
说完这两句话,她便重新陷入了沉默。
但这两句话,已经足够了。
它们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扇早已锈死的、名为“希望”的大门。
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我们之间,真的有了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一种不再是主人与玩物、支配与服从的、真正平等的可能性。
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爱”的可能性。
就在我沉浸在那份突如其来的、几乎要将我溺毙的“可能性”中时,她再次开口,说出了一句让我灵魂都为之震颤的话。
“做我男朋友吧。”
她的声音依旧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在我死寂的心海里,炸开了万丈狂澜。
我完全呆住了,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思维能力的傻子,只是怔怔地看着她。大脑因为这句过于跳跃的话而彻底宕机,无数的疑问、惊恐、狂喜和自卑,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堵住了我的喉咙。
我……配吗?
一个被她当做玩物调教了那么久的奴隶,一个用最卑贱的方式出卖了自己身体和尊严的妓男,一个……在不久前还跪在她脚下、连呼吸都要看她脸色的存在……我,配做她的男朋友吗?
我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些代表着我所有不堪过往的、羞耻的记忆,像无数条毒蛇,死死地缠绕着我的声带。
她似乎看穿了我所有的挣扎和自卑。她没有给我时间去犹豫,去退缩。她只是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第一次,在那晚之后,真正地、笔直地,望进了我的眼睛里。
那双曾盛满了冰冷、支配、欲望和痛苦的眸子,此刻,只剩下一种澄澈的、不容置疑的认真。
“别问为什么,也别想配不配。”她打断了我所有未出口的、愚蠢的自我否定,“我只问你,想,还是不想。”
一个字,是生与死的边界。
一个字,是天堂与地狱的分野。
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我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能感觉到血液在血管里疯狂地奔涌。我的脑海里,闪过了我们之间所有的画面——实验室里初见的惊艳,桌底下卑劣的窥探,她脚下屈辱的臣服,被她支配的狂喜,以及……那个地狱之夜里,她为我流下的、那滴滚烫的眼泪。
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欢愉,所有的自卑,所有的爱慕,最终,都汇聚成了一个字。
“……想。”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却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破釜沉舟般的坚定。
听到我这个字的瞬间,她那一直紧绷的、完美的优等生面具,终于彻底地、无可挽回地,碎裂了。
一抹极淡的、却又真实无比的、如释重负的微笑,从她的嘴角,缓缓地漾开。那微笑,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动人。
“我一直都觉得,你很优秀。”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的鼻音,“你努力,善良,你也是唯一一个,会真心待我的人。”
她没有提那个地狱般的夜晚,没有提我是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去拯救她。
但答案,已经全部写在了她的眼神里。
我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回过无数个画面。
那些我还不知道她真面目的日子里,作为她最忠诚的学弟,我曾如何拼尽全力,只想为她分忧。
深夜的实验室里,看到她因为一个棘手的算法而疲惫不堪,我会通宵查阅资料,第二天早上将一份整理好的笔记和一杯热好的牛奶,悄悄放在她的桌上。
项目交付前,因为数据不理想,她在实验室大发雷霆,是我默默地重新跑了一遍所有的模型,找到了那个被忽略的异常值,替她解了围。
……
这么多年,我一点一滴的关心和照顾,她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她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独一无二的珍宝。
我突然从模糊的记忆中,回想起那晚黑人的话。
“你以为你为什么还活着?”
“你本来早该像一条不听话的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了。”
“是她,主动向‘主人们’请求……才让你这条小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
直到此刻我才终于懂得。
她当初那份决绝的拒绝,并非因为不爱,而是源于一种更深沉、更绝望的保护。
她害怕我接受不了这样活在泥沼里的她,害怕她世界的污浊,会玷污我这个在她眼中还干净、还纯粹的学弟。
她本不想破坏在我眼中那纯洁美好的形象。
所以她推开我,用冷漠武装自己。
直到我的存在碍了别人的眼,即将被除掉的时候,她才退无可退。
为了保全我,她只能选择用最极端、最羞辱的方式,诱惑我,毁掉我,然后重新塑造成只属于她的形状。
她亲手将我从一个仰慕者,变成一件匍匐在她脚边的玩物,用我的臣服与屈辱,为我打造了一座最安全、也最变态的囚笼。
这既是救赎,也是一场豪赌。
她想看看,当她不堪的真面目彻底暴露时,我会如何选择,同时也给了她一个机会,让我见识到她内心那扭曲的黑暗。
而我,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兴奋地、战栗地,将自己内心深处那同样扭曲、同样渴望被支配的黑暗,彻底释放了出来。
我们是同一类人,天生就该在黑暗中彼此纠缠。
那一刻我才明白,在那场漫长的、扭曲的游戏里,沦陷的,从来都不止我一个。
她也是。
就在我沉浸在这份来之不易的、几乎不真实的幸福感中时,她却轻轻地摇了摇头,将我从幻想中拉回了残酷的现实。
“但是,”她脸上的笑意敛去,眼神重新变得清醒而锐利,“我必须让你做出选择。”
她将两只手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近乎谈判的、无比严肃的姿态看着我。
“第一条路,”她说,“如果你不愿意再回到过去,那么,从今天起,我就彻底放弃我所有的‘爱好’。我会和‘那边’断绝一切联系,处理掉所有其他的‘玩物’。”
“我不再是女王,你也不再是奴隶。我们就像一对最普通的校园情侣,一起上课,一起毕业,一起过最正常的生活。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女朋友。”
她说到“正常的生活”时,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在说一个遥远国度般的陌生感。
我能听出她话里的决绝。她是在告诉我,为了我,她愿意放弃那个充满权力与欲望的黑暗帝国。她愿意为了我,从一个女王,变回一个普通的女人。
这份承诺的份量,几乎让我窒息。
“第二条路……”她顿了顿,眼神变得幽深而复杂,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支配我一切的女王,“如果你……还想回到之前的样子。那么,除了你是我的男朋友这个身份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我灵魂最深处、那块名为“M属性”的烙印上。
“其他劣等男性,如果表现得好,或许还有被我打开锁,作为奖赏,得到一次卑微释放的资格。”
“而你,没有。”
“你将永远不配用你自己的肉棒射精。你的囚笼,将是你爱我的勋章,是你作为我唯一‘男朋友’的、永恒的誓约。你将永远被我锁住,被我填满,成为我最忠诚的、也是最卑贱的奴隶。”
“而且,”她补充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残忍,“我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事业’和‘欲望’。你依旧要在某些夜晚,等着我,等着我从别的男人的床上下来,再去用你的身体,来‘伺候’我。”
说到这里,她的眼神,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几乎是邪恶的变化。
她就像一个披着圣女外衣的魅魔,用最无辜的姿态,低语着最堕落的邀请。
“甚至,”她舔了舔自己那漂亮的、涂着蔻丹的嘴唇,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病态的期待,“在那天晚上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又多了一个新的‘爱好’。”
“你的忍耐度,似乎超出了我的期待。”
“我发现,我好像……很喜欢看你被他们操的样子。”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像魔鬼的耳语,却又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属于女性的、最原始的兴奋。
她那头瀑布般的、柔顺的黑长直,此刻正安静地垂在她的肩头,几缕发丝滑落下来,半遮住她那张本该是清纯禁欲的、优等生的脸。
这副纯洁的、仿佛不染尘埃的外表,与她此刻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粘稠而病态的欲望,形成了最惊心动魄的反差。
“我喜欢看你那张漂亮的脸,因为被那些巨大的、属于黑人的东西贯穿,而露出混杂着痛苦和极致快感的、淫荡的表情。我喜欢听你用那种雌堕的、哭泣般的腔调,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求着他们,操得你更深一点。”
“你不知道,你那个样子,有多迷人。”
“我曾经以为,”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般的、迷离的追忆,“我最享受的是支配你,是用那根模仿主人尺寸的黑色假阳具,把你操到哭泣求饶。”
“但那天晚上之后,我才发现,我错了。我见识到了一种……我永远无法拥有的力量。那种只属于真正雄性的绝对力量,是任何精巧的玩具都无法模仿的真实,也是我作为女性,永远无法给予你的东西。”
“所以,”她看着我,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属于她最深层性癖的邀请,“如果你选择这条路,你将不再仅仅是我的‘专属玩物’。你还将成为我服侍‘主人们’的同伴,我最好的姐妹。”
“你会和我一起,跪在他们面前。你会和我一起,被他们使用。你会亲眼看着我,被他们弄得死去活来。然后,你再用你那张漂亮的、沾满了他们精液的脸,来亲吻我,来告诉我,你有多爱我。”
我的喉咙一阵发干,一个我无法控制的问题,脱口而出:“他们……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回去?”
我无法理解,在经历了那样惨无人道的轮奸之后,在经历了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后,她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地狱。
听到我的问题,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种混合着野心、欲望和一丝无奈的、复杂的表情。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我。”她说得直白而坦诚,“无论是我的野心,还是我的欲望。”
“我的科研,我的事业,我所有想在这个世界上达成的目标,都需要借助他们背后的、庞大的资源和权力。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够企及的高度。我需要他们,做我的踏脚石。”
“同样的……”她的眼神变得迷离,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属于暗夜的、情欲的沙哑,“我的身体,也需要他们。只有他们那种尺寸的、属于征服者的阳具,才配进入我的身体,才能真正地、填满我的空虚。其他的劣等男性……不配,也根本无法满足我。”
“哪怕你,也一样。”
她毫不避讳地,向我袒露了她那根植于灵魂深处的、对强大黑人男性的性癖。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她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近乎于哲学家的、冰冷的狂热,“我为什么要调教你们这些劣等的男性,为什么要给你们戴上贞操锁?”
“因为你们不配。”
她一字一顿,像是在宣判,“你们那可笑的尺寸、那软弱无力的硬度、那稀薄污浊的精子……你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劣质基因的产物。那样的东西,根本不配进入我,更何况是在我的身体里留下后代。”
“被锁住,被调教,都只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废物,认清自己的位置。”
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是女王,但她也渴望被更强者征服。而我,以及其他无数的男性,在她眼中,都只是不配进入她身体的、只能用来玩弄的“劣等男性”。
说完这番话,她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看着我脸上那因为极致的顺从而显得有些空洞的表情,她眼中的侵略感慢慢褪去,第一次浮现出了一丝心疼。
“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重了?”她的声音里,不再有女王的威严,反而带着一丝害怕伤害到我的、小心翼翼的温度。
她似乎终于意识到,在我说出那个“想”之后,她再也不需要在我面前戴上那冰冷的面具。
“宝宝,”她凝视着我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道,“不论你怎么选,你都是我的男朋友。你都是我的唯一。”
“而且,请相信我,”她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我从未见过的、森然而又决绝的冷笑,“他们带给你,带给我的所有痛苦和屈辱,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千倍百倍地,偿还回来。”
那句话里,蕴含着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庞大的谋划和决心。我这才隐约明白,她不仅仅是在沉沦,更是在蛰伏。她在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去编织一张巨大而又致命的网。
她,在与魔鬼共舞。
两条路,泾渭分明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一条,是通往阳光下的、正常人的爱情。但那也意味着,我将永远失去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王,只能拥有一个“普通”的林知夏。
另一条,是回到阴影下的、扭曲的主奴关系。我将永远作为她最卑贱的玩物存在,甚至要忍受她属于别的男人的事实。但同时,我也能永远地,拥有那个独一无二的、支配我一切的、真正的女王。
我的沉默,似乎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没有催促,也没有逼迫。她只是缓缓地从我对面起身,裙摆在地板上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然后,在我的注视下,她走到了我的身边,轻轻地坐下。
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一张桌子的宽度,缩短到了零。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混杂着高级香水和她自身体香的、令人心悸的气息。
她转过头,那双漂亮的眼睛,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映着星光的湖水,静静地凝视着我。
似乎是为了弥补刚才对我的冰冷,她做了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动作。
她的手,那只曾用最羞辱的方式检查过我身体、也曾用最温柔的姿态抚摸过我头发的手,此刻,却带着一种属于女朋友的亲昵,探入了我的裤裆。
没有了冰冷的囚笼,她的手指第一次,毫无阻碍地,触碰到了我那因为紧张和激动而早已苏醒的、滚烫的肉体。她的指尖很凉,像上好的羊脂白玉,与我皮肤接触的瞬间,激起了一阵让我灵魂都为之战栗的电流。
我浑身一颤,像被电流击中。
她没有丝毫的犹豫。她的手指,像一把最精密的、带着绝对控制权的卡尺,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圈住了我最敏感的冠状沟。不带任何情欲,却又充满了极致的诱惑。
“给出你的答案。”
她的声音,像魔鬼的耳语,贴着我的嘴唇响起。
下一秒,她吻住了我。
那是一个真实的、柔软的、带着她唇上甜美气息的吻。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支配和命令,这是一个平等的、属于恋人之间的吻
“轰——!”
我的大脑,彻底炸成了一片绚烂的、幸福的空白。
那一瞬间,我大脑中所有名为“理智”的弦,尽数崩断。
幸福感,混合着最原始的性欲,像一场积蓄了百年的火山,轰然爆发。我梦寐以求的、连在最疯狂的春梦里都不敢奢望的场景,此刻,正以一种比梦境更不真实的方式,成为了现实。
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思考。我的下体,再也无法抑制地,在她那象征着禁锢与许可的手指圈中,疯狂地、本能地,开始前后抽插。
我渴望着,我祈求着,我像一个即将渴死的旅人,疯狂地想要在她这里,得到那最终极的、也是我唯一渴望的甘露。
这个我幻想了无数次、连在梦里都不敢奢求的场景,竟然变成了现实!她吻着我,她的手握着我,她给了我选择……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爱情吗?
没有锁,没有肛塞,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命令。只有我和她,像一对最普通的情侣,进行着最亲密的接触。
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圈着我的那只手,没有像以前用小腿夹住我时那样,随着我的抽动而越来越松。她的手指,依旧坚定地、有力地环绕着我,像是一种纵容,一种充满爱意的默许,一种无声的邀请,邀请我冲破禁锢,邀请我……射精。
幸福感和性欲,像两股交缠的、毁灭性的海啸,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防线。我几乎就要在她的手中、她的吻中,将我所有的爱意和欲望,尽数喷薄而出。
但是……
但是……
一幅幅画面,不受控制地,在我那被欲望烧得滚烫的脑海里,疯狂地回荡。
是那个深夜实验室里,她用冰冷的声音命令我“跪下”时,那高高在上的、女王般的侧脸。
是那个阳光午后,她用穿着白丝袜的脚尖,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时,那带着一丝戏谑的、残忍的微笑。
是那个地狱之夜,她被无数黑人轮奸后,像破碎的娃娃一样躺在床上时,那空洞的、失去一切光芒的眼神。
以及……她为了我,流下的那滴眼泪。
我忽然意识到……
我喜欢的,我爱着的,早已不是那个最初幻想中、遥不可及的、纯洁的女神了。
我喜欢的,是那个有野心、有欲望、甚至会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的、真实的她。
我喜欢的,是那个会高高在上、也会遍体鳞伤,会冰冷残忍、也会为我流泪的,完整的、独一无二的……林知夏。
我不能让她为了我,放弃那个真实的、完整的自己。
我更不能……让我自己,失去那个我真正爱着的、独一无二的女王。
我想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女朋友。
我想要的,是我的女王。是我的主人。是那个……会亲手为我锁上贞操锁的、独一无二的她。
那根在她指圈里疯狂抽插的肉棒,在即将达到高潮的、最顶点的瞬间,像是被施了最恶毒的咒语,缓缓地,一寸一寸地,慢了下来。
最终,在距离那扇名为“释放”的大门仅一步之遥时,它彻底停下——
带着无法泯灭的渴望、绝望的留恋,以及……甘之如饴的臣服。
寸止。
我用最卑微的、也最虔诚的方式,给出了我的答案。
我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
她笑了。
【9】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
不是因为闹钟,也不是因为窗外刺眼的阳光。
而是因为一种……阔别已久的、陌生的寂静。
我躺在自己那张狭窄的出租屋单人床上,意识像一艘沉船,缓缓地从漆黑的海底上浮。我茫然地睁开眼,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每日清晨那准时到来的、被贞操锁勒紧的、因晨勃而产生的剧痛。
而是一种空荡荡的、几乎让我感到恐慌的……自由。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伸向了我的胯下。
那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冰冷的金属,没有禁锢的囚笼,没有那把悬在我灵魂之上的、属于她的锁。
我……自由了?
这个念头刚一浮现,我的大脑就“轰”的一声,仿佛被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无数破碎的、尖锐的、沾满了血与精液的画面,像爆炸的玻璃碎片,从记忆的深海中疯狂地翻涌上来,将我瞬间吞噬。
……那是一个巨大的、像宫殿一样的房间。十几座黑色的、由肌肉和欲望组成的山峦,将我团团围住,他们的眼神,像一群审视着祭品的野兽……
……我跪在柔软的波斯地毯上,人生中第一次,用我那因为恐惧而不断颤抖的嘴唇,笨拙地、屈辱地,去亲吻一个陌生男人的、还残留着汗水咸腥味的脚趾……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身后那个魔鬼般的身影,就从银盘里,又捻起了一粒白色的药片……
……“不!”我听到自己发出了绝望的嘶吼。我开始意识到,单纯的服侍是不够的。我必须……取悦他们。我开始调动我所有的、在这段时间里被雌化后训练出的本能,我的眼神变得献媚,我的腰肢变得柔软,我开始用一种我自己都感到恶心的、骚浪的姿态,去扭动我的身体,去用舌头讨好地舔舐他们的指尖……
……我的表演成功了。第一个男人,在我卖力的口交和抚弄下,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野兽般的咆哮,将他滚烫的精液,尽数灌进了我的喉咙。而那个魔鬼,也遵守了诺言,将一粒药片,丢进了垃圾桶。我看到了希望……
……但很快,我就绝望了。我的讨好,我的雌化,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原始的兽欲。他们不再满足于这种一对一的游戏。一只手,两只手,无数只手,开始在我的身上肆意抚摸,拉扯,他们像对待一个公共妓女一样,将我翻来覆去……
……然后,是后庭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剧痛。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破布,被一根烧红的铁杵,狠狠地、毫不留情地贯穿。我疼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但我不能。我看见那个魔鬼又要伸手去拿药……
……“不!求求您!操我!用您尊贵的鸡巴操我这只母狗的屁眼!”我开始用我能想到的、最下贱的语言,疯狂地乞求着,“只要您射出来!就不用让她吃药了!求求您了!狠狠地操我!”
……我的乞求,成了他们狂欢的号角。更多的、滚烫的、巨大的阳具,开始轮流地、甚至同时地,撕扯着我早已不堪重负的后穴。我感觉自己被彻底地、反复地洞穿,意识在剧痛和一种诡异的、被填满的满足感之间,反复横跳……
……在无尽的凌辱中,我看到了她。她被人扶着,靠在不远处的沙发上。她的眼神,已经恢复了一丝清明。她看着我,这个为了她,正被一群男人当做母狗一样轮奸的、卑微的学弟。
“……别管我了……”我听到她用一种近乎崩溃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对我说,“放弃吧……求你了……”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从她那张苍白的、沾满污秽的脸上,不断地滑落。
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哭。
她不是在为自己的遭遇而哭。
她是在为我。
“啊——!”
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早已一片冰凉。我分不清那是汗水,还是眼泪。
阳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下了一块安静而温暖的光斑。世界如此正常,正常到让我觉得,昨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过于真实的、荒诞的噩梦。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没有锁,没有肛塞,除了身上残留的一些可疑的痕迹,一切都好像恢复了原样。
或许……真的是梦?
就在我试图用这个理由麻痹自己的时候,一股熟悉的、尖锐的刺痛,从我的后庭深处,清晰地、蛮横地传来。
那痛感,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刻骨铭心。
它无情地提醒着我——
那不是梦。
我用我最卑贱的尊严,换回了她的神智。
而我的身体,也永远地,烙上了那场疯狂夜宴的、无法磨灭的印记。
在那之后的一周里,世界仿佛陷入了停摆。
我没有去学校,林知夏也没有联系我。那扇曾经禁锢着我的、无形的牢笼,似乎消失了。没有命令,没有任务,没有那些冰冷的、提醒我身份的刑具。我像一个被突然剪断了线的木偶,瘫软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就在我几乎要以为,我们的人生将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远离的直线,再无交集时,我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
是她发来的短信,内容简单到极致:【今晚七点,上次那家私房菜馆。】
没有称呼,没有多余的解释。
我怀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既恐惧又渴望的复杂心情,赴了这个约。
当我走进那个熟悉的、雅致的包厢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已经到了,正安静地坐在窗边。而她今天的穿着,几乎是精准地、完美地,命中了我在无数个深夜幻想中,为她描绘过的、最纯洁也最色情的模样。
那头我无比熟悉的、瀑布般的黑长直,此刻被精心打理过,柔顺地披在身后,让她整个人的气质,都显得清冷而禁欲。
一件剪裁合体的黑色校服西装外套,里面是洁白的衬衫,胸前系着一个漂亮的红色格子领结。下身是一条同款的红色格子短裙,裙摆整齐地搭在她的膝上。
而她的腿上,则是一双崭新的白丝小腿袜,搭配着一双似乎从来没见她穿过的、棕色的Haruta小皮鞋,似乎还带着崭新皮革的味道。
她就像一个刚刚放学的、家教极好的贵族女校优等生,干净、清纯,不染一丝尘埃。
我敢肯定,我从未见过她穿这一身。
那双白丝小腿袜,纤维在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没有一丝褶皱,也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那双棕色小皮鞋,鞋头没有任何皮革的褶皱,光亮得可以倒映出窗外的光。
这不是她那些在被主人们“享用”时穿着的、脚尖发黄的、事后被无数劣等男人舔舐过的“工作袜”;
也不是那双早已沾染了无数劣等精斑与舌尖唾液痕迹、带着无法彻底洗净的淫靡气息的“工作鞋”。
此刻的它们,干净、笔挺、崭新得不带任何过去的影子,像是从尘世之外专程送来的礼物。
所有的一切都崭新得不带一丝褶皱,这让我无法不产生一个荒唐却又甜蜜的念头——这份纯洁,这身未被任何人见过的、崭新的装扮,是她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身干净、纯情的装扮,却让我的后穴,不受控制地、条件反射般地,传来了一阵熟悉的、空虚的悸动。
那顿饭,我们吃得异常沉默。
服务员每一次进来上菜,都像一个尽职的报时鸟,用碗碟碰撞的清脆声响,提醒着我们时间的流逝。
而我们之间,除了沉默,就只剩下一种太过正常的“正常”。
没有了之前那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没有了那种施舍般的宠溺,更没有了那种不容置喙的命令。她只是安静地吃着饭,偶尔会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眼神看我一眼,然后迅速移开。
那眼神里,有愧疚,有感激,有怜悯,甚至还有一丝……我不敢深究的、平等且温柔的情愫。
这种平等,比之前任何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都更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像一个习惯了被锁链拴着的囚犯,在锁链被解开之后,反而不知道该如何走路。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她说话。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由那个地狱般的夜晚所凝固成的、巨大的鸿沟。
终于,在最后一道甜品被撤下之后,她开了口。
“对不起。”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和颤抖。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她。
“也……谢谢你。”她没有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深沉的夜色上,仿佛在对着整个世界,说出这句迟来的、份量重如山岳的感谢。
说完这两句话,她便重新陷入了沉默。
但这两句话,已经足够了。
它们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扇早已锈死的、名为“希望”的大门。
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我们之间,真的有了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一种不再是主人与玩物、支配与服从的、真正平等的可能性。
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爱”的可能性。
就在我沉浸在那份突如其来的、几乎要将我溺毙的“可能性”中时,她再次开口,说出了一句让我灵魂都为之震颤的话。
“做我男朋友吧。”
她的声音依旧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在我死寂的心海里,炸开了万丈狂澜。
我完全呆住了,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思维能力的傻子,只是怔怔地看着她。大脑因为这句过于跳跃的话而彻底宕机,无数的疑问、惊恐、狂喜和自卑,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堵住了我的喉咙。
我……配吗?
一个被她当做玩物调教了那么久的奴隶,一个用最卑贱的方式出卖了自己身体和尊严的妓男,一个……在不久前还跪在她脚下、连呼吸都要看她脸色的存在……我,配做她的男朋友吗?
我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些代表着我所有不堪过往的、羞耻的记忆,像无数条毒蛇,死死地缠绕着我的声带。
她似乎看穿了我所有的挣扎和自卑。她没有给我时间去犹豫,去退缩。她只是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第一次,在那晚之后,真正地、笔直地,望进了我的眼睛里。
那双曾盛满了冰冷、支配、欲望和痛苦的眸子,此刻,只剩下一种澄澈的、不容置疑的认真。
“别问为什么,也别想配不配。”她打断了我所有未出口的、愚蠢的自我否定,“我只问你,想,还是不想。”
一个字,是生与死的边界。
一个字,是天堂与地狱的分野。
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我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能感觉到血液在血管里疯狂地奔涌。我的脑海里,闪过了我们之间所有的画面——实验室里初见的惊艳,桌底下卑劣的窥探,她脚下屈辱的臣服,被她支配的狂喜,以及……那个地狱之夜里,她为我流下的、那滴滚烫的眼泪。
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欢愉,所有的自卑,所有的爱慕,最终,都汇聚成了一个字。
“……想。”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却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破釜沉舟般的坚定。
听到我这个字的瞬间,她那一直紧绷的、完美的优等生面具,终于彻底地、无可挽回地,碎裂了。
一抹极淡的、却又真实无比的、如释重负的微笑,从她的嘴角,缓缓地漾开。那微笑,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动人。
“我一直都觉得,你很优秀。”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的鼻音,“你努力,善良,你也是唯一一个,会真心待我的人。”
她没有提那个地狱般的夜晚,没有提我是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去拯救她。
但答案,已经全部写在了她的眼神里。
我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回过无数个画面。
那些我还不知道她真面目的日子里,作为她最忠诚的学弟,我曾如何拼尽全力,只想为她分忧。
深夜的实验室里,看到她因为一个棘手的算法而疲惫不堪,我会通宵查阅资料,第二天早上将一份整理好的笔记和一杯热好的牛奶,悄悄放在她的桌上。
项目交付前,因为数据不理想,她在实验室大发雷霆,是我默默地重新跑了一遍所有的模型,找到了那个被忽略的异常值,替她解了围。
……
这么多年,我一点一滴的关心和照顾,她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她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独一无二的珍宝。
我突然从模糊的记忆中,回想起那晚黑人的话。
“你以为你为什么还活着?”
“你本来早该像一条不听话的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了。”
“是她,主动向‘主人们’请求……才让你这条小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
直到此刻我才终于懂得。
她当初那份决绝的拒绝,并非因为不爱,而是源于一种更深沉、更绝望的保护。
她害怕我接受不了这样活在泥沼里的她,害怕她世界的污浊,会玷污我这个在她眼中还干净、还纯粹的学弟。
她本不想破坏在我眼中那纯洁美好的形象。
所以她推开我,用冷漠武装自己。
直到我的存在碍了别人的眼,即将被除掉的时候,她才退无可退。
为了保全我,她只能选择用最极端、最羞辱的方式,诱惑我,毁掉我,然后重新塑造成只属于她的形状。
她亲手将我从一个仰慕者,变成一件匍匐在她脚边的玩物,用我的臣服与屈辱,为我打造了一座最安全、也最变态的囚笼。
这既是救赎,也是一场豪赌。
她想看看,当她不堪的真面目彻底暴露时,我会如何选择,同时也给了她一个机会,让我见识到她内心那扭曲的黑暗。
而我,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兴奋地、战栗地,将自己内心深处那同样扭曲、同样渴望被支配的黑暗,彻底释放了出来。
我们是同一类人,天生就该在黑暗中彼此纠缠。
那一刻我才明白,在那场漫长的、扭曲的游戏里,沦陷的,从来都不止我一个。
她也是。
就在我沉浸在这份来之不易的、几乎不真实的幸福感中时,她却轻轻地摇了摇头,将我从幻想中拉回了残酷的现实。
“但是,”她脸上的笑意敛去,眼神重新变得清醒而锐利,“我必须让你做出选择。”
她将两只手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近乎谈判的、无比严肃的姿态看着我。
“第一条路,”她说,“如果你不愿意再回到过去,那么,从今天起,我就彻底放弃我所有的‘爱好’。我会和‘那边’断绝一切联系,处理掉所有其他的‘玩物’。”
“我不再是女王,你也不再是奴隶。我们就像一对最普通的校园情侣,一起上课,一起毕业,一起过最正常的生活。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女朋友。”
她说到“正常的生活”时,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在说一个遥远国度般的陌生感。
我能听出她话里的决绝。她是在告诉我,为了我,她愿意放弃那个充满权力与欲望的黑暗帝国。她愿意为了我,从一个女王,变回一个普通的女人。
这份承诺的份量,几乎让我窒息。
“第二条路……”她顿了顿,眼神变得幽深而复杂,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支配我一切的女王,“如果你……还想回到之前的样子。那么,除了你是我的男朋友这个身份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我灵魂最深处、那块名为“M属性”的烙印上。
“其他劣等男性,如果表现得好,或许还有被我打开锁,作为奖赏,得到一次卑微释放的资格。”
“而你,没有。”
“你将永远不配用你自己的肉棒射精。你的囚笼,将是你爱我的勋章,是你作为我唯一‘男朋友’的、永恒的誓约。你将永远被我锁住,被我填满,成为我最忠诚的、也是最卑贱的奴隶。”
“而且,”她补充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残忍,“我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事业’和‘欲望’。你依旧要在某些夜晚,等着我,等着我从别的男人的床上下来,再去用你的身体,来‘伺候’我。”
说到这里,她的眼神,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几乎是邪恶的变化。
她就像一个披着圣女外衣的魅魔,用最无辜的姿态,低语着最堕落的邀请。
“甚至,”她舔了舔自己那漂亮的、涂着蔻丹的嘴唇,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病态的期待,“在那天晚上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又多了一个新的‘爱好’。”
“你的忍耐度,似乎超出了我的期待。”
“我发现,我好像……很喜欢看你被他们操的样子。”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像魔鬼的耳语,却又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属于女性的、最原始的兴奋。
她那头瀑布般的、柔顺的黑长直,此刻正安静地垂在她的肩头,几缕发丝滑落下来,半遮住她那张本该是清纯禁欲的、优等生的脸。
这副纯洁的、仿佛不染尘埃的外表,与她此刻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粘稠而病态的欲望,形成了最惊心动魄的反差。
“我喜欢看你那张漂亮的脸,因为被那些巨大的、属于黑人的东西贯穿,而露出混杂着痛苦和极致快感的、淫荡的表情。我喜欢听你用那种雌堕的、哭泣般的腔调,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求着他们,操得你更深一点。”
“你不知道,你那个样子,有多迷人。”
“我曾经以为,”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般的、迷离的追忆,“我最享受的是支配你,是用那根模仿主人尺寸的黑色假阳具,把你操到哭泣求饶。”
“但那天晚上之后,我才发现,我错了。我见识到了一种……我永远无法拥有的力量。那种只属于真正雄性的绝对力量,是任何精巧的玩具都无法模仿的真实,也是我作为女性,永远无法给予你的东西。”
“所以,”她看着我,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属于她最深层性癖的邀请,“如果你选择这条路,你将不再仅仅是我的‘专属玩物’。你还将成为我服侍‘主人们’的同伴,我最好的姐妹。”
“你会和我一起,跪在他们面前。你会和我一起,被他们使用。你会亲眼看着我,被他们弄得死去活来。然后,你再用你那张漂亮的、沾满了他们精液的脸,来亲吻我,来告诉我,你有多爱我。”
我的喉咙一阵发干,一个我无法控制的问题,脱口而出:“他们……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回去?”
我无法理解,在经历了那样惨无人道的轮奸之后,在经历了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后,她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地狱。
听到我的问题,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种混合着野心、欲望和一丝无奈的、复杂的表情。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我。”她说得直白而坦诚,“无论是我的野心,还是我的欲望。”
“我的科研,我的事业,我所有想在这个世界上达成的目标,都需要借助他们背后的、庞大的资源和权力。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够企及的高度。我需要他们,做我的踏脚石。”
“同样的……”她的眼神变得迷离,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属于暗夜的、情欲的沙哑,“我的身体,也需要他们。只有他们那种尺寸的、属于征服者的阳具,才配进入我的身体,才能真正地、填满我的空虚。其他的劣等男性……不配,也根本无法满足我。”
“哪怕你,也一样。”
她毫不避讳地,向我袒露了她那根植于灵魂深处的、对强大黑人男性的性癖。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她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近乎于哲学家的、冰冷的狂热,“我为什么要调教你们这些劣等的男性,为什么要给你们戴上贞操锁?”
“因为你们不配。”
她一字一顿,像是在宣判,“你们那可笑的尺寸、那软弱无力的硬度、那稀薄污浊的精子……你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劣质基因的产物。那样的东西,根本不配进入我,更何况是在我的身体里留下后代。”
“被锁住,被调教,都只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废物,认清自己的位置。”
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是女王,但她也渴望被更强者征服。而我,以及其他无数的男性,在她眼中,都只是不配进入她身体的、只能用来玩弄的“劣等男性”。
说完这番话,她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看着我脸上那因为极致的顺从而显得有些空洞的表情,她眼中的侵略感慢慢褪去,第一次浮现出了一丝心疼。
“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重了?”她的声音里,不再有女王的威严,反而带着一丝害怕伤害到我的、小心翼翼的温度。
她似乎终于意识到,在我说出那个“想”之后,她再也不需要在我面前戴上那冰冷的面具。
“宝宝,”她凝视着我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道,“不论你怎么选,你都是我的男朋友。你都是我的唯一。”
“而且,请相信我,”她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我从未见过的、森然而又决绝的冷笑,“他们带给你,带给我的所有痛苦和屈辱,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千倍百倍地,偿还回来。”
那句话里,蕴含着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庞大的谋划和决心。我这才隐约明白,她不仅仅是在沉沦,更是在蛰伏。她在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去编织一张巨大而又致命的网。
她,在与魔鬼共舞。
两条路,泾渭分明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一条,是通往阳光下的、正常人的爱情。但那也意味着,我将永远失去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王,只能拥有一个“普通”的林知夏。
另一条,是回到阴影下的、扭曲的主奴关系。我将永远作为她最卑贱的玩物存在,甚至要忍受她属于别的男人的事实。但同时,我也能永远地,拥有那个独一无二的、支配我一切的、真正的女王。
我的沉默,似乎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没有催促,也没有逼迫。她只是缓缓地从我对面起身,裙摆在地板上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然后,在我的注视下,她走到了我的身边,轻轻地坐下。
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一张桌子的宽度,缩短到了零。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混杂着高级香水和她自身体香的、令人心悸的气息。
她转过头,那双漂亮的眼睛,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映着星光的湖水,静静地凝视着我。
似乎是为了弥补刚才对我的冰冷,她做了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动作。
她的手,那只曾用最羞辱的方式检查过我身体、也曾用最温柔的姿态抚摸过我头发的手,此刻,却带着一种属于女朋友的亲昵,探入了我的裤裆。
没有了冰冷的囚笼,她的手指第一次,毫无阻碍地,触碰到了我那因为紧张和激动而早已苏醒的、滚烫的肉体。她的指尖很凉,像上好的羊脂白玉,与我皮肤接触的瞬间,激起了一阵让我灵魂都为之战栗的电流。
我浑身一颤,像被电流击中。
她没有丝毫的犹豫。她的手指,像一把最精密的、带着绝对控制权的卡尺,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圈住了我最敏感的冠状沟。不带任何情欲,却又充满了极致的诱惑。
“给出你的答案。”
她的声音,像魔鬼的耳语,贴着我的嘴唇响起。
下一秒,她吻住了我。
那是一个真实的、柔软的、带着她唇上甜美气息的吻。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支配和命令,这是一个平等的、属于恋人之间的吻
“轰——!”
我的大脑,彻底炸成了一片绚烂的、幸福的空白。
那一瞬间,我大脑中所有名为“理智”的弦,尽数崩断。
幸福感,混合着最原始的性欲,像一场积蓄了百年的火山,轰然爆发。我梦寐以求的、连在最疯狂的春梦里都不敢奢望的场景,此刻,正以一种比梦境更不真实的方式,成为了现实。
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思考。我的下体,再也无法抑制地,在她那象征着禁锢与许可的手指圈中,疯狂地、本能地,开始前后抽插。
我渴望着,我祈求着,我像一个即将渴死的旅人,疯狂地想要在她这里,得到那最终极的、也是我唯一渴望的甘露。
这个我幻想了无数次、连在梦里都不敢奢求的场景,竟然变成了现实!她吻着我,她的手握着我,她给了我选择……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爱情吗?
没有锁,没有肛塞,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命令。只有我和她,像一对最普通的情侣,进行着最亲密的接触。
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圈着我的那只手,没有像以前用小腿夹住我时那样,随着我的抽动而越来越松。她的手指,依旧坚定地、有力地环绕着我,像是一种纵容,一种充满爱意的默许,一种无声的邀请,邀请我冲破禁锢,邀请我……射精。
幸福感和性欲,像两股交缠的、毁灭性的海啸,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防线。我几乎就要在她的手中、她的吻中,将我所有的爱意和欲望,尽数喷薄而出。
但是……
但是……
一幅幅画面,不受控制地,在我那被欲望烧得滚烫的脑海里,疯狂地回荡。
是那个深夜实验室里,她用冰冷的声音命令我“跪下”时,那高高在上的、女王般的侧脸。
是那个阳光午后,她用穿着白丝袜的脚尖,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时,那带着一丝戏谑的、残忍的微笑。
是那个地狱之夜,她被无数黑人轮奸后,像破碎的娃娃一样躺在床上时,那空洞的、失去一切光芒的眼神。
以及……她为了我,流下的那滴眼泪。
我忽然意识到……
我喜欢的,我爱着的,早已不是那个最初幻想中、遥不可及的、纯洁的女神了。
我喜欢的,是那个有野心、有欲望、甚至会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的、真实的她。
我喜欢的,是那个会高高在上、也会遍体鳞伤,会冰冷残忍、也会为我流泪的,完整的、独一无二的……林知夏。
我不能让她为了我,放弃那个真实的、完整的自己。
我更不能……让我自己,失去那个我真正爱着的、独一无二的女王。
我想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女朋友。
我想要的,是我的女王。是我的主人。是那个……会亲手为我锁上贞操锁的、独一无二的她。
那根在她指圈里疯狂抽插的肉棒,在即将达到高潮的、最顶点的瞬间,像是被施了最恶毒的咒语,缓缓地,一寸一寸地,慢了下来。
最终,在距离那扇名为“释放”的大门仅一步之遥时,它彻底停下——
带着无法泯灭的渴望、绝望的留恋,以及……甘之如饴的臣服。
寸止。
我用最卑微的、也最虔诚的方式,给出了我的答案。
我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
她笑了。
牛逼啊,写的真好,希望有后续"两姐妹"被黑人一起调教和两人确认关系后日常调教的描写,还有女主是怎么利用黑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还有个矛盾就是后续女主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但是又怎么满足自己那种渴望被黑人支配的欲望呢
可以,期待续作,真是很符合xp的文
目前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文章,看了七八年m文,这算是我目前看完的最淫乱的,之前从来没尝试过这么淫荡的文章,这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接受范围,但是确实写的很不错,作者的文笔确实挺不错
BetaDenier:↑男女主都成公交车了还不淫乱(bushi)打工战士:↑目前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文章,看了七八年m文,这算是我目前看完的最淫乱的,之前从来没尝试过这么淫荡的文章,这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接受范围,但是确实写的很不错,作者的文笔确实挺不错这能叫淫乱嘛都快完本了女主都没给男主打过飞机(bushi)
楼主写的太牛了,雌堕太棒了
唯一困惑的是,如果女主真的很爱男主,但是却会想要某个不确定身份的别人的精子作为后代?这个设定稍微有点让人困惑,有点像满足绿帽性癖的说法但好像不是那么真实()
唯一困惑的是,如果女主真的很爱男主,但是却会想要某个不确定身份的别人的精子作为后代?这个设定稍微有点让人困惑,有点像满足绿帽性癖的说法但好像不是那么真实()
jacktrades33:↑楼主写的太牛了,雌堕太棒了这个是学姐一上头说的话(当然实际怎么发展我也没想好,估计不会出现生小孩这种画面)
唯一困惑的是,如果女主真的很爱男主,但是却会想要某个不确定身份的别人的精子作为后代?这个设定稍微有点让人困惑,有点像满足绿帽性癖的说法但好像不是那么真实()
BetaDenier:↑完美 就是说你不配那里感觉把男主涵盖进去有一点绝情,要是“它们”(劣等品)不配感觉就爽起来了🤤,毕竟男主在女主心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jacktrades33:↑楼主写的太牛了,雌堕太棒了这个是学姐一上头说的话(当然实际怎么发展我也没想好,估计不会出现生小孩这种画面)
唯一困惑的是,如果女主真的很爱男主,但是却会想要某个不确定身份的别人的精子作为后代?这个设定稍微有点让人困惑,有点像满足绿帽性癖的说法但好像不是那么真实()
另:催更催更催更
腰肌劳损:↑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我先不延伸等回头总结下问题写个总结BetaDenier:↑完美 就是说你不配那里感觉把男主涵盖进去有一点绝情,要是“它们”(劣等品)不配感觉就爽起来了🤤,毕竟男主在女主心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jacktrades33:↑楼主写的太牛了,雌堕太棒了这个是学姐一上头说的话(当然实际怎么发展我也没想好,估计不会出现生小孩这种画面)
唯一困惑的是,如果女主真的很爱男主,但是却会想要某个不确定身份的别人的精子作为后代?这个设定稍微有点让人困惑,有点像满足绿帽性癖的说法但好像不是那么真实()
另:催更催更催更
BetaDenier:↑OK,静候楼主佳音腰肌劳损:↑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我先不延伸等回头总结下问题写个总结BetaDenier:↑完美 就是说你不配那里感觉把男主涵盖进去有一点绝情,要是“它们”(劣等品)不配感觉就爽起来了🤤,毕竟男主在女主心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jacktrades33:↑楼主写的太牛了,雌堕太棒了这个是学姐一上头说的话(当然实际怎么发展我也没想好,估计不会出现生小孩这种画面)
唯一困惑的是,如果女主真的很爱男主,但是却会想要某个不确定身份的别人的精子作为后代?这个设定稍微有点让人困惑,有点像满足绿帽性癖的说法但好像不是那么真实()
另:催更催更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