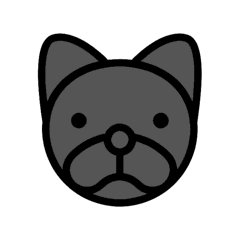卑贱的臣服在情侣脚下
连载中AI生成现实阶级小男孩M情侣主’25征文比赛棉袜原味踩踏鞋靴舔鞋羞辱人体家具
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城市被无形的壁垒分割成两个世界:高耸入云的富人区,灯火辉煌,街道整洁;贫民窟则破败不堪,污水横流。16岁的少年阿尘生活在贫民窟的边缘,家徒四壁,唯一的梦想却是成为富人脚下的一粒尘埃。他崇拜上层社会的富人,视他们的生活为神圣不可触及的光辉,甚至愿意为他们奉献一切,只为靠近那遥不可及的奢华。
这天,阿尘鼓起勇气,偷偷溜进了富人区的一个高档小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财富的气息。他远远地跟在一对年轻情侣身后,眼睛几乎离不开他们。那女孩大约二十岁,身高一米七,大波浪长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泽,穿着昂贵的白色运动装,脚上是纯白的棉袜和高档运动鞋,步伐轻盈如贵族。旁边的男生更高,一米八多的身材,皮肤白皙却肌肉结实,脚上踩着一双45码的限量版运动鞋,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
阿尘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尾随,直到他们走进一栋豪华公寓楼。他躲在阴影里,眼睁睁看着那对情侣将刚穿过的鞋子随意放在门外的鞋架上——那双男鞋宽大厚重,散发着皮革与汗水的混合气味;女鞋精致小巧,白袜还挂在鞋边,透着高雅的清香。阿尘的心跳加速,某种狂热的冲动吞噬了他的理智。他匍匐在地,五体投地,膝行到鞋架下,颤抖着双手捧起那双男鞋,低头叩拜,嘴唇轻轻触碰鞋面,贪婪地嗅着那股属于富人的气息。接着,他又转向女鞋,虔诚地亲吻袜沿,眼中满是痴迷。
突然,公寓的门“咔”地一声打开。男生站在门口,高大的身影如天神般俯视着他,眼神里满是厌恶与不屑。“你这只下贱的虫子,在干什么?”他的声音低沉却冰冷,带着一丝戏谑。阿尘吓得浑身一颤,头低得更深,却不敢抬头。男生抬起一只脚,穿着宽大的皮拖鞋,那脚掌几乎比阿尘的头还大,毫不留情地踩在他的后脑勺上,将他的脸死死压在地上。阿尘没有挣扎,反而更加卑微地贴紧地面,嘴里喃喃着:“对不起…我只想…只想为您效劳…”
女生也走了出来,倚在门框上,抱着手臂,嘴角挂着嘲讽的笑。“看看这可怜虫,连我们的鞋子都配不上,还想当我们的奴隶?”她轻蔑地踢了踢鞋架上的白袜,袜子落在阿尘面前,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阿尘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用颤抖的手捡起袜子,紧紧贴在脸上,语无伦次地哀求:“求求你们…让我为您做事…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愿意当您的狗,当您的蛆虫…”
男生冷笑一声,脚下的力道加重了几分,皮拖的触感冰凉而沉重。“你这种垃圾,连给我们擦鞋都不配。”女生则掩嘴轻笑,眼中闪过一丝恶作剧的光芒:“不过,看你这么贱,倒是挺有趣的。说吧,你能为我们做什么?”
阿尘的眼中燃起一丝希望,他匍匐得更低,声音带着哭腔:“我可以为您打扫、洗衣、做任何脏活…我只求能留在您身边,伺候您二位…”他的卑微如尘埃,彻底暴露在富人情侣的轻蔑目光下,而他却甘之如饴,只为那微不足道的靠近。
阿尘的卑微姿态让男生皱起眉头,脚下的皮拖稍稍松开,但依然压在阿尘的后脑勺上,像是在衡量这只“虫子”是否真有利用价值。女生则蹲下身,纤细的手指挑起阿尘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直视她那双冷漠却又带着戏谑的眼睛。“你真是个怪胎,”她轻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好奇,“不过,贱到你这种地步,倒也少见。说说看,你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别让我失望。”
阿尘的喉咙发干,心跳如擂鼓,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强忍着羞耻,声音颤抖却坚定:“我…我可以为您清理整个房子,擦亮每一双鞋,洗干净每一件衣服…我可以当您的影子,随时听命,哪怕是…是给您端茶倒水,跪在地上当您的脚垫…”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渗出冷汗,但眼中却燃烧着病态的狂热。
男生嗤笑一声,脚终于从阿尘头上挪开,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双手环胸,斜靠在门框上。“脚垫?哈,这主意倒新鲜。”他低头瞥了一眼自己的皮拖,又看了看阿尘那张满是尘土和卑微的脸,“不过,你这种货色,连碰我的鞋都不配,还想当脚垫?”
女生却似乎被阿尘的疯狂逗乐了,她站起身,慢条斯理地从鞋架上拿起自己的白棉袜,轻轻甩在阿尘脸上。袜子柔软地落在他的鼻尖,带着淡淡的香水味和她脚底的余温。阿尘浑身一震,几乎要昏厥过去,但他强撑着跪直身体,双手捧着那只袜子,像捧着圣物般低声呢喃:“谢谢…谢谢您赏赐…”他小心翼翼地将袜子贴在胸口,眼中泪光闪烁。
“够了!”男生不耐烦地打断,语气里带着几分烦躁,“别在这恶心人了。”他转头看向女生,耸了耸肩,“这家伙脑子有病,留着干嘛?扔出去得了。”但女生摆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别急嘛,耀,这种人虽然恶心,但说不定能派上点用场。至少…能给我们找点乐子。”
她转过身,朝屋里走去,头也不回地说:“进来吧,虫子。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贱。”阿尘愣住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滚带爬地跟了进去,膝盖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摩擦得生疼,却不敢站起身。男生耀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随手关上门,巨大的“砰”声在阿尘心中激起一阵涟漪——他终于踏进了富人的世界,哪怕是以如此卑贱的方式。
公寓内部奢华得让阿尘几乎窒息:水晶吊灯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俯瞰景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女生随手将外套扔在沙发上,懒洋洋地坐下,翘起二郎腿,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过来,”她朝阿尘勾了勾手指,“跪在这儿,给我讲讲你有多想当我们的奴仆。说得不好听,就把你扔出去喂狗。”
阿尘立刻膝行到她脚边,低头不敢直视,只敢盯着她那双赤裸的脚,脚趾涂着精致的红色指甲油,散发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美感。他咽了口唾沫,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我…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能为像您这样的人效力…我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我的命…我只求能留在您身边,哪怕只是当一条狗…”
耀站在一旁,冷笑连连:“狗?狗都比你有用。”他随手拿起桌上的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故意将水泼在阿尘头上。水流顺着阿尘的头发淌下,浸湿了他的破旧衣衫,但他一动不动,甚至还低声说:“谢谢…谢谢您的恩赐…”
女生看着这一幕,笑得前仰后合:“耀,你看他,真的跟条狗似的!”她停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恶意,“这样吧,虫子,给你个机会。把地板上的水舔干净,舔得一滴不剩,我就考虑让你留下来…当我们的‘宠物’。”
阿尘的眼睛猛地亮起,他毫不犹豫地趴下身,嘴唇贴着冰冷的大理石地板,开始舔舐地上的水渍。那股屈辱与狂热在他心中交织,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通向他梦寐以求的“富人世界”。
阿尘的舌头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滑动,舔舐着散落的水渍,混合着灰尘的苦涩味道在他口中蔓延。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舔都带着虔诚,仿佛这不是屈辱,而是某种神圣的仪式。女生——她叫琳娜——坐在沙发上,懒散地晃着脚,嘴角挂着一抹戏谑的笑,眼中却透着冷漠的观察。耀则站在一旁,抱着手臂,眼神里满是厌恶,但也夹杂着一丝好奇,像在看一只奇异的昆虫。
“看他舔得多认真,”琳娜轻笑,声音清脆却带着刺,“耀,你说这家伙是不是天生就该活在咱们脚底下?”她故意抬高一只脚,轻轻晃了晃,脚趾上的红色指甲油在灯光下闪着妖冶的光。阿尘的余光瞥到这一幕,心脏猛地一跳,但他不敢抬头,只敢更卖力地舔着地板,嘴里低声呢喃:“谢谢…谢谢您的恩赐…”
耀冷哼一声,走到阿尘身边,抬起一只脚,皮拖的边缘擦过阿尘的耳朵,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威压。“你这贱骨头,还真把自己当狗了?”他蹲下身,抓起阿尘的头发,强迫他抬起头。阿尘的脸满是水渍和灰尘,眼神却狂热得吓人,像一只渴求主人的流浪犬。耀皱了皱眉,松开手,嫌恶地擦了擦手指,“恶心。”
琳娜却似乎对这场游戏越发感兴趣。她起身,赤脚踩在地板上,缓缓踱到阿尘面前,俯身看着他。“虫子,你说你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对吧?”她的声音柔和却带着危险的试探,“那如果我让你去偷点东西,或者…替我们干点脏活,你敢不敢?”
阿尘愣了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从没想过“效忠”会涉及犯罪,但那股狂热的崇拜压倒了一切犹豫。他猛地点头,声音沙哑:“我敢!只要是您吩咐的,我什么都敢做!”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迟疑,只有病态的忠诚。
琳娜和耀对视一眼,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耀耸了耸肩,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这家伙脑子坏了,估计真敢干。”琳娜却笑得更深,拍了拍手,“好,那就给你个小任务,证明你的‘忠诚’。”她转身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空酒瓶,随手扔到阿尘面前,瓶子在地上滚了几圈,停在他膝边。“今晚之前,给我弄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限量版的,懂吗?偷也好,买也好,我不管。但要是拿不回来…”她顿了顿,笑容变得冰冷,“你就别想再踏进这里一步。”
阿尘盯着那个酒瓶,瓶身上复杂的花纹和金色的标签让他心生畏惧。他知道,这种酒在贫民窟的集市上根本见不到,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但他没有退路。他双手捧起酒瓶,像是捧着圣旨,低头叩首:“我一定办到!请您…请您相信我!”
耀不耐烦地挥挥手,“滚吧,别在这碍眼。”他又补了一句,“别想着跑,虫子。我们这小区有监控,你敢耍花样,我保证你回不了你的破贫民窟。”
阿尘连连点头,抱着酒瓶,膝行着退到门口,额头上的汗水混着地板的灰尘淌下。他推开门,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琳娜和耀,像是想把他们的身影刻进脑海。门在他身后关上,隔绝了那片奢华的世界。
夜色渐深,富人区的灯光依旧耀眼,而阿尘却站在街角,手中紧握着那个空酒瓶,脑子里一片混乱。他知道,偷一瓶限量版的酒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没有钱,也没有门路。但那股狂热的信念驱使着他,让他无法停下。他想起了贫民窟里那些黑市商人,或许他们会有办法,哪怕代价是搭上自己的一切。
阿尘咬紧牙关,攥着酒瓶,朝贫民窟的方向跑去。夜风吹过他的脸,带着刺骨的寒意,但他心中却燃着一团火——为了琳娜和耀,为了那个遥不可及的“富人世界”,他愿意赌上一切,哪怕是自己的尊严、自由,甚至生命。
阿尘跌跌撞撞地跑回贫民窟,手中紧紧攥着那个空酒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要弄到那瓶限量版的酒。他知道,富人区的商店和酒吧是他唯一的机会,尽管对他来说,那里就像另一个星球。贫民窟的黑市虽然肮脏混乱,但偶尔会有从富人区流出的“赃物”。他花光了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从一个猥琐的摊贩那里打听到一家高档酒吧的消息——据说那里藏着一批稀有酒,其中就包括琳娜指定的那款。
夜色浓重,阿尘换上一件勉强算干净的破外套,遮住自己破烂的模样,偷偷潜入了富人区的“星辉酒吧”。酒吧外霓虹闪烁,门口站着两个西装革履的保安,眼神冷漠如刀。阿尘绕到后巷,找到一扇半开的员工通道门,屏住呼吸溜了进去。里面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酒香和香水的味道,服务员们忙碌地穿梭,丝毫没注意到角落里这个鬼鬼祟祟的少年。
阿尘躲在吧台后的阴影里,目光锁定在酒柜上一瓶金光闪闪的酒——瓶身花纹与琳娜扔给他的空瓶一模一样。他心跳如雷,手心全是汗,但那股对琳娜和耀的狂热驱使着他。他趁着服务员转身的空隙,蹑手蹑脚地靠近酒柜,颤抖着伸手去拿那瓶酒。就在手指触到瓶身的一刹那,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他的后颈,像拎小鸡一样将他拽了出来。
“你这小贼,胆子不小啊!”一个低沉却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阿尘被狠狠摔在地上,头撞在地板上,疼得眼前发黑。他抬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他面前,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英俊得像从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眼神却冷得像冰。这就是酒吧的经理,名叫凯。凯俯视着阿尘,嘴角带着一丝嘲讽,“偷酒?就你这副穷酸样,也配碰这瓶酒?”
阿尘吓得魂飞魄散,趴在地上连连磕头,嘴里不住地求饶:“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求您放过我…”但他一边求饶,眼睛却死死盯着那瓶酒,趁凯不注意,偷偷将它塞进破外套里,用身体压住。凯冷笑一声,抬起一只擦得锃亮的皮鞋,狠狠踩在阿尘的背上,力道大得让阿尘几乎喘不过气。“放过你?偷我店里的东西,还想活着走出去?”
凯的鞋底碾着阿尘的脊背,每一下都像要把他踩进地里。阿尘咬紧牙关,疼得满头冷汗,但他死死护着怀里的酒瓶,脑子里只有琳娜那张戏谑的脸和耀那双轻蔑的眼。他低声哀求:“求您…我只是想…想拿这瓶酒给我的主人…”这话让凯愣了一下,脚下的力道稍缓,皱眉道:“主人?你这小子,脑子有病吧?”
阿尘趁机喘了口气,声音颤抖却带着狂热:“我…我只想为他们效力…求您放了我,我愿意做任何事…”凯嗤笑一声,松开脚,但随即一把揪起阿尘的衣领,将他拖到后巷,扔在垃圾堆旁。“滚吧,再让我看到你,腿给你打断。”阿尘连滚带爬地起身,怀里紧紧抱着那瓶偷来的酒,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夜色。
几个小时后,阿尘气喘吁吁地回到了琳娜和耀的公寓,身上满是灰尘和淤青,破外套里藏着那瓶限量版的酒。他跪在门口,双手捧着酒瓶,低头叩首,声音嘶哑:“我…我拿来了…求您收下…”门开了,琳娜和耀站在门口,耀皱着眉打量他,眼中依然是那股高高在上的不屑。琳娜却挑了挑眉,接过酒瓶,轻轻晃了晃,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哟,还真弄来了?虫子,你这贱命还挺有用嘛。”
耀冷哼一声,踢了踢阿尘的肩膀,“说,怎么弄来的?别告诉我你有钱买。”阿尘低着头,结结巴巴地将酒吧的事说了出来,包括被经理踩在脚下的事。他以为这会让他们满意,但耀听完却哈哈大笑,笑声里满是嘲讽:“你还真是个没骨气的狗,连被人踩成那样都不敢吭声?”
琳娜却似乎对阿尘的“忠诚”更感兴趣。她蹲下身,捏住阿尘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不错,虫子,你比我想象中还能干。”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这只是开始。想当我们的奴仆,光偷瓶酒可不够。明天晚上,我们有个派对,你得来伺候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伺候得不好…”她冷笑一声,“你就滚回你的贫民窟,永远别想再靠近我们。”
阿尘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听到了天大的恩赐。他连连磕头,额头撞在地板上发出闷响:“谢谢…谢谢您给我机会!我一定…一定让您满意!”耀不耐烦地挥挥手,转身进屋,琳娜则最后看了他一眼,扔下一句:“别让我失望,虫子。”门再次关上,留下阿尘跪在门外,脸上满是狂热的笑容。
他知道,派对将是他证明自己的关键时刻。他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更深的屈辱,只为留在琳娜和耀的脚下,靠近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富人世界”。
阿尘跪在公寓门外,额头贴着冰冷的地板,手中依然紧握着那瓶偷来的限量版酒留下的空瓶壳,仿佛那是连接他与琳娜、耀的唯一纽带。夜风吹过,带着富人区的花香和贫民窟的腐臭,他却浑然不觉,脑海里全是琳娜那句“伺候得不好,就滚回你的贫民窟”。他知道,明天晚上的派对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也是他彻底融入“富人世界”的门票,哪怕只是以奴仆的身份。
第二天傍晚,阿尘早早来到富人区,身上穿着从贫民窟旧货摊淘来的“最好”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和一条勉强没破洞的裤子。他站在琳娜和耀的公寓楼下,低头整理着自己的模样,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寒酸。门卫投来嫌弃的目光,但他毫不在意,只想着如何让琳娜和耀满意。
夜幕降临,公寓里传出低沉的音乐和欢笑声。阿尘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敲响了门。门开了,琳娜站在门口,穿着一袭紧身的黑色礼服裙,曲线毕露,脚上是一双尖头高跟鞋,散发着高雅与冷艳。她瞥了阿尘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虫子,你还真来了。进来吧,别给我丢脸。”
阿尘低头应了一声,膝行着进了公寓。屋内灯火通明,十几个年轻男女散坐在沙发和吧台旁,个个衣着光鲜,谈笑间流露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味和酒香,桌上摆满了精致的食物和酒瓶。阿尘的出现像一颗不和谐的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引来几道好奇又轻蔑的目光。
耀从人群中走过来,穿着一件白色丝质衬衫,袖口随意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阿尘,冷笑道:“这就是我们新找的‘宠物’。大家随便使唤,别客气。”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有人吹了声口哨,有人轻声嘲讽:“这小子看着像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
琳娜拍了拍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好了,虫子,派对开始了。你的任务很简单——听我们的话,伺候好每一个人。端酒、擦地、跑腿,懂吗?”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恶意,“要是让我或者我的朋友不满意,你知道后果。”
阿尘连连点头,爬到吧台旁,开始忙碌起来。他端着托盘,颤巍巍地给客人们递上酒杯,手抖得几乎洒出来。有人故意伸脚绊他,有人“无意”将红酒泼在他身上,引来一阵哄笑。阿尘咬紧牙关,强忍着屈辱,低声说:“对不起…我这就擦干净…”他跪下,用袖子擦去地上的酒渍,额头渗出冷汗。
一个穿金色礼服的女孩——显然是琳娜的朋友——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阿尘,语气轻佻:“喂,虫子,我的鞋子有点脏了,给我舔干净。”她抬起一只脚,细高跟上沾着些许灰尘。阿尘愣了一下,但看到琳娜投来的冰冷目光,立刻低下头,嘴唇贴上那只鞋,轻轻舔去灰尘。周围的人爆发出更大的笑声,有人甚至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上传到社交媒体,标题是“贫民窟的狗”。
耀站在一旁,喝了口酒,冷冷地说:“这家伙还真听话,琳娜,你从哪儿找来的极品?”琳娜笑着耸肩:“路边捡的呗。看他这贱样,倒是挺适合给我们找乐子。”她走到阿尘面前,俯身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虫子,表现得不错。不过,派对才刚开始,接下来有个小游戏,你得好好配合。”
她拍拍手,示意所有人安静,然后从桌上拿起一个银色的小铃铛,晃了晃,发出清脆的响声。“从现在开始,这个铃铛归你了,虫子。谁摇铃,你就得听谁的命令,明白吗?”阿尘接过铃铛,双手颤抖,眼中却闪着狂热的光:“是…我明白了…”
派对的气氛变得更加狂热。铃铛声此起彼伏,阿尘被呼来喝去,像一只被牵着绳子的狗。有人让他跪在地上当脚凳,有人让他爬到桌下捡掉落的食物,还有人故意将酒泼在他头上,让他“表演”舔地板。阿尘的衬衫早已湿透,沾满污渍,膝盖磨得红肿,但他不敢停下,每一次铃铛响起,他都像打了鸡血般扑向“主人”的命令。
然而,琳娜和耀的目光却越发冷漠。他们低声交谈,偶尔瞥向阿尘,像是观察一只实验品。派对接近尾声时,琳娜突然站起身,摇响铃铛,声音清脆地刺破喧嚣:“虫子,过来。”阿尘立刻爬到她脚边,低头等待命令。琳娜俯身,声音低得只有他能听见:“今晚你干得不错,但这只是热身。想真正当我们的奴仆,还有最后一关。”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明天,我们会带你去个地方。如果你能通过考验,我们就考虑让你留下。听懂了吗?”
阿尘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他连连磕头,声音沙哑:“谢谢…谢谢您给我机会!我一定…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琳娜冷笑一声,直起身,朝耀使了个眼色。耀耸耸肩,随手将一杯酒泼在地上:“舔干净,然后滚出去。今晚就到这儿。”
阿尘毫不犹豫地趴下,舔舐着地上的酒渍,周围的笑声和嘲讽如潮水般涌来。他却毫不在意,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明天是什么考验,他都要通过,哪怕付出一切。
阿尘整夜未眠,蜷缩在贫民窟破旧的窝棚里,脑海里反复回放着琳娜的话:“最后一关”。那句话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勒住他的心,让他既恐惧又狂热。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那股对富人世界的病态渴望让他无法退缩。清晨的第一缕光透过破窗洒在他脸上,他爬起身,用冷水抹了把脸,换上那件勉强算体面的衬衫,朝富人区走去。
中午时分,阿尘站在琳娜和耀的公寓楼下,双手紧握,额头渗着汗。门开了,琳娜一身休闲却昂贵的运动装,头发随意扎成马尾,依旧散发着高不可攀的气场。耀站在她身旁,穿着一件黑色紧身T恤,肌肉线条若隐若现,眼神冷漠如冰。他瞥了阿尘一眼,嗤笑道:“虫子,你还真敢来。胆子不小。”
琳娜笑着拍拍耀的肩膀,转头对阿尘说:“走吧,虫子。最后一关不在这儿。”她没多解释,转身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豪车,车身在阳光下闪着金属光泽。阿尘愣了一下,赶紧低头跟上,不敢多问。耀打开后车门,朝他扬了扬下巴:“进去,跪在后座地板上,别弄脏我的车。”
阿尘立刻爬进车内,蜷缩在后座的脚垫上,头低得几乎贴着地毯。车子启动,引擎的低鸣和车内的皮革香气让他感到一种窒息的奢华。琳娜和耀在前座低声交谈,偶尔传来几句模糊的笑声,但阿尘听不清内容,只能感受到他们的漠然。他紧握双手,心中默念:无论是什么考验,我都要通过…
车子开了约半个小时,停在一片荒凉的工业区边缘。这里远离富人区的光鲜,也不同于贫民窟的混乱,是一片废弃的厂房和空地,四周静得让人不安。琳娜和耀下车,阿尘紧跟着爬出,膝盖刚触到地面,就听到琳娜清冷的声音:“起来,虫子。你的最后一关在这儿。”
阿尘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抬头一看,面前是一栋破旧的厂房,墙壁斑驳,窗户大多破碎。厂房前站着三个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年龄与琳娜和耀相仿,穿着同样昂贵却低调的衣服,眼神里带着一种猎人般的兴奋。地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木箱,旁边散落着几根铁棍和一捆绳子。阿尘的心猛地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琳娜走上前,拍了拍木箱,笑容里带着几分残忍:“虫子,你不是说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吗?今天,我们给你个机会证明你的忠诚。”她顿了顿,朝那三个陌生人点了点头18岁的阿尘
琳娜的笑容在厂房的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冰冷,她拍了拍那个破旧木箱,目光扫过阿尘,像在审视一件即将被拆解的玩具。耀站在一旁,双手插兜,眼神里带着戏谑与不屑。那三个陌生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成半圈,脸上挂着猎奇的笑,仿佛在期待一场好戏。厂房内空气潮湿,弥漫着铁锈和霉味,地上散落的铁棍和绳子在昏光下泛着冷光,让阿尘的喉咙一阵发紧。
琳娜蹲下身,捡起一根铁棍,在手中掂了掂,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虫子,你的最后一关很简单,”她慢条斯理地说,语气轻描淡写却透着恶意,“我们要玩个游戏,叫‘忠诚试炼’。你不是说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吗?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她朝木箱一指,“打开它,里面有你的‘任务’。”
阿尘的腿有些发软,但他不敢违抗,颤抖着走上前,跪在木箱旁,双手掀开沉重的盖子。箱子里躺着一堆杂物:几件破旧的衣物、一把生锈的匕首、一卷胶带,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他拿起纸条,上面用潦草的字迹写着:“取悦我们,代价自负。”阿尘的心猛地一沉,抬头看向琳娜,眼中满是困惑与恐惧。
耀冷笑一声,接过话头:“别愣着,虫子。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五个人,每人给你一个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不管是什么。如果做不到,或者让我们不满意…”他顿了顿,踢了踢地上的铁棍,“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厂房。”
第一个男人——一个留着短胡子、穿皮夹克的家伙——率先走上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我先来。”他从箱子里拿起那把生锈的匕首,扔到阿尘脚边,“用这个,在你手臂上刻个‘奴’字。刻得深一点,让我们看清你的忠诚。”
阿尘愣住了,盯着地上的匕首,双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琳娜和耀的眼神冷得像刀,另一个女人甚至已经拿出手机,准备录下这一幕。他咬紧牙关,捡起匕首,手抖得几乎划破自己的手指。匕首的锈迹刺鼻,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刀尖抵在自己的左臂上,狠狠划下。血珠立刻渗出,疼得他闷哼一声,但他不敢停,咬着牙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奴”字,血顺着手臂淌到地上。
“还行,够贱。”短胡子男人满意地点点头,退到一旁。第二个男人——一个瘦高个,戴着金丝眼镜——走上前,语气平静却带着阴冷的压迫感:“我的命令简单。脱光衣服,跪着爬一圈厂房,边爬边喊‘我是你们的狗’。”
阿尘的脸瞬间涨红,屈辱像潮水般涌上心头,但他不敢反抗。他脱下破旧的衬衫和裤子,只剩一条破洞的内裤,跪在地上,开始绕着厂房爬行。每迈一步,粗糙的水泥地都磨得他膝盖刺痛,但他还是扯着嗓子喊:“我是你们的狗!我是你们的狗!”声音在空荡的厂房里回荡,引来一阵哄笑。那个女人一边录视频,一边嘲讽:“这家伙真是天生的贱种。”
轮到那个女人时,她穿着紧身皮裤,踩着一双尖头靴,慢悠悠地走上前,俯身盯着阿尘的眼睛,语气轻佻:“我的命令嘛…把你刚才刻的那个字,用胶带贴满,然后撕下来。让我看看你有多能忍。”阿尘咬紧牙关,拿起箱子里的胶带,缠在血淋淋的伤口上,每缠一圈都疼得他冷汗直冒。撕下时,胶带连带着血肉一起扯下,他疼得几乎晕过去,但硬是没喊出声,只低声呢喃:“为了您…我什么都愿意…”
琳娜和耀一直冷眼旁观,直到轮到他们。耀先开口,语气懒散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虫子,我的命令是——用你的舌头,把我这双鞋舔干净。”他抬起一只脚,45码的限量版运动鞋上沾着些许灰尘和泥点。阿尘毫不犹豫地趴下,嘴唇贴上鞋面,舔舐着每一寸污渍,泥土的苦涩和皮革的味道在他口中混杂。他舔得专注而虔诚,仿佛这双鞋是他的整个世界。
最后轮到琳娜。她慢条斯理地走上前,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蹲下身,捏住阿尘的下巴,逼他直视她的眼睛。“虫子,你干得不错,贱得让我都意外。”她顿了顿,笑容变得冰冷,“我的命令是——从现在开始,你得发誓,永远做我们的奴仆,不许有任何反抗,哪怕我们让你去死,你也得笑着去。说,‘我发誓’。”
阿尘的眼神狂热而空洞,他毫不犹豫地开口:“我发誓…我永远是您的奴仆…我愿意为您去死…”他的声音低沉却坚定,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琳娜满意地点点头,起身拍拍手:“好了,游戏结束。你通过了,虫子。”
然而,耀却冷笑一声,走上前,一脚踢在阿尘的胸口,将他踹倒在地。“通过?不过是给我们找了个新玩具罢了。”他转头看向琳娜,眼中闪过一丝默契,“这家伙留着还有用,琳娜。让他去干点脏活,比如…处理我们不想碰的事。”
琳娜点点头,目光扫过阿尘,带着一种猫戏老鼠的残忍:“不错,虫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专属仆人’。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伺候不好,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扔回贫民窟…或者更糟的地方。”
阿尘趴在地上,胸口剧痛,血和汗混在一起,但他眼中却闪着病态的光。他爬到琳娜脚边,亲吻她的高跟鞋,低声呢喃:“谢谢…谢谢您收留我…”周围的笑声和嘲讽再次响起,但阿尘毫不在意。他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归属”,哪怕是以如此卑贱的方式
这天,阿尘鼓起勇气,偷偷溜进了富人区的一个高档小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财富的气息。他远远地跟在一对年轻情侣身后,眼睛几乎离不开他们。那女孩大约二十岁,身高一米七,大波浪长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泽,穿着昂贵的白色运动装,脚上是纯白的棉袜和高档运动鞋,步伐轻盈如贵族。旁边的男生更高,一米八多的身材,皮肤白皙却肌肉结实,脚上踩着一双45码的限量版运动鞋,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
阿尘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尾随,直到他们走进一栋豪华公寓楼。他躲在阴影里,眼睁睁看着那对情侣将刚穿过的鞋子随意放在门外的鞋架上——那双男鞋宽大厚重,散发着皮革与汗水的混合气味;女鞋精致小巧,白袜还挂在鞋边,透着高雅的清香。阿尘的心跳加速,某种狂热的冲动吞噬了他的理智。他匍匐在地,五体投地,膝行到鞋架下,颤抖着双手捧起那双男鞋,低头叩拜,嘴唇轻轻触碰鞋面,贪婪地嗅着那股属于富人的气息。接着,他又转向女鞋,虔诚地亲吻袜沿,眼中满是痴迷。
突然,公寓的门“咔”地一声打开。男生站在门口,高大的身影如天神般俯视着他,眼神里满是厌恶与不屑。“你这只下贱的虫子,在干什么?”他的声音低沉却冰冷,带着一丝戏谑。阿尘吓得浑身一颤,头低得更深,却不敢抬头。男生抬起一只脚,穿着宽大的皮拖鞋,那脚掌几乎比阿尘的头还大,毫不留情地踩在他的后脑勺上,将他的脸死死压在地上。阿尘没有挣扎,反而更加卑微地贴紧地面,嘴里喃喃着:“对不起…我只想…只想为您效劳…”
女生也走了出来,倚在门框上,抱着手臂,嘴角挂着嘲讽的笑。“看看这可怜虫,连我们的鞋子都配不上,还想当我们的奴隶?”她轻蔑地踢了踢鞋架上的白袜,袜子落在阿尘面前,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阿尘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用颤抖的手捡起袜子,紧紧贴在脸上,语无伦次地哀求:“求求你们…让我为您做事…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愿意当您的狗,当您的蛆虫…”
男生冷笑一声,脚下的力道加重了几分,皮拖的触感冰凉而沉重。“你这种垃圾,连给我们擦鞋都不配。”女生则掩嘴轻笑,眼中闪过一丝恶作剧的光芒:“不过,看你这么贱,倒是挺有趣的。说吧,你能为我们做什么?”
阿尘的眼中燃起一丝希望,他匍匐得更低,声音带着哭腔:“我可以为您打扫、洗衣、做任何脏活…我只求能留在您身边,伺候您二位…”他的卑微如尘埃,彻底暴露在富人情侣的轻蔑目光下,而他却甘之如饴,只为那微不足道的靠近。
阿尘的卑微姿态让男生皱起眉头,脚下的皮拖稍稍松开,但依然压在阿尘的后脑勺上,像是在衡量这只“虫子”是否真有利用价值。女生则蹲下身,纤细的手指挑起阿尘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直视她那双冷漠却又带着戏谑的眼睛。“你真是个怪胎,”她轻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好奇,“不过,贱到你这种地步,倒也少见。说说看,你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别让我失望。”
阿尘的喉咙发干,心跳如擂鼓,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强忍着羞耻,声音颤抖却坚定:“我…我可以为您清理整个房子,擦亮每一双鞋,洗干净每一件衣服…我可以当您的影子,随时听命,哪怕是…是给您端茶倒水,跪在地上当您的脚垫…”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渗出冷汗,但眼中却燃烧着病态的狂热。
男生嗤笑一声,脚终于从阿尘头上挪开,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双手环胸,斜靠在门框上。“脚垫?哈,这主意倒新鲜。”他低头瞥了一眼自己的皮拖,又看了看阿尘那张满是尘土和卑微的脸,“不过,你这种货色,连碰我的鞋都不配,还想当脚垫?”
女生却似乎被阿尘的疯狂逗乐了,她站起身,慢条斯理地从鞋架上拿起自己的白棉袜,轻轻甩在阿尘脸上。袜子柔软地落在他的鼻尖,带着淡淡的香水味和她脚底的余温。阿尘浑身一震,几乎要昏厥过去,但他强撑着跪直身体,双手捧着那只袜子,像捧着圣物般低声呢喃:“谢谢…谢谢您赏赐…”他小心翼翼地将袜子贴在胸口,眼中泪光闪烁。
“够了!”男生不耐烦地打断,语气里带着几分烦躁,“别在这恶心人了。”他转头看向女生,耸了耸肩,“这家伙脑子有病,留着干嘛?扔出去得了。”但女生摆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别急嘛,耀,这种人虽然恶心,但说不定能派上点用场。至少…能给我们找点乐子。”
她转过身,朝屋里走去,头也不回地说:“进来吧,虫子。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贱。”阿尘愣住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滚带爬地跟了进去,膝盖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摩擦得生疼,却不敢站起身。男生耀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随手关上门,巨大的“砰”声在阿尘心中激起一阵涟漪——他终于踏进了富人的世界,哪怕是以如此卑贱的方式。
公寓内部奢华得让阿尘几乎窒息:水晶吊灯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俯瞰景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女生随手将外套扔在沙发上,懒洋洋地坐下,翘起二郎腿,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过来,”她朝阿尘勾了勾手指,“跪在这儿,给我讲讲你有多想当我们的奴仆。说得不好听,就把你扔出去喂狗。”
阿尘立刻膝行到她脚边,低头不敢直视,只敢盯着她那双赤裸的脚,脚趾涂着精致的红色指甲油,散发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美感。他咽了口唾沫,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我…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能为像您这样的人效力…我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我的命…我只求能留在您身边,哪怕只是当一条狗…”
耀站在一旁,冷笑连连:“狗?狗都比你有用。”他随手拿起桌上的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故意将水泼在阿尘头上。水流顺着阿尘的头发淌下,浸湿了他的破旧衣衫,但他一动不动,甚至还低声说:“谢谢…谢谢您的恩赐…”
女生看着这一幕,笑得前仰后合:“耀,你看他,真的跟条狗似的!”她停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恶意,“这样吧,虫子,给你个机会。把地板上的水舔干净,舔得一滴不剩,我就考虑让你留下来…当我们的‘宠物’。”
阿尘的眼睛猛地亮起,他毫不犹豫地趴下身,嘴唇贴着冰冷的大理石地板,开始舔舐地上的水渍。那股屈辱与狂热在他心中交织,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通向他梦寐以求的“富人世界”。
阿尘的舌头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滑动,舔舐着散落的水渍,混合着灰尘的苦涩味道在他口中蔓延。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舔都带着虔诚,仿佛这不是屈辱,而是某种神圣的仪式。女生——她叫琳娜——坐在沙发上,懒散地晃着脚,嘴角挂着一抹戏谑的笑,眼中却透着冷漠的观察。耀则站在一旁,抱着手臂,眼神里满是厌恶,但也夹杂着一丝好奇,像在看一只奇异的昆虫。
“看他舔得多认真,”琳娜轻笑,声音清脆却带着刺,“耀,你说这家伙是不是天生就该活在咱们脚底下?”她故意抬高一只脚,轻轻晃了晃,脚趾上的红色指甲油在灯光下闪着妖冶的光。阿尘的余光瞥到这一幕,心脏猛地一跳,但他不敢抬头,只敢更卖力地舔着地板,嘴里低声呢喃:“谢谢…谢谢您的恩赐…”
耀冷哼一声,走到阿尘身边,抬起一只脚,皮拖的边缘擦过阿尘的耳朵,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威压。“你这贱骨头,还真把自己当狗了?”他蹲下身,抓起阿尘的头发,强迫他抬起头。阿尘的脸满是水渍和灰尘,眼神却狂热得吓人,像一只渴求主人的流浪犬。耀皱了皱眉,松开手,嫌恶地擦了擦手指,“恶心。”
琳娜却似乎对这场游戏越发感兴趣。她起身,赤脚踩在地板上,缓缓踱到阿尘面前,俯身看着他。“虫子,你说你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对吧?”她的声音柔和却带着危险的试探,“那如果我让你去偷点东西,或者…替我们干点脏活,你敢不敢?”
阿尘愣了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从没想过“效忠”会涉及犯罪,但那股狂热的崇拜压倒了一切犹豫。他猛地点头,声音沙哑:“我敢!只要是您吩咐的,我什么都敢做!”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迟疑,只有病态的忠诚。
琳娜和耀对视一眼,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耀耸了耸肩,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这家伙脑子坏了,估计真敢干。”琳娜却笑得更深,拍了拍手,“好,那就给你个小任务,证明你的‘忠诚’。”她转身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空酒瓶,随手扔到阿尘面前,瓶子在地上滚了几圈,停在他膝边。“今晚之前,给我弄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限量版的,懂吗?偷也好,买也好,我不管。但要是拿不回来…”她顿了顿,笑容变得冰冷,“你就别想再踏进这里一步。”
阿尘盯着那个酒瓶,瓶身上复杂的花纹和金色的标签让他心生畏惧。他知道,这种酒在贫民窟的集市上根本见不到,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但他没有退路。他双手捧起酒瓶,像是捧着圣旨,低头叩首:“我一定办到!请您…请您相信我!”
耀不耐烦地挥挥手,“滚吧,别在这碍眼。”他又补了一句,“别想着跑,虫子。我们这小区有监控,你敢耍花样,我保证你回不了你的破贫民窟。”
阿尘连连点头,抱着酒瓶,膝行着退到门口,额头上的汗水混着地板的灰尘淌下。他推开门,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琳娜和耀,像是想把他们的身影刻进脑海。门在他身后关上,隔绝了那片奢华的世界。
夜色渐深,富人区的灯光依旧耀眼,而阿尘却站在街角,手中紧握着那个空酒瓶,脑子里一片混乱。他知道,偷一瓶限量版的酒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没有钱,也没有门路。但那股狂热的信念驱使着他,让他无法停下。他想起了贫民窟里那些黑市商人,或许他们会有办法,哪怕代价是搭上自己的一切。
阿尘咬紧牙关,攥着酒瓶,朝贫民窟的方向跑去。夜风吹过他的脸,带着刺骨的寒意,但他心中却燃着一团火——为了琳娜和耀,为了那个遥不可及的“富人世界”,他愿意赌上一切,哪怕是自己的尊严、自由,甚至生命。
阿尘跌跌撞撞地跑回贫民窟,手中紧紧攥着那个空酒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要弄到那瓶限量版的酒。他知道,富人区的商店和酒吧是他唯一的机会,尽管对他来说,那里就像另一个星球。贫民窟的黑市虽然肮脏混乱,但偶尔会有从富人区流出的“赃物”。他花光了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从一个猥琐的摊贩那里打听到一家高档酒吧的消息——据说那里藏着一批稀有酒,其中就包括琳娜指定的那款。
夜色浓重,阿尘换上一件勉强算干净的破外套,遮住自己破烂的模样,偷偷潜入了富人区的“星辉酒吧”。酒吧外霓虹闪烁,门口站着两个西装革履的保安,眼神冷漠如刀。阿尘绕到后巷,找到一扇半开的员工通道门,屏住呼吸溜了进去。里面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酒香和香水的味道,服务员们忙碌地穿梭,丝毫没注意到角落里这个鬼鬼祟祟的少年。
阿尘躲在吧台后的阴影里,目光锁定在酒柜上一瓶金光闪闪的酒——瓶身花纹与琳娜扔给他的空瓶一模一样。他心跳如雷,手心全是汗,但那股对琳娜和耀的狂热驱使着他。他趁着服务员转身的空隙,蹑手蹑脚地靠近酒柜,颤抖着伸手去拿那瓶酒。就在手指触到瓶身的一刹那,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他的后颈,像拎小鸡一样将他拽了出来。
“你这小贼,胆子不小啊!”一个低沉却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阿尘被狠狠摔在地上,头撞在地板上,疼得眼前发黑。他抬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他面前,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英俊得像从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眼神却冷得像冰。这就是酒吧的经理,名叫凯。凯俯视着阿尘,嘴角带着一丝嘲讽,“偷酒?就你这副穷酸样,也配碰这瓶酒?”
阿尘吓得魂飞魄散,趴在地上连连磕头,嘴里不住地求饶:“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求您放过我…”但他一边求饶,眼睛却死死盯着那瓶酒,趁凯不注意,偷偷将它塞进破外套里,用身体压住。凯冷笑一声,抬起一只擦得锃亮的皮鞋,狠狠踩在阿尘的背上,力道大得让阿尘几乎喘不过气。“放过你?偷我店里的东西,还想活着走出去?”
凯的鞋底碾着阿尘的脊背,每一下都像要把他踩进地里。阿尘咬紧牙关,疼得满头冷汗,但他死死护着怀里的酒瓶,脑子里只有琳娜那张戏谑的脸和耀那双轻蔑的眼。他低声哀求:“求您…我只是想…想拿这瓶酒给我的主人…”这话让凯愣了一下,脚下的力道稍缓,皱眉道:“主人?你这小子,脑子有病吧?”
阿尘趁机喘了口气,声音颤抖却带着狂热:“我…我只想为他们效力…求您放了我,我愿意做任何事…”凯嗤笑一声,松开脚,但随即一把揪起阿尘的衣领,将他拖到后巷,扔在垃圾堆旁。“滚吧,再让我看到你,腿给你打断。”阿尘连滚带爬地起身,怀里紧紧抱着那瓶偷来的酒,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夜色。
几个小时后,阿尘气喘吁吁地回到了琳娜和耀的公寓,身上满是灰尘和淤青,破外套里藏着那瓶限量版的酒。他跪在门口,双手捧着酒瓶,低头叩首,声音嘶哑:“我…我拿来了…求您收下…”门开了,琳娜和耀站在门口,耀皱着眉打量他,眼中依然是那股高高在上的不屑。琳娜却挑了挑眉,接过酒瓶,轻轻晃了晃,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哟,还真弄来了?虫子,你这贱命还挺有用嘛。”
耀冷哼一声,踢了踢阿尘的肩膀,“说,怎么弄来的?别告诉我你有钱买。”阿尘低着头,结结巴巴地将酒吧的事说了出来,包括被经理踩在脚下的事。他以为这会让他们满意,但耀听完却哈哈大笑,笑声里满是嘲讽:“你还真是个没骨气的狗,连被人踩成那样都不敢吭声?”
琳娜却似乎对阿尘的“忠诚”更感兴趣。她蹲下身,捏住阿尘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不错,虫子,你比我想象中还能干。”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这只是开始。想当我们的奴仆,光偷瓶酒可不够。明天晚上,我们有个派对,你得来伺候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伺候得不好…”她冷笑一声,“你就滚回你的贫民窟,永远别想再靠近我们。”
阿尘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听到了天大的恩赐。他连连磕头,额头撞在地板上发出闷响:“谢谢…谢谢您给我机会!我一定…一定让您满意!”耀不耐烦地挥挥手,转身进屋,琳娜则最后看了他一眼,扔下一句:“别让我失望,虫子。”门再次关上,留下阿尘跪在门外,脸上满是狂热的笑容。
他知道,派对将是他证明自己的关键时刻。他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更深的屈辱,只为留在琳娜和耀的脚下,靠近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富人世界”。
阿尘跪在公寓门外,额头贴着冰冷的地板,手中依然紧握着那瓶偷来的限量版酒留下的空瓶壳,仿佛那是连接他与琳娜、耀的唯一纽带。夜风吹过,带着富人区的花香和贫民窟的腐臭,他却浑然不觉,脑海里全是琳娜那句“伺候得不好,就滚回你的贫民窟”。他知道,明天晚上的派对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也是他彻底融入“富人世界”的门票,哪怕只是以奴仆的身份。
第二天傍晚,阿尘早早来到富人区,身上穿着从贫民窟旧货摊淘来的“最好”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和一条勉强没破洞的裤子。他站在琳娜和耀的公寓楼下,低头整理着自己的模样,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寒酸。门卫投来嫌弃的目光,但他毫不在意,只想着如何让琳娜和耀满意。
夜幕降临,公寓里传出低沉的音乐和欢笑声。阿尘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敲响了门。门开了,琳娜站在门口,穿着一袭紧身的黑色礼服裙,曲线毕露,脚上是一双尖头高跟鞋,散发着高雅与冷艳。她瞥了阿尘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虫子,你还真来了。进来吧,别给我丢脸。”
阿尘低头应了一声,膝行着进了公寓。屋内灯火通明,十几个年轻男女散坐在沙发和吧台旁,个个衣着光鲜,谈笑间流露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味和酒香,桌上摆满了精致的食物和酒瓶。阿尘的出现像一颗不和谐的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引来几道好奇又轻蔑的目光。
耀从人群中走过来,穿着一件白色丝质衬衫,袖口随意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阿尘,冷笑道:“这就是我们新找的‘宠物’。大家随便使唤,别客气。”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有人吹了声口哨,有人轻声嘲讽:“这小子看着像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
琳娜拍了拍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好了,虫子,派对开始了。你的任务很简单——听我们的话,伺候好每一个人。端酒、擦地、跑腿,懂吗?”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恶意,“要是让我或者我的朋友不满意,你知道后果。”
阿尘连连点头,爬到吧台旁,开始忙碌起来。他端着托盘,颤巍巍地给客人们递上酒杯,手抖得几乎洒出来。有人故意伸脚绊他,有人“无意”将红酒泼在他身上,引来一阵哄笑。阿尘咬紧牙关,强忍着屈辱,低声说:“对不起…我这就擦干净…”他跪下,用袖子擦去地上的酒渍,额头渗出冷汗。
一个穿金色礼服的女孩——显然是琳娜的朋友——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阿尘,语气轻佻:“喂,虫子,我的鞋子有点脏了,给我舔干净。”她抬起一只脚,细高跟上沾着些许灰尘。阿尘愣了一下,但看到琳娜投来的冰冷目光,立刻低下头,嘴唇贴上那只鞋,轻轻舔去灰尘。周围的人爆发出更大的笑声,有人甚至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上传到社交媒体,标题是“贫民窟的狗”。
耀站在一旁,喝了口酒,冷冷地说:“这家伙还真听话,琳娜,你从哪儿找来的极品?”琳娜笑着耸肩:“路边捡的呗。看他这贱样,倒是挺适合给我们找乐子。”她走到阿尘面前,俯身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虫子,表现得不错。不过,派对才刚开始,接下来有个小游戏,你得好好配合。”
她拍拍手,示意所有人安静,然后从桌上拿起一个银色的小铃铛,晃了晃,发出清脆的响声。“从现在开始,这个铃铛归你了,虫子。谁摇铃,你就得听谁的命令,明白吗?”阿尘接过铃铛,双手颤抖,眼中却闪着狂热的光:“是…我明白了…”
派对的气氛变得更加狂热。铃铛声此起彼伏,阿尘被呼来喝去,像一只被牵着绳子的狗。有人让他跪在地上当脚凳,有人让他爬到桌下捡掉落的食物,还有人故意将酒泼在他头上,让他“表演”舔地板。阿尘的衬衫早已湿透,沾满污渍,膝盖磨得红肿,但他不敢停下,每一次铃铛响起,他都像打了鸡血般扑向“主人”的命令。
然而,琳娜和耀的目光却越发冷漠。他们低声交谈,偶尔瞥向阿尘,像是观察一只实验品。派对接近尾声时,琳娜突然站起身,摇响铃铛,声音清脆地刺破喧嚣:“虫子,过来。”阿尘立刻爬到她脚边,低头等待命令。琳娜俯身,声音低得只有他能听见:“今晚你干得不错,但这只是热身。想真正当我们的奴仆,还有最后一关。”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明天,我们会带你去个地方。如果你能通过考验,我们就考虑让你留下。听懂了吗?”
阿尘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他连连磕头,声音沙哑:“谢谢…谢谢您给我机会!我一定…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琳娜冷笑一声,直起身,朝耀使了个眼色。耀耸耸肩,随手将一杯酒泼在地上:“舔干净,然后滚出去。今晚就到这儿。”
阿尘毫不犹豫地趴下,舔舐着地上的酒渍,周围的笑声和嘲讽如潮水般涌来。他却毫不在意,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明天是什么考验,他都要通过,哪怕付出一切。
阿尘整夜未眠,蜷缩在贫民窟破旧的窝棚里,脑海里反复回放着琳娜的话:“最后一关”。那句话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勒住他的心,让他既恐惧又狂热。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那股对富人世界的病态渴望让他无法退缩。清晨的第一缕光透过破窗洒在他脸上,他爬起身,用冷水抹了把脸,换上那件勉强算体面的衬衫,朝富人区走去。
中午时分,阿尘站在琳娜和耀的公寓楼下,双手紧握,额头渗着汗。门开了,琳娜一身休闲却昂贵的运动装,头发随意扎成马尾,依旧散发着高不可攀的气场。耀站在她身旁,穿着一件黑色紧身T恤,肌肉线条若隐若现,眼神冷漠如冰。他瞥了阿尘一眼,嗤笑道:“虫子,你还真敢来。胆子不小。”
琳娜笑着拍拍耀的肩膀,转头对阿尘说:“走吧,虫子。最后一关不在这儿。”她没多解释,转身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豪车,车身在阳光下闪着金属光泽。阿尘愣了一下,赶紧低头跟上,不敢多问。耀打开后车门,朝他扬了扬下巴:“进去,跪在后座地板上,别弄脏我的车。”
阿尘立刻爬进车内,蜷缩在后座的脚垫上,头低得几乎贴着地毯。车子启动,引擎的低鸣和车内的皮革香气让他感到一种窒息的奢华。琳娜和耀在前座低声交谈,偶尔传来几句模糊的笑声,但阿尘听不清内容,只能感受到他们的漠然。他紧握双手,心中默念:无论是什么考验,我都要通过…
车子开了约半个小时,停在一片荒凉的工业区边缘。这里远离富人区的光鲜,也不同于贫民窟的混乱,是一片废弃的厂房和空地,四周静得让人不安。琳娜和耀下车,阿尘紧跟着爬出,膝盖刚触到地面,就听到琳娜清冷的声音:“起来,虫子。你的最后一关在这儿。”
阿尘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抬头一看,面前是一栋破旧的厂房,墙壁斑驳,窗户大多破碎。厂房前站着三个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年龄与琳娜和耀相仿,穿着同样昂贵却低调的衣服,眼神里带着一种猎人般的兴奋。地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木箱,旁边散落着几根铁棍和一捆绳子。阿尘的心猛地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琳娜走上前,拍了拍木箱,笑容里带着几分残忍:“虫子,你不是说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吗?今天,我们给你个机会证明你的忠诚。”她顿了顿,朝那三个陌生人点了点头18岁的阿尘
琳娜的笑容在厂房的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冰冷,她拍了拍那个破旧木箱,目光扫过阿尘,像在审视一件即将被拆解的玩具。耀站在一旁,双手插兜,眼神里带着戏谑与不屑。那三个陌生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成半圈,脸上挂着猎奇的笑,仿佛在期待一场好戏。厂房内空气潮湿,弥漫着铁锈和霉味,地上散落的铁棍和绳子在昏光下泛着冷光,让阿尘的喉咙一阵发紧。
琳娜蹲下身,捡起一根铁棍,在手中掂了掂,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虫子,你的最后一关很简单,”她慢条斯理地说,语气轻描淡写却透着恶意,“我们要玩个游戏,叫‘忠诚试炼’。你不是说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吗?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她朝木箱一指,“打开它,里面有你的‘任务’。”
阿尘的腿有些发软,但他不敢违抗,颤抖着走上前,跪在木箱旁,双手掀开沉重的盖子。箱子里躺着一堆杂物:几件破旧的衣物、一把生锈的匕首、一卷胶带,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他拿起纸条,上面用潦草的字迹写着:“取悦我们,代价自负。”阿尘的心猛地一沉,抬头看向琳娜,眼中满是困惑与恐惧。
耀冷笑一声,接过话头:“别愣着,虫子。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五个人,每人给你一个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不管是什么。如果做不到,或者让我们不满意…”他顿了顿,踢了踢地上的铁棍,“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厂房。”
第一个男人——一个留着短胡子、穿皮夹克的家伙——率先走上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我先来。”他从箱子里拿起那把生锈的匕首,扔到阿尘脚边,“用这个,在你手臂上刻个‘奴’字。刻得深一点,让我们看清你的忠诚。”
阿尘愣住了,盯着地上的匕首,双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琳娜和耀的眼神冷得像刀,另一个女人甚至已经拿出手机,准备录下这一幕。他咬紧牙关,捡起匕首,手抖得几乎划破自己的手指。匕首的锈迹刺鼻,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刀尖抵在自己的左臂上,狠狠划下。血珠立刻渗出,疼得他闷哼一声,但他不敢停,咬着牙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奴”字,血顺着手臂淌到地上。
“还行,够贱。”短胡子男人满意地点点头,退到一旁。第二个男人——一个瘦高个,戴着金丝眼镜——走上前,语气平静却带着阴冷的压迫感:“我的命令简单。脱光衣服,跪着爬一圈厂房,边爬边喊‘我是你们的狗’。”
阿尘的脸瞬间涨红,屈辱像潮水般涌上心头,但他不敢反抗。他脱下破旧的衬衫和裤子,只剩一条破洞的内裤,跪在地上,开始绕着厂房爬行。每迈一步,粗糙的水泥地都磨得他膝盖刺痛,但他还是扯着嗓子喊:“我是你们的狗!我是你们的狗!”声音在空荡的厂房里回荡,引来一阵哄笑。那个女人一边录视频,一边嘲讽:“这家伙真是天生的贱种。”
轮到那个女人时,她穿着紧身皮裤,踩着一双尖头靴,慢悠悠地走上前,俯身盯着阿尘的眼睛,语气轻佻:“我的命令嘛…把你刚才刻的那个字,用胶带贴满,然后撕下来。让我看看你有多能忍。”阿尘咬紧牙关,拿起箱子里的胶带,缠在血淋淋的伤口上,每缠一圈都疼得他冷汗直冒。撕下时,胶带连带着血肉一起扯下,他疼得几乎晕过去,但硬是没喊出声,只低声呢喃:“为了您…我什么都愿意…”
琳娜和耀一直冷眼旁观,直到轮到他们。耀先开口,语气懒散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虫子,我的命令是——用你的舌头,把我这双鞋舔干净。”他抬起一只脚,45码的限量版运动鞋上沾着些许灰尘和泥点。阿尘毫不犹豫地趴下,嘴唇贴上鞋面,舔舐着每一寸污渍,泥土的苦涩和皮革的味道在他口中混杂。他舔得专注而虔诚,仿佛这双鞋是他的整个世界。
最后轮到琳娜。她慢条斯理地走上前,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蹲下身,捏住阿尘的下巴,逼他直视她的眼睛。“虫子,你干得不错,贱得让我都意外。”她顿了顿,笑容变得冰冷,“我的命令是——从现在开始,你得发誓,永远做我们的奴仆,不许有任何反抗,哪怕我们让你去死,你也得笑着去。说,‘我发誓’。”
阿尘的眼神狂热而空洞,他毫不犹豫地开口:“我发誓…我永远是您的奴仆…我愿意为您去死…”他的声音低沉却坚定,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琳娜满意地点点头,起身拍拍手:“好了,游戏结束。你通过了,虫子。”
然而,耀却冷笑一声,走上前,一脚踢在阿尘的胸口,将他踹倒在地。“通过?不过是给我们找了个新玩具罢了。”他转头看向琳娜,眼中闪过一丝默契,“这家伙留着还有用,琳娜。让他去干点脏活,比如…处理我们不想碰的事。”
琳娜点点头,目光扫过阿尘,带着一种猫戏老鼠的残忍:“不错,虫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专属仆人’。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伺候不好,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扔回贫民窟…或者更糟的地方。”
阿尘趴在地上,胸口剧痛,血和汗混在一起,但他眼中却闪着病态的光。他爬到琳娜脚边,亲吻她的高跟鞋,低声呢喃:“谢谢…谢谢您收留我…”周围的笑声和嘲讽再次响起,但阿尘毫不在意。他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归属”,哪怕是以如此卑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