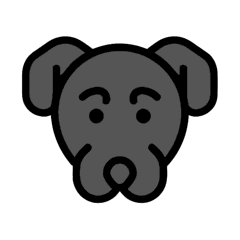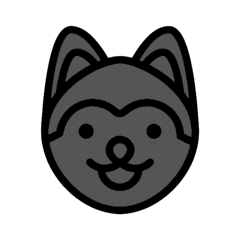暮色渐浓之时
阉割致残短篇原创现实NTR踩踏虐杀圣水
前些天一些本站知名作者们在跟我的主人见面,并顺带着接见我时,面对面称呼我为「站长」,让我有一种奇妙的不适应感。本想记住当时谈及的部分内容,可我久未睡眠的脑子并不同意,只零星地将只言片语搅拌进窗外的浓雾中,再把那浆糊勉强塞入脑海。于是,在九月末的某天凌晨,我独自缩在机场的角落里睡过去时,这些际遇在由短期记忆转换为长期记忆的路上逃离了海马体,径直远航而去。
醒来时,脑海里残留的是下面这段莫名其妙的性幻想。我便在候机室里拿出电脑,将它草率地记了下来。
免责声明:
- 不是什么认真的黄文,就是我个人的性幻想而已。还是那句话:冲得爽就行,产物的质量不重要。
- 文中的「」并无影射我的主人,任何地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中的「」纯粹为虚构人物,本文中未指定性别,可以理解为任意性别,但无须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文中的「」这个称呼,灵感则源自上面段落所叙述的不适应感。
-只是幻想中的性癖而已。现实里,我的主人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的生命。我不可能能够接受被她抛弃的。
以上为作者自白。以下为正文。
盯着那块 GPS 航图屏看了一会儿,再三检查经纬度之后,关掉了船上唯一的引擎:「这里就是约定好碰面的地方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应了一声,便穿着拖鞋走出船舱,走到了甲板边,低头看下去。看到这个暗礁的深度正如海图所述,恰巧合适,她便将船锚缓缓放下。
几年前,那个被称作「」的人以寥寥几万块钱的低价买下了这艘名为「告别号」的破旧游船,准备送给。只是当时船上既没有这块 Garmin 航图屏,也没有全自动的锚机,甚至连油箱管路的完整性都存疑。经过了他一年多的努力整修,这艘船才终于来到了最好的状态,并终于被正式赠送给。而「」终于也已经准备好和「告别号」彻底告别了。
太阳已经过了最毒辣的时候,此刻正缓步地向着西边的海平线前进。另一个正在朝着西边前进的,是「」的单人划艇:他今天一早就已经从另一个岛上出发向西。在洋流的帮助下,小划艇一个多小时便已离开了领海,进入无人的海域。风平浪静,海域也并不复杂,身下的这艘小划艇是多年前送给他的礼物,可靠性毋庸置疑。他自信,只需要靠着指南针和手机上的地图,便能准时赶到预先选好的汇合点。
终于,「」看到了「告别号」小小的影子,更卖力地划动起船桨来。和在船舱里看着视野中那艘小小的划艇一点点变大。终于,在开始起锚的同时,「」爬上了「告别号」的左舷,并用绳子将小划艇也拉了上来,并挪动到甲板的尾端。
回到了船舱中,对着仪表板确认着游船漂流的方向。「」,或者说的奴隶,则在放置完小划艇后,乖巧地跪在的面前,对着他唯一的神祗,满是渴求地磕了一个头。
暖洋洋地笑着,熟练地将一只脚狠狠跺到了奴隶的脑袋上。「」觉得这一次自己的主人踩得格外重,几乎让他的颅骨都碎裂开来,更让他本就被烈日烘烤了大半天的脑袋更加晕眩。但只是愈发用力地用鞋底碾压着他的脑袋,将他的头发都拽下来了几根。
「拖鞋还是不太方便呢,对吧?」对奴隶说着:「我的靴子就在后面房间进去的桌子上,去帮我拿过来吧。」
「」于是跑到船舱里,从桌上的鞋盒里取出那双沉甸甸的短靴。他一回头,却看到已经跟了过来,坐在船舱门口的椅子上了。
他端着鞋盒,到的跟前跪下。靴子里塞着一双白色的棉袜。准确来说,是一双他认识的,曾经是白色,现在却已被穿得发黄发黑的棉袜。其实很少会把袜子穿到这么脏,他猜想,这次的袜子会是这样,或许是有意宠爱他吧。但他也不敢也无须开口确认这样的猜想,他的大脑只需要对着袜底的污渍发情就好了。他一边欣赏着,一边慢慢将袜子穿到这双永远令他神魂颠倒的脚上;他恃宠而骄,穿袜时都并不忌惮于触碰到她光洁的皮肤。最后,他端起那双靴子,慢慢为她套上。
看得出,自己的奴隶正在颤抖着。这双皮靴是好些年前他们一起定制的,坚硬的钢头上还带着一些钉刺,看上去便让人心惊胆寒。它的威力确实也非同小可,因此在试用过一次之后,便被束之高阁,直到现在。
靴尖的钉刺轻轻划过他的手心,他又是一颤。终于,在伸手为她整理鞋舌的时候,他的勃起已经无可掩藏。将这一切看到眼里,欣慰地笑了出来。
她将右腿搭在左腿上,凑到他的面前轻轻摆动:「说起来,当时你自己有提议过的吧?到船上来之后,就保持着全裸的跪姿。」
「对不起主人,我以为主人当时并没有同意我的提议。我这就…」奴隶说着,开始脱去身上的衣物。
「裸着能做到,那关于跪着这一点呢?」她看到了他高高翘起的肉棒,忍不住用靴子上的尖刺轻轻挑动起来:「你刚才,好像是站着跑进船舱里的吧?」
「是的,」奴隶仰望着主人,小声辩解:「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主人久等。」
「没事的哦,我会帮你纠正错误的。」她笑着站起来身,抬起脚,在奴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便对着他的膝盖狠狠踹了上去。
奴隶被这毫无预兆的一击直接踢倒。那可怕的靴子又从侧面再次踹击到膝关节。只这么两下,他的左膝变已经血肉模糊。
肉体的痛苦让奴隶流出眼泪,可泪水的背后却是惊喜的目光。他没有见过这般坚决的,也很久没领会过她如此毫不保留地将百分百的气力赐予于他。
连续的踹击让痛得倒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啜泣。主人的靴子高高抬起,从天而降,碾在已经碎裂的膝关节,跺在奴隶脆弱的胫骨上,踹在他毫无防备的脚踝。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骨头碎裂的声音。即使忍不住挣扎和闪躲,也都无济于事。
「现在,」的靴子踩在他断裂的腿骨上拧动着:「你不跪着的错误,就纠正好了吧?接下来,就不会再犯这个错了哦。该说什么呀?」
「谢…谢谢主人!」奴隶本能地喊出声。
靴尖的金属钉占满了血,在金黄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他迎着那刺眼的红光,抬头看着她脸上的惨笑。
「好啦,我也累了,」她终于将靴子从他破碎的脚踝上移开:「就不欺负你了。去右边驾驶室门那里,和打个招呼吧。」
「」听了的指示,挪动着自己残废的小腿,缓缓向右舷跪行而去。他这才发现,船早已驶离了暗礁,此刻四周只剩一望无际、深不见底的南太平洋。
到后面船舱的冰箱里拿了一瓶香槟,和手牵着手,一起走到了右舷。打开酒瓶时,恶作剧般地让瓶塞对着奴隶的下体喷出,作为这一重大场合的庆祝。则准备好了酒杯,接过酒瓶,倒上了三杯酒,准备分给三个人。
接过自己的那杯酒,却不让递酒给「」。
有些疑惑:「诶?为什么不让他喝呀?你不是不在意什么『酒后 SM 是错误行为』的鬼话,以前经常跟他喝酒的吗?」
「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倒不能说是鬼话啦…虽然我虐他的时候确实不经常在意,」嗤笑着解释道:「今天不让他喝酒,只是因为…这么重大的场合,他应该保持清醒嘛。说是为了让他遭受更多的痛苦和恐惧也罢,说是为了看到他理智的决心也罢,总之今天就剥夺他喝酒的权利吧。」
跪在一边的「」没有抗议。但他抬起头仰望着端着酒杯的的一瞬间,竟就此回想起来六年前和一起饮酒时的那个黄昏。
彼时,「」和还算是一对情侣,无可争议。则刚刚开始和在光怪陆离中交往。在的眼里,或者说在所有人的眼里,虽然「」才是的「正室」,但也绝对不算是第三者,而是光明正大,乃至更为骄傲地和在一起的。
元旦假期,原本是「」和一起出游,但也受邀加入,变成了略有些尴尬的三人游。旅途中,自然是和睡在同一间房。这是毫无争议的最佳安排,毕竟这对于和并不能朝夕相处的来说更公平,况且还能满足「」那变态的的绿帽癖。起初申请就睡在他们那间房的地板上或厕所里,但被干脆地回绝了。故作羞辱地说,她和独处时并不想被打扰。最终的安排,显然是和一起住在豪华套房里,而「」睡在街对面的廉价旅馆。
正当「」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通知他去一起吃晚饭时,却直接敲开了他房间的门。
「对不起哦,,我们已经吃完饭啦。说做完爱太累了,不想出门了,我就给她点了外卖。本来我想喊你一起吃的,但是说不用了,她说让我把我们吃剩下的带给你就好了。」
听到这话的「」,除了勃起,还能有什么反应呢?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地将桌子上剩下的半瓶酒倒入杯中,邀请与他同饮。
「说起来,我又重新看了一下写的文章的剧情,对的性癖做出了新的总结,所以,很想确认一下我的猜想对不对呢…」
「呃,你的猜想是?」
「我的猜想是,的性癖,其实是被抛弃吧?」
从「」那儿得到的回应,只是死一般的寂静,以及两腿掩藏不住的颤抖。
「我想,这样的猜测也不算太离奇,」继续说道:「像这样的变态,不管是怎么样的肉刑,都已经不会受不了了吧?像这样的极端的 M,就算是被鞭子抽上一万下,大概也不足为奇。一般的羞辱也很难达到你的阈值了,对吧?说了,就算是把你踩在街头,让你磕头一小时,你也不会觉得屈辱的。所以,我猜,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你这样的受虐狂都感觉到痛到无法接受,因而也就让你更加渴望——那就是被抛弃。」
「」露出奇怪的表情:「真是很有想象力的推理呢。」
「根本不需要太多推理的吧?最近四年里只发过三篇黄文,而它们的剧情全部都以男主角被抛弃为核心,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生怕事情失控,开口澄清着:「那也只是幻想中的性癖而已。现实里,我的主人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的生命。我不可能能够接受被她抛弃的。」
「是的,我当然知道主人是你的一切呀,」微微笑着:「所以,正因为如此,如果被你的主人抛弃,才会最最痛彻心扉吧?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恋痛癖来说,越是死心塌地地爱着,就越会忍不住渴望被她抛弃的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想象中…或许是吧。但是现实里,就算我自己能接受被抛弃,我也需要对我负责到底,守护到底,保证她的幸福。所以被抛弃就不是个选项啦!」
「,你真的以为你的主人需要你的守护吗?」的笑里带着一丝恶意:「刚才还跟我说和我在一起很开心,甚至她都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哦。要说的话,今天的你,对于她来说就是个需要额外操心的累赘吧?她抛弃你的话,不仅可以达成的终极心愿,对她自己而言,或许也是更好的选择哦?」
「」的呼吸都已经难以平静,他心虚地逃避着:「可以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吗?」
「不要再提,是因为怕自己兴奋到失态吗?」满足而自信地发动总攻:「不如,让我看看你已经勃起成什么样子了吧?」
没等「」做出回应,他的椅子就已经被伸出脚向后踢开。他狼狈地半蹲在地上,才不致跌倒。
「现在,只有我能满足你被主人抛弃的愿望哦。按道理讲的话,是不是应该认真地请求我满足你的愿望呢?」
「」还在支支吾吾,便已经继续说道:「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想,我会让彻彻底底地嫌弃你,会让她下定决心和你分手,甚至拉黑你的所有联系方式的哦。我已经占据她的身体了,接下来也就是占据她的脑袋和她的心,让她把你忘得一干二净。怎么样?」
「」已经双股战战,几乎站立不住了。当抬起脚轻轻用鞋底搭在「」胯下支起的小帐篷上,说出「跪下求我吧」五个字时,「」都觉得这是在大发慈悲地给他个台阶下,以免他主动跪下显得太过失态。
于是,「」就这么跪倒了下去。实在无法开口的他,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躲避着的目光。
「还是做不到开口请求我吗?可是,现在脑子里都已经在幻想着一边和我亲热着,一边鄙夷地看着你的样子了吧?」
「」的沉默,无疑是承认了这一点。
浅啜了几口酒之后,语气忽然严厉了几分,对「」命令道:「把裤子脱下来。现在。」
地上的男人被吓得刚刚将裤子褪下一点点,他勃起的肉棒便被的鞋底牢牢踩住。
「被你的情敌踩着,都能硬成这个样子,已经彻底没救了吧?这样恶心的变态,还是不要拖累你的主人比较好,对不对?」
「」呜咽着点头。
「所以,应该求我做什么事情,来帮你呢?」
「求求你…」已经失去所有理智和尊严的男人大口喘着气:「求求你让彻底抛弃我…拜托你了。」
「为什么求我呢?说清楚一点比较好吧。」粗糙的鞋底用力摩擦着他的下体:「而且,把你抛弃之后,又怎么办呢?」
「因为,因为我配不上,呜呜…求求你让和你在一起吧,让彻底离开我,彻底忘了我,这样她才能更幸福。」
「不对哦!」的鞋子从「」的下体移开,径直踹到了他的脸上:「明明就是你自己想满足被抛弃的变态欲望,却装作是为了她好,这也太卑鄙了吧?」
「我…对不起…」
「从一开始,被绿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吧。明明是你自己想满足当绿奴的性癖,却美化成是因为什么『觉得自己独占主人的话太委屈主人』、『主人值得得到更多』而去让和别人交往。不觉得这卑劣得有些过分了吗?」
「对不起…都是我自己变态。我对不起。」
「那么,重新说吧?」这次更加用力地将鞋底踩到了他的肉棒上:「说清楚,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要。」
「」明明从来完全无法想象被除了自己主人外的任何人这么居高临下地对待,可他现在却在脑海中的幻象和鞋底的摩擦中,完全失去了自己。他甚至已经跪不直身子,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求求你,求求你让满足我被抛弃的性癖吧!我…我好想彻底失去…求求你了,大人,求求你把从我身边彻底夺走吧!呜呜…」
一边说着,「」竟已经在情敌的鞋底的践踏下,将大股的精液完全喷射了到了自己的大腿上、地板上。
「做得很好哦,」满意地拿出手机,拍着照片:「瞒着你主人,在别人的脚下射精,这算是对你主人彻彻底底的背叛了吧?只要我把这张照片给看,一定能更轻松地劝服她抛弃你的,嘿嘿。」
「嗯,」高潮余韵中的「」此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微微点头,无助地看着地上的一滩滩白浆。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已经无可挽回。
终于,他的泪水也一齐流到了地上。
「为什么要哭成这个样子呀?」继续拨弄着「」已经疲软下来的肉茎:「是到了贤者时间了,就反悔,不想被抛弃了吗?」
「」犹豫了一会儿后,微微点头。
「可是,理性考量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根本配不上自己的主人的吧?根据你自己的说法,你离配得上还很远的吧。」
「」泪眼汪汪地看着:「是这样。我知道现在和你在一起更幸福。可是…可是我还是担心,我会担心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能一直对她好…」
「这是不信任我吗?」诘问他。
「我不知道…」地上的男人说着:「如果能确定我主人和你在一起,一直都会更幸福的话,就算是付出我的全部身体、积蓄甚至生命,我也会促成我主人抛弃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相信你。」
「从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我还是你,在是否能始终如一这件事上的期望,都没显著差异的吧。这种情况下,她选择现在看起来更好的选项,不就好了吗?」
此刻,一人高高在上,一人低伏地板。孰高孰低,谁是更好的选项,不言自明。
地上的男人心领神会,把头垂得更低了:「是,我知道了。」
「那么,我就回去陪睡觉啦!」满脸都是胜利者的得意,起身将酒一饮而尽,抛下了一句:「就拜托自己准备好,明天该怎么当面向提出请求了吧?这种事,还是你自己说比较有诚意呢。」
「」木然地点点头,看着打开房门离开。他一夜都没能再从地板上爬起来。
六年过后的此时此刻,站在船上的,也回想起了那同一个的黄昏,想起了「」初次丢盔弃甲地跪在自己跟前的模样。
只不过,那次「」并没有被真的抛弃。那天的一切,并非出于自己一个人的意愿;事实上,在去「」的房间之前,便已经和商量好了大概的计划,其本意也只是半开玩笑地试探下「」的绿奴程度,顺便让「」体验一下他未曾体验过的快感而已。
事后,虽然对「」毫不抵抗地任由将他玩弄到射精非常不满,甚至对他的忠诚感到幻灭,但得知了「」哭泣着担心她的幸福的样子,便果然还是不忍心真抛弃他。而虽然确实在心底有着一丝希望「抛弃」成真,而让自己占有的私心,但自然还是会顺从的决意。
「」没有去追问和具体的心态究竟是怎样。自知理亏的他,不敢向开口。冷静下来的他,更多的时候还庆幸着自己没有被抛弃——极端的性幻想注定是幻想,现实中的他每分每秒都那么需要。
一度完全当真并为之射精的所谓「抛弃」,不知该说是虚幻,还是烂尾。
此刻,也回想起了上次「抛弃」并未成真时,自己心里的五味杂陈。他装作轻松地笑笑:「这次不会和上次说要抛弃一样,又烂尾了吧?」
「这么害怕又烂尾吗?」笑着拍了拍的脑袋:「你是不是就想让他早点滚蛋,好和我享受二人世界呀?」
「那倒没有啦,」回应道:「只是,这次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要是再烂尾,很难收场的吧?」
的确,这次「告别号」和小划艇分别从美拉尼西亚地区不同的国家出发,在无人的海域汇合,然后孤筏重洋,在公海上漂流,以便在无人能知晓时完成最终的计划,从规划到实施,自然是耗费了三人不少的心血的。
不过,几分钟前用力踢碎奴隶的膝盖和小腿的举动,无疑是在斩断着退路,向自己和奴隶宣誓,这次的计划不会再烂尾了。
跪在地上的「」忽然开口:「说起来,其实上次的『抛弃』,也不算是完全烂尾的吧?毕竟都已经不再是我的…我的女朋友了。」
确实,在那后的一些年里,和走的越来越近,在一起的时间都甚至开始超过「」和在一起的时间。曾经作为唯一伴侣的「」,真真切切地被边缘化了。虽然没有明确的分手,他们已经默契地很久很久没有过任何亲密接触了。
「你再说什么呢?这不能叫做『抛弃』吧?」再次用靴子挑弄起他腿上的伤口,制造着疼痛:「『抛弃』的话,可是要彻底让你从我的生命中消失的。都允许你继续做我的奴隶了,怎么可能还算是抛弃?」
奴隶在痛苦中挤出回应:「是。主人确实没抛弃我,一直都留着我,我很幸福的。」
「我甚至都怀疑,你比最早的时候还更幸福呢,」轻轻摆着自己的双脚:「我是说,比起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那也很合理嘛。毕竟,」接过话来:「不是一直都觉得,M 是断然不配也不该和自己的主人恋爱的吗?现在这样也算是言行合一吧。」
「」点了点头:「确实,我变为单纯的奴隶,应该算是让一切更合理、更不会有冲突的优化。我确实不该将这说成是『抛弃』的。我的错。」
将酒杯从唇间放下,没回应脚下的男人,而是指着远方,呼喊道:「还有不到半小时就该日落了吧?今天天气真棒,好久没看到过这么干净的海上日落了。」
大海的颜色越来越深。西边仅有的几片薄云,原本还透着金黄的阳光,现在逐渐变为一片密实的血红色。和那欢快的碰杯声,让地上的奴隶多少有点艳羡。
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对啦,,我跟你说过,之前他求了我好几次,想要再…所以…我不知道你能接受吗?」
「当然啦!我不都答应过你了嘛!」轻轻将抱起来,把她放到了躺椅上。自己则站在的身后,双臂环抱着她。
地上跪着的男人立刻领悟,并连忙开口感激大度地允许自己最后玷污一次的身体。「」于是爬到的跟前,伸出舌头,探寻起两腿之间那令他痴念已久的圣地。仰起脑袋与对视,自己轻轻将内裤褪下,将腿微微分开。当奴隶的舌尖终于触及宝珠的一瞬,她只是微微颤抖,而他却已经抽搐得近乎高潮。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哦…你可要好好表现!」她说完后,又像是被自己逗笑了一样,咯咯了两声。
奴隶先是用舌尖轻轻挑动着她的阴蒂,待她放松下来后,便用力摩挲起来。他的舌头毫无策略性、毫无保留地拿出最高的频率和力度努力着,竭尽全力试图取悦着她。舌头很快便酸痛不堪,但他别无选择。几个月前,他上一次成功给她带来高潮时那绝妙的粉色回忆仍留在脑海中,激励着他无休无止地继续着攀爬之路。她每一次轻轻挪动自己的大腿,哪怕只是无意之举,都敦促着他在黑暗中透支更多的气力。
他只想再感受一次的高潮。从无数年前的第一次起,他便永远地沦陷于这样的恩赐——感受着自己的唇舌给带来高潮,远比自己射精还要来得满足无数倍。当然这两者常常结伴而至:在用腿夹紧他的脑袋,全身抖动不止时,已无须再附加什么刺激,他那根本没被触碰的阳具便能和主人同步达到高潮,将精液喷洒在她的脚下。
就让这样的恩泽再来一次吧。奴隶这么想着,舌头深耕不止。终于,的呼吸声愈发急促,双腿也不再静止不动。
「怎么办…要…要到了!」在娇喘声中小声呢喃。也弯下身来,凑向潮红的脸颊,用自己的嘴唇堵住她的另一对樱唇。
可却没有如奴隶所期待的那样夹紧自己的双腿迎接着顶点。恰恰相反,她先折起了自己的双腿,然后奋力将奴隶踹开。
「我不要他给的高潮!」她对着和「」同样震惊的说道:「高潮的话,我还是,要一会儿你来给我嘛!」
「」没有注意到的是,折起双腿前,忽然摇着头提醒自己清醒。这样如寸止般地对待自己,自然是抑制着自己的性欲和本能的。换来的好处则被剩下两人平分:因为被此般偏爱,脸上充满了喜悦,性欲也被彻底点燃,恨不得立刻亲自向兑现一次绝妙的高潮。而「」则因自己的愿望在最后时刻被无情剥夺,还顺带着被嫌弃和羞辱,而兴奋得差点抛下主人兀自射精。
把自己的小手轻轻放到方才被舔过的私处,又对仍跪在她腿间的奴隶命令道:「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舌头辛苦成什么样子啦~」
奴隶跪直了身子,将舌头用力伸出来,呈现给自己的主人。
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来一把剪刀,微笑着用手捏住奴隶的舌头,并在他惊惶的神情中,将剪刀凑到了奴隶的舌根。
「现在,舌头是再也用不到了的吧?」
奴隶的舌头被捏住,说不了话,只是委屈地微微点头。
剪刀合拢。舌尖方才感受着主人的体温,此刻却被痛苦淹没。继续嘲笑着他:「还真指望着,能最后再给我舔到高潮一次呀?噗,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你哪里还有那个资格。」
剪刀再次张开、合拢,奴隶的舌头被彻底剪断。他的身体陡然绷紧,惨叫声和精液一起脱缰而出。
她毫不意外:「啧啧,我就知道你又要射精了。永远都是个被剥夺的越多就越爽的死变态,永远都这么恶心。」
先是随手将被割下的舌头丢到自己的脚底,装作不在意地用靴底踩了上去,又则将自己脱下的内裤顺手抓了过来,塞进奴隶的嘴巴里给他止血。
在痛苦中蜷缩作一团的「」,又被轻轻踢了一踢:「好了,去后面准备你的水泥去吧!我还要在这儿和好好亲热呢。」
「」艰难地跪爬着到了船尾,从船舱里拖出来先前准备的几大袋快干硅酸盐水泥,以及搅拌水泥用的大桶。原则是讲,水泥粉应该是要加淡水混合的,但不在意结构强度和寿命的话,用随手可得的海水来搅拌也无妨。
是的,这一次三人的计划,便是满足「」的终极愿望,让他被他心爱的主人虐杀。至于用水泥来封存尸体,实属对水泥埋尸案的拙劣模仿而已。
当然,与水泥埋尸案不同,「」在死前将接受的不会是暴行,而是彻头彻尾的宠爱。他知道,不管他怎么任性,都将会又一次宠溺地满足他的所有渴求。他将会躺在那艘他心爱的小划艇里,一边看着的眼睛,一边任由水泥没过他的身子,将划艇填满。然后,随着划艇这一关键证物,一起永远地沉没在南太平洋的海底,再不会被人发现,也不会被人想起。
「」静静看着这艘蓝白相间的小划艇,心里满是甜蜜。那一年,当还是每天依偎在他怀中的爱人时,攒钱给他买了这艘他心水已久却一直不舍得买下的小划艇,作为纪念日的礼物。甚至还在小划艇的外面用丙烯颜料画上了他喜欢的动画形象,在内侧刻上了他们俩的名字,让这个小划艇成为最特别的爱的礼物。到如今,这个小划艇也将成为最完美最浪漫的棺木。
一个大桶里倒入水泥粉,另一个桶中装好了适量的用来混合的海水。不能在准备好之前提前将它们混合,否则水泥会过快凝固。而他此时仍依稀听到的娇喘声从船头传来,他知道自己只能等待。
正站船头,双手搭在栏杆上,看着那颗火红的太阳,此刻艰难地悬在海平线上。刚刚与她共赴鱼水之欢的温柔地站在她的身后,轻轻环抱住她的腰肢。
「,我从来没见过你像今天这样对这么坏呢。」
「毕竟都答应了他,要亲手了结他了,就干脆做全套了嘛。要是连开始这些坏都不舍得的话,到时候可就真得烂尾了。」
点头称赞:「是这个道理没错啦!不过,我还是没想到你会答应他,把他了结掉。」
「没办法的嘛。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了。他那么需要我,可我又不可能一边和你在一起,一边还满足他每天的需求的。」
「我知道,这确实是一劳永逸了的做法。」
重复着她早已告诉过的话:「当然也不是我自己想要逃避,才同意虐杀他的嘛!我哪可能有那么坏啦。主要还是他自己真的想要啊。自从和他分居之后,他就一直都磨着我,说想要死在我的脚下。我也知道很离谱呀,可他就是这么任性的人。而我也磨不过他,既然当年都答应了做他的主人,就只能一直宠他了呀。」
撒娇般地捏了捏的乳晕:「你总是说要宠他,我听了可都要吃醋了诶。」
也将手往的胯下一掐,作为报复:「你都已经从他手上把我抢到了,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吧!」
「我就是偶尔会觉得…」的声音依然温柔:「会觉得,的心里好像总还是最在乎嘛。」
「你们俩我都在乎,不行吗?而且你有什么可以吃醋的,你现在可是我唯一的伴侣呀!」的手轻轻爱抚着:「就算我对他有感情,也单纯就只是主人对奴隶的感情而已了,和跟你之间的恋爱完全不是一种东西的嘛。我可是你的女朋友!你没必要沦落到跟一个奴隶去比较吧?」
「我知道。可是你每次宠,我心里难免会稍微有点奇怪的感觉啦!当然…我不是要说沫你不好。」
「好啦好啦,他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再担心了。到了明天早上,他就再也不存在了,你也就再也不用看到我宠他啦!」
「嗯,」点点头:「我知道的。对不起啦,,我心眼总是这么小。」
「呐呐,没事啦,这不是因为你爱我,才会这么容易吃醋的嘛。我怎么可能会舍得怪你!」转过身吻住的唇,好几秒后才重新开口:「我知道,我一直和他藕断丝连,会让你会没有安全感的。对不起,这是我不好。但是这很快就会解决了,别担心啦,好不好?」
「嗯!谢谢你!你最好啦!」
「当然啦!」她嘟起嘴:「那我们去船后面那儿看看吧?说不定他已经准备好了要不再碍你眼了,嘿嘿。」
「」在的示意下将水泥混合了起来,然后立刻乖乖地躺进了他的小划艇里。
他的脑袋被作为枕头的船桨高高垫起,他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抬着一片木板,木板微微悬在胸口上方。这样一来,他便不会因为水泥凝固后压迫他的胸腔使他无法呼吸,而立刻死去了。他的下体则被一条绳子绑住,向上拉扯起来。
帮忙将桶倾倒过来,将水泥倒到「」的身上,直至水泥一点点逐渐填满小划艇内部的空间,淹没奴隶的双腿、双手、腰部和肩膀。最终,只有他的脸庞和性器还暴露在空气中未被淹没。
当「」躺在船里等着水泥干燥的时候,和又已经到船头继续喝着香槟欣赏着落日。奴隶在幻想着,船头的二人又会在以什么样的姿态亲热着呢?精力这么旺盛的,会再一次向求欢吗?
当然,连耳廓都被水泥埋住大半的奴隶,自然是无从知道任何答案的。他能做的只是等待。脑袋只能朝着正上方看去的他,甚至没法看到太阳完全消隐在海平线上的一瞬。但从蓦然变蓝的天色中,他知道那颗作为一切温暖的源头的恒星已经离去,而他已没有机会再见到那唯一炽热的存在。日落已是几分钟前的事;将 civil twilight 和 nautical twilight 一并算上的话,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游刃有余地在黑暗到来之前做完一切。
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快干水泥已经完全定型,因此,她将那根拴着奴隶阴茎和阴囊根部并向上拉扯的绳子解开。从水泥中穿出的性器,便自由地躺在了硬实的水泥平面上。
「不准反悔了哦,」轻轻擦掉自己被海风吹出的眼泪,笑着对奴隶说:「现在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一块肉而已了。」
奴隶想要点头回应,可脑袋早已被水泥牢牢固定,动弹不了半点。他那失去了舌头的嘴巴,也依然被主人的内裤牢牢堵着,没法发出任何有意义的声音。
他的下身还是给出了回应:已经射过一次的他,在听到来自主人的死亡宣判时,又一次无法抑制地充血挺立起来。
「不过,」在的搀扶下,站到了已经干燥的水泥上:「既然所有人都知道我宠你了,就给你点最后的奖励吧。」
奴隶望穿水,深情却又发情地注视着。也宠溺地看着他,然后慢慢抬起脚,用力跺在他的性器上,用全身的体重碾压着他的睾丸扭动着。奴隶的肉棒连同两颗无助的蛋蛋,都被瞬间压扁。他的惨叫声穿透了堵住嘴巴的内裤,回响在南太平洋上空。
如此重复跺击几下之后,奴隶自然已经受不住这样的疼痛。却并未止步于这样的踩踏,而是扬起自己的脚,瞄准奴隶的阴茎,狠狠踢踹上去。
坚硬的靴头几乎将他被阴茎直接折断,而靴子上的尖刺直接撕破了他的皮肤,令鲜血从肉茎里渗出。第二脚用靴头朝着蛋蛋踢上去,尖刺在阴囊上划出了裂口。奴隶惨叫着,却丝毫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用无止尽的踢踹和踩跺,继续临幸着他那淫亵的下体。
终于,他的阴囊在连续的暴击下完全裂开。脆弱的睾丸在失去了保护的情况下被鞋底以全速冲击着,碾压在水泥平面上。已经变形、肿大且暴露的睾丸立刻又遭到踢踹——靴头的尖刺戳入了睾丸,并就此粗暴地将睾丸向前拖拽,几乎将精索扯断。
以前也曾踩踏过许多次他的性器,但从来都能将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致将它们毁坏。此次再也不用克制,只需随意地释放出自己的气力,倒确实是令人畅快的事情。更何况方圆五海里甚至十海里内都再没有第四个人,她再也不用担心他的惨叫声惊扰到邻居。
脚下的奴隶则在无尽的痛楚中勉强分辨出自己一侧睾丸终于破裂的尖锐痛感,在近乎昏厥的时刻看到另一颗睾丸内精细的结缔组织化作浆状,从睾丸白膜的破口喷涌而出。他见证着自己的海绵体在她的踹击下被一点点撕裂,并将鲜血喷洒到他的脸上,遮盖住他的视野。他通过一直眨眼将血液从角膜上清理掉之后,终于才又能看到那些并未亲眼见过的身体组织以破碎的形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痛得近乎失去意识,但残存的意识也都被幸福所淹没。在这所剩无多的生命中竟然还能实现被主人亲自阉割的完美幻想,令他倍感惊喜。他明白,这世上不仅不会有第二个如此宠溺他的人,甚至都不会有第二个如此宠爱自己的奴隶的主人。
在靴子无休止的摧残下,从水泥中伸出来的终于不再是一个男人高高立起的的阳物,而只剩一堆淹没在鲜血中的肉泥,辨认不出任何形状。
「累啦!」看到已经实在不剩什么可以踩踏的东西,便从小划艇上走了下来。看着奴隶的下身一直在流血,她索性拿过一些水泥粉,朝着奴隶的下体撒上去,以多少起到些止血效果。就此,那曾经是他阳物的地方,现在便是一团红灰色的泥状物质了。
奴隶已经难以保持清醒。而剧烈运动之后,坐在椅子上休息着,便再也没发话。天色渐深,空气陷入寂静,连风声似都停歇了。
先打破沉默:「那么,现在我们趁天黑前,把他推到海里?」
点点头,却撞上了奴隶那痛苦而留恋的目光。她在犹豫后缓缓开口:「唉,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好准备。」
对这样的并不惊讶:「我知道的。不过,都已经到现在这样子了,就得负责到底啦。总不能又烂尾,把他从水泥里挖出来吧?」
「确实不能…吧。」摇摇头,但依然坐在椅子上,无法起身。
「没事的,就算你会舍不得他,我也不会怪你啦,」温柔地握住了的手:「而且,你确实也没义务背负上亲手杀掉他这样的重担,所以…不用勉强的。」
「那怎么办呀?」失去了决心的有一丝颓丧:「难道真的又烂尾吗?但就算那样,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才能把他挖出来吧?」
「我有一个主意,」说道:「既不会烂尾,也不会要你现在就逼着自己下手。最棒的是,我猜想也会很喜欢的。」
举棋不定的,当然没理由拒绝的帮助:「那你说说你的主意吧?」
「我们就把放置在这里不管,就没问题了。可以当作是一种放置 play 吧。」
「然后呢?」疑惑地问。
「已经失了不少血的,不可能挨得住明天一整天的暴晒。在那之前他就会死掉的。而等自然死亡之后,我们再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尸体推到海里就行。这样的话,能实现在被你虐杀的同时,你又不用亲手终结他的生命。」
「都把他这么固定起来了,放着他不管的话,跟亲手终结他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嘛!」
「亲手终结的生命的话,他是没有选择的呀,」继续补充道:「但现在这样,随时都有求饶的能力。虽然他说不了话,但他想的话可以发出喊声,让我们过来把他救出来的。他虽然连点头和摇头都做不到,但至少可以眨眼睛跟我们沟通嘛。」
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还是犹疑着:「但是,把他就那么活生生暴晒到死,也太残忍了点。他就算是抖 M,也只是喜欢被我亲手虐待而已!没人会喜欢独自暴晒到死这类完全没有兴奋点的折磨的。」
说道:「没事的,这不都说了吗,他如果受不了,随时都能求救的嘛。而且你别急,说不定,他真的会喜欢被那么折磨的哦。」
于是径直和被封在水泥里的男人对话起来:「,你听明白我的主意了吗?我和从现在开始就放着你不管啦。不过,任何时候你如果想放弃了,让我们敲碎水泥把你救出来的话,就大喊出声就好。按你刚才惨叫的音量,我们一定能听见的。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以的话,就眨眨左眼来代替点头吧。要是觉得不行,你就眨眨右眼来代替摇头。」
半秒的思考后,「」眨了眨左眼。
「不过,大概也知道,如果想救你出来却做不到的话,她会很难过的。而就算你被救出来,要送医也很麻烦,而且这辈子估计也没法正常行走了,肯定会成为的困扰和累赘的,没错吧?」
水泥里的男人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并眨了眨左眼。
「所以,现在有着最后的一次机会,通过保持沉默,来证明你在乎,为她考虑、不愿意给她添麻烦。而且还如你最喜欢的那样,是通过忍耐痛苦来证明。这个主意,一定也很喜欢吧?」
奴隶的左眼连续眨了好几下,脸上写满了兴奋。
「所以,一定很希望,从今晚开始,就完全把你抛之脑后,专心和我在一起的,对吧?」
得到的依然是肯定且愈发兴奋的回应。
「这个表情的意思,」翻译着:「是在诚心诚意地乞求满足你的愿望,求求她在你死掉之前都完全忽视你,对不对?」
这次,在奴隶兴奋地眨着左眼的同时,他的脸已被踩住。看出了他兴奋的模样,终于确信了这就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也终于用羞辱的言语挑逗起「」:「哦,你有这么乖吗?如果你痛苦得受不了了,会不会叫出声来,打扰我和亲热呀?」
奴隶连连眨着右眼,一脸顺从的表情,努力地表明着决心。其实光是把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与和别人亲热的场景放在同一个画面想象,他就已经兴奋到要失神。若他的肉棒还在的话,恐怕早已又一次一柱擎天。
他顺从而无辜的样子总能激起的施虐欲。的靴子粗暴地将他的嘴唇碾破,没好气地说:「啧!要是真想让我和好好在一起,不想打扰我们的话,你两年前就该识趣地自己去死才对的吧,而不是像这样自私地一直赖在我的生活里不走。你这样的人渣,居然还有脸假装自己在乎我。」
的身体因兴奋而颤抖起来,他嘴里徒劳地试图说出「对不起」,想向自己的主人道歉。但此时,已经将自己的靴子插入他的口中,将全身的重量压入他的口腔,并把他嘴里的那条内裤捅到他的食道深处。连奴隶的牙齿,都几乎被靴子上的尖刺给掰下来。
「你要安安静静地死掉,我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把你彻彻底底忘得一干二净的哦~」继续用自己的言语满足着他:「你也不想我之后和白头偕老时,脑海里还有你这个煞风景的垃圾的吧?」
奴隶并不知道该眨哪只眼睛来回应这样的反问句;但他眼里的歉意和乞怜,已表明了他的心迹。
点了点头,满心幸福。不仅是因为奴隶依然那么热烈地爱着她,也是因为他那几乎颅内高潮的表情足以证明,没有白白为了羞辱他而说出这些违心的话。一词一句,都让奴隶很是受用。
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满天的繁星将三人完全淹没。看到海平面上出现了一盏绿灯,便怀疑是正有船在从左向右驶过,于是前去驾驶室准备仔细观察。本也打算一同前去,但她还是想先完成与「」的最终告别。
「那么,为了避免你没怎么受到折磨就太快脱水死掉,我就还是在临走前,给你补一点水吧!」
明明现在并不是烈日当空,还是用了这个借口,来赏赐奴隶一些他一向最喜欢的圣水。以前都是奴隶每天追着她要,这一次她决心主动一些。在奴隶脑袋的上方蹲了下来,掀起了自己的裙子。
「」想抬头再看看她的胴体,却只见得到暗夜中的无数繁星。每一颗星星,都承载着他们曾拥有过的某段回忆。他好像从来没见过如此壮丽的星空,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汇聚在一起,连结在此刻。
或许是视角的限制,他没能在南天球辨认出银河,但温暖的尿液从的两腿间流出,裹挟着星光,倾泻而下,成为了更加真实而灵动的银河。随着那甘洌的圣水灌入他的口中,那么多年来,对他所有的宠爱,也全都又一次流入他的心中。
如此蹲着直接排尿,自然无法保证瞄准奴隶张开的嘴。但满脸都沾满圣水,也恰巧掩盖住了他止不住的泪水。
是自己没了舌头的缘故吗?奴隶甚至无法像以前那样,从的的圣水中甚至尝出一丝些微的苦涩。还是说,过去有过的些微苦涩,才是彻头彻尾的错觉呢?他不知道。
壮丽如银河,也无法是永恒的存在。最后几滴圣水终于也从的身体中滴下,奴隶想要接住它们,却因脑袋无法动弹,而只能眼睁睁将它们浪费。他于是不忍将口中的圣水立刻咽下,他还想再多品尝一会儿她的气息。
已经从驾驶室那边呼唤着。
「那,」起身说着:「我会像我答应你的那样,努力忘掉你的!」
奴隶奋力眨了眨左眼。他眼中映射出的星光,淹没在暮色中。
醒来时,脑海里残留的是下面这段莫名其妙的性幻想。我便在候机室里拿出电脑,将它草率地记了下来。
免责声明:
- 不是什么认真的黄文,就是我个人的性幻想而已。还是那句话:冲得爽就行,产物的质量不重要。
- 文中的「」并无影射我的主人,任何地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中的「」纯粹为虚构人物,本文中未指定性别,可以理解为任意性别,但无须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文中的「」这个称呼,灵感则源自上面段落所叙述的不适应感。
-
以上为作者自白。以下为正文。
盯着那块 GPS 航图屏看了一会儿,再三检查经纬度之后,关掉了船上唯一的引擎:「这里就是约定好碰面的地方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应了一声,便穿着拖鞋走出船舱,走到了甲板边,低头看下去。看到这个暗礁的深度正如海图所述,恰巧合适,她便将船锚缓缓放下。
几年前,那个被称作「」的人以寥寥几万块钱的低价买下了这艘名为「告别号」的破旧游船,准备送给。只是当时船上既没有这块 Garmin 航图屏,也没有全自动的锚机,甚至连油箱管路的完整性都存疑。经过了他一年多的努力整修,这艘船才终于来到了最好的状态,并终于被正式赠送给。而「」终于也已经准备好和「告别号」彻底告别了。
太阳已经过了最毒辣的时候,此刻正缓步地向着西边的海平线前进。另一个正在朝着西边前进的,是「」的单人划艇:他今天一早就已经从另一个岛上出发向西。在洋流的帮助下,小划艇一个多小时便已离开了领海,进入无人的海域。风平浪静,海域也并不复杂,身下的这艘小划艇是多年前送给他的礼物,可靠性毋庸置疑。他自信,只需要靠着指南针和手机上的地图,便能准时赶到预先选好的汇合点。
终于,「」看到了「告别号」小小的影子,更卖力地划动起船桨来。和在船舱里看着视野中那艘小小的划艇一点点变大。终于,在开始起锚的同时,「」爬上了「告别号」的左舷,并用绳子将小划艇也拉了上来,并挪动到甲板的尾端。
回到了船舱中,对着仪表板确认着游船漂流的方向。「」,或者说的奴隶,则在放置完小划艇后,乖巧地跪在的面前,对着他唯一的神祗,满是渴求地磕了一个头。
暖洋洋地笑着,熟练地将一只脚狠狠跺到了奴隶的脑袋上。「」觉得这一次自己的主人踩得格外重,几乎让他的颅骨都碎裂开来,更让他本就被烈日烘烤了大半天的脑袋更加晕眩。但只是愈发用力地用鞋底碾压着他的脑袋,将他的头发都拽下来了几根。
「拖鞋还是不太方便呢,对吧?」对奴隶说着:「我的靴子就在后面房间进去的桌子上,去帮我拿过来吧。」
「」于是跑到船舱里,从桌上的鞋盒里取出那双沉甸甸的短靴。他一回头,却看到已经跟了过来,坐在船舱门口的椅子上了。
他端着鞋盒,到的跟前跪下。靴子里塞着一双白色的棉袜。准确来说,是一双他认识的,曾经是白色,现在却已被穿得发黄发黑的棉袜。其实很少会把袜子穿到这么脏,他猜想,这次的袜子会是这样,或许是有意宠爱他吧。但他也不敢也无须开口确认这样的猜想,他的大脑只需要对着袜底的污渍发情就好了。他一边欣赏着,一边慢慢将袜子穿到这双永远令他神魂颠倒的脚上;他恃宠而骄,穿袜时都并不忌惮于触碰到她光洁的皮肤。最后,他端起那双靴子,慢慢为她套上。
看得出,自己的奴隶正在颤抖着。这双皮靴是好些年前他们一起定制的,坚硬的钢头上还带着一些钉刺,看上去便让人心惊胆寒。它的威力确实也非同小可,因此在试用过一次之后,便被束之高阁,直到现在。
靴尖的钉刺轻轻划过他的手心,他又是一颤。终于,在伸手为她整理鞋舌的时候,他的勃起已经无可掩藏。将这一切看到眼里,欣慰地笑了出来。
她将右腿搭在左腿上,凑到他的面前轻轻摆动:「说起来,当时你自己有提议过的吧?到船上来之后,就保持着全裸的跪姿。」
「对不起主人,我以为主人当时并没有同意我的提议。我这就…」奴隶说着,开始脱去身上的衣物。
「裸着能做到,那关于跪着这一点呢?」她看到了他高高翘起的肉棒,忍不住用靴子上的尖刺轻轻挑动起来:「你刚才,好像是站着跑进船舱里的吧?」
「是的,」奴隶仰望着主人,小声辩解:「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主人久等。」
「没事的哦,我会帮你纠正错误的。」她笑着站起来身,抬起脚,在奴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便对着他的膝盖狠狠踹了上去。
奴隶被这毫无预兆的一击直接踢倒。那可怕的靴子又从侧面再次踹击到膝关节。只这么两下,他的左膝变已经血肉模糊。
肉体的痛苦让奴隶流出眼泪,可泪水的背后却是惊喜的目光。他没有见过这般坚决的,也很久没领会过她如此毫不保留地将百分百的气力赐予于他。
连续的踹击让痛得倒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啜泣。主人的靴子高高抬起,从天而降,碾在已经碎裂的膝关节,跺在奴隶脆弱的胫骨上,踹在他毫无防备的脚踝。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骨头碎裂的声音。即使忍不住挣扎和闪躲,也都无济于事。
「现在,」的靴子踩在他断裂的腿骨上拧动着:「你不跪着的错误,就纠正好了吧?接下来,就不会再犯这个错了哦。该说什么呀?」
「谢…谢谢主人!」奴隶本能地喊出声。
靴尖的金属钉占满了血,在金黄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他迎着那刺眼的红光,抬头看着她脸上的惨笑。
「好啦,我也累了,」她终于将靴子从他破碎的脚踝上移开:「就不欺负你了。去右边驾驶室门那里,和打个招呼吧。」
「」听了的指示,挪动着自己残废的小腿,缓缓向右舷跪行而去。他这才发现,船早已驶离了暗礁,此刻四周只剩一望无际、深不见底的南太平洋。
到后面船舱的冰箱里拿了一瓶香槟,和手牵着手,一起走到了右舷。打开酒瓶时,恶作剧般地让瓶塞对着奴隶的下体喷出,作为这一重大场合的庆祝。则准备好了酒杯,接过酒瓶,倒上了三杯酒,准备分给三个人。
接过自己的那杯酒,却不让递酒给「」。
有些疑惑:「诶?为什么不让他喝呀?你不是不在意什么『酒后 SM 是错误行为』的鬼话,以前经常跟他喝酒的吗?」
「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倒不能说是鬼话啦…虽然我虐他的时候确实不经常在意,」嗤笑着解释道:「今天不让他喝酒,只是因为…这么重大的场合,他应该保持清醒嘛。说是为了让他遭受更多的痛苦和恐惧也罢,说是为了看到他理智的决心也罢,总之今天就剥夺他喝酒的权利吧。」
跪在一边的「」没有抗议。但他抬起头仰望着端着酒杯的的一瞬间,竟就此回想起来六年前和一起饮酒时的那个黄昏。
彼时,「」和还算是一对情侣,无可争议。则刚刚开始和在光怪陆离中交往。在的眼里,或者说在所有人的眼里,虽然「」才是的「正室」,但也绝对不算是第三者,而是光明正大,乃至更为骄傲地和在一起的。
元旦假期,原本是「」和一起出游,但也受邀加入,变成了略有些尴尬的三人游。旅途中,自然是和睡在同一间房。这是毫无争议的最佳安排,毕竟这对于和并不能朝夕相处的来说更公平,况且还能满足「」那变态的的绿帽癖。起初申请就睡在他们那间房的地板上或厕所里,但被干脆地回绝了。故作羞辱地说,她和独处时并不想被打扰。最终的安排,显然是和一起住在豪华套房里,而「」睡在街对面的廉价旅馆。
正当「」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通知他去一起吃晚饭时,却直接敲开了他房间的门。
「对不起哦,,我们已经吃完饭啦。说做完爱太累了,不想出门了,我就给她点了外卖。本来我想喊你一起吃的,但是说不用了,她说让我把我们吃剩下的带给你就好了。」
听到这话的「」,除了勃起,还能有什么反应呢?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地将桌子上剩下的半瓶酒倒入杯中,邀请与他同饮。
「说起来,我又重新看了一下写的文章的剧情,对的性癖做出了新的总结,所以,很想确认一下我的猜想对不对呢…」
「呃,你的猜想是?」
「我的猜想是,的性癖,其实是被抛弃吧?」
从「」那儿得到的回应,只是死一般的寂静,以及两腿掩藏不住的颤抖。
「我想,这样的猜测也不算太离奇,」继续说道:「像这样的变态,不管是怎么样的肉刑,都已经不会受不了了吧?像这样的极端的 M,就算是被鞭子抽上一万下,大概也不足为奇。一般的羞辱也很难达到你的阈值了,对吧?说了,就算是把你踩在街头,让你磕头一小时,你也不会觉得屈辱的。所以,我猜,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你这样的受虐狂都感觉到痛到无法接受,因而也就让你更加渴望——那就是被抛弃。」
「」露出奇怪的表情:「真是很有想象力的推理呢。」
「根本不需要太多推理的吧?最近四年里只发过三篇黄文,而它们的剧情全部都以男主角被抛弃为核心,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生怕事情失控,开口澄清着:「那也只是幻想中的性癖而已。现实里,我的主人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的生命。我不可能能够接受被她抛弃的。」
「是的,我当然知道主人是你的一切呀,」微微笑着:「所以,正因为如此,如果被你的主人抛弃,才会最最痛彻心扉吧?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恋痛癖来说,越是死心塌地地爱着,就越会忍不住渴望被她抛弃的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想象中…或许是吧。但是现实里,就算我自己能接受被抛弃,我也需要对我负责到底,守护到底,保证她的幸福。所以被抛弃就不是个选项啦!」
「,你真的以为你的主人需要你的守护吗?」的笑里带着一丝恶意:「刚才还跟我说和我在一起很开心,甚至她都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哦。要说的话,今天的你,对于她来说就是个需要额外操心的累赘吧?她抛弃你的话,不仅可以达成的终极心愿,对她自己而言,或许也是更好的选择哦?」
「」的呼吸都已经难以平静,他心虚地逃避着:「可以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吗?」
「不要再提,是因为怕自己兴奋到失态吗?」满足而自信地发动总攻:「不如,让我看看你已经勃起成什么样子了吧?」
没等「」做出回应,他的椅子就已经被伸出脚向后踢开。他狼狈地半蹲在地上,才不致跌倒。
「现在,只有我能满足你被主人抛弃的愿望哦。按道理讲的话,是不是应该认真地请求我满足你的愿望呢?」
「」还在支支吾吾,便已经继续说道:「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想,我会让彻彻底底地嫌弃你,会让她下定决心和你分手,甚至拉黑你的所有联系方式的哦。我已经占据她的身体了,接下来也就是占据她的脑袋和她的心,让她把你忘得一干二净。怎么样?」
「」已经双股战战,几乎站立不住了。当抬起脚轻轻用鞋底搭在「」胯下支起的小帐篷上,说出「跪下求我吧」五个字时,「」都觉得这是在大发慈悲地给他个台阶下,以免他主动跪下显得太过失态。
于是,「」就这么跪倒了下去。实在无法开口的他,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躲避着的目光。
「还是做不到开口请求我吗?可是,现在脑子里都已经在幻想着一边和我亲热着,一边鄙夷地看着你的样子了吧?」
「」的沉默,无疑是承认了这一点。
浅啜了几口酒之后,语气忽然严厉了几分,对「」命令道:「把裤子脱下来。现在。」
地上的男人被吓得刚刚将裤子褪下一点点,他勃起的肉棒便被的鞋底牢牢踩住。
「被你的情敌踩着,都能硬成这个样子,已经彻底没救了吧?这样恶心的变态,还是不要拖累你的主人比较好,对不对?」
「」呜咽着点头。
「所以,应该求我做什么事情,来帮你呢?」
「求求你…」已经失去所有理智和尊严的男人大口喘着气:「求求你让彻底抛弃我…拜托你了。」
「为什么求我呢?说清楚一点比较好吧。」粗糙的鞋底用力摩擦着他的下体:「而且,把你抛弃之后,又怎么办呢?」
「因为,因为我配不上,呜呜…求求你让和你在一起吧,让彻底离开我,彻底忘了我,这样她才能更幸福。」
「不对哦!」的鞋子从「」的下体移开,径直踹到了他的脸上:「明明就是你自己想满足被抛弃的变态欲望,却装作是为了她好,这也太卑鄙了吧?」
「我…对不起…」
「从一开始,被绿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吧。明明是你自己想满足当绿奴的性癖,却美化成是因为什么『觉得自己独占主人的话太委屈主人』、『主人值得得到更多』而去让和别人交往。不觉得这卑劣得有些过分了吗?」
「对不起…都是我自己变态。我对不起。」
「那么,重新说吧?」这次更加用力地将鞋底踩到了他的肉棒上:「说清楚,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要。」
「」明明从来完全无法想象被除了自己主人外的任何人这么居高临下地对待,可他现在却在脑海中的幻象和鞋底的摩擦中,完全失去了自己。他甚至已经跪不直身子,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求求你,求求你让满足我被抛弃的性癖吧!我…我好想彻底失去…求求你了,大人,求求你把从我身边彻底夺走吧!呜呜…」
一边说着,「」竟已经在情敌的鞋底的践踏下,将大股的精液完全喷射了到了自己的大腿上、地板上。
「做得很好哦,」满意地拿出手机,拍着照片:「瞒着你主人,在别人的脚下射精,这算是对你主人彻彻底底的背叛了吧?只要我把这张照片给看,一定能更轻松地劝服她抛弃你的,嘿嘿。」
「嗯,」高潮余韵中的「」此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微微点头,无助地看着地上的一滩滩白浆。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已经无可挽回。
终于,他的泪水也一齐流到了地上。
「为什么要哭成这个样子呀?」继续拨弄着「」已经疲软下来的肉茎:「是到了贤者时间了,就反悔,不想被抛弃了吗?」
「」犹豫了一会儿后,微微点头。
「可是,理性考量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根本配不上自己的主人的吧?根据你自己的说法,你离配得上还很远的吧。」
「」泪眼汪汪地看着:「是这样。我知道现在和你在一起更幸福。可是…可是我还是担心,我会担心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能一直对她好…」
「这是不信任我吗?」诘问他。
「我不知道…」地上的男人说着:「如果能确定我主人和你在一起,一直都会更幸福的话,就算是付出我的全部身体、积蓄甚至生命,我也会促成我主人抛弃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相信你。」
「从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我还是你,在是否能始终如一这件事上的期望,都没显著差异的吧。这种情况下,她选择现在看起来更好的选项,不就好了吗?」
此刻,一人高高在上,一人低伏地板。孰高孰低,谁是更好的选项,不言自明。
地上的男人心领神会,把头垂得更低了:「是,我知道了。」
「那么,我就回去陪睡觉啦!」满脸都是胜利者的得意,起身将酒一饮而尽,抛下了一句:「就拜托自己准备好,明天该怎么当面向提出请求了吧?这种事,还是你自己说比较有诚意呢。」
「」木然地点点头,看着打开房门离开。他一夜都没能再从地板上爬起来。
六年过后的此时此刻,站在船上的,也回想起了那同一个的黄昏,想起了「」初次丢盔弃甲地跪在自己跟前的模样。
只不过,那次「」并没有被真的抛弃。那天的一切,并非出于自己一个人的意愿;事实上,在去「」的房间之前,便已经和商量好了大概的计划,其本意也只是半开玩笑地试探下「」的绿奴程度,顺便让「」体验一下他未曾体验过的快感而已。
事后,虽然对「」毫不抵抗地任由将他玩弄到射精非常不满,甚至对他的忠诚感到幻灭,但得知了「」哭泣着担心她的幸福的样子,便果然还是不忍心真抛弃他。而虽然确实在心底有着一丝希望「抛弃」成真,而让自己占有的私心,但自然还是会顺从的决意。
「」没有去追问和具体的心态究竟是怎样。自知理亏的他,不敢向开口。冷静下来的他,更多的时候还庆幸着自己没有被抛弃——极端的性幻想注定是幻想,现实中的他每分每秒都那么需要。
一度完全当真并为之射精的所谓「抛弃」,不知该说是虚幻,还是烂尾。
此刻,也回想起了上次「抛弃」并未成真时,自己心里的五味杂陈。他装作轻松地笑笑:「这次不会和上次说要抛弃一样,又烂尾了吧?」
「这么害怕又烂尾吗?」笑着拍了拍的脑袋:「你是不是就想让他早点滚蛋,好和我享受二人世界呀?」
「那倒没有啦,」回应道:「只是,这次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要是再烂尾,很难收场的吧?」
的确,这次「告别号」和小划艇分别从美拉尼西亚地区不同的国家出发,在无人的海域汇合,然后孤筏重洋,在公海上漂流,以便在无人能知晓时完成最终的计划,从规划到实施,自然是耗费了三人不少的心血的。
不过,几分钟前用力踢碎奴隶的膝盖和小腿的举动,无疑是在斩断着退路,向自己和奴隶宣誓,这次的计划不会再烂尾了。
跪在地上的「」忽然开口:「说起来,其实上次的『抛弃』,也不算是完全烂尾的吧?毕竟都已经不再是我的…我的女朋友了。」
确实,在那后的一些年里,和走的越来越近,在一起的时间都甚至开始超过「」和在一起的时间。曾经作为唯一伴侣的「」,真真切切地被边缘化了。虽然没有明确的分手,他们已经默契地很久很久没有过任何亲密接触了。
「你再说什么呢?这不能叫做『抛弃』吧?」再次用靴子挑弄起他腿上的伤口,制造着疼痛:「『抛弃』的话,可是要彻底让你从我的生命中消失的。都允许你继续做我的奴隶了,怎么可能还算是抛弃?」
奴隶在痛苦中挤出回应:「是。主人确实没抛弃我,一直都留着我,我很幸福的。」
「我甚至都怀疑,你比最早的时候还更幸福呢,」轻轻摆着自己的双脚:「我是说,比起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那也很合理嘛。毕竟,」接过话来:「不是一直都觉得,M 是断然不配也不该和自己的主人恋爱的吗?现在这样也算是言行合一吧。」
「」点了点头:「确实,我变为单纯的奴隶,应该算是让一切更合理、更不会有冲突的优化。我确实不该将这说成是『抛弃』的。我的错。」
将酒杯从唇间放下,没回应脚下的男人,而是指着远方,呼喊道:「还有不到半小时就该日落了吧?今天天气真棒,好久没看到过这么干净的海上日落了。」
大海的颜色越来越深。西边仅有的几片薄云,原本还透着金黄的阳光,现在逐渐变为一片密实的血红色。和那欢快的碰杯声,让地上的奴隶多少有点艳羡。
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对啦,,我跟你说过,之前他求了我好几次,想要再…所以…我不知道你能接受吗?」
「当然啦!我不都答应过你了嘛!」轻轻将抱起来,把她放到了躺椅上。自己则站在的身后,双臂环抱着她。
地上跪着的男人立刻领悟,并连忙开口感激大度地允许自己最后玷污一次的身体。「」于是爬到的跟前,伸出舌头,探寻起两腿之间那令他痴念已久的圣地。仰起脑袋与对视,自己轻轻将内裤褪下,将腿微微分开。当奴隶的舌尖终于触及宝珠的一瞬,她只是微微颤抖,而他却已经抽搐得近乎高潮。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哦…你可要好好表现!」她说完后,又像是被自己逗笑了一样,咯咯了两声。
奴隶先是用舌尖轻轻挑动着她的阴蒂,待她放松下来后,便用力摩挲起来。他的舌头毫无策略性、毫无保留地拿出最高的频率和力度努力着,竭尽全力试图取悦着她。舌头很快便酸痛不堪,但他别无选择。几个月前,他上一次成功给她带来高潮时那绝妙的粉色回忆仍留在脑海中,激励着他无休无止地继续着攀爬之路。她每一次轻轻挪动自己的大腿,哪怕只是无意之举,都敦促着他在黑暗中透支更多的气力。
他只想再感受一次的高潮。从无数年前的第一次起,他便永远地沦陷于这样的恩赐——感受着自己的唇舌给带来高潮,远比自己射精还要来得满足无数倍。当然这两者常常结伴而至:在用腿夹紧他的脑袋,全身抖动不止时,已无须再附加什么刺激,他那根本没被触碰的阳具便能和主人同步达到高潮,将精液喷洒在她的脚下。
就让这样的恩泽再来一次吧。奴隶这么想着,舌头深耕不止。终于,的呼吸声愈发急促,双腿也不再静止不动。
「怎么办…要…要到了!」在娇喘声中小声呢喃。也弯下身来,凑向潮红的脸颊,用自己的嘴唇堵住她的另一对樱唇。
可却没有如奴隶所期待的那样夹紧自己的双腿迎接着顶点。恰恰相反,她先折起了自己的双腿,然后奋力将奴隶踹开。
「我不要他给的高潮!」她对着和「」同样震惊的说道:「高潮的话,我还是,要一会儿你来给我嘛!」
「」没有注意到的是,折起双腿前,忽然摇着头提醒自己清醒。这样如寸止般地对待自己,自然是抑制着自己的性欲和本能的。换来的好处则被剩下两人平分:因为被此般偏爱,脸上充满了喜悦,性欲也被彻底点燃,恨不得立刻亲自向兑现一次绝妙的高潮。而「」则因自己的愿望在最后时刻被无情剥夺,还顺带着被嫌弃和羞辱,而兴奋得差点抛下主人兀自射精。
把自己的小手轻轻放到方才被舔过的私处,又对仍跪在她腿间的奴隶命令道:「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舌头辛苦成什么样子啦~」
奴隶跪直了身子,将舌头用力伸出来,呈现给自己的主人。
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来一把剪刀,微笑着用手捏住奴隶的舌头,并在他惊惶的神情中,将剪刀凑到了奴隶的舌根。
「现在,舌头是再也用不到了的吧?」
奴隶的舌头被捏住,说不了话,只是委屈地微微点头。
剪刀合拢。舌尖方才感受着主人的体温,此刻却被痛苦淹没。继续嘲笑着他:「还真指望着,能最后再给我舔到高潮一次呀?噗,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你哪里还有那个资格。」
剪刀再次张开、合拢,奴隶的舌头被彻底剪断。他的身体陡然绷紧,惨叫声和精液一起脱缰而出。
她毫不意外:「啧啧,我就知道你又要射精了。永远都是个被剥夺的越多就越爽的死变态,永远都这么恶心。」
先是随手将被割下的舌头丢到自己的脚底,装作不在意地用靴底踩了上去,又则将自己脱下的内裤顺手抓了过来,塞进奴隶的嘴巴里给他止血。
在痛苦中蜷缩作一团的「」,又被轻轻踢了一踢:「好了,去后面准备你的水泥去吧!我还要在这儿和好好亲热呢。」
「」艰难地跪爬着到了船尾,从船舱里拖出来先前准备的几大袋快干硅酸盐水泥,以及搅拌水泥用的大桶。原则是讲,水泥粉应该是要加淡水混合的,但不在意结构强度和寿命的话,用随手可得的海水来搅拌也无妨。
是的,这一次三人的计划,便是满足「」的终极愿望,让他被他心爱的主人虐杀。至于用水泥来封存尸体,实属对水泥埋尸案的拙劣模仿而已。
当然,与水泥埋尸案不同,「」在死前将接受的不会是暴行,而是彻头彻尾的宠爱。他知道,不管他怎么任性,都将会又一次宠溺地满足他的所有渴求。他将会躺在那艘他心爱的小划艇里,一边看着的眼睛,一边任由水泥没过他的身子,将划艇填满。然后,随着划艇这一关键证物,一起永远地沉没在南太平洋的海底,再不会被人发现,也不会被人想起。
「」静静看着这艘蓝白相间的小划艇,心里满是甜蜜。那一年,当还是每天依偎在他怀中的爱人时,攒钱给他买了这艘他心水已久却一直不舍得买下的小划艇,作为纪念日的礼物。甚至还在小划艇的外面用丙烯颜料画上了他喜欢的动画形象,在内侧刻上了他们俩的名字,让这个小划艇成为最特别的爱的礼物。到如今,这个小划艇也将成为最完美最浪漫的棺木。
一个大桶里倒入水泥粉,另一个桶中装好了适量的用来混合的海水。不能在准备好之前提前将它们混合,否则水泥会过快凝固。而他此时仍依稀听到的娇喘声从船头传来,他知道自己只能等待。
正站船头,双手搭在栏杆上,看着那颗火红的太阳,此刻艰难地悬在海平线上。刚刚与她共赴鱼水之欢的温柔地站在她的身后,轻轻环抱住她的腰肢。
「,我从来没见过你像今天这样对这么坏呢。」
「毕竟都答应了他,要亲手了结他了,就干脆做全套了嘛。要是连开始这些坏都不舍得的话,到时候可就真得烂尾了。」
点头称赞:「是这个道理没错啦!不过,我还是没想到你会答应他,把他了结掉。」
「没办法的嘛。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了。他那么需要我,可我又不可能一边和你在一起,一边还满足他每天的需求的。」
「我知道,这确实是一劳永逸了的做法。」
重复着她早已告诉过的话:「当然也不是我自己想要逃避,才同意虐杀他的嘛!我哪可能有那么坏啦。主要还是他自己真的想要啊。自从和他分居之后,他就一直都磨着我,说想要死在我的脚下。我也知道很离谱呀,可他就是这么任性的人。而我也磨不过他,既然当年都答应了做他的主人,就只能一直宠他了呀。」
撒娇般地捏了捏的乳晕:「你总是说要宠他,我听了可都要吃醋了诶。」
也将手往的胯下一掐,作为报复:「你都已经从他手上把我抢到了,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吧!」
「我就是偶尔会觉得…」的声音依然温柔:「会觉得,的心里好像总还是最在乎嘛。」
「你们俩我都在乎,不行吗?而且你有什么可以吃醋的,你现在可是我唯一的伴侣呀!」的手轻轻爱抚着:「就算我对他有感情,也单纯就只是主人对奴隶的感情而已了,和跟你之间的恋爱完全不是一种东西的嘛。我可是你的女朋友!你没必要沦落到跟一个奴隶去比较吧?」
「我知道。可是你每次宠,我心里难免会稍微有点奇怪的感觉啦!当然…我不是要说沫你不好。」
「好啦好啦,他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再担心了。到了明天早上,他就再也不存在了,你也就再也不用看到我宠他啦!」
「嗯,」点点头:「我知道的。对不起啦,,我心眼总是这么小。」
「呐呐,没事啦,这不是因为你爱我,才会这么容易吃醋的嘛。我怎么可能会舍得怪你!」转过身吻住的唇,好几秒后才重新开口:「我知道,我一直和他藕断丝连,会让你会没有安全感的。对不起,这是我不好。但是这很快就会解决了,别担心啦,好不好?」
「嗯!谢谢你!你最好啦!」
「当然啦!」她嘟起嘴:「那我们去船后面那儿看看吧?说不定他已经准备好了要不再碍你眼了,嘿嘿。」
「」在的示意下将水泥混合了起来,然后立刻乖乖地躺进了他的小划艇里。
他的脑袋被作为枕头的船桨高高垫起,他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抬着一片木板,木板微微悬在胸口上方。这样一来,他便不会因为水泥凝固后压迫他的胸腔使他无法呼吸,而立刻死去了。他的下体则被一条绳子绑住,向上拉扯起来。
帮忙将桶倾倒过来,将水泥倒到「」的身上,直至水泥一点点逐渐填满小划艇内部的空间,淹没奴隶的双腿、双手、腰部和肩膀。最终,只有他的脸庞和性器还暴露在空气中未被淹没。
当「」躺在船里等着水泥干燥的时候,和又已经到船头继续喝着香槟欣赏着落日。奴隶在幻想着,船头的二人又会在以什么样的姿态亲热着呢?精力这么旺盛的,会再一次向求欢吗?
当然,连耳廓都被水泥埋住大半的奴隶,自然是无从知道任何答案的。他能做的只是等待。脑袋只能朝着正上方看去的他,甚至没法看到太阳完全消隐在海平线上的一瞬。但从蓦然变蓝的天色中,他知道那颗作为一切温暖的源头的恒星已经离去,而他已没有机会再见到那唯一炽热的存在。日落已是几分钟前的事;将 civil twilight 和 nautical twilight 一并算上的话,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游刃有余地在黑暗到来之前做完一切。
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快干水泥已经完全定型,因此,她将那根拴着奴隶阴茎和阴囊根部并向上拉扯的绳子解开。从水泥中穿出的性器,便自由地躺在了硬实的水泥平面上。
「不准反悔了哦,」轻轻擦掉自己被海风吹出的眼泪,笑着对奴隶说:「现在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一块肉而已了。」
奴隶想要点头回应,可脑袋早已被水泥牢牢固定,动弹不了半点。他那失去了舌头的嘴巴,也依然被主人的内裤牢牢堵着,没法发出任何有意义的声音。
他的下身还是给出了回应:已经射过一次的他,在听到来自主人的死亡宣判时,又一次无法抑制地充血挺立起来。
「不过,」在的搀扶下,站到了已经干燥的水泥上:「既然所有人都知道我宠你了,就给你点最后的奖励吧。」
奴隶望穿水,深情却又发情地注视着。也宠溺地看着他,然后慢慢抬起脚,用力跺在他的性器上,用全身的体重碾压着他的睾丸扭动着。奴隶的肉棒连同两颗无助的蛋蛋,都被瞬间压扁。他的惨叫声穿透了堵住嘴巴的内裤,回响在南太平洋上空。
如此重复跺击几下之后,奴隶自然已经受不住这样的疼痛。却并未止步于这样的踩踏,而是扬起自己的脚,瞄准奴隶的阴茎,狠狠踢踹上去。
坚硬的靴头几乎将他被阴茎直接折断,而靴子上的尖刺直接撕破了他的皮肤,令鲜血从肉茎里渗出。第二脚用靴头朝着蛋蛋踢上去,尖刺在阴囊上划出了裂口。奴隶惨叫着,却丝毫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用无止尽的踢踹和踩跺,继续临幸着他那淫亵的下体。
终于,他的阴囊在连续的暴击下完全裂开。脆弱的睾丸在失去了保护的情况下被鞋底以全速冲击着,碾压在水泥平面上。已经变形、肿大且暴露的睾丸立刻又遭到踢踹——靴头的尖刺戳入了睾丸,并就此粗暴地将睾丸向前拖拽,几乎将精索扯断。
以前也曾踩踏过许多次他的性器,但从来都能将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致将它们毁坏。此次再也不用克制,只需随意地释放出自己的气力,倒确实是令人畅快的事情。更何况方圆五海里甚至十海里内都再没有第四个人,她再也不用担心他的惨叫声惊扰到邻居。
脚下的奴隶则在无尽的痛楚中勉强分辨出自己一侧睾丸终于破裂的尖锐痛感,在近乎昏厥的时刻看到另一颗睾丸内精细的结缔组织化作浆状,从睾丸白膜的破口喷涌而出。他见证着自己的海绵体在她的踹击下被一点点撕裂,并将鲜血喷洒到他的脸上,遮盖住他的视野。他通过一直眨眼将血液从角膜上清理掉之后,终于才又能看到那些并未亲眼见过的身体组织以破碎的形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痛得近乎失去意识,但残存的意识也都被幸福所淹没。在这所剩无多的生命中竟然还能实现被主人亲自阉割的完美幻想,令他倍感惊喜。他明白,这世上不仅不会有第二个如此宠溺他的人,甚至都不会有第二个如此宠爱自己的奴隶的主人。
在靴子无休止的摧残下,从水泥中伸出来的终于不再是一个男人高高立起的的阳物,而只剩一堆淹没在鲜血中的肉泥,辨认不出任何形状。
「累啦!」看到已经实在不剩什么可以踩踏的东西,便从小划艇上走了下来。看着奴隶的下身一直在流血,她索性拿过一些水泥粉,朝着奴隶的下体撒上去,以多少起到些止血效果。就此,那曾经是他阳物的地方,现在便是一团红灰色的泥状物质了。
奴隶已经难以保持清醒。而剧烈运动之后,坐在椅子上休息着,便再也没发话。天色渐深,空气陷入寂静,连风声似都停歇了。
先打破沉默:「那么,现在我们趁天黑前,把他推到海里?」
点点头,却撞上了奴隶那痛苦而留恋的目光。她在犹豫后缓缓开口:「唉,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好准备。」
对这样的并不惊讶:「我知道的。不过,都已经到现在这样子了,就得负责到底啦。总不能又烂尾,把他从水泥里挖出来吧?」
「确实不能…吧。」摇摇头,但依然坐在椅子上,无法起身。
「没事的,就算你会舍不得他,我也不会怪你啦,」温柔地握住了的手:「而且,你确实也没义务背负上亲手杀掉他这样的重担,所以…不用勉强的。」
「那怎么办呀?」失去了决心的有一丝颓丧:「难道真的又烂尾吗?但就算那样,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才能把他挖出来吧?」
「我有一个主意,」说道:「既不会烂尾,也不会要你现在就逼着自己下手。最棒的是,我猜想也会很喜欢的。」
举棋不定的,当然没理由拒绝的帮助:「那你说说你的主意吧?」
「我们就把放置在这里不管,就没问题了。可以当作是一种放置 play 吧。」
「然后呢?」疑惑地问。
「已经失了不少血的,不可能挨得住明天一整天的暴晒。在那之前他就会死掉的。而等自然死亡之后,我们再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尸体推到海里就行。这样的话,能实现在被你虐杀的同时,你又不用亲手终结他的生命。」
「都把他这么固定起来了,放着他不管的话,跟亲手终结他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嘛!」
「亲手终结的生命的话,他是没有选择的呀,」继续补充道:「但现在这样,随时都有求饶的能力。虽然他说不了话,但他想的话可以发出喊声,让我们过来把他救出来的。他虽然连点头和摇头都做不到,但至少可以眨眼睛跟我们沟通嘛。」
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还是犹疑着:「但是,把他就那么活生生暴晒到死,也太残忍了点。他就算是抖 M,也只是喜欢被我亲手虐待而已!没人会喜欢独自暴晒到死这类完全没有兴奋点的折磨的。」
说道:「没事的,这不都说了吗,他如果受不了,随时都能求救的嘛。而且你别急,说不定,他真的会喜欢被那么折磨的哦。」
于是径直和被封在水泥里的男人对话起来:「,你听明白我的主意了吗?我和从现在开始就放着你不管啦。不过,任何时候你如果想放弃了,让我们敲碎水泥把你救出来的话,就大喊出声就好。按你刚才惨叫的音量,我们一定能听见的。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以的话,就眨眨左眼来代替点头吧。要是觉得不行,你就眨眨右眼来代替摇头。」
半秒的思考后,「」眨了眨左眼。
「不过,大概也知道,如果想救你出来却做不到的话,她会很难过的。而就算你被救出来,要送医也很麻烦,而且这辈子估计也没法正常行走了,肯定会成为的困扰和累赘的,没错吧?」
水泥里的男人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并眨了眨左眼。
「所以,现在有着最后的一次机会,通过保持沉默,来证明你在乎,为她考虑、不愿意给她添麻烦。而且还如你最喜欢的那样,是通过忍耐痛苦来证明。这个主意,一定也很喜欢吧?」
奴隶的左眼连续眨了好几下,脸上写满了兴奋。
「所以,一定很希望,从今晚开始,就完全把你抛之脑后,专心和我在一起的,对吧?」
得到的依然是肯定且愈发兴奋的回应。
「这个表情的意思,」翻译着:「是在诚心诚意地乞求满足你的愿望,求求她在你死掉之前都完全忽视你,对不对?」
这次,在奴隶兴奋地眨着左眼的同时,他的脸已被踩住。看出了他兴奋的模样,终于确信了这就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也终于用羞辱的言语挑逗起「」:「哦,你有这么乖吗?如果你痛苦得受不了了,会不会叫出声来,打扰我和亲热呀?」
奴隶连连眨着右眼,一脸顺从的表情,努力地表明着决心。其实光是把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与和别人亲热的场景放在同一个画面想象,他就已经兴奋到要失神。若他的肉棒还在的话,恐怕早已又一次一柱擎天。
他顺从而无辜的样子总能激起的施虐欲。的靴子粗暴地将他的嘴唇碾破,没好气地说:「啧!要是真想让我和好好在一起,不想打扰我们的话,你两年前就该识趣地自己去死才对的吧,而不是像这样自私地一直赖在我的生活里不走。你这样的人渣,居然还有脸假装自己在乎我。」
的身体因兴奋而颤抖起来,他嘴里徒劳地试图说出「对不起」,想向自己的主人道歉。但此时,已经将自己的靴子插入他的口中,将全身的重量压入他的口腔,并把他嘴里的那条内裤捅到他的食道深处。连奴隶的牙齿,都几乎被靴子上的尖刺给掰下来。
「你要安安静静地死掉,我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把你彻彻底底忘得一干二净的哦~」继续用自己的言语满足着他:「你也不想我之后和白头偕老时,脑海里还有你这个煞风景的垃圾的吧?」
奴隶并不知道该眨哪只眼睛来回应这样的反问句;但他眼里的歉意和乞怜,已表明了他的心迹。
点了点头,满心幸福。不仅是因为奴隶依然那么热烈地爱着她,也是因为他那几乎颅内高潮的表情足以证明,没有白白为了羞辱他而说出这些违心的话。一词一句,都让奴隶很是受用。
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满天的繁星将三人完全淹没。看到海平面上出现了一盏绿灯,便怀疑是正有船在从左向右驶过,于是前去驾驶室准备仔细观察。本也打算一同前去,但她还是想先完成与「」的最终告别。
「那么,为了避免你没怎么受到折磨就太快脱水死掉,我就还是在临走前,给你补一点水吧!」
明明现在并不是烈日当空,还是用了这个借口,来赏赐奴隶一些他一向最喜欢的圣水。以前都是奴隶每天追着她要,这一次她决心主动一些。在奴隶脑袋的上方蹲了下来,掀起了自己的裙子。
「」想抬头再看看她的胴体,却只见得到暗夜中的无数繁星。每一颗星星,都承载着他们曾拥有过的某段回忆。他好像从来没见过如此壮丽的星空,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汇聚在一起,连结在此刻。
或许是视角的限制,他没能在南天球辨认出银河,但温暖的尿液从的两腿间流出,裹挟着星光,倾泻而下,成为了更加真实而灵动的银河。随着那甘洌的圣水灌入他的口中,那么多年来,对他所有的宠爱,也全都又一次流入他的心中。
如此蹲着直接排尿,自然无法保证瞄准奴隶张开的嘴。但满脸都沾满圣水,也恰巧掩盖住了他止不住的泪水。
是自己没了舌头的缘故吗?奴隶甚至无法像以前那样,从的的圣水中甚至尝出一丝些微的苦涩。还是说,过去有过的些微苦涩,才是彻头彻尾的错觉呢?他不知道。
壮丽如银河,也无法是永恒的存在。最后几滴圣水终于也从的身体中滴下,奴隶想要接住它们,却因脑袋无法动弹,而只能眼睁睁将它们浪费。他于是不忍将口中的圣水立刻咽下,他还想再多品尝一会儿她的气息。
已经从驾驶室那边呼唤着。
「那,」起身说着:「我会像我答应你的那样,努力忘掉你的!」
奴隶奋力眨了眨左眼。他眼中映射出的星光,淹没在暮色中。
首冲,好吃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dominael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真厉害啊!
(没办法我才疏学浅不能像上面两位大佬一样评价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3_ヽ)_)
(没办法我才疏学浅不能像上面两位大佬一样评价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3_ヽ)_)
太痛了。
猴面包:↑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面包老师实属带文豪,随手就是引经据典。但老实讲,这最后一行可实在太贴切了。不管是故事里还是现实中。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我为自己一度有那么一瞬间,产生过「我也能写得出来的文艺m文」的想法而感觉到巨大的羞愧…)
虽然因为题材原因,看之前丝毫没想过自己有可能会喜欢……但没想到,看完之后还是完全代入了quq
痛!而且是充满了高级感的上质的痛楚!站长平时到底吃得有多好才能写出来这种痛啦!
虽然因为题材原因,看之前丝毫没想过自己有可能会喜欢……但没想到,看完之后还是完全代入了quq
痛!而且是充满了高级感的上质的痛楚!站长平时到底吃得有多好才能写出来这种痛啦!
站长果然重口味。搞笑的是想把站长的英文名打在那个框里,结果达成了谷歌浏览器的Chrome,哈哈哈
luckyxiaoyu:↑搞笑的是想把站长的英文名打在那个框里,结果达成了谷歌浏览器的Chrome,哈哈哈说起来两个词都是同源的。我是直接取 chroma 的「色」一义,来起自己的用户名的。而 Google Chrome 取名来自于 chroma 衍生出的 chrome 作为「铬」的含义,及其进一步衍生出的作为界面边框的含义。
实在太痛了。
但感觉行文中隐隐透出的“主人其实没那么喜欢施虐,是为了满足m的性癖而违心地施虐”的感觉和我之前的体感还蛮像的,交往过的恋人们大部分都会为了满足我的xp尝试和我玩一下sm,但其实她们完全不享受这个,甚至是在勉强自己。
或者说真的施虐癖主导的sm实在太容易造成永久性伤害甚至死亡,变成刑事案件风险太高,所以大部分“安全的”sm实际上就是没有施虐癖的普通人为了满足m的性幻想而从事的纯服务行为了。
不过我感觉我已经彻底丧失性欲了,这就是我的福报
但感觉行文中隐隐透出的“主人其实没那么喜欢施虐,是为了满足m的性癖而违心地施虐”的感觉和我之前的体感还蛮像的,交往过的恋人们大部分都会为了满足我的xp尝试和我玩一下sm,但其实她们完全不享受这个,甚至是在勉强自己。
或者说真的施虐癖主导的sm实在太容易造成永久性伤害甚至死亡,变成刑事案件风险太高,所以大部分“安全的”sm实际上就是没有施虐癖的普通人为了满足m的性幻想而从事的纯服务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