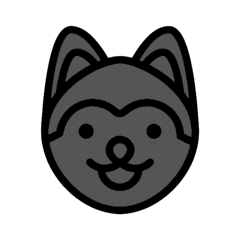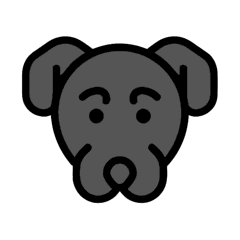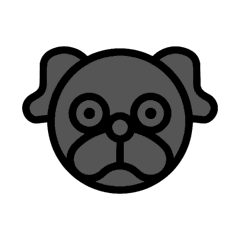告白
连载中原创
最近的心境比较适合写这两位的故事,与前文《唯物主义》不同,这部我选择以林鸢的第一视角来写。刚好今天失眠了,刚好手机还有电,刚好想写了,真是太巧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夜雨终究是带走了残存的暑热,可仲秋的凉爽并没有使我的心情变得愉悦。经期的延迟导致最近的睡眠质量每况愈下,我不耐烦地切着车内的歌,窗外的天空真的阴沉地像在哭一样。在这片城郊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随着模糊的指示标七拐八拐后,我终于看到了想要到达的楼栋。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有些像是两年前,包括但不限于因通风不良而积淤的霉味,熄火开门的那一刹,接踵而至的呼吸都是潮湿而黏腻的。几颗硕大的水滴毫无节奏地撞击在车顶,溅起的水花沾到了我脸上。我望着层顶的排水管摸了摸脸,有些被气笑般的叹了口气,本来就因为最近皮肤的干燥有些卡粉,这下怕是更好看了。
“秦苾!给我开门!”我对着手机嘶吼。
和两年前不同,我乘坐电梯来到他的楼层,在推开虚掩的门那一瞬间,只觉得一股清爽的气息扑来,说不出具体的味道,和屋内的陈设一样干净简洁。
两年前那间垃圾室我是记忆犹新的,他当时蹲坐在一堆“残骸”正中,看上去像一条觅不到食的流浪狗。
那小狗如今正坐在窗前的凳子上,鼓捣着一架古筝。 天气不热,他满头是汗,忙碌得像是一个拼不好积木的孩子。
其实有时候我也有些怀念秦老师两年前的那副模样,又或许是更久远的时候。人总是矛盾的,你我皆是如此,对唾手可得之物不屑一顾,对千呼万唤之物珍惜有加,可那窃喜的劲头短暂得像是昙花一现,风一吹就没了。
我和秦苾相反,他骗不了别人,却擅长骗自己。
而我骗不了自己,若是把前文念出口,那会把自己逗得笑场。
“我就说琴弦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断了,原来是林大小姐你大驾光临。”
他“百忙之中”迸出一句话来气我,头都没抬。我想抄起挎包扔到他脸上,看看他什么反应,太可气了。
“秦老师,” 我们的关系很奇怪,也复杂,但总归是不必互相太客气的那一种。屋内的木地板被他擦得一尘不染,但我故意没有换上他给我准备在门口的拖鞋,而是径直走了进去,毫不拘礼地直接坐到沙发上。
“离开我这几个月你好像过得很开心啊?”
确实,我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他带给我的那种松弛惬意的感觉,直白的说就是什么文人傲骨与世无争的那副臭不要脸的姿态。但这种可恶中又带了点怪异,我太了解他了。
又或者说,我太不了解他了,反正,我不喜欢。
我专门过来看他,他还在弄些有的没的,我不喜欢。
这屋子太干净了,干净得有种窒息感,像是我的每次举手投足都破坏了他的意境,我不喜欢。
这里是顶楼,阳光透过云层直直地射来,刺眼又燥热,我不喜欢!
“开心,开心。。” 他敷衍着回了几句,眼睛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续弦的双手。
若我们不是这种关系,那他的这种态度傲慢得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逐客。我有些忍不了,从包里取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将他桌上的玻璃烟灰缸在移动的过程中狠狠地砸出砰的一声。
炸雷声响过后,他终于是抬起头看我了,讨好般贱兮兮笑了笑,我这才注意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副丑的要死的黑框眼镜。
“哎呀,这不是说好让我出来单独住一段时间找找灵感吗,林大小姐你这是闹哪样啊?”
“你这灵感找得好啊秦老师,我看你昨天那首诗就很有灵感啊,点赞和评论都很多不是吗?尤其是结尾那几句,‘季风已经离我太远,我会埋在土壤中生长,直到来年’,写得多接地气啊。” 没抽两口,我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碾了又碾。
“你也觉得不错对吧,哎,我这几个月每天打打零工写写诗,过得还真挺舒服的,不过美中不足就是干妈你不在身边,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难熬得哦,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居然。。。” 他的琴弦已经续好,一边调音一边说着,聒噪地像一只扁嘴鸭。
“秦苾。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你想去死,对吧?” 今天总归是烦躁的,没那么多闲心陪他过家家,既然他要把我当傻瓜,那我便给他一耳光就对了。
精神上的。像他从前对我那样。
啪的一声脆响,新弦在调音的过程中骤然断裂,惊悚的回应在这间小屋里炸开,他这里的隔音一定是不好的。
小狗木讷地呆坐在琴前表情僵住了,盯着我的脸,一手撑着岳山,一手扶着调音盒,先前的松弛感去哪儿了呢?
呵。
终究是真实了,终究是和两年前一样了。
不过,这证明我对这几句诗的解读是正确的。看来,我的确是了解他的。
他有句话说的很对,我很喜欢给他穿上衣服之后又把他扒个精光。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不是吗。
可是,看到他这幅模样,我脑海中蹦出的词居然是“委屈巴巴”,他表现出的这幅死样子,就好像小媳妇似的。哈哈哈,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否恰当,那个暗藏韬晦夸夸其谈的是他,精虫上脑贱如蝼蚁的也是他,在夏天的储物间光着膀子画画,在冬夜的街道上背着我散步,趴在地板上给我讲课,跪在电影院里为我口交。
自负的卑微的,骄傲的,庸俗的,一个人怎么能有这么多副面孔啊,不是吗?
恰巧还都是,我喜欢的。
我们的关系相对而言很复杂,如果要理解成为情侣也说得过去。可是他不曾明确跟我表白,我也不曾主动跟他示爱,我们只是经常做爱,经常做一些他喜欢我也喜欢的“事”。我们大学时谈过一年的恋爱,后来他被我的闺蜜抢走了,直到两年前我才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了原因。我给了那个婊子一笔钱,客客气气地让她滚,当然这只是为了省事而已,并不代表我会忘了这件事,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让她知道抢我东西的下场。 我对爱的理解有些片面,我对这个男人的理解也很片面。当我得知他的癖好,并且同时得知这是让我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时,我先是震惊,随后是愤怒。我想报复他们两个人,但我真的看到他瘫坐在地上的时候,原先的愤怒又莫名地消散了干净。我只觉得他需要我救他,而我必须要救他。 凭什么要救他?怎么救?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救他。我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试探,去做尝试,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而他用语言抗拒我,用行为伤害我,数次。他喜欢被虐待的感觉,喜欢被当做一条狗来对待,喜欢我踩他,踢他,鞭打他,喜欢舔我的脚,甚至是阴部,而我好像也很喜欢他带给我的这种反馈。 按理说,我们应该很合适才对。
可是我内心深深的明白,这绝对是错误的。
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错误的原因。
我像是踩着他匍匐的影子,只是,他会随着影子一起趴下去罢了。
当然,这绝对不是所有的原因。
我好像看了他好久,后者却还沉浸在我道破他心思的懵懂中。为什么我会说是懵懂,那是因为我觉得那可怜的小狗狗像是要鼻涕眼泪一股脑流出来了呢。其实我有些不明白,明明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在自我的折磨中挣扎着走不出来,像是一次次沉沦在腐臭的沼泽中,我刚一放手,他又陷进去了。
陷到了另一个泥潭里。
“秦老师,为什么?” 我走到他面前,捏了捏他的耳朵,语气很温柔,不是演出来的。他经常开玩笑喊我干妈,这时我也真的有点哄儿子的感觉了。
“你之前写给我诗里的结尾不是说要牵着我的手,一起弹琴,一起放风筝吗?”
他笑了,笑着笑着把眼泪笑出来了。
“林鸢。。” 听得出他已经刻意在抑制了,可是声音还是有些哽咽,他演技差得不值一提,还不如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我懂他什么意思。其实他不用说话,眼神也能告诉我。
什么意思呢? 无非是皮痒了呗。
东西放车上的,一些,小玩具,很久没用过了。我来之前已经猜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出。还什么把自己‘ 埋在土里,等明年 ’,蠢货一个,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太可气了!
“林鸢,我能把衣服脱了吗?这是你给我买的,我怕一会儿打坏了。” 我从车里取了些东西回来时,秦苾指了指身上的白色T恤一脸正经地问我。T恤的正中印着一名眼神深邃的大胡子欧洲男子,我们逛商城的时候都觉得那男子看起来像高迪,然后就买下来了。
“可以。” 我看他那副糗样,只觉得在跟一个未成年小屁孩对话。 一件衣服都这么爱惜的人,会不爱惜自己的命吗?真的好笑。有时候越聪明的人就越蠢,这不矛盾。
小狗狗穿了条黑色的平角裤规规矩矩地趴在客厅正中,他的主人正用他的洗脸巾擦拭着马鞭上的水渍。秦苾的身材算是好看的那种,虽说不上虎背蜂腰,但也是结实健康的,最关键的是,足够白皙,像他那脸蛋儿一样。我很想在他的背上刻上我的名字,靴子的高跟应该是不错的工具,用他最喜欢的那一双。可我的名字笔画不少,用脚来书写更是有些难度,应该呈现出的效果是不会有美感的吧。 叫两声吧。鞭子划破空气的声响跃起,我应当是用尽了全力,击打在他皮肉的刹那,我盼望能听到一些嘶鸣,像失蹄的劣马在被惩戒时应当做出的反馈。看来之前的实践实在是不够彻底,病根依旧存在着,看似神奇的疗效而时长却不过数月而已。
叫两声啊!清脆悦耳的击打声是欢快的节奏,暗红的血瘀随机地出现在他原本光洁的背上。其实也算不上光洁,隐约是可以见到一些从前留下的痕迹,突兀的,透明的。有些是我留下的,有些大概是那个婊子留下的,浅的是我留下的,深的是她留下的。
秦苾闭着眼一动不动,像是山羊又像是倔驴。我能猜到他脑子里如今在幻想些什么画面,我也知道他下体那块肉此时已经肿胀地如同山丘,但这不重要。
浅的是我留下的,深的,是她,留下的。其实,这也不重要。
我说过,我骗不了自己,我又想笑了。
可眼下的光景总是愉悦的,我的手被震得有些发麻,大抵是好久没有如此用力地宣泄了,像是用鞭子抽死了那烦人的酷夏。秦苾是喜欢痛的,或许痛是他的病,亦是他的药。我从来就是一个庸医,一个幻想着用加大剂量的方法让瘾君子戒毒的庸医,听起来多么可笑啊。
可是,庸医真的就想治好患者的病吗。像是把完整的拼图肆意瓦解,又像是站在湖泊的边上,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有些愉悦是一个人的,而另外的,或许是两个人的。
我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看来那迟到的老朋友终于是要来了。
叫两声,听话。
若人陷在情绪中,连表情都无法控制,更何况手脚。恍然间想起了那天的电影院,耳边还回荡着星舰的轰鸣,胯下的小狗在我的催促下用舌头工作,我的感官在无数次蓄力中若有若无地积蓄着能量,终于在最后一次启动之后穿过雾霭,划破苍穹,而后,便是寂静如夜的满天繁星。
我的手臂更麻了。
“啊!” 沉默的小羊羔终究是颤抖着呼嚎着,断断续续,又撕心裂肺。
我知道他哭了,也知道他射了。
或许是的吧。
“秦老师,为什么突然发这种神经啊?” 我坐在椅子上,抓起他的头,居高临下地欣赏着他的痛苦表情,白色的高跟鞋微微挑起他的下巴,这可以理解为实践后的抚慰。
不,他还需要更痛苦一些才行。
我从包里掏出一小瓶便携式医用酒精,平时用来喷手的玩意儿,这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随着我手指的按压,喷头嘶地一声,原本皮肉破裂的鞭痕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告诉我啊。” 此时我并没有什么怜悯之心,想在那原本洁白的画布上找到一块白净的位置抚摸几下,可从脖颈到腰部,那画布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可以放手的皮肉了。
“你不说我替你说吧。你是觉得自己浪费了几年,和曾经那些完全不如你的朋友同学现在居然有差距了。所以想着要不死了算了?你不信唯物主义的对吧,你相信会有来生是吧?又或者说,你只是想逃避现实而已?”
这一幕又像极了从前,我对他的说教总是以长辈似的方式进行着。真的是,清醒的时候像个智者贤师,糊涂的时候又像个小屁孩,好像男人都这样。
真切而沉闷的哭声持续着,终究是湮灭了我所有的兴致。我叹了口气,轻轻地扶起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他起身很慢,大概是碍于背上密密麻麻的鞭痕,背部肌肉的每一次运动都会伴随着剧痛。
其实我有点内疚。
哎,为了他好,对吧。
完全是,为了他好!
别笑场。
别笑场!保持该有的姿态!
我用纸巾轻轻地给他擦眼泪和鼻涕,小狗的哭泣却完全止不住,最后直接把头埋到了我怀里。温热的,脏兮兮的,唉算了。我抚摸着他的头,撸猫般顺着他的头发摸摸捏捏。这种触感也是愉悦的,大概可以形容为宁静,温和。秦老师的头发很干净,很柔软,我逗他,用手指蘸了点他的眼泪喂到他嘴里,看着他撒娇似抗拒的样子。
他哭,我笑。
太可爱了,比撸猫可好玩太多了。
窗外传来了小贩的叫卖声, 隐约间能闻到隔壁邻居厨房里散发的饭菜香气,都是我好久不曾有过的体验了。我跟秦老师聊了好多最近的事,压抑在心间的一些烦闷好似终于打开了闸口。
身体里的另一些东西也同样打开了闸口,在夕阳的柔光终于拨开了云雾照到我脸上的时候,一股来自腹部的暖流缓缓流出,姗姗来迟。
完了啊!这次是真的完了!
“林鸢,你身上什么味道?怎么怪怪的。”
秦苾眼睛红肿地从我怀中坐起身来,看起来像是刚睡醒那副模样。
丢脸死了!
“去给我拿卫生巾啊!”
“啊?我这哪来的那种玩意儿啊!”
“快去买啊!”
“哦,好!”
“回来!把衣服穿上啊喂!”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有些像是两年前,包括但不限于因通风不良而积淤的霉味,熄火开门的那一刹,接踵而至的呼吸都是潮湿而黏腻的。几颗硕大的水滴毫无节奏地撞击在车顶,溅起的水花沾到了我脸上。我望着层顶的排水管摸了摸脸,有些被气笑般的叹了口气,本来就因为最近皮肤的干燥有些卡粉,这下怕是更好看了。
“秦苾!给我开门!”我对着手机嘶吼。
和两年前不同,我乘坐电梯来到他的楼层,在推开虚掩的门那一瞬间,只觉得一股清爽的气息扑来,说不出具体的味道,和屋内的陈设一样干净简洁。
两年前那间垃圾室我是记忆犹新的,他当时蹲坐在一堆“残骸”正中,看上去像一条觅不到食的流浪狗。
那小狗如今正坐在窗前的凳子上,鼓捣着一架古筝。 天气不热,他满头是汗,忙碌得像是一个拼不好积木的孩子。
其实有时候我也有些怀念秦老师两年前的那副模样,又或许是更久远的时候。人总是矛盾的,你我皆是如此,对唾手可得之物不屑一顾,对千呼万唤之物珍惜有加,可那窃喜的劲头短暂得像是昙花一现,风一吹就没了。
我和秦苾相反,他骗不了别人,却擅长骗自己。
而我骗不了自己,若是把前文念出口,那会把自己逗得笑场。
“我就说琴弦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断了,原来是林大小姐你大驾光临。”
他“百忙之中”迸出一句话来气我,头都没抬。我想抄起挎包扔到他脸上,看看他什么反应,太可气了。
“秦老师,” 我们的关系很奇怪,也复杂,但总归是不必互相太客气的那一种。屋内的木地板被他擦得一尘不染,但我故意没有换上他给我准备在门口的拖鞋,而是径直走了进去,毫不拘礼地直接坐到沙发上。
“离开我这几个月你好像过得很开心啊?”
确实,我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他带给我的那种松弛惬意的感觉,直白的说就是什么文人傲骨与世无争的那副臭不要脸的姿态。但这种可恶中又带了点怪异,我太了解他了。
又或者说,我太不了解他了,反正,我不喜欢。
我专门过来看他,他还在弄些有的没的,我不喜欢。
这屋子太干净了,干净得有种窒息感,像是我的每次举手投足都破坏了他的意境,我不喜欢。
这里是顶楼,阳光透过云层直直地射来,刺眼又燥热,我不喜欢!
“开心,开心。。” 他敷衍着回了几句,眼睛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续弦的双手。
若我们不是这种关系,那他的这种态度傲慢得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逐客。我有些忍不了,从包里取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将他桌上的玻璃烟灰缸在移动的过程中狠狠地砸出砰的一声。
炸雷声响过后,他终于是抬起头看我了,讨好般贱兮兮笑了笑,我这才注意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副丑的要死的黑框眼镜。
“哎呀,这不是说好让我出来单独住一段时间找找灵感吗,林大小姐你这是闹哪样啊?”
“你这灵感找得好啊秦老师,我看你昨天那首诗就很有灵感啊,点赞和评论都很多不是吗?尤其是结尾那几句,‘季风已经离我太远,我会埋在土壤中生长,直到来年’,写得多接地气啊。” 没抽两口,我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碾了又碾。
“你也觉得不错对吧,哎,我这几个月每天打打零工写写诗,过得还真挺舒服的,不过美中不足就是干妈你不在身边,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难熬得哦,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居然。。。” 他的琴弦已经续好,一边调音一边说着,聒噪地像一只扁嘴鸭。
“秦苾。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你想去死,对吧?” 今天总归是烦躁的,没那么多闲心陪他过家家,既然他要把我当傻瓜,那我便给他一耳光就对了。
精神上的。像他从前对我那样。
啪的一声脆响,新弦在调音的过程中骤然断裂,惊悚的回应在这间小屋里炸开,他这里的隔音一定是不好的。
小狗木讷地呆坐在琴前表情僵住了,盯着我的脸,一手撑着岳山,一手扶着调音盒,先前的松弛感去哪儿了呢?
呵。
终究是真实了,终究是和两年前一样了。
不过,这证明我对这几句诗的解读是正确的。看来,我的确是了解他的。
他有句话说的很对,我很喜欢给他穿上衣服之后又把他扒个精光。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不是吗。
可是,看到他这幅模样,我脑海中蹦出的词居然是“委屈巴巴”,他表现出的这幅死样子,就好像小媳妇似的。哈哈哈,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否恰当,那个暗藏韬晦夸夸其谈的是他,精虫上脑贱如蝼蚁的也是他,在夏天的储物间光着膀子画画,在冬夜的街道上背着我散步,趴在地板上给我讲课,跪在电影院里为我口交。
自负的卑微的,骄傲的,庸俗的,一个人怎么能有这么多副面孔啊,不是吗?
恰巧还都是,我喜欢的。
我们的关系相对而言很复杂,如果要理解成为情侣也说得过去。可是他不曾明确跟我表白,我也不曾主动跟他示爱,我们只是经常做爱,经常做一些他喜欢我也喜欢的“事”。我们大学时谈过一年的恋爱,后来他被我的闺蜜抢走了,直到两年前我才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了原因。我给了那个婊子一笔钱,客客气气地让她滚,当然这只是为了省事而已,并不代表我会忘了这件事,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让她知道抢我东西的下场。 我对爱的理解有些片面,我对这个男人的理解也很片面。当我得知他的癖好,并且同时得知这是让我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时,我先是震惊,随后是愤怒。我想报复他们两个人,但我真的看到他瘫坐在地上的时候,原先的愤怒又莫名地消散了干净。我只觉得他需要我救他,而我必须要救他。 凭什么要救他?怎么救?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救他。我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试探,去做尝试,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而他用语言抗拒我,用行为伤害我,数次。他喜欢被虐待的感觉,喜欢被当做一条狗来对待,喜欢我踩他,踢他,鞭打他,喜欢舔我的脚,甚至是阴部,而我好像也很喜欢他带给我的这种反馈。 按理说,我们应该很合适才对。
可是我内心深深的明白,这绝对是错误的。
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错误的原因。
我像是踩着他匍匐的影子,只是,他会随着影子一起趴下去罢了。
当然,这绝对不是所有的原因。
我好像看了他好久,后者却还沉浸在我道破他心思的懵懂中。为什么我会说是懵懂,那是因为我觉得那可怜的小狗狗像是要鼻涕眼泪一股脑流出来了呢。其实我有些不明白,明明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在自我的折磨中挣扎着走不出来,像是一次次沉沦在腐臭的沼泽中,我刚一放手,他又陷进去了。
陷到了另一个泥潭里。
“秦老师,为什么?” 我走到他面前,捏了捏他的耳朵,语气很温柔,不是演出来的。他经常开玩笑喊我干妈,这时我也真的有点哄儿子的感觉了。
“你之前写给我诗里的结尾不是说要牵着我的手,一起弹琴,一起放风筝吗?”
他笑了,笑着笑着把眼泪笑出来了。
“林鸢。。” 听得出他已经刻意在抑制了,可是声音还是有些哽咽,他演技差得不值一提,还不如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我懂他什么意思。其实他不用说话,眼神也能告诉我。
什么意思呢? 无非是皮痒了呗。
东西放车上的,一些,小玩具,很久没用过了。我来之前已经猜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出。还什么把自己‘ 埋在土里,等明年 ’,蠢货一个,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太可气了!
“林鸢,我能把衣服脱了吗?这是你给我买的,我怕一会儿打坏了。” 我从车里取了些东西回来时,秦苾指了指身上的白色T恤一脸正经地问我。T恤的正中印着一名眼神深邃的大胡子欧洲男子,我们逛商城的时候都觉得那男子看起来像高迪,然后就买下来了。
“可以。” 我看他那副糗样,只觉得在跟一个未成年小屁孩对话。 一件衣服都这么爱惜的人,会不爱惜自己的命吗?真的好笑。有时候越聪明的人就越蠢,这不矛盾。
小狗狗穿了条黑色的平角裤规规矩矩地趴在客厅正中,他的主人正用他的洗脸巾擦拭着马鞭上的水渍。秦苾的身材算是好看的那种,虽说不上虎背蜂腰,但也是结实健康的,最关键的是,足够白皙,像他那脸蛋儿一样。我很想在他的背上刻上我的名字,靴子的高跟应该是不错的工具,用他最喜欢的那一双。可我的名字笔画不少,用脚来书写更是有些难度,应该呈现出的效果是不会有美感的吧。 叫两声吧。鞭子划破空气的声响跃起,我应当是用尽了全力,击打在他皮肉的刹那,我盼望能听到一些嘶鸣,像失蹄的劣马在被惩戒时应当做出的反馈。看来之前的实践实在是不够彻底,病根依旧存在着,看似神奇的疗效而时长却不过数月而已。
叫两声啊!清脆悦耳的击打声是欢快的节奏,暗红的血瘀随机地出现在他原本光洁的背上。其实也算不上光洁,隐约是可以见到一些从前留下的痕迹,突兀的,透明的。有些是我留下的,有些大概是那个婊子留下的,浅的是我留下的,深的是她留下的。
秦苾闭着眼一动不动,像是山羊又像是倔驴。我能猜到他脑子里如今在幻想些什么画面,我也知道他下体那块肉此时已经肿胀地如同山丘,但这不重要。
浅的是我留下的,深的,是她,留下的。其实,这也不重要。
我说过,我骗不了自己,我又想笑了。
可眼下的光景总是愉悦的,我的手被震得有些发麻,大抵是好久没有如此用力地宣泄了,像是用鞭子抽死了那烦人的酷夏。秦苾是喜欢痛的,或许痛是他的病,亦是他的药。我从来就是一个庸医,一个幻想着用加大剂量的方法让瘾君子戒毒的庸医,听起来多么可笑啊。
可是,庸医真的就想治好患者的病吗。像是把完整的拼图肆意瓦解,又像是站在湖泊的边上,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有些愉悦是一个人的,而另外的,或许是两个人的。
我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看来那迟到的老朋友终于是要来了。
叫两声,听话。
若人陷在情绪中,连表情都无法控制,更何况手脚。恍然间想起了那天的电影院,耳边还回荡着星舰的轰鸣,胯下的小狗在我的催促下用舌头工作,我的感官在无数次蓄力中若有若无地积蓄着能量,终于在最后一次启动之后穿过雾霭,划破苍穹,而后,便是寂静如夜的满天繁星。
我的手臂更麻了。
“啊!” 沉默的小羊羔终究是颤抖着呼嚎着,断断续续,又撕心裂肺。
我知道他哭了,也知道他射了。
或许是的吧。
“秦老师,为什么突然发这种神经啊?” 我坐在椅子上,抓起他的头,居高临下地欣赏着他的痛苦表情,白色的高跟鞋微微挑起他的下巴,这可以理解为实践后的抚慰。
不,他还需要更痛苦一些才行。
我从包里掏出一小瓶便携式医用酒精,平时用来喷手的玩意儿,这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随着我手指的按压,喷头嘶地一声,原本皮肉破裂的鞭痕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告诉我啊。” 此时我并没有什么怜悯之心,想在那原本洁白的画布上找到一块白净的位置抚摸几下,可从脖颈到腰部,那画布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可以放手的皮肉了。
“你不说我替你说吧。你是觉得自己浪费了几年,和曾经那些完全不如你的朋友同学现在居然有差距了。所以想着要不死了算了?你不信唯物主义的对吧,你相信会有来生是吧?又或者说,你只是想逃避现实而已?”
这一幕又像极了从前,我对他的说教总是以长辈似的方式进行着。真的是,清醒的时候像个智者贤师,糊涂的时候又像个小屁孩,好像男人都这样。
真切而沉闷的哭声持续着,终究是湮灭了我所有的兴致。我叹了口气,轻轻地扶起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他起身很慢,大概是碍于背上密密麻麻的鞭痕,背部肌肉的每一次运动都会伴随着剧痛。
其实我有点内疚。
哎,为了他好,对吧。
完全是,为了他好!
别笑场。
别笑场!保持该有的姿态!
我用纸巾轻轻地给他擦眼泪和鼻涕,小狗的哭泣却完全止不住,最后直接把头埋到了我怀里。温热的,脏兮兮的,唉算了。我抚摸着他的头,撸猫般顺着他的头发摸摸捏捏。这种触感也是愉悦的,大概可以形容为宁静,温和。秦老师的头发很干净,很柔软,我逗他,用手指蘸了点他的眼泪喂到他嘴里,看着他撒娇似抗拒的样子。
他哭,我笑。
太可爱了,比撸猫可好玩太多了。
窗外传来了小贩的叫卖声, 隐约间能闻到隔壁邻居厨房里散发的饭菜香气,都是我好久不曾有过的体验了。我跟秦老师聊了好多最近的事,压抑在心间的一些烦闷好似终于打开了闸口。
身体里的另一些东西也同样打开了闸口,在夕阳的柔光终于拨开了云雾照到我脸上的时候,一股来自腹部的暖流缓缓流出,姗姗来迟。
完了啊!这次是真的完了!
“林鸢,你身上什么味道?怎么怪怪的。”
秦苾眼睛红肿地从我怀中坐起身来,看起来像是刚睡醒那副模样。
丢脸死了!
“去给我拿卫生巾啊!”
“啊?我这哪来的那种玩意儿啊!”
“快去买啊!”
“哦,好!”
“回来!把衣服穿上啊喂!”
好耶!
humulation:↑好耶!摸摸猫老师!
好好好,回来了
luckyxiaoyu:↑好好好,回来了hh我一直在的啊,只是前段时间要考试什么的没啥空写东西😂😂
(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