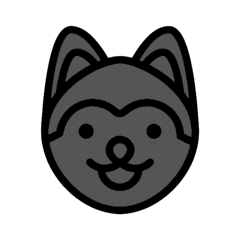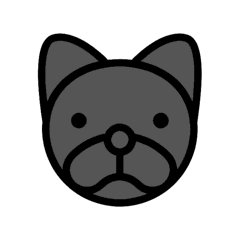昭阳
原创
一张宣纸,练笔所用,成则裱之,毁则入篓。
—盐
—盐
楔子
鎏金漆饰的门楣之下,一位白衣素装的男子以王侯之礼俯身跪叩,冬雪飘零在漫漫长夜中,他的背脊与发束早已染白,却恰如庭中那茂密生长的毛竹一般,虽曲而未折。
“长公主殿下,白某一介布衣,贱如草芥,不识礼法,不察尊卑。殿下殷殷之期,在下惶恐不已,实不敢以萤草之光伴玄烛之阙。然,南雀虽小,亦有悲鸣,恬有三问,斗胆望殿下解之。”
“蠢货。”殿中女子端坐正厅,身着绛红大髦,外裹雪白狐裘,下穿羊毛毡靴,此时沉声轻骂一句,端起桌上杯盏,小啜一口,却发现原本滚烫的茶水早已凉透。
“你问。”音声不怒自威,低沉如黄钟大吕,却似有刻意。
“殿下何所归,殿下何所为,殿下,何所求?”
男子微微抬头,明眸似水,亦温亦柔,却韧如磐石一般。彻骨的寒意使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僵硬,白气氤氲在鼻尖,有些模糊了视线。
“可笑。”随着冷哼一声,女子矫捷几步来到门槛之旁。飞雪飘到她的脸上,寒风穿堂而过,她理了理胸前的绑带,俯视身下男子,缓缓说道:
“终吾一生,既可辅父王兄长于庙堂之上,亦可携轻剑白马游江湖之远,不违天道,赤心光明,死后必不至堕入地狱之中。有人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我被骂惯了,无妨,无妨。白公子曾转告我,当不争一世,而争百世之名。那,名,为何物?争之,何用?”
四目相对,针尖麦芒,风雪依旧呼啸,竹丛丝丝作响。
“殿下,何所爱?”
男子仰视着她,那大髦的衣角随风摇摆,抽打到他的脸上。
“我答公子这最后一问,公子可应我入阁之邀?”
她跨出门外,绕着男子缓缓踱步,最终弯下腰来,向他伸出右手。
瑰丽的湖石伫立在庭中小景,它受惯了寒霜,亦见惯了枯荣。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本宫,知道了。”虽心中早有准备,但如此直白的拒绝还是让自幼鲜有挫折的她心生愤懑,那弯下的腰身似乎从礼贤下士的姿态变成了自求自讨的羞辱。
“公子的话,却是好生伤人。”
她取下狐裘,扔在风雪之中,随后毅然向屋内走去。
没让他起身,也没让他退下。
只有一句寒意盎然的回答,最终幽幽地从屋内传出。
“我所爱,是这天下。”
—————————————————————————-
一座简陋的酒馆开设在宽阔的驰道旁,此地过于偏僻,鲜有客商打尖,而在如此寒冷的冬夜,竟迎来了两位客人的光顾。二人分桌而坐,气氛并不融洽。
靠门边的那位看上去是名身材魁梧的精壮男子,披着墨绿蓑衣,带着一顶斗笠,他的头压得很低,看不清楚他的面容,既不喝酒,也不言语。
靠柜台边的这位是个一袭黑衣的年轻小伙,他的衣服早已被染上抹抹殷红,靠近点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左边袖管空空如也,似已失一臂。然而,他看起来好像心情不错,一边啃着酱棒骨一边大口饮酒,待一坛老酒下肚,竟主动与对桌的蓑衣客喊起话来。
“嘿,追我三日,竟是不饿?”
见蓑衣客不答,他毫不在意,咧嘴笑着继续问道,
“不渴?”“不累?”
店家是一位须发皆白的瘦小老者,或许是看惯了江湖中熙熙攘攘的恩怨,对屋内似一触即发的打杀毫不在意。
反正,打赢了,赔桌椅钱。打输了,赔命。
有一身着麻衣女子提着酒坛,静静地站在小伙身旁,从年龄来看应该是老者的孙女,从打扮来看自然是酒馆唯一的跑堂,而她虽然身材高挑,举止灵敏,然脸上陈痂遍布,似是火伤,看起来太过于瘆人。
“兄台。”小伙似乎并没有因为无人理他而扫了兴致,酒越喝越多,话也越来越密。
“江湖浩渺,你我朝夕相伴多日,甚是有缘。然而你要取我性命,我却又不愿给,不如先共饮一碗,再做厮杀,如何?”
“可以。”
蓑衣客终于说话了,声音中气十足,却故意压得低沉。他右手一招,示意倒酒。
女子连忙跑去,呜喑不清地说着什么,伴随着一些手势和肢体动作,看上去似乎是个哑巴。
随着桌前酒碗斟满,蓑衣客轻轻端起,碗到嘴边,却不入喉。
“小兄弟,黄泉路冷,酒可暖身。”
“哈哈哈!”
小伙双目入炬,神盈气清,好像越喝越精神抖擞。
“那小弟陪兄台多饮几杯!”
听见自己的嘲讽被小伙反击而回,蓑衣客并不恼怒,
“既你我如此投缘,那不如坦诚相待,我有一问,若小兄弟能够如实告知,莫说是多饮几杯,就是饮罢之后,你我就此别过也未尝不可。”
“好!兄台请讲!”小伙爽朗一笑,空碗翻转,指节轻扣,似在玩耍,似在配乐。
“敢问阁下,是否为,长公主昭阳,麾下门客?”蓑衣客声音极其微小,且一字一顿,缓缓问道。
“哈哈哈!”小伙并未看他本人,而是看了看他手中酒碗,随后朗声说道:
“既然与兄台有约,在下定当知无不言,不过,我答之前,请兄台满饮此杯。”
“这有何难?”蓑衣客终于端起酒碗一饮而尽,三天的追击的确让他早已又累又渴,虽不至于太过影响实力,但如此寒冬时节,有酒可饮真乃幸事,若不是大事重要,想快点从小伙口中听到答案,他真想再来一碗,或者一坛。
“说吧小兄弟。”他酒碗朝下,碗中之酒一滴不剩,满脸期待地看着小伙。
“我是!”小伙眼看着蓑衣客喉头颤动收缩,确定他已然喝下。
“我乃长公主亲自任命的‘云翳’第一剑客,实话告诉你,我还为殿下侍过寝呢!哈哈哈!”
啪。
正当小伙大笑之时,忽然飞来一记巴掌,重重拍打在他的脸颊之上,势大力沉,躲之不及。
“你这丑婆。。”他看向女跑堂,这巴掌自然来自于她,可骂人的话说到半截,他竟莫名的隐约有些心慌。
“蠢货。”那女子早已把酒坛放到桌上,寻一长椅坐下,此时举手投足之间,又哪有半分下人之气。
在听到这熟悉的骂词之后,小伙原本疑惑的心终于得到了确认,一股寒意自下而上直冲天灵。他面如死灰,之前那股豪爽英武的气概荡然无存,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小跑到女子身前扑通跪下。
“长公主殿下!”
“蠢货!”女子抓起小伙的头发,怒目圆睁地看着他,朝他另一侧脸又是一巴掌。
“如此称呼,莫不知隔墙有耳?”
他此刻匍匐在女子脚边,连微微抬头都不敢了,耳听着她的训斥,额上的汗珠滚滚而下。
“昭阳。。长公主。”
这变故来得太快,但对蓑衣客这等剑客来说,本应早就作出反应。
这酒,是真的太烈了?
剑客想逃出去,可门窗早已为了遮挡风雪而全部紧闭。他右手微微提起,想从鞘中取剑,可稍一运气,只觉浑身绵软,酥麻,就像是,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刚洗完热水澡,躺在妓女的床上,被她用舌头亲舔一般。
再一运气,只觉胸中一阵阻滞,剧痛随之袭来,接而困意上脑,使他意识渐失,恍然之间,鼻眼二窍有乌血渗出,止将不住,越流越多。
随着沉重的咚咚两声,他的上半身倒在了桌上,头颅与桌面碰撞又弹起后,终究是再没了一丝气息。
小伙听到声响,偷摸着抬头,想用余光去嫖,却不料和女子的目光撞个正着。
“死士重五。”见外敌已死,女子抬手揭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陈痂与烧痕”也随之消失,美目流转,似流风回雪,其面容灵秀绝美,显露无遗,即使螺黛不施,身着麻衣,也丝毫不影响其璀璨贵气。
她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坐姿坚韧挺拔,眼神不怒自威,俯视着脚边死士
“属下在!”
“你从八岁那年被选召到云翳,至今已有十年了吧。我,何时让你侍过寝?”
“属下。。”小伙惶恐。喝酒吹牛,脑子一热。
虽然大多数时候受到的只有长公主的鞭子与打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其深深的爱慕之情,即使身份悬殊,云泥之别,但想想总是没问题的吧。只是这荒郊野外,酒后胡言,竟被长公主一句不漏地听了去,哎!
“属下疯言疯语,愿自毁口舌,自毁口舌!”
“罢了。”昭阳轻轻踩住死士的脑袋,示意他不要再磕头了,随后轻轻一踢。
“起来吧。你已失一臂,若再失口条,以后岂不是废人一个,养你何用。”
“多谢殿下!”虽然言辞冰冷,但长公主的性情他是知道的,这样说那几乎就是没事了。
“你知道用计骗那剑客喝下毒酒,还算机灵。”
听到夸奖,重五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我闻到‘春潮’的味道就知道是援兵到了,只是那蓑衣剑客是信阳侯麾下第一高手,真要拼杀起来,怕是胜负难料,毒死再好不过。只是没想到,竟是。。。”
“没想到竟是我亲自前来?”昭阳起身,从老者手中接过数个酒碗,一一排在木桌之上。
“说吧,详细点。”
“是。”重五单臂拱手,痛彻心扉之意涌上面庞,浑身微颤,左肩空袖似在摇摆。
“那老狗早有防备,府中不仅门客众多,甚至藏有甲士弩手。同行七人,除我之外,尽皆惨死。”
“蠢货。”
“属下技艺不精,办事不力,请殿下责罚!”
“不。”昭阳摆好了酒碗,又去往柜边,随后提起一坛新酒,向碗中缓缓倒上。
“我说我自己。”
“殿。。殿下。”昭阳这忽如其来的言辞让重五一时有些不明所以,舌头都打起结来。
微黄的米酒被逐一斟好,仔细一看,满满八碗。
“死士重五,告诉我,你的真名实姓。”昭阳手扶酒坛,身姿灼灼,注视死士,眼中之神气,竟唯有肃杀。
“寇。。寇青。”
死士这次并不是因为舌头打结,而是他似乎早已忘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回想起来甚至有些陌生,叫唤出来亦是拗口,更不清楚长公主忽然问起是为何意。
“好,寇青。”昭阳端起一碗满酒,虽酒满将溢,然则纹丝不动。
“我饮一碗,汝饮七碗。”
此言一出,寇青默然,昭阳之意,其心知肚明。他解下束带,长发倾泻而下,俯仰之间,泪光潸然。
“死士伯三,谢长公主赐酒!”寇青脑中回忆着这个名字归属者的模样,随后端起一碗,豪饮而尽,饮罢过后,用力一掷,随着清脆的一声,陶碗碎为齑粉。
“死士叔九,谢长公主赐酒!”“死士仲四,谢长公主赐酒!”
。。。
他连饮六碗,连唤六人,云翳七士,竟似全员到齐。酒为殿下亲赐亲斟,他们同饮美酒,同享殊荣。
地上一片狼藉,桌上唯余一碗。
“死士,寇青,谢,长公主赐酒!”
最后一碗,最后一士。
昭阳举碗,与之相碰,一同饮罢,二碗齐碎。
“筱伯,这善后事宜就交给你了。”昭阳望向柜内老者,吩咐一句。
“请殿下放心。”老者原本佝偻的腰又微微弯了一些,语气恭敬地回答道,取出一件绣袍披风,双手递了过去。
“走。”昭阳接过披风,望了寇青一眼。
风雪呼啸得更厉害了,不断有折断的树枝咔咔作响,大地早已银装素裹,山林寂静,甚是可怕。
此时定不是赶路的好时候,但毕竟此地不是荥阳,不宜久留。
一匹高大健壮的白马站立在马厩之内,它不停地踱步,鼻口白气四溢,似在等待主人,又似在以此取暖。
饮酒过度,最怕霜寒,狂风略过,寇青只觉一阵反胃。他衣衫单薄,却无披风御寒,虽不至于瑟瑟发抖,却也是刺骨万分。
昭阳在马厩前站住,又回头冷冷地望向寇青一眼。
寇青明了,连忙小跑几步,在马蹄边上蹲下。他左臂已失,以肉躯做上马石必不稳贴,只有右臂暗自用力,略微往鼻尖位置靠拢,以此来形成一个较为牢固的三角支架。地面更加冰冷,他的手掌和膝盖此时宛如置于冰窖之中,却懒得计较,只是呸呸两口,吐了吐不小心吃进口中的马厩茅草。
“走吧。”随着左脚重重一踩,一枚潮湿的靴底印记盖在了寇青背上,昭阳翻身上马,微微调整坐姿,拉了拉缰绳,往风雪中走去。
风雪迷眼,白马徐徐前行,步缓蹄慢。寇青从昭阳手中接过缰绳,以独臂拽着,在马前先行。
“冷吗?”昭阳问道。
“冷!”寇青笑着答道,本性洒脱再次浮现。只是忘形之际,口中又多饮了几口飞雪。
“今日得以与殿下同饮,死也值了,风雪何惧之有!哈哈哈!”
二人谈话之际,只听嘶嘶数声,晃眼之间,竟似有一活物横栏在驰道之上。风雪太大,看不太清,定睛望去,竟是一条吊睛白额大虫,离她们不过数丈距离。它岿然不动,张口低吟着,双眼通红,杀气四溢。按理说,此等气候此物应该在洞穴内沉眠,而若遇到,那定是饿了好久。
寇青在幼年时曾跟随父辈们进山打猎,也见过老虎,甚至也见过数人协作捕杀老虎的全过程。但如今,他已失一臂,自然是失了些胆气,且孤身一人。不,有长公主在旁,可是,自己能让殿下涉险吗?
“去。”昭阳端坐马背上命令道,声音沉稳,似是丝毫不惊。
听到命令,寇青扔下缰绳,拔出腰间佩剑。可是,虽然自己也算是杀人无数,可毕竟是首次与这般巨兽搏斗,虎啸阵阵,使他浑身战战兢兢,肢体有些畏缩,甚至,心中有些胆怯。
“去啊!”见他迟疑不决,昭阳举起马鞭,重重抽打他的背上,命令中带有怒气。
寇青单薄的黑衣背后霎时突现一道血印,冷风灌入,伴随着鞭打的疼痛,寇青的心中竟莫名地生出一股强烈的勇气。
他似乎,喜欢这种感觉。
于是,一头独臂醉虎,在主人的驱赶下,终于举起剑,向另一头饿虎扑去。
可他,终究是喝了太多的酒了。虽自觉步伐更加轻盈,但看起来却是杂乱无章,滑稽无比。而更为滑稽的是,在他离饿虎不到一丈距离之时,竟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了下去,随着胃中剧烈的翻涌,酸臭的酒液裹着酱骨肉一齐被呕吐出来。
“啊!”
他的喊叫无比痛苦,不是因为饿虎在前而即将丧命,也不是因为鞭痕与严寒。而是,长公主殿下亲自为他斟的酒,就这样,没了。
“蠢货。”看到他这幅丑态,昭阳眉黛紧锁,骂起了她那句时常挂在嘴边的词汇。话音一落,她熟练地从鞍鞯旁取下长弓与箭矢,顷刻之间弓箭蓄势待发,英姿既烈而美,就似古书中言道那般,前推泰山,发如虎尾。
长箭飞驰而去,正中大虫眉心,弓力极强,寒光略过,箭身已完全嵌入虎脑之中。
那大虫长啸一声,霎时山林俱颤,它挣扎着尝试站起来,脑中热血却流淌不止,爪下白雪渐成血泊,最终,重重倒了下去。
“真想赏你一箭。”眼见大虫死透,昭阳作势又起一箭,对准那仍在呕吐的独臂死士。吸气凝神,压了压怒气后,最终还是作罢。
清晨的阳光带来一丝难得的温暖,在诺大的长公主府上,仆人们一边有说有笑的聊着些什么,一边清扫着院中积雪。
“筱伯。”昭阳用过早点,正在仆人的伺候下用新茶漱口。
“老朽在。”老者的腰还是依旧那么佝偻,微微拱手。他的手上有许多被抓伤的痕迹,看起来应该是信鸽所为。
“今日有何要事吗?”昭阳问道,拾起暖巾擦了擦嘴。
“有。”老者缓缓答道,“刑狱有信传来,于三日前在蓟城抓获一名覃国间者,兹事体大,希望长公主能亲自前去审问。
“哎。”昭阳轻叹一声,“这司寇一职当真繁琐,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推了去,能落不少清净。”
说到“寇”字,昭阳忽然想起了什么。
“那位酒剑士醒了吗?”
“醒了,身体已无大碍。云翳经此一役,元气有损,老朽定会再择良士,悉心培养,以备长公主。。。”
“罢了。”昭阳望向庭中,晨曦柔抚之下,早鸟脆鸣,枝上落雪扑簌。
“给菡国多留些好儿郎吧。那毛头小子虽无大用,但毕竟对我还算忠心,待他痊愈,让其做我身边一士。白公子曾说,清肃内政,杀人无用,唯有诛心,我若早听他言,也不至于让这么多猛士英杰为我殒命。”
她难得露出一丝哀伤,而这幅神色却是转瞬即逝。
“对了,我之前问白公子的话,他有回复吗?”
“回信刚到。”老者似无需书信,一字一句皆在脑中。
“白公子说,如今中州七国,虽强弱不一,而各有长短,但尚无有一国堪灭另一国之可能,非是不能,实是不可,因为群雄如群虎,群虎环伺之下,若强虎鲸吞弱虎,而其余五虎必不会袖手旁观。”
“公子妙喻啊。”昭阳点头,脑中忽有一阵酸涩闪过。
“莜伯,数日前,我梦中得见白公子。他跪在门外,予我四问。我悉数答之,而后邀他入阁,而他却。。”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请问,他是以此句自白拒绝殿下的吗?”老者笑了笑,他侍奉这位殿下已近十年,二人之间主仆虚礼有时可以将就一点。
“莜伯神人,竟能窥我之梦。”
“非也。”老者摇摇头,“老朽非有窥梦之能,只是与那白公子神交太久,过于熟悉了。
“不来便不来吧,本宫倒无所谓。”昭阳脸色一变,心境似亦随之变化,“莜伯你刚才说,刑狱抓获的是覃国的间者?”
“是的,殿下。”
“那,走吧,去看看。”
鎏金漆饰的门楣之下,一位白衣素装的男子以王侯之礼俯身跪叩,冬雪飘零在漫漫长夜中,他的背脊与发束早已染白,却恰如庭中那茂密生长的毛竹一般,虽曲而未折。
“长公主殿下,白某一介布衣,贱如草芥,不识礼法,不察尊卑。殿下殷殷之期,在下惶恐不已,实不敢以萤草之光伴玄烛之阙。然,南雀虽小,亦有悲鸣,恬有三问,斗胆望殿下解之。”
“蠢货。”殿中女子端坐正厅,身着绛红大髦,外裹雪白狐裘,下穿羊毛毡靴,此时沉声轻骂一句,端起桌上杯盏,小啜一口,却发现原本滚烫的茶水早已凉透。
“你问。”音声不怒自威,低沉如黄钟大吕,却似有刻意。
“殿下何所归,殿下何所为,殿下,何所求?”
男子微微抬头,明眸似水,亦温亦柔,却韧如磐石一般。彻骨的寒意使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僵硬,白气氤氲在鼻尖,有些模糊了视线。
“可笑。”随着冷哼一声,女子矫捷几步来到门槛之旁。飞雪飘到她的脸上,寒风穿堂而过,她理了理胸前的绑带,俯视身下男子,缓缓说道:
“终吾一生,既可辅父王兄长于庙堂之上,亦可携轻剑白马游江湖之远,不违天道,赤心光明,死后必不至堕入地狱之中。有人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我被骂惯了,无妨,无妨。白公子曾转告我,当不争一世,而争百世之名。那,名,为何物?争之,何用?”
四目相对,针尖麦芒,风雪依旧呼啸,竹丛丝丝作响。
“殿下,何所爱?”
男子仰视着她,那大髦的衣角随风摇摆,抽打到他的脸上。
“我答公子这最后一问,公子可应我入阁之邀?”
她跨出门外,绕着男子缓缓踱步,最终弯下腰来,向他伸出右手。
瑰丽的湖石伫立在庭中小景,它受惯了寒霜,亦见惯了枯荣。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本宫,知道了。”虽心中早有准备,但如此直白的拒绝还是让自幼鲜有挫折的她心生愤懑,那弯下的腰身似乎从礼贤下士的姿态变成了自求自讨的羞辱。
“公子的话,却是好生伤人。”
她取下狐裘,扔在风雪之中,随后毅然向屋内走去。
没让他起身,也没让他退下。
只有一句寒意盎然的回答,最终幽幽地从屋内传出。
“我所爱,是这天下。”
—————————————————————————-
一座简陋的酒馆开设在宽阔的驰道旁,此地过于偏僻,鲜有客商打尖,而在如此寒冷的冬夜,竟迎来了两位客人的光顾。二人分桌而坐,气氛并不融洽。
靠门边的那位看上去是名身材魁梧的精壮男子,披着墨绿蓑衣,带着一顶斗笠,他的头压得很低,看不清楚他的面容,既不喝酒,也不言语。
靠柜台边的这位是个一袭黑衣的年轻小伙,他的衣服早已被染上抹抹殷红,靠近点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左边袖管空空如也,似已失一臂。然而,他看起来好像心情不错,一边啃着酱棒骨一边大口饮酒,待一坛老酒下肚,竟主动与对桌的蓑衣客喊起话来。
“嘿,追我三日,竟是不饿?”
见蓑衣客不答,他毫不在意,咧嘴笑着继续问道,
“不渴?”“不累?”
店家是一位须发皆白的瘦小老者,或许是看惯了江湖中熙熙攘攘的恩怨,对屋内似一触即发的打杀毫不在意。
反正,打赢了,赔桌椅钱。打输了,赔命。
有一身着麻衣女子提着酒坛,静静地站在小伙身旁,从年龄来看应该是老者的孙女,从打扮来看自然是酒馆唯一的跑堂,而她虽然身材高挑,举止灵敏,然脸上陈痂遍布,似是火伤,看起来太过于瘆人。
“兄台。”小伙似乎并没有因为无人理他而扫了兴致,酒越喝越多,话也越来越密。
“江湖浩渺,你我朝夕相伴多日,甚是有缘。然而你要取我性命,我却又不愿给,不如先共饮一碗,再做厮杀,如何?”
“可以。”
蓑衣客终于说话了,声音中气十足,却故意压得低沉。他右手一招,示意倒酒。
女子连忙跑去,呜喑不清地说着什么,伴随着一些手势和肢体动作,看上去似乎是个哑巴。
随着桌前酒碗斟满,蓑衣客轻轻端起,碗到嘴边,却不入喉。
“小兄弟,黄泉路冷,酒可暖身。”
“哈哈哈!”
小伙双目入炬,神盈气清,好像越喝越精神抖擞。
“那小弟陪兄台多饮几杯!”
听见自己的嘲讽被小伙反击而回,蓑衣客并不恼怒,
“既你我如此投缘,那不如坦诚相待,我有一问,若小兄弟能够如实告知,莫说是多饮几杯,就是饮罢之后,你我就此别过也未尝不可。”
“好!兄台请讲!”小伙爽朗一笑,空碗翻转,指节轻扣,似在玩耍,似在配乐。
“敢问阁下,是否为,长公主昭阳,麾下门客?”蓑衣客声音极其微小,且一字一顿,缓缓问道。
“哈哈哈!”小伙并未看他本人,而是看了看他手中酒碗,随后朗声说道:
“既然与兄台有约,在下定当知无不言,不过,我答之前,请兄台满饮此杯。”
“这有何难?”蓑衣客终于端起酒碗一饮而尽,三天的追击的确让他早已又累又渴,虽不至于太过影响实力,但如此寒冬时节,有酒可饮真乃幸事,若不是大事重要,想快点从小伙口中听到答案,他真想再来一碗,或者一坛。
“说吧小兄弟。”他酒碗朝下,碗中之酒一滴不剩,满脸期待地看着小伙。
“我是!”小伙眼看着蓑衣客喉头颤动收缩,确定他已然喝下。
“我乃长公主亲自任命的‘云翳’第一剑客,实话告诉你,我还为殿下侍过寝呢!哈哈哈!”
啪。
正当小伙大笑之时,忽然飞来一记巴掌,重重拍打在他的脸颊之上,势大力沉,躲之不及。
“你这丑婆。。”他看向女跑堂,这巴掌自然来自于她,可骂人的话说到半截,他竟莫名的隐约有些心慌。
“蠢货。”那女子早已把酒坛放到桌上,寻一长椅坐下,此时举手投足之间,又哪有半分下人之气。
在听到这熟悉的骂词之后,小伙原本疑惑的心终于得到了确认,一股寒意自下而上直冲天灵。他面如死灰,之前那股豪爽英武的气概荡然无存,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小跑到女子身前扑通跪下。
“长公主殿下!”
“蠢货!”女子抓起小伙的头发,怒目圆睁地看着他,朝他另一侧脸又是一巴掌。
“如此称呼,莫不知隔墙有耳?”
他此刻匍匐在女子脚边,连微微抬头都不敢了,耳听着她的训斥,额上的汗珠滚滚而下。
“昭阳。。长公主。”
这变故来得太快,但对蓑衣客这等剑客来说,本应早就作出反应。
这酒,是真的太烈了?
剑客想逃出去,可门窗早已为了遮挡风雪而全部紧闭。他右手微微提起,想从鞘中取剑,可稍一运气,只觉浑身绵软,酥麻,就像是,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刚洗完热水澡,躺在妓女的床上,被她用舌头亲舔一般。
再一运气,只觉胸中一阵阻滞,剧痛随之袭来,接而困意上脑,使他意识渐失,恍然之间,鼻眼二窍有乌血渗出,止将不住,越流越多。
随着沉重的咚咚两声,他的上半身倒在了桌上,头颅与桌面碰撞又弹起后,终究是再没了一丝气息。
小伙听到声响,偷摸着抬头,想用余光去嫖,却不料和女子的目光撞个正着。
“死士重五。”见外敌已死,女子抬手揭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陈痂与烧痕”也随之消失,美目流转,似流风回雪,其面容灵秀绝美,显露无遗,即使螺黛不施,身着麻衣,也丝毫不影响其璀璨贵气。
她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坐姿坚韧挺拔,眼神不怒自威,俯视着脚边死士
“属下在!”
“你从八岁那年被选召到云翳,至今已有十年了吧。我,何时让你侍过寝?”
“属下。。”小伙惶恐。喝酒吹牛,脑子一热。
虽然大多数时候受到的只有长公主的鞭子与打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其深深的爱慕之情,即使身份悬殊,云泥之别,但想想总是没问题的吧。只是这荒郊野外,酒后胡言,竟被长公主一句不漏地听了去,哎!
“属下疯言疯语,愿自毁口舌,自毁口舌!”
“罢了。”昭阳轻轻踩住死士的脑袋,示意他不要再磕头了,随后轻轻一踢。
“起来吧。你已失一臂,若再失口条,以后岂不是废人一个,养你何用。”
“多谢殿下!”虽然言辞冰冷,但长公主的性情他是知道的,这样说那几乎就是没事了。
“你知道用计骗那剑客喝下毒酒,还算机灵。”
听到夸奖,重五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我闻到‘春潮’的味道就知道是援兵到了,只是那蓑衣剑客是信阳侯麾下第一高手,真要拼杀起来,怕是胜负难料,毒死再好不过。只是没想到,竟是。。。”
“没想到竟是我亲自前来?”昭阳起身,从老者手中接过数个酒碗,一一排在木桌之上。
“说吧,详细点。”
“是。”重五单臂拱手,痛彻心扉之意涌上面庞,浑身微颤,左肩空袖似在摇摆。
“那老狗早有防备,府中不仅门客众多,甚至藏有甲士弩手。同行七人,除我之外,尽皆惨死。”
“蠢货。”
“属下技艺不精,办事不力,请殿下责罚!”
“不。”昭阳摆好了酒碗,又去往柜边,随后提起一坛新酒,向碗中缓缓倒上。
“我说我自己。”
“殿。。殿下。”昭阳这忽如其来的言辞让重五一时有些不明所以,舌头都打起结来。
微黄的米酒被逐一斟好,仔细一看,满满八碗。
“死士重五,告诉我,你的真名实姓。”昭阳手扶酒坛,身姿灼灼,注视死士,眼中之神气,竟唯有肃杀。
“寇。。寇青。”
死士这次并不是因为舌头打结,而是他似乎早已忘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回想起来甚至有些陌生,叫唤出来亦是拗口,更不清楚长公主忽然问起是为何意。
“好,寇青。”昭阳端起一碗满酒,虽酒满将溢,然则纹丝不动。
“我饮一碗,汝饮七碗。”
此言一出,寇青默然,昭阳之意,其心知肚明。他解下束带,长发倾泻而下,俯仰之间,泪光潸然。
“死士伯三,谢长公主赐酒!”寇青脑中回忆着这个名字归属者的模样,随后端起一碗,豪饮而尽,饮罢过后,用力一掷,随着清脆的一声,陶碗碎为齑粉。
“死士叔九,谢长公主赐酒!”“死士仲四,谢长公主赐酒!”
。。。
他连饮六碗,连唤六人,云翳七士,竟似全员到齐。酒为殿下亲赐亲斟,他们同饮美酒,同享殊荣。
地上一片狼藉,桌上唯余一碗。
“死士,寇青,谢,长公主赐酒!”
最后一碗,最后一士。
昭阳举碗,与之相碰,一同饮罢,二碗齐碎。
“筱伯,这善后事宜就交给你了。”昭阳望向柜内老者,吩咐一句。
“请殿下放心。”老者原本佝偻的腰又微微弯了一些,语气恭敬地回答道,取出一件绣袍披风,双手递了过去。
“走。”昭阳接过披风,望了寇青一眼。
风雪呼啸得更厉害了,不断有折断的树枝咔咔作响,大地早已银装素裹,山林寂静,甚是可怕。
此时定不是赶路的好时候,但毕竟此地不是荥阳,不宜久留。
一匹高大健壮的白马站立在马厩之内,它不停地踱步,鼻口白气四溢,似在等待主人,又似在以此取暖。
饮酒过度,最怕霜寒,狂风略过,寇青只觉一阵反胃。他衣衫单薄,却无披风御寒,虽不至于瑟瑟发抖,却也是刺骨万分。
昭阳在马厩前站住,又回头冷冷地望向寇青一眼。
寇青明了,连忙小跑几步,在马蹄边上蹲下。他左臂已失,以肉躯做上马石必不稳贴,只有右臂暗自用力,略微往鼻尖位置靠拢,以此来形成一个较为牢固的三角支架。地面更加冰冷,他的手掌和膝盖此时宛如置于冰窖之中,却懒得计较,只是呸呸两口,吐了吐不小心吃进口中的马厩茅草。
“走吧。”随着左脚重重一踩,一枚潮湿的靴底印记盖在了寇青背上,昭阳翻身上马,微微调整坐姿,拉了拉缰绳,往风雪中走去。
风雪迷眼,白马徐徐前行,步缓蹄慢。寇青从昭阳手中接过缰绳,以独臂拽着,在马前先行。
“冷吗?”昭阳问道。
“冷!”寇青笑着答道,本性洒脱再次浮现。只是忘形之际,口中又多饮了几口飞雪。
“今日得以与殿下同饮,死也值了,风雪何惧之有!哈哈哈!”
二人谈话之际,只听嘶嘶数声,晃眼之间,竟似有一活物横栏在驰道之上。风雪太大,看不太清,定睛望去,竟是一条吊睛白额大虫,离她们不过数丈距离。它岿然不动,张口低吟着,双眼通红,杀气四溢。按理说,此等气候此物应该在洞穴内沉眠,而若遇到,那定是饿了好久。
寇青在幼年时曾跟随父辈们进山打猎,也见过老虎,甚至也见过数人协作捕杀老虎的全过程。但如今,他已失一臂,自然是失了些胆气,且孤身一人。不,有长公主在旁,可是,自己能让殿下涉险吗?
“去。”昭阳端坐马背上命令道,声音沉稳,似是丝毫不惊。
听到命令,寇青扔下缰绳,拔出腰间佩剑。可是,虽然自己也算是杀人无数,可毕竟是首次与这般巨兽搏斗,虎啸阵阵,使他浑身战战兢兢,肢体有些畏缩,甚至,心中有些胆怯。
“去啊!”见他迟疑不决,昭阳举起马鞭,重重抽打他的背上,命令中带有怒气。
寇青单薄的黑衣背后霎时突现一道血印,冷风灌入,伴随着鞭打的疼痛,寇青的心中竟莫名地生出一股强烈的勇气。
他似乎,喜欢这种感觉。
于是,一头独臂醉虎,在主人的驱赶下,终于举起剑,向另一头饿虎扑去。
可他,终究是喝了太多的酒了。虽自觉步伐更加轻盈,但看起来却是杂乱无章,滑稽无比。而更为滑稽的是,在他离饿虎不到一丈距离之时,竟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了下去,随着胃中剧烈的翻涌,酸臭的酒液裹着酱骨肉一齐被呕吐出来。
“啊!”
他的喊叫无比痛苦,不是因为饿虎在前而即将丧命,也不是因为鞭痕与严寒。而是,长公主殿下亲自为他斟的酒,就这样,没了。
“蠢货。”看到他这幅丑态,昭阳眉黛紧锁,骂起了她那句时常挂在嘴边的词汇。话音一落,她熟练地从鞍鞯旁取下长弓与箭矢,顷刻之间弓箭蓄势待发,英姿既烈而美,就似古书中言道那般,前推泰山,发如虎尾。
长箭飞驰而去,正中大虫眉心,弓力极强,寒光略过,箭身已完全嵌入虎脑之中。
那大虫长啸一声,霎时山林俱颤,它挣扎着尝试站起来,脑中热血却流淌不止,爪下白雪渐成血泊,最终,重重倒了下去。
“真想赏你一箭。”眼见大虫死透,昭阳作势又起一箭,对准那仍在呕吐的独臂死士。吸气凝神,压了压怒气后,最终还是作罢。
清晨的阳光带来一丝难得的温暖,在诺大的长公主府上,仆人们一边有说有笑的聊着些什么,一边清扫着院中积雪。
“筱伯。”昭阳用过早点,正在仆人的伺候下用新茶漱口。
“老朽在。”老者的腰还是依旧那么佝偻,微微拱手。他的手上有许多被抓伤的痕迹,看起来应该是信鸽所为。
“今日有何要事吗?”昭阳问道,拾起暖巾擦了擦嘴。
“有。”老者缓缓答道,“刑狱有信传来,于三日前在蓟城抓获一名覃国间者,兹事体大,希望长公主能亲自前去审问。
“哎。”昭阳轻叹一声,“这司寇一职当真繁琐,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推了去,能落不少清净。”
说到“寇”字,昭阳忽然想起了什么。
“那位酒剑士醒了吗?”
“醒了,身体已无大碍。云翳经此一役,元气有损,老朽定会再择良士,悉心培养,以备长公主。。。”
“罢了。”昭阳望向庭中,晨曦柔抚之下,早鸟脆鸣,枝上落雪扑簌。
“给菡国多留些好儿郎吧。那毛头小子虽无大用,但毕竟对我还算忠心,待他痊愈,让其做我身边一士。白公子曾说,清肃内政,杀人无用,唯有诛心,我若早听他言,也不至于让这么多猛士英杰为我殒命。”
她难得露出一丝哀伤,而这幅神色却是转瞬即逝。
“对了,我之前问白公子的话,他有回复吗?”
“回信刚到。”老者似无需书信,一字一句皆在脑中。
“白公子说,如今中州七国,虽强弱不一,而各有长短,但尚无有一国堪灭另一国之可能,非是不能,实是不可,因为群雄如群虎,群虎环伺之下,若强虎鲸吞弱虎,而其余五虎必不会袖手旁观。”
“公子妙喻啊。”昭阳点头,脑中忽有一阵酸涩闪过。
“莜伯,数日前,我梦中得见白公子。他跪在门外,予我四问。我悉数答之,而后邀他入阁,而他却。。”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请问,他是以此句自白拒绝殿下的吗?”老者笑了笑,他侍奉这位殿下已近十年,二人之间主仆虚礼有时可以将就一点。
“莜伯神人,竟能窥我之梦。”
“非也。”老者摇摇头,“老朽非有窥梦之能,只是与那白公子神交太久,过于熟悉了。
“不来便不来吧,本宫倒无所谓。”昭阳脸色一变,心境似亦随之变化,“莜伯你刚才说,刑狱抓获的是覃国的间者?”
“是的,殿下。”
“那,走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