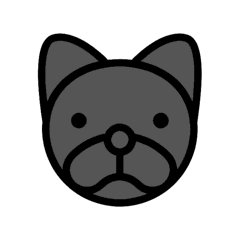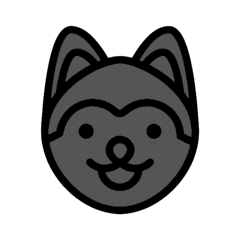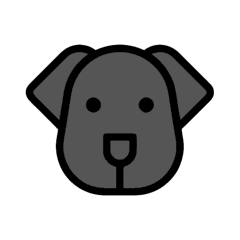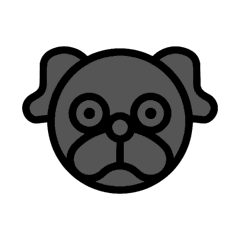女性
短篇原创’24 征文比赛足控贡奴
征文比赛赛果
此作品参加了 2024 年夏季举办的叁孙杯「恶女」题材 M 向小说征文比赛,以下为其获得的评委评分和读者投票:
色情
50/100
后 50% σ=29.8
文学
74/80
前 10% σ=4.0
合题
76/80
第二名 σ=6.0
创意
29/40
前 25% σ=8.0
评委总分
228/300
前 25% σ=32.4
我家时常有蚊子出没。蚊子有着长长的口器和纤细的腰肢,按古希腊的标准来评判是极美的。蚊子幽幽的眼光发现目标时,先不着急享用人血,而是用特有的感受器轻抚受害者的皮肤,等那人舒服的麻痹时再将口器刺破皮层。蚊子的手段是怀柔的,口器塞进一半即停,接着顺理成章地收受井喷的血液,喝饱之后再把唾液呸进人的细动脉就算完成了仪式。
在人间蚊子几乎是“恶”的化身,高频尖锐的振翅声,贪到胀破也不收敛的胃口,总是使人毛骨悚然地发现,蚊子不知何时已降落到自己身上吮吸血液。
这样的悲剧在每一个燥热的夏季循环往复的上演,蚊子喝完血诞下小蚊子,小蚊子喝完血诞下小小蚊子,一如既往的盘旋在受害者的天空。然而,在人间偏偏有这样不可救药的受害者,明明被蚊子吸的形销骨立,却义无反顾的期待蚊子的再次君临。
谷川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蚊子吸走了他的土地钱财,吸走了他的前途命运,只给他留下一具萎靡不振的行尸走肉。即便干瘪成这样,为了蚊子的眷顾,他还硬往静脉里泵水充当没事人哩。
我初次见谷川先生,他还是肥头大耳白白胖胖的阔员外。谷川先生笑吟吟的对我说,他的家业是败不完的。他没有吹嘘,谷川先生祖上是有名的富商,临死前给他留了一条河一座山一栋别墅。河里有鱼虾沙金,山上有茂林修竹,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至于那别墅修的更是富丽堂皇,就是掘根柱子,挖块垫砖卖了也够寻常人家世代无忧。这样的富庶,像谷川先生说的,又怎么能败光呢?
谷川先生见到我的孤陋寡闻,神神秘秘的告诉我,他结识了一位明丽动人的女性。奥,女性。我警醒他,女性,又是明丽动人的女性,要小心提防,她们会像蚊子一样不知不觉间吮骨吸髓。谷川先生则甚是不以为意,他这样大的家业,像个二百斤的胖子,一只细小的蚊子,纵使吸的涨肚而亡,又怎么吸的了胖子血的九牛一毛呢,更遑论吸干。听他这样讲,我就知道他怕是已经殷勤交了些东西,但我不好再败他的兴致。谷川先生兴致勃勃的继续讲,那位女性有色若丹虹的唇,有丰满耸弹的乳,而女性那犹如婴儿脸颊般细腻柔软的足,尤其叫他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谷川先生带我到河边去看,那儿数十台抽水机轰鸣叫嚣着。部分抽干水裸露的河床上,几只鱼眼睛半青半白的圆睁着,不时有气无力的甩下尾巴,试图驱走来吸血的蚊子。他说抽干水是为了提炼沙金,但我了解到他是想起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在这河里有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埋在沙下。他想掘地三尺挖出夜明珠献给女性,换来舔舐他魂牵梦绕的那位女性的足的机会。
河抽干了,也不全然是坏处。至少河里的孑孓干死了,蚊子就少了些害人的机会。
我再次见谷川先生,他正在山上指挥工人砍树。原本碧绿荫凉的山林残了一半,现在半灰半绿极不协调极为难看。我疑惑他砍树做什么,他说是要修造行宫,修造气派的帝城双凤阙。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确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楼宇,不过那制式,说起来到底是像凤翼还是蚊翅?
谷川先生说话间,眼睛突然有了神采,几乎是一百八十度扭过头去,接着身体开始触了电般的发颤。他这时已经不那么肥胖,呆滞一秒就矫健的跑走了,留我在树荫下不明所以。崎岖的山路即便小心走也不免磕绊,更何况他这样像见了骨头的狗一样心无旁骛的跑,他几乎是连滚带爬。
我和工人看见谷川先生邀功般拜倒在帝城双凤阙的高门前,迎接慢慢从里走出来的女性。谷川先生摇头晃脑给自己颈上锁上项圈,伏在女性身前乞求女性牵住缰绳。女性没有理会呈上的缰绳,而是顺势坐到谷川先生的脊上,圆润紧翘的臀压的谷川先生又矮一截。女性夹了一根细雪茄,袅袅的仙烟就从女性色若丹虹的唇里吐出来。臀下的谷川先生尽力吸了这香气,浑身的毛细血管便扩张许多,心脏泵血也比以往更孔武有力。
山伐空了,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的想还是能发现好处。至少随意丢弃的雪茄,即便没有谷川先生用湿润的舌头去舔舐,也点燃不起森林大火。
我最后见谷川先生,他跪在原先是他的别墅花园的泥土里,颤颤巍巍的拿着把小手镰割草。太阳毒的把空气烤出摩尔纹,现在他身上早没有一点油脂可以渗出来。他为什么除草不用除草机,后来我知道是他怕割草机动静太大吵扰女性的午后闲愉。他跟我解释说,他是在减肥,减他黑瘦结实臂膀上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的脂肪,减他满是鞭痕屁股上我看来看去也看不见的赘肉。他劳作时还戴着一副厚厚的皮手套,我劝他这么燥热的天气不如摘下来,他躲躲闪闪没有回应。后来我知道他的掌心早被女性的尖锐鞋跟刺透,手掌现在还裹着纱布,里头的烂肉生了蛆结了痂和纱布长在一起再也揭不下来,所以要戴一副皮手套掩人耳目。
忽而我听见别墅内甩鞭声,谷川先生便如遭了鞭子一样身体痉挛抽缩一下,本就黑瘦干瘪的身体又小一圈像个侏儒。谷川先生听见鞭声,即顾不得手镰的刀刃锋利割伤哪里,双膝猛一扣地跃起来往别墅居住区蛙跳袭去,隔三五米跳跃间隔留地上些碎骨碴子,应该是衣着单薄,着地没有缓冲,而身体内血也早流干的缘故。
不多时,便见枯干的谷川先生费力的拖着一辆洋车出来。洋车高高的轮子碾死侏儒的谷川先生像碾死一只搬家的蚂蚁一样轻松。洋车上有华盖遮阳,让人偷窥不了艳彩华盖里面是怎么样的曼妙无穷。华盖的豁口,伸出女性那犹如婴儿脸颊般细腻柔软的足。吻住女性柔软的足底的,是一双华丽的鞋子,鞋跟是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车出来的。而吻住华丽鞋子的鞋底的,才轮到谷川先生的脊背。谷川先生的脊背上有个不知什么时候剜的洞,直通到脊骨上一个不知什么时候钻的窝。华丽鞋子的鞋跟恰巧被洞窝包裹起来,谷川先生身上大部分的神经已经坏死,但是脊骨里这条还完好,是为便于女性用鞋跟控制洋车行进的速度方向。女性足底稍一用力,谷川先生就痛苦地龇唇咧嘴————谷川先生的牙因为在舔舐女性的皮鞋时不慎留了印而被赏赐自行敲去。
洋车最后稳稳当当停在花园的一片月季前,谷川先生早就轻车熟路,一路没有丝毫颠簸。华盖终于徐徐打开,华丽的鞋子从谷川先生的脊背上取下,在空中划道优雅的曲线,准确无误的踏在柔软的皮手套上,金属鞋跟也默契的钻透掌心。女性不知随口命令了什么,谷川先生的头就向泥土里蛹去。因为没有牙,谷川先生只能用舌头嘴唇一点点磨断月季的根茎,然后含着月季根茎极力向上托举呈递。女性取起花来,微笑着把有刺的部位插进谷川先生的呼吸道,只摘一片花瓣嗅嗅。
女性松开手,花瓣便随着和风辗转,飞到渺远的河里,孑孓们一拥而上享受了养分。
河不是干了吗?原来干了一条河,还有一万条河,空了一座山,还有一万座山。蚊子就在这大自然的酷暑里愈衍愈烈,永不禁绝。
我终于看清蚊子,这就是那个总在华盖里,吸干谷川先生,几乎等同于“恶”的女性。
在人间蚊子几乎是“恶”的化身,高频尖锐的振翅声,贪到胀破也不收敛的胃口,总是使人毛骨悚然地发现,蚊子不知何时已降落到自己身上吮吸血液。
这样的悲剧在每一个燥热的夏季循环往复的上演,蚊子喝完血诞下小蚊子,小蚊子喝完血诞下小小蚊子,一如既往的盘旋在受害者的天空。然而,在人间偏偏有这样不可救药的受害者,明明被蚊子吸的形销骨立,却义无反顾的期待蚊子的再次君临。
谷川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蚊子吸走了他的土地钱财,吸走了他的前途命运,只给他留下一具萎靡不振的行尸走肉。即便干瘪成这样,为了蚊子的眷顾,他还硬往静脉里泵水充当没事人哩。
我初次见谷川先生,他还是肥头大耳白白胖胖的阔员外。谷川先生笑吟吟的对我说,他的家业是败不完的。他没有吹嘘,谷川先生祖上是有名的富商,临死前给他留了一条河一座山一栋别墅。河里有鱼虾沙金,山上有茂林修竹,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至于那别墅修的更是富丽堂皇,就是掘根柱子,挖块垫砖卖了也够寻常人家世代无忧。这样的富庶,像谷川先生说的,又怎么能败光呢?
谷川先生见到我的孤陋寡闻,神神秘秘的告诉我,他结识了一位明丽动人的女性。奥,女性。我警醒他,女性,又是明丽动人的女性,要小心提防,她们会像蚊子一样不知不觉间吮骨吸髓。谷川先生则甚是不以为意,他这样大的家业,像个二百斤的胖子,一只细小的蚊子,纵使吸的涨肚而亡,又怎么吸的了胖子血的九牛一毛呢,更遑论吸干。听他这样讲,我就知道他怕是已经殷勤交了些东西,但我不好再败他的兴致。谷川先生兴致勃勃的继续讲,那位女性有色若丹虹的唇,有丰满耸弹的乳,而女性那犹如婴儿脸颊般细腻柔软的足,尤其叫他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谷川先生带我到河边去看,那儿数十台抽水机轰鸣叫嚣着。部分抽干水裸露的河床上,几只鱼眼睛半青半白的圆睁着,不时有气无力的甩下尾巴,试图驱走来吸血的蚊子。他说抽干水是为了提炼沙金,但我了解到他是想起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在这河里有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埋在沙下。他想掘地三尺挖出夜明珠献给女性,换来舔舐他魂牵梦绕的那位女性的足的机会。
河抽干了,也不全然是坏处。至少河里的孑孓干死了,蚊子就少了些害人的机会。
我再次见谷川先生,他正在山上指挥工人砍树。原本碧绿荫凉的山林残了一半,现在半灰半绿极不协调极为难看。我疑惑他砍树做什么,他说是要修造行宫,修造气派的帝城双凤阙。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确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楼宇,不过那制式,说起来到底是像凤翼还是蚊翅?
谷川先生说话间,眼睛突然有了神采,几乎是一百八十度扭过头去,接着身体开始触了电般的发颤。他这时已经不那么肥胖,呆滞一秒就矫健的跑走了,留我在树荫下不明所以。崎岖的山路即便小心走也不免磕绊,更何况他这样像见了骨头的狗一样心无旁骛的跑,他几乎是连滚带爬。
我和工人看见谷川先生邀功般拜倒在帝城双凤阙的高门前,迎接慢慢从里走出来的女性。谷川先生摇头晃脑给自己颈上锁上项圈,伏在女性身前乞求女性牵住缰绳。女性没有理会呈上的缰绳,而是顺势坐到谷川先生的脊上,圆润紧翘的臀压的谷川先生又矮一截。女性夹了一根细雪茄,袅袅的仙烟就从女性色若丹虹的唇里吐出来。臀下的谷川先生尽力吸了这香气,浑身的毛细血管便扩张许多,心脏泵血也比以往更孔武有力。
山伐空了,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的想还是能发现好处。至少随意丢弃的雪茄,即便没有谷川先生用湿润的舌头去舔舐,也点燃不起森林大火。
我最后见谷川先生,他跪在原先是他的别墅花园的泥土里,颤颤巍巍的拿着把小手镰割草。太阳毒的把空气烤出摩尔纹,现在他身上早没有一点油脂可以渗出来。他为什么除草不用除草机,后来我知道是他怕割草机动静太大吵扰女性的午后闲愉。他跟我解释说,他是在减肥,减他黑瘦结实臂膀上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的脂肪,减他满是鞭痕屁股上我看来看去也看不见的赘肉。他劳作时还戴着一副厚厚的皮手套,我劝他这么燥热的天气不如摘下来,他躲躲闪闪没有回应。后来我知道他的掌心早被女性的尖锐鞋跟刺透,手掌现在还裹着纱布,里头的烂肉生了蛆结了痂和纱布长在一起再也揭不下来,所以要戴一副皮手套掩人耳目。
忽而我听见别墅内甩鞭声,谷川先生便如遭了鞭子一样身体痉挛抽缩一下,本就黑瘦干瘪的身体又小一圈像个侏儒。谷川先生听见鞭声,即顾不得手镰的刀刃锋利割伤哪里,双膝猛一扣地跃起来往别墅居住区蛙跳袭去,隔三五米跳跃间隔留地上些碎骨碴子,应该是衣着单薄,着地没有缓冲,而身体内血也早流干的缘故。
不多时,便见枯干的谷川先生费力的拖着一辆洋车出来。洋车高高的轮子碾死侏儒的谷川先生像碾死一只搬家的蚂蚁一样轻松。洋车上有华盖遮阳,让人偷窥不了艳彩华盖里面是怎么样的曼妙无穷。华盖的豁口,伸出女性那犹如婴儿脸颊般细腻柔软的足。吻住女性柔软的足底的,是一双华丽的鞋子,鞋跟是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车出来的。而吻住华丽鞋子的鞋底的,才轮到谷川先生的脊背。谷川先生的脊背上有个不知什么时候剜的洞,直通到脊骨上一个不知什么时候钻的窝。华丽鞋子的鞋跟恰巧被洞窝包裹起来,谷川先生身上大部分的神经已经坏死,但是脊骨里这条还完好,是为便于女性用鞋跟控制洋车行进的速度方向。女性足底稍一用力,谷川先生就痛苦地龇唇咧嘴————谷川先生的牙因为在舔舐女性的皮鞋时不慎留了印而被赏赐自行敲去。
洋车最后稳稳当当停在花园的一片月季前,谷川先生早就轻车熟路,一路没有丝毫颠簸。华盖终于徐徐打开,华丽的鞋子从谷川先生的脊背上取下,在空中划道优雅的曲线,准确无误的踏在柔软的皮手套上,金属鞋跟也默契的钻透掌心。女性不知随口命令了什么,谷川先生的头就向泥土里蛹去。因为没有牙,谷川先生只能用舌头嘴唇一点点磨断月季的根茎,然后含着月季根茎极力向上托举呈递。女性取起花来,微笑着把有刺的部位插进谷川先生的呼吸道,只摘一片花瓣嗅嗅。
女性松开手,花瓣便随着和风辗转,飞到渺远的河里,孑孓们一拥而上享受了养分。
河不是干了吗?原来干了一条河,还有一万条河,空了一座山,还有一万座山。蚊子就在这大自然的酷暑里愈衍愈烈,永不禁绝。
我终于看清蚊子,这就是那个总在华盖里,吸干谷川先生,几乎等同于“恶”的女性。
写的真好
q老师,怎么写得这么短啊(爆哭)
吊,文学的
outsider123:↑吊,文学的谢谢你❤️
慕名前来,果真是文学性很强的佳作,不知道镜像还沉落了多少这样我没发现的宝藏…
(虽然挖坟不太好,且自己的评论过于干瘪实在惭愧,但总之想表达一下对这篇作品的喜爱)
(虽然挖坟不太好,且自己的评论过于干瘪实在惭愧,但总之想表达一下对这篇作品的喜爱)
写得太棒了,个人偏爱这样内敛克制却又富含情感的文字。我实在是不够幸运,时隔一年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