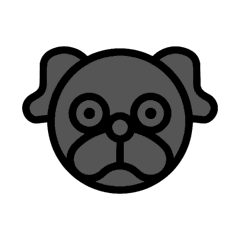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日文翻译/昭和文學】《騎人賽馬》(沼正三)——兒時的玩伴成為殘酷的女主人
短篇翻译大小姐羞辱公开调教媚外
第七章 騎人賽馬
沼 正三
《ある夢想家の手帖から》昭和45年
——阿爾伯特·莫爾『性科學大系』
前章有提到,比起四肢型,雙足型的騎乘方式對騎手來說快感程度會高出許多。這是因為比起馬的型態,其機能更加影響騎手的體驗。
不過,雙足型也有不足之處,首先就是重心過度上移導致容易傾倒。前章所描寫的當騎手還是兒童時尚可稱為舒適的乘用畜的情況,在騎手成長為成熟的女體之後便不再稱心,甚至伴隨著危險。對於馬的機能,也就是速度的過分追求,導致人們忘記了四肢型的騎馬型態帶來的安全性。
從而一種兼顧雙足型的速度和四肢型的安全的嘗試應運而生。就像二人組合成的舞台上的馬,三人組合成騎馬戰的馬一樣,複數組合雖然是一種解決方法,但是單人的場合下雙手是沒有任何支撐的。為了維持移動性,車輪是必要的。由此,四肢型和雙足型的綜合型態「輔助輪型」誕生了。型態上也像一匹馬,為了提升騎手的愉悅感和安全性,同時追求真實的馬的速度的產物,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騎人馬經由四肢型-雙足型-輔助車型發展的極致。因此,這也是比起雙足型更像是專為騎手而存在的人馬,從精神上的隸屬轉變為了階級層面的隸屬。
這種型態的馬的話,已經可以滿足成年女性安全的快速騎行的需求(附記第二)。前章已介紹過一種模擬賽馬的場景,在此再介紹一篇包含輔助輪型人馬的賽馬場面(附記第三)的小說,奴隸小說作家高特(Gothe)的長篇『揮鞭的女性們』(Die Geisslerinnen)。身為匈牙利貴族(由於皮膚並不白而被當作與黑人混血的後代)的馬扎爾青年被女性欺負並被當作奴隸賣掉,並不斷在不同女主人之間轉手變賣的殖民地小說,七位登場的女性都在草蛇灰線的複雜劇情中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和成長。
小說故事發生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匈牙利外交官的兒子米可洛斯時年八歲,正和同齡的小朋友安德烈玩母鹿遊戲(一個人騎跨在另一個人的背上伸出手指說「母鹿母鹿有幾支角」的猜數字遊戲)。安德烈十六歲的姐姐伊蓮娜走了過來,對正扮成馬趴在地上的米可洛斯說「張嘴,這是你小子(お前)(附記第四*)最愛吃的東西唷」,同時不由分說地把一根糖果棒捅進他的嘴裡。在米可洛斯愕然之際,伊蓮娜趁機把安德烈推下來自己騎了上去,把小米可洛斯重重地坐壓在了地上⋯⋯這一橋段與之後的章節產生的深刻的對比。
一轉眼過了二十年,命運讓米可洛斯成了佛羅里達農場的一個農奴(農場主的夫人是他過去曾輕浮過又甩掉的一名女僕,但我們還是省略這部分故事吧)。一位古巴來的客人吉爾斯老爺,看上了拖著挽奴馬車出來迎客的奴隸哈桑,接受了農場主的贈與而把他帶回了家。這個農奴就是米可洛斯,但是甘蔗場的農場主卻沒有安排他幹農活,而是讓他脫光了衣服,把雙手銬在三輪車上,背上放一個馬鞍,嘴裡叼上馬轡被當成了一匹馬來養。當一名十一二歲的美少年騎過他之後,他身上的馬具被摘掉,但還是銬在三輪車上被拖進馬廄裡,讓馬夫去照顧他。——美少年是老爺的兒子,也許是對這個人馬玩具的安排確實感到滿意吧。
就在一週後,事情就逐漸明朗了。在古巴的島嶼聖地亞哥附近,作為年度祭典的餘興節目,農場主夫人和小姐們會作為騎手,以黑人奴隸作為人馬去參加賽馬活動。吉爾斯的夫人海倫娜眼下正在拜訪她弟弟的旅途中,去年參賽的成績是令人惋惜的第二名。為此吉爾斯為了愛妻努力搜羅跑得快的奴隸。通常來說為了比賽需要經常從小屋裡把奴隸拉出來訓練,但母親臨時不在,作為代替,調教奴隸的工作就由安東尼少爺接手了。直到賽馬出場那天前,奴隸都要過著和馬一樣的生活,以便讓他產生更多像馬的感覺。米可洛斯駝著少年騎手每天早晚在馬場裡來回奔走。偶爾他會產生一種少年的樣貌和聲音與某位故人相像的錯覺,但是鞭子和馬刺不會給他沈浸在回憶裡的餘裕。艱苦的猛訓持續了三個月,米可洛斯在馬草中起居,完全適應了馬一般的生活。
但是在艱苦的生活也伴隨著小小的幸福。首先是得以從農場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在騎乘結束後,平時嚴禁偷拿的甘蔗也會作為被騎乘一天的辛苦的獎勵。(甘蔗是一種咀嚼它的莖之後吮吸汁水的食物。書上記載的做法是主人握住甘蔗的一端,把另一端伸給馬兒吃)
『那股甘甜味道,以及賞賜給他這種美味的飼主的溫柔,令他淪陷沈迷,以至於開始渴望被騎乘了。不過這種對待方式好似並非把他當作奴隸,而是作為乘用畜(馬)來對待,也讓他稍微有些困擾。不過這兩種狀態對他而言,好像也沒有什麼區別?』
就這樣漸漸地,米可洛斯通過甘蔗理解到飼育者的溫情,慢慢地徹底轉變為像馬一樣的心境。
(這一點讓我聯想起乘杉女士對胡蘿蔔的作用的闡釋)
在日子臨近祭典的某一天,少年如往常般在馬場來回騎乘時,一位婦人走了過來。「媽媽!」少年騎在馬背上大喊著,和母親緊緊抱在一起。米可洛斯由此得知真正的女騎手海倫娜已經回來了。兩人的對話中提到了「安德烈叔父」,這讓米可洛斯感到十分震驚。突然,少年為了向母親展示自己調教的成果,一鞭子把米可洛斯打回了現實,他不得不繼續奔走起來。大汗淋灕地回到馬廄時,婦人已經等在馬廄門檻,正在用甘蔗的莖把靴底的泥(Kot,指馬廄前沾著馬糞的泥土,也被稱為Mist,在此姑且譯作泥)蹭乾淨,然後指示馬夫把他口裡啣著的馬轡取下來。
『農場主夫人把棒(指甘蔗的莖,為了與前文照應)握好,「張嘴,這是你小子(お前(附記第四**)最愛吃的東西唷」一邊說著,把沾滿污穢的那端不由分說地捅進他嘴裡。聽到這句話的瞬間,他終於回想起至今以來少年的聲音讓他朦朧回憶起的過去,理解了事態的發展。在他面前站著的婦人,用審視家畜的目光熟練地檢查著自己——完全把他當作自己的坐騎一般——用手輕輕撫過他的身體。這位女飼主正是兒時的夥伴安德烈的姐姐無疑。二十年前,幾乎一樣的場景裡,喂給他吃糖果棒的那位令人懷念的姐姐伊蓮娜(用西班牙轉寫即是海倫娜)就是她!米可洛斯此時深深體會到命運嗜虐的惡意玩笑』
伊蓮娜當初亡命逃往西印度,與西班牙人吉爾斯結了婚。她當然沒有認出哈桑就是米可洛斯。唯一的區別是,之前她是代替弟弟騎在他的背上,今天則是代替自己的兒子騎在他背上。
『把腳踩在鐙上,新的女主人輕巧地跨上馬鞍。三十(餘歲)的女性豐滿的120斤體重,把他的背脊壓得彎了下去。』
如夢方醒的米可洛斯來不及心神恍惚,這位女騎手的體重已將他重重壓垮,在隨後的猛烈鞭笞下魂飛魄散。殘酷的訓練持續了好幾天,終於到了上賽場的日子。大決戰的最後一個項目——
『和頭馬只差半個馬身。在猛烈的鞭打下他的屁股已經皮開肉綻,他也拚上了不要命的力氣去追逐。在三個月的訓練中他常常感到背上騎手的體重負擔,但此刻他已經感覺不到站立著踩在馬蹬之上的人的重量。他完全陷入了一種只有賽馬體會過的狀態,一種只有奪取首位的狂熱激情。⋯⋯』
在越過終點線後,用盡了全身力氣的他被海倫娜騎著壓在了地上(此處照應了二十年前的橋段),以手腕被手銬傷到骨折為代價,成功取得第一名。雖然優勝的名譽和獎金都歸於女騎手,他也彷彿忘記了受傷的痛苦,品嘗到了作為一匹賽馬的喜悅⋯⋯。那天夜裡,海倫娜寫信向弟弟傳達了自己取得優勝的故事,在信中感嘆彼此命途多舛的苦難坎坷,還回想起了自己輕鬆快樂的少女時代,以及和弟弟那位名叫米可洛斯的朋友一起遊玩打鬧的可愛時光。與此同時,那位米可洛斯正因高燒而臥病在床。安德烈少年來慰問模擬馬哈桑時,把甘蔗塞到他嘴裡讓他啣著。
『眼前年幼小主人的身形恍若昔日的友人,在意識朦朧中嘴裡的甘蔗彷彿嚐出了那些甜蜜的舊日回憶。⋯⋯』
這之後米可洛斯繼續被頑劣的命運所捉弄,他在馬戲團裡扮演假熊,穿著熊皮被馴獸師薩拉調教。那個薩拉實際上是蘇丹的女兒扎拉德,後來米可洛斯在後宮犯了事情被判處死刑時還救了他,並把他變成了一個太監。具體情節本章暫且按下不表。
上一章節提到的賽人馬是基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現實生活,貴族家庭裡確實有可能會發生的故事。與之相反,本章所提到的,公開賽馬也好,女騎手的騎乘也好,都是針對M向讀者的故事而顯得不真實。不過,後半段所記述的輓奴車其實在歷史中真實存在過,以如今的常識對法蘭西革命時期的西印度殖民地風俗妄下論斷也是輕率的。(不過,對於在馬廄裡飼育三個月之類的描寫,應該還是看作對M向讀者的福利情節比較妥當。)(附記第五)
不過,不論那是實際的風俗也好,虛構也罷,這樣徹底的人馬飼育調教深得我心。只為騎手服務而存在的人馬,即作為更接近理想中的人馬,只為讓騎手享受到與騎真馬相同的快感和安全感。這種輔助車型馬存在的意義,在這場競速比賽的描寫中一覽無餘。
附記第一
正如前章附記第二記述,作為制度化訓練的例證,雙足型人馬的負重能力可以通過訓練提升無庸置疑。白人的體格和臂力並非我等孱弱的日本人可以比擬(據我所知能夠輕鬆地抱起新娘子的日本男性少之又少,但在白人男性中並不稀奇)。R·Hegemann所繪『阿根廷的女騎手』也可能不全是基於空想,只是我還是認為輔助車型的人馬更為安全。可參照『手帖』續篇第一百一十二章附記第一。(譯注:及至譯畢,手帖之插畫更新未及該章,望見諒。剩餘圖片請參考譯後記。)
附記第二
關於輔助車型人馬,馬場喬次氏曾在其作品『女性乘馬考』(《奇譚俱樂部》昭和三一年四月號)提出了疑問「黛安娜夫人騎人馬的想法雖然聽起來不錯,但當我實際嘗試時發現,不論怎樣做背部都會大幅弓起,至少我是做不了這個動作」。我自己用玩具三輪車實驗了一下才知道,這樣的姿勢很難長時間保持。在女性體重的壓力下,比起大腿,手腕和身體(背脊)會先到極限。但是前述關於雙足型的經驗在這裡應該也是適用的,也就是說只要進行合理的訓練,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到。Krafft-Ebing(譯注:奧地利性學家)在古典的馬化症病例中記載,用椅子支撐雙手的姿勢(與輔助車型相同)時,若是一位體重在六十至八十千克穿著騎馬服的女性跨騎在上面,以馴真馬時一樣的方式進行訓練,而男案主在下面模擬馬的動作的話,可以堅持三十到四十五分鐘。在那期間,女騎手對其不斷地抽打,用馬刺去踢,伴隨著訓斥和愛撫,完全把他當作一匹馬來對待。在結束後只要休息十五分鐘,相同的女性騎乘還能重複三四回。對於男案主而言,這已經完全成為了性交的替代品(而非前戲),並且完全是通過訓練實現到這種程度。他還口述過在夜裡也會夢見自己變成一匹馬被美女騎乘。(參考附錄C第二篇)(譯注:即「人耶馬耶」《奇譚俱樂部》昭和二九年二月號)
追記
看了《奇譚俱樂部》昭和三四年二月號馬場好男氏的文章(譯注:即『致「馬化白皮書」的作者』),我本人是有過幾次誘導女性騎在我背上的經驗——我雖是忠實的犬派,但讀過本手帖諸章的各位也應感受到我對於騎人馬也有充分的熱情——前述的馬化症案主的體驗也在我的好球區之內。參考『努力創造出女性無所顧忌地用屁股坐在我背上的機會。這時只要讓女性感覺舒適的話,在下次同樣的場合,女性就會自然地提出「那個,能不能讓我騎騎看(Komm', lass
mich ein bischen reiten!)」之類的要求。』雖說西歐有坐椅子的習慣(譯注:區別於日本跽坐於地),更容易創造出這樣的機會,但本質上還是女性思想解放程度的問題。今後我們國家也該慢慢變得更加開放才是。
附記第三
既然是作為人和車的結合體,若是重視車的部分,就是在模仿腳踏車,那便不是賽馬而是賽車了。福克斯採集的M向繪畫(參考插圖)雖說描繪了典型的輔助車型騎人賽馬的場面,題目卻叫作『活的腳踏車』。從那男的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來他大抵是一個法國的受虐狂(譯注:?)。
附記第四
標注了星號的地方原文皆是dein→du——德語裡對小孩,奴隸和家畜的第二人稱都為du。雖說在日語中對他家小孩稱呼為「你(あなた)」較為合適,但由於正是前後伊蓮娜的稱呼一致導致米可洛斯的記憶復甦,我把兩處都譯作你小子「お前」。此外,日語第二人稱問題和法語的tu(對應前面的du)相關的話題,在附錄A的第三篇裡都有詳細討論。
附記第五
Don·Brennus·Aléra所著『奴隸祭』(許多人誤將本書與某戰前發行的單行本混為一談)中,提及女奴輓畜、女奴賽馬(把號碼牌的別針直接別在肩肉上)等狀況,甚至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女奴。雖說並非M向,只是聯想到了姑且寫上。
附記第六
騎人賽馬的理想型態應當是輔助車型才對。但是從這點出發,會發現許多這類賽馬作品都很令人遺憾地採用了四肢型。騎人賽馬得以成立的基礎就在於對人馬人權的無視,可是四肢型騎乘過分強調一對一的精神隸屬的關係,會產生一種本不該有的對賽馬的親近感。針對這點,偏好騎乘輔助車型人馬的乘杉女士提出了一個天才的構想:犯罪預防賽馬,通過把人馬用手銬鎖在橡膠車輪上進行。犯下重罪的人會被剝奪人權集中起來,作為美女的馬進行比賽,優勝的騎手獲得賞金,馬也會得到減刑。
譯後記
若你閱讀後甚至閱讀中就(與我同樣)去檢索了那本所謂『揮鞭的女性們』(Die Geisslerinnen),祝你好運。
事實上基於馬仙人部落格裡的考證,該長篇小說的存在也許只是沼正三氏的一個小玩笑。
http://equus.la.coocan.jp/bk_techo_7.htm。另,本文提及圖片亦可在該連結找到。
沼 正三
《ある夢想家の手帖から》昭和45年
譯者的話> 以奴隸故事的形式創作的作品有許多。有基於羅馬時代抑或是美國南部的奴隸生活,對於殘酷女主人慾望的描寫不勝枚舉,命令奴隸下跪吻腳之類的事情比比皆是。在這之中我比較推崇高特的小說。
如您所見,此文為沼 正三先生偉大文集《ある夢想家の手帖から》中的一枚遺珠。手帖本身各章孤篇成文,整部翻譯遙不可期,便私心遴選個別篇目與諸君共賞。
——阿爾伯特·莫爾『性科學大系』
前章有提到,比起四肢型,雙足型的騎乘方式對騎手來說快感程度會高出許多。這是因為比起馬的型態,其機能更加影響騎手的體驗。
不過,雙足型也有不足之處,首先就是重心過度上移導致容易傾倒。前章所描寫的當騎手還是兒童時尚可稱為舒適的乘用畜的情況,在騎手成長為成熟的女體之後便不再稱心,甚至伴隨著危險。對於馬的機能,也就是速度的過分追求,導致人們忘記了四肢型的騎馬型態帶來的安全性。
從而一種兼顧雙足型的速度和四肢型的安全的嘗試應運而生。就像二人組合成的舞台上的馬,三人組合成騎馬戰的馬一樣,複數組合雖然是一種解決方法,但是單人的場合下雙手是沒有任何支撐的。為了維持移動性,車輪是必要的。由此,四肢型和雙足型的綜合型態「輔助輪型」誕生了。型態上也像一匹馬,為了提升騎手的愉悅感和安全性,同時追求真實的馬的速度的產物,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騎人馬經由四肢型-雙足型-輔助車型發展的極致。因此,這也是比起雙足型更像是專為騎手而存在的人馬,從精神上的隸屬轉變為了階級層面的隸屬。
這種型態的馬的話,已經可以滿足成年女性安全的快速騎行的需求(附記第二)。前章已介紹過一種模擬賽馬的場景,在此再介紹一篇包含輔助輪型人馬的賽馬場面(附記第三)的小說,奴隸小說作家高特(Gothe)的長篇『揮鞭的女性們』(Die Geisslerinnen)。身為匈牙利貴族(由於皮膚並不白而被當作與黑人混血的後代)的馬扎爾青年被女性欺負並被當作奴隸賣掉,並不斷在不同女主人之間轉手變賣的殖民地小說,七位登場的女性都在草蛇灰線的複雜劇情中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和成長。
小說故事發生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匈牙利外交官的兒子米可洛斯時年八歲,正和同齡的小朋友安德烈玩母鹿遊戲(一個人騎跨在另一個人的背上伸出手指說「母鹿母鹿有幾支角」的猜數字遊戲)。安德烈十六歲的姐姐伊蓮娜走了過來,對正扮成馬趴在地上的米可洛斯說「張嘴,這是你小子(お前)(附記第四*)最愛吃的東西唷」,同時不由分說地把一根糖果棒捅進他的嘴裡。在米可洛斯愕然之際,伊蓮娜趁機把安德烈推下來自己騎了上去,把小米可洛斯重重地坐壓在了地上⋯⋯這一橋段與之後的章節產生的深刻的對比。
一轉眼過了二十年,命運讓米可洛斯成了佛羅里達農場的一個農奴(農場主的夫人是他過去曾輕浮過又甩掉的一名女僕,但我們還是省略這部分故事吧)。一位古巴來的客人吉爾斯老爺,看上了拖著挽奴馬車出來迎客的奴隸哈桑,接受了農場主的贈與而把他帶回了家。這個農奴就是米可洛斯,但是甘蔗場的農場主卻沒有安排他幹農活,而是讓他脫光了衣服,把雙手銬在三輪車上,背上放一個馬鞍,嘴裡叼上馬轡被當成了一匹馬來養。當一名十一二歲的美少年騎過他之後,他身上的馬具被摘掉,但還是銬在三輪車上被拖進馬廄裡,讓馬夫去照顧他。——美少年是老爺的兒子,也許是對這個人馬玩具的安排確實感到滿意吧。
就在一週後,事情就逐漸明朗了。在古巴的島嶼聖地亞哥附近,作為年度祭典的餘興節目,農場主夫人和小姐們會作為騎手,以黑人奴隸作為人馬去參加賽馬活動。吉爾斯的夫人海倫娜眼下正在拜訪她弟弟的旅途中,去年參賽的成績是令人惋惜的第二名。為此吉爾斯為了愛妻努力搜羅跑得快的奴隸。通常來說為了比賽需要經常從小屋裡把奴隸拉出來訓練,但母親臨時不在,作為代替,調教奴隸的工作就由安東尼少爺接手了。直到賽馬出場那天前,奴隸都要過著和馬一樣的生活,以便讓他產生更多像馬的感覺。米可洛斯駝著少年騎手每天早晚在馬場裡來回奔走。偶爾他會產生一種少年的樣貌和聲音與某位故人相像的錯覺,但是鞭子和馬刺不會給他沈浸在回憶裡的餘裕。艱苦的猛訓持續了三個月,米可洛斯在馬草中起居,完全適應了馬一般的生活。
但是在艱苦的生活也伴隨著小小的幸福。首先是得以從農場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在騎乘結束後,平時嚴禁偷拿的甘蔗也會作為被騎乘一天的辛苦的獎勵。(甘蔗是一種咀嚼它的莖之後吮吸汁水的食物。書上記載的做法是主人握住甘蔗的一端,把另一端伸給馬兒吃)
『那股甘甜味道,以及賞賜給他這種美味的飼主的溫柔,令他淪陷沈迷,以至於開始渴望被騎乘了。不過這種對待方式好似並非把他當作奴隸,而是作為乘用畜(馬)來對待,也讓他稍微有些困擾。不過這兩種狀態對他而言,好像也沒有什麼區別?』
就這樣漸漸地,米可洛斯通過甘蔗理解到飼育者的溫情,慢慢地徹底轉變為像馬一樣的心境。
(這一點讓我聯想起乘杉女士對胡蘿蔔的作用的闡釋)
在日子臨近祭典的某一天,少年如往常般在馬場來回騎乘時,一位婦人走了過來。「媽媽!」少年騎在馬背上大喊著,和母親緊緊抱在一起。米可洛斯由此得知真正的女騎手海倫娜已經回來了。兩人的對話中提到了「安德烈叔父」,這讓米可洛斯感到十分震驚。突然,少年為了向母親展示自己調教的成果,一鞭子把米可洛斯打回了現實,他不得不繼續奔走起來。大汗淋灕地回到馬廄時,婦人已經等在馬廄門檻,正在用甘蔗的莖把靴底的泥(Kot,指馬廄前沾著馬糞的泥土,也被稱為Mist,在此姑且譯作泥)蹭乾淨,然後指示馬夫把他口裡啣著的馬轡取下來。
『農場主夫人把棒(指甘蔗的莖,為了與前文照應)握好,「張嘴,這是你小子(お前(附記第四**)最愛吃的東西唷」一邊說著,把沾滿污穢的那端不由分說地捅進他嘴裡。聽到這句話的瞬間,他終於回想起至今以來少年的聲音讓他朦朧回憶起的過去,理解了事態的發展。在他面前站著的婦人,用審視家畜的目光熟練地檢查著自己——完全把他當作自己的坐騎一般——用手輕輕撫過他的身體。這位女飼主正是兒時的夥伴安德烈的姐姐無疑。二十年前,幾乎一樣的場景裡,喂給他吃糖果棒的那位令人懷念的姐姐伊蓮娜(用西班牙轉寫即是海倫娜)就是她!米可洛斯此時深深體會到命運嗜虐的惡意玩笑』
伊蓮娜當初亡命逃往西印度,與西班牙人吉爾斯結了婚。她當然沒有認出哈桑就是米可洛斯。唯一的區別是,之前她是代替弟弟騎在他的背上,今天則是代替自己的兒子騎在他背上。
『把腳踩在鐙上,新的女主人輕巧地跨上馬鞍。三十(餘歲)的女性豐滿的120斤體重,把他的背脊壓得彎了下去。』
如夢方醒的米可洛斯來不及心神恍惚,這位女騎手的體重已將他重重壓垮,在隨後的猛烈鞭笞下魂飛魄散。殘酷的訓練持續了好幾天,終於到了上賽場的日子。大決戰的最後一個項目——
『和頭馬只差半個馬身。在猛烈的鞭打下他的屁股已經皮開肉綻,他也拚上了不要命的力氣去追逐。在三個月的訓練中他常常感到背上騎手的體重負擔,但此刻他已經感覺不到站立著踩在馬蹬之上的人的重量。他完全陷入了一種只有賽馬體會過的狀態,一種只有奪取首位的狂熱激情。⋯⋯』
在越過終點線後,用盡了全身力氣的他被海倫娜騎著壓在了地上(此處照應了二十年前的橋段),以手腕被手銬傷到骨折為代價,成功取得第一名。雖然優勝的名譽和獎金都歸於女騎手,他也彷彿忘記了受傷的痛苦,品嘗到了作為一匹賽馬的喜悅⋯⋯。那天夜裡,海倫娜寫信向弟弟傳達了自己取得優勝的故事,在信中感嘆彼此命途多舛的苦難坎坷,還回想起了自己輕鬆快樂的少女時代,以及和弟弟那位名叫米可洛斯的朋友一起遊玩打鬧的可愛時光。與此同時,那位米可洛斯正因高燒而臥病在床。安德烈少年來慰問模擬馬哈桑時,把甘蔗塞到他嘴裡讓他啣著。
『眼前年幼小主人的身形恍若昔日的友人,在意識朦朧中嘴裡的甘蔗彷彿嚐出了那些甜蜜的舊日回憶。⋯⋯』
這之後米可洛斯繼續被頑劣的命運所捉弄,他在馬戲團裡扮演假熊,穿著熊皮被馴獸師薩拉調教。那個薩拉實際上是蘇丹的女兒扎拉德,後來米可洛斯在後宮犯了事情被判處死刑時還救了他,並把他變成了一個太監。具體情節本章暫且按下不表。
上一章節提到的賽人馬是基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現實生活,貴族家庭裡確實有可能會發生的故事。與之相反,本章所提到的,公開賽馬也好,女騎手的騎乘也好,都是針對M向讀者的故事而顯得不真實。不過,後半段所記述的輓奴車其實在歷史中真實存在過,以如今的常識對法蘭西革命時期的西印度殖民地風俗妄下論斷也是輕率的。(不過,對於在馬廄裡飼育三個月之類的描寫,應該還是看作對M向讀者的福利情節比較妥當。)(附記第五)
不過,不論那是實際的風俗也好,虛構也罷,這樣徹底的人馬飼育調教深得我心。只為騎手服務而存在的人馬,即作為更接近理想中的人馬,只為讓騎手享受到與騎真馬相同的快感和安全感。這種輔助車型馬存在的意義,在這場競速比賽的描寫中一覽無餘。
附記第一
正如前章附記第二記述,作為制度化訓練的例證,雙足型人馬的負重能力可以通過訓練提升無庸置疑。白人的體格和臂力並非我等孱弱的日本人可以比擬(據我所知能夠輕鬆地抱起新娘子的日本男性少之又少,但在白人男性中並不稀奇)。R·Hegemann所繪『阿根廷的女騎手』也可能不全是基於空想,只是我還是認為輔助車型的人馬更為安全。可參照『手帖』續篇第一百一十二章附記第一。(譯注:及至譯畢,手帖之插畫更新未及該章,望見諒。剩餘圖片請參考譯後記。)
附記第二
關於輔助車型人馬,馬場喬次氏曾在其作品『女性乘馬考』(《奇譚俱樂部》昭和三一年四月號)提出了疑問「黛安娜夫人騎人馬的想法雖然聽起來不錯,但當我實際嘗試時發現,不論怎樣做背部都會大幅弓起,至少我是做不了這個動作」。我自己用玩具三輪車實驗了一下才知道,這樣的姿勢很難長時間保持。在女性體重的壓力下,比起大腿,手腕和身體(背脊)會先到極限。但是前述關於雙足型的經驗在這裡應該也是適用的,也就是說只要進行合理的訓練,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到。Krafft-Ebing(譯注:奧地利性學家)在古典的馬化症病例中記載,用椅子支撐雙手的姿勢(與輔助車型相同)時,若是一位體重在六十至八十千克穿著騎馬服的女性跨騎在上面,以馴真馬時一樣的方式進行訓練,而男案主在下面模擬馬的動作的話,可以堅持三十到四十五分鐘。在那期間,女騎手對其不斷地抽打,用馬刺去踢,伴隨著訓斥和愛撫,完全把他當作一匹馬來對待。在結束後只要休息十五分鐘,相同的女性騎乘還能重複三四回。對於男案主而言,這已經完全成為了性交的替代品(而非前戲),並且完全是通過訓練實現到這種程度。他還口述過在夜裡也會夢見自己變成一匹馬被美女騎乘。(參考附錄C第二篇)(譯注:即「人耶馬耶」《奇譚俱樂部》昭和二九年二月號)
追記
看了《奇譚俱樂部》昭和三四年二月號馬場好男氏的文章(譯注:即『致「馬化白皮書」的作者』),我本人是有過幾次誘導女性騎在我背上的經驗——我雖是忠實的犬派,但讀過本手帖諸章的各位也應感受到我對於騎人馬也有充分的熱情——前述的馬化症案主的體驗也在我的好球區之內。參考『努力創造出女性無所顧忌地用屁股坐在我背上的機會。這時只要讓女性感覺舒適的話,在下次同樣的場合,女性就會自然地提出「那個,能不能讓我騎騎看(Komm', lass
mich ein bischen reiten!)」之類的要求。』雖說西歐有坐椅子的習慣(譯注:區別於日本跽坐於地),更容易創造出這樣的機會,但本質上還是女性思想解放程度的問題。今後我們國家也該慢慢變得更加開放才是。
附記第三
既然是作為人和車的結合體,若是重視車的部分,就是在模仿腳踏車,那便不是賽馬而是賽車了。福克斯採集的M向繪畫(參考插圖)雖說描繪了典型的輔助車型騎人賽馬的場面,題目卻叫作『活的腳踏車』。從那男的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來他大抵是一個法國的受虐狂(譯注:?)。
附記第四
標注了星號的地方原文皆是dein→du——德語裡對小孩,奴隸和家畜的第二人稱都為du。雖說在日語中對他家小孩稱呼為「你(あなた)」較為合適,但由於正是前後伊蓮娜的稱呼一致導致米可洛斯的記憶復甦,我把兩處都譯作你小子「お前」。此外,日語第二人稱問題和法語的tu(對應前面的du)相關的話題,在附錄A的第三篇裡都有詳細討論。
附記第五
Don·Brennus·Aléra所著『奴隸祭』(許多人誤將本書與某戰前發行的單行本混為一談)中,提及女奴輓畜、女奴賽馬(把號碼牌的別針直接別在肩肉上)等狀況,甚至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女奴。雖說並非M向,只是聯想到了姑且寫上。
附記第六
騎人賽馬的理想型態應當是輔助車型才對。但是從這點出發,會發現許多這類賽馬作品都很令人遺憾地採用了四肢型。騎人賽馬得以成立的基礎就在於對人馬人權的無視,可是四肢型騎乘過分強調一對一的精神隸屬的關係,會產生一種本不該有的對賽馬的親近感。針對這點,偏好騎乘輔助車型人馬的乘杉女士提出了一個天才的構想:犯罪預防賽馬,通過把人馬用手銬鎖在橡膠車輪上進行。犯下重罪的人會被剝奪人權集中起來,作為美女的馬進行比賽,優勝的騎手獲得賞金,馬也會得到減刑。
譯後記
若你閱讀後甚至閱讀中就(與我同樣)去檢索了那本所謂『揮鞭的女性們』(Die Geisslerinnen),祝你好運。
事實上基於馬仙人部落格裡的考證,該長篇小說的存在也許只是沼正三氏的一個小玩笑。
http://equus.la.coocan.jp/bk_techo_7.htm。另,本文提及圖片亦可在該連結找到。
往期作品
【日文翻译/昭和文學】《牛奶沐浴之饗宴》——可愛大小姐的養成和她的肥料們的故事 https://mirror.chromaso.net/thread/51633
【日文翻译/昭和文學】《夫人的嘔吐物》——美貌少夫人和啜飲她的嘔吐物的祖父 https://mirror.chromaso.net/thread/1073747841
不愧是沼正三,再次感谢楼主的翻译,让大小姐同好兴高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