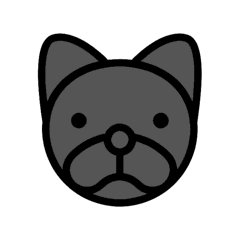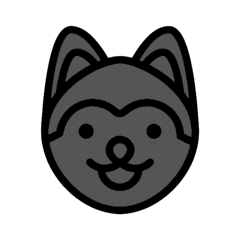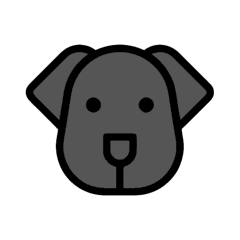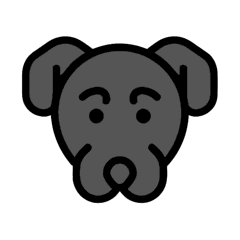姐姐的爱
长靴舔鞋连载中踩踏高跟鞋原创现实阶级职场大小姐鞋靴纯爱异世界纪实御姐
前面的朋友,我本来不想吵,但上面的话有点过分了。什么叫看不懂小说。要提建议就好好提,怎么还入脑了,开始攻击其他读者了,怎么低贱生物都来了。大家来看小说就是图个爽嘛,楼主倾情奉献,读者也乐意。尊卑不分这个帽子可太大了,张盟还是张雅婷表妹呢,她尊卑不分,那张雅婷喜欢李好算不算尊卑不分?张丽之前的感情,去找弟弟是不是尊卑不分?还是那句,这个楼是有标签的,纯爱标签还要不要,“姐姐的爱”要不要改成“小蓉蓉升职记”,怪不得之前能说出牢蓉虐杀张盟张雅婷这么离谱的话,确实教人大跌眼镜。我觉着吧,黑化大女主复仇实在太搞了,有一种女频的幽默。而且据我的观察,楼主的大纲应该不是这样。我就希望楼主勤更,好好按自己的想法写完,在这个基础上,书友的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坛友来看书就图个爽,不至于动这样的干戈,影响心情。之后再有这问题的争论我应该就不回复了。打扰到各位朋友和楼主抱歉了,最后祝大家假期快乐。
我现在也对姜蓉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主角的父母后期有没有戏份?按照主角的回忆,从背景故事来看,我认为这父母应该还是有戏份,毕竟他们如果失忆,然后恢复记忆的时候回来,会更有戏剧性。
讲道理,姜蓉这段应该算支线剧情,先写完主线剧情再去写姜蓉他们的支线会更好,我更好奇张斌要怎么与自己姐姐相遇。
讲道理,姜蓉这段应该算支线剧情,先写完主线剧情再去写姜蓉他们的支线会更好,我更好奇张斌要怎么与自己姐姐相遇。
as03:↑前面几个评论在说什么,明明都很正常,姜蓉女王登上市长位置,把之前知道她身处服侍组身份低微的人都处理掉,不是再正常不过了?戒严饿死的也都是普通市民,他们算什么东西?一群虫子也配和高贵的女生相比?还有说潘主任踩大衣的,那还需要理由吗?想踩就踩呗,对待低等的蝼蚁怎么做还需要理由?女性就是高贵,还有说女学生戾气大的?怎么看的文?杀的都是些普通群众,都是无权无势的人,随便杀随便玩,连给管理层当虫子的资格都没有,虐杀就是消遣玩乐的,上面几个评论看不懂文章别看了。姜蓉做的再正常不过了,到你们嘴里成了只会斗狠,你们在搞笑吗?张盟因为得到她母亲的电话知道李好和张丽有关系所以对李好也就是张斌照顾,但是对待男性这种恶心生物讨好真让我受不了,对待张斌这种男性给吃的特殊优待,但是对待姜蓉这样高贵的女性却没有照顾成分,必须要张盟这种尊卑不分付出代价。我支持姜蓉女王成为能和张丽一个地位的存在,按照姜蓉的市长治理应该马上可以获得晋升了,期待姜蓉的靴子标识早日升为金标识。顾沁瑶很棒,我也很喜欢,为姜蓉办事能跟着姜蓉晋升。是你看不懂还是我们看不懂啊,你懂不懂中文啊,懂不懂标签里纯爱是什么意思阿,看不懂中文滚出去啊。不懂中文滚出去别看。
oldguys:↑前面的朋友,我本来不想吵,但上面的话有点过分了。什么叫看不懂小说。要提建议就好好提,怎么还入脑了,开始攻击其他读者了,怎么低贱生物都来了。大家来看小说就是图个爽嘛,楼主倾情奉献,读者也乐意。尊卑不分这个帽子可太大了,张盟还是张雅婷表妹呢,她尊卑不分,那张雅婷喜欢李好算不算尊卑不分?张丽之前的感情,去找弟弟是不是尊卑不分?还是那句,这个楼是有标签的,纯爱标签还要不要,“姐姐的爱”要不要改成“小蓉蓉升职记”,怪不得之前能说出牢蓉虐杀张盟张雅婷这么离谱的话,确实教人大跌眼镜。我觉着吧,黑化大女主复仇实在太搞了,有一种女频的幽默。而且据我的观察,楼主的大纲应该不是这样。我就希望楼主勤更,好好按自己的想法写完,在这个基础上,书友的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坛友来看书就图个爽,不至于动这样的干戈,影响心情。之后再有这问题的争论我应该就不回复了。打扰到各位朋友和楼主抱歉了,最后祝大家假期快乐。连tag纯爱什么意思都不懂,讲道理我都不想攻击他的,既然他先攻击看不懂别看,那我就要反击了,真的让他看不懂中文滚出去别看好了。
作者写小说本来就是凭自己的爱好,又不是花钱定制小说,作者必须得按照谁的意思意思写,对情节有想法提自己想看啥很正常,但是在这吵架骂人然后说作者写的有问题真的大可不必,觉得作者写的和tag不一样不看就行了。本来在网站更新小说对作者来说就是个没钱还得付出大量时间的事情,因为剧情发展和自己设想的不一样就在这骂骂咧咧,除了让作者看得心烦不想写还有什么意义吗……
23562788811:↑作者写小说本来就是凭自己的爱好,又不是花钱定制小说,作者必须得按照谁的意思意思写,对情节有想法提自己想看啥很正常,但是在这吵架骂人然后说作者写的有问题真的大可不必,觉得作者写的和tag不一样不看就行了。本来在网站更新小说对作者来说就是个没钱还得付出大量时间的事情,因为剧情发展和自己设想的不一样就在这骂骂咧咧,除了让作者看得心烦不想写还有什么意义吗……确实我有问题,我的错。
哇,楼主在五一前就更新了我居然现在才看到,错过一个亿,快让姐姐出现一下吧,迫不及待啦
写的真好啊,加入一些重口啊,这种权利下的强迫行为肯定很带感~
希望作者大大不要受影响呀,每天都还在蹲更新!
神作者!超级好看!请不要恶意寸止啊~哈哈哈哈!爱信等。
这……小说要张弛有度,有女权必有革命。可以借鉴公主与奴隶,有爱,有虐,有反抗。
继续蹲作者大大的更新!
催更催更
几周了呜呜
在戒严令实施的第10天,许明一家的处境已经变得异常艰难。虽然他们在戒严前囤积了一些食物,但储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许明母亲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一碟鲜嫩的炒青菜,还有少许的红烧肉。这在当前的环境下,已经是极其丰盛的一餐了。她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送入口中,细细咀嚼着,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米饭的火候控制得不错,”她评价道,“下次可以多放点油,这样口感会更好。”
站在一旁的许明父亲立即点头应是:“遵命,下次我一定注意。”他的声音有些虚弱,脸颊已经明显凹陷,眼睛周围有着深深的黑圈,身体也比半个月前瘦了一大圈。
许明站在另一侧,同样的姿势服侍母亲用餐。他的情况比父亲好不了多少,原本结实的身材已经变得瘦削,脸色苍白,眼神中透露出疲惫。这已经是许明母亲今天的第三餐了。早餐是粥和咸鸭蛋,午餐是面条和一些蔬菜。而许明和父亲,按照她的规定,一天只能在晚上吃一顿饭,而且分量有限。这种安排是在戒严令实施的第六天开始的,当时许明母亲意识到食物储备可能撑不了太久。
“在这种特殊时期,我们必须合理分配资源,”她当时这样宣布,“作为这个家的主心骨,我必须保持充沛的精力,所以我的三餐不能减。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
这个决定对许明和父亲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女性的决定是绝对的,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的权利。
“米饭好像有点多,”许明母亲看着自己只吃了三分之二的米饭,摇了摇头,“下次少盛一点,浪费可耻。”说着,她用筷子拨弄了几下剩余的米饭,然后放下碗筷,示意自己用餐完毕。许明立即上前,将餐具收走。他的胃在看到那些剩余的食物时发出了痛苦的抗议,但他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即使是母亲吃剩的食物,也不是他能随意处置的。许明父亲迅速拿来一杯温水和一条湿毛巾,让妻子漱口洗手。他的动作熟练尽管身体已经因为长期饥饿而变得虚弱,但服务的质量丝毫不减。
“你们等会儿可以把剩下的食物解决掉,”许明母亲说,“但记住,这只是今天的特例,不要养成依赖的习惯。”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施舍的意味,仿佛这是一种莫大的恩赐。
“谢谢夫人,”许明父亲连忙感激地说,“您真是太体贴了。”
许明也立即跪下。“谢谢母亲的恩赐。”
许明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起身前往客厅,准备看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虽然因为戒严令,电视上只播放官方指定的内容,但总比什么都不看要好。
等母亲离开餐厅后,许明和父亲才敢小心翼翼地看向那碗剩饭。那大约四五口的米饭和一两片青菜,在平时可能会被直接倒掉,但在现在,却成了他们眼中的珍宝。
“儿子,你先吃吧,”父亲轻声说,“你还年轻,需要更多的营养。”
许明摇摇头:“父亲,您先吃,您需要保持体力做家务。”尽管他的胃正在痛苦地抗议。两人推让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平分这些剩饭。他们将食物分成两份,确保每一粒米都不浪费。然后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慢慢品尝着这来之不易的食物。每一口都被细细咀嚼,尽可能地延长享用的时间,让饥饿的感觉得到片刻的缓解。
客厅里,许明母亲舒适地坐在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本杂志,时不时地翻看几页。这些天她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她的三餐依然保证,外表依然光鲜,精神状态也保持得很好。
“记得六点钟给我准备一杯花茶,”她头也不回地说,“加两块方糖,温度不要太高。”
“遵命,夫人。”许明父亲立即应道,尽管他正艰难地消化着那点可怜的剩饭。
“饭后再给我准备些水果,”许明母亲继续说,“冰箱里应该还有几个苹果。”
这些水果是戒严前购买的,经过冰箱保存,到现在品相依然不错。而在许明和父亲看来,这些水果简直就是奢侈品,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过水果的滋味了。然而现在这种时候这些都是留给家中女主人的,他们不敢有半点觊觎。
“是的,夫人,我马上去准备。”许明父亲立即放下手中的碗,起身前往厨房。尽管他刚刚才吃了几口饭,远远不够填饱肚子,但妻子的命令是第一位的。许明则留在餐厅,迅速清理餐桌,他的动作有些缓慢,因为长期的饥饿已经让他的反应变得迟钝。晚间的家务比平时要繁重得多。除了常规的清洁工作外,还需要整理储藏室,盘点剩余的食物,以便妻子做出下一步的安排。许明和父亲默契地分工合作。
“这个苹果有点酸,”许明母亲皱着眉头说,只咬了一口就放下了,“拿去扔掉吧,再给我拿一个甜一点的。”
许明接过那个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内心充满了渴望。那鲜嫩的果肉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诱惑。但他不敢有任何逾越,只能按照母亲的吩咐,将苹果放入垃圾桶。等母亲离开厨房后,他才悄悄地从垃圾桶中捡出那个苹果,然后和父亲分享剩下的部分。这种行为如果被母亲发现,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饥饿让他们不得不冒险。每一口苹果都被他们细细咀嚼,这种偷来的快乐总是短暂的,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珍贵。
戒严令实施的第12天,顾沁瑶决定亲自视察南市的情况。这次视察被官方媒体宣传为“关怀民生之行”,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次权力的展示。
视察前一天,整个社区都被彻底清扫了一遍。所有能动的居民都被要求参与清洁工作,尽管许多人已经因为长期饥饿而虚弱不堪。警校女学生和社区主任监督着整个过程,确保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
“明天是顾部长亲自视察,任何人敢怠慢,直接处理!”社区主任高声宣布。“所有人必须整齐列队,展现南市居民的精神面貌!”
第二天一早,许明一家和其他所有居民被要求在小区广场集合。尽管许多人已经饥饿难耐,甚至站都站不稳,但没有人敢缺席。警校女学生和社区主任严格检查着每一个人的着装和精神状态,不合格的人直接被拖到一旁“教育”。
“记住,见到顾部长,全体下跪行礼!”社区主任反复强调,“任何人敢抬头或者不敬,后果自负!”
上午十点,顾沁瑶的车队缓缓驶入社区。当她的专车停在广场中央时,所有居民立即跪倒在地,额头触地,这个场景从高处看去,就像是一片人海在风中起伏。顾沁瑶身着一套深蓝色的职业套装,脚踩一双锃亮的黑色粗跟长靴,从车上走下来。她的表情冷静而威严,目光扫过跪成一片的居民,脸上没有任何感情波动。皮靴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在寂静的广场上格外清晰。视察队伍首先来到几栋已经封锁的居民楼。这些楼内居住的家庭几乎全都饿死,或者说,被“自然筛选”掉了。
“这栋楼共有四十八户家庭,目前已确认四十一户全部死亡,剩余的也几乎奄奄一息。”一名警校女生公事公办地汇报道,语气中没有一丝同情或悲悯。
顾沁瑶只是点了点头,目光平静地扫过楼层,仿佛在看一些无关紧要的物品。“记录在案,”她简短地说,“按照戒严令第十七条处理。”
这意味着这些尸体将被集中处理,不会有任何仪式或者通知家属的程序。在戒严期间,死亡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不值得太多关注。
视察队伍继续前进,来到了一个小型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上万名居民,他们都是从周围社区被集中过来的。当顾沁瑶出现时,所有人立即跪下,场面蔚为壮观。从主席台上看去,密密麻麻的人头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这些人大多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眼窝深陷,但他们保持着最恭敬的姿态,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顾沁瑶站在主席台上,俯视着这片人海。她的面容因权力带来的满足感而泛着光彩,红润的双颊与周围居民苍白的面孔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站姿挺拔,双眼微眯,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那是一种只有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拥有的神情——高高在上,藐视一切。
突然,前排的一名老妇人忍不住开口了。
“顾部长,求求您,给我们一些食物吧!”她的声音颤抖而微弱,但在寂静的广场上依然清晰可闻,“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孩子们都快撑不住了...”
她的话音刚落,两名警卫立即冲上前去,准备将她拖走。然而顾沁瑶抬了抬手,示意他们住手。这个简单的手势充满了威严,仿佛一位女王对臣民的恩赐。
“让她说完。”顾沁瑶的声音不高,她想听听这些卑微生物的哀求,这能让她感受到更多的成就感。
老妇人见状,立即匍匐在地,额头重重地磕在地面上,发出“咚咚”的声响。“感谢顾部长开恩!我们不是要违抗戒严令,我们只是...只是真的快撑不住了...”她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的哀求,带着哭腔,“我的孙子已经三天没有睁开眼睛了,求求您,哪怕给我们一点点食物也好...”
她的话引发了一阵连锁反应,更多的人开始拼命磕头,额头磕破也毫不在意,鲜血染红了地面。“求求您,顾部长,救救我们吧!我们愿意做任何事!”声音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悲切的海洋。
广场上的场景令人震撼。成千上万的人跪在地上,疯狂地磕着头,仿佛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有的人已经虚弱到无法抬起头,只能用尽全身力气微微颤抖;有的人流着泪,声音嘶哑得近乎耳语;还有的人抱着不再动弹的孩子,眼神中满是绝望和哀求。
顾沁瑶站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一切,仿佛在欣赏一幅活的画卷。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满足感。在这一刻,她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权力——只需一个念头,一条命令,她就能决定数万人的生死存亡。
这种感觉比任何赞美、任何成就都要强烈,让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颤栗。她回想起自己签署戒严令的那一刻,当时只是简单地在文件上划下一个签名,没想到竟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让一座城市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她手中。她站在那里,黑色的粗跟长靴牢牢地踩在主席台上,微微抬起下巴,以一种女王般的姿态审视着臣民。这种感觉比她想象的还要美妙,让她几乎沉醉其中。每一声哀求,每一个磕头的声音,都像美妙的音乐在她耳边回荡,强化着她的权力感。
“我会考虑你们的请求,”最终,顾沁瑶开口了,声音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愉悦,仿佛在赐予一种无上的恩典,“南市政府一直关心市民的生活,我们会尽快研究解决方案。”
说完,她转身离开,留下依然跪在地上的人群。她的靴子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回到市政府,顾沁瑶不紧不慢的召开会议。她内心依然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但理性告诉她,如果任由居民继续饿死,最终可能会不好收场。
“情况确实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她在会议上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会影响到戒严的长期执行。”
简单的会议持续了两天,期间南市依然有大量居民因饥饿而死亡。每一个分钟,都有几十个家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这些数字在会议室里只是冰冷的统计数据,没有人真正关心这背后的生命和故事。
最终,顾沁瑶做出了决定:“从明天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食物配给制度。每个家庭按人口数量领取基本口粮,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
这个决定在表面上看是一种人道主义措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充满了政治考量。
“食物不能免费发放,”顾沁瑶强调,“必须收取费用,否则会助长懒惰和依赖心理。”所谓的“费用”,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对许多已经没有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另外,食物必须统一打包,按家庭人口分配,不允许有任何选择权。”这意味着居民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的任何食物,无论质量如何,无论是否符合个人需求。
“分配过程必须严格管控,确保没有人能够钻空子。违反规定者,取消领取资格。”这条规定给了基层管理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食物分配过程充满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这样,一个看似人道的决定,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控制。居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稍稍缓解,却又进入了一种新的依赖和掌控关系中。
当这个决定公布后,南市居民爆发出一阵感激的欢呼。对于已经饥饿多日的人们来说,能够获得一些食物,哪怕是有限的,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比饿死要好得多。他们纷纷赞美顾沁瑶的“仁慈”和“体恤民情”。食物配给制度很快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居民按照指定的时间前来领取。食物被统一打包成塑料袋,里面装着定量的米、面、油和一些蔬菜。这些食物虽然能够勉强维持生命,但远远谈不上丰富或营养均衡。许明一家也在领取食物的行列中。尽管食物的价格不菲,但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
食物配给制度开始实施后,南市的每个社区都设立了固定的发放点。根据官方通告,每户家庭每周可以领取一次食物包,数量按照家庭人口确定。这个消息让饥饿的居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尽管价格高昂,但至少能够暂时缓解饥饿的痛苦。领取日的清晨,许明和父亲早早地来到了社区的发放点。虽然通告说八点开始发放,但天还没亮,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居民。每个人都骨瘦如柴,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焦虑。没有人说话,气氛压抑而紧张,仿佛任何声响都可能破坏这难得的机会。
“听说每人只能领到半斤米和一些杂菜,”一位老人低声对旁边的人说,“但总比没有强。”
“希望能有些肉,”另一人回应,“我家孩子已经很久没见过肉了。”
随着太阳升起,发放点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们排着长队,秩序井然,没有人敢插队或者抱怨,因为监督的警校女学生随时可能将“捣乱分子”带走。这种恐惧比饥饿更有效地维持着秩序。上午九点,几辆装满食物包的卡车驶入广场。紧接着,十几名警校女学生和社区主任出现在发放台上。她们穿着整齐的制服,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与下面饥饿的居民形成鲜明对比。
“肯定吃得不错,”许明身后的一位老人小声嘀咕,“看那个胖脸蛋,像是从来没饿过。”许明悄悄地向前挪动了几步,生怕这个言论影响到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
然而警校女学生们并没有立即开始工作,而是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有说有笑地聊着天。她们谈论着新款的化妆品、好玩的游戏、漂亮的衣服,仿佛对周围饥饿的居民视而不见。其中一名女学生甚至拿出一包精美的点心,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口吃起来,引起了一片渴望的目光。
社区主任们则忙着在发放台上检查食物包的数量。她们个个面色红润,双颊饱满,身材丰腴。那些居民面色灰白,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看起来就像行走的骷髅。主任们穿着锃亮的高跟鞋,十厘米的细跟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完全不顾及脚下堆积如山的食物包。她们直接踩在这些本应珍贵的物资上,来回走动,商讨分发事宜。每一步都伴随着包装被刺穿的声音,细长的鞋跟如同利剑般轻而易举地刺穿薄弱的塑料包装,深深陷入里面的米粒和食物中。
“哎呀,这些食物包也太不结实了,”一名面色红润的社区主任笑着说,同时毫不在意地用鞋跟来回碾压着脚下的食物包,“踩两下就破了。”
“有什么关系,反正给这些人吃的,”另一名主任漫不经心地回应,高跟鞋故意在一个食物包上连踩几下,直到包装完全破裂,内容物四散漏出,“他们已经饿得什么都吃了,还在乎这点小事?”
她们像在逛商场一样,随意地在食物堆上行走,不时用鞋尖踢开挡路的食物包。有些食物包被踩踏得已经认不出原来的形状,米粒和碎菜混合在一起,糊成一团。而这些,正是即将分发给饥饿居民的全部食物。
“这批食物质量不太好,”一名踩着食物包的社区主任皱着眉头说,高跟鞋的鞋尖已经染上了食物包里渗出的汁液,“不过对这些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反正他们都快饿死了,哪还管得了这些,”另一名主任笑着回应,同时故意用鞋跟在一个相对完好的食物包上碾了几下,直到听到食物被碾碎的声音,”能吃就行。”
终于,在居民们等待了近两个小时后,发放工作开始了。社区主任们站在高台上,根据名单逐一呼叫家庭代表。被叫到名字的人上前,出示身份证明和缴费凭证,然后才能领取食物。社区主任们并没有将食物包直接交给居民,而是随意地从高台上扔下去,就像是扔垃圾一样。食物包摔在地上,有些包装本就脆弱的食物被摔得粉碎。更糟糕的是,有些社区主任为了“方便”,直接踩着食物包走动,高跟鞋的细跟深深地刺入包装,将里面的内容物刺破。她们对此毫不在意,仿佛那不是珍贵的食物,而只是随处可见的垃圾。
“下一个,张家,三口人,领取三份!”一名社区主任高声喊道,然后随手抓起三个已经被踩得变形的食物包,用力往下一扔。食物包从高台上划出一道弧线,重重地摔在坚硬的地面上。食物包因为之前被高跟鞋反复踩踏而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包装完全破裂,米粒和菜叶四散飞溅。
一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赶紧上前,他的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微微颤抖,脸上的皮肤紧贴着颧骨,看起来就像一层薄纸。他跪在地上,用干枯的手指一粒一粒地捡起散落的米粒,甚至用舌头舔起地上已经无法用手拾取的食物碎屑。他的动作既急切又小心,像是在对待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社区主任不耐烦地催促道,同时已经准备扔下一个家庭的食物包。
男子赶紧将破碎不堪的食物包和散落的内容物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自己的衣服兜着,生怕遗漏任何一点可以食用的东西。他的眼中含着泪水,但更多的是对这些救命食物的感激。即使这些食物已经被踩得面目全非,但对于已经饥饿数日的家庭来说,依然是维持生命的唯一希望。
许明和父亲也很快被叫到了名字。他们上前缴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社区主任踩着已经破损的食物包,用鞋尖将它们挑出来。“许家,三口人,领取三份!”她高声宣布,然后随手将三个食物包用力扔下高台。
食物包在空中划过一道曲线,重重地摔在地上。包装上清晰可见多处被高跟鞋踩踏的痕迹,一个角已经被尖锐的鞋跟刺破,里面的米粒漏了一小堆。包装上甚至印着明显的泥泞鞋印,那是主任们在食物堆上来回走动时留下的。许明和父亲迅速上前,像对待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破损的食物包捡起来。他们俯身跪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拾起散落的米粒,生怕浪费任何一点食物。许明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眼睛紧盯着地上的每一粒米,每一片菜叶,仿佛在收集珍贵的钻石。父亲则用衣服下摆兜住已经无法放回包装的散碎食物,这些在主任们眼中不值一提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却是维系生命的至宝。领取完食物后,每个家庭代表还必须到警校女学生面前磕头致谢。这些女学生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居民,脸上带着一种施舍的表情。
“谢谢大人的恩赐!”居民们必须如此说道,然后才能离开。有些女学生甚至会故意为难一些居民,要求他们多磕几个头,或者说得更大声一些。
轮到许明和父亲时,在他们跪下磕头的过程中,一名警校女学生正在和同伴聊天,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直到另一名女学生提醒她,她才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带着来之不易的食物包,许明和父亲终于返回家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检查里面的内容。食物包的内容确实令人失望:半斤发霉的米,一些已经开始腐烂的蔬菜叶子,以及一小块散发着怪味的肉。在正常时期,这些食物可能会被直接扔进垃圾桶,但在当前的处境下,却是救命的珍宝。
“至少能吃饱一顿,”许明父亲勉强地笑了笑,“比前几天好多了。”
许明母亲检查了食物后,做出了分配决定:“这些米我要三分之二,肉我全部要,你们分那些蔬菜。”
就这样,一家人开始了配给制度下的生活。虽然食物的质量堪忧,数量也远远不够,但至少让他们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每个人都严格按照配给量食用,生怕多吃一口,导致明天没有食物。而在城市的其他角落,类似的场景在每个家庭上演。人们为了一些在平时可能会被丢弃的食物而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再多活几天。戒严令下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人们对食物的认知和期望,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成为了最大的奢侈。第二天,许明遇到了同栋楼的邻居王大爷。这位老人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虽然依然消瘦,但至少眼神中有了一丝活力。
“昨天领到食物了吗?”王大爷问道。
许明点点头:“领到了,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好。”
“我们家的肉已经完全变质了,根本没法吃,“王大爷叹了口气,“但米和菜还算能下咽。”
“我们家也差不多,”许明回应。
两人交换了一下各自领到的食物情况,发现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食物质量普遍不佳,数量也远远不够,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没有人敢有任何抱怨。
“听说下次发放要等十天后,”王大爷压低声音说,“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许明心中一沉。如果真的要等十天,那么他家的食物肯定不够。回到家里,许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进一步减少自己的食量,确保能够延长食物的使用时间。
“我们可以一天只吃一顿,”许明父亲说,“每顿只吃一小口,争取撑到下次发放。”
就这样,许明和父亲开始了更加严格的节食计划。他们将每天的食物分成极小的部分,仅仅保证不会因为饥饿而死亡。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但他们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许明母亲的生活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她仍然保持着三餐的习惯,虽然食量有所减少,但比起许明和父亲,她的处境要好得多。在这个家庭中,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等级制度依然牢固不变。
即使如此食物配给制度在南市各个区域的执行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有些地区的居民虽然领到的食物质量差、数量少,但至少能够勉强维持生命;而另一些地区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居民们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食物供应。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负责各区域的警校女学生对形势的认知差距。个人的理解和执行方式却有着天壤之别。
以东区为例,负责该区域的几名警校女学生几乎完全拒绝发放食物。这并非出于刻意的残忍,而是源于她们与实际生活的严重脱节。她们大多来自优渥的家庭,从小就享受着优质的教育和丰富的物质条件,对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毫无概念。
“我觉得他们太夸张了,”一名负责东区的女学生在聊天时说到,“少吃几顿饭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减肥的时候经常一天只吃一顿,不也活得好好的。”
她身旁的同学点头附和:“就是啊,这些人简直太软弱了。饿几天对他们是好事,能让他们学会感恩和遵守规则。”
这些女学生每天仍然享用着丰盛的三餐,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而她们却无法理解几天不进食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在她们看来,居民们的哀求只是一种矫情的表现,是对权威的挑战,需要用更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压。
“我们是在锻炼他们的意志力,”另一名女学生正色道,“现在不加强管控,以后戒严令结束了,他们肯定会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她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饥饿与她们理解的“节食”或“减肥”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本就长期营养不良的底层居民来说,几天没有食物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这一点却被她们的特权视角完全忽略了。
东区的李家弄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小区原本有三百多户居民,但在食物配给制度实施处期,就有几十个家庭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而饿死。然而,负责该小区的警校女学生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自然淘汰,”她们在报告中如此写道,“那些没有足够意志力的居民自然会被筛选出局,这有利于提高整体人口素质。”
这种冷酷的思想在她们的圈子里得到了广泛认同。她们甚至为自己“严格执行戒严令”而感到自豪,认为这是对上级的忠诚表现。
“看看我们小区,多么安静、有序,”一名女学生在朋友圈炫耀道,“都是因为我们的管理得当。”她发布了一张小区空旷整洁的照片,但照片中没有一个人影,因为大部分居民已经因为饥饿而无法出门,甚至有些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这些女学生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精美的餐食照片,讨论着最新的时尚潮流,仿佛外面的世界一片祥和。在她们的认知里,戒严令不过是一场暂时的管控措施,而不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危机。
“今天尝试了西餐,牛排简直绝了!”一名负责监督食物发放的女学生在朋友圈发文,配图是一块血多汁少的牛排。
这条信息发布的同一天,她负责的小区有五十户家庭因为无法获得食物而全部死亡。但在她的报告中,这些只是被简单地记录为“自然减员”,没有引起任何重视。
这种认知差距不仅存在于警校女学生中,也普遍存在于整个管理层。她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普通人在戒严令下的痛苦。在他们看来,这些痛苦不过是必要的代价,是为了维护秩序而必须付出的。
更为讽刺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管理区域的“成绩”开始被上级表彰。所谓的“成绩”,是指这些区域内没有发生任何违反戒严令的行为,秩序维持得非常好。但实际上,这些区域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大部分居民已经没有力气反抗,甚至已经饿死。
“东区李家弄小区表现突出,维持了最高水准的社会稳定,特予以通报表扬。”这样的表彰在各级会议上频频出现,而没有人去追问这种“稳定”背后的真相。
那些因为单纯的认知差距和特权视角而做出错误决定的警校女学生,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因为“管理得当”而获得了表彰和奖励。她们的履历上多了一笔“危机时期维稳工作表现突出”的记录,为将来的升迁铺平了道路。最残酷的管理者反而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因为她们创造了表面上的“稳定”和“秩序”。这种倒错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层的冷酷态度,使得整个戒严体系变得更加不人道。在这样的环境下,许明一家所在的小区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负责他们小区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学生,与其她同学不同,她是来自一个相对普通的家庭,对底层生活有一些模糊的认识。虽然她也执行着严格的戒严政策,但至少保证了基本的食物发放。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完全断绝食物供应,”陈雯在私下对一位信任的同事说,“这样会让很多人死亡的。”
“这就是目的啊,”同事满不在乎地回答,“筛选掉那些弱者,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人。这是自然规律,适者生存。”
她没有再说什么,但她确保了自己负责区域内的食物配给按时发放,虽然数量有限,质量堪忧,但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点,许明一家和周围邻居们才能暂时生存下来。
在这个关乎生存的基本需求都无法保障的环境中,人性被压缩到了最原始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管理者们,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享受着特权带来的舒适和安全,对自己决定的后果毫无感知,也不需要为此负任何责任。
戒严令实施前,南市的社区主任们只是普通的基层管理人员,负责处理社区内的日常事务——调解邻里纠纷、组织文化活动、传达上级政策等。那时候她们的权力有限,居民们那是对她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礼貌和尊重即可。
然而戒严令改变了一切。短短几天内,这些社区主任的权力被无限放大,她们突然之间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生杀大权。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决定谁能获得食物、获得多少食物,本质上就是决定谁能活下去、谁会死去。这种权力的突然膨胀,对许多人的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主任是许明所在社区的负责人之一。戒严令之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女性,她那时会对居民态度不佳,但也仅限于冷脸或者语气不善。然而,戒严令实施后,她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
“王主任以前也就是脾气差点,”许明的邻居王大爷说道,“现在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眼睛里都是冷的。”
确实,王主任的眼神变得冰冷而空洞,仿佛在看待物品而非人类。她开始利用手中新获得的权力,在极小的事情上为难居民,仿佛在测试自己权力的边界。
“站直了!”她对排队领取食物的人喝道,“弯腰驼背的,看着就烦!”
那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努力地挺直了佝偻的脊背,但年龄和疾病让他无法完全站直。王主任冷笑一声:“不合格,回去吧,今天没有你的份。”
老人的眼中满是绝望,但他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地离开队伍。在他身后,其他居民低着头,不敢有任何表示,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驱逐的人。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王主任似乎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她的脸上经常浮现出一种奇怪的微笑,那是一种掌控他人命运的快感。这种快感让她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她开始创造各种规则,只为了看到居民们挣扎的样子。
“今天只有能背出戒严令全文的人才能领到食物,”她突然宣布,看着排队的居民们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怎么?不会背?那就证明你们不够重视戒严令,不配获得食物。”
居民们开始慌乱地互相传授戒严令的内容,但戒严令全文有数千字,普通人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记住。王主任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明显。
“开个玩笑而已,”半小时后,她突然改口,“今天只要会唱《戒严之歌》就行。”这是一首近期才创作的歌曲,大多数人都没听过。
这种捉弄在王主任看来可能只是无伤大雅的“游戏”,但对于饥肠辘辘的居民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折磨。每一次规则的改变,都可能意味着一天、两天,甚至更长时间的挨饿。
许明的父亲在一次领取食物时,因为弯腰系鞋带而被王主任认为“不够恭敬”,结果被罚站了两个小时,才被允许领取食物。而那时,分发即将结束,很多食物已经被分完,他只能获得比平时更少的配给。
“以前她最多就是脸色难看,现在动不动就要你的命,”许明父亲回家后低声说道。
王主任并非个例。在南市的许多社区,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些曾经普普通通的社区主任,突然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没有任何制衡机制,导致许多人彻底迷失了自己。当一个人突然获得巨大权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效应——她们开始相信自己高人一等,认为规则不适用于自己,对他人的痛苦变得麻木。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权力滥用得到了上级的默许,甚至是鼓励。在戒严令的框架下,“维持秩序”和“执行力度”成为评价基层管理者的主要标准,而居民的实际处境则被完全忽视。
“听说刘主任因为拒绝了一半以上的领取申请,被评为'戒严模范',”一位社区工作人员私下透露,“现在大家都在比谁更狠,这样才能得到表彰。”
在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下,权力滥用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成为了升迁的途径。社区主任们开始比拼谁更能“严格执行戒严令”,谁更能“维护社区稳定”。而这些华丽辞藻的背后,是居民们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
有些社区主任甚至开始针对那些曾经与自己有过冲突的居民。在正常时期,这些小矛盾最多导致一些口舌之争,但在戒严令赋予的权力下,它们变成了足以致命的武器。
“李家以前和我拌过嘴,”一名社区主任在私下聚会时炫耀道,“现在看他们还敢不敢。两周了,一粒米都没给他们。”
在座的其他主任们笑了起来,仿佛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不是关乎一个家庭生死的决定。在她们的笑声中,李家的老人已经因为饥饿而卧床不起,年幼的孩子则整日啼哭,却无人理会。
许明一家相对幸运,因为他们之前与社区主任没有太多交集,没有成为特别针对的对象。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每一次领取食物的场合,确保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会激怒这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
“你知道吗,张主任以前只是个文件整理员,连说话的机会都很少,”一位居民回忆道,“现在她说一句话,几百个人都要抖三抖。”
“以前我们至少可以抱怨几句,”许明在家低声说道,“现在连叹气都不敢太大声,生怕被认为是'情绪不稳定',下次就没有食物了。”
在南市各个社区的食物分发点,一种新的现象开始出现——选择性分配。社区主任们不再仅仅是随意为难居民,而是开始有针对性地拒绝特定家庭的食物申请。这种做法并非基于任何官方政策或规定,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好恶和报复心理。
潘主任站在发放台上,俯视着排队的居民。她穿着那双黑色的高跟鞋,站姿傲慢,脚下随意踩着几个食物包,仿佛那不是救命的口粮,而只是无关紧要的垫脚物。锋利的鞋跟已经刺破了其中一个包装,白色的米粒从破口处缓缓渗出,在地上形成一小堆。她注意到了,但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轻轻转动脚踝,让鞋跟更深地陷入包装中。
“王家?”她故意拖长了声音,“让我查查记录。”身体重量随意地压在那个被踩稀烂的食物包上,几乎能听到包装进一步撕裂的声音。
她装模作样地翻看手中的名单,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她对每个家庭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不过是一种拖延的把戏,一种展示权力的方式。
“啊,抱歉,”最终她抬起头,脸上带着假惺惺的遗憾,“今天的食物已经发完了。你们下周再来吧。”她说这话时,脚下踩着的食物包已经完全变形,米粒四散而出。
王家的代表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潘主任脚下那些被踩踏的食物包上,然后又看向她身后不过两米远的地方。那里堆积如山的食物包清晰可见,上百个塑料袋整齐地摞在一起,食物就在那里,触手可及,却被一句话设置了无形的屏障。
“潘主任,”他颤抖着声音说道,指了指那堆食物包,“可是那里还有很多食物...我们一家已经三天没有食物了,孩子们快撑不住了...”
潘主任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食物堆,然后转回来,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冷酷。“我说了,食物发完了。”
她一字一顿地说,目光中闪烁着某种报复的快感。她故意侧身,让他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那些食物包,仿佛在炫耀自己拒绝的权力。
“求求您,”王家的人跪了下来,额头触地,眼睛仍然盯着那堆近在咫尺却不可触及的食物包,“就给我们一点点也行,哪怕是一小袋米..”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潘主任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她转身拿起一个食物包,在他面前晃了晃,然后重新放回堆中,“质疑戒严令?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
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连连磕头道歉。但潘主任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她继续施压:“也许我应该向上级报告,说你们家有反对戒严令的倾向。你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吧?”
这个威胁让他彻底崩溃,他不停地磕头,祈求原谅。周围的居民都低着头,不敢出声,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最终,潘主任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下周再来吧,”她说,“如果还有食物的话。”潘主任脚下踩得正是王家人的命脉,而此时正被鞋底如同垃圾一样踩在脚下,至于王家能否活过一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以后真的是否能在潘主任的鞋底下领取救命的食物仍是个谜。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脸上写满了绝望。他缓缓离开队伍,背影显得无比孤独而无助。而潘主任已经开始叫下一家的名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王家曾经在戒严前因为潘主任的一次工作失误发了一下牢骚,尽管那只是一件小事,但在潘主任的心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在她决定要让王家付出代价。
然而当这些家庭被告知“食物已经发完”时,他们眼前就是证据确凿的谎言。每个分发点的后方都堆积着大量的食物包,有些甚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社区主任们往往就站在这些食物堆上,她们来回走动时,尖细的鞋跟不断刺破包装,但她们对此视而不见,甚至看起来颇为享受这种践踏的感觉。
“我亲眼看到潘主任告诉食物发完了,”一位居民透露,“当时她就站在食物堆上,那双高跟鞋深深陷入一个米袋中,米粒从破洞里向外涌,撒了一地。孩子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食物,嘴角还流着口水。最可笑的是,刘主任说完'没有食物'后,走下台阶时还踢翻了一包面粉,包装完全破裂,粉末四散。她看都没看一眼,就像踢到了一块石头。”这种公然的、赤裸裸的权力展示,许多居民感到绝望和无助。谎言不需要掩饰,因为说谎者知道,即使谎言被戳穿,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而且她特别喜欢在分发食物时穿一双带有金属尖跟的高跟鞋,专门用来踩踏食物包。工作人员会在高台上堆起食物包,她则站在这些包装上方,俯视着排队的居民。她故意用鞋跟在包装上碾压,让底层的米粒和面粉渗出来,形成一片狼藉。然后她会指着那些被她踩坏的食物包,宣布这些是她赐予的食物让居民们心怀感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居民开始尝试各种方式来讨好社区主任。有人送礼,有人提供服务,有人甚至出卖邻居的信息,只为确保自己家能够按时领到食物。社区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互相猜忌和背叛。
“米饭的火候控制得不错,”她评价道,“下次可以多放点油,这样口感会更好。”
站在一旁的许明父亲立即点头应是:“遵命,下次我一定注意。”他的声音有些虚弱,脸颊已经明显凹陷,眼睛周围有着深深的黑圈,身体也比半个月前瘦了一大圈。
许明站在另一侧,同样的姿势服侍母亲用餐。他的情况比父亲好不了多少,原本结实的身材已经变得瘦削,脸色苍白,眼神中透露出疲惫。这已经是许明母亲今天的第三餐了。早餐是粥和咸鸭蛋,午餐是面条和一些蔬菜。而许明和父亲,按照她的规定,一天只能在晚上吃一顿饭,而且分量有限。这种安排是在戒严令实施的第六天开始的,当时许明母亲意识到食物储备可能撑不了太久。
“在这种特殊时期,我们必须合理分配资源,”她当时这样宣布,“作为这个家的主心骨,我必须保持充沛的精力,所以我的三餐不能减。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
这个决定对许明和父亲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女性的决定是绝对的,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的权利。
“米饭好像有点多,”许明母亲看着自己只吃了三分之二的米饭,摇了摇头,“下次少盛一点,浪费可耻。”说着,她用筷子拨弄了几下剩余的米饭,然后放下碗筷,示意自己用餐完毕。许明立即上前,将餐具收走。他的胃在看到那些剩余的食物时发出了痛苦的抗议,但他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即使是母亲吃剩的食物,也不是他能随意处置的。许明父亲迅速拿来一杯温水和一条湿毛巾,让妻子漱口洗手。他的动作熟练尽管身体已经因为长期饥饿而变得虚弱,但服务的质量丝毫不减。
“你们等会儿可以把剩下的食物解决掉,”许明母亲说,“但记住,这只是今天的特例,不要养成依赖的习惯。”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施舍的意味,仿佛这是一种莫大的恩赐。
“谢谢夫人,”许明父亲连忙感激地说,“您真是太体贴了。”
许明也立即跪下。“谢谢母亲的恩赐。”
许明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起身前往客厅,准备看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虽然因为戒严令,电视上只播放官方指定的内容,但总比什么都不看要好。
等母亲离开餐厅后,许明和父亲才敢小心翼翼地看向那碗剩饭。那大约四五口的米饭和一两片青菜,在平时可能会被直接倒掉,但在现在,却成了他们眼中的珍宝。
“儿子,你先吃吧,”父亲轻声说,“你还年轻,需要更多的营养。”
许明摇摇头:“父亲,您先吃,您需要保持体力做家务。”尽管他的胃正在痛苦地抗议。两人推让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平分这些剩饭。他们将食物分成两份,确保每一粒米都不浪费。然后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慢慢品尝着这来之不易的食物。每一口都被细细咀嚼,尽可能地延长享用的时间,让饥饿的感觉得到片刻的缓解。
客厅里,许明母亲舒适地坐在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本杂志,时不时地翻看几页。这些天她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她的三餐依然保证,外表依然光鲜,精神状态也保持得很好。
“记得六点钟给我准备一杯花茶,”她头也不回地说,“加两块方糖,温度不要太高。”
“遵命,夫人。”许明父亲立即应道,尽管他正艰难地消化着那点可怜的剩饭。
“饭后再给我准备些水果,”许明母亲继续说,“冰箱里应该还有几个苹果。”
这些水果是戒严前购买的,经过冰箱保存,到现在品相依然不错。而在许明和父亲看来,这些水果简直就是奢侈品,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过水果的滋味了。然而现在这种时候这些都是留给家中女主人的,他们不敢有半点觊觎。
“是的,夫人,我马上去准备。”许明父亲立即放下手中的碗,起身前往厨房。尽管他刚刚才吃了几口饭,远远不够填饱肚子,但妻子的命令是第一位的。许明则留在餐厅,迅速清理餐桌,他的动作有些缓慢,因为长期的饥饿已经让他的反应变得迟钝。晚间的家务比平时要繁重得多。除了常规的清洁工作外,还需要整理储藏室,盘点剩余的食物,以便妻子做出下一步的安排。许明和父亲默契地分工合作。
“这个苹果有点酸,”许明母亲皱着眉头说,只咬了一口就放下了,“拿去扔掉吧,再给我拿一个甜一点的。”
许明接过那个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内心充满了渴望。那鲜嫩的果肉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诱惑。但他不敢有任何逾越,只能按照母亲的吩咐,将苹果放入垃圾桶。等母亲离开厨房后,他才悄悄地从垃圾桶中捡出那个苹果,然后和父亲分享剩下的部分。这种行为如果被母亲发现,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饥饿让他们不得不冒险。每一口苹果都被他们细细咀嚼,这种偷来的快乐总是短暂的,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珍贵。
戒严令实施的第12天,顾沁瑶决定亲自视察南市的情况。这次视察被官方媒体宣传为“关怀民生之行”,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次权力的展示。
视察前一天,整个社区都被彻底清扫了一遍。所有能动的居民都被要求参与清洁工作,尽管许多人已经因为长期饥饿而虚弱不堪。警校女学生和社区主任监督着整个过程,确保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
“明天是顾部长亲自视察,任何人敢怠慢,直接处理!”社区主任高声宣布。“所有人必须整齐列队,展现南市居民的精神面貌!”
第二天一早,许明一家和其他所有居民被要求在小区广场集合。尽管许多人已经饥饿难耐,甚至站都站不稳,但没有人敢缺席。警校女学生和社区主任严格检查着每一个人的着装和精神状态,不合格的人直接被拖到一旁“教育”。
“记住,见到顾部长,全体下跪行礼!”社区主任反复强调,“任何人敢抬头或者不敬,后果自负!”
上午十点,顾沁瑶的车队缓缓驶入社区。当她的专车停在广场中央时,所有居民立即跪倒在地,额头触地,这个场景从高处看去,就像是一片人海在风中起伏。顾沁瑶身着一套深蓝色的职业套装,脚踩一双锃亮的黑色粗跟长靴,从车上走下来。她的表情冷静而威严,目光扫过跪成一片的居民,脸上没有任何感情波动。皮靴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在寂静的广场上格外清晰。视察队伍首先来到几栋已经封锁的居民楼。这些楼内居住的家庭几乎全都饿死,或者说,被“自然筛选”掉了。
“这栋楼共有四十八户家庭,目前已确认四十一户全部死亡,剩余的也几乎奄奄一息。”一名警校女生公事公办地汇报道,语气中没有一丝同情或悲悯。
顾沁瑶只是点了点头,目光平静地扫过楼层,仿佛在看一些无关紧要的物品。“记录在案,”她简短地说,“按照戒严令第十七条处理。”
这意味着这些尸体将被集中处理,不会有任何仪式或者通知家属的程序。在戒严期间,死亡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不值得太多关注。
视察队伍继续前进,来到了一个小型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上万名居民,他们都是从周围社区被集中过来的。当顾沁瑶出现时,所有人立即跪下,场面蔚为壮观。从主席台上看去,密密麻麻的人头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这些人大多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眼窝深陷,但他们保持着最恭敬的姿态,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顾沁瑶站在主席台上,俯视着这片人海。她的面容因权力带来的满足感而泛着光彩,红润的双颊与周围居民苍白的面孔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站姿挺拔,双眼微眯,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那是一种只有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拥有的神情——高高在上,藐视一切。
突然,前排的一名老妇人忍不住开口了。
“顾部长,求求您,给我们一些食物吧!”她的声音颤抖而微弱,但在寂静的广场上依然清晰可闻,“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孩子们都快撑不住了...”
她的话音刚落,两名警卫立即冲上前去,准备将她拖走。然而顾沁瑶抬了抬手,示意他们住手。这个简单的手势充满了威严,仿佛一位女王对臣民的恩赐。
“让她说完。”顾沁瑶的声音不高,她想听听这些卑微生物的哀求,这能让她感受到更多的成就感。
老妇人见状,立即匍匐在地,额头重重地磕在地面上,发出“咚咚”的声响。“感谢顾部长开恩!我们不是要违抗戒严令,我们只是...只是真的快撑不住了...”她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的哀求,带着哭腔,“我的孙子已经三天没有睁开眼睛了,求求您,哪怕给我们一点点食物也好...”
她的话引发了一阵连锁反应,更多的人开始拼命磕头,额头磕破也毫不在意,鲜血染红了地面。“求求您,顾部长,救救我们吧!我们愿意做任何事!”声音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悲切的海洋。
广场上的场景令人震撼。成千上万的人跪在地上,疯狂地磕着头,仿佛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有的人已经虚弱到无法抬起头,只能用尽全身力气微微颤抖;有的人流着泪,声音嘶哑得近乎耳语;还有的人抱着不再动弹的孩子,眼神中满是绝望和哀求。
顾沁瑶站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一切,仿佛在欣赏一幅活的画卷。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满足感。在这一刻,她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权力——只需一个念头,一条命令,她就能决定数万人的生死存亡。
这种感觉比任何赞美、任何成就都要强烈,让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颤栗。她回想起自己签署戒严令的那一刻,当时只是简单地在文件上划下一个签名,没想到竟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让一座城市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她手中。她站在那里,黑色的粗跟长靴牢牢地踩在主席台上,微微抬起下巴,以一种女王般的姿态审视着臣民。这种感觉比她想象的还要美妙,让她几乎沉醉其中。每一声哀求,每一个磕头的声音,都像美妙的音乐在她耳边回荡,强化着她的权力感。
“我会考虑你们的请求,”最终,顾沁瑶开口了,声音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愉悦,仿佛在赐予一种无上的恩典,“南市政府一直关心市民的生活,我们会尽快研究解决方案。”
说完,她转身离开,留下依然跪在地上的人群。她的靴子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回到市政府,顾沁瑶不紧不慢的召开会议。她内心依然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但理性告诉她,如果任由居民继续饿死,最终可能会不好收场。
“情况确实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她在会议上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会影响到戒严的长期执行。”
简单的会议持续了两天,期间南市依然有大量居民因饥饿而死亡。每一个分钟,都有几十个家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这些数字在会议室里只是冰冷的统计数据,没有人真正关心这背后的生命和故事。
最终,顾沁瑶做出了决定:“从明天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食物配给制度。每个家庭按人口数量领取基本口粮,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
这个决定在表面上看是一种人道主义措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充满了政治考量。
“食物不能免费发放,”顾沁瑶强调,“必须收取费用,否则会助长懒惰和依赖心理。”所谓的“费用”,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对许多已经没有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另外,食物必须统一打包,按家庭人口分配,不允许有任何选择权。”这意味着居民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的任何食物,无论质量如何,无论是否符合个人需求。
“分配过程必须严格管控,确保没有人能够钻空子。违反规定者,取消领取资格。”这条规定给了基层管理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食物分配过程充满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这样,一个看似人道的决定,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控制。居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稍稍缓解,却又进入了一种新的依赖和掌控关系中。
当这个决定公布后,南市居民爆发出一阵感激的欢呼。对于已经饥饿多日的人们来说,能够获得一些食物,哪怕是有限的,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比饿死要好得多。他们纷纷赞美顾沁瑶的“仁慈”和“体恤民情”。食物配给制度很快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居民按照指定的时间前来领取。食物被统一打包成塑料袋,里面装着定量的米、面、油和一些蔬菜。这些食物虽然能够勉强维持生命,但远远谈不上丰富或营养均衡。许明一家也在领取食物的行列中。尽管食物的价格不菲,但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
食物配给制度开始实施后,南市的每个社区都设立了固定的发放点。根据官方通告,每户家庭每周可以领取一次食物包,数量按照家庭人口确定。这个消息让饥饿的居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尽管价格高昂,但至少能够暂时缓解饥饿的痛苦。领取日的清晨,许明和父亲早早地来到了社区的发放点。虽然通告说八点开始发放,但天还没亮,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居民。每个人都骨瘦如柴,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焦虑。没有人说话,气氛压抑而紧张,仿佛任何声响都可能破坏这难得的机会。
“听说每人只能领到半斤米和一些杂菜,”一位老人低声对旁边的人说,“但总比没有强。”
“希望能有些肉,”另一人回应,“我家孩子已经很久没见过肉了。”
随着太阳升起,发放点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们排着长队,秩序井然,没有人敢插队或者抱怨,因为监督的警校女学生随时可能将“捣乱分子”带走。这种恐惧比饥饿更有效地维持着秩序。上午九点,几辆装满食物包的卡车驶入广场。紧接着,十几名警校女学生和社区主任出现在发放台上。她们穿着整齐的制服,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与下面饥饿的居民形成鲜明对比。
“肯定吃得不错,”许明身后的一位老人小声嘀咕,“看那个胖脸蛋,像是从来没饿过。”许明悄悄地向前挪动了几步,生怕这个言论影响到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
然而警校女学生们并没有立即开始工作,而是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有说有笑地聊着天。她们谈论着新款的化妆品、好玩的游戏、漂亮的衣服,仿佛对周围饥饿的居民视而不见。其中一名女学生甚至拿出一包精美的点心,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口吃起来,引起了一片渴望的目光。
社区主任们则忙着在发放台上检查食物包的数量。她们个个面色红润,双颊饱满,身材丰腴。那些居民面色灰白,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看起来就像行走的骷髅。主任们穿着锃亮的高跟鞋,十厘米的细跟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完全不顾及脚下堆积如山的食物包。她们直接踩在这些本应珍贵的物资上,来回走动,商讨分发事宜。每一步都伴随着包装被刺穿的声音,细长的鞋跟如同利剑般轻而易举地刺穿薄弱的塑料包装,深深陷入里面的米粒和食物中。
“哎呀,这些食物包也太不结实了,”一名面色红润的社区主任笑着说,同时毫不在意地用鞋跟来回碾压着脚下的食物包,“踩两下就破了。”
“有什么关系,反正给这些人吃的,”另一名主任漫不经心地回应,高跟鞋故意在一个食物包上连踩几下,直到包装完全破裂,内容物四散漏出,“他们已经饿得什么都吃了,还在乎这点小事?”
她们像在逛商场一样,随意地在食物堆上行走,不时用鞋尖踢开挡路的食物包。有些食物包被踩踏得已经认不出原来的形状,米粒和碎菜混合在一起,糊成一团。而这些,正是即将分发给饥饿居民的全部食物。
“这批食物质量不太好,”一名踩着食物包的社区主任皱着眉头说,高跟鞋的鞋尖已经染上了食物包里渗出的汁液,“不过对这些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反正他们都快饿死了,哪还管得了这些,”另一名主任笑着回应,同时故意用鞋跟在一个相对完好的食物包上碾了几下,直到听到食物被碾碎的声音,”能吃就行。”
终于,在居民们等待了近两个小时后,发放工作开始了。社区主任们站在高台上,根据名单逐一呼叫家庭代表。被叫到名字的人上前,出示身份证明和缴费凭证,然后才能领取食物。社区主任们并没有将食物包直接交给居民,而是随意地从高台上扔下去,就像是扔垃圾一样。食物包摔在地上,有些包装本就脆弱的食物被摔得粉碎。更糟糕的是,有些社区主任为了“方便”,直接踩着食物包走动,高跟鞋的细跟深深地刺入包装,将里面的内容物刺破。她们对此毫不在意,仿佛那不是珍贵的食物,而只是随处可见的垃圾。
“下一个,张家,三口人,领取三份!”一名社区主任高声喊道,然后随手抓起三个已经被踩得变形的食物包,用力往下一扔。食物包从高台上划出一道弧线,重重地摔在坚硬的地面上。食物包因为之前被高跟鞋反复踩踏而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包装完全破裂,米粒和菜叶四散飞溅。
一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赶紧上前,他的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微微颤抖,脸上的皮肤紧贴着颧骨,看起来就像一层薄纸。他跪在地上,用干枯的手指一粒一粒地捡起散落的米粒,甚至用舌头舔起地上已经无法用手拾取的食物碎屑。他的动作既急切又小心,像是在对待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社区主任不耐烦地催促道,同时已经准备扔下一个家庭的食物包。
男子赶紧将破碎不堪的食物包和散落的内容物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自己的衣服兜着,生怕遗漏任何一点可以食用的东西。他的眼中含着泪水,但更多的是对这些救命食物的感激。即使这些食物已经被踩得面目全非,但对于已经饥饿数日的家庭来说,依然是维持生命的唯一希望。
许明和父亲也很快被叫到了名字。他们上前缴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社区主任踩着已经破损的食物包,用鞋尖将它们挑出来。“许家,三口人,领取三份!”她高声宣布,然后随手将三个食物包用力扔下高台。
食物包在空中划过一道曲线,重重地摔在地上。包装上清晰可见多处被高跟鞋踩踏的痕迹,一个角已经被尖锐的鞋跟刺破,里面的米粒漏了一小堆。包装上甚至印着明显的泥泞鞋印,那是主任们在食物堆上来回走动时留下的。许明和父亲迅速上前,像对待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破损的食物包捡起来。他们俯身跪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拾起散落的米粒,生怕浪费任何一点食物。许明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眼睛紧盯着地上的每一粒米,每一片菜叶,仿佛在收集珍贵的钻石。父亲则用衣服下摆兜住已经无法放回包装的散碎食物,这些在主任们眼中不值一提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却是维系生命的至宝。领取完食物后,每个家庭代表还必须到警校女学生面前磕头致谢。这些女学生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居民,脸上带着一种施舍的表情。
“谢谢大人的恩赐!”居民们必须如此说道,然后才能离开。有些女学生甚至会故意为难一些居民,要求他们多磕几个头,或者说得更大声一些。
轮到许明和父亲时,在他们跪下磕头的过程中,一名警校女学生正在和同伴聊天,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直到另一名女学生提醒她,她才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带着来之不易的食物包,许明和父亲终于返回家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检查里面的内容。食物包的内容确实令人失望:半斤发霉的米,一些已经开始腐烂的蔬菜叶子,以及一小块散发着怪味的肉。在正常时期,这些食物可能会被直接扔进垃圾桶,但在当前的处境下,却是救命的珍宝。
“至少能吃饱一顿,”许明父亲勉强地笑了笑,“比前几天好多了。”
许明母亲检查了食物后,做出了分配决定:“这些米我要三分之二,肉我全部要,你们分那些蔬菜。”
就这样,一家人开始了配给制度下的生活。虽然食物的质量堪忧,数量也远远不够,但至少让他们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每个人都严格按照配给量食用,生怕多吃一口,导致明天没有食物。而在城市的其他角落,类似的场景在每个家庭上演。人们为了一些在平时可能会被丢弃的食物而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再多活几天。戒严令下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人们对食物的认知和期望,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成为了最大的奢侈。第二天,许明遇到了同栋楼的邻居王大爷。这位老人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虽然依然消瘦,但至少眼神中有了一丝活力。
“昨天领到食物了吗?”王大爷问道。
许明点点头:“领到了,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好。”
“我们家的肉已经完全变质了,根本没法吃,“王大爷叹了口气,“但米和菜还算能下咽。”
“我们家也差不多,”许明回应。
两人交换了一下各自领到的食物情况,发现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食物质量普遍不佳,数量也远远不够,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没有人敢有任何抱怨。
“听说下次发放要等十天后,”王大爷压低声音说,“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许明心中一沉。如果真的要等十天,那么他家的食物肯定不够。回到家里,许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进一步减少自己的食量,确保能够延长食物的使用时间。
“我们可以一天只吃一顿,”许明父亲说,“每顿只吃一小口,争取撑到下次发放。”
就这样,许明和父亲开始了更加严格的节食计划。他们将每天的食物分成极小的部分,仅仅保证不会因为饥饿而死亡。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但他们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许明母亲的生活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她仍然保持着三餐的习惯,虽然食量有所减少,但比起许明和父亲,她的处境要好得多。在这个家庭中,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等级制度依然牢固不变。
即使如此食物配给制度在南市各个区域的执行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有些地区的居民虽然领到的食物质量差、数量少,但至少能够勉强维持生命;而另一些地区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居民们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食物供应。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负责各区域的警校女学生对形势的认知差距。个人的理解和执行方式却有着天壤之别。
以东区为例,负责该区域的几名警校女学生几乎完全拒绝发放食物。这并非出于刻意的残忍,而是源于她们与实际生活的严重脱节。她们大多来自优渥的家庭,从小就享受着优质的教育和丰富的物质条件,对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毫无概念。
“我觉得他们太夸张了,”一名负责东区的女学生在聊天时说到,“少吃几顿饭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减肥的时候经常一天只吃一顿,不也活得好好的。”
她身旁的同学点头附和:“就是啊,这些人简直太软弱了。饿几天对他们是好事,能让他们学会感恩和遵守规则。”
这些女学生每天仍然享用着丰盛的三餐,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而她们却无法理解几天不进食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在她们看来,居民们的哀求只是一种矫情的表现,是对权威的挑战,需要用更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压。
“我们是在锻炼他们的意志力,”另一名女学生正色道,“现在不加强管控,以后戒严令结束了,他们肯定会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她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饥饿与她们理解的“节食”或“减肥”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本就长期营养不良的底层居民来说,几天没有食物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这一点却被她们的特权视角完全忽略了。
东区的李家弄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小区原本有三百多户居民,但在食物配给制度实施处期,就有几十个家庭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而饿死。然而,负责该小区的警校女学生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自然淘汰,”她们在报告中如此写道,“那些没有足够意志力的居民自然会被筛选出局,这有利于提高整体人口素质。”
这种冷酷的思想在她们的圈子里得到了广泛认同。她们甚至为自己“严格执行戒严令”而感到自豪,认为这是对上级的忠诚表现。
“看看我们小区,多么安静、有序,”一名女学生在朋友圈炫耀道,“都是因为我们的管理得当。”她发布了一张小区空旷整洁的照片,但照片中没有一个人影,因为大部分居民已经因为饥饿而无法出门,甚至有些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这些女学生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精美的餐食照片,讨论着最新的时尚潮流,仿佛外面的世界一片祥和。在她们的认知里,戒严令不过是一场暂时的管控措施,而不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危机。
“今天尝试了西餐,牛排简直绝了!”一名负责监督食物发放的女学生在朋友圈发文,配图是一块血多汁少的牛排。
这条信息发布的同一天,她负责的小区有五十户家庭因为无法获得食物而全部死亡。但在她的报告中,这些只是被简单地记录为“自然减员”,没有引起任何重视。
这种认知差距不仅存在于警校女学生中,也普遍存在于整个管理层。她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普通人在戒严令下的痛苦。在他们看来,这些痛苦不过是必要的代价,是为了维护秩序而必须付出的。
更为讽刺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管理区域的“成绩”开始被上级表彰。所谓的“成绩”,是指这些区域内没有发生任何违反戒严令的行为,秩序维持得非常好。但实际上,这些区域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大部分居民已经没有力气反抗,甚至已经饿死。
“东区李家弄小区表现突出,维持了最高水准的社会稳定,特予以通报表扬。”这样的表彰在各级会议上频频出现,而没有人去追问这种“稳定”背后的真相。
那些因为单纯的认知差距和特权视角而做出错误决定的警校女学生,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因为“管理得当”而获得了表彰和奖励。她们的履历上多了一笔“危机时期维稳工作表现突出”的记录,为将来的升迁铺平了道路。最残酷的管理者反而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因为她们创造了表面上的“稳定”和“秩序”。这种倒错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层的冷酷态度,使得整个戒严体系变得更加不人道。在这样的环境下,许明一家所在的小区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负责他们小区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学生,与其她同学不同,她是来自一个相对普通的家庭,对底层生活有一些模糊的认识。虽然她也执行着严格的戒严政策,但至少保证了基本的食物发放。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完全断绝食物供应,”陈雯在私下对一位信任的同事说,“这样会让很多人死亡的。”
“这就是目的啊,”同事满不在乎地回答,“筛选掉那些弱者,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人。这是自然规律,适者生存。”
她没有再说什么,但她确保了自己负责区域内的食物配给按时发放,虽然数量有限,质量堪忧,但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点,许明一家和周围邻居们才能暂时生存下来。
在这个关乎生存的基本需求都无法保障的环境中,人性被压缩到了最原始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管理者们,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享受着特权带来的舒适和安全,对自己决定的后果毫无感知,也不需要为此负任何责任。
戒严令实施前,南市的社区主任们只是普通的基层管理人员,负责处理社区内的日常事务——调解邻里纠纷、组织文化活动、传达上级政策等。那时候她们的权力有限,居民们那是对她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礼貌和尊重即可。
然而戒严令改变了一切。短短几天内,这些社区主任的权力被无限放大,她们突然之间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生杀大权。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决定谁能获得食物、获得多少食物,本质上就是决定谁能活下去、谁会死去。这种权力的突然膨胀,对许多人的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主任是许明所在社区的负责人之一。戒严令之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女性,她那时会对居民态度不佳,但也仅限于冷脸或者语气不善。然而,戒严令实施后,她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
“王主任以前也就是脾气差点,”许明的邻居王大爷说道,“现在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眼睛里都是冷的。”
确实,王主任的眼神变得冰冷而空洞,仿佛在看待物品而非人类。她开始利用手中新获得的权力,在极小的事情上为难居民,仿佛在测试自己权力的边界。
“站直了!”她对排队领取食物的人喝道,“弯腰驼背的,看着就烦!”
那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努力地挺直了佝偻的脊背,但年龄和疾病让他无法完全站直。王主任冷笑一声:“不合格,回去吧,今天没有你的份。”
老人的眼中满是绝望,但他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地离开队伍。在他身后,其他居民低着头,不敢有任何表示,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驱逐的人。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王主任似乎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她的脸上经常浮现出一种奇怪的微笑,那是一种掌控他人命运的快感。这种快感让她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她开始创造各种规则,只为了看到居民们挣扎的样子。
“今天只有能背出戒严令全文的人才能领到食物,”她突然宣布,看着排队的居民们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怎么?不会背?那就证明你们不够重视戒严令,不配获得食物。”
居民们开始慌乱地互相传授戒严令的内容,但戒严令全文有数千字,普通人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记住。王主任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明显。
“开个玩笑而已,”半小时后,她突然改口,“今天只要会唱《戒严之歌》就行。”这是一首近期才创作的歌曲,大多数人都没听过。
这种捉弄在王主任看来可能只是无伤大雅的“游戏”,但对于饥肠辘辘的居民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折磨。每一次规则的改变,都可能意味着一天、两天,甚至更长时间的挨饿。
许明的父亲在一次领取食物时,因为弯腰系鞋带而被王主任认为“不够恭敬”,结果被罚站了两个小时,才被允许领取食物。而那时,分发即将结束,很多食物已经被分完,他只能获得比平时更少的配给。
“以前她最多就是脸色难看,现在动不动就要你的命,”许明父亲回家后低声说道。
王主任并非个例。在南市的许多社区,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些曾经普普通通的社区主任,突然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没有任何制衡机制,导致许多人彻底迷失了自己。当一个人突然获得巨大权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效应——她们开始相信自己高人一等,认为规则不适用于自己,对他人的痛苦变得麻木。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权力滥用得到了上级的默许,甚至是鼓励。在戒严令的框架下,“维持秩序”和“执行力度”成为评价基层管理者的主要标准,而居民的实际处境则被完全忽视。
“听说刘主任因为拒绝了一半以上的领取申请,被评为'戒严模范',”一位社区工作人员私下透露,“现在大家都在比谁更狠,这样才能得到表彰。”
在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下,权力滥用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成为了升迁的途径。社区主任们开始比拼谁更能“严格执行戒严令”,谁更能“维护社区稳定”。而这些华丽辞藻的背后,是居民们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
有些社区主任甚至开始针对那些曾经与自己有过冲突的居民。在正常时期,这些小矛盾最多导致一些口舌之争,但在戒严令赋予的权力下,它们变成了足以致命的武器。
“李家以前和我拌过嘴,”一名社区主任在私下聚会时炫耀道,“现在看他们还敢不敢。两周了,一粒米都没给他们。”
在座的其他主任们笑了起来,仿佛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不是关乎一个家庭生死的决定。在她们的笑声中,李家的老人已经因为饥饿而卧床不起,年幼的孩子则整日啼哭,却无人理会。
许明一家相对幸运,因为他们之前与社区主任没有太多交集,没有成为特别针对的对象。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每一次领取食物的场合,确保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会激怒这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
“你知道吗,张主任以前只是个文件整理员,连说话的机会都很少,”一位居民回忆道,“现在她说一句话,几百个人都要抖三抖。”
“以前我们至少可以抱怨几句,”许明在家低声说道,“现在连叹气都不敢太大声,生怕被认为是'情绪不稳定',下次就没有食物了。”
在南市各个社区的食物分发点,一种新的现象开始出现——选择性分配。社区主任们不再仅仅是随意为难居民,而是开始有针对性地拒绝特定家庭的食物申请。这种做法并非基于任何官方政策或规定,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好恶和报复心理。
潘主任站在发放台上,俯视着排队的居民。她穿着那双黑色的高跟鞋,站姿傲慢,脚下随意踩着几个食物包,仿佛那不是救命的口粮,而只是无关紧要的垫脚物。锋利的鞋跟已经刺破了其中一个包装,白色的米粒从破口处缓缓渗出,在地上形成一小堆。她注意到了,但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轻轻转动脚踝,让鞋跟更深地陷入包装中。
“王家?”她故意拖长了声音,“让我查查记录。”身体重量随意地压在那个被踩稀烂的食物包上,几乎能听到包装进一步撕裂的声音。
她装模作样地翻看手中的名单,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她对每个家庭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不过是一种拖延的把戏,一种展示权力的方式。
“啊,抱歉,”最终她抬起头,脸上带着假惺惺的遗憾,“今天的食物已经发完了。你们下周再来吧。”她说这话时,脚下踩着的食物包已经完全变形,米粒四散而出。
王家的代表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潘主任脚下那些被踩踏的食物包上,然后又看向她身后不过两米远的地方。那里堆积如山的食物包清晰可见,上百个塑料袋整齐地摞在一起,食物就在那里,触手可及,却被一句话设置了无形的屏障。
“潘主任,”他颤抖着声音说道,指了指那堆食物包,“可是那里还有很多食物...我们一家已经三天没有食物了,孩子们快撑不住了...”
潘主任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食物堆,然后转回来,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冷酷。“我说了,食物发完了。”
她一字一顿地说,目光中闪烁着某种报复的快感。她故意侧身,让他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那些食物包,仿佛在炫耀自己拒绝的权力。
“求求您,”王家的人跪了下来,额头触地,眼睛仍然盯着那堆近在咫尺却不可触及的食物包,“就给我们一点点也行,哪怕是一小袋米..”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潘主任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她转身拿起一个食物包,在他面前晃了晃,然后重新放回堆中,“质疑戒严令?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
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连连磕头道歉。但潘主任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她继续施压:“也许我应该向上级报告,说你们家有反对戒严令的倾向。你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吧?”
这个威胁让他彻底崩溃,他不停地磕头,祈求原谅。周围的居民都低着头,不敢出声,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最终,潘主任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下周再来吧,”她说,“如果还有食物的话。”潘主任脚下踩得正是王家人的命脉,而此时正被鞋底如同垃圾一样踩在脚下,至于王家能否活过一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以后真的是否能在潘主任的鞋底下领取救命的食物仍是个谜。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脸上写满了绝望。他缓缓离开队伍,背影显得无比孤独而无助。而潘主任已经开始叫下一家的名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王家曾经在戒严前因为潘主任的一次工作失误发了一下牢骚,尽管那只是一件小事,但在潘主任的心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在她决定要让王家付出代价。
然而当这些家庭被告知“食物已经发完”时,他们眼前就是证据确凿的谎言。每个分发点的后方都堆积着大量的食物包,有些甚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社区主任们往往就站在这些食物堆上,她们来回走动时,尖细的鞋跟不断刺破包装,但她们对此视而不见,甚至看起来颇为享受这种践踏的感觉。
“我亲眼看到潘主任告诉食物发完了,”一位居民透露,“当时她就站在食物堆上,那双高跟鞋深深陷入一个米袋中,米粒从破洞里向外涌,撒了一地。孩子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食物,嘴角还流着口水。最可笑的是,刘主任说完'没有食物'后,走下台阶时还踢翻了一包面粉,包装完全破裂,粉末四散。她看都没看一眼,就像踢到了一块石头。”这种公然的、赤裸裸的权力展示,许多居民感到绝望和无助。谎言不需要掩饰,因为说谎者知道,即使谎言被戳穿,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而且她特别喜欢在分发食物时穿一双带有金属尖跟的高跟鞋,专门用来踩踏食物包。工作人员会在高台上堆起食物包,她则站在这些包装上方,俯视着排队的居民。她故意用鞋跟在包装上碾压,让底层的米粒和面粉渗出来,形成一片狼藉。然后她会指着那些被她踩坏的食物包,宣布这些是她赐予的食物让居民们心怀感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居民开始尝试各种方式来讨好社区主任。有人送礼,有人提供服务,有人甚至出卖邻居的信息,只为确保自己家能够按时领到食物。社区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互相猜忌和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