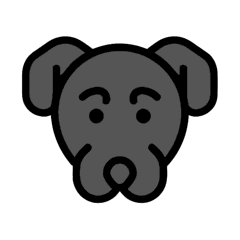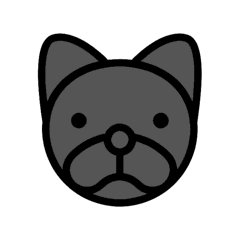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缅怀》
百合短篇原创
最后一丝写作自信也在这篇消耗光了,以后有缘再见吧。
# 缅怀
文/人仿
我看着那只脏兮兮的三花狼吞虎咽地吃完地上的火腿肠,坠着硕大的腹部舔起毛来,忍不住伸手摸摸那颗毛茸茸的脑袋。它并不在意,耳朵抖了抖,继续舔它的毛。
天空阴沉得厉害,云压得很低,面前老旧的居民楼像一座没人祭扫的墓碑,阴曈曈地罩着我,张开它黑漆漆的大口,等待我自投罗网。
闹钟响了,我站起身,深深吸了一口气,握住脖子上的吊坠,迈步走进单元门口。楼道里很昏暗,门上和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一层叠一层。水泥台阶踏起来咚咚响,在安静的楼道里很扎耳。
我数着楼层,来到一扇防盗门前。样式过时的门上装着新潮的电子锁,我按了按上面门铃的标志,里面响起音乐声。过了几秒,门打开了,里面探出一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
“你找谁?”她问。
“是冷柔大人吗?我是微信上预约过的。”我说。
“你就是人仿?我还以为你是个男的。我不是女同,你回去吧,定金回头我微信退给你。”冷柔作势要关门。
“等一下!”我赶紧扒住门边,把准备好的话术一股脑说出来,“就一次可以吗?我女朋友是个s,她最近嫌弃我当不好m,想要分手,所以我才背着她出来找你,想学学怎么做合格的m。你就当帮帮我好吗?”
冷柔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在我的吊坠上停留了一会,撇撇嘴,说:“有个漂亮的女奴玩玩也行,我去换个衣服,你跪在门口等着吧。”
我看着冷柔砰地一声关上门,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不能耍滑头,她可能正在猫眼里看着我。楼道里很安静,静得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嗵嗵的,很快。
我把手伸进口袋,那柄小巧精致的弹簧刀依然静静地躺在最深处,这很好。我握紧它,想象着把它捅进冷柔心脏时的场景。屋子里传出高跟鞋的声音,我松开小刀,把它往更深的地方塞了塞——现在还没到用它的时候,她还没有忏悔。
门开了,冷柔换了一身漆皮的女王装扮,染成浅红酒颜色的大波浪长发盖住了她的肩膀,纤细的锁骨下,硬质的皮革束腰托起一对比我大得多的乳房,在她腰身上勾勒出诱惑的曲线。我开始明白雪莉为什么会选择她了。
“进来吧。”冷柔斜倚在门框上,双腿交叉着,堪堪遮住一半屁股的漆皮内裤在三角区挤出褶皱,泛着条纹状的白光。
我从她身侧爬进屋子。那是个狭小的屋子,陈年的烟味和女人的香水味一起,侵刻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即使打开窗户通风也不会散去。屋子里的门都关着,冷柔关上门,跨过我的头,走进客厅。我跟过去,她坐到一张褪色的布沙发上,用漆皮大腿靴的靴尖点点地面。
我爬过去,低下头。她的靴子擦得很亮,靴面上扭曲地映着我的身影,脚腕处有一些褶皱,鞋跟大概有12厘米。很明显,这不是一双用来走路的靴子,而是一件“床上用品”。
“抬头,看着我。”她温柔地捏住我的下巴,引导我把头放到她穿着黑丝的大腿间。“说说吧,你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没办法体会到m的心态,我女友说我都是在逢场作戏,没有进入‘真正的m的状态’,让她每次调教和做爱都是草草收场。”我说。
“不是我说你女朋友的坏话,这应该怪她,她没有让你真正体会到做m的乐趣。你没体会过这种乐趣,自然不会有热情去把自己放到m的心态中去。”她用涂着冷峻的黑色指甲油的手指,温柔地磨蹭我的脸颊。
“那……”
“别担心,”她将大拇指插入我的嘴巴,向旁边轻轻扯开我的嘴唇,“我会教你如何感受m的乐趣的。”她推开我,“好了,先去把衣服脱了。”
“内衣也脱吗?”我问。
“当然。”她从茶几上拿来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好好体会脱衣服时的羞耻感。”淡蓝色的烟雾伴随着话语,从她涂了深红色口红的嘴唇间,螺旋着逃向空中。
我脱下鞋袜,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捏着卫衣的口袋,脱掉了它,然后又解开了牛仔裤的搭扣,在冷柔的吐烟声中拉开了拉链。金属拉链发出令人羞耻的声音,伴随着细微的布料摩擦声,我的双腿摆脱了坚硬的帆布束缚。而后,我犹豫起来。
“衣服放到这来。”冷柔拍拍沙发的边缘,我把衣服堆在沙发上,把卫衣的口袋朝外。
“呃……”纵使我什么也不想说,代表抗拒的单调音符还是从喉咙间泄露了出来。
“先脱bra。”冷柔淡淡地命令道。
我的意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自动操控我的手伸到背后,解开了胸罩,又脱下了内裤。摘下吊坠的时候,我才苏醒过来,连忙用胳膊挡在胸前。
“手放下。”她说。我的手放下了。
她一面抽烟,一面用她那双能吸走人灵魂的黑色眸子,欣赏我的裸体,用人文主义画家在艺术馆里,观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的那种方式。
嗡,嗡,屋子里响起手机振动的声音。冷柔找了找,从沙发缝隙里翻出一个手机,随意瞟了一眼,关了静音。
“备用机,没事的。”或许是看到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她说道。
刚刚的插曲吹散了空气中的暧昧和羞耻,氛围变得像放凉了的泡面一般的软烂无味。冷柔从画廊里信步而行的艺术家,堕成了普通的情趣女王。而我也从一只瑟瑟发抖的待宰羔羊,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裸体女人。
“把内衣放过来吧,我们开始。”冷柔打破尴尬。
我把内衣和吊坠放到衣服上面,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吊坠处于正中间,最高的地方,像只眼睛,注视着四周。而我真正的眼睛,则被冷柔用一个皮质的眼罩遮盖了。
“怎么样,难受吗?”冷柔调了调眼罩的位置。
眼前一片漆黑,刚刚还在眼前的家具以极快的速度退远了,退到了无穷远的地方,隐没在无限的黑暗里。我忍不住抬手摸了一下右前方,我记得那是沙发的方向。但什么都没摸到。
“不难受,就是有点……不适应。”我说。
有什么东西凑了过来,一股热热的气流吹进耳洞,“放松,把身体交给我。”冷柔用气音,轻轻在耳边说道。
接下来,我听到嘀的一声,然后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一股冰凉的冷气吹到我的背上,激起一片汗毛。空调?她为什么在这种有点凉的阴天开空调?
“有点冷。”我仰起头,冲着印象里她的位置说。
没有回音。
“冷柔?”我呼唤道。
没有回音。
空调的风力加强了,冷气流像沙丁鱼群一样盘绕着我的身体,钻过我的腋下和阴部,在躯干上游弋。我感觉越来越冷,打了个哆嗦。
忽然,我听到皮革摩擦的吱吱声,一只温热的手掌贴上了小腹,按在丹田的位置。我感受着那股热力渗透皮肤,扩散到内脏中去,它逐渐向上游移,经过我的双乳之间,掠过脖子和下巴,最终离开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有些失落,失去了那一点温暖,我又孤零零地回到冷气中了。
好在,没过几秒钟,冷柔的手又回来了。我能想象到她指尖的黑色指甲油反着光,抚在我的后颈上,沿着脊椎一路向下摸索,带起一溜若隐若现的痒和酥麻,最后摸进股沟。我的臀不禁一缩,接着就感受到她的手指在抽离。还没等我想明白,胳膊已经抬了起来,去抓她的手。
我的胳膊打在她的胳膊上,我反手抓住她的手腕,将她的手拉到我的胸口。“冷。”我说。
冷柔把我推倒,身子压了上来。她撩开垂在我脸上的她的发梢,我能感受到她温热的鼻息吹在我脸上。
“马上就热起来了。”她说。我闻到她唇间吹出香烟爆珠里的薄荷香气。
唇角印上来两片柔软的东西,她用舌头探进我的口腔。那片潮湿黏腻的东西在我口腔中画圈,像是一只章鱼脚,在各个角落留下痕迹,和我的舌头贴在一起,互相交缠、蠕动。她向我口中呵出一股潮湿的雾气,附着在口腔内壁上,作为她来过的签名。
她用膝盖顶住我的阴部,两片外阴唇受到皮革的挤压,在光亮的漆皮上留下浅浅的水渍,慢慢变形,向两边分开,露出那条淫靡的缝隙。光滑的皮面轻轻摩擦我的阴唇,扯动阴蒂,一点快感像森林里浮现的萤火虫,从全身的血液中冒出来,顺着血管循环到四肢百骸。
“嘶……”我轻轻抽了口气,脚背不自觉地绷直了,脊背也向上反弓起来。
“唔嗯……”她的唇更紧实地压上来,堵住了我的嘴。我们两个的鼻息混在一起,搅起湍流,吹过我的脸颊。
逐渐燃起的欲火驱散了冷意,我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不行,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对……”我轻轻推开冷柔。
“什么?”她问我。
“不是这种感觉……”我说。
她狠狠咬了一下我的嘴唇,起身离开。冷风直直地吹在我的肚子和乳间,我打了个寒颤。她坐到沙发上,翻了个白眼,翘起腿,用小女孩看到带刺毛毛虫的嫌恶眼神看着我。
“那你想要什么感觉啊,大小姐?”冷柔啪地点上一支烟。
“我也不知道,反正这种温情的、像普通恋爱般的不行。”我说。
“行了,别撒谎了。”
“什么?”
“你就不是个m,你一点m的倾向都没有,你也没有什么s女友。”她把烟在玻璃茶几上磕磕,就像法官在宣判时敲木槌那样。
“的确。”
“说吧,为什么撒谎。”
“你不是也撒谎了吗?说自己不搞女同,梳妆台上却放着秒潮和双头龙。”我说。
“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比起女m,男m的钱要好赚得多。”
“我也只是不想被当成找茬的。我女友其实是个m,我是来学怎么做s的。”
“哦?”她的上半身向我这边探过来,“你通过被调,学怎么做s?”
“掌握m的感受才能更好地调教。”
“我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调教女s的一天。”她站起来,带着好奇和贪婪,盯着我看,“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兴奋、更残忍,你想个安全词吧。”
“不需要安全词。”我说。
“好好好,我就喜欢你这样桀骜不驯的。你越高傲,跪在我脚底下哀嚎和求我的时候我就越爽。”冷柔说着,拿来一条绳子。
她让我趴下,然后踩住我的背。纤细的靴跟戳得很疼,我能想象到它刻着防滑纹的橡胶帽在她刻意的踩压下,陷进我的皮肤,在上面印上规整的方格印记,以及灰黑色的尘土。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捉鬼游戏。”她用麻绳把我的手腕和脚腕捆在一起,然后拿了一个口球塞进我的嘴里,“我会不断鞭打你,直到你用手摸到我为止。”
在被捆成驷马的状态下摸到她?我瞪大眼睛,努力向上看,但最高只能看到她大腿靴的顶部,看不到她的眼神,也无从确认她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
啪!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腿外侧炸开,灼烫的痛楚瞬间把我从无谓的期待中扯了出来,很明显她是认真的。我慌忙扭动身体,挥舞手腕,向她示意我的手还被捆着,不可能摸到她。
“怎么,腾不出手来?真可怜。”冷柔一边讥讽,一边再次挥动藤条。
我听到一声哨响,随后是火辣辣的疼痛,好像有人拿盛着热汤的碗底按在我的大腿上。以前为了调教女友,我在自己身上试过鞭子,但那时远比不上现在这样痛。我扭动手腕,绳圈在拉扯中变形,但仍然紧固,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反而深深勒进我的皮肤中。冷柔没有停下的意思,马鞭持续不断地抽在原先的鞭痕上,灼热得像开水一遍遍浇在上面。我高声叫喊,尽力扭动,却在口球和麻绳之下,衰减为轻微的呜呜声和小幅度的蠕动。
我努力转过头,看着摆在沙发上的卫衣,里面有我的小刀,但我现在不可能够到它,也不可能把它暴露在冷柔面前。
冷柔的高跟靴在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她走到我的面前,抬脚踩住我的脸颊,一瞬间,我的眼前只剩下了她泛着光的鲜红靴底。
“唔!”我尝试甩头摆脱她的踩踏,她的腿很沉重,我扭不开。
坚硬的靴底在我脸上碾来碾去,细长的靴跟在我眼前晃动。我像虫子一样在地板上蠕动,忽然有一瞬,我感到手腕外侧的绳子似乎挪动了一点。我尝试重复刚才的动作,似乎把手腕向外侧打开,然后左右旋转,就能把绳子蹭松。
“还抓不到我吗?那我可要换藤条咯。”冷柔说着,用藤条划破空气,发出的声音比马鞭更响亮、尖锐。
下一秒,藤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灼热尖锐的剧痛催动我快速蹭着绳子。我一边大幅扭动身体,徒劳地躲避着必中的鞭挞,一边尽力以最快的速度蹭开了绳子。在冷柔准备再次挥下藤条的前一刻,我抽出手来,握住她包裹在漆皮里的脚踝,在她脚底呜呜叫起来。
“恭喜。”冷柔没感情地说了一句,解开了我的口球。
我的口水流了一地,沾在头发和脸颊上,冰凉又黏腻,十分恶心。我尽力抬起头不去碰那摊口水,大口喘着气。
“你……这是设计好的?”我问。
“当然,这就是个简单的魔术结。”冷柔拿起绳子给我演示,“你看,在打绳结的时候,从圈里多穿过一截三折的绳子,然后把朝里的那一折扭转,从另一边翻回来,就可以做出看着和感觉上都勒的很紧,挣扎不开,但实际上只要往手腕外侧旋转,蹭开绳结的开关,绳结就会自动脱扣解开的魔术结。”
我翻过身,躺着看她。漆皮的比基尼在胯部勒进她的大腿根,一些阴毛从被遮盖的三角地带的边缘露出来,被荡在空中的绳子拨弄着。
随后,冷柔让我站起来,岔开腿,她用一根带棍子的脚镣拷住了我的双脚,让我无法和尚退。然后她拿来一根长绳,在上面打了个粗大的绳结,抵在我的阴部。长期使用产生的毛刺扎在阴唇上,有种过敏的刺痒感。卡好之后,她捋直那根绳子,向上绕过肩膀,再垂下来,环绕住我的胳膊肘。随后,她在我的腰上缠了另一条绳子,然后把肘部的绳圈固定在上面。
“你猜猜我接下来要玩什么?”冷柔一边调整绳子一边问我。
“不知道。”我说。
“真的猜不出来?”她用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像是已经在脑海中脑补出我痛苦的样子了。
“猜不出来……”我犹豫地说。
我的话还没说完,冷柔飞快地抬腿,坚硬的漆皮靴面正中我的阴部。那个平常不小心碰到都会难受很久的地方,突然受到重击,一股令我作呕的疼痛瞬间在下腹爆发,仿佛有个皮球被硬塞进我的肚子,不断充气胀大,挤扁周围的内脏。我的胃像是被一只有力的铁手攥住了,被强迫一抽一抽地收缩,化作干呕涌上喉口。
我夹不住腿,两只手也因为被绳子掣肘而不能去捂,只能弯下腰,踮起脚尖,尽可能地蜷缩起来,绷紧全身的肌肉,来对抗这股比痛经还要恐怖的胀痛。
“这才第一下,就不行了?”冷柔拽住我的头发,迫使我抬起头。“那后面九下怎么办呢?”
我的视野无法聚焦,我看着模糊的她,说不出话,只能扭动肩膀,寻找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舒服姿势。忽然,我感觉到肘部有一块凸出来的绳子,随着动作微微挪动。
原来这也是个魔术结,我按着刚才的步骤一点点松开束缚,但留下最后一点。如果我现在就解开,冷柔一定会重新把我捆上,不如等她踢的一瞬间再挣开,这样还能挡一脚。
“第二下要来咯。”冷柔向后撩起小腿。
我慌忙松开绳结,猛地把手伸向阴部。还没听到皮靴撞击肉体的声音,就感觉一个粗糙的东西破开了阴唇,大力塞进了外阴。捆在阴部的麻绳完全勒了进去,将那道脆弱私密的缝隙扯得变形。
“啊!”我尖叫着,倒在地上,腹肌绷紧。两腿夹不住,手也被束缚在离阴部还有一掌的地方。我看向冷柔,她正看着我大笑。
“这是第二种魔术结,松开之后会重新勒紧。”她笑着说。
“你!”我抽着气,阴部的刺激让我大脑一片空白。
“你不是要学怎么当s吗?”冷柔把纤细的靴跟插进我的嘴里,“这就是当s的第一步,打破奴的认知,让他们惊讶。这样他们才不会只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奉你为主,而是真正从心里感觉到他们是在被你戏弄,意识到自己的意志毫无作用,从而明白你才是局面的掌控者。”
“听说过用细铁链栓象的故事吗?”冷柔继续说,“在象还小的时候,用一根小象无法挣脱的细铁链拴住它,这样即使它长大后轻易就能挣断铁链,也不会去尝试反抗。M也是如此,你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然后你就可以肆意虐待他们了。m会逐渐明白,希望和绝望都掌握在s的手里,只有遵守s的意志,才能获得更好的结局。”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的身体逐渐冷却下来,刚刚出的汗黏在皮肤上,像是有湿滑的舌头把我浑身舔了一遍。再继续下去的话,还没报仇,我就先完蛋了。
我甩头吐出冷柔的鞋跟,问她:“那万一有m真得忍得住不去挡呢?”
“那她就不需要调教了。”冷柔说。
“不,我的意思是,如果她觉得这种程度并不能满足她呢?”
“那你还真倒霉,作为新手s,很怕遇到这种欲求不满的m。”
“你遇到过吗?”
“曾经有过一个,她很疯狂。”冷柔看着手里的藤条,但心神并不在上面。
的确,她很疯狂。我在心中默默点头。
“不过她后来离开了。”冷柔说。
“为什么?调教的时候出事了?”
“不是!”她忽然叫道,随后又收敛为了哀叹般的语气,“她的心不在我这。”
“不在你这?”
“我调教她的时候,见过她肩膀上纹着她前女友的名字,张璇。然后,后来有一天,她忽然说要离开,在最后一次调教的时候,她吸了太多rush,陷入失神状态,在高潮时,她直勾勾地盯着我,嘴里叫的却是张璇。”
“……这样啊。”
“我问她心里想着别人,为什么还来找我。她说她很爱她前女友,但忍不了不和谐的性生活,就跟她前女友商量,分开一段时间,让她想想。她说她心里明白精神依靠和肉体欲望她只能选择一个,所以她决定试验一下到底离开哪个更难受,于是找上了我。”
“嗯……”我一时间不想说话。
“我这么说,是不是感觉她挺渣的?”冷柔问。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她把玩手里的藤条。
“但我就是没法讨厌她,我太爱她了。”她说。
“爱到要杀了她?”我忍不住出言讥讽。
冷柔愣了一下,但马上回过神来,叫道:“当然不是!我又不是病娇!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变态的想法!”
“因为我的女友就是这样死的。”
“哪样?”
“被一个疯狂爱她的人杀了,警方说是意外身亡,但我不相信那些自甘冒险之类的屁话。”
“你觉得自己比警察还厉害?”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你女友都死了,你还来我这干什么?”
“缅怀她,我想知道她一直在追求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我想体会最激烈、最痛苦的东西。”
“我不玩见血和永久伤害的。”
“其他的也行,比如电击啥的。”
“我没有电击。”
“那个电线不是吗?还连着电压表。改装的?”我冲客厅角落蒙着黑布的那堆东西扬扬头,那黑布的角落露出了一些电线。
“那个是坏的。”冷柔的声音很冷漠。
“我可以加钱。”
“不是钱的问题。”
“你不会用出过问题吧?”我说。
“没有!”她高声说,“你可别后悔!”
“我说了,我是来缅怀的,在感受到她的感受之前,我不会退缩。”我盯着她的眼睛。
冷柔没有说话,她解开我的绳子,让我靠到墙上的X形架上,开始一轮新的捆绑。她先把绳子在我的手腕上松松饶了两圈,然后转到背面去连接背上和腿上的绳子,拽紧。然后把电极贴在我的身上,一对贴在大腿内侧,一对贴在侧腹。
接着,她插上插头,按动开关。随着继电器闭合的清脆喀哒声,皮肤表面传来一点微麻的感觉。冷柔扭转按钮,电压表上的数字逐渐增大,酥麻的感觉越来越大,我的肌肉开始不自觉地跳动起来,随后变成控制不住的抽搐。
“你就是张璇吧?我认得你的吊坠,她戴过。”她问。
“你,就是,用这个,杀了她,吧?”我反问,声音颤抖得厉害。
“我没有杀她,那是意外。”她的声音异常冷静。
“你知道,她有,心脏病。她,曾经,跟我说过,终于,找到一个,能接受,她有心脏病的,新伴侣。所以,你用这个,能突破安全电压,的电击,电死了她。”我用尽力气,一顿一顿地说。
“是啊,不过我承认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警察已经结案了,她是自甘冒险。”
“自首吧。”我对她说。
“你把我逼到这份上,对你有什么好处?她不是也抛弃你了?”
“我和你,不一样。”我说。
“确实,”她把电压旋钮向右拧,电压表上的数字变成刺目的红色,“我是活人,而你是死人。你不是想缅怀吗?现在你马上就要尝到和她一样的死法了。”
我的全身开始剧烈抽出,电极似乎长出了铁刺,扎进我的皮肤里,随后又变成烙铁,灼痛和刺痛一齐迸发。我努力和电流争夺肢体的控制权,扭动手腕,挣开绳子。
“你怎么?!”冷柔往后退了一步。
我扯掉身上的电极,强撑着身体,大口喘着气,勉强保持直立。
“多亏了你的教导,你绕到背后的时候,我在手腕上打了魔术结。”我看着她下意识把藤条举在胸前,一步步朝她逼近,“感到惊讶了?打破认知了?那是不是说明我现在可以进入到第二步,肆意虐待你了?”
“你别过来!”她左右挥舞藤条,抽在空气上。
我和她在客厅里对峙,慢慢绕着圈。我离沙发越来越近,在贴近我的衣服的时候,我迅速抽出弹簧刀,冲到冷柔怀里,把锋利的刀刃比在她脸上。
“别动!不然你的脸就要开花!”我呵斥她。
“我不动……不动……”她扔掉藤条,砸在我脚面上。
我推倒她,骑坐在她身上,用地上的绳子把她的手腕捆在一起,绕过阴部,再捆到腰上。然后我暂时放下小刀,双手把她拖到X形架上,让她趴在地上,小腿竖起,然后用另一根绳子把小腿并拢,和架子捆在一起。
“录音我会交给警察的,很快就会有警察上门‘解救’你。”我穿好衣服,戴上吊坠,冲她展示了一下我的录音笔,然后开门出去。
我在门外默数着,数到十二的时候,我知道冷柔发现了我故意留在地上的小刀,因为我听到门后传来她的惨叫。魔术结的确是个好发明。
天空阴沉得厉害,云压得很低,面前是一座没人祭扫的墓碑,阴曈曈地立在草地上。
“你没告诉过我,你离开后在身上纹了我的名字,我差点就要以为只有我是个怀旧的人,会一直戴着你的吊坠。”我摸着吊坠,对她说。“可惜我到现在依然对sm没有兴趣,不能体会到你的感受。不过你之前一直说想喝我的圣水,我嫌脏从来没同意过,今天我给你带来了。”
我拧开那瓶淡黄色的液体,洒在墓前的草坪里,那些水分很快渗入土壤,消失不见。
我在她的墓前放下一束花,随后起身离开。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 缅怀
文/人仿
我看着那只脏兮兮的三花狼吞虎咽地吃完地上的火腿肠,坠着硕大的腹部舔起毛来,忍不住伸手摸摸那颗毛茸茸的脑袋。它并不在意,耳朵抖了抖,继续舔它的毛。
天空阴沉得厉害,云压得很低,面前老旧的居民楼像一座没人祭扫的墓碑,阴曈曈地罩着我,张开它黑漆漆的大口,等待我自投罗网。
闹钟响了,我站起身,深深吸了一口气,握住脖子上的吊坠,迈步走进单元门口。楼道里很昏暗,门上和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一层叠一层。水泥台阶踏起来咚咚响,在安静的楼道里很扎耳。
我数着楼层,来到一扇防盗门前。样式过时的门上装着新潮的电子锁,我按了按上面门铃的标志,里面响起音乐声。过了几秒,门打开了,里面探出一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
“你找谁?”她问。
“是冷柔大人吗?我是微信上预约过的。”我说。
“你就是人仿?我还以为你是个男的。我不是女同,你回去吧,定金回头我微信退给你。”冷柔作势要关门。
“等一下!”我赶紧扒住门边,把准备好的话术一股脑说出来,“就一次可以吗?我女朋友是个s,她最近嫌弃我当不好m,想要分手,所以我才背着她出来找你,想学学怎么做合格的m。你就当帮帮我好吗?”
冷柔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在我的吊坠上停留了一会,撇撇嘴,说:“有个漂亮的女奴玩玩也行,我去换个衣服,你跪在门口等着吧。”
我看着冷柔砰地一声关上门,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不能耍滑头,她可能正在猫眼里看着我。楼道里很安静,静得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嗵嗵的,很快。
我把手伸进口袋,那柄小巧精致的弹簧刀依然静静地躺在最深处,这很好。我握紧它,想象着把它捅进冷柔心脏时的场景。屋子里传出高跟鞋的声音,我松开小刀,把它往更深的地方塞了塞——现在还没到用它的时候,她还没有忏悔。
门开了,冷柔换了一身漆皮的女王装扮,染成浅红酒颜色的大波浪长发盖住了她的肩膀,纤细的锁骨下,硬质的皮革束腰托起一对比我大得多的乳房,在她腰身上勾勒出诱惑的曲线。我开始明白雪莉为什么会选择她了。
“进来吧。”冷柔斜倚在门框上,双腿交叉着,堪堪遮住一半屁股的漆皮内裤在三角区挤出褶皱,泛着条纹状的白光。
我从她身侧爬进屋子。那是个狭小的屋子,陈年的烟味和女人的香水味一起,侵刻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即使打开窗户通风也不会散去。屋子里的门都关着,冷柔关上门,跨过我的头,走进客厅。我跟过去,她坐到一张褪色的布沙发上,用漆皮大腿靴的靴尖点点地面。
我爬过去,低下头。她的靴子擦得很亮,靴面上扭曲地映着我的身影,脚腕处有一些褶皱,鞋跟大概有12厘米。很明显,这不是一双用来走路的靴子,而是一件“床上用品”。
“抬头,看着我。”她温柔地捏住我的下巴,引导我把头放到她穿着黑丝的大腿间。“说说吧,你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没办法体会到m的心态,我女友说我都是在逢场作戏,没有进入‘真正的m的状态’,让她每次调教和做爱都是草草收场。”我说。
“不是我说你女朋友的坏话,这应该怪她,她没有让你真正体会到做m的乐趣。你没体会过这种乐趣,自然不会有热情去把自己放到m的心态中去。”她用涂着冷峻的黑色指甲油的手指,温柔地磨蹭我的脸颊。
“那……”
“别担心,”她将大拇指插入我的嘴巴,向旁边轻轻扯开我的嘴唇,“我会教你如何感受m的乐趣的。”她推开我,“好了,先去把衣服脱了。”
“内衣也脱吗?”我问。
“当然。”她从茶几上拿来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好好体会脱衣服时的羞耻感。”淡蓝色的烟雾伴随着话语,从她涂了深红色口红的嘴唇间,螺旋着逃向空中。
我脱下鞋袜,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捏着卫衣的口袋,脱掉了它,然后又解开了牛仔裤的搭扣,在冷柔的吐烟声中拉开了拉链。金属拉链发出令人羞耻的声音,伴随着细微的布料摩擦声,我的双腿摆脱了坚硬的帆布束缚。而后,我犹豫起来。
“衣服放到这来。”冷柔拍拍沙发的边缘,我把衣服堆在沙发上,把卫衣的口袋朝外。
“呃……”纵使我什么也不想说,代表抗拒的单调音符还是从喉咙间泄露了出来。
“先脱bra。”冷柔淡淡地命令道。
我的意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自动操控我的手伸到背后,解开了胸罩,又脱下了内裤。摘下吊坠的时候,我才苏醒过来,连忙用胳膊挡在胸前。
“手放下。”她说。我的手放下了。
她一面抽烟,一面用她那双能吸走人灵魂的黑色眸子,欣赏我的裸体,用人文主义画家在艺术馆里,观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的那种方式。
嗡,嗡,屋子里响起手机振动的声音。冷柔找了找,从沙发缝隙里翻出一个手机,随意瞟了一眼,关了静音。
“备用机,没事的。”或许是看到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她说道。
刚刚的插曲吹散了空气中的暧昧和羞耻,氛围变得像放凉了的泡面一般的软烂无味。冷柔从画廊里信步而行的艺术家,堕成了普通的情趣女王。而我也从一只瑟瑟发抖的待宰羔羊,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裸体女人。
“把内衣放过来吧,我们开始。”冷柔打破尴尬。
我把内衣和吊坠放到衣服上面,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吊坠处于正中间,最高的地方,像只眼睛,注视着四周。而我真正的眼睛,则被冷柔用一个皮质的眼罩遮盖了。
“怎么样,难受吗?”冷柔调了调眼罩的位置。
眼前一片漆黑,刚刚还在眼前的家具以极快的速度退远了,退到了无穷远的地方,隐没在无限的黑暗里。我忍不住抬手摸了一下右前方,我记得那是沙发的方向。但什么都没摸到。
“不难受,就是有点……不适应。”我说。
有什么东西凑了过来,一股热热的气流吹进耳洞,“放松,把身体交给我。”冷柔用气音,轻轻在耳边说道。
接下来,我听到嘀的一声,然后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一股冰凉的冷气吹到我的背上,激起一片汗毛。空调?她为什么在这种有点凉的阴天开空调?
“有点冷。”我仰起头,冲着印象里她的位置说。
没有回音。
“冷柔?”我呼唤道。
没有回音。
空调的风力加强了,冷气流像沙丁鱼群一样盘绕着我的身体,钻过我的腋下和阴部,在躯干上游弋。我感觉越来越冷,打了个哆嗦。
忽然,我听到皮革摩擦的吱吱声,一只温热的手掌贴上了小腹,按在丹田的位置。我感受着那股热力渗透皮肤,扩散到内脏中去,它逐渐向上游移,经过我的双乳之间,掠过脖子和下巴,最终离开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有些失落,失去了那一点温暖,我又孤零零地回到冷气中了。
好在,没过几秒钟,冷柔的手又回来了。我能想象到她指尖的黑色指甲油反着光,抚在我的后颈上,沿着脊椎一路向下摸索,带起一溜若隐若现的痒和酥麻,最后摸进股沟。我的臀不禁一缩,接着就感受到她的手指在抽离。还没等我想明白,胳膊已经抬了起来,去抓她的手。
我的胳膊打在她的胳膊上,我反手抓住她的手腕,将她的手拉到我的胸口。“冷。”我说。
冷柔把我推倒,身子压了上来。她撩开垂在我脸上的她的发梢,我能感受到她温热的鼻息吹在我脸上。
“马上就热起来了。”她说。我闻到她唇间吹出香烟爆珠里的薄荷香气。
唇角印上来两片柔软的东西,她用舌头探进我的口腔。那片潮湿黏腻的东西在我口腔中画圈,像是一只章鱼脚,在各个角落留下痕迹,和我的舌头贴在一起,互相交缠、蠕动。她向我口中呵出一股潮湿的雾气,附着在口腔内壁上,作为她来过的签名。
她用膝盖顶住我的阴部,两片外阴唇受到皮革的挤压,在光亮的漆皮上留下浅浅的水渍,慢慢变形,向两边分开,露出那条淫靡的缝隙。光滑的皮面轻轻摩擦我的阴唇,扯动阴蒂,一点快感像森林里浮现的萤火虫,从全身的血液中冒出来,顺着血管循环到四肢百骸。
“嘶……”我轻轻抽了口气,脚背不自觉地绷直了,脊背也向上反弓起来。
“唔嗯……”她的唇更紧实地压上来,堵住了我的嘴。我们两个的鼻息混在一起,搅起湍流,吹过我的脸颊。
逐渐燃起的欲火驱散了冷意,我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不行,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对……”我轻轻推开冷柔。
“什么?”她问我。
“不是这种感觉……”我说。
她狠狠咬了一下我的嘴唇,起身离开。冷风直直地吹在我的肚子和乳间,我打了个寒颤。她坐到沙发上,翻了个白眼,翘起腿,用小女孩看到带刺毛毛虫的嫌恶眼神看着我。
“那你想要什么感觉啊,大小姐?”冷柔啪地点上一支烟。
“我也不知道,反正这种温情的、像普通恋爱般的不行。”我说。
“行了,别撒谎了。”
“什么?”
“你就不是个m,你一点m的倾向都没有,你也没有什么s女友。”她把烟在玻璃茶几上磕磕,就像法官在宣判时敲木槌那样。
“的确。”
“说吧,为什么撒谎。”
“你不是也撒谎了吗?说自己不搞女同,梳妆台上却放着秒潮和双头龙。”我说。
“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比起女m,男m的钱要好赚得多。”
“我也只是不想被当成找茬的。我女友其实是个m,我是来学怎么做s的。”
“哦?”她的上半身向我这边探过来,“你通过被调,学怎么做s?”
“掌握m的感受才能更好地调教。”
“我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调教女s的一天。”她站起来,带着好奇和贪婪,盯着我看,“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兴奋、更残忍,你想个安全词吧。”
“不需要安全词。”我说。
“好好好,我就喜欢你这样桀骜不驯的。你越高傲,跪在我脚底下哀嚎和求我的时候我就越爽。”冷柔说着,拿来一条绳子。
她让我趴下,然后踩住我的背。纤细的靴跟戳得很疼,我能想象到它刻着防滑纹的橡胶帽在她刻意的踩压下,陷进我的皮肤,在上面印上规整的方格印记,以及灰黑色的尘土。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捉鬼游戏。”她用麻绳把我的手腕和脚腕捆在一起,然后拿了一个口球塞进我的嘴里,“我会不断鞭打你,直到你用手摸到我为止。”
在被捆成驷马的状态下摸到她?我瞪大眼睛,努力向上看,但最高只能看到她大腿靴的顶部,看不到她的眼神,也无从确认她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
啪!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腿外侧炸开,灼烫的痛楚瞬间把我从无谓的期待中扯了出来,很明显她是认真的。我慌忙扭动身体,挥舞手腕,向她示意我的手还被捆着,不可能摸到她。
“怎么,腾不出手来?真可怜。”冷柔一边讥讽,一边再次挥动藤条。
我听到一声哨响,随后是火辣辣的疼痛,好像有人拿盛着热汤的碗底按在我的大腿上。以前为了调教女友,我在自己身上试过鞭子,但那时远比不上现在这样痛。我扭动手腕,绳圈在拉扯中变形,但仍然紧固,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反而深深勒进我的皮肤中。冷柔没有停下的意思,马鞭持续不断地抽在原先的鞭痕上,灼热得像开水一遍遍浇在上面。我高声叫喊,尽力扭动,却在口球和麻绳之下,衰减为轻微的呜呜声和小幅度的蠕动。
我努力转过头,看着摆在沙发上的卫衣,里面有我的小刀,但我现在不可能够到它,也不可能把它暴露在冷柔面前。
冷柔的高跟靴在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她走到我的面前,抬脚踩住我的脸颊,一瞬间,我的眼前只剩下了她泛着光的鲜红靴底。
“唔!”我尝试甩头摆脱她的踩踏,她的腿很沉重,我扭不开。
坚硬的靴底在我脸上碾来碾去,细长的靴跟在我眼前晃动。我像虫子一样在地板上蠕动,忽然有一瞬,我感到手腕外侧的绳子似乎挪动了一点。我尝试重复刚才的动作,似乎把手腕向外侧打开,然后左右旋转,就能把绳子蹭松。
“还抓不到我吗?那我可要换藤条咯。”冷柔说着,用藤条划破空气,发出的声音比马鞭更响亮、尖锐。
下一秒,藤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灼热尖锐的剧痛催动我快速蹭着绳子。我一边大幅扭动身体,徒劳地躲避着必中的鞭挞,一边尽力以最快的速度蹭开了绳子。在冷柔准备再次挥下藤条的前一刻,我抽出手来,握住她包裹在漆皮里的脚踝,在她脚底呜呜叫起来。
“恭喜。”冷柔没感情地说了一句,解开了我的口球。
我的口水流了一地,沾在头发和脸颊上,冰凉又黏腻,十分恶心。我尽力抬起头不去碰那摊口水,大口喘着气。
“你……这是设计好的?”我问。
“当然,这就是个简单的魔术结。”冷柔拿起绳子给我演示,“你看,在打绳结的时候,从圈里多穿过一截三折的绳子,然后把朝里的那一折扭转,从另一边翻回来,就可以做出看着和感觉上都勒的很紧,挣扎不开,但实际上只要往手腕外侧旋转,蹭开绳结的开关,绳结就会自动脱扣解开的魔术结。”
我翻过身,躺着看她。漆皮的比基尼在胯部勒进她的大腿根,一些阴毛从被遮盖的三角地带的边缘露出来,被荡在空中的绳子拨弄着。
随后,冷柔让我站起来,岔开腿,她用一根带棍子的脚镣拷住了我的双脚,让我无法和尚退。然后她拿来一根长绳,在上面打了个粗大的绳结,抵在我的阴部。长期使用产生的毛刺扎在阴唇上,有种过敏的刺痒感。卡好之后,她捋直那根绳子,向上绕过肩膀,再垂下来,环绕住我的胳膊肘。随后,她在我的腰上缠了另一条绳子,然后把肘部的绳圈固定在上面。
“你猜猜我接下来要玩什么?”冷柔一边调整绳子一边问我。
“不知道。”我说。
“真的猜不出来?”她用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像是已经在脑海中脑补出我痛苦的样子了。
“猜不出来……”我犹豫地说。
我的话还没说完,冷柔飞快地抬腿,坚硬的漆皮靴面正中我的阴部。那个平常不小心碰到都会难受很久的地方,突然受到重击,一股令我作呕的疼痛瞬间在下腹爆发,仿佛有个皮球被硬塞进我的肚子,不断充气胀大,挤扁周围的内脏。我的胃像是被一只有力的铁手攥住了,被强迫一抽一抽地收缩,化作干呕涌上喉口。
我夹不住腿,两只手也因为被绳子掣肘而不能去捂,只能弯下腰,踮起脚尖,尽可能地蜷缩起来,绷紧全身的肌肉,来对抗这股比痛经还要恐怖的胀痛。
“这才第一下,就不行了?”冷柔拽住我的头发,迫使我抬起头。“那后面九下怎么办呢?”
我的视野无法聚焦,我看着模糊的她,说不出话,只能扭动肩膀,寻找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舒服姿势。忽然,我感觉到肘部有一块凸出来的绳子,随着动作微微挪动。
原来这也是个魔术结,我按着刚才的步骤一点点松开束缚,但留下最后一点。如果我现在就解开,冷柔一定会重新把我捆上,不如等她踢的一瞬间再挣开,这样还能挡一脚。
“第二下要来咯。”冷柔向后撩起小腿。
我慌忙松开绳结,猛地把手伸向阴部。还没听到皮靴撞击肉体的声音,就感觉一个粗糙的东西破开了阴唇,大力塞进了外阴。捆在阴部的麻绳完全勒了进去,将那道脆弱私密的缝隙扯得变形。
“啊!”我尖叫着,倒在地上,腹肌绷紧。两腿夹不住,手也被束缚在离阴部还有一掌的地方。我看向冷柔,她正看着我大笑。
“这是第二种魔术结,松开之后会重新勒紧。”她笑着说。
“你!”我抽着气,阴部的刺激让我大脑一片空白。
“你不是要学怎么当s吗?”冷柔把纤细的靴跟插进我的嘴里,“这就是当s的第一步,打破奴的认知,让他们惊讶。这样他们才不会只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奉你为主,而是真正从心里感觉到他们是在被你戏弄,意识到自己的意志毫无作用,从而明白你才是局面的掌控者。”
“听说过用细铁链栓象的故事吗?”冷柔继续说,“在象还小的时候,用一根小象无法挣脱的细铁链拴住它,这样即使它长大后轻易就能挣断铁链,也不会去尝试反抗。M也是如此,你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然后你就可以肆意虐待他们了。m会逐渐明白,希望和绝望都掌握在s的手里,只有遵守s的意志,才能获得更好的结局。”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的身体逐渐冷却下来,刚刚出的汗黏在皮肤上,像是有湿滑的舌头把我浑身舔了一遍。再继续下去的话,还没报仇,我就先完蛋了。
我甩头吐出冷柔的鞋跟,问她:“那万一有m真得忍得住不去挡呢?”
“那她就不需要调教了。”冷柔说。
“不,我的意思是,如果她觉得这种程度并不能满足她呢?”
“那你还真倒霉,作为新手s,很怕遇到这种欲求不满的m。”
“你遇到过吗?”
“曾经有过一个,她很疯狂。”冷柔看着手里的藤条,但心神并不在上面。
的确,她很疯狂。我在心中默默点头。
“不过她后来离开了。”冷柔说。
“为什么?调教的时候出事了?”
“不是!”她忽然叫道,随后又收敛为了哀叹般的语气,“她的心不在我这。”
“不在你这?”
“我调教她的时候,见过她肩膀上纹着她前女友的名字,张璇。然后,后来有一天,她忽然说要离开,在最后一次调教的时候,她吸了太多rush,陷入失神状态,在高潮时,她直勾勾地盯着我,嘴里叫的却是张璇。”
“……这样啊。”
“我问她心里想着别人,为什么还来找我。她说她很爱她前女友,但忍不了不和谐的性生活,就跟她前女友商量,分开一段时间,让她想想。她说她心里明白精神依靠和肉体欲望她只能选择一个,所以她决定试验一下到底离开哪个更难受,于是找上了我。”
“嗯……”我一时间不想说话。
“我这么说,是不是感觉她挺渣的?”冷柔问。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她把玩手里的藤条。
“但我就是没法讨厌她,我太爱她了。”她说。
“爱到要杀了她?”我忍不住出言讥讽。
冷柔愣了一下,但马上回过神来,叫道:“当然不是!我又不是病娇!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变态的想法!”
“因为我的女友就是这样死的。”
“哪样?”
“被一个疯狂爱她的人杀了,警方说是意外身亡,但我不相信那些自甘冒险之类的屁话。”
“你觉得自己比警察还厉害?”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你女友都死了,你还来我这干什么?”
“缅怀她,我想知道她一直在追求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我想体会最激烈、最痛苦的东西。”
“我不玩见血和永久伤害的。”
“其他的也行,比如电击啥的。”
“我没有电击。”
“那个电线不是吗?还连着电压表。改装的?”我冲客厅角落蒙着黑布的那堆东西扬扬头,那黑布的角落露出了一些电线。
“那个是坏的。”冷柔的声音很冷漠。
“我可以加钱。”
“不是钱的问题。”
“你不会用出过问题吧?”我说。
“没有!”她高声说,“你可别后悔!”
“我说了,我是来缅怀的,在感受到她的感受之前,我不会退缩。”我盯着她的眼睛。
冷柔没有说话,她解开我的绳子,让我靠到墙上的X形架上,开始一轮新的捆绑。她先把绳子在我的手腕上松松饶了两圈,然后转到背面去连接背上和腿上的绳子,拽紧。然后把电极贴在我的身上,一对贴在大腿内侧,一对贴在侧腹。
接着,她插上插头,按动开关。随着继电器闭合的清脆喀哒声,皮肤表面传来一点微麻的感觉。冷柔扭转按钮,电压表上的数字逐渐增大,酥麻的感觉越来越大,我的肌肉开始不自觉地跳动起来,随后变成控制不住的抽搐。
“你就是张璇吧?我认得你的吊坠,她戴过。”她问。
“你,就是,用这个,杀了她,吧?”我反问,声音颤抖得厉害。
“我没有杀她,那是意外。”她的声音异常冷静。
“你知道,她有,心脏病。她,曾经,跟我说过,终于,找到一个,能接受,她有心脏病的,新伴侣。所以,你用这个,能突破安全电压,的电击,电死了她。”我用尽力气,一顿一顿地说。
“是啊,不过我承认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警察已经结案了,她是自甘冒险。”
“自首吧。”我对她说。
“你把我逼到这份上,对你有什么好处?她不是也抛弃你了?”
“我和你,不一样。”我说。
“确实,”她把电压旋钮向右拧,电压表上的数字变成刺目的红色,“我是活人,而你是死人。你不是想缅怀吗?现在你马上就要尝到和她一样的死法了。”
我的全身开始剧烈抽出,电极似乎长出了铁刺,扎进我的皮肤里,随后又变成烙铁,灼痛和刺痛一齐迸发。我努力和电流争夺肢体的控制权,扭动手腕,挣开绳子。
“你怎么?!”冷柔往后退了一步。
我扯掉身上的电极,强撑着身体,大口喘着气,勉强保持直立。
“多亏了你的教导,你绕到背后的时候,我在手腕上打了魔术结。”我看着她下意识把藤条举在胸前,一步步朝她逼近,“感到惊讶了?打破认知了?那是不是说明我现在可以进入到第二步,肆意虐待你了?”
“你别过来!”她左右挥舞藤条,抽在空气上。
我和她在客厅里对峙,慢慢绕着圈。我离沙发越来越近,在贴近我的衣服的时候,我迅速抽出弹簧刀,冲到冷柔怀里,把锋利的刀刃比在她脸上。
“别动!不然你的脸就要开花!”我呵斥她。
“我不动……不动……”她扔掉藤条,砸在我脚面上。
我推倒她,骑坐在她身上,用地上的绳子把她的手腕捆在一起,绕过阴部,再捆到腰上。然后我暂时放下小刀,双手把她拖到X形架上,让她趴在地上,小腿竖起,然后用另一根绳子把小腿并拢,和架子捆在一起。
“录音我会交给警察的,很快就会有警察上门‘解救’你。”我穿好衣服,戴上吊坠,冲她展示了一下我的录音笔,然后开门出去。
我在门外默数着,数到十二的时候,我知道冷柔发现了我故意留在地上的小刀,因为我听到门后传来她的惨叫。魔术结的确是个好发明。
天空阴沉得厉害,云压得很低,面前是一座没人祭扫的墓碑,阴曈曈地立在草地上。
“你没告诉过我,你离开后在身上纹了我的名字,我差点就要以为只有我是个怀旧的人,会一直戴着你的吊坠。”我摸着吊坠,对她说。“可惜我到现在依然对sm没有兴趣,不能体会到你的感受。不过你之前一直说想喝我的圣水,我嫌脏从来没同意过,今天我给你带来了。”
我拧开那瓶淡黄色的液体,洒在墓前的草坪里,那些水分很快渗入土壤,消失不见。
我在她的墓前放下一束花,随后起身离开。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还是让我拿下一楼吧。
其实写得挺好的,我挺喜欢。
其实写得挺好的,我挺喜欢。
真好看
kingking1234:↑真好看谢谢!
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