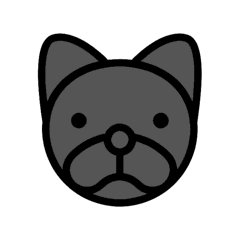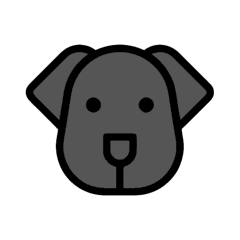爱与平等的伊甸园(4.14)萌新渣作
阶级连载中原创大小姐
1.小云,小云。
江小云是出生在中产家庭,而向来对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不屑一顾的人。他对成金太郎和old money投以同等地鄙视,对此则言必称“下里巴人,俗不可耐”。他会为早年上山下乡一视同仁而欢欣,会对某时期计生委单对“农村户口”“汉族”的屠戮进行义愤填膺地抨击——尽管他的家庭因为前者饱受苦难,他因为后者的区分措施才逃过一劫无事诞生。他痛恨不公,厌恶特权,又时时刻刻生活在不公里。他对奥威尔《动物农场》里“人生来平等,但有的人更平等”的说法忌讳莫深。与此相对的是,他对贫苦人,无论是纯真善良的,还是奸佞狡诈的,均抱以极大地理解和共情。他是深刻认为底层无恶人的,只要是生活贫苦受压迫的人,无论作怎么样的恶,都是可以网开一面宽恕的,可以认为那恶行是受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某鲶鱼东窗事发时,他在微博仿效骆宾王《讨武曌檄》,激扬万字作“讨鲶鱼檄”,以昭彰其对特权嫉恶如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清高态。文毕已是深夜,他扯开窗帘往外瞥一眼,东九区依旧霓虹闪烁,看不见层云遮掩的黯淡月光。他并不知道檄文能不能过审,在以往这种事无所谓的,他只是享受创作的过程,且习惯于顾影自怜。但这次,他暗暗地希冀着,也许某鲶鱼真的会看到他的文字。他当然不愿意去私信鲶鱼,这太卑躬屈膝了。扣上三防电脑的屏幕,江小云躺在床上神思游离。他希望自己一躺下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毕竟创作那篇文章已经使他心力交瘁,他到明天起床之前都打不出一个字,说不出一句话了。换句话说,他把今天近乎所有的精力都赤忱地奉献给了鲶鱼,哪怕是批判。可是他睡不着,他知道还有一件事等着他去做。他决意忘记那事,可是那件事就在他脑子里不紧不慢的等着他,告知他他的供奉仪式还差一个环节,笃定他一定会去完善。辗转反侧之后,他果然在一片黑暗沉寂的房间里坐了起来,兀然掀开了老古董索尼电脑的屏幕,急不可耐地找回鲶鱼大小姐发言的微博页面,那些视底层为蛆虫的,触目惊心的言论。他紧盯着房间里唯一的光亮,目不转睛。不多时他的屌已经涨得难受,他依旧不想解开腰上昨晚系死的带子,他已经为这种事后悔无数次了,可是,倘若他再不解开腰带他的屌就要开始抽搐了。面对着幽幽从窗外吹来的凉风和屏幕上粗鄙暴戾的几行字,想象屏幕外的人是怎么样的颐指气使,江小云的藐视权贵,文人风骨短暂消失在了这个夜晚,他又一次落下粘稠的泪。
江小云的气息到底平稳下来。“我倒不比她差。其一我同样润出来了,日本也是发达国家。其二,嗯,我的索尼三防机,防水性甚于Macbook。”他一番论证得出了他想要的的结论,所谓鲶鱼并不比他高贵。他摩挲着电脑,不禁哑然失笑,或是为这幼稚的想法感到无奈。不过,无论是打标枪,还是拿自己对比鲶鱼的论证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到了明天,他依旧是愤世嫉俗的贫民之友。
然而,距江小云上次吟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现在的他也在吟唱,不过内容却变成了“烛炬帝志,唯死是向”,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在遇见她之前,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在修学业成绩优异,众人对他鞭辟入里的文字的赞许,刺激他的野心膨胀着,他设想日后怎么样大刀阔斧改造社会,怎么样像镰刀收割麦田一样把任何压迫人的人,无论是特权阶级还是旧贵族的残渣余孽通通割成和平民一样高的齐穗,社会再无人上人和人压迫人的行为发生,日本俨然成为“无鱼之白河”。他本人则跟实行改革的松平定信一样,被记载在历史书里给学生们摇头晃脑地背诵,而且是以一个汉人的身份。可惜,可惜,他如此伟大崇高的愿景在遇见她后就溃败作鸟兽散了,结局总不些说不出的滑稽。
那本来应该是个稀疏平常的下午,江小云想。倘若不是中年秃顶大腹便便的校长突然召集大家通知了三校合并的消息,他现在也不至于一想到她膝盖就发软。合校,在当时的他看来是无所谓的,他的才能不会因合校变得平庸,他的前景不会因合校变得阴翳。但他得知三校之正一是赫赫有名的贵族学校时,他还是忧虑一会,并不是担心他会比这些酒囊饭袋还要才疏学浅,而是他对“贵族”的警惕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过,他可以借此便利窥探upper class的奢靡,揭露和批评她们的恶贯满盈,新造一副韩熙载夜宴图。
江小云的身体并不强壮,甚至可以用孱弱形容,当他费力的抱着硕大的书包前往新校舍时,看到了让他口干舌燥的场面。一辆劳斯莱斯停在树荫下,后车门旁跪趴着一个人,车门被打开,另一人手持遮阳伞遮挡住了大部分美妙光景,他只看得到一只十分纤细的包裹着丝袜的小腿缓慢优雅伸出车内,和跪趴的仆人的背部接触的是小巧精致的皮鞋,看不出由来。主仆显然都对此习以为常。江小云对贵族们生活方式的容许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在他笔下钟鸣鼎食已经是罄竹难书罪不容诛程度的奢靡,他对古文的说法深以为然。书里说的,喝仪狄酿的酒是奢靡之举,吃易牙做的饭是穷奢极欲,和南之威行鱼水之欢是穷奢极欲,甚至流连高台、陂池也是穷奢极欲。因此当他看见这一幕时心里忽然受到一阵悸痛,贵族们比他所痛恨的更加罪恶深重。江小云共情那个跪趴在车旁的可怜人,把他认定为他和贵族抗争的盟友。可是当江小云经过劳斯莱斯时,只低着头瞄一眼依旧跪趴在原地形同枯槁的他,江小云迈开的步子就突然像跨台阶一样踩了个空。他错愕的发现,被她当做地毯踩过的人,被他认定为盟友的人,在她悠然踏过的西装上,巴黎世家的标志清晰可见。她不记得有这个人,他就要一直跪到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可见他确实是受压迫者,但是,但是,这怎么能谈得上“贫苦”呢?江小云咽下唾沫,更不抬头,惊魂未定的加速离开。他显然误判了,这样的人不会是他的盟友。可是瞬间他又意识到他的快步走是心虚和不自然的,像鲤趋于庭一样别扭。孔鲤趋庭而过是恐惧孔子的威严,他加速难道是因为惧怕她吗?他对她们从始至终都必须是愤恨的,哪怕一点恐惧也会让他气泄芒针,他必须劝自己相信他不畏惧她们,和她们的鹰犬走狗,尽管她并不在意他的自娱自乐。
但在当时,江小云确实是在恐惧她。他习惯以最坏的形势揣测,他害怕她或许会在前面忽然叫住他,说:“喂,那只支那猪!”倘若发生这种境况,他怎么才能不让他本就颤抖不已的膝盖轰然叩地。他感到莫名地沮丧和烦躁,对自己是否真的有改变如此普遍的人压迫人的现状的伟力产生了不自信。江小云心烦意燥时,总习惯背“心若冰清,天塌不惊”,来了日本也不肯入乡随俗改成数质数,这是腐朽文人凝滞于物的小小傲骨。这样做当然是想把刚才的所见祛除脑外,可惜收效甚微。那只纤细完美的小腿丝毫不讲道理的占据了他的大脑,随意踏在他的思想上作威作福,像烙铁般在他心脏上留下一个滚烫的鞋印。咣!或是巨大书包阻挡视线的缘由,神思游离的他竟没有注意到面前印着循环(MEGURU)哥卡通形象的绿色垃圾桶,几乎一头栽倒在里面。这对他而言实在是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不过还好没有人看到。
“同学,没事吧?”
江小云扶正眼镜抬起头,恰好对上略带笑意的她的视线。
她站在前几米的地方,和他略有一些高度差。
她手执一把繁复纹饰的遮阳伞,银色的长发随风摇曳,红色的瞳孔里焕发着妖冶的光,白皙的过分的皮肤好像不能见光的吸血鬼族一样,身上纯白的礼服和颈上恰到好处的黑色蝴蝶结点缀组成了一副吊诡至极而又姽婳至极的定格画。
他的视线先是在她过分标致宛若为了满足他的xp而生产的圣洁面孔上,但只一秒就好像被灼痛般滑落到她不甚丰满的欧派(◦˙▽˙◦)上,再低到裙摆黑色的束边里掩盖着的吊带丝袜,最后停留在那双把他踩进垃圾桶的罪魁祸首棕色皮鞋上。
“无事,见笑,见笑了。我正是犯了瓜田不纳履的忌讳了,实在贻笑大方。”
他盯住那双精致的鞋子,不敢抬起灼热的头颅,同样灼热的小头却悄然昂首。这样尴尬的场面使他言不过脑地滥用典故,也不考虑对面的人能否理解华夏俚语。
“没事就好。呱甜……你是外国人吗?”
她充满好奇地发问。
“是,不过我来这里不很短的时间了。”
他不太想回答她,可有喙不应声也写在他的社交禁令里,只好避重就轻的回答。
“原来如此。你的日语很熟练呢。嗯~有缘再见,——MEGURU君。”
她眼见他目光躲闪不愿和她对视,只好莞尔一笑,转过身去,无奈的摆摆手遣散了严阵以待的保镖或者仆从们。
“我本来就够引人注目了。”她对他们说。
夸张的公主护卫队给她带来了不少莺莺燕燕,他们围着她,夸赞她的美貌,崇拜她的高贵,作态像无人区三步一叩首的朝圣者一样虔诚。这一幕自然也成了江小云眼里的又一粒沙子,他顿时觉得朱子诚不欺江也: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当然,底层贫苦人是不在其中的,江小云早为他们脑补好了不得不攀炎附势的理由。至于她,江小云想,有一天他会把她挂到路灯上的。他的反抗之心熊熊燃烧着,把她断定为只会压榨民脂民膏的无才无德之人。无才尚可理解,毕竟不能谁都同他一样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少德不可宽恕,她怎么能把人当地毯踩还如此理所应当。江小云依旧对此愤愤不平。他在踌躇满志时,总是记不起主观臆断的害处。
江小云几乎不需要费任何力就能适应新环境,因为他早习惯于做来客。初来异乡时多少还有些惶恐拘谨,鞠躬也不甚标准,被老先生教训过,现在早就轻车熟路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编班级里还是有许多老面孔的,譬如迷恋大欧派的小a,喜欢打galgame的小b,还有…………她?!他料想不到她也和他一个班级,他的窘态是被她一览无余观赏过的,他对她多少有些忌医讳疾。当小a向他窃窃私语被众星捧月般围起来的她的时候,他故作不在意的向那边瞥一眼。
“哦。她的欧派很大吗?那里人太多了看不真切。”
小b狂热的推搡他,说他们竟有幸和一个超级美少女共处一室。
“什么?毕秀金?是指那个戴近视眼镜的雀斑女孩吗?嘛,挺可爱的。”
他刻意装作没听清的样子,随意找了个簇拥在她身边的人敷衍。
“什么啊,江君总不会看不出我说的是谁?”
他当然知道,她太突兀了,不止是美貌,还有看上去就不甚健康的独一无二的气息,任何人初次看到她,心脏都会莫名的刺痛。
“…………我是汉人,和你们的审美总归是有差异的。”
他迟疑一会,然后说。可惜,他的屌貌似不大认同他的说法。
她上台做介绍时,他涣散双目,心脏却砰砰跳个不停。他说她没什么特别的,不必要付诸以额外地关注。
她把名字写到黑板上,她的手指比无尘粉笔还要纤细,粉笔摩擦黑板上的镀膜发出沙沙的声音。她的力气显然不很足,不像讲课的先生那么孔武有力,写字都只能听见砰砰的撞击声。
她说她是“宫泽凛”,希望大家关照她。
他听到沙沙的声音消失了,才聚焦看一眼黑板上的字。她的笔锋相当尖锐,像瑞士军刀剖开他的胸腔,把他心脏上的轻巧俏皮的鞋印暴露出来。所以他咬牙切齿地评价这字不好。他说,写字,尤其是女孩子的字,还是婉转莹润些的好。
流程结束之后,江小云无意识往那边注目,同学们不约而同的聚过去,各怀鬼胎的和她搭讪。哪怕他不想听,他们谄媚的声音还是钻进他的耳蜗。
“宫泽大人,我是成田造船的。宫泽家对日本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个,我们也收到了贵府举办的慈善会的邀请。不胜感激荣幸,期待可以为社会尽些绵薄之力!”
“嗯,是吗?感谢参与。我们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
“是!宫泽家的恩情甚重,我是成田造船的!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话……”
“嗯,好,我记住了。”
“宫泽大人,关于贵府提出的粉末冶金工业新规,我们已经有贯彻执行了,请多多关照!我是中野金属的。”
“明白了,我会向家父转述。”
江小云越听心脏跳的越快,她的权势很盛超过他的预料,他厌恶看到这些人殷勤讨好她的奴才相,因为他总是不自觉的设身处地。他劝自己相信,他的膝盖宁折不弯绝不会像他们一样卑躬屈膝。
他带着复杂的情绪看她,自卑和自负在他心中博弈着,但这次他很难再像面对某鲶鱼时那样找到平衡点。此刻他无比期待放课,只要放课,只要放课,他就不用再受此等煎熬折磨,回家之后有手冲打,有廉价小奶茶喝,他很快会忘记现在的抑郁寡欢。
解放的铃声终于响了,他如释重负呼口气,也体验一次陶潜在回家路上的风飘飘而吹衣。他正欲舟遥遥以轻扬的归家,但不幸她牵着他脖子拴的绳子把他拽回来。
“MEGURU君?噢,应该说是江君。真巧我们又见面了。”
她仿佛发现了挂在他脖子上的金色的狗牌,那上面用可爱的字体镌刻着他的名字。
他颤栗一下,不得不收回迈出去的脚步。
“呃,你是……姓宫泽的吧?幸得偶遭,真熙皞。”
他佯装忘记实际他早默念了数十遍并且烂熟于心的她的姓名,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她。
“江君还真是出口成章呢。总觉得江君之前有往这边看,嗯,果然是错觉吧。”
她逼他承认他在注意她了,可是他偏偏很不情愿承认。承认了不就代表刚刚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在表演吗?然而他避无可避。他咽下唾液,像咽下掺着铁钉的烟丝泡水一样费力。
“是、因为有些在意宫泽同学的外表。宫泽君很漂亮。”
他不愿意和她对视,从身高来说他是比她高,但气势反而弱一头。
“谢谢。但江君能不能抬起头来呢?说话总是盯着人家的鞋子可不太礼貌。”
“啊、好,是、是,抱歉我…………”
他被勒令抬起头来,像被抽了鞭子的驯马一样不情不愿。他的自傲只在执笔时占上风,现在萎缩成她鞋底的一粒尘埃。
“江君,真的很是温良呢。”
她轻轻的感叹,像风吹过银铃,卷过稻田消失在天际。
江小云一阵苦笑,他无奈于自己的怯弱,为她积威之所劫,竟不敢当面质疑批判她草菅人命。他本应横眉冷对千夫指,现在却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很感激你的赞誉,但人不总是而且总不是那样简单的。——王莽也有谦恭未篡时,勾践做为奴作仆时也谨小慎微。”
他前面的话是对她说的,后面的话是对自己说的。现在,对她的软弱是不足可悲的,他将成为第二个王莽勾践。他籍此找回挥毫洒墨创作檄文时的嫉恶如仇。
“江君是勾践吗?”
她的眼睛里是可爱的迷茫,让他有些柔情泛滥,他警戒自己她是蹂躏底民的恶魔。
“我没有那样的魄力。”
江小云不假思索的否定,不想被她窥探过多想法。
“唔,这样吗?江君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
她还是笑吟吟的,把他的敌意消融回春。
“我不会去做谁的奴仆,也不会卧薪尝胆,更不会有勇气杀回马枪,倘我是勾践,早在被俘虏前就学不肯过江东的霸王自刎归天了。”
他自嘲地说,但这和他真实想法相去甚远,不知道能不能让她相信。他正像给齐宣王吹芋的南郭先生一样心虚。
“原来如此,江君啊,正像幽静的兰花一样谦逊。”
她微笑着说他是兰,而不是别的什么梅竹菊,这很难不让人多想。
接着他们讨论文学,讨论音乐,他小心翼翼试探了半天她也没有在他面前露怯,他发现她不是他预想的寡才之人,她的学识好像并不比他寡陋,这让他大失所望。但没关系,江小云想,或许他懂阳春白雪,但她肯定不懂下里巴人,她会氩弧焊吗?她会刮腻子吗?她会装变压器吗?肯定不会,这是他沾沾自喜比她优越的地方。 而且,她少德是肯定的,不然怎么能把人当地毯踩还如此理所应当?难道就因为漂亮和有钱吗?一想到这江小云就愤愤不平。
他对她说“四月石榴火样红“是他家乡的雅乐,是值得传颂百世的经典,他希望唱给她听。
四月石榴火样红,
南徐州发来了那,
长毛兵,是天兵,
哎嘿哟,杀富济贫救百姓!!!!!!!!!
唱完之后,他肆无忌惮的大笑,嘴里可以塞下四五个鸡蛋。于是她就要往他的嘴里塞鸡蛋,他问为什么,她说,她对此感到好奇,难道不可以吗?他说可以。于是她拿来了一篮共四十五个鸡蛋,他的瞳孔本来有鸡蛋大小,现在猛缩到鹌鹑蛋大小,他想跟她狡辩是四或五个鸡蛋,但他的嘴里已经塞满鸡蛋,只能发出呕哑嘲哳的声音。她一个个的鸡蛋往里放,不管他能不能装得下,势必要把一篮鸡蛋全塞进去,他拼命下咽,无论是蛋清蛋黄还是蛋壳以及血液,蛋壳把他的咽喉食道划破,让后来的鸡蛋不在需要经过咀嚼才能下滑,他成了个细口垃圾桶。他想他终于是要死掉了,这一切起源都是因为她一时兴起想看他的笑究竟是不是肆无忌惮的笑。悔恨使他的泪腺高潮,给四十五个鸡蛋又加了些盐味,这样一来他的死大概不会很体面了,因为秃鹫之类的腐生动物最爱咸鸡蛋。他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客死他乡,全尸也没有留下。想到这里,他的泪淌的更勤更咸。
这就是在她面前唱“洪秀全起义”的后果,设想一番惊出冷汗的他赶紧把三分得意的笑收回二分得意。这,才是温良恭谦让的汉人。发乎情止乎意淫。这不是小狗吗?不是,这是温良恭谦让的汉人。
分别时,他鬼使神差的问她要了联系方式,她慷慨的应允了,这让他得以仰望天上的帝城双凤阙。他也应允给她看他咽呜半天憋出来的讨xx檄小作文。归家后,他慎重的点击了“我是江,请多指教☺️”的好友申请发送按钮。
已经是月入层云光黯淡的时分了,他的好友申请依然没有被通过。他想或许是她太忙了。江小云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渺远的梦。他看见她坐在柯尼塞格的铁壳子里,轮胎踩在他为她修筑的耗尽心力的一马平川的宽阔道路上,这道路凹的每一厘他都用他的血和精液填满夯实,凸的每一厘他都用他的舌头和屌舔磨平整,以保证她的绝对安全。她对这样的安逸感到厌烦,一心寻求危险的刺激,把车加速到四百五十公里的顶速享受死在旦夕的快感。柯尼塞格一轰而过,无意碾死了一只可怜的蚂蚁演说家。蚂蚁议员直到去世前还在演讲,滔滔不绝提倡多收消费税,降低征税起点,集社会财富以供她挥霍,他孜孜不倦地歌颂她的高贵伟大,正像个狂热的传教士。他死的这样滑稽,又能去哪里申冤呢?江小云半夜醒来后,遮住湿漉的内裤闭上眼睛不闻不见默如磐石。
江小云是出生在中产家庭,而向来对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不屑一顾的人。他对成金太郎和old money投以同等地鄙视,对此则言必称“下里巴人,俗不可耐”。他会为早年上山下乡一视同仁而欢欣,会对某时期计生委单对“农村户口”“汉族”的屠戮进行义愤填膺地抨击——尽管他的家庭因为前者饱受苦难,他因为后者的区分措施才逃过一劫无事诞生。他痛恨不公,厌恶特权,又时时刻刻生活在不公里。他对奥威尔《动物农场》里“人生来平等,但有的人更平等”的说法忌讳莫深。与此相对的是,他对贫苦人,无论是纯真善良的,还是奸佞狡诈的,均抱以极大地理解和共情。他是深刻认为底层无恶人的,只要是生活贫苦受压迫的人,无论作怎么样的恶,都是可以网开一面宽恕的,可以认为那恶行是受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某鲶鱼东窗事发时,他在微博仿效骆宾王《讨武曌檄》,激扬万字作“讨鲶鱼檄”,以昭彰其对特权嫉恶如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清高态。文毕已是深夜,他扯开窗帘往外瞥一眼,东九区依旧霓虹闪烁,看不见层云遮掩的黯淡月光。他并不知道檄文能不能过审,在以往这种事无所谓的,他只是享受创作的过程,且习惯于顾影自怜。但这次,他暗暗地希冀着,也许某鲶鱼真的会看到他的文字。他当然不愿意去私信鲶鱼,这太卑躬屈膝了。扣上三防电脑的屏幕,江小云躺在床上神思游离。他希望自己一躺下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毕竟创作那篇文章已经使他心力交瘁,他到明天起床之前都打不出一个字,说不出一句话了。换句话说,他把今天近乎所有的精力都赤忱地奉献给了鲶鱼,哪怕是批判。可是他睡不着,他知道还有一件事等着他去做。他决意忘记那事,可是那件事就在他脑子里不紧不慢的等着他,告知他他的供奉仪式还差一个环节,笃定他一定会去完善。辗转反侧之后,他果然在一片黑暗沉寂的房间里坐了起来,兀然掀开了老古董索尼电脑的屏幕,急不可耐地找回鲶鱼大小姐发言的微博页面,那些视底层为蛆虫的,触目惊心的言论。他紧盯着房间里唯一的光亮,目不转睛。不多时他的屌已经涨得难受,他依旧不想解开腰上昨晚系死的带子,他已经为这种事后悔无数次了,可是,倘若他再不解开腰带他的屌就要开始抽搐了。面对着幽幽从窗外吹来的凉风和屏幕上粗鄙暴戾的几行字,想象屏幕外的人是怎么样的颐指气使,江小云的藐视权贵,文人风骨短暂消失在了这个夜晚,他又一次落下粘稠的泪。
江小云的气息到底平稳下来。“我倒不比她差。其一我同样润出来了,日本也是发达国家。其二,嗯,我的索尼三防机,防水性甚于Macbook。”他一番论证得出了他想要的的结论,所谓鲶鱼并不比他高贵。他摩挲着电脑,不禁哑然失笑,或是为这幼稚的想法感到无奈。不过,无论是打标枪,还是拿自己对比鲶鱼的论证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到了明天,他依旧是愤世嫉俗的贫民之友。
然而,距江小云上次吟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现在的他也在吟唱,不过内容却变成了“烛炬帝志,唯死是向”,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在遇见她之前,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在修学业成绩优异,众人对他鞭辟入里的文字的赞许,刺激他的野心膨胀着,他设想日后怎么样大刀阔斧改造社会,怎么样像镰刀收割麦田一样把任何压迫人的人,无论是特权阶级还是旧贵族的残渣余孽通通割成和平民一样高的齐穗,社会再无人上人和人压迫人的行为发生,日本俨然成为“无鱼之白河”。他本人则跟实行改革的松平定信一样,被记载在历史书里给学生们摇头晃脑地背诵,而且是以一个汉人的身份。可惜,可惜,他如此伟大崇高的愿景在遇见她后就溃败作鸟兽散了,结局总不些说不出的滑稽。
那本来应该是个稀疏平常的下午,江小云想。倘若不是中年秃顶大腹便便的校长突然召集大家通知了三校合并的消息,他现在也不至于一想到她膝盖就发软。合校,在当时的他看来是无所谓的,他的才能不会因合校变得平庸,他的前景不会因合校变得阴翳。但他得知三校之正一是赫赫有名的贵族学校时,他还是忧虑一会,并不是担心他会比这些酒囊饭袋还要才疏学浅,而是他对“贵族”的警惕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过,他可以借此便利窥探upper class的奢靡,揭露和批评她们的恶贯满盈,新造一副韩熙载夜宴图。
江小云的身体并不强壮,甚至可以用孱弱形容,当他费力的抱着硕大的书包前往新校舍时,看到了让他口干舌燥的场面。一辆劳斯莱斯停在树荫下,后车门旁跪趴着一个人,车门被打开,另一人手持遮阳伞遮挡住了大部分美妙光景,他只看得到一只十分纤细的包裹着丝袜的小腿缓慢优雅伸出车内,和跪趴的仆人的背部接触的是小巧精致的皮鞋,看不出由来。主仆显然都对此习以为常。江小云对贵族们生活方式的容许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在他笔下钟鸣鼎食已经是罄竹难书罪不容诛程度的奢靡,他对古文的说法深以为然。书里说的,喝仪狄酿的酒是奢靡之举,吃易牙做的饭是穷奢极欲,和南之威行鱼水之欢是穷奢极欲,甚至流连高台、陂池也是穷奢极欲。因此当他看见这一幕时心里忽然受到一阵悸痛,贵族们比他所痛恨的更加罪恶深重。江小云共情那个跪趴在车旁的可怜人,把他认定为他和贵族抗争的盟友。可是当江小云经过劳斯莱斯时,只低着头瞄一眼依旧跪趴在原地形同枯槁的他,江小云迈开的步子就突然像跨台阶一样踩了个空。他错愕的发现,被她当做地毯踩过的人,被他认定为盟友的人,在她悠然踏过的西装上,巴黎世家的标志清晰可见。她不记得有这个人,他就要一直跪到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可见他确实是受压迫者,但是,但是,这怎么能谈得上“贫苦”呢?江小云咽下唾沫,更不抬头,惊魂未定的加速离开。他显然误判了,这样的人不会是他的盟友。可是瞬间他又意识到他的快步走是心虚和不自然的,像鲤趋于庭一样别扭。孔鲤趋庭而过是恐惧孔子的威严,他加速难道是因为惧怕她吗?他对她们从始至终都必须是愤恨的,哪怕一点恐惧也会让他气泄芒针,他必须劝自己相信他不畏惧她们,和她们的鹰犬走狗,尽管她并不在意他的自娱自乐。
但在当时,江小云确实是在恐惧她。他习惯以最坏的形势揣测,他害怕她或许会在前面忽然叫住他,说:“喂,那只支那猪!”倘若发生这种境况,他怎么才能不让他本就颤抖不已的膝盖轰然叩地。他感到莫名地沮丧和烦躁,对自己是否真的有改变如此普遍的人压迫人的现状的伟力产生了不自信。江小云心烦意燥时,总习惯背“心若冰清,天塌不惊”,来了日本也不肯入乡随俗改成数质数,这是腐朽文人凝滞于物的小小傲骨。这样做当然是想把刚才的所见祛除脑外,可惜收效甚微。那只纤细完美的小腿丝毫不讲道理的占据了他的大脑,随意踏在他的思想上作威作福,像烙铁般在他心脏上留下一个滚烫的鞋印。咣!或是巨大书包阻挡视线的缘由,神思游离的他竟没有注意到面前印着循环(MEGURU)哥卡通形象的绿色垃圾桶,几乎一头栽倒在里面。这对他而言实在是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不过还好没有人看到。
“同学,没事吧?”
江小云扶正眼镜抬起头,恰好对上略带笑意的她的视线。
她站在前几米的地方,和他略有一些高度差。
她手执一把繁复纹饰的遮阳伞,银色的长发随风摇曳,红色的瞳孔里焕发着妖冶的光,白皙的过分的皮肤好像不能见光的吸血鬼族一样,身上纯白的礼服和颈上恰到好处的黑色蝴蝶结点缀组成了一副吊诡至极而又姽婳至极的定格画。
他的视线先是在她过分标致宛若为了满足他的xp而生产的圣洁面孔上,但只一秒就好像被灼痛般滑落到她不甚丰满的欧派(◦˙▽˙◦)上,再低到裙摆黑色的束边里掩盖着的吊带丝袜,最后停留在那双把他踩进垃圾桶的罪魁祸首棕色皮鞋上。
“无事,见笑,见笑了。我正是犯了瓜田不纳履的忌讳了,实在贻笑大方。”
他盯住那双精致的鞋子,不敢抬起灼热的头颅,同样灼热的小头却悄然昂首。这样尴尬的场面使他言不过脑地滥用典故,也不考虑对面的人能否理解华夏俚语。
“没事就好。呱甜……你是外国人吗?”
她充满好奇地发问。
“是,不过我来这里不很短的时间了。”
他不太想回答她,可有喙不应声也写在他的社交禁令里,只好避重就轻的回答。
“原来如此。你的日语很熟练呢。嗯~有缘再见,——MEGURU君。”
她眼见他目光躲闪不愿和她对视,只好莞尔一笑,转过身去,无奈的摆摆手遣散了严阵以待的保镖或者仆从们。
“我本来就够引人注目了。”她对他们说。
夸张的公主护卫队给她带来了不少莺莺燕燕,他们围着她,夸赞她的美貌,崇拜她的高贵,作态像无人区三步一叩首的朝圣者一样虔诚。这一幕自然也成了江小云眼里的又一粒沙子,他顿时觉得朱子诚不欺江也: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当然,底层贫苦人是不在其中的,江小云早为他们脑补好了不得不攀炎附势的理由。至于她,江小云想,有一天他会把她挂到路灯上的。他的反抗之心熊熊燃烧着,把她断定为只会压榨民脂民膏的无才无德之人。无才尚可理解,毕竟不能谁都同他一样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少德不可宽恕,她怎么能把人当地毯踩还如此理所应当。江小云依旧对此愤愤不平。他在踌躇满志时,总是记不起主观臆断的害处。
江小云几乎不需要费任何力就能适应新环境,因为他早习惯于做来客。初来异乡时多少还有些惶恐拘谨,鞠躬也不甚标准,被老先生教训过,现在早就轻车熟路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编班级里还是有许多老面孔的,譬如迷恋大欧派的小a,喜欢打galgame的小b,还有…………她?!他料想不到她也和他一个班级,他的窘态是被她一览无余观赏过的,他对她多少有些忌医讳疾。当小a向他窃窃私语被众星捧月般围起来的她的时候,他故作不在意的向那边瞥一眼。
“哦。她的欧派很大吗?那里人太多了看不真切。”
小b狂热的推搡他,说他们竟有幸和一个超级美少女共处一室。
“什么?毕秀金?是指那个戴近视眼镜的雀斑女孩吗?嘛,挺可爱的。”
他刻意装作没听清的样子,随意找了个簇拥在她身边的人敷衍。
“什么啊,江君总不会看不出我说的是谁?”
他当然知道,她太突兀了,不止是美貌,还有看上去就不甚健康的独一无二的气息,任何人初次看到她,心脏都会莫名的刺痛。
“…………我是汉人,和你们的审美总归是有差异的。”
他迟疑一会,然后说。可惜,他的屌貌似不大认同他的说法。
她上台做介绍时,他涣散双目,心脏却砰砰跳个不停。他说她没什么特别的,不必要付诸以额外地关注。
她把名字写到黑板上,她的手指比无尘粉笔还要纤细,粉笔摩擦黑板上的镀膜发出沙沙的声音。她的力气显然不很足,不像讲课的先生那么孔武有力,写字都只能听见砰砰的撞击声。
她说她是“宫泽凛”,希望大家关照她。
他听到沙沙的声音消失了,才聚焦看一眼黑板上的字。她的笔锋相当尖锐,像瑞士军刀剖开他的胸腔,把他心脏上的轻巧俏皮的鞋印暴露出来。所以他咬牙切齿地评价这字不好。他说,写字,尤其是女孩子的字,还是婉转莹润些的好。
流程结束之后,江小云无意识往那边注目,同学们不约而同的聚过去,各怀鬼胎的和她搭讪。哪怕他不想听,他们谄媚的声音还是钻进他的耳蜗。
“宫泽大人,我是成田造船的。宫泽家对日本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个,我们也收到了贵府举办的慈善会的邀请。不胜感激荣幸,期待可以为社会尽些绵薄之力!”
“嗯,是吗?感谢参与。我们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
“是!宫泽家的恩情甚重,我是成田造船的!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话……”
“嗯,好,我记住了。”
“宫泽大人,关于贵府提出的粉末冶金工业新规,我们已经有贯彻执行了,请多多关照!我是中野金属的。”
“明白了,我会向家父转述。”
江小云越听心脏跳的越快,她的权势很盛超过他的预料,他厌恶看到这些人殷勤讨好她的奴才相,因为他总是不自觉的设身处地。他劝自己相信,他的膝盖宁折不弯绝不会像他们一样卑躬屈膝。
他带着复杂的情绪看她,自卑和自负在他心中博弈着,但这次他很难再像面对某鲶鱼时那样找到平衡点。此刻他无比期待放课,只要放课,只要放课,他就不用再受此等煎熬折磨,回家之后有手冲打,有廉价小奶茶喝,他很快会忘记现在的抑郁寡欢。
解放的铃声终于响了,他如释重负呼口气,也体验一次陶潜在回家路上的风飘飘而吹衣。他正欲舟遥遥以轻扬的归家,但不幸她牵着他脖子拴的绳子把他拽回来。
“MEGURU君?噢,应该说是江君。真巧我们又见面了。”
她仿佛发现了挂在他脖子上的金色的狗牌,那上面用可爱的字体镌刻着他的名字。
他颤栗一下,不得不收回迈出去的脚步。
“呃,你是……姓宫泽的吧?幸得偶遭,真熙皞。”
他佯装忘记实际他早默念了数十遍并且烂熟于心的她的姓名,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她。
“江君还真是出口成章呢。总觉得江君之前有往这边看,嗯,果然是错觉吧。”
她逼他承认他在注意她了,可是他偏偏很不情愿承认。承认了不就代表刚刚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在表演吗?然而他避无可避。他咽下唾液,像咽下掺着铁钉的烟丝泡水一样费力。
“是、因为有些在意宫泽同学的外表。宫泽君很漂亮。”
他不愿意和她对视,从身高来说他是比她高,但气势反而弱一头。
“谢谢。但江君能不能抬起头来呢?说话总是盯着人家的鞋子可不太礼貌。”
“啊、好,是、是,抱歉我…………”
他被勒令抬起头来,像被抽了鞭子的驯马一样不情不愿。他的自傲只在执笔时占上风,现在萎缩成她鞋底的一粒尘埃。
“江君,真的很是温良呢。”
她轻轻的感叹,像风吹过银铃,卷过稻田消失在天际。
江小云一阵苦笑,他无奈于自己的怯弱,为她积威之所劫,竟不敢当面质疑批判她草菅人命。他本应横眉冷对千夫指,现在却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很感激你的赞誉,但人不总是而且总不是那样简单的。——王莽也有谦恭未篡时,勾践做为奴作仆时也谨小慎微。”
他前面的话是对她说的,后面的话是对自己说的。现在,对她的软弱是不足可悲的,他将成为第二个王莽勾践。他籍此找回挥毫洒墨创作檄文时的嫉恶如仇。
“江君是勾践吗?”
她的眼睛里是可爱的迷茫,让他有些柔情泛滥,他警戒自己她是蹂躏底民的恶魔。
“我没有那样的魄力。”
江小云不假思索的否定,不想被她窥探过多想法。
“唔,这样吗?江君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
她还是笑吟吟的,把他的敌意消融回春。
“我不会去做谁的奴仆,也不会卧薪尝胆,更不会有勇气杀回马枪,倘我是勾践,早在被俘虏前就学不肯过江东的霸王自刎归天了。”
他自嘲地说,但这和他真实想法相去甚远,不知道能不能让她相信。他正像给齐宣王吹芋的南郭先生一样心虚。
“原来如此,江君啊,正像幽静的兰花一样谦逊。”
她微笑着说他是兰,而不是别的什么梅竹菊,这很难不让人多想。
接着他们讨论文学,讨论音乐,他小心翼翼试探了半天她也没有在他面前露怯,他发现她不是他预想的寡才之人,她的学识好像并不比他寡陋,这让他大失所望。但没关系,江小云想,或许他懂阳春白雪,但她肯定不懂下里巴人,她会氩弧焊吗?她会刮腻子吗?她会装变压器吗?肯定不会,这是他沾沾自喜比她优越的地方。 而且,她少德是肯定的,不然怎么能把人当地毯踩还如此理所应当?难道就因为漂亮和有钱吗?一想到这江小云就愤愤不平。
他对她说“四月石榴火样红“是他家乡的雅乐,是值得传颂百世的经典,他希望唱给她听。
四月石榴火样红,
南徐州发来了那,
长毛兵,是天兵,
哎嘿哟,杀富济贫救百姓!!!!!!!!!
唱完之后,他肆无忌惮的大笑,嘴里可以塞下四五个鸡蛋。于是她就要往他的嘴里塞鸡蛋,他问为什么,她说,她对此感到好奇,难道不可以吗?他说可以。于是她拿来了一篮共四十五个鸡蛋,他的瞳孔本来有鸡蛋大小,现在猛缩到鹌鹑蛋大小,他想跟她狡辩是四或五个鸡蛋,但他的嘴里已经塞满鸡蛋,只能发出呕哑嘲哳的声音。她一个个的鸡蛋往里放,不管他能不能装得下,势必要把一篮鸡蛋全塞进去,他拼命下咽,无论是蛋清蛋黄还是蛋壳以及血液,蛋壳把他的咽喉食道划破,让后来的鸡蛋不在需要经过咀嚼才能下滑,他成了个细口垃圾桶。他想他终于是要死掉了,这一切起源都是因为她一时兴起想看他的笑究竟是不是肆无忌惮的笑。悔恨使他的泪腺高潮,给四十五个鸡蛋又加了些盐味,这样一来他的死大概不会很体面了,因为秃鹫之类的腐生动物最爱咸鸡蛋。他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客死他乡,全尸也没有留下。想到这里,他的泪淌的更勤更咸。
这就是在她面前唱“洪秀全起义”的后果,设想一番惊出冷汗的他赶紧把三分得意的笑收回二分得意。这,才是温良恭谦让的汉人。发乎情止乎意淫。这不是小狗吗?不是,这是温良恭谦让的汉人。
分别时,他鬼使神差的问她要了联系方式,她慷慨的应允了,这让他得以仰望天上的帝城双凤阙。他也应允给她看他咽呜半天憋出来的讨xx檄小作文。归家后,他慎重的点击了“我是江,请多指教☺️”的好友申请发送按钮。
已经是月入层云光黯淡的时分了,他的好友申请依然没有被通过。他想或许是她太忙了。江小云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渺远的梦。他看见她坐在柯尼塞格的铁壳子里,轮胎踩在他为她修筑的耗尽心力的一马平川的宽阔道路上,这道路凹的每一厘他都用他的血和精液填满夯实,凸的每一厘他都用他的舌头和屌舔磨平整,以保证她的绝对安全。她对这样的安逸感到厌烦,一心寻求危险的刺激,把车加速到四百五十公里的顶速享受死在旦夕的快感。柯尼塞格一轰而过,无意碾死了一只可怜的蚂蚁演说家。蚂蚁议员直到去世前还在演讲,滔滔不绝提倡多收消费税,降低征税起点,集社会财富以供她挥霍,他孜孜不倦地歌颂她的高贵伟大,正像个狂热的传教士。他死的这样滑稽,又能去哪里申冤呢?江小云半夜醒来后,遮住湿漉的内裤闭上眼睛不闻不见默如磐石。
大小姐题材就是好,期待后续正式的展开~
好看,我也觉得鲶鱼色
牛的 期待更新
引经用典顺手捻来,byd还挺抽象,让我绷不住好几次。期待下文。
2.伯乐相马
江小云情愿睡过去就不再醒来,他实在为自己的下作欲望感到难堪。可是太阳落下了总还是要升起,他也不是射完精就死了。
他把被子一遍遍的叠直到型成病态的豆腐块,再斟酌早餐煎蛋撒的芝麻粒究竟几克合适。做这些的原因并不是他忽然患上了强迫症,而是在尽可能拖延面对审判结果的时间。做完一切之后,他终究还是不得不拿起手机来。他叹口气,颤颤巍巍打开社交软件,紧张的心情好像跪在朝堂下等待宣判的瑟瑟发抖的受审刑犯。她说,死罪!他就了无生机昏死过去。她说,赦免!他就叩头如捣蒜谢恩。——————pass!谢天谢地她终于想起来通过他的申请,他如释重负,嘴角稍微扬一扬,心里却高兴的手舞足蹈,嗯,君子喜怒不形于色。
实际上,江小云早就忘却那天煎蛋究竟撒了几克芝麻,但她的一句一话他记忆犹新。她说对他嬉笑怒骂的文字很感兴趣,命他现在发过去。可是他睡了一觉改变了想法,觉得那小作文写的太露了,给她看就是跟美国大兵唱打倒美帝野心狼。好在他以前为了过平台审核做的销锋镝的事情不算少,也算轻车熟路了。他说肥肠抱歉,要到今晚才能发。她疑惑现在为什么不能发,他解释要给成语做注释,她才看得懂。上课时,他也心不在焉,想象她明白他隐晦的用意之后的反应,不自觉的往那里侧目,偷偷看她穿的学院制服和踏在桌子底梁上的小靴子,然后猛然惊醒告诫自己革命家应当有破釜沉舟的暴戾之气而不是整天谨小慎微的向谁邀功讨好谁。
四月的微风那样和煦,吹的他心旌摇曳,心脏也迸发出久违的活力,或许可以给她做个蹦蹦床踩着玩。老先生还在台上讲“昔新罗请援于高丽”,不过台下似乎少有人还在忧虑任那的威胁了。直到老先生的惊堂木再拍下去,江小云才如梦初醒知道放课了。他卷起潦草划下他的想法的草纸,往里长吹口气把身家性命寄托在里面。江小云翘首以盼,希望她尽早离开教室,这样他就可以不跟她打交道就回家。他总觉得每面对她时膝盖就发抖没大有底气。但他抬头就发现她正对他别有深意的笑,他知道躲不过去了,只能步履维艰的踱过去,小心翼翼地给她鞠躬。
“嗯。江君这是?”她的笑比之前多些戏谑,但他低着头看不见。
“宫泽同学,我来向您道歉……”江小云觉得这实在很羞耻,为什么要给同学鞠这么深的躬,还讲这么卑微的话。
“你错在哪了?”她看着紧张的他,饶有兴致的发问。
“呃,是我考虑不周,临渴而掘井也,答应的事情没做到,对不起。”他本不觉得他有错,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这么讲。
“嘛,这倒没事,毕竟江君还要上课,当然以学业为重。至于我,哪怕今晚再找借口拖延也没关系哦?”
“啊,真的吗?”江小云一阵窃喜,顿时觉得躬鞠的不亏。
“江君啊,你这么喜欢得寸进尺的吗?
嗯,我改主意了。
到家之前我要收到你的邮件。”
她慢条斯理的陈述,无视他因恐惧放大的瞳孔。
“顺便一提,我是回家部的哦。”
“我……”江小云呆在原地,他总不能给劳斯莱斯轮胎下撒钉子。
“倘江君还不想走的话,我就先失陪了。
————希望我们明天还能再见。”她轻飘飘的话砸到他身上如富士山般沉重。
“不不不,不要啊,我讲错话了。还请您务必再宽限些,因为……中译日也很有些繁琐,另外我还须得增删改查一番,也费时间的,我肥肠抱歉。”他的腰弯的比递投降书的冈村宁次还要低。
“可是江君很是不乖呢,事到如今还在找借口。”她搓起他几乎低到尘埃里去的头颅上的一缕头发,卷起来缠绕在青葱玉指上。
“这样不老实的江君,是该受到些惩罚吧?”
“惩,惩罚?!您怜悯我身体孱弱经不起折腾……”他也不清楚为什么稀里糊涂就要受罚了。
“那可不关我的事哦~江君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她的语调渐渐冷下来,让他也感受一番寒彻骨。
“我,我,请宫泽大人责罚我失约推诿之过错,我实在罪不容诛,如何处置乎悉听尊便……”江小云欲哭无泪,只能垂头丧气把扼住他咽喉的锁链奉献上去。
“嗯,你总算肯说一句人话。
不过江君也不用害怕,毕竟我还没看到你的文字,我不会玩的太过火的。”她拂过他颤颤巍巍的脸颊站起身来,轻风扬起少女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气掠过江小云的嗅觉。
她应承着同学们的恭维离开教室,他等她不见人影再跟上去,否则在同学眼里不是像个书童形影不离跟着主人一样了。但她每次停下和同学打招呼他就要扮出一副赏花吟月的样子,次数多了很有些尴尬。
赏花,江小云是来者不拒的。无论海棠水仙还是梧桐,连路边狗尾巴草江小云也要蹲下来夸赞一番绒密而鞘弛,乃逗狗耍猫之良才也。出了学校,人终于少起来,他才敢靠她近一点,试图狡辩他离她那么远绝不是忌惮什么,是怕地上的灰土扬尘沾染天宫。
“我累了。”她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一脸茫然的江小云。
“那边公园有座椅,您先休息一会,我让司机把您的车开过来?”他厌恶自己说的话做的事,但说起来做起来行云流水。
“我累了。”她又重复一遍,盯着他看,知道他会明白她的意思。
“我……”他知道她的想法,但他铁骨铮铮怎么可能那样做。
“宫泽大人……请您上马。”他不愿意归不愿意,但没有第二个选择。他屈辱的双膝叩地,手掌接触沥青路面时才知道勾践的苦楚。
“很好,江君也不是傻子嘛。”她看到这一幕并不着急骑上去,而是随手摘了一根狗尾巴草扫弄江小云的鼻腔。
“不许打喷嚏。”她发觉江小云呼吸沉重起来,随即补充道。
“这点程度都承受不了的马匹,我怎么敢骑呢?”
不料她的话没能让他自尊心更进一步受挫,反倒让他的屌不服气了。
“求您,宫泽大人,求您上马,敝乃为宫泽大人的胯下之物而生,若不能竭敝之力以侍大人,敝当……,……当即刻赴死”
他清楚这折磨他坚持不多久,只能得屏住最后一口气讲卑躬屈膝的话,然后用脸颊去蹭她的靴子,极尽温驯卑微之态。
反正,反正这话勾践也讲过,这事勾践也做过,最后还不是攻守异也了,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这样啊,嗯,姑且算江君过关好了。”
她终于开心起来,轻轻跨坐上去,不足九十斤的重量对孱弱的小云来说也已经是可承受的极限了。
“良马可不会让主人的裙子着地哦,江君?”
“抱歉,我罪不容诛,我该剜心剖腹……”他道歉早就得心应手,相比全身肌肉发力才能撑起主人,显然说两句肥肠抱歉要轻松的多。
“……那好吧,江君再坚持一会,车上有随行医师和麻醉药,会让江君无痛离世的。”
“……我开个玩笑,我还不想死啊,况且我死了对您也是痛失良臣……”江小云委屈的说。
“我又不缺一匹马。何况还是匹病弱的、自以为是的蠢马。对吧,江君。”她的声音又沉下来,可是小云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真的没力气了,我身体不壮硕您是知道的,可是这不影响我对您的赤胆忠心啊……”江小云苦口婆心的解释,尽全力绷紧身体抬高她的身体,直至她的靴底到他的口鼻处高。
“是吗?貌似你的下体快撑破衣服了,它的力气是来自?”她的小腿不安分的荡着,靴底有意无意蹭过某个坚硬如铁的棍棍。
“!!!呃,这个这个,它这个,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屌……也是一样,我是故意让它变大的,是为了您的骑乘体验……”他紧张到冒虚汗,然后开始胡说八道,说到最后声音也颤抖起来,无处不透露着心虚。
她没有再说话,或许是觉得再说的话他就扮不下去了,泡泡还是吹大了再戳破来的有意思。这段路并不长,对马上的美少女来讲是静谧美好悠然的黄昏小憩,对他却是患得患失,永生难忘的五分四十秒。
江小云的头伏到地下,他只看到她踩着人垫优雅坐进车里,却没注意到脸埋进地面,恭敬跪趴在车下的侍从物是人非。或许这对她只是个一次性的脚垫,不坏也要换掉罢。
她对他说:“江君说的所谓骑乘体验,恕我直言,简直糟糕透了,我没有骑过这么糟糕的马。
嗯,今晚再失约的话,为了骑乘体验,江君恐怕要失掉什么碍事的东西了。”
“是…………”
车暴力加速扬起的大量粉尘湮进他肺部纤维,让他咳嗽不止,即便如此他仍急促呼吸着空气里的煤矽和石棉粉,他现在没功夫站起来,他的手紧紧攥住早早淌出先走液的屌,苦苦哀求它不要射。
江小云情愿睡过去就不再醒来,他实在为自己的下作欲望感到难堪。可是太阳落下了总还是要升起,他也不是射完精就死了。
他把被子一遍遍的叠直到型成病态的豆腐块,再斟酌早餐煎蛋撒的芝麻粒究竟几克合适。做这些的原因并不是他忽然患上了强迫症,而是在尽可能拖延面对审判结果的时间。做完一切之后,他终究还是不得不拿起手机来。他叹口气,颤颤巍巍打开社交软件,紧张的心情好像跪在朝堂下等待宣判的瑟瑟发抖的受审刑犯。她说,死罪!他就了无生机昏死过去。她说,赦免!他就叩头如捣蒜谢恩。——————pass!谢天谢地她终于想起来通过他的申请,他如释重负,嘴角稍微扬一扬,心里却高兴的手舞足蹈,嗯,君子喜怒不形于色。
实际上,江小云早就忘却那天煎蛋究竟撒了几克芝麻,但她的一句一话他记忆犹新。她说对他嬉笑怒骂的文字很感兴趣,命他现在发过去。可是他睡了一觉改变了想法,觉得那小作文写的太露了,给她看就是跟美国大兵唱打倒美帝野心狼。好在他以前为了过平台审核做的销锋镝的事情不算少,也算轻车熟路了。他说肥肠抱歉,要到今晚才能发。她疑惑现在为什么不能发,他解释要给成语做注释,她才看得懂。上课时,他也心不在焉,想象她明白他隐晦的用意之后的反应,不自觉的往那里侧目,偷偷看她穿的学院制服和踏在桌子底梁上的小靴子,然后猛然惊醒告诫自己革命家应当有破釜沉舟的暴戾之气而不是整天谨小慎微的向谁邀功讨好谁。
四月的微风那样和煦,吹的他心旌摇曳,心脏也迸发出久违的活力,或许可以给她做个蹦蹦床踩着玩。老先生还在台上讲“昔新罗请援于高丽”,不过台下似乎少有人还在忧虑任那的威胁了。直到老先生的惊堂木再拍下去,江小云才如梦初醒知道放课了。他卷起潦草划下他的想法的草纸,往里长吹口气把身家性命寄托在里面。江小云翘首以盼,希望她尽早离开教室,这样他就可以不跟她打交道就回家。他总觉得每面对她时膝盖就发抖没大有底气。但他抬头就发现她正对他别有深意的笑,他知道躲不过去了,只能步履维艰的踱过去,小心翼翼地给她鞠躬。
“嗯。江君这是?”她的笑比之前多些戏谑,但他低着头看不见。
“宫泽同学,我来向您道歉……”江小云觉得这实在很羞耻,为什么要给同学鞠这么深的躬,还讲这么卑微的话。
“你错在哪了?”她看着紧张的他,饶有兴致的发问。
“呃,是我考虑不周,临渴而掘井也,答应的事情没做到,对不起。”他本不觉得他有错,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这么讲。
“嘛,这倒没事,毕竟江君还要上课,当然以学业为重。至于我,哪怕今晚再找借口拖延也没关系哦?”
“啊,真的吗?”江小云一阵窃喜,顿时觉得躬鞠的不亏。
“江君啊,你这么喜欢得寸进尺的吗?
嗯,我改主意了。
到家之前我要收到你的邮件。”
她慢条斯理的陈述,无视他因恐惧放大的瞳孔。
“顺便一提,我是回家部的哦。”
“我……”江小云呆在原地,他总不能给劳斯莱斯轮胎下撒钉子。
“倘江君还不想走的话,我就先失陪了。
————希望我们明天还能再见。”她轻飘飘的话砸到他身上如富士山般沉重。
“不不不,不要啊,我讲错话了。还请您务必再宽限些,因为……中译日也很有些繁琐,另外我还须得增删改查一番,也费时间的,我肥肠抱歉。”他的腰弯的比递投降书的冈村宁次还要低。
“可是江君很是不乖呢,事到如今还在找借口。”她搓起他几乎低到尘埃里去的头颅上的一缕头发,卷起来缠绕在青葱玉指上。
“这样不老实的江君,是该受到些惩罚吧?”
“惩,惩罚?!您怜悯我身体孱弱经不起折腾……”他也不清楚为什么稀里糊涂就要受罚了。
“那可不关我的事哦~江君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她的语调渐渐冷下来,让他也感受一番寒彻骨。
“我,我,请宫泽大人责罚我失约推诿之过错,我实在罪不容诛,如何处置乎悉听尊便……”江小云欲哭无泪,只能垂头丧气把扼住他咽喉的锁链奉献上去。
“嗯,你总算肯说一句人话。
不过江君也不用害怕,毕竟我还没看到你的文字,我不会玩的太过火的。”她拂过他颤颤巍巍的脸颊站起身来,轻风扬起少女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气掠过江小云的嗅觉。
她应承着同学们的恭维离开教室,他等她不见人影再跟上去,否则在同学眼里不是像个书童形影不离跟着主人一样了。但她每次停下和同学打招呼他就要扮出一副赏花吟月的样子,次数多了很有些尴尬。
赏花,江小云是来者不拒的。无论海棠水仙还是梧桐,连路边狗尾巴草江小云也要蹲下来夸赞一番绒密而鞘弛,乃逗狗耍猫之良才也。出了学校,人终于少起来,他才敢靠她近一点,试图狡辩他离她那么远绝不是忌惮什么,是怕地上的灰土扬尘沾染天宫。
“我累了。”她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一脸茫然的江小云。
“那边公园有座椅,您先休息一会,我让司机把您的车开过来?”他厌恶自己说的话做的事,但说起来做起来行云流水。
“我累了。”她又重复一遍,盯着他看,知道他会明白她的意思。
“我……”他知道她的想法,但他铁骨铮铮怎么可能那样做。
“宫泽大人……请您上马。”他不愿意归不愿意,但没有第二个选择。他屈辱的双膝叩地,手掌接触沥青路面时才知道勾践的苦楚。
“很好,江君也不是傻子嘛。”她看到这一幕并不着急骑上去,而是随手摘了一根狗尾巴草扫弄江小云的鼻腔。
“不许打喷嚏。”她发觉江小云呼吸沉重起来,随即补充道。
“这点程度都承受不了的马匹,我怎么敢骑呢?”
不料她的话没能让他自尊心更进一步受挫,反倒让他的屌不服气了。
“求您,宫泽大人,求您上马,敝乃为宫泽大人的胯下之物而生,若不能竭敝之力以侍大人,敝当……,……当即刻赴死”
他清楚这折磨他坚持不多久,只能得屏住最后一口气讲卑躬屈膝的话,然后用脸颊去蹭她的靴子,极尽温驯卑微之态。
反正,反正这话勾践也讲过,这事勾践也做过,最后还不是攻守异也了,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这样啊,嗯,姑且算江君过关好了。”
她终于开心起来,轻轻跨坐上去,不足九十斤的重量对孱弱的小云来说也已经是可承受的极限了。
“良马可不会让主人的裙子着地哦,江君?”
“抱歉,我罪不容诛,我该剜心剖腹……”他道歉早就得心应手,相比全身肌肉发力才能撑起主人,显然说两句肥肠抱歉要轻松的多。
“……那好吧,江君再坚持一会,车上有随行医师和麻醉药,会让江君无痛离世的。”
“……我开个玩笑,我还不想死啊,况且我死了对您也是痛失良臣……”江小云委屈的说。
“我又不缺一匹马。何况还是匹病弱的、自以为是的蠢马。对吧,江君。”她的声音又沉下来,可是小云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真的没力气了,我身体不壮硕您是知道的,可是这不影响我对您的赤胆忠心啊……”江小云苦口婆心的解释,尽全力绷紧身体抬高她的身体,直至她的靴底到他的口鼻处高。
“是吗?貌似你的下体快撑破衣服了,它的力气是来自?”她的小腿不安分的荡着,靴底有意无意蹭过某个坚硬如铁的棍棍。
“!!!呃,这个这个,它这个,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屌……也是一样,我是故意让它变大的,是为了您的骑乘体验……”他紧张到冒虚汗,然后开始胡说八道,说到最后声音也颤抖起来,无处不透露着心虚。
她没有再说话,或许是觉得再说的话他就扮不下去了,泡泡还是吹大了再戳破来的有意思。这段路并不长,对马上的美少女来讲是静谧美好悠然的黄昏小憩,对他却是患得患失,永生难忘的五分四十秒。
江小云的头伏到地下,他只看到她踩着人垫优雅坐进车里,却没注意到脸埋进地面,恭敬跪趴在车下的侍从物是人非。或许这对她只是个一次性的脚垫,不坏也要换掉罢。
她对他说:“江君说的所谓骑乘体验,恕我直言,简直糟糕透了,我没有骑过这么糟糕的马。
嗯,今晚再失约的话,为了骑乘体验,江君恐怕要失掉什么碍事的东西了。”
“是…………”
车暴力加速扬起的大量粉尘湮进他肺部纤维,让他咳嗽不止,即便如此他仍急促呼吸着空气里的煤矽和石棉粉,他现在没功夫站起来,他的手紧紧攥住早早淌出先走液的屌,苦苦哀求它不要射。
超开心更新了。不过感觉第二章的进度比第一章快很多,感觉叙事节奏慢一点会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