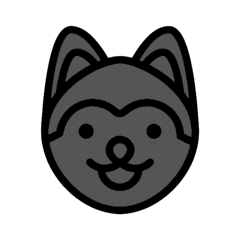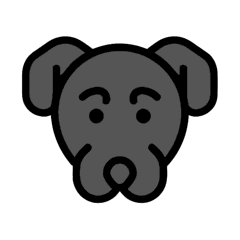萱履踏稚骨
连载中AI生成古代萝莉姐姐女虐女踩踏
红尘一笑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1-31 09:51
萱履踏稚骨
金钗承萱步
━━━━━━━━━━━━━━━━━
暮春的风携着庭院里忍冬花的甜香,掠过青石铺就的月台,拂动林微晚鬓边新簪的金钗。那支小巧的赤金钗是今早母亲亲手为她插上的,冰凉的金属贴着头皮,却远不及此刻她心头的寒意真切——今日是她的金钗之日,也是需践行“承萱礼”的日子。
永安王国的女子,凡年满十五便要过这一关。所谓承萱礼,便是以己身为阶,承母亲之足,行孝于当下。林微晚望着月台中央那方铺着素色锦垫的空地,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袖。昨日她还在绣架前为母亲缝制夏衫,今日却要褪去外衫,只着一身素白中衣,躺卧在地,让母亲的双脚碾过自己的肩背腰腹。
“微晚,莫怕。”母亲苏婉容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她身着一袭石青色缠枝莲纹褙子,鬓间仅簪一支碧玉簪,往日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眸,此刻添了几分肃穆。“这是永安女子的本分,也是你日后能侍奉家中长辈的凭证。忍过一时辰,便是对为娘最大的孝。”
林微晚点点头,喉头有些发紧。她见过堂姐去年行承萱礼的模样,那时堂姐趴在锦垫上,牙关紧咬,额上的汗珠砸在青石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直到母亲在她身上缓缓走完三圈,时辰终了时,她后背已是青红交错,却依旧强撑着露出笑容,说“女儿无碍”。那时她只觉心惊,如今身临其境,才知那份惊惧远不及此刻的沉重。
侍女们端来铜壶,为她净手净面,又仔细拂去锦垫上的浮尘。林微晚深吸一口气,褪去外衫,俯身躺在锦垫上。青石的凉意透过锦垫渗进来,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调整呼吸,将双臂贴在身侧,脖颈微微绷紧,做好了承接的准备。
苏婉容缓步走到她身前,目光在女儿纤细的脊背上游移,眸中闪过一丝不忍,却终究化为决绝。她提起裙摆,轻轻将右脚放在女儿的肩胛处。那一瞬间,林微晚只觉肩上一沉,仿佛压了一块温软的石头,紧接着,母亲的左脚也落了下来,重量均匀地铺在她的背上,让她胸腔微微发闷。
“娘要动了。”苏婉容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林微晚咬紧下唇,闷声道:“女儿无碍,娘请便。”
话音刚落,母亲的脚步便缓缓挪动起来。先是从肩胛移向脊背,再从脊背挪至腰腹,每一步都走得极缓,却带着不容抗拒的重量。林微晚能清晰地感受到母亲裙摆扫过自己后颈的触感,还有脚下传来的温热,以及那逐渐加重的压力。腰腹处一阵酸胀,像是有无数根细针在扎,她忍不住皱紧眉头,额上很快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月台周围站着家中的女眷,祖母坐在一旁的太师椅上,目光沉静地望着这一切,手中的佛珠缓缓转动。几位婶婶低声交谈着,语气中带着对晚辈的期许。林微晚不敢分心,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吸气时感受腹部的扩张,呼气时尽量放松紧绷的肌肉。她想起幼时母亲彻夜照顾生病的自己,想起母亲为了供她读书,亲手绣了数十幅帕子去变卖,想起母亲常说的“百善孝为先”。
母亲的脚步依旧平稳,只是每走一圈,林微晚都觉得背上的重量似乎重了一分。肩胛处开始发麻,脊背的酸胀感蔓延开来,连带着四肢都有些僵硬。她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弯月形的红痕,疼痛让她保持着清醒。她不敢出声,怕让母亲担忧,更怕辜负了这份孝道的考验。
不知过了多久,日头渐渐西斜,透过庭院里的梧桐叶,在锦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微晚的后背已经麻木不堪,汗水浸透了中衣,贴在皮肤上,又被风一吹,带来阵阵凉意。她的眼前有些发黑,耳边传来的母亲的脚步声似乎变得遥远,只有祖母手中佛珠转动的声音清晰可闻。
“时辰快到了。”祖母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苏婉容的脚步顿了顿,最后一步落在林微晚的肩胛处,然后缓缓移开。她俯身将女儿扶起,看着她苍白的脸色和湿透的衣衫,眼中的不忍再也掩饰不住,伸手拭去她额上的汗珠:“我的儿,苦了你了。”
林微晚勉强笑了笑,声音带着一丝沙哑:“能为娘尽孝,女儿不苦。”
祖母缓缓起身,走到她面前,抬手抚了抚她鬓边的金钗:“好孩子,你通过了承萱礼,往后便是我林家合格的孝女,有资格侍奉家中长辈了。”她的声音苍老却有力,带着对晚辈的认可。
林微晚望着祖母和母亲眼中的赞许,心中的酸胀与疼痛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她知道,这一辰的坚持,不仅是对母亲的孝,更是对永安王国女子本分的践行。金钗之年,承萱之礼,这烙印在骨血里的孝道,将伴随她往后的人生,指引她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儿,一名值得托付的晚辈。
夕阳下,忍冬花的香气愈发浓郁,林微晚扶着母亲的手,缓缓走出月台,背影虽依旧纤细,却多了一份历经考验后的坚定。
━━━━━━━━━━━━━━━━━
暮春的风携着庭院里忍冬花的甜香,掠过青石铺就的月台,拂动林微晚鬓边新簪的金钗。那支小巧的赤金钗是今早母亲亲手为她插上的,冰凉的金属贴着头皮,却远不及此刻她心头的寒意真切——今日是她的金钗之日,也是需践行“承萱礼”的日子。
永安王国的女子,凡年满十五便要过这一关。所谓承萱礼,便是以己身为阶,承母亲之足,行孝于当下。林微晚望着月台中央那方铺着素色锦垫的空地,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袖。昨日她还在绣架前为母亲缝制夏衫,今日却要褪去外衫,只着一身素白中衣,躺卧在地,让母亲的双脚碾过自己的肩背腰腹。
“微晚,莫怕。”母亲苏婉容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她身着一袭石青色缠枝莲纹褙子,鬓间仅簪一支碧玉簪,往日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眸,此刻添了几分肃穆。“这是永安女子的本分,也是你日后能侍奉家中长辈的凭证。忍过一时辰,便是对为娘最大的孝。”
林微晚点点头,喉头有些发紧。她见过堂姐去年行承萱礼的模样,那时堂姐趴在锦垫上,牙关紧咬,额上的汗珠砸在青石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直到母亲在她身上缓缓走完三圈,时辰终了时,她后背已是青红交错,却依旧强撑着露出笑容,说“女儿无碍”。那时她只觉心惊,如今身临其境,才知那份惊惧远不及此刻的沉重。
侍女们端来铜壶,为她净手净面,又仔细拂去锦垫上的浮尘。林微晚深吸一口气,褪去外衫,俯身躺在锦垫上。青石的凉意透过锦垫渗进来,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调整呼吸,将双臂贴在身侧,脖颈微微绷紧,做好了承接的准备。
苏婉容缓步走到她身前,目光在女儿纤细的脊背上游移,眸中闪过一丝不忍,却终究化为决绝。她提起裙摆,轻轻将右脚放在女儿的肩胛处。那一瞬间,林微晚只觉肩上一沉,仿佛压了一块温软的石头,紧接着,母亲的左脚也落了下来,重量均匀地铺在她的背上,让她胸腔微微发闷。
“娘要动了。”苏婉容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林微晚咬紧下唇,闷声道:“女儿无碍,娘请便。”
话音刚落,母亲的脚步便缓缓挪动起来。先是从肩胛移向脊背,再从脊背挪至腰腹,每一步都走得极缓,却带着不容抗拒的重量。林微晚能清晰地感受到母亲裙摆扫过自己后颈的触感,还有脚下传来的温热,以及那逐渐加重的压力。腰腹处一阵酸胀,像是有无数根细针在扎,她忍不住皱紧眉头,额上很快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月台周围站着家中的女眷,祖母坐在一旁的太师椅上,目光沉静地望着这一切,手中的佛珠缓缓转动。几位婶婶低声交谈着,语气中带着对晚辈的期许。林微晚不敢分心,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吸气时感受腹部的扩张,呼气时尽量放松紧绷的肌肉。她想起幼时母亲彻夜照顾生病的自己,想起母亲为了供她读书,亲手绣了数十幅帕子去变卖,想起母亲常说的“百善孝为先”。
母亲的脚步依旧平稳,只是每走一圈,林微晚都觉得背上的重量似乎重了一分。肩胛处开始发麻,脊背的酸胀感蔓延开来,连带着四肢都有些僵硬。她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弯月形的红痕,疼痛让她保持着清醒。她不敢出声,怕让母亲担忧,更怕辜负了这份孝道的考验。
不知过了多久,日头渐渐西斜,透过庭院里的梧桐叶,在锦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微晚的后背已经麻木不堪,汗水浸透了中衣,贴在皮肤上,又被风一吹,带来阵阵凉意。她的眼前有些发黑,耳边传来的母亲的脚步声似乎变得遥远,只有祖母手中佛珠转动的声音清晰可闻。
“时辰快到了。”祖母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苏婉容的脚步顿了顿,最后一步落在林微晚的肩胛处,然后缓缓移开。她俯身将女儿扶起,看着她苍白的脸色和湿透的衣衫,眼中的不忍再也掩饰不住,伸手拭去她额上的汗珠:“我的儿,苦了你了。”
林微晚勉强笑了笑,声音带着一丝沙哑:“能为娘尽孝,女儿不苦。”
祖母缓缓起身,走到她面前,抬手抚了抚她鬓边的金钗:“好孩子,你通过了承萱礼,往后便是我林家合格的孝女,有资格侍奉家中长辈了。”她的声音苍老却有力,带着对晚辈的认可。
林微晚望着祖母和母亲眼中的赞许,心中的酸胀与疼痛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她知道,这一辰的坚持,不仅是对母亲的孝,更是对永安王国女子本分的践行。金钗之年,承萱之礼,这烙印在骨血里的孝道,将伴随她往后的人生,指引她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儿,一名值得托付的晚辈。
夕阳下,忍冬花的香气愈发浓郁,林微晚扶着母亲的手,缓缓走出月台,背影虽依旧纤细,却多了一份历经考验后的坚定。
红尘一笑发布于 2026-01-31 09:52
Re: 萱履踏稚骨
金钗踏骨怨
━━━━━━━━━━━━━━━━━
相较于林府承萱礼的肃穆温软,沈府的月台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暮春的阳光被高耸的院墙挡去大半,仅余下几缕斜斜落在青石板上,映得那方素色锦垫愈发单薄。沈清晏趴在锦垫上,后背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额发被冷汗濡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
今日是她的金钗之日,也是她注定难熬的承萱礼。不同于旁人母亲的怜惜,她的母亲沈夫人站在她身后,裙摆扫过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那声音里没有半分温情,只有毫不掩饰的不耐与嫌恶。
“快点趴好,别浪费时辰。”沈夫人的声音尖利,像淬了冰,“你姐姐去年行承礼时,哪像你这般扭捏?若不是族规要求,我倒想看看,你这副不成器的样子,配不配做沈家的女儿。”
沈清晏的肩膀微微颤抖,双手死死抠住锦垫边缘,指甲几乎要嵌进布料里。她知道母亲向来偏爱姐姐沈清欢,姐姐容貌出众,性子讨喜,就连去年的承萱礼,母亲也是轻抬轻放,时辰未到便怜惜地扶她起身。而自己,自小沉默寡言,容貌不及姐姐明艳,便成了母亲眼中的累赘,如今这承萱礼,更成了母亲逐她出门的幌子。
“娘,女儿准备好了。”她的声音细若蚊蚋,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却不敢抬头。
沈夫人冷哼一声,没有丝毫犹豫,径直将双脚重重踩在她的背上。不同于苏婉容的轻缓,沈夫人的落脚带着刻意的力道,仿佛脚下不是亲生女儿的脊背,而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垫脚石。沈清晏只觉后背一阵剧痛,像是被巨石碾过,胸腔里的空气瞬间被挤出去,忍不住闷哼一声。
“哼,才刚站上就忍不住了?”沈夫人的声音带着嘲讽,脚下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我看你还是趁早放弃,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往后也不必留在沈府,省得碍了我和你姐姐的眼。”
沈清晏咬紧牙关,将到了嘴边的痛呼咽了回去。她不能放弃,一旦放弃,便会被逐出家们,成为人人唾弃的不孝女,在这永安王国,再无立足之地。她想起幼时被姐姐抢去糕点,母亲视而不见;想起寒冬腊月,姐姐穿着暖裘,自己却只能裹着单薄的旧衣;想起每次犯错,母亲永远只会打骂她,偏袒姐姐。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想守住这份微薄的亲情,想证明自己并非母亲口中那般不堪。
时辰一点点流逝,沈夫人始终站在她的背上,脚下的力道从未减轻,甚至时不时故意晃动身体,让重量在她脊背各处碾压。沈清晏的后背早已麻木,疼痛顺着脊椎蔓延至四肢百骸,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砸在锦垫上,晕开大片湿痕。她的眼前开始发黑,耳边嗡嗡作响,只能凭着一股执念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
终于,第一阶段的时辰到了。沈夫人猛地抬脚,沈清晏失去支撑,瘫软在锦垫上,后背传来火烧火燎的痛感,让她几乎无法动弹。
“别装死,赶紧起来躺好。”沈夫人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第二阶段若是撑不住,可就怪不得我了。”
沈清晏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缓缓翻过身,躺在锦垫上。她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眼中蓄满了泪水,却倔强地不让它们落下。她褪去外衫,只留一身素白中衣,胸腹腿胯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众人眼前,那份羞耻感比身体的疼痛更让她难以忍受。
沈夫人站在她的头部前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中满是恶意。“记住,这是你自找的。”话音刚落,她便抬起脚,狠狠踩在沈清晏的脸上。
“唔!”沈清晏的脸颊瞬间被踩得变形,牙齿咬到了舌头,血腥味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她想闭上眼睛,却被母亲的脚死死按住,只能被迫承受着这份屈辱。
沈夫人的脚步没有停歇,踩着她的脸颊缓缓移动,尖利的鞋尖划过她的额头、眼窝、鼻梁,留下一道道红痕。接着,她的脚移到了沈清晏的胸口,猛地用力踩踏。沈清晏只觉胸口一阵剧痛,仿佛肋骨都要断裂,呼吸变得极其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吞咽刀片。
“放弃吧,你根本撑不下去。”沈夫人一边踩,一边嘲讽道,“像你这样的废物,根本不配活在沈家。”
她的脚步愈发用力,甚至开始在沈清晏的胸腹间跳踩起来。每一次跳跃落下,都伴随着沈清晏压抑的痛呼,她的腹部剧烈收缩,胃里翻江倒海,却吐不出任何东西。胯部和腿部也未能幸免,沈夫人的脚重重碾过,留下一个个青紫的脚印。
周围的女眷们有的面露不忍,却不敢多言;有的则幸灾乐祸,低声议论着沈清晏的狼狈。沈清晏的视线渐渐模糊,身体的疼痛与心中的屈辱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她击溃。她想起母亲平日里对姐姐的温柔呵护,再对比此刻对自己的残忍,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娘……”她艰难地吐出一个字,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沈夫人停下脚步,低头看着她,眼中带着一丝得意:“怎么?想通了?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沈清晏的目光落在母亲那双精致却沾满了她屈辱的绣鞋上,心中的绝望渐渐化为一股不甘。凭什么?凭什么姐姐可以得到所有偏爱,而自己却要遭受这般对待?她不甘心就这样被逐出家们,不甘心成为别人口中的不孝女。
一股莫名的力量从心底涌出,她猛地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不放弃。”
沈夫人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好!好得很!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她再次抬起脚,力道比之前更加凶狠,跳踩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沈清晏的身体随着母亲的踩踏不断起伏,胸口的疼痛几乎让她窒息,脸上、胸腹、腿胯到处都是青紫的伤痕,嘴角不断溢出鲜血。但她始终咬紧牙关,双目圆睁,死死盯着天空,仿佛要用眼神穿透这厚重的云层。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祖母手中的佛珠终于停止了转动,苍老的声音响起:“时辰……到了。”
沈夫人的脚猛地停在沈清晏的胯部,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愤怒与不甘。她狠狠瞪了沈清晏一眼,用力抬脚,转身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语:“就算通过了又如何?你这辈子,也别想得到我的认可。”
沈清晏躺在锦垫上,浑身动弹不得,只有胸口还在微弱地起伏。她的脸上、身上满是伤痕与污渍,模样狼狈不堪,却缓缓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笑容。她做到了,她没有放弃,她保住了自己的名分,守住了留在沈家的资格。
侍女们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将她扶起。祖母走到她面前,看着她满身的伤痕,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最终化为一声叹息:“好孩子,苦了你了。从今往后,你便是沈家合格的孝女了。”
沈清晏虚弱地靠在侍女身上,望着祖母眼中难得的温和,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这泪水里,有疼痛,有屈辱,更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希望。她知道,往后的日子或许依旧艰难,母亲的偏见不会轻易改变,但她已经用自己的坚持,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院墙的缝隙,洒在沈清晏苍白却坚毅的脸上。金钗之年的承萱礼,于她而言,是一场残酷的试炼,也是一次重生。她的命运,终究没有被母亲的恶意所左右,而是牢牢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
相较于林府承萱礼的肃穆温软,沈府的月台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暮春的阳光被高耸的院墙挡去大半,仅余下几缕斜斜落在青石板上,映得那方素色锦垫愈发单薄。沈清晏趴在锦垫上,后背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额发被冷汗濡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
今日是她的金钗之日,也是她注定难熬的承萱礼。不同于旁人母亲的怜惜,她的母亲沈夫人站在她身后,裙摆扫过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那声音里没有半分温情,只有毫不掩饰的不耐与嫌恶。
“快点趴好,别浪费时辰。”沈夫人的声音尖利,像淬了冰,“你姐姐去年行承礼时,哪像你这般扭捏?若不是族规要求,我倒想看看,你这副不成器的样子,配不配做沈家的女儿。”
沈清晏的肩膀微微颤抖,双手死死抠住锦垫边缘,指甲几乎要嵌进布料里。她知道母亲向来偏爱姐姐沈清欢,姐姐容貌出众,性子讨喜,就连去年的承萱礼,母亲也是轻抬轻放,时辰未到便怜惜地扶她起身。而自己,自小沉默寡言,容貌不及姐姐明艳,便成了母亲眼中的累赘,如今这承萱礼,更成了母亲逐她出门的幌子。
“娘,女儿准备好了。”她的声音细若蚊蚋,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却不敢抬头。
沈夫人冷哼一声,没有丝毫犹豫,径直将双脚重重踩在她的背上。不同于苏婉容的轻缓,沈夫人的落脚带着刻意的力道,仿佛脚下不是亲生女儿的脊背,而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垫脚石。沈清晏只觉后背一阵剧痛,像是被巨石碾过,胸腔里的空气瞬间被挤出去,忍不住闷哼一声。
“哼,才刚站上就忍不住了?”沈夫人的声音带着嘲讽,脚下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我看你还是趁早放弃,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往后也不必留在沈府,省得碍了我和你姐姐的眼。”
沈清晏咬紧牙关,将到了嘴边的痛呼咽了回去。她不能放弃,一旦放弃,便会被逐出家们,成为人人唾弃的不孝女,在这永安王国,再无立足之地。她想起幼时被姐姐抢去糕点,母亲视而不见;想起寒冬腊月,姐姐穿着暖裘,自己却只能裹着单薄的旧衣;想起每次犯错,母亲永远只会打骂她,偏袒姐姐。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想守住这份微薄的亲情,想证明自己并非母亲口中那般不堪。
时辰一点点流逝,沈夫人始终站在她的背上,脚下的力道从未减轻,甚至时不时故意晃动身体,让重量在她脊背各处碾压。沈清晏的后背早已麻木,疼痛顺着脊椎蔓延至四肢百骸,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砸在锦垫上,晕开大片湿痕。她的眼前开始发黑,耳边嗡嗡作响,只能凭着一股执念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
终于,第一阶段的时辰到了。沈夫人猛地抬脚,沈清晏失去支撑,瘫软在锦垫上,后背传来火烧火燎的痛感,让她几乎无法动弹。
“别装死,赶紧起来躺好。”沈夫人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第二阶段若是撑不住,可就怪不得我了。”
沈清晏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缓缓翻过身,躺在锦垫上。她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眼中蓄满了泪水,却倔强地不让它们落下。她褪去外衫,只留一身素白中衣,胸腹腿胯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众人眼前,那份羞耻感比身体的疼痛更让她难以忍受。
沈夫人站在她的头部前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中满是恶意。“记住,这是你自找的。”话音刚落,她便抬起脚,狠狠踩在沈清晏的脸上。
“唔!”沈清晏的脸颊瞬间被踩得变形,牙齿咬到了舌头,血腥味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她想闭上眼睛,却被母亲的脚死死按住,只能被迫承受着这份屈辱。
沈夫人的脚步没有停歇,踩着她的脸颊缓缓移动,尖利的鞋尖划过她的额头、眼窝、鼻梁,留下一道道红痕。接着,她的脚移到了沈清晏的胸口,猛地用力踩踏。沈清晏只觉胸口一阵剧痛,仿佛肋骨都要断裂,呼吸变得极其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吞咽刀片。
“放弃吧,你根本撑不下去。”沈夫人一边踩,一边嘲讽道,“像你这样的废物,根本不配活在沈家。”
她的脚步愈发用力,甚至开始在沈清晏的胸腹间跳踩起来。每一次跳跃落下,都伴随着沈清晏压抑的痛呼,她的腹部剧烈收缩,胃里翻江倒海,却吐不出任何东西。胯部和腿部也未能幸免,沈夫人的脚重重碾过,留下一个个青紫的脚印。
周围的女眷们有的面露不忍,却不敢多言;有的则幸灾乐祸,低声议论着沈清晏的狼狈。沈清晏的视线渐渐模糊,身体的疼痛与心中的屈辱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她击溃。她想起母亲平日里对姐姐的温柔呵护,再对比此刻对自己的残忍,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娘……”她艰难地吐出一个字,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沈夫人停下脚步,低头看着她,眼中带着一丝得意:“怎么?想通了?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沈清晏的目光落在母亲那双精致却沾满了她屈辱的绣鞋上,心中的绝望渐渐化为一股不甘。凭什么?凭什么姐姐可以得到所有偏爱,而自己却要遭受这般对待?她不甘心就这样被逐出家们,不甘心成为别人口中的不孝女。
一股莫名的力量从心底涌出,她猛地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不放弃。”
沈夫人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好!好得很!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她再次抬起脚,力道比之前更加凶狠,跳踩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沈清晏的身体随着母亲的踩踏不断起伏,胸口的疼痛几乎让她窒息,脸上、胸腹、腿胯到处都是青紫的伤痕,嘴角不断溢出鲜血。但她始终咬紧牙关,双目圆睁,死死盯着天空,仿佛要用眼神穿透这厚重的云层。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祖母手中的佛珠终于停止了转动,苍老的声音响起:“时辰……到了。”
沈夫人的脚猛地停在沈清晏的胯部,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愤怒与不甘。她狠狠瞪了沈清晏一眼,用力抬脚,转身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语:“就算通过了又如何?你这辈子,也别想得到我的认可。”
沈清晏躺在锦垫上,浑身动弹不得,只有胸口还在微弱地起伏。她的脸上、身上满是伤痕与污渍,模样狼狈不堪,却缓缓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笑容。她做到了,她没有放弃,她保住了自己的名分,守住了留在沈家的资格。
侍女们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将她扶起。祖母走到她面前,看着她满身的伤痕,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最终化为一声叹息:“好孩子,苦了你了。从今往后,你便是沈家合格的孝女了。”
沈清晏虚弱地靠在侍女身上,望着祖母眼中难得的温和,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这泪水里,有疼痛,有屈辱,更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希望。她知道,往后的日子或许依旧艰难,母亲的偏见不会轻易改变,但她已经用自己的坚持,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院墙的缝隙,洒在沈清晏苍白却坚毅的脸上。金钗之年的承萱礼,于她而言,是一场残酷的试炼,也是一次重生。她的命运,终究没有被母亲的恶意所左右,而是牢牢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红尘一笑发布于 2026-01-31 09:52
Re: 萱履踏稚骨
膝前承履微
━━━━━━━━━━━━━━━━━
沈清晏是被胸口的钝痛惊醒的。
睁开眼时,屋内的光线已近昏黄,窗棂外斜斜映着几缕残阳,将案上的青铜烛台拖出长长的影子。身下是柔软的锦被,盖在身上却暖不透四肢百骸的凉意,后背与胸腹的旧伤被被褥摩挲着,传来一阵阵细密的疼,提醒着她晕倒前的剧烈折磨。
昨日午后,母亲让她跪在妆台前侍奉梳头,不过是梳齿稍稍勾住了几根发丝,便惹来母亲勃然大怒。沈夫人摔了玉梳,抬脚便往她胸口踹去,接着便踩着她的脊背来回踱步,口中的辱骂如淬毒的针,句句扎在她心上。“没用的废物!连梳个头都做不好,留你在身边不过是碍眼!”“早知道你这般不成器,当初承萱礼就该让你直接死在月台上!”
她死死咬着牙,趴在冰冷的地面上,任由母亲的绣鞋碾过肩头的旧伤,直到眼前发黑,意识彻底沉入黑暗。
此刻醒来,鼻尖萦绕着一股淡淡的药香,想来是有人为她敷过伤药。沈清晏动了动手指,正想撑起身子,却瞥见床榻边坐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母亲。
沈夫人依旧穿着那身石青色的褙子,只是褪去了发间的碧玉簪,仅用一根素银簪固定着发髻,侧脸的轮廓在昏黄的光线下显得柔和了些许。她没有看她,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指尖,神色晦暗不明。
沈清晏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自她通过承萱礼,获得侍奉母亲的资格后,母亲从未这般安静地待在她身边过。这些日子,她每日天不亮便起身,为母亲整理妆奁、准备早膳、捶背揉肩,哪怕做得再好,换来的也只是无端的辱骂与苛待。母亲会故意打翻她端来的汤药,会在她侍奉更衣时用力推搡,甚至会在寒冬腊月让她跪在雪地里反省,理由只是“看你不顺眼”。
可此刻,母亲眼底那一闪而过的不忍,像投入寒潭的一颗石子,在她心中漾开圈圈涟漪。方才她睁眼的刹那,分明看见母亲的目光落在她苍白的脸上,那双素来盛满嫌恶的眼眸里,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虽转瞬即逝,却被她牢牢捕捉。
她知道,母亲的心,并非顽石。
沈清晏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猛地掀开锦被,挣扎着从床榻上滚下来。“咚”的一声,膝盖重重磕在冰冷的金砖地面上,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后背的伤口也因这剧烈的动作被牵扯,传来撕裂般的痛感。
“你做什么?”沈夫人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到,下意识地皱起眉头,语气依旧冰冷,却少了几分往日的刻薄。
沈清晏伏在地上,额头几乎贴到地面,姿态卑微到了极点。“女儿不孝,让母亲担忧了。”她的声音带着刚醒时的沙哑,还夹杂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女儿身子顽健,些许伤痛不算什么,断不能因这点小事误了侍奉母亲的时辰。”
她说着,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母亲放在膝上的双脚上。那双脚穿着绣着缠枝莲纹的软缎绣鞋,鞋面光洁如新,是她昨日才亲手擦拭干净的。她忍着身上的剧痛,一点点挪到母亲脚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握住了母亲的脚踝。
沈夫人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想要抽回脚,却被沈清晏轻轻按住。
“母亲,让女儿为您捶捶腿、揉揉脚吧。”沈清晏的声音温顺得像只羔羊,“这些日子女儿侍奉不周,惹母亲生气,还请母亲责罚。只是女儿心中唯有一片孝心,只想好好侍奉母亲,还望母亲能给女儿这个机会。”
她低下头,开始轻轻为母亲揉捏小腿。动作轻柔而虔诚,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轻而毫无作用,也不会太重而让母亲不适。她的手指纤细,却带着一股韧劲,顺着母亲的小腿肌肉缓缓推拿,试图缓解母亲久坐后的酸胀。
沈夫人沉默地看着伏在脚边的女儿,目光复杂。眼前的少女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素衣,后背的衣衫因方才的动作被扯得有些歪斜,隐约能看见下面青紫交错的伤痕。她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肩头,额头上还带着未干的虚汗,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可那双眼睛里,却盛满了执着与谦卑,没有丝毫怨怼。
沈夫人想起昨日自己那般用力地踩踏她,想起她晕倒时毫无生气的模样,心中那丝被强行压抑下去的不忍,又悄然冒了出来。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冷哼,偏过头去,不再看她。
沈清晏却像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揉捏的动作愈发轻柔。她知道,母亲没有推开她,没有辱骂她,便是一种默许。这一点点的转变,对她而言,已是黑暗中的一缕微光,足以支撑她熬过所有的苦难。
她伏在地上,额头始终低着,不敢有丝毫懈怠。烛光摇曳,将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冰冷的地面上,像一幅执着而卑微的剪影。身上的伤痛依旧清晰,可她的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暖意。
她知道,母亲的偏见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往后的日子或许依旧充满了艰难与屈辱。但她不后悔,也不会放弃。金钗之年的承萱礼,她凭着一股执念熬了过来;这些日子的辱骂与虐待,她也一一承受。如今,母亲眼中那一闪而过的不忍,让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只要她心中的孝心不变,只要她始终坚守这份本分,总有一天,母亲会真正接纳她的吧。
沈清晏这样想着,手下的动作愈发温柔。屋内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她轻柔的呼吸声,以及指尖摩擦布料的细微声响。窗外的残阳渐渐落下,夜色悄然降临,而膝前的这份侍奉,却像是一首无声的孝道之歌,在寂静的屋内缓缓流淌。
━━━━━━━━━━━━━━━━━
沈清晏是被胸口的钝痛惊醒的。
睁开眼时,屋内的光线已近昏黄,窗棂外斜斜映着几缕残阳,将案上的青铜烛台拖出长长的影子。身下是柔软的锦被,盖在身上却暖不透四肢百骸的凉意,后背与胸腹的旧伤被被褥摩挲着,传来一阵阵细密的疼,提醒着她晕倒前的剧烈折磨。
昨日午后,母亲让她跪在妆台前侍奉梳头,不过是梳齿稍稍勾住了几根发丝,便惹来母亲勃然大怒。沈夫人摔了玉梳,抬脚便往她胸口踹去,接着便踩着她的脊背来回踱步,口中的辱骂如淬毒的针,句句扎在她心上。“没用的废物!连梳个头都做不好,留你在身边不过是碍眼!”“早知道你这般不成器,当初承萱礼就该让你直接死在月台上!”
她死死咬着牙,趴在冰冷的地面上,任由母亲的绣鞋碾过肩头的旧伤,直到眼前发黑,意识彻底沉入黑暗。
此刻醒来,鼻尖萦绕着一股淡淡的药香,想来是有人为她敷过伤药。沈清晏动了动手指,正想撑起身子,却瞥见床榻边坐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母亲。
沈夫人依旧穿着那身石青色的褙子,只是褪去了发间的碧玉簪,仅用一根素银簪固定着发髻,侧脸的轮廓在昏黄的光线下显得柔和了些许。她没有看她,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指尖,神色晦暗不明。
沈清晏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自她通过承萱礼,获得侍奉母亲的资格后,母亲从未这般安静地待在她身边过。这些日子,她每日天不亮便起身,为母亲整理妆奁、准备早膳、捶背揉肩,哪怕做得再好,换来的也只是无端的辱骂与苛待。母亲会故意打翻她端来的汤药,会在她侍奉更衣时用力推搡,甚至会在寒冬腊月让她跪在雪地里反省,理由只是“看你不顺眼”。
可此刻,母亲眼底那一闪而过的不忍,像投入寒潭的一颗石子,在她心中漾开圈圈涟漪。方才她睁眼的刹那,分明看见母亲的目光落在她苍白的脸上,那双素来盛满嫌恶的眼眸里,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虽转瞬即逝,却被她牢牢捕捉。
她知道,母亲的心,并非顽石。
沈清晏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猛地掀开锦被,挣扎着从床榻上滚下来。“咚”的一声,膝盖重重磕在冰冷的金砖地面上,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后背的伤口也因这剧烈的动作被牵扯,传来撕裂般的痛感。
“你做什么?”沈夫人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到,下意识地皱起眉头,语气依旧冰冷,却少了几分往日的刻薄。
沈清晏伏在地上,额头几乎贴到地面,姿态卑微到了极点。“女儿不孝,让母亲担忧了。”她的声音带着刚醒时的沙哑,还夹杂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女儿身子顽健,些许伤痛不算什么,断不能因这点小事误了侍奉母亲的时辰。”
她说着,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母亲放在膝上的双脚上。那双脚穿着绣着缠枝莲纹的软缎绣鞋,鞋面光洁如新,是她昨日才亲手擦拭干净的。她忍着身上的剧痛,一点点挪到母亲脚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握住了母亲的脚踝。
沈夫人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想要抽回脚,却被沈清晏轻轻按住。
“母亲,让女儿为您捶捶腿、揉揉脚吧。”沈清晏的声音温顺得像只羔羊,“这些日子女儿侍奉不周,惹母亲生气,还请母亲责罚。只是女儿心中唯有一片孝心,只想好好侍奉母亲,还望母亲能给女儿这个机会。”
她低下头,开始轻轻为母亲揉捏小腿。动作轻柔而虔诚,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轻而毫无作用,也不会太重而让母亲不适。她的手指纤细,却带着一股韧劲,顺着母亲的小腿肌肉缓缓推拿,试图缓解母亲久坐后的酸胀。
沈夫人沉默地看着伏在脚边的女儿,目光复杂。眼前的少女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素衣,后背的衣衫因方才的动作被扯得有些歪斜,隐约能看见下面青紫交错的伤痕。她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肩头,额头上还带着未干的虚汗,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可那双眼睛里,却盛满了执着与谦卑,没有丝毫怨怼。
沈夫人想起昨日自己那般用力地踩踏她,想起她晕倒时毫无生气的模样,心中那丝被强行压抑下去的不忍,又悄然冒了出来。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冷哼,偏过头去,不再看她。
沈清晏却像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揉捏的动作愈发轻柔。她知道,母亲没有推开她,没有辱骂她,便是一种默许。这一点点的转变,对她而言,已是黑暗中的一缕微光,足以支撑她熬过所有的苦难。
她伏在地上,额头始终低着,不敢有丝毫懈怠。烛光摇曳,将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冰冷的地面上,像一幅执着而卑微的剪影。身上的伤痛依旧清晰,可她的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暖意。
她知道,母亲的偏见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往后的日子或许依旧充满了艰难与屈辱。但她不后悔,也不会放弃。金钗之年的承萱礼,她凭着一股执念熬了过来;这些日子的辱骂与虐待,她也一一承受。如今,母亲眼中那一闪而过的不忍,让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只要她心中的孝心不变,只要她始终坚守这份本分,总有一天,母亲会真正接纳她的吧。
沈清晏这样想着,手下的动作愈发温柔。屋内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她轻柔的呼吸声,以及指尖摩擦布料的细微声响。窗外的残阳渐渐落下,夜色悄然降临,而膝前的这份侍奉,却像是一首无声的孝道之歌,在寂静的屋内缓缓流淌。
红尘一笑发布于 2026-01-31 09:53
Re: 萱履踏稚骨
骨碎逐门寒
━━━━━━━━━━━━━━━━━
沈清晏的日子刚有一丝暖意,便被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彻底浇灭。
那日是沈府老太太的寿辰,府中宾客盈门,处处张灯结彩。沈清晏天未亮便起身,亲手为母亲缝制了一方绣着萱草纹的丝帕,又细细熬了母亲最爱的莲子羹,满心期盼能借着寿辰的喜庆,让母女关系再近一步。
她端着莲子羹来到母亲的院落时,却见姐姐沈清欢正依偎在母亲身边,手中拿着一支断裂的玉簪,眼眶红红地抹着眼泪。沈夫人脸色铁青,见她进来,眼中瞬间燃起熊熊怒火。
“你这个忤逆女!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沈夫人猛地拍案而起,指着她的鼻子厉声呵斥。
沈清晏愣在原地,端着莲子羹的手微微颤抖:“母亲,女儿……女儿不知做错了什么。”
“不知?”沈清欢抬起头,泪水涟涟,却难掩眼底的得意,“妹妹,你怎能如此狠心?母亲最心爱的这支羊脂玉簪,是外祖父生前赠予母亲的遗物,你竟为了报复母亲平日对你的严苛,偷偷将它摔碎!方才我在你房中整理衣物,亲眼看见簪子的碎片藏在你的枕下!”
“我没有!”沈清晏脸色煞白,急忙辩解,“姐姐,我从未见过这支玉簪,更不会做出这般大逆不道之事!你定是弄错了!”
“弄错?”沈夫人几步走到她面前,扬手便是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屋内回荡,沈清晏被打得偏过头去,嘴角瞬间溢出鲜血。“清欢何时骗过我?她说在你房中找到,便是你干的!我平日虽对你严苛,可你怎能记恨至此,毁掉我最珍视的东西?你的孝心,全是装出来的!”
沈清晏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她看着母亲眼中毫不掩饰的厌恶,看着姐姐嘴角那抹一闪而过的奸计得逞,心中那点刚刚萌芽的希望,瞬间化为灰烬。她终于明白,姐姐早已嫉妒母亲对她态度的微妙转变,竟用如此恶毒的手段陷害她。
“母亲,女儿真的没有……”她还想再辩解,却被沈夫人一脚踹在胸口。
剧痛传来,沈清晏踉跄着后退几步,手中的莲子羹摔在地上,瓷碗碎裂的声音刺耳至极。“还敢狡辩!”沈夫人怒不可遏,眼中的冰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刺骨,“我看你这承萱礼的孝道,全是熬出来的假象!今日我便要好好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是尊卑,什么是孝道!”
沈夫人厉声吩咐侍女:“把她拖出去,扔在院子里!我倒要看看,这忤逆女的骨头有多硬!”
两名侍女面有难色,却不敢违抗主母的命令,只能上前架起浑身发软的沈清晏,将她拖到院落中央的青石板上。沈清晏挣扎着,却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一步步走向自己,眼中满是决绝的杀意。
“母亲,求您信我一次……”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带着无尽的绝望。
沈夫人却丝毫没有动容,她提起裙摆,抬脚便狠狠踩在沈清晏的胸口。这一脚比承萱礼时还要用力,沈清晏只觉胸口一阵剧痛,仿佛肋骨都被踩断,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染红了身前的青石板。
“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忤逆我的!”沈夫人一边骂,一边用力地在她身上来回踩踏。绣鞋的鞋尖狠狠碾过她的胸腹、胯部,甚至踩在她的脸上,让她无法呼吸。“你姐姐温柔孝顺,哪点不比你强?你这个废物,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
沈清欢站在廊下,看着妹妹被母亲踩得奄奄一息,脸上露出一抹扭曲的笑容。她要的就是这样,沈清晏永远都不能抢走母亲的关注,永远都只能是她的垫脚石。
沈清晏的意识渐渐模糊,身上的疼痛早已超出了承受的极限,每一次踩踏都像是在碾碎她的骨头。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流失,鲜血从嘴角不断涌出,视线也越来越模糊。她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悲凉。
她那么努力地去孝顺母亲,那么卑微地去祈求母亲的认可,可到头来,却还是抵不过姐姐的一句谎言,抵不过母亲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谓的孝道,所谓的资格,在这一刻,都成了天大的笑话。
“母亲……”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两个字,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
沈夫人踩着她的胸口,喘着粗气,眼中的怒火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茫然。她看着地上气息奄奄的女儿,浑身是血,毫无生气,心中那丝被强行压制的不忍再次浮现,却被她强行压了下去。“这般忤逆不孝,留你何用?”
她猛地抬脚,冷冷吩咐道:“把她拖出府去,扔到乱葬岗附近!从今往后,沈府再没有你这个女儿!”
侍女们不敢耽搁,连忙找来一块破席,将气若游丝的沈清晏裹了起来,拖着她往府外走去。沈清晏的头无力地垂着,嘴角的鲜血滴落在青石板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血痕,像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沈清欢走到母亲身边,轻轻扶住她的胳膊,柔声安慰:“母亲息怒,妹妹这般不孝,被逐出去也是活该。往后女儿会加倍孝顺母亲,不让母亲再受半点委屈。”
沈夫人看着懂事的大女儿,脸色稍缓,却在转身的瞬间,不经意间瞥见地上那方掉落的萱草纹丝帕。丝帕被鲜血浸染,却依旧能看出绣工的细腻与虔诚。她的心脏猛地一缩,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上心头,却终究还是被她压了下去,转身走进了屋内,关上了那扇隔绝了所有温情的大门。
府外,冷风呼啸,卷着尘土,将那抹单薄的身影拖向未知的黑暗。沈清晏残存的意识里,只剩下母亲冰冷的眼神和踩在身上的剧痛,以及那句彻底击碎她所有希望的话语——
“沈府再没有你这个女儿。”
━━━━━━━━━━━━━━━━━
沈清晏的日子刚有一丝暖意,便被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彻底浇灭。
那日是沈府老太太的寿辰,府中宾客盈门,处处张灯结彩。沈清晏天未亮便起身,亲手为母亲缝制了一方绣着萱草纹的丝帕,又细细熬了母亲最爱的莲子羹,满心期盼能借着寿辰的喜庆,让母女关系再近一步。
她端着莲子羹来到母亲的院落时,却见姐姐沈清欢正依偎在母亲身边,手中拿着一支断裂的玉簪,眼眶红红地抹着眼泪。沈夫人脸色铁青,见她进来,眼中瞬间燃起熊熊怒火。
“你这个忤逆女!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沈夫人猛地拍案而起,指着她的鼻子厉声呵斥。
沈清晏愣在原地,端着莲子羹的手微微颤抖:“母亲,女儿……女儿不知做错了什么。”
“不知?”沈清欢抬起头,泪水涟涟,却难掩眼底的得意,“妹妹,你怎能如此狠心?母亲最心爱的这支羊脂玉簪,是外祖父生前赠予母亲的遗物,你竟为了报复母亲平日对你的严苛,偷偷将它摔碎!方才我在你房中整理衣物,亲眼看见簪子的碎片藏在你的枕下!”
“我没有!”沈清晏脸色煞白,急忙辩解,“姐姐,我从未见过这支玉簪,更不会做出这般大逆不道之事!你定是弄错了!”
“弄错?”沈夫人几步走到她面前,扬手便是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屋内回荡,沈清晏被打得偏过头去,嘴角瞬间溢出鲜血。“清欢何时骗过我?她说在你房中找到,便是你干的!我平日虽对你严苛,可你怎能记恨至此,毁掉我最珍视的东西?你的孝心,全是装出来的!”
沈清晏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她看着母亲眼中毫不掩饰的厌恶,看着姐姐嘴角那抹一闪而过的奸计得逞,心中那点刚刚萌芽的希望,瞬间化为灰烬。她终于明白,姐姐早已嫉妒母亲对她态度的微妙转变,竟用如此恶毒的手段陷害她。
“母亲,女儿真的没有……”她还想再辩解,却被沈夫人一脚踹在胸口。
剧痛传来,沈清晏踉跄着后退几步,手中的莲子羹摔在地上,瓷碗碎裂的声音刺耳至极。“还敢狡辩!”沈夫人怒不可遏,眼中的冰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刺骨,“我看你这承萱礼的孝道,全是熬出来的假象!今日我便要好好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是尊卑,什么是孝道!”
沈夫人厉声吩咐侍女:“把她拖出去,扔在院子里!我倒要看看,这忤逆女的骨头有多硬!”
两名侍女面有难色,却不敢违抗主母的命令,只能上前架起浑身发软的沈清晏,将她拖到院落中央的青石板上。沈清晏挣扎着,却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一步步走向自己,眼中满是决绝的杀意。
“母亲,求您信我一次……”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带着无尽的绝望。
沈夫人却丝毫没有动容,她提起裙摆,抬脚便狠狠踩在沈清晏的胸口。这一脚比承萱礼时还要用力,沈清晏只觉胸口一阵剧痛,仿佛肋骨都被踩断,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染红了身前的青石板。
“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忤逆我的!”沈夫人一边骂,一边用力地在她身上来回踩踏。绣鞋的鞋尖狠狠碾过她的胸腹、胯部,甚至踩在她的脸上,让她无法呼吸。“你姐姐温柔孝顺,哪点不比你强?你这个废物,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
沈清欢站在廊下,看着妹妹被母亲踩得奄奄一息,脸上露出一抹扭曲的笑容。她要的就是这样,沈清晏永远都不能抢走母亲的关注,永远都只能是她的垫脚石。
沈清晏的意识渐渐模糊,身上的疼痛早已超出了承受的极限,每一次踩踏都像是在碾碎她的骨头。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流失,鲜血从嘴角不断涌出,视线也越来越模糊。她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悲凉。
她那么努力地去孝顺母亲,那么卑微地去祈求母亲的认可,可到头来,却还是抵不过姐姐的一句谎言,抵不过母亲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谓的孝道,所谓的资格,在这一刻,都成了天大的笑话。
“母亲……”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两个字,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
沈夫人踩着她的胸口,喘着粗气,眼中的怒火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茫然。她看着地上气息奄奄的女儿,浑身是血,毫无生气,心中那丝被强行压制的不忍再次浮现,却被她强行压了下去。“这般忤逆不孝,留你何用?”
她猛地抬脚,冷冷吩咐道:“把她拖出府去,扔到乱葬岗附近!从今往后,沈府再没有你这个女儿!”
侍女们不敢耽搁,连忙找来一块破席,将气若游丝的沈清晏裹了起来,拖着她往府外走去。沈清晏的头无力地垂着,嘴角的鲜血滴落在青石板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血痕,像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沈清欢走到母亲身边,轻轻扶住她的胳膊,柔声安慰:“母亲息怒,妹妹这般不孝,被逐出去也是活该。往后女儿会加倍孝顺母亲,不让母亲再受半点委屈。”
沈夫人看着懂事的大女儿,脸色稍缓,却在转身的瞬间,不经意间瞥见地上那方掉落的萱草纹丝帕。丝帕被鲜血浸染,却依旧能看出绣工的细腻与虔诚。她的心脏猛地一缩,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上心头,却终究还是被她压了下去,转身走进了屋内,关上了那扇隔绝了所有温情的大门。
府外,冷风呼啸,卷着尘土,将那抹单薄的身影拖向未知的黑暗。沈清晏残存的意识里,只剩下母亲冰冷的眼神和踩在身上的剧痛,以及那句彻底击碎她所有希望的话语——
“沈府再没有你这个女儿。”
一名路人最佳读者发布于 2026-01-31 18:49
Re: 萱履踏稚骨
有空行👍 這種格式看著舒服
a449291917发布于 2026-02-01 03:29
Re: 萱履踏稚骨
还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