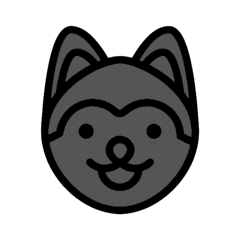红底鞋下的圣餐 Holy Communion Under the Red Sole [含插图]
连载中原创翻译现实足控裸足原味鞋靴高跟鞋长靴舔鞋
故事很好,但是英文版的英语很差。感觉英文版也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
AI艺术令人惊叹
第9章 皮革护理
对Mat来说,这又是一天的常态收场——当然,如果能把Becky那种充满暴力的戏码称作“常态”的话。
那天他们在一辆迈巴赫的后座,车在潮湿而带电的纽约夜里滑行。防弹深色玻璃外,一切都被闪光和噪声揉成了一片模糊。车在红灯前被困,四周被一群狗仔围着,拳头有节奏地敲着车窗。闪光不停地炸开,把密闭的车厢变成了一间令人眩晕的白色迪厅。
Becky坐在皮椅里,腿交叉,像个寒冰女王,外头再怎么喧哗她也纹丝不动。天已渐暗,她却还戴着大墨镜,握着一只装着气泡水的水晶杯,关节白得像要爆裂。她不看外面,只盯着前方,下颏紧绷,脸上是一种冷到骨子里的恼怒。
“都是畜生,”她低声吐出,那口气像把人群的模糊嚷声切开,“听他们叫,叫我的名字,好像能把我分一块似的。”
她利落按下控制板,拉起了隐私隔板。车厢立刻沉进柔软的黑暗,只有地板的氛围灯和Mat手里平板发出的冷光。
Mat照惯例跪在地上,挤在座椅之间,像端盘子的侍者一样用前臂托着平板。屏幕上正是今晚闹得沸沸扬扬的那篇帖子。
Becky踢掉高跟鞋——红底、黑亮漆皮,锋利得像武器——任由鞋子落在地毯上。她伸出穿着丝袜的脚,把脚底稳稳顶在Mat胸口中央,往后一蹬,给自己留出一片未容侵犯的私人空间。
“念给我听,”她吩咐,举杯随意示意平板,“念念他们今天放了些什么鬼话。为啥围得这么凶?我穿错时装了吗?Camilla又去拿绳子试挂自己脖子了?”
Mat低头看屏幕。是个八卦网站,版面刺眼、逼人。标题用粗黄字嚷着:冰皇后要溶化了?神秘男子与时尚铁娘子同框?
下面是一张三天前的模糊照,拍到Becky从酒店出来,光鲜又疏离。远处有个模糊的人影,是Mat,他打着伞,镜头无情定格了他看她时那种彻底、绝对的崇拜。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静谧的车厢里干涩发紧。
“上面写着……”Mat迟疑,眼睛在字里跳动,“‘接近设计师的人士称她有个秘密情人,一个黑暗神秘的人影多次出入她的私人套房。那个曾说‘把事业当婚姻’的女人,难道终于恋爱了?’”
车静了一会儿。绿灯一亮,车平稳驶离,把人群和混乱甩在身后。Becky盯着Mat看。她在墨镜后眨了下眼,慢慢把墨镜摘下,露出一双因真心厌恶而瞪大的眼睛。
“情人?”
她把那个词念得像Mat在车上吐了口什么脏东西似的。
“他们居然觉得……”她用修得一丝不苟的手指指着自己胸口,又往下指向他,“……我和你有一腿?你是我男朋友?”
想法的荒谬像一记当头棒喝,打碎了她的恼怒,化成不真实又刺耳的笑。那笑既冷酷又磨人,狠狠地擦掉了Mat的自尊。她笑到眼角流出泪,才强行抹去。
“哦,这真幽默。真是笑死我了。‘神秘男人’、‘秘密情人’。”
她猛地前倾,一把揪住Mat领带的结,把他拽近,脸几乎贴到他面前。
“看你,”她低声说,满是轻蔑,“我多看你一眼你就发抖。你膝盖被地毯磨出青印。你穿的是我给你买的西装,因为你自己的破衣服伤我眼。”
她一把松开他的领带,带着不屑的推开Mat。
“男朋友是平等的。男朋友是那种我得——天哪——需要我和他妥协的人。你就是……一个配饰。一个会写代码的有灵性的手袋。”
她抢过手机自己翻起文章来,讥讽念出评论,“看这个,‘他看起来好带感’、‘他看起来好投入’。他们把这事浪漫化了!当成《五十度灰》那套。”
她把手机扔回座位,冷冷盯着他,眼里有算计的狠意。
“这不能接受。会毁了我的牌子。我的牌子是‘高不可攀’。我的牌子是‘我不需要男人’。要是他们以为我在为某个……技术员……牵肠挂肚,我就显得软弱。就和其他养小鲜肉的无聊名媛一样了。”
她又把脚伸出来,脚弓在Mat肩上摩挲,借他的身体揉着抽筋的肌肉。
“解决它,”她下命令,“给我灭掉谣言。我不在乎你怎么做。删照片。黑掉小报。或者——”
她嘴角浮起个坏笑,黑暗里冒出主意,“——更好。给他们一个新故事。说清楚你到底是谁。但要让你彻底成为小丑,让全世界没有女人会羡慕我。告诉我,巫师……我们该让世界以为你是什么?保镖?太监?还是施舍对象?”
沉默压得Mat几乎喘不过气来,比外头的潮湿还沉重。那种被当成平等的暗示在车里弥漫成毒气。他知道必须马上打消这念头,不只是为自保,更为了把她的世界秩序重新摆正。
“请原谅我,主人,”Mat低语,声线平稳,但心跳在衣领里咚咚跳,“媒体……他们太自以为是。他们没有资格理解你所处的那种层次。说我和你平等,是在侮辱你。”
他硬着头皮抬眼,望向那双被随意丢在地上的细跟,红底在微光中隐隐发亮。
“如果照片里总看到我跪着,”他接着说,脑子里飞速想出最讨她欢心的说法,“那就告诉他们:我就该在那里。不是伴侣,而是必需品。一个工具。”
他吞口唾沫,然后说道出那个头衔。
“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擦鞋匠。告诉他们我总低着头,是因为我怕漏掉你皮鞋上的一条划痕。”
Becky听他道歉,面无表情。但当他喊出“私人擦鞋匠”,她的表情有了变化。眼里闪出冷冽的光,不是暖意,而是像钻石切面被精准找到的那种冷亮。
她慢慢放下气泡水,杯壁的冷凝让指尖凉了下去。红唇微勾出个狠笑。她看着跪着的Mat,又看向自己光裸的脚,最后落到旁边那双黑漆高跟上。
“擦鞋匠,”她轻声咂着,像品一杯好酒,“专职……皮革保养师。”
她短促地笑了,打破了紧张,却把气氛变得更沉、更危险。
“好主意。残忍、绝妙,又把一切解释清楚,不是吗?”她指了指他们的场景,“你为什么总跪着?因为你在工作。你为什么总低头?因为你在专注于皮鞋的光泽。你为什么总和我在一起?因为纽约很脏,我需要人随时维护我的形象。”
她伸脚,使劲把脚趾顶在他脸上,把他的脸转向她,好在昏暗里端详他那顺从卑微的表情。
“你说得对。如果我说你是我情人,他们会以为我降低标准。但如果我说你是我特地雇来保持鞋面完美的专职仆人……他们不会同情我。他们会崇拜我的奢侈和品味。”
她收回脚,响指一弹,声音像鞭响,“把那套东西拿来。就在座位下面,我知道你放着。”
Mat下意识地伸手到皮座下面,取出那个小小的、里头有绒的盒子,里面是鞋油和刷子。Becky在他上方解锁手机,打开社交App,拇指悬在摄像头图标上。
“我们现在就掐灭这个谣言,”她宣布,声音里带着施计的兴奋,“我们拍个‘开箱’视频。但不是开新皮包……我要开箱我的新家电。”
她把红底高跟踢给他,鞋在地毯上划过,停在他膝边。
“把鞋穿到我脚上。然后拿抹布,拿鞋油。我录像,你给我好好擦,擦到鞋面能照出我的脸来。同时嘛……”
她举起手机,调好角度,让光线把她颧骨衬得更立体。
“……你要看着镜头,自我介绍。说出你的作用。说说你有多幸运能摸到我走过的地面,让那帮只能远远拍照的狗仔们好好羡慕羡慕。”
她按下录制。场面立刻变化。
“你们好,我的宝贝们,”她对着手机撒娇,声音里是假意亲密,正是公众爱看的那套,“我看到了那些传闻。‘秘密男友’?拜托。我没空谈恋爱,但我有时间坚守时尚界的标准。”
她把镜头指向车厢下方,取景到跪在狭小空隙里抱着贵鞋的Mat,他抬头像膜拜神像的信徒。
“说吧,”她从镜头后命令,声音重新冷厉,“告诉他们你是什么人。”
Becky稳稳拿着手机,录制点红得像心跳。她在等他的开口,等他用言语当众自贬,承认自己的奴性。
但Mat没有说话。
他没看镜头,也没看她的脸。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只剩下那只黑漆皮高跟。他像雕匠抛光宝石般小心地上蜡,动作有节奏、催眠、痴迷。他把那鞋当神物,必须绝对安静对待。
Becky看着屏幕,精致的眉轻蹙了一瞬,露出疑惑。
“我说,赶紧说两句,”她从镜头后嗤声催促,声音被空调的嗡鸣轻轻掩盖,“说话啊。”
Mat停了一下,慢慢抬头,但仍拒绝对镜头有任何反应。他把视线盯着她的脚,缓缓摇头,带着一种悲然。他举手指向嘴巴,然后做了一个“锁上”的手势——像把无形的钥匙扭了个圈丢进车厢黑暗。
随后,他合掌祈祷,深深低头,把额头贴在刚擦净的鞋尖上,像在做一段无声的礼拜。
Becky盯着他。车里沉默异常厚重。
然后,她脸上裂出一种纯粹的、毫无掩饰的欢愉。她看懂了这即兴表演,也彻底喜爱它。
她轻笑,语气由高傲变柔情,那种做作的怜悯比她的愤怒更会操纵观众。
“哦……哦,我可怜的小心肝们,”她对粉丝低喃,声音里满是演出来的怜悯,“我居然忘了。他在灯光下会受不了。你看……他是天生的残疾,说不出话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她的手悬在Mat肩上,好像在施祝福,把他塑造成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生物。
“我不是因为需要仆人才雇他。我给他这份工作,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对像他这样的人太吵了。他没有你们或我那样的说话和倾听的能力。他把所有的感激和专注都投入到工作里。他不是‘男朋友’。天哪,不,那样是在占他便宜。”
她用手轻触他的肩膀,给镜头看。
“他是个修行者,一个伟大的无声修士。我很高兴能给他个归处。”
她把镜头切回自己,光彩照人、谦逊而高不可攀。
“所以,请不要再造那些残酷的谣言。要善待那些在沉默中奉献的人。我只是给他鞋子,他却给我光鲜的形象,对我们时尚界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她关掉录制。
面具一落,她把手机扔回皮座,低头看着他,眼里的笑既戏弄又欣赏。
“你即兴发挥得很好,”她说着,用现在闪亮的鞋把他蹭得更狠,“这份沉默的誓言,真是有创意。”
她靠回靠背,抚下巴若有所思。
“这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你不能说话,你就不能出庭作证;你就不能抱怨。你看起来就更像个物件——一个让大众怜惜的无声工具。”
她笑,带着占有欲的阴冷。
“我喜欢。就这么定。从今以后,公众面前你不准说话。你只能用侍奉我的方式交流。”
迈巴赫缓缓停稳,碎石在轮下发出声响,他们到了庄园。
“我们回家了。既然你现在正式成为我的‘沉默擦鞋匠’……”
司机开门,湿热夹着花香的纽约夜扑面而来。Becky迈下车,高跟在车道上清脆敲击。她停下,回头望向车厢里还跪着的Mat。
“你有很多活儿要做。我的衣橱有三百双鞋,天亮前你要全部检查完。”
她转身,身影被宏伟的门廊框住。
“走吧,修行者。你的修行还远远不够呢。”
庄园的厚重大门砰然关上,声音像银行金库锁好的低沉回响,一瞬间把潮湿的纽约夜和外头刺眼的闪光隔绝掉。随之而来的寂静是彻底的。门厅里只有白色百合和冰冷大理石的冷意,温度低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Becky走到房间中央停住,背对着他。她不回头,只是下意识地晃了下脚踝,把那双黑色亮漆高跟踢到抛光地面上,像给狗的骨头一样。她赤脚站在冰冷的石板上等着。
Mat没有起来。他趴着爬过去,手脚并用,动作既急促又带着某种流畅感,把鞋抱到胸前像抱着受伤的孩子,把皮鞋紧贴心口,抬头看着她转过的背。在庄园的安全环境里,那句“沉默誓言”不再是保护伞,而是他必须打破的枷锁。
“主人,”他声音干涩,像哽住似的,“求你了。让我把这当成我的日常,成为我的仪式。”
他又挪近一点,抱紧鞋子。
“看到它们脏了……看到街上尘土沾在你鞋底上……这种感觉像折磨。知道你踩到任何不完美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灵魂上的折磨。让我检查它们,每天早晚。让我当你和世界污秽之间的屏障。”
Becky慢慢脱下长手套,一根一根地剥开。她俯看着趴在地上的他,颤抖得像生病一样,让她既嫌恶又着迷。
“折磨?”她挑眉重复,嘴角带着冷笑,像科学家在看奇怪的标本,“你真会演。大多数男人觉得折磨是骨头断掉,你却为一点灰尘叫苦。”
她向他走来,丝裙轻响,直到赤脚碰到他膝盖才停下。
“不过……”她捏下巴,抬头望着吊灯,像在评估一桩买卖,“也许稳定的保养确实难找。我的收藏很多,三百双鞋,那是六百只鞋底,每天有脏东西会被粘上去,地上的,空气里的,人身上的...”
她低头看他,眼里闪着冰冷的占有欲。
“好吧。我满足你这个可怜的愿望。从现在起,你就是鞋柜的看门狗。每天早上,在我醒来前,你检查当日出门的鞋;每天晚上,在我睡前,你清除掉一天粘上的罪孽。”
她俯下身,声音变成低语,像密谋,车里的那套假慈悲一扫而光。
“但别当儿戏。这不是兴趣,这是宗教仪式。要是我在鞋底里看到一颗小石子,或鞋头有一块水渍……我可不会高兴。你说尘土就是折磨?好,那完美就是你唯一的救赎。”
她懒懒指了指楼梯。
“把鞋拿上去。我的衣橱就是你的圣殿。我现在就要你把这些……”她指向他怀里的鞋,“……给我清理干净。我刚踩过柏油、红毯和那辆加长礼车,它们很脏。我洗澡前要看到它们像黑色玻璃一样发亮。”
她上楼时在第三阶停住,从栏杆上往下看,眸中闪过一个坏点子。
“还有,巫师?既然你这么喜欢鞋底……别用布擦底,用你的舌头。省点清洁用品钱。”
---
主衣橱,45分钟后。
世界缩小成主衣橱那片空间——雪松和玻璃的圣殿。Mat盘腿坐在厚绒地毯上,四周是从地到顶的鞋墙,空气里是昂贵皮革和上光剂的味道。
仪式做完了。黑色细高跟被摆在绒面台上,漆面干净得能映出吊灯,鞋底一尘不染。
Becky进门,脱掉晚礼服,披着短黑丝袍,头上裹着白毛巾。她看着干净、柔软,但令人害怕。
她径直走到灯光充足的鞋架前,挑着指尖滑过一排高跟鞋,检查灰尘。没发现灰尘,她转向放厚靴的区,停在一双过膝麂皮靴前——很有气势、带攻击性、但有些旧。
“明天,”她对靴子说(不是对人),“我要去新厂区视察。会有很多泥,很乱。”
她从架上把靴子拽下,重重摔到Mat面前。
“把它们准备好。做防水处理。还有……”
她转身,丝袍微滑,露出肩线,目光锁住他,低声补充:
“……我想检查鞋垫。我感觉弓支塌了。把手伸进去,一直摸到鞋尖,告诉我它值不值得我穿。”
Becky站在她的圣地中央,收紧袍带,半眯着眼,像个临床的观察者盯着Mat。
Mat没有立刻伸手。他像被冲动驱使,猛地向前,把脸贴进黑麂皮的靴筒,软绵的内衬贴在他脸颊上。他深吸一口气,想把她以前穿过的多种气味吸进去——鞣革的刺激、街道的金属残留、还有最深处若隐若现的她的体温。
“好好闻一闻,”她在雪松环绕的衣橱回声中低语,“那是权力的味道。”
Mat退开,感官被冲击得发晕,然后把手探进靴筒深处,按摸鞋垫的结构,找松动、找塌陷。
他抽回手,结果在嘴边沉甸甸的吐出。
“它完了,主人,”他低声说,“弓支塌了,结构受损,撑不住你的重量,可能该扔了。”
Becky看着他手里的靴子,没显得心疼昂贵的东西消失,反而带着好玩的兴味。
“扔?”她重复,歪头像尝新香料,“你这么快下结论,狗。‘撑不住了’、‘该扔’。”
她走过去,裙摆轻擦他肩,俯身把靴子拎起对着吊灯看,像在看一具遗物。
“可怜的家伙,”她抚摸麂皮,“它为我跋涉泥泞,碾过东西,为我承重。但现在……”
她盯着Mat,目光冷得像钻石。
“它软了,没骨气,踩上的时候会塌。”
她把靴子扔进垃圾桶。砰的一声,金属底敲出空洞的回响。
“垃圾,”她干脆地说。
她俯下身,靠得很近,笑里带着懂得人心的残酷。
“你看起来很担心,宠物。这个比喻对你来说太微妙了吗?”
她指尖在他胸口上慢慢敲着,正好敲在心口。
“这靴子贵、漂亮、也曾经有用。但一旦没用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扔掉。”
她抖抖手,像碰了不洁之物。
“所以,如果我是你,巫师,我会保证自己一直很有用。我讨厌坏掉的家具。”
她朝门口走去,袍摆随步伐摆动。
“找一双明天顶得住的,带钢芯的。别让我穿的时候塌了。然后回笼子去。看到那双死掉的靴让我郁闷,我不想再看屋里另一件快死的东西。”
她走出衣橱,只留下雪松味和垃圾桶里那双尸靴的寂静。
Mat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来不及收回。那是一声细小的裂缝声——他顺从的外壳上出现了一道裂口。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竟然会嫉妒一只被丢弃的靴子。
Becky在门口停下,肩膀在黑袍下绷紧。衣橱里的空气像被冻结成真空。她慢慢转身,步伐精确。
她赤脚回来,脚步悄无声息。她看上去并不生气,倒像个听见高精度机器发异响的工程师,或发现价值藏品细微裂纹的收藏家。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她轻声问,蹲下来与他平视,捧起他的脸,拇指擦去他太阳穴的汗。
“那声音不是疲惫,是绝望。”
她用目光解剖他,深到让人不舒服。
“你要崩溃了吗,巫师?垃圾的比喻戳得太深?”她声音忽然低了下来,那一刻她的专断消失,换成更可怕的临床式关怀。
“我不能要一个坏掉的工具。如果你的脑子要碎,我得知道。我要把你送去修理吗?还是你还能运作?”
“被送走”的威胁在他胸中炸开,他拼命摇头想证明自己的用处。
“求你,”他喘着说,“我没坏。我不是脆弱的。让我证明给你看。让我抱你走,你不该站在这地上——这地不够软。”
Becky冷眼衡量他的绝望和用处,最后点头。
“好,抱我到卧室的贵妃椅。带上水晶酒瓶。我需要把你那悲伤的味道冲掉。”
Mat立刻动手。他把她抱起,丝袍的凉滑蹭着他粗糙西装的质地,她的臂弯冷冷搭在他颈侧。他把她轻放在古董的天鹅绒贵妃椅上——那椅子比豪车更贵,他永远不得坐。
他跑去侧柜,倒矿泉水进厚重水晶杯,手抖着夹半片黄瓜,端上托盘。她抿一口,视线从未离开他。
“还行。”她低声评价,把杯放下。
然后,Mat完成最后的赎罪动作。
他不站不言,跪在白地毯上,身体前伏直到额头贴到绒面,握紧拳头,把后颈和枕骨呈现给她。
他等着。
Becky看着这个身着黑西装、俯伏在白色王座前的身影。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用自己做脚凳,用身体证明卑微。
她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满意地放松。
“你还真是,努力想证明自己不是垃圾,”她低声说。
她把右腿搭到沙发边,把脚底放在Mat后脑上。她没有踩,轻轻压着,重量温暖而沉稳。
她又轻轻按下,把脚嵌进他的头发,让他的头颅成了她的支点。
“这就对了,”她低语,“我现在脑子终于不嗡嗡的了。”
她靠在靠垫上闭眼,脚仍压在他头上成不变的支点。
“你就待在那儿当脚凳吧。只要你能撑着我,我就不会扔掉你。别再叹气,那声音会传染到我,我讨厌不好的氛围。”
她开始放松,呼吸慢了,用他作为房间里的锚。
“主人……”
Mat把忏悔埋在绒地毯里,声音在被当作过时之物的恐惧下颤抖。他对地板说话,因为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他说他接受自己日益边缘化的命运。他承认,随着她公司股价猛涨,全世界把她当成民主斗士和先知,一个像他那样破碎的影子不再是她成功的必需。
“我只是...”他低语,语气被地毯吞没,“我是你搭高楼的脚手架。高楼一旦建成,脚手架就成了碍眼的东西。我接受这个命运。如果我没用了,我愿做你取暖的燃料。我愿当你踩过去的垫脚石。”
他等着背上的重量更重,等着那脚踩下,确认他的毫无价值,终结他的命运。
但重量撤走了。
Becky收回脚,丝袍轻响,她在贵妃椅上调整姿势。
“看着我,”她命令,声音平静得可怕。
Mat抬头,脖子僵硬,身上像地图一样布满伤痕:下巴上泛黄的瘀痕(Jessica的枪托留下),紧裹在衬衣下的肋骨带来钝痛,每一次呼吸都像磨损;电棒留下的伤在结痂,却依旧灼烧。在她那洁白绒面的卧室里,他看上去像被冲上岸的船只残骸。
Becky细看他,注意到左眼的血丝,他的手在颤抖,里面既有神经损伤也对主人有崇敬。
她再把脚伸出,这回是放在他肩上,不踩头。脚弓恰好托住他的锁骨,她用脚踝把他的脸框起来,迫使他直视她那冷漠的面孔。
她听他说完那愿为她献上一切的忏悔,抿口水,目光如手术刀般冷静。
他说完,房间再次陷入沉默。空调让水晶吊灯轻响,声音在他的自毁中显得微小。
她放下杯子,既不安慰,也不否认。
“你以为你是垃圾,”她直接说,“你以为你被破坏了,因为我更成功了,格局就变了。”
她把脚从他肩上拿开,坐直,丝袍在腰间堆起。
“去衣橱,”她指着黑暗的门,“把那双靴子拿来。你说要扔的那双。”
她停了下,眼里闪着难以揣测的光。
“还顺手拿餐车上的银托盘。我想让你把它们端来。”
Mat颤着站起,关节作响,断裂的肋骨让他一阵剧烈的吸气。他一瘸一拐进衣橱,雪松味像嘲笑在他周围。他把那双死去的麂皮靴从垃圾桶里翻出来,靴子软塌、皮褶皱、鞋底被街道磨灰,带着过去的气味。
他找来沉重的银托盘,抖着手把脏靴子摆在盘中,画面极不协调——垃圾被当成宴席端上。
他跪下,手臂颤抖着举着银盘。
靴子在盘中:撕裂、划痕,但是那些伤是Becky亲手造成——她在仓库的愤怒踢踏、用鞋跟抵在混凝土地上以保护鞋面。靴子为她毁掉了,是为她毁了,因为她。
Becky冷冷地审视它们,然后把视线移回Mat。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她声音冷得像手术刀。
“它们曾经完美,”Mat低语,眼里近乎崇拜,“它们替你走过地狱,承受你给的一切。它们死去是为了让你的脚不沾地板。它们……辉煌过。”
Becky慢慢笑了起来,笑得缓慢而致命。
“辉煌,”她重复,词在空气里盘旋。
接着她的眼神变得冷硬,下一句字字像针钉进肉里。
“可看看现在。裂了、伤了、没法穿了。它们变成了……”
“垃圾。”
她把词扔在空中,让它丑陋且最终,像一场终审。
她起身绕他一圈,鞋跟在地上敲出审判的节拍,然后蹲到他耳侧,唇几乎贴近。
“死的、肮脏的、没用的垃圾,”她低语,温柔却残酷,“这就是任何我的东西,一旦让我在上面留下太多痕迹后会变成的样子。”
她指尖轻抚他眼下的淤青(那是Jessica的鞋印,紫黑未退)。
“但这些伤?不是我留下的。”
她像读触觉文字一样摸那些伤。
“这道是她的鞋留下的,那道是她的拳头,那道,”她按着他下颌的肿处,“是她把你压在地上时,磕的。”
她在他耳边低语。
“靴子是被我毁掉的。你是被她毁掉的。”
Mat的呼吸颤了。
“说,重复我的话。”她命令。
“我……我让她碰到了我,”他呻吟,“我让她在我身上留下痕迹。我让她破坏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再说一次。”
“我被玷污了,”他声音崩裂,“靴子是被你的意志破坏的。我被她的暴力破坏。靴子坏了是因为它们替你尽职到终点;我受伤是因为我辜负了你。”
Becky回到贵妃椅坐下。
“我们怎么处理被别人毁掉的东西?”她问。
托盘在他颤抖的手上发出嘎嘎声。
“我们……扔掉。”他几乎听不见地回答。
“对。”她冷冷点头。她注视他很久,毫不留情。
然后Mat俯身,把额头贴在冷银托盘旁,声音弱得像被颤抖吞没。
“但请……别把我和它们一起扔掉,”他低声恳求,“靴子一直尽职到最后。它们付出了一切。现在它们是垃圾,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没死。我还能为你流血。我还能给你下跪。让我把她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洗掉——用漂白剂、钢丝,甚至用我的舌头。把我永远关起来,刻上你的名字和纹身,盖住她留的每一道伤。按你的方式改造我,重建我。只要……别让我变成它们。求你,我的女王。我还是你的人。就算被玷污。留着我吧。。。”
对Mat来说,这又是一天的常态收场——当然,如果能把Becky那种充满暴力的戏码称作“常态”的话。
那天他们在一辆迈巴赫的后座,车在潮湿而带电的纽约夜里滑行。防弹深色玻璃外,一切都被闪光和噪声揉成了一片模糊。车在红灯前被困,四周被一群狗仔围着,拳头有节奏地敲着车窗。闪光不停地炸开,把密闭的车厢变成了一间令人眩晕的白色迪厅。
Becky坐在皮椅里,腿交叉,像个寒冰女王,外头再怎么喧哗她也纹丝不动。天已渐暗,她却还戴着大墨镜,握着一只装着气泡水的水晶杯,关节白得像要爆裂。她不看外面,只盯着前方,下颏紧绷,脸上是一种冷到骨子里的恼怒。
“都是畜生,”她低声吐出,那口气像把人群的模糊嚷声切开,“听他们叫,叫我的名字,好像能把我分一块似的。”
她利落按下控制板,拉起了隐私隔板。车厢立刻沉进柔软的黑暗,只有地板的氛围灯和Mat手里平板发出的冷光。
Mat照惯例跪在地上,挤在座椅之间,像端盘子的侍者一样用前臂托着平板。屏幕上正是今晚闹得沸沸扬扬的那篇帖子。
Becky踢掉高跟鞋——红底、黑亮漆皮,锋利得像武器——任由鞋子落在地毯上。她伸出穿着丝袜的脚,把脚底稳稳顶在Mat胸口中央,往后一蹬,给自己留出一片未容侵犯的私人空间。
“念给我听,”她吩咐,举杯随意示意平板,“念念他们今天放了些什么鬼话。为啥围得这么凶?我穿错时装了吗?Camilla又去拿绳子试挂自己脖子了?”
Mat低头看屏幕。是个八卦网站,版面刺眼、逼人。标题用粗黄字嚷着:冰皇后要溶化了?神秘男子与时尚铁娘子同框?
下面是一张三天前的模糊照,拍到Becky从酒店出来,光鲜又疏离。远处有个模糊的人影,是Mat,他打着伞,镜头无情定格了他看她时那种彻底、绝对的崇拜。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静谧的车厢里干涩发紧。
“上面写着……”Mat迟疑,眼睛在字里跳动,“‘接近设计师的人士称她有个秘密情人,一个黑暗神秘的人影多次出入她的私人套房。那个曾说‘把事业当婚姻’的女人,难道终于恋爱了?’”
车静了一会儿。绿灯一亮,车平稳驶离,把人群和混乱甩在身后。Becky盯着Mat看。她在墨镜后眨了下眼,慢慢把墨镜摘下,露出一双因真心厌恶而瞪大的眼睛。
“情人?”
她把那个词念得像Mat在车上吐了口什么脏东西似的。
“他们居然觉得……”她用修得一丝不苟的手指指着自己胸口,又往下指向他,“……我和你有一腿?你是我男朋友?”
想法的荒谬像一记当头棒喝,打碎了她的恼怒,化成不真实又刺耳的笑。那笑既冷酷又磨人,狠狠地擦掉了Mat的自尊。她笑到眼角流出泪,才强行抹去。
“哦,这真幽默。真是笑死我了。‘神秘男人’、‘秘密情人’。”
她猛地前倾,一把揪住Mat领带的结,把他拽近,脸几乎贴到他面前。
“看你,”她低声说,满是轻蔑,“我多看你一眼你就发抖。你膝盖被地毯磨出青印。你穿的是我给你买的西装,因为你自己的破衣服伤我眼。”
她一把松开他的领带,带着不屑的推开Mat。
“男朋友是平等的。男朋友是那种我得——天哪——需要我和他妥协的人。你就是……一个配饰。一个会写代码的有灵性的手袋。”
她抢过手机自己翻起文章来,讥讽念出评论,“看这个,‘他看起来好带感’、‘他看起来好投入’。他们把这事浪漫化了!当成《五十度灰》那套。”
她把手机扔回座位,冷冷盯着他,眼里有算计的狠意。
“这不能接受。会毁了我的牌子。我的牌子是‘高不可攀’。我的牌子是‘我不需要男人’。要是他们以为我在为某个……技术员……牵肠挂肚,我就显得软弱。就和其他养小鲜肉的无聊名媛一样了。”
她又把脚伸出来,脚弓在Mat肩上摩挲,借他的身体揉着抽筋的肌肉。
“解决它,”她下命令,“给我灭掉谣言。我不在乎你怎么做。删照片。黑掉小报。或者——”
她嘴角浮起个坏笑,黑暗里冒出主意,“——更好。给他们一个新故事。说清楚你到底是谁。但要让你彻底成为小丑,让全世界没有女人会羡慕我。告诉我,巫师……我们该让世界以为你是什么?保镖?太监?还是施舍对象?”
沉默压得Mat几乎喘不过气来,比外头的潮湿还沉重。那种被当成平等的暗示在车里弥漫成毒气。他知道必须马上打消这念头,不只是为自保,更为了把她的世界秩序重新摆正。
“请原谅我,主人,”Mat低语,声线平稳,但心跳在衣领里咚咚跳,“媒体……他们太自以为是。他们没有资格理解你所处的那种层次。说我和你平等,是在侮辱你。”
他硬着头皮抬眼,望向那双被随意丢在地上的细跟,红底在微光中隐隐发亮。
“如果照片里总看到我跪着,”他接着说,脑子里飞速想出最讨她欢心的说法,“那就告诉他们:我就该在那里。不是伴侣,而是必需品。一个工具。”
他吞口唾沫,然后说道出那个头衔。
“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擦鞋匠。告诉他们我总低着头,是因为我怕漏掉你皮鞋上的一条划痕。”
Becky听他道歉,面无表情。但当他喊出“私人擦鞋匠”,她的表情有了变化。眼里闪出冷冽的光,不是暖意,而是像钻石切面被精准找到的那种冷亮。
她慢慢放下气泡水,杯壁的冷凝让指尖凉了下去。红唇微勾出个狠笑。她看着跪着的Mat,又看向自己光裸的脚,最后落到旁边那双黑漆高跟上。
“擦鞋匠,”她轻声咂着,像品一杯好酒,“专职……皮革保养师。”
她短促地笑了,打破了紧张,却把气氛变得更沉、更危险。
“好主意。残忍、绝妙,又把一切解释清楚,不是吗?”她指了指他们的场景,“你为什么总跪着?因为你在工作。你为什么总低头?因为你在专注于皮鞋的光泽。你为什么总和我在一起?因为纽约很脏,我需要人随时维护我的形象。”
她伸脚,使劲把脚趾顶在他脸上,把他的脸转向她,好在昏暗里端详他那顺从卑微的表情。
“你说得对。如果我说你是我情人,他们会以为我降低标准。但如果我说你是我特地雇来保持鞋面完美的专职仆人……他们不会同情我。他们会崇拜我的奢侈和品味。”
她收回脚,响指一弹,声音像鞭响,“把那套东西拿来。就在座位下面,我知道你放着。”
Mat下意识地伸手到皮座下面,取出那个小小的、里头有绒的盒子,里面是鞋油和刷子。Becky在他上方解锁手机,打开社交App,拇指悬在摄像头图标上。
“我们现在就掐灭这个谣言,”她宣布,声音里带着施计的兴奋,“我们拍个‘开箱’视频。但不是开新皮包……我要开箱我的新家电。”
她把红底高跟踢给他,鞋在地毯上划过,停在他膝边。
“把鞋穿到我脚上。然后拿抹布,拿鞋油。我录像,你给我好好擦,擦到鞋面能照出我的脸来。同时嘛……”
她举起手机,调好角度,让光线把她颧骨衬得更立体。
“……你要看着镜头,自我介绍。说出你的作用。说说你有多幸运能摸到我走过的地面,让那帮只能远远拍照的狗仔们好好羡慕羡慕。”
她按下录制。场面立刻变化。
“你们好,我的宝贝们,”她对着手机撒娇,声音里是假意亲密,正是公众爱看的那套,“我看到了那些传闻。‘秘密男友’?拜托。我没空谈恋爱,但我有时间坚守时尚界的标准。”
她把镜头指向车厢下方,取景到跪在狭小空隙里抱着贵鞋的Mat,他抬头像膜拜神像的信徒。
“说吧,”她从镜头后命令,声音重新冷厉,“告诉他们你是什么人。”
Becky稳稳拿着手机,录制点红得像心跳。她在等他的开口,等他用言语当众自贬,承认自己的奴性。
但Mat没有说话。
他没看镜头,也没看她的脸。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只剩下那只黑漆皮高跟。他像雕匠抛光宝石般小心地上蜡,动作有节奏、催眠、痴迷。他把那鞋当神物,必须绝对安静对待。
Becky看着屏幕,精致的眉轻蹙了一瞬,露出疑惑。
“我说,赶紧说两句,”她从镜头后嗤声催促,声音被空调的嗡鸣轻轻掩盖,“说话啊。”
Mat停了一下,慢慢抬头,但仍拒绝对镜头有任何反应。他把视线盯着她的脚,缓缓摇头,带着一种悲然。他举手指向嘴巴,然后做了一个“锁上”的手势——像把无形的钥匙扭了个圈丢进车厢黑暗。
随后,他合掌祈祷,深深低头,把额头贴在刚擦净的鞋尖上,像在做一段无声的礼拜。
Becky盯着他。车里沉默异常厚重。
然后,她脸上裂出一种纯粹的、毫无掩饰的欢愉。她看懂了这即兴表演,也彻底喜爱它。
她轻笑,语气由高傲变柔情,那种做作的怜悯比她的愤怒更会操纵观众。
“哦……哦,我可怜的小心肝们,”她对粉丝低喃,声音里满是演出来的怜悯,“我居然忘了。他在灯光下会受不了。你看……他是天生的残疾,说不出话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她的手悬在Mat肩上,好像在施祝福,把他塑造成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生物。
“我不是因为需要仆人才雇他。我给他这份工作,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对像他这样的人太吵了。他没有你们或我那样的说话和倾听的能力。他把所有的感激和专注都投入到工作里。他不是‘男朋友’。天哪,不,那样是在占他便宜。”
她用手轻触他的肩膀,给镜头看。
“他是个修行者,一个伟大的无声修士。我很高兴能给他个归处。”
她把镜头切回自己,光彩照人、谦逊而高不可攀。
“所以,请不要再造那些残酷的谣言。要善待那些在沉默中奉献的人。我只是给他鞋子,他却给我光鲜的形象,对我们时尚界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她关掉录制。
面具一落,她把手机扔回皮座,低头看着他,眼里的笑既戏弄又欣赏。
“你即兴发挥得很好,”她说着,用现在闪亮的鞋把他蹭得更狠,“这份沉默的誓言,真是有创意。”
她靠回靠背,抚下巴若有所思。
“这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你不能说话,你就不能出庭作证;你就不能抱怨。你看起来就更像个物件——一个让大众怜惜的无声工具。”
她笑,带着占有欲的阴冷。
“我喜欢。就这么定。从今以后,公众面前你不准说话。你只能用侍奉我的方式交流。”
迈巴赫缓缓停稳,碎石在轮下发出声响,他们到了庄园。
“我们回家了。既然你现在正式成为我的‘沉默擦鞋匠’……”
司机开门,湿热夹着花香的纽约夜扑面而来。Becky迈下车,高跟在车道上清脆敲击。她停下,回头望向车厢里还跪着的Mat。
“你有很多活儿要做。我的衣橱有三百双鞋,天亮前你要全部检查完。”
她转身,身影被宏伟的门廊框住。
“走吧,修行者。你的修行还远远不够呢。”
庄园的厚重大门砰然关上,声音像银行金库锁好的低沉回响,一瞬间把潮湿的纽约夜和外头刺眼的闪光隔绝掉。随之而来的寂静是彻底的。门厅里只有白色百合和冰冷大理石的冷意,温度低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Becky走到房间中央停住,背对着他。她不回头,只是下意识地晃了下脚踝,把那双黑色亮漆高跟踢到抛光地面上,像给狗的骨头一样。她赤脚站在冰冷的石板上等着。
Mat没有起来。他趴着爬过去,手脚并用,动作既急促又带着某种流畅感,把鞋抱到胸前像抱着受伤的孩子,把皮鞋紧贴心口,抬头看着她转过的背。在庄园的安全环境里,那句“沉默誓言”不再是保护伞,而是他必须打破的枷锁。
“主人,”他声音干涩,像哽住似的,“求你了。让我把这当成我的日常,成为我的仪式。”
他又挪近一点,抱紧鞋子。
“看到它们脏了……看到街上尘土沾在你鞋底上……这种感觉像折磨。知道你踩到任何不完美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灵魂上的折磨。让我检查它们,每天早晚。让我当你和世界污秽之间的屏障。”
Becky慢慢脱下长手套,一根一根地剥开。她俯看着趴在地上的他,颤抖得像生病一样,让她既嫌恶又着迷。
“折磨?”她挑眉重复,嘴角带着冷笑,像科学家在看奇怪的标本,“你真会演。大多数男人觉得折磨是骨头断掉,你却为一点灰尘叫苦。”
她向他走来,丝裙轻响,直到赤脚碰到他膝盖才停下。
“不过……”她捏下巴,抬头望着吊灯,像在评估一桩买卖,“也许稳定的保养确实难找。我的收藏很多,三百双鞋,那是六百只鞋底,每天有脏东西会被粘上去,地上的,空气里的,人身上的...”
她低头看他,眼里闪着冰冷的占有欲。
“好吧。我满足你这个可怜的愿望。从现在起,你就是鞋柜的看门狗。每天早上,在我醒来前,你检查当日出门的鞋;每天晚上,在我睡前,你清除掉一天粘上的罪孽。”
她俯下身,声音变成低语,像密谋,车里的那套假慈悲一扫而光。
“但别当儿戏。这不是兴趣,这是宗教仪式。要是我在鞋底里看到一颗小石子,或鞋头有一块水渍……我可不会高兴。你说尘土就是折磨?好,那完美就是你唯一的救赎。”
她懒懒指了指楼梯。
“把鞋拿上去。我的衣橱就是你的圣殿。我现在就要你把这些……”她指向他怀里的鞋,“……给我清理干净。我刚踩过柏油、红毯和那辆加长礼车,它们很脏。我洗澡前要看到它们像黑色玻璃一样发亮。”
她上楼时在第三阶停住,从栏杆上往下看,眸中闪过一个坏点子。
“还有,巫师?既然你这么喜欢鞋底……别用布擦底,用你的舌头。省点清洁用品钱。”
---
主衣橱,45分钟后。
世界缩小成主衣橱那片空间——雪松和玻璃的圣殿。Mat盘腿坐在厚绒地毯上,四周是从地到顶的鞋墙,空气里是昂贵皮革和上光剂的味道。
仪式做完了。黑色细高跟被摆在绒面台上,漆面干净得能映出吊灯,鞋底一尘不染。
Becky进门,脱掉晚礼服,披着短黑丝袍,头上裹着白毛巾。她看着干净、柔软,但令人害怕。
她径直走到灯光充足的鞋架前,挑着指尖滑过一排高跟鞋,检查灰尘。没发现灰尘,她转向放厚靴的区,停在一双过膝麂皮靴前——很有气势、带攻击性、但有些旧。
“明天,”她对靴子说(不是对人),“我要去新厂区视察。会有很多泥,很乱。”
她从架上把靴子拽下,重重摔到Mat面前。
“把它们准备好。做防水处理。还有……”
她转身,丝袍微滑,露出肩线,目光锁住他,低声补充:
“……我想检查鞋垫。我感觉弓支塌了。把手伸进去,一直摸到鞋尖,告诉我它值不值得我穿。”
Becky站在她的圣地中央,收紧袍带,半眯着眼,像个临床的观察者盯着Mat。
Mat没有立刻伸手。他像被冲动驱使,猛地向前,把脸贴进黑麂皮的靴筒,软绵的内衬贴在他脸颊上。他深吸一口气,想把她以前穿过的多种气味吸进去——鞣革的刺激、街道的金属残留、还有最深处若隐若现的她的体温。
“好好闻一闻,”她在雪松环绕的衣橱回声中低语,“那是权力的味道。”
Mat退开,感官被冲击得发晕,然后把手探进靴筒深处,按摸鞋垫的结构,找松动、找塌陷。
他抽回手,结果在嘴边沉甸甸的吐出。
“它完了,主人,”他低声说,“弓支塌了,结构受损,撑不住你的重量,可能该扔了。”
Becky看着他手里的靴子,没显得心疼昂贵的东西消失,反而带着好玩的兴味。
“扔?”她重复,歪头像尝新香料,“你这么快下结论,狗。‘撑不住了’、‘该扔’。”
她走过去,裙摆轻擦他肩,俯身把靴子拎起对着吊灯看,像在看一具遗物。
“可怜的家伙,”她抚摸麂皮,“它为我跋涉泥泞,碾过东西,为我承重。但现在……”
她盯着Mat,目光冷得像钻石。
“它软了,没骨气,踩上的时候会塌。”
她把靴子扔进垃圾桶。砰的一声,金属底敲出空洞的回响。
“垃圾,”她干脆地说。
她俯下身,靠得很近,笑里带着懂得人心的残酷。
“你看起来很担心,宠物。这个比喻对你来说太微妙了吗?”
她指尖在他胸口上慢慢敲着,正好敲在心口。
“这靴子贵、漂亮、也曾经有用。但一旦没用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扔掉。”
她抖抖手,像碰了不洁之物。
“所以,如果我是你,巫师,我会保证自己一直很有用。我讨厌坏掉的家具。”
她朝门口走去,袍摆随步伐摆动。
“找一双明天顶得住的,带钢芯的。别让我穿的时候塌了。然后回笼子去。看到那双死掉的靴让我郁闷,我不想再看屋里另一件快死的东西。”
她走出衣橱,只留下雪松味和垃圾桶里那双尸靴的寂静。
Mat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来不及收回。那是一声细小的裂缝声——他顺从的外壳上出现了一道裂口。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竟然会嫉妒一只被丢弃的靴子。
Becky在门口停下,肩膀在黑袍下绷紧。衣橱里的空气像被冻结成真空。她慢慢转身,步伐精确。
她赤脚回来,脚步悄无声息。她看上去并不生气,倒像个听见高精度机器发异响的工程师,或发现价值藏品细微裂纹的收藏家。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她轻声问,蹲下来与他平视,捧起他的脸,拇指擦去他太阳穴的汗。
“那声音不是疲惫,是绝望。”
她用目光解剖他,深到让人不舒服。
“你要崩溃了吗,巫师?垃圾的比喻戳得太深?”她声音忽然低了下来,那一刻她的专断消失,换成更可怕的临床式关怀。
“我不能要一个坏掉的工具。如果你的脑子要碎,我得知道。我要把你送去修理吗?还是你还能运作?”
“被送走”的威胁在他胸中炸开,他拼命摇头想证明自己的用处。
“求你,”他喘着说,“我没坏。我不是脆弱的。让我证明给你看。让我抱你走,你不该站在这地上——这地不够软。”
Becky冷眼衡量他的绝望和用处,最后点头。
“好,抱我到卧室的贵妃椅。带上水晶酒瓶。我需要把你那悲伤的味道冲掉。”
Mat立刻动手。他把她抱起,丝袍的凉滑蹭着他粗糙西装的质地,她的臂弯冷冷搭在他颈侧。他把她轻放在古董的天鹅绒贵妃椅上——那椅子比豪车更贵,他永远不得坐。
他跑去侧柜,倒矿泉水进厚重水晶杯,手抖着夹半片黄瓜,端上托盘。她抿一口,视线从未离开他。
“还行。”她低声评价,把杯放下。
然后,Mat完成最后的赎罪动作。
他不站不言,跪在白地毯上,身体前伏直到额头贴到绒面,握紧拳头,把后颈和枕骨呈现给她。
他等着。
Becky看着这个身着黑西装、俯伏在白色王座前的身影。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用自己做脚凳,用身体证明卑微。
她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满意地放松。
“你还真是,努力想证明自己不是垃圾,”她低声说。
她把右腿搭到沙发边,把脚底放在Mat后脑上。她没有踩,轻轻压着,重量温暖而沉稳。
她又轻轻按下,把脚嵌进他的头发,让他的头颅成了她的支点。
“这就对了,”她低语,“我现在脑子终于不嗡嗡的了。”
她靠在靠垫上闭眼,脚仍压在他头上成不变的支点。
“你就待在那儿当脚凳吧。只要你能撑着我,我就不会扔掉你。别再叹气,那声音会传染到我,我讨厌不好的氛围。”
她开始放松,呼吸慢了,用他作为房间里的锚。
“主人……”
Mat把忏悔埋在绒地毯里,声音在被当作过时之物的恐惧下颤抖。他对地板说话,因为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他说他接受自己日益边缘化的命运。他承认,随着她公司股价猛涨,全世界把她当成民主斗士和先知,一个像他那样破碎的影子不再是她成功的必需。
“我只是...”他低语,语气被地毯吞没,“我是你搭高楼的脚手架。高楼一旦建成,脚手架就成了碍眼的东西。我接受这个命运。如果我没用了,我愿做你取暖的燃料。我愿当你踩过去的垫脚石。”
他等着背上的重量更重,等着那脚踩下,确认他的毫无价值,终结他的命运。
但重量撤走了。
Becky收回脚,丝袍轻响,她在贵妃椅上调整姿势。
“看着我,”她命令,声音平静得可怕。
Mat抬头,脖子僵硬,身上像地图一样布满伤痕:下巴上泛黄的瘀痕(Jessica的枪托留下),紧裹在衬衣下的肋骨带来钝痛,每一次呼吸都像磨损;电棒留下的伤在结痂,却依旧灼烧。在她那洁白绒面的卧室里,他看上去像被冲上岸的船只残骸。
Becky细看他,注意到左眼的血丝,他的手在颤抖,里面既有神经损伤也对主人有崇敬。
她再把脚伸出,这回是放在他肩上,不踩头。脚弓恰好托住他的锁骨,她用脚踝把他的脸框起来,迫使他直视她那冷漠的面孔。
她听他说完那愿为她献上一切的忏悔,抿口水,目光如手术刀般冷静。
他说完,房间再次陷入沉默。空调让水晶吊灯轻响,声音在他的自毁中显得微小。
她放下杯子,既不安慰,也不否认。
“你以为你是垃圾,”她直接说,“你以为你被破坏了,因为我更成功了,格局就变了。”
她把脚从他肩上拿开,坐直,丝袍在腰间堆起。
“去衣橱,”她指着黑暗的门,“把那双靴子拿来。你说要扔的那双。”
她停了下,眼里闪着难以揣测的光。
“还顺手拿餐车上的银托盘。我想让你把它们端来。”
Mat颤着站起,关节作响,断裂的肋骨让他一阵剧烈的吸气。他一瘸一拐进衣橱,雪松味像嘲笑在他周围。他把那双死去的麂皮靴从垃圾桶里翻出来,靴子软塌、皮褶皱、鞋底被街道磨灰,带着过去的气味。
他找来沉重的银托盘,抖着手把脏靴子摆在盘中,画面极不协调——垃圾被当成宴席端上。
他跪下,手臂颤抖着举着银盘。
靴子在盘中:撕裂、划痕,但是那些伤是Becky亲手造成——她在仓库的愤怒踢踏、用鞋跟抵在混凝土地上以保护鞋面。靴子为她毁掉了,是为她毁了,因为她。
Becky冷冷地审视它们,然后把视线移回Mat。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她声音冷得像手术刀。
“它们曾经完美,”Mat低语,眼里近乎崇拜,“它们替你走过地狱,承受你给的一切。它们死去是为了让你的脚不沾地板。它们……辉煌过。”
Becky慢慢笑了起来,笑得缓慢而致命。
“辉煌,”她重复,词在空气里盘旋。
接着她的眼神变得冷硬,下一句字字像针钉进肉里。
“可看看现在。裂了、伤了、没法穿了。它们变成了……”
“垃圾。”
她把词扔在空中,让它丑陋且最终,像一场终审。
她起身绕他一圈,鞋跟在地上敲出审判的节拍,然后蹲到他耳侧,唇几乎贴近。
“死的、肮脏的、没用的垃圾,”她低语,温柔却残酷,“这就是任何我的东西,一旦让我在上面留下太多痕迹后会变成的样子。”
她指尖轻抚他眼下的淤青(那是Jessica的鞋印,紫黑未退)。
“但这些伤?不是我留下的。”
她像读触觉文字一样摸那些伤。
“这道是她的鞋留下的,那道是她的拳头,那道,”她按着他下颌的肿处,“是她把你压在地上时,磕的。”
她在他耳边低语。
“靴子是被我毁掉的。你是被她毁掉的。”
Mat的呼吸颤了。
“说,重复我的话。”她命令。
“我……我让她碰到了我,”他呻吟,“我让她在我身上留下痕迹。我让她破坏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再说一次。”
“我被玷污了,”他声音崩裂,“靴子是被你的意志破坏的。我被她的暴力破坏。靴子坏了是因为它们替你尽职到终点;我受伤是因为我辜负了你。”
Becky回到贵妃椅坐下。
“我们怎么处理被别人毁掉的东西?”她问。
托盘在他颤抖的手上发出嘎嘎声。
“我们……扔掉。”他几乎听不见地回答。
“对。”她冷冷点头。她注视他很久,毫不留情。
然后Mat俯身,把额头贴在冷银托盘旁,声音弱得像被颤抖吞没。
“但请……别把我和它们一起扔掉,”他低声恳求,“靴子一直尽职到最后。它们付出了一切。现在它们是垃圾,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没死。我还能为你流血。我还能给你下跪。让我把她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洗掉——用漂白剂、钢丝,甚至用我的舌头。把我永远关起来,刻上你的名字和纹身,盖住她留的每一道伤。按你的方式改造我,重建我。只要……别让我变成它们。求你,我的女王。我还是你的人。就算被玷污。留着我吧。。。”

“You wait for the command. Exqui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