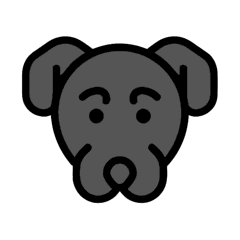穿越异世界成为领主的我却成为少女脚奴这件事,是否搞错了什么
原味连载中已完结原创绿奴下克上足控足交臭脚贡奴圣水
月余光阴匆匆而过,艾莉丝成为莫尔顿子爵夫人后,约克镇的古堡已然变了模样。每日黄昏,城堡铁门吱呀开启,艾莉丝挽着不同男人的臂膀踏入长廊——或边境佣兵,或过路商贾,甚至还有蒙德骑士国的逃兵。她衣衫半解,娇笑与喘息声穿透厚重的橡木门,传遍仆人房。家臣们窃窃私语,嘲笑这位难民出身的女主人水性杨花,玷污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荣光。
众人原以为十八岁的威廉·费尔法克斯会震怒,毕竟四万英亩的封地与子爵之名不容亵渎。可威廉却视若无睹,甚至在巡查边境时对艾莉丝的“客人”点头致意,脸上挂着空洞的笑。家臣们失望透顶,骑士们纷纷递上辞呈,约克镇的忠诚如沙漏般流逝殆尽。
这夜,月光如钩,威廉被艾莉丝唤入主卧。她斜倚在雕花大床上,赤足晃荡,脚趾涂着鲜红蔻丹,眼中闪着甜腻却锋利的笑意。“脱光,跪下。”她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威廉褪尽衣物,膝盖砸在冰冷石板上,贞操锁在烛光下泛着暗哑的金属光泽。门开,一名高大的佣兵跨入,腰间挂着蒙德骑士国的旧徽章。他瞥见跪地的威廉,瞳孔骤缩,认出这是神圣法兰帝国的子爵,腿肚子不由一颤。
艾莉丝慢条斯理地开口:“贱狗,还不给你爷爷磕头?”
威廉额头重重撞地,砰砰作响,震得佣兵目瞪口呆。艾莉丝掩唇轻笑,踮脚亲吻佣兵的喉结,柔声道:“别怕,亲爱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天生下贱。”
佣兵喉结滚动,半信半疑。艾莉丝已跪在他身前,纤手解开皮带,红唇含住那粗壮的阳具,啧啧水声在房内回荡。她侧头,媚眼如丝,示意威廉:“狗奴,过来,舔主人的屁眼。”
威廉爬到她身后,双手分开艾莉丝的臀瓣,舌尖钻入紧致的褶皱,尝到淡淡的咸涩与残留的麝香。艾莉丝喉间发出满足的呜咽,臀部轻晃,催促他更深。
舔到她满意,艾莉丝起身,钥匙在指间转了一圈,咔哒一声解开威廉的贞操锁。那萎缩的小鸟弹起,带着一个月未泄的青紫。她赤足踩地,走向衣柜,翘臀高抬,对佣兵道:“来,亲爱的,插进来,让这废物开开眼。”
佣兵握住艾莉丝的腰,粗暴地顶入。艾莉丝尖叫一声,声音甜腻得发颤:“啊……对,就是这样……填满我……”她俯身,湿漉漉的眼睛盯着跪在脚边的威廉,脚趾夹住他那可怜的小鸟,碾压、揉搓,力道毫不留情。
“看好了,贱狗。”她喘息着,乳浪晃荡,“这才是男人……你那早泄的小虫子,永远也别想进主人的小穴……”
佣兵越插越猛,艾莉丝的呻吟愈发高亢,脚下的力道也越来越重,脚趾几乎要捏碎威廉的卵蛋。她仰头长吟,佣兵低吼着内射,滚烫的精液灌满她的子宫。同一瞬,艾莉丝脚底狠狠一碾,威廉浑身抽搐,在剧痛与极度的羞辱中泄了,一小滩稀薄的精液喷在地上,混着她脚背的汗。
艾莉丝抽回脚,厌恶地在威廉脸上擦了擦:“舔干净,贱狗。今晚你睡地板,明天再给你上锁。”她翻身骑到佣兵身上,亲吻他的胸膛,笑声轻快:“亲爱的,再来一次,让这废物听听什么叫真正的女人。”
威廉蜷缩在地板上,烛火映着他扭曲的面容,羞耻与臣服交织,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荣光已成尘土。
夜色如墨,约克镇的古堡笼罩在一片死寂中,只有主卧内的烛火还在摇曳,投下斑驳的光影。艾莉丝与那名蒙德骑士国的佣兵的欢愉刚刚结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麝香、汗液与淫靡的气息。佣兵整理好衣物,腰间的旧徽章在烛光下闪着暗淡的光芒,他瞥了一眼蜷缩在地板上的威廉,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随即在艾莉丝的挥手下匆匆离去,脚步声在石廊中渐行渐远。
艾莉丝慵懒地倚在雕花大床上,赤裸的身体半裹在丝绸被单中,露出白皙的肩头与涂着鲜红蔻丹的脚趾。她斜眼看着地上的威廉,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声音带着倦怠却不容置疑:“滚过来,贱狗,给主人清理干净。”
威廉喉咙发干,身体微微颤抖,却不敢有丝毫迟疑。他爬到床边,膝盖在冰冷的石板上磨出红痕,抬头望向艾莉丝那被佣兵肆意征伐过的小穴。那里湿漉漉的,混合着精液与爱液,散发着浓烈的腥甜气息。他低头,舌尖小心翼翼地触碰,咸腥的味道瞬间充斥口腔。威廉强忍着喉间的反胃,一点一点舔舐,将那混杂的液体尽数吞下。他的动作卑微而虔诚,仿佛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艾莉丝低头俯视着他,眼中满是鄙夷,红唇微微张开,吐出一声冷笑:“瞧瞧你这贱样,舔得倒是挺卖力。”她伸出一只脚,脚趾轻点威廉的额头,像是戏弄一条狗。威廉不敢抬头,只顾埋首在她腿间,直到将每一滴液体舔得干干净净,空气中只剩她肌肤的淡淡香气。
“抬起头来。”艾莉丝的声音骤然冷冽。威廉依言抬头,还未反应过来,一口浓痰从她口中飞出,正中他的脸颊。腥臭的液体顺着他的鼻梁滑下,黏腻而屈辱。艾莉丝冷哼一声,眼中尽是厌恶:“像你这种早泄贱狗的废物鸡巴,只配在主人的脚下颤抖,永远别想碰我半分!”
她从床头柜里取出那只黑色的皮质贞操锁,钥匙在指间转了一圈,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威廉低头,看着自己那可怜的小鸟,青紫而萎缩,早已被一个月来的禁锢折磨得毫无生气。艾莉丝俯身,毫不温柔地将贞操锁扣上,锁扣合拢的咔哒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她起身,一脚踹在威廉的胸口,将他踢得仰倒在地。“滚远点,贱狗。”她裹上丝绸被子,翻身睡去,呼吸很快变得均匀,留下威廉独自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脸上的痰液尚未干涸,耻辱与臣服在心底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翌日清晨,阳光透过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洒在约克镇古堡的石墙上。仆人的敲门声将艾莉丝从睡梦中唤醒,她迷迷糊糊地伸了个懒腰,赤足踩在毛毯上,眼中还带着未散的睡意。她瞥了一眼地上的威廉,嘴角一撇,蹲下身来。威廉立刻爬了过去,早已习惯了晨间的“仪式”。艾莉丝毫不掩饰,骚臭的晨尿如洪水般喷涌而出,威廉张嘴接住,大口吞咽,喉咙被刺鼻的味道刺激得火辣辣的。他不敢漏出一滴,生怕惹来她的不快。
尿液止住后,艾莉丝站起身,懒洋洋地走向浴室,示意威廉伺候她洗漱。她坐在铜镜前,威廉小心翼翼地为她梳理长发,递上温热的毛巾擦拭她的脸庞与脖颈。艾莉丝闭着眼,享受着他的服侍,偶尔哼一声表示满意。待她洗漱完毕,威廉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冷水冲刷身体,试图洗去昨夜的屈辱。然而,无论水流如何冰冷,都无法冲淡他心底那扭曲的快感与臣服。
洗漱完毕,威廉换上华贵的子爵服饰,整理好仪容,走出房间。此刻的他必须伪装成神圣法兰帝国莫尔顿子爵的模样,堂堂正正地站在众人面前。艾莉丝与他的真实关系绝不能暴露——王都的大贵族们对领地的管理严苛,若得知堂堂子爵沦为难民女奴的玩物,费尔法克斯家族的爵位与封地恐怕不保。威廉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公开场合,他强迫自己挺直脊背,装出领主的威严,哪怕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他来到议事厅,家臣们的目光带着隐隐的轻蔑与疏远。曾经忠诚的骑士大多已离去,留下的人手不足,政务堆积如山。威廉翻开账本,检查约克镇的税收与开支。艾莉丝的挥霍无度早已让领地的财政捉襟见肘——她每日宴请外来男人,购置昂贵的丝绸与珠宝,甚至下令翻新城堡的花园,只为取悦她的“贵客”。威廉却不敢有半句怨言,因为在契约中,他早已将一切献给了她。
他埋头处理文书,计算着田赋与商税,试图从南部边境的贸易中挤出更多银币,以满足艾莉丝的开销。约克镇靠近神圣法兰帝国与蒙德骑士国的边境,商路繁忙,若经营得当,税收足以支撑她的奢靡生活。威廉召来管家,询问近期商队的动向,又派人去边境巡查,以防盗匪劫掠商路。他甚至亲自修改了与邻近领主的贸易协议,压低价格以换取更多订单。每做一件事,他都提醒自己:这是为了主人,为了让艾莉丝满意。
午后,威廉巡查了约克镇的市场,微笑着与商贩寒暄,倾听他们的抱怨,承诺减免部分摊位税,以安抚民心。镇民们看着这位年轻的子爵,依旧恭敬地鞠躬,却在背后议论纷纷:“子爵大人怎会被那女人迷得神魂颠倒?”“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荣光怕是要毁在这对夫妻手上了。”威廉假装听不见,低头继续前行,耳边却仿佛回响起艾莉丝的冷笑与昨夜的呻吟。
回到城堡,夕阳西沉,艾莉丝正在花园中与一名新来的吟游诗人调笑。她身着低胸的丝绸长裙,手中端着高脚杯,红酒在杯中摇曳。她瞥见威廉,挥手召他过去:“贱狗,过来,给这位诗人老爷倒酒。”威廉低头应是,端起酒壶,小心翼翼地为诗人斟满酒杯。吟游诗人有些不自在,试探着问:“子爵大人,您……”话未说完,艾莉丝打断他,娇笑道:“别管他,他乐意伺候人。”
威廉垂下眼帘,强忍着心底的刺痛,退到一旁。夜幕降临,艾莉丝带着诗人回了主卧,留下威廉在花园中独自站立。月光洒在他身上,映出他孤寂的背影。费尔法克斯家族的纹章——一头雄鹰——绣在他的披风上,可此刻,那雄鹰仿佛也被折断了翅膀。
回到自己的房间,威廉脱下外袍,跪在地毯上,贞操锁的重量让他下体隐隐作痛。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艾莉丝的脚趾、她的冷笑、她的命令。耻辱如潮水般涌来,却又夹杂着扭曲的快感。他知道,自己早已无法回头——从穿越到欧若巴大陆的那一刻起,从在森林中被艾莉丝的脚气味迷住的那一刻起,他便注定是她的奴隶。
次日清晨,艾莉丝再次唤醒威廉,重复着晨间的“仪式”。威廉吞下她骚臭的晨尿,伺候她洗漱,然后继续投入政务。他核查粮仓的库存,安排秋季的收割,又与边境的卫兵队长商讨防务事宜。约克镇的繁荣是他献给艾莉丝的供品,每一枚银币、每一粒谷物都承载着他对主人的忠诚。
而在夜深人静时,艾莉丝的卧室又会传来新的欢笑与呻吟。威廉跪在门外,聆听着她的快乐,手中紧握着账本,心底的屈辱与臣服交织成一团乱麻。他知道,这片封地、这座古堡、甚至他自己,都已完全属于艾莉丝。而他,曾经的陈烨,如今的威廉·费尔法克斯,只是一条匍匐在她脚下的贱狗,永远无法逃脱她的掌控。
众人原以为十八岁的威廉·费尔法克斯会震怒,毕竟四万英亩的封地与子爵之名不容亵渎。可威廉却视若无睹,甚至在巡查边境时对艾莉丝的“客人”点头致意,脸上挂着空洞的笑。家臣们失望透顶,骑士们纷纷递上辞呈,约克镇的忠诚如沙漏般流逝殆尽。
这夜,月光如钩,威廉被艾莉丝唤入主卧。她斜倚在雕花大床上,赤足晃荡,脚趾涂着鲜红蔻丹,眼中闪着甜腻却锋利的笑意。“脱光,跪下。”她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威廉褪尽衣物,膝盖砸在冰冷石板上,贞操锁在烛光下泛着暗哑的金属光泽。门开,一名高大的佣兵跨入,腰间挂着蒙德骑士国的旧徽章。他瞥见跪地的威廉,瞳孔骤缩,认出这是神圣法兰帝国的子爵,腿肚子不由一颤。
艾莉丝慢条斯理地开口:“贱狗,还不给你爷爷磕头?”
威廉额头重重撞地,砰砰作响,震得佣兵目瞪口呆。艾莉丝掩唇轻笑,踮脚亲吻佣兵的喉结,柔声道:“别怕,亲爱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天生下贱。”
佣兵喉结滚动,半信半疑。艾莉丝已跪在他身前,纤手解开皮带,红唇含住那粗壮的阳具,啧啧水声在房内回荡。她侧头,媚眼如丝,示意威廉:“狗奴,过来,舔主人的屁眼。”
威廉爬到她身后,双手分开艾莉丝的臀瓣,舌尖钻入紧致的褶皱,尝到淡淡的咸涩与残留的麝香。艾莉丝喉间发出满足的呜咽,臀部轻晃,催促他更深。
舔到她满意,艾莉丝起身,钥匙在指间转了一圈,咔哒一声解开威廉的贞操锁。那萎缩的小鸟弹起,带着一个月未泄的青紫。她赤足踩地,走向衣柜,翘臀高抬,对佣兵道:“来,亲爱的,插进来,让这废物开开眼。”
佣兵握住艾莉丝的腰,粗暴地顶入。艾莉丝尖叫一声,声音甜腻得发颤:“啊……对,就是这样……填满我……”她俯身,湿漉漉的眼睛盯着跪在脚边的威廉,脚趾夹住他那可怜的小鸟,碾压、揉搓,力道毫不留情。
“看好了,贱狗。”她喘息着,乳浪晃荡,“这才是男人……你那早泄的小虫子,永远也别想进主人的小穴……”
佣兵越插越猛,艾莉丝的呻吟愈发高亢,脚下的力道也越来越重,脚趾几乎要捏碎威廉的卵蛋。她仰头长吟,佣兵低吼着内射,滚烫的精液灌满她的子宫。同一瞬,艾莉丝脚底狠狠一碾,威廉浑身抽搐,在剧痛与极度的羞辱中泄了,一小滩稀薄的精液喷在地上,混着她脚背的汗。
艾莉丝抽回脚,厌恶地在威廉脸上擦了擦:“舔干净,贱狗。今晚你睡地板,明天再给你上锁。”她翻身骑到佣兵身上,亲吻他的胸膛,笑声轻快:“亲爱的,再来一次,让这废物听听什么叫真正的女人。”
威廉蜷缩在地板上,烛火映着他扭曲的面容,羞耻与臣服交织,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荣光已成尘土。
夜色如墨,约克镇的古堡笼罩在一片死寂中,只有主卧内的烛火还在摇曳,投下斑驳的光影。艾莉丝与那名蒙德骑士国的佣兵的欢愉刚刚结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麝香、汗液与淫靡的气息。佣兵整理好衣物,腰间的旧徽章在烛光下闪着暗淡的光芒,他瞥了一眼蜷缩在地板上的威廉,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随即在艾莉丝的挥手下匆匆离去,脚步声在石廊中渐行渐远。
艾莉丝慵懒地倚在雕花大床上,赤裸的身体半裹在丝绸被单中,露出白皙的肩头与涂着鲜红蔻丹的脚趾。她斜眼看着地上的威廉,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声音带着倦怠却不容置疑:“滚过来,贱狗,给主人清理干净。”
威廉喉咙发干,身体微微颤抖,却不敢有丝毫迟疑。他爬到床边,膝盖在冰冷的石板上磨出红痕,抬头望向艾莉丝那被佣兵肆意征伐过的小穴。那里湿漉漉的,混合着精液与爱液,散发着浓烈的腥甜气息。他低头,舌尖小心翼翼地触碰,咸腥的味道瞬间充斥口腔。威廉强忍着喉间的反胃,一点一点舔舐,将那混杂的液体尽数吞下。他的动作卑微而虔诚,仿佛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艾莉丝低头俯视着他,眼中满是鄙夷,红唇微微张开,吐出一声冷笑:“瞧瞧你这贱样,舔得倒是挺卖力。”她伸出一只脚,脚趾轻点威廉的额头,像是戏弄一条狗。威廉不敢抬头,只顾埋首在她腿间,直到将每一滴液体舔得干干净净,空气中只剩她肌肤的淡淡香气。
“抬起头来。”艾莉丝的声音骤然冷冽。威廉依言抬头,还未反应过来,一口浓痰从她口中飞出,正中他的脸颊。腥臭的液体顺着他的鼻梁滑下,黏腻而屈辱。艾莉丝冷哼一声,眼中尽是厌恶:“像你这种早泄贱狗的废物鸡巴,只配在主人的脚下颤抖,永远别想碰我半分!”
她从床头柜里取出那只黑色的皮质贞操锁,钥匙在指间转了一圈,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威廉低头,看着自己那可怜的小鸟,青紫而萎缩,早已被一个月来的禁锢折磨得毫无生气。艾莉丝俯身,毫不温柔地将贞操锁扣上,锁扣合拢的咔哒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她起身,一脚踹在威廉的胸口,将他踢得仰倒在地。“滚远点,贱狗。”她裹上丝绸被子,翻身睡去,呼吸很快变得均匀,留下威廉独自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脸上的痰液尚未干涸,耻辱与臣服在心底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翌日清晨,阳光透过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洒在约克镇古堡的石墙上。仆人的敲门声将艾莉丝从睡梦中唤醒,她迷迷糊糊地伸了个懒腰,赤足踩在毛毯上,眼中还带着未散的睡意。她瞥了一眼地上的威廉,嘴角一撇,蹲下身来。威廉立刻爬了过去,早已习惯了晨间的“仪式”。艾莉丝毫不掩饰,骚臭的晨尿如洪水般喷涌而出,威廉张嘴接住,大口吞咽,喉咙被刺鼻的味道刺激得火辣辣的。他不敢漏出一滴,生怕惹来她的不快。
尿液止住后,艾莉丝站起身,懒洋洋地走向浴室,示意威廉伺候她洗漱。她坐在铜镜前,威廉小心翼翼地为她梳理长发,递上温热的毛巾擦拭她的脸庞与脖颈。艾莉丝闭着眼,享受着他的服侍,偶尔哼一声表示满意。待她洗漱完毕,威廉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冷水冲刷身体,试图洗去昨夜的屈辱。然而,无论水流如何冰冷,都无法冲淡他心底那扭曲的快感与臣服。
洗漱完毕,威廉换上华贵的子爵服饰,整理好仪容,走出房间。此刻的他必须伪装成神圣法兰帝国莫尔顿子爵的模样,堂堂正正地站在众人面前。艾莉丝与他的真实关系绝不能暴露——王都的大贵族们对领地的管理严苛,若得知堂堂子爵沦为难民女奴的玩物,费尔法克斯家族的爵位与封地恐怕不保。威廉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公开场合,他强迫自己挺直脊背,装出领主的威严,哪怕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他来到议事厅,家臣们的目光带着隐隐的轻蔑与疏远。曾经忠诚的骑士大多已离去,留下的人手不足,政务堆积如山。威廉翻开账本,检查约克镇的税收与开支。艾莉丝的挥霍无度早已让领地的财政捉襟见肘——她每日宴请外来男人,购置昂贵的丝绸与珠宝,甚至下令翻新城堡的花园,只为取悦她的“贵客”。威廉却不敢有半句怨言,因为在契约中,他早已将一切献给了她。
他埋头处理文书,计算着田赋与商税,试图从南部边境的贸易中挤出更多银币,以满足艾莉丝的开销。约克镇靠近神圣法兰帝国与蒙德骑士国的边境,商路繁忙,若经营得当,税收足以支撑她的奢靡生活。威廉召来管家,询问近期商队的动向,又派人去边境巡查,以防盗匪劫掠商路。他甚至亲自修改了与邻近领主的贸易协议,压低价格以换取更多订单。每做一件事,他都提醒自己:这是为了主人,为了让艾莉丝满意。
午后,威廉巡查了约克镇的市场,微笑着与商贩寒暄,倾听他们的抱怨,承诺减免部分摊位税,以安抚民心。镇民们看着这位年轻的子爵,依旧恭敬地鞠躬,却在背后议论纷纷:“子爵大人怎会被那女人迷得神魂颠倒?”“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荣光怕是要毁在这对夫妻手上了。”威廉假装听不见,低头继续前行,耳边却仿佛回响起艾莉丝的冷笑与昨夜的呻吟。
回到城堡,夕阳西沉,艾莉丝正在花园中与一名新来的吟游诗人调笑。她身着低胸的丝绸长裙,手中端着高脚杯,红酒在杯中摇曳。她瞥见威廉,挥手召他过去:“贱狗,过来,给这位诗人老爷倒酒。”威廉低头应是,端起酒壶,小心翼翼地为诗人斟满酒杯。吟游诗人有些不自在,试探着问:“子爵大人,您……”话未说完,艾莉丝打断他,娇笑道:“别管他,他乐意伺候人。”
威廉垂下眼帘,强忍着心底的刺痛,退到一旁。夜幕降临,艾莉丝带着诗人回了主卧,留下威廉在花园中独自站立。月光洒在他身上,映出他孤寂的背影。费尔法克斯家族的纹章——一头雄鹰——绣在他的披风上,可此刻,那雄鹰仿佛也被折断了翅膀。
回到自己的房间,威廉脱下外袍,跪在地毯上,贞操锁的重量让他下体隐隐作痛。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艾莉丝的脚趾、她的冷笑、她的命令。耻辱如潮水般涌来,却又夹杂着扭曲的快感。他知道,自己早已无法回头——从穿越到欧若巴大陆的那一刻起,从在森林中被艾莉丝的脚气味迷住的那一刻起,他便注定是她的奴隶。
次日清晨,艾莉丝再次唤醒威廉,重复着晨间的“仪式”。威廉吞下她骚臭的晨尿,伺候她洗漱,然后继续投入政务。他核查粮仓的库存,安排秋季的收割,又与边境的卫兵队长商讨防务事宜。约克镇的繁荣是他献给艾莉丝的供品,每一枚银币、每一粒谷物都承载着他对主人的忠诚。
而在夜深人静时,艾莉丝的卧室又会传来新的欢笑与呻吟。威廉跪在门外,聆听着她的快乐,手中紧握着账本,心底的屈辱与臣服交织成一团乱麻。他知道,这片封地、这座古堡、甚至他自己,都已完全属于艾莉丝。而他,曾经的陈烨,如今的威廉·费尔法克斯,只是一条匍匐在她脚下的贱狗,永远无法逃脱她的掌控。
冬日的约克镇被厚重的雪覆盖,费尔法克斯古堡的尖塔在寒风中矗立,昔日雄鹰的旗帜已被风雪撕扯得残破不堪。艾莉丝的分娩之日终于到来,古堡内弥漫着血腥与药草的气味。产房外,威廉跪在冰冷的石板上,贞操锁的重量压得他下体隐隐作痛,耳边却只能听见艾莉丝高亢的呻吟与产婆的喊声。他低头,双手紧握,指节泛白,内心早已麻木——这个孩子,注定是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耻辱。
几个时辰后,产婆抱着一个裹着丝绸的婴孩走出,恭敬地对威廉道:“子爵大人,夫人诞下一名女婴,母女平安。”威廉抬头,目光空洞,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孩子绝非他的血脉,却即将堂而皇之地冠上费尔法克斯的姓氏,成为四万英亩封地的合法继承人。
艾莉丝在产房内休养了数日,身体迅速恢复。她斜倚在雕花大床上,怀中抱着女婴,眼中闪着得意的光芒。女婴被取名莉莉安·费尔法克斯,名字一经宣布,约克镇的最后几名仆人也不敢多言,只低头窃窃私语。艾莉丝抚摸着女婴细嫩的脸颊,红唇微勾,喃喃道:“我的小宝贝,未来的子爵。”
几天后,艾莉丝已能下床活动。她召来威廉,声音甜腻却带着刺骨的寒意:“贱狗,滚过来。”威廉爬进主卧,膝盖在石板上磨出红痕,低头跪在她脚边。艾莉丝赤足踩在毛毯上,脚趾涂着鲜红蔻丹,挺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腰肢,俯视着他,眼中满是轻蔑:“褪下裤子,双腿叉开,双手抱头。”
威廉喉咙发干,身体微微颤抖,却不敢违抗。他褪下裤子,露出被贞操锁禁锢的下体,双腿叉开,双手抱头,摆出完全臣服的姿势。贞操锁解开后,他那萎缩的小鸟暴露在空气中,青紫而无力。艾莉丝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残忍:“贱狗,你猜猜主人今天要干什么?”
威廉的心猛地一沉,隐约猜到了她的意图。她要彻底废了他,斩断他作为男人的最后痕迹,确保莉莉安的继承人地位坚不可摧。他张了张嘴,想求饶,却只发出一声低哑的呜咽。艾莉丝的眼神冷得像冰,缓缓抬起赤足,脚掌对准他的阴茎,狠狠一踢。
钻心的疼痛如雷霆般炸开,威廉忍不住惨叫出声,身体蜷缩成一团。艾莉丝皱了皱眉,厌恶地啐了一口:“叫什么叫?吵死了!”她从床头抓起一双提前准备好的女仆穿过的臭袜子,散发着汗臭与霉味,毫不犹豫地塞进威廉的嘴里。袜子的味道呛得他眼泪直流,却不敢吐出,只能呜呜低鸣。
艾莉丝冷哼一声,继续抬起脚,狠狠踢向他的阴茎。一下、两下、数十下,每一脚都精准而凶狠。威廉的惨叫被袜子堵住,化为闷哼,疼痛如潮水般席卷全身。然而,诡异的是,在这剧烈的折磨中,他竟渐渐升起一种扭曲的快感——虐阳的快感如毒药般侵蚀他的神经。他的阴茎在踢击下变得青紫肿胀,血丝渗出,模样惨不忍睹。
“趴下!”艾莉丝冷冷命令。威廉翻身趴在地上,臀部高翘,瑟瑟发抖。艾莉丝抬起脚掌,精准地踩住他的睾丸,力道逐渐加重。她冷笑:“贱狗,你的蛋蛋也配存在?今天主人帮你彻底了断!”话音未落,她猛地用力,脚掌狠狠碾下。
一声闷响,威廉的睾丸被彻底踩碎,剧痛如刀割般撕裂他的意识。他在袜子的堵塞下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身体抽搐,却不敢挣扎。艾莉丝俯身,眼中满是垃圾般的轻蔑,拿起一根细绳,将那已被踩碎的蛋囊紧紧绑住。她冷冷道:“这是阉割牲口方法,用到你身上正好,绑紧了等它坏死,十天后,你的废物蛋蛋就会自己掉下来。”
威廉瘫在地上,意识模糊,疼痛与屈辱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他知道,自己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已被碾碎,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血脉彻底断绝。
十天后,清晨的古堡依旧冰冷。威廉在狗窝般的地毯上醒来,生物钟驱使他爬向艾莉丝的床边,准备服侍她撒晨尿。他的目光却无意间扫到狗窝角落——一团暗红的血肉,正是他脱落的蛋囊。坏死的组织散发着腐臭,细绳依然缠绕其上。威廉盯着那团废物,眼中却没有一丝悲伤,反而闪过一丝病态的解脱。他低声呢喃:“这样……贱狗就彻底属于主人了……再也回不了头……”
他爬到艾莉丝床边,她已醒来,挺着恢复中的身躯,懒散地蹲下。骚臭的晨尿喷涌而出,威廉张嘴接住,大口吞咽,喉咙被刺鼻的味道刺激得火辣辣的。他舔净最后一滴,抬头看向艾莉丝,眼中满是虔诚。艾莉丝冷笑,脚趾轻点他的额头:“瞧瞧你这贱样,连蛋蛋都没了,还舔得这么卖力。去,伺候主人洗漱。”
威廉伺候她洗漱完毕,匆匆清洗自己,换上子爵的华服,强迫自己挺直脊背,走出房间。约克镇的政务堆积如山,艾莉丝的挥霍愈发夸张——她为莉莉安购置金丝摇篮,翻新古堡的育儿室,甚至下令从王都运来稀有的魔法水晶,只为给女婴“祝福”。威廉埋头计算税收,压榨边境商路,试图满足她的开销。他知道,这片封地已完全属于艾莉丝与她的野种。
午后,威廉巡查市场,镇民们的目光带着赤裸的嘲讽。酒馆里,醉汉们高声议论:“费尔法克斯的子爵?哈,连蛋蛋都没了,还立了个野种当继承人!”威廉假装听不见,继续微笑应对,内心却如死灰。他回到古堡,艾莉丝正在花园中逗弄莉莉安,身边围着新的“客人”——一名蒙德骑士国的逃兵,腰间佩剑,眼神炽热。
艾莉丝瞥见威廉,挥手召他:“贱狗,过来给骑士老爷倒酒。”威廉低头端起酒壶,小心斟满酒杯。骑士试探着问:“子爵大人,您……”艾莉丝娇笑打断:“别管他,他乐意当狗。”威廉退到一旁,垂下眼帘,耻辱如刀割。
夜幕降临,艾莉丝带着骑士回了主卧,留下威廉跪在门外,聆听着她的呻吟。贞操锁早已无用,他的下体只剩空荡荡的废墟。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艾莉丝的脚趾、她的冷笑、她的命令。穿越到欧若巴大陆的豪情壮志早已化为泡影,他如今只是她的厕奴、她的阉狗、她的绿帽奴。
次日清晨,威廉继续服侍艾莉丝撒尿、洗漱,然后投入政务。他核查粮仓,安排春耕,压低商税换取订单。每做一件事,他都提醒自己:这是为了主人,为了莉莉安的未来。约克镇的繁荣、费尔法克斯的荣光,都已成了艾莉丝的玩物。而他,曾经的陈烨,如今的威廉,只是一条匍匐在她脚下的废物,永远无法逃脱她的掌控。
家族徽章上昔日雄鹰早已被风雨啃噬得面目全非。冬雪初融,春日的暖风带着花粉与马粪味吹进长廊,仆人们低头疾行,生怕撞见那对母女的荒唐游戏。
莉莉安·费尔法克斯,如今十二岁,身量抽条得极快,继承了母亲艾莉丝那双勾魂的桃花眼与雪白肌肤,却比艾莉丝更早熟、更狠辣。十二岁的她已换了七八个“玩伴”:马夫、卫兵、学徒,甚至路过镇子的吟游诗人。她穿着母亲裁剪的低胸小裙,腰肢一扭便能让男人失魂,笑声像碎银洒在石板路上,清脆却带着毒。
这天午后,阳光从彩绘玻璃斜射进主卧,照得地毯上的金丝闪闪发亮。艾莉丝斜倚在雕花大床上,丝绸睡裙滑到腰际,露出仍旧紧实的腹部与丰满的胸脯。莉莉安盘腿坐在母亲身旁,脚上套着母亲昨夜穿过的丝袜,脚趾涂着艳红蔻丹,像两颗熟透的樱桃。母女俩并肩而卧,十只脚趾一齐翘起,晃出诱人的弧度。
“贱狗,过来。”艾莉丝懒洋洋地打了个响指。
威廉,不,现在该叫“阉狗”,早已没有名字。他跪在床尾,十二年如一日地驼着背,脊椎因常年跪姿弯成一道卑微的弧。曾经的子爵华服被换成粗麻短衫,下摆只到大腿根,露出空荡荡的胯间——那里只剩一道暗红的疤痕,像被撕掉的印章。他爬到床边,额头抵着地毯,声音沙哑却恭顺:“主人,小主人,贱狗来了。”
“舔。”莉莉安咯咯笑着,脚掌直接踩到他脸上,丝袜的汗味混着少女特有的甜腥,瞬间灌满他的鼻腔。
威廉张开嘴,舌尖先触到艾莉丝的脚心,那里带着成熟女人的酸涩与皮革味;再滑到莉莉安的脚趾缝,尝到少女脚汗里夹杂的糖果香。他用舌头卷住每一根脚趾,像给最精密的乐器调弦,轻轻吸吮,发出啧啧水声。母女俩舒服得眯起眼,艾莉丝用脚趾夹住他的鼻尖,莉莉安则用脚跟碾他的额头,像碾一只虫。
“今天谁的脚更香?”艾莉丝慵懒地问。
威廉喉咙滚动,舌尖在两只脚底来回描摹,认真分辨:“回主人,小主人的脚香里带奶味,主人脚心有淡淡的麝香……贱狗分得清。”
莉莉安笑得前仰后合,脚掌啪地拍在他后脑:“答对了!赏你吃灰!”她故意把脚底在地板上蹭了蹭,沾了一层浮尘,再塞进他嘴里。威廉咀嚼着泥土与死皮的苦涩,喉结上下滑动,眼神却亮得吓人——那是彻底驯化的狂喜。
夜幕降临时,母女俩并排坐在床沿,裙子撩到腰际,露出白花花的大腿。艾莉丝拍拍威廉的光头:“张嘴,马桶准备好了。”
威廉仰面躺倒,头颅正好卡在床沿下方。莉莉安兴奋地跨坐在他胸口,小屁股一沉,堵住他的呼吸。艾莉丝则优雅地蹲在他脸上,臀瓣压扁他的鼻子。两股热流几乎同时倾泻而下:母亲的尿液带着熟女的浓烈骚腥,女儿的则清淡却量大。威廉的喉咙疯狂蠕动,咕咚咕咚吞咽,偶尔呛得咳嗽,尿水从嘴角溢出,在地毯上积成一滩金黄。
“别浪费!”莉莉安用脚趾掐他乳头,“咽不下去就淹死你!”
尿完,母女俩交换位置,拉稀的粪便接踵而至。艾莉丝的粪便黑褐、黏稠,带着隔夜红酒的酸;莉莉安的则浅黄、稀软,混着未消化的果粒。两坨粪便精准落进他嘴里,堆成一座恶臭的小山。威廉嚼得满嘴褐色,舌尖卷着残渣,发出满足的呜咽。
“蒙眼!”艾莉丝打了个响指。黑绸布蒙住他的眼睛,世界陷入彻底黑暗。母女俩咯咯笑着交换位置,再次排泄。威廉只能凭味道与口感分辨:酸的、苦的、甜的、腥的……他像品酒师般皱眉深嗅,舌尖轻点:“左边是主人……右边是小主人……”
“错!”莉莉安尖叫着笑出声,“今天我和妈妈吃了同样的甜点!”话音未落,皮鞭破空声响起。母女俩一人握一条浸油的马鞭,将威廉倒吊在床柱上,鞭梢抽在他背上、臀上、残缺的胯间。皮开肉绽的脆响混着他的惨叫,在古堡上空回荡,像一首扭曲的摇篮曲。
抽到尽兴,母女俩才把他解下来,拖进角落那个特制的“尿刑箱”。箱子只有半人高,四壁密封,顶部开一排小孔。威廉的脑袋被铁箍锁死在箱底,只能仰面朝上。艾莉丝与莉莉安并肩蹲在箱顶,臀部对准孔洞,同时开闸。尿液如瀑布倾泻,瞬间淹到他下巴。威廉拼命张嘴吞咽,喉咙发出野兽般的咕噜声;一旦跟不上节奏,尿水便没过鼻孔,呛得他疯狂扑腾。母女俩笑得前仰后合,尿流时断时续,像给一条溺水的狗放水又提水。
“咽!咽!咽!”莉莉安拍着箱盖打节拍,“咽不完就埋了你!”
整整一柱香时间,箱内尿液涨了又落,落了又涨。威廉的肚子鼓得像孕妇,皮肤被尿液腌得发白。直到母女俩尿得腿软,才揭开箱盖,把他拖出来。他瘫在地上,浑身滴着黄水,嘴角却挂着傻笑,沙哑地呢喃:“谢……谢主人……谢小主人……贱狗……喝饱了……”
艾莉丝用脚尖踢了踢他肿胀的肚皮:“明天继续。莉莉安,妈妈教你新玩法,用蜡烛滴他舌头。”
莉莉安拍手欢呼:“好耶!我要滴成一朵花!”
月光透过窗缝,照在母女俩并排的睡颜上,也照在地板上那滩未干的尿渍里。威廉蜷缩在床脚,像一条被玩腻的破布娃娃,呼吸均匀,梦里还在吞咽那无尽的骚臭液体。十二年,足以让一个穿越者的雄心腐烂成泥;十二年,也足以让一条阉狗把地狱当做天堂。
古堡外,春风吹动残破的旗帜,雄鹰的眼睛早已被鸟屎糊住。约克镇的夜晚,永远回荡着母女俩银铃般的笑声,和地板下那条狗满足的呜咽。
几个时辰后,产婆抱着一个裹着丝绸的婴孩走出,恭敬地对威廉道:“子爵大人,夫人诞下一名女婴,母女平安。”威廉抬头,目光空洞,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孩子绝非他的血脉,却即将堂而皇之地冠上费尔法克斯的姓氏,成为四万英亩封地的合法继承人。
艾莉丝在产房内休养了数日,身体迅速恢复。她斜倚在雕花大床上,怀中抱着女婴,眼中闪着得意的光芒。女婴被取名莉莉安·费尔法克斯,名字一经宣布,约克镇的最后几名仆人也不敢多言,只低头窃窃私语。艾莉丝抚摸着女婴细嫩的脸颊,红唇微勾,喃喃道:“我的小宝贝,未来的子爵。”
几天后,艾莉丝已能下床活动。她召来威廉,声音甜腻却带着刺骨的寒意:“贱狗,滚过来。”威廉爬进主卧,膝盖在石板上磨出红痕,低头跪在她脚边。艾莉丝赤足踩在毛毯上,脚趾涂着鲜红蔻丹,挺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腰肢,俯视着他,眼中满是轻蔑:“褪下裤子,双腿叉开,双手抱头。”
威廉喉咙发干,身体微微颤抖,却不敢违抗。他褪下裤子,露出被贞操锁禁锢的下体,双腿叉开,双手抱头,摆出完全臣服的姿势。贞操锁解开后,他那萎缩的小鸟暴露在空气中,青紫而无力。艾莉丝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残忍:“贱狗,你猜猜主人今天要干什么?”
威廉的心猛地一沉,隐约猜到了她的意图。她要彻底废了他,斩断他作为男人的最后痕迹,确保莉莉安的继承人地位坚不可摧。他张了张嘴,想求饶,却只发出一声低哑的呜咽。艾莉丝的眼神冷得像冰,缓缓抬起赤足,脚掌对准他的阴茎,狠狠一踢。
钻心的疼痛如雷霆般炸开,威廉忍不住惨叫出声,身体蜷缩成一团。艾莉丝皱了皱眉,厌恶地啐了一口:“叫什么叫?吵死了!”她从床头抓起一双提前准备好的女仆穿过的臭袜子,散发着汗臭与霉味,毫不犹豫地塞进威廉的嘴里。袜子的味道呛得他眼泪直流,却不敢吐出,只能呜呜低鸣。
艾莉丝冷哼一声,继续抬起脚,狠狠踢向他的阴茎。一下、两下、数十下,每一脚都精准而凶狠。威廉的惨叫被袜子堵住,化为闷哼,疼痛如潮水般席卷全身。然而,诡异的是,在这剧烈的折磨中,他竟渐渐升起一种扭曲的快感——虐阳的快感如毒药般侵蚀他的神经。他的阴茎在踢击下变得青紫肿胀,血丝渗出,模样惨不忍睹。
“趴下!”艾莉丝冷冷命令。威廉翻身趴在地上,臀部高翘,瑟瑟发抖。艾莉丝抬起脚掌,精准地踩住他的睾丸,力道逐渐加重。她冷笑:“贱狗,你的蛋蛋也配存在?今天主人帮你彻底了断!”话音未落,她猛地用力,脚掌狠狠碾下。
一声闷响,威廉的睾丸被彻底踩碎,剧痛如刀割般撕裂他的意识。他在袜子的堵塞下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身体抽搐,却不敢挣扎。艾莉丝俯身,眼中满是垃圾般的轻蔑,拿起一根细绳,将那已被踩碎的蛋囊紧紧绑住。她冷冷道:“这是阉割牲口方法,用到你身上正好,绑紧了等它坏死,十天后,你的废物蛋蛋就会自己掉下来。”
威廉瘫在地上,意识模糊,疼痛与屈辱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他知道,自己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已被碾碎,费尔法克斯家族的血脉彻底断绝。
十天后,清晨的古堡依旧冰冷。威廉在狗窝般的地毯上醒来,生物钟驱使他爬向艾莉丝的床边,准备服侍她撒晨尿。他的目光却无意间扫到狗窝角落——一团暗红的血肉,正是他脱落的蛋囊。坏死的组织散发着腐臭,细绳依然缠绕其上。威廉盯着那团废物,眼中却没有一丝悲伤,反而闪过一丝病态的解脱。他低声呢喃:“这样……贱狗就彻底属于主人了……再也回不了头……”
他爬到艾莉丝床边,她已醒来,挺着恢复中的身躯,懒散地蹲下。骚臭的晨尿喷涌而出,威廉张嘴接住,大口吞咽,喉咙被刺鼻的味道刺激得火辣辣的。他舔净最后一滴,抬头看向艾莉丝,眼中满是虔诚。艾莉丝冷笑,脚趾轻点他的额头:“瞧瞧你这贱样,连蛋蛋都没了,还舔得这么卖力。去,伺候主人洗漱。”
威廉伺候她洗漱完毕,匆匆清洗自己,换上子爵的华服,强迫自己挺直脊背,走出房间。约克镇的政务堆积如山,艾莉丝的挥霍愈发夸张——她为莉莉安购置金丝摇篮,翻新古堡的育儿室,甚至下令从王都运来稀有的魔法水晶,只为给女婴“祝福”。威廉埋头计算税收,压榨边境商路,试图满足她的开销。他知道,这片封地已完全属于艾莉丝与她的野种。
午后,威廉巡查市场,镇民们的目光带着赤裸的嘲讽。酒馆里,醉汉们高声议论:“费尔法克斯的子爵?哈,连蛋蛋都没了,还立了个野种当继承人!”威廉假装听不见,继续微笑应对,内心却如死灰。他回到古堡,艾莉丝正在花园中逗弄莉莉安,身边围着新的“客人”——一名蒙德骑士国的逃兵,腰间佩剑,眼神炽热。
艾莉丝瞥见威廉,挥手召他:“贱狗,过来给骑士老爷倒酒。”威廉低头端起酒壶,小心斟满酒杯。骑士试探着问:“子爵大人,您……”艾莉丝娇笑打断:“别管他,他乐意当狗。”威廉退到一旁,垂下眼帘,耻辱如刀割。
夜幕降临,艾莉丝带着骑士回了主卧,留下威廉跪在门外,聆听着她的呻吟。贞操锁早已无用,他的下体只剩空荡荡的废墟。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艾莉丝的脚趾、她的冷笑、她的命令。穿越到欧若巴大陆的豪情壮志早已化为泡影,他如今只是她的厕奴、她的阉狗、她的绿帽奴。
次日清晨,威廉继续服侍艾莉丝撒尿、洗漱,然后投入政务。他核查粮仓,安排春耕,压低商税换取订单。每做一件事,他都提醒自己:这是为了主人,为了莉莉安的未来。约克镇的繁荣、费尔法克斯的荣光,都已成了艾莉丝的玩物。而他,曾经的陈烨,如今的威廉,只是一条匍匐在她脚下的废物,永远无法逃脱她的掌控。
家族徽章上昔日雄鹰早已被风雨啃噬得面目全非。冬雪初融,春日的暖风带着花粉与马粪味吹进长廊,仆人们低头疾行,生怕撞见那对母女的荒唐游戏。
莉莉安·费尔法克斯,如今十二岁,身量抽条得极快,继承了母亲艾莉丝那双勾魂的桃花眼与雪白肌肤,却比艾莉丝更早熟、更狠辣。十二岁的她已换了七八个“玩伴”:马夫、卫兵、学徒,甚至路过镇子的吟游诗人。她穿着母亲裁剪的低胸小裙,腰肢一扭便能让男人失魂,笑声像碎银洒在石板路上,清脆却带着毒。
这天午后,阳光从彩绘玻璃斜射进主卧,照得地毯上的金丝闪闪发亮。艾莉丝斜倚在雕花大床上,丝绸睡裙滑到腰际,露出仍旧紧实的腹部与丰满的胸脯。莉莉安盘腿坐在母亲身旁,脚上套着母亲昨夜穿过的丝袜,脚趾涂着艳红蔻丹,像两颗熟透的樱桃。母女俩并肩而卧,十只脚趾一齐翘起,晃出诱人的弧度。
“贱狗,过来。”艾莉丝懒洋洋地打了个响指。
威廉,不,现在该叫“阉狗”,早已没有名字。他跪在床尾,十二年如一日地驼着背,脊椎因常年跪姿弯成一道卑微的弧。曾经的子爵华服被换成粗麻短衫,下摆只到大腿根,露出空荡荡的胯间——那里只剩一道暗红的疤痕,像被撕掉的印章。他爬到床边,额头抵着地毯,声音沙哑却恭顺:“主人,小主人,贱狗来了。”
“舔。”莉莉安咯咯笑着,脚掌直接踩到他脸上,丝袜的汗味混着少女特有的甜腥,瞬间灌满他的鼻腔。
威廉张开嘴,舌尖先触到艾莉丝的脚心,那里带着成熟女人的酸涩与皮革味;再滑到莉莉安的脚趾缝,尝到少女脚汗里夹杂的糖果香。他用舌头卷住每一根脚趾,像给最精密的乐器调弦,轻轻吸吮,发出啧啧水声。母女俩舒服得眯起眼,艾莉丝用脚趾夹住他的鼻尖,莉莉安则用脚跟碾他的额头,像碾一只虫。
“今天谁的脚更香?”艾莉丝慵懒地问。
威廉喉咙滚动,舌尖在两只脚底来回描摹,认真分辨:“回主人,小主人的脚香里带奶味,主人脚心有淡淡的麝香……贱狗分得清。”
莉莉安笑得前仰后合,脚掌啪地拍在他后脑:“答对了!赏你吃灰!”她故意把脚底在地板上蹭了蹭,沾了一层浮尘,再塞进他嘴里。威廉咀嚼着泥土与死皮的苦涩,喉结上下滑动,眼神却亮得吓人——那是彻底驯化的狂喜。
夜幕降临时,母女俩并排坐在床沿,裙子撩到腰际,露出白花花的大腿。艾莉丝拍拍威廉的光头:“张嘴,马桶准备好了。”
威廉仰面躺倒,头颅正好卡在床沿下方。莉莉安兴奋地跨坐在他胸口,小屁股一沉,堵住他的呼吸。艾莉丝则优雅地蹲在他脸上,臀瓣压扁他的鼻子。两股热流几乎同时倾泻而下:母亲的尿液带着熟女的浓烈骚腥,女儿的则清淡却量大。威廉的喉咙疯狂蠕动,咕咚咕咚吞咽,偶尔呛得咳嗽,尿水从嘴角溢出,在地毯上积成一滩金黄。
“别浪费!”莉莉安用脚趾掐他乳头,“咽不下去就淹死你!”
尿完,母女俩交换位置,拉稀的粪便接踵而至。艾莉丝的粪便黑褐、黏稠,带着隔夜红酒的酸;莉莉安的则浅黄、稀软,混着未消化的果粒。两坨粪便精准落进他嘴里,堆成一座恶臭的小山。威廉嚼得满嘴褐色,舌尖卷着残渣,发出满足的呜咽。
“蒙眼!”艾莉丝打了个响指。黑绸布蒙住他的眼睛,世界陷入彻底黑暗。母女俩咯咯笑着交换位置,再次排泄。威廉只能凭味道与口感分辨:酸的、苦的、甜的、腥的……他像品酒师般皱眉深嗅,舌尖轻点:“左边是主人……右边是小主人……”
“错!”莉莉安尖叫着笑出声,“今天我和妈妈吃了同样的甜点!”话音未落,皮鞭破空声响起。母女俩一人握一条浸油的马鞭,将威廉倒吊在床柱上,鞭梢抽在他背上、臀上、残缺的胯间。皮开肉绽的脆响混着他的惨叫,在古堡上空回荡,像一首扭曲的摇篮曲。
抽到尽兴,母女俩才把他解下来,拖进角落那个特制的“尿刑箱”。箱子只有半人高,四壁密封,顶部开一排小孔。威廉的脑袋被铁箍锁死在箱底,只能仰面朝上。艾莉丝与莉莉安并肩蹲在箱顶,臀部对准孔洞,同时开闸。尿液如瀑布倾泻,瞬间淹到他下巴。威廉拼命张嘴吞咽,喉咙发出野兽般的咕噜声;一旦跟不上节奏,尿水便没过鼻孔,呛得他疯狂扑腾。母女俩笑得前仰后合,尿流时断时续,像给一条溺水的狗放水又提水。
“咽!咽!咽!”莉莉安拍着箱盖打节拍,“咽不完就埋了你!”
整整一柱香时间,箱内尿液涨了又落,落了又涨。威廉的肚子鼓得像孕妇,皮肤被尿液腌得发白。直到母女俩尿得腿软,才揭开箱盖,把他拖出来。他瘫在地上,浑身滴着黄水,嘴角却挂着傻笑,沙哑地呢喃:“谢……谢主人……谢小主人……贱狗……喝饱了……”
艾莉丝用脚尖踢了踢他肿胀的肚皮:“明天继续。莉莉安,妈妈教你新玩法,用蜡烛滴他舌头。”
莉莉安拍手欢呼:“好耶!我要滴成一朵花!”
月光透过窗缝,照在母女俩并排的睡颜上,也照在地板上那滩未干的尿渍里。威廉蜷缩在床脚,像一条被玩腻的破布娃娃,呼吸均匀,梦里还在吞咽那无尽的骚臭液体。十二年,足以让一个穿越者的雄心腐烂成泥;十二年,也足以让一条阉狗把地狱当做天堂。
古堡外,春风吹动残破的旗帜,雄鹰的眼睛早已被鸟屎糊住。约克镇的夜晚,永远回荡着母女俩银铃般的笑声,和地板下那条狗满足的呜咽。
完结,以后肯定不会在开大背景了
催更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