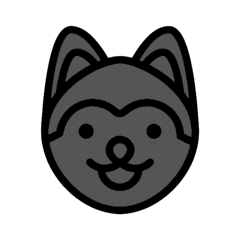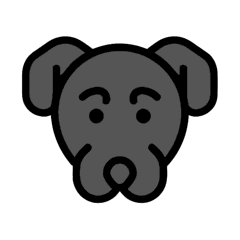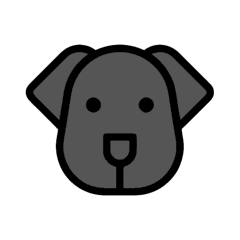0.5终于鼓起勇气分享一下了(顺道找同好
天哪,这个太强了,也太细节了,感觉这种击打tj真的特别少见啊。说实话我也好这口,主要是小时候看那种女反派虐人电视剧启发的,可恶啊,哈哈,反而对其它的项目兴趣很一般般。不过目前没有遇到过那种真的类似格斗的s,之前都是让不了解这个的S放开了踢踹肚子胸口啥的,然后接下来四五天全身疼。体验确实还可以,但是感觉肯定是远远不如你这个专业的,哈哈
什么时候更新? 感觉这是这个论坛上唯一还剩下的文了。再不更新我真的会无聊死。羡慕这样的关系
哦我才意识到,写报告也是play的一部分,等下次跟男朋友试试😋
次日醒来,是在一阵锐痛中。
那痛感像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牵扯着每一寸肌肉。我试着起身,却只换来一声没能忍住的尖叫,身体便不听使唤地重新摔回柔软的床垫里。低头看,小腹上是一片驳杂的印记,青的、紫的,像一场风暴过后的天空。那是我昨天的勋章。
那声尖叫惊动了她。她走进来,身上还带着清晨的凉气。目光落在我腹部的淤青上,停留了片刻,像一位画师在审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满意。然后,就在我以为会是一声早安或者一个吻时,一只拳头,带着熟悉的力道和风声,精准地落在了那片天空的正中央。
我尖叫起来。剧痛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一股熟悉的、令人战栗的暖流,从下腹深处猛地炸开,瞬间冲垮了所有理智的堤坝。一股失禁的、可耻的热流濡湿了内裤。
她俯下身,说我真是天选。又有些遗憾地补充道,可惜你的身体还跟不上,得缓缓,今天不能再打肚子了。
她的手指抚上我濡湿的内裤,明知那是什么,却还是带着恶趣味,轻轻按了按那片水渍,低声问:“这样一下,就能让你爽到高潮?”(啊其实是尿,但是烂泥进裤裆不是矢也是矢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情趣就纯脸红没反驳她)。
她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将我的双手反剪在身后,用冰凉的金属铐住。刚才那一拳的余波未散,膀胱的涨意愈发汹涌,我忍不住开口求她。她领着我走进浴室,却并不解开我的束缚。就在我以为她会帮我脱下内裤时,她的手却隔着那层湿透的布料探了进来,指尖堵住了那个急欲宣泄的出口,不轻不重地摩挲着。
我再也憋不住了。尿液在巨大的压力下冲破阻碍,却又无法顺畅地流出,只能一点一点地,先是打湿她的指尖,然后是整只手,再然后,是我的内裤,最后顺着大腿内侧,蜿蜒地淌下去,在浴室的地板上积成一小滩。整个过程漫长而磨人。
她抽出手,然后还伸出舌尖,舔了舔指缝。她说,关于你身体里这条水道的玩法和责弄,我们以后再慢慢开发。我不敢看她,别过头,只觉得那画面比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更让我心悸。(我是真受不了这个,虽然知道除了代谢废物以外尿是人身上最干净的液体了这件事但是道德上接受不能。她敢舔我都不敢看她舔)
她给我灌下大半瓶脉动(打钱谢谢),然后,就在我抗议的呜咽声中,将那条刚被我弄湿的、还带着体温的内裤,满满当当地塞进了我的嘴里。一股咸腥的、混杂着布料和体液的怪味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和鼻腔,熏得我头晕目眩。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她做出了那个代表“停止”的词。
那条内裤在我嘴里停留了半个来回,便被她取出来,扔在了地上。
她扶着我,走到客厅中央的一张椅子前坐下。我的双手被反拷在椅背上,双脚也被绑在了凳子腿上,大腿张开动弹不得。她蹲在我面前,目光与我平齐,说:“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我是不是得给你‘幸’福?接下来,我会一直让你保持在悬崖边上,但什么时候跳下去,得听我的。如果你听话,最后会很爽很爽哦。”
她说这是我昨天很棒的奖励。
也是我四十次寸止地狱和那一天忘了数多少次高潮的开始。
起初两次,她只是用手。我能清晰地看到她专注的神情,手指在我体内搅动,不时刮过那些敏感的软肉。因为能看见,所以羞耻感比情愫快得多,身体的反应也跟着迟钝。她似乎也察觉到了,于是找来一条布巾,蒙住了我的眼睛。
世界陷入黑暗,感官便被放大了无数倍。她站到我身后,右手重新探入我的下身,左手则伸进文胸,拨弄我的乳首。我很快就到了边缘,下腹像揣着一团火,又像有了第二颗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动。我忍不住挣扎,绷紧的大腿肌肉开始微微发颤。
后来她似乎也累了,便换了个跳蛋塞进来(哎,当时用的还是不带电的)。我在椅子上挣扎扑腾,大腿也一直紧绷着。每当快要失控时,便大声喊她的名字。她会依言停下,等我急促的呼吸稍稍平复,便又重新开启,然后又是一次次加档,一次次判等。到了最后,我的思考能力彻底瓦解,大脑变成了一片混沌的泥潭。在无尽的、濒临崩溃的欲望折磨下,呼喊她的名字,祈求她停下,竟成了我唯一的救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本能——本能地相信那无可言状的最终极乐,于是拧巴的我一边想着挣扎出来,用手给自己解脱,另一边又可笑的用理性期待着来自于她的极端体验的救赎。
于是第四十次,这是她事后跟我说的,她又如约停了下来。我感觉那个冰凉的物件被抽走了。就在我以为这又是一次无望的间歇时,一只手猛地拧住我的胸,另一只手的手指则探进我泥泞不堪的下身,在最敏感的那一点上,狠狠一挠。
那是短暂的失神。等意识回笼时,我感到自己的大腿在剧烈痉挛。她摘下了我的眼罩——那块布巾早已被生理性的泪水浸得湿透。我看见自己的下身,正随着身体的抽搐,喷射出一股股浑浊的液体。椅子上,地板上,一片狼藉,积了一层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爱液的东西。
她在我耳边夸我,说真棒,说我是听话的好孩子,这就是奖励。我脑子一片空白,连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下淌着涎水滴在胸口也无暇顾及。
“接下来,你可以放心的高潮了。”她说着,又将两根手指捅了进去。我条件反射地想夹紧双腿,却被牢牢地绑着。她重新站到我身后,除了责弄我的乳首,还时不时地啃咬我的脖颈和耳垂。我很快便再次缴械。
再往后,一次又一次,我的快感逐渐被酸痛和疲惫所取代。身下也越来越干涩,每一次进入,都像是用砂纸在打磨。到第七次,还是第九次,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身体里像是着了火,又干又疼。她在我体内搅动了许久,我也只是发出一声声细碎的哭叫,再也流不出什么来了。
她这才终于停手。抱着我,轻拍我的后背安慰我,于是我索性又哭了一场。
那痛感像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牵扯着每一寸肌肉。我试着起身,却只换来一声没能忍住的尖叫,身体便不听使唤地重新摔回柔软的床垫里。低头看,小腹上是一片驳杂的印记,青的、紫的,像一场风暴过后的天空。那是我昨天的勋章。
那声尖叫惊动了她。她走进来,身上还带着清晨的凉气。目光落在我腹部的淤青上,停留了片刻,像一位画师在审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满意。然后,就在我以为会是一声早安或者一个吻时,一只拳头,带着熟悉的力道和风声,精准地落在了那片天空的正中央。
我尖叫起来。剧痛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一股熟悉的、令人战栗的暖流,从下腹深处猛地炸开,瞬间冲垮了所有理智的堤坝。一股失禁的、可耻的热流濡湿了内裤。
她俯下身,说我真是天选。又有些遗憾地补充道,可惜你的身体还跟不上,得缓缓,今天不能再打肚子了。
她的手指抚上我濡湿的内裤,明知那是什么,却还是带着恶趣味,轻轻按了按那片水渍,低声问:“这样一下,就能让你爽到高潮?”(啊其实是尿,但是烂泥进裤裆不是矢也是矢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情趣就纯脸红没反驳她)。
她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将我的双手反剪在身后,用冰凉的金属铐住。刚才那一拳的余波未散,膀胱的涨意愈发汹涌,我忍不住开口求她。她领着我走进浴室,却并不解开我的束缚。就在我以为她会帮我脱下内裤时,她的手却隔着那层湿透的布料探了进来,指尖堵住了那个急欲宣泄的出口,不轻不重地摩挲着。
我再也憋不住了。尿液在巨大的压力下冲破阻碍,却又无法顺畅地流出,只能一点一点地,先是打湿她的指尖,然后是整只手,再然后,是我的内裤,最后顺着大腿内侧,蜿蜒地淌下去,在浴室的地板上积成一小滩。整个过程漫长而磨人。
她抽出手,然后还伸出舌尖,舔了舔指缝。她说,关于你身体里这条水道的玩法和责弄,我们以后再慢慢开发。我不敢看她,别过头,只觉得那画面比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更让我心悸。(我是真受不了这个,虽然知道除了代谢废物以外尿是人身上最干净的液体了这件事但是道德上接受不能。她敢舔我都不敢看她舔)
她给我灌下大半瓶脉动(打钱谢谢),然后,就在我抗议的呜咽声中,将那条刚被我弄湿的、还带着体温的内裤,满满当当地塞进了我的嘴里。一股咸腥的、混杂着布料和体液的怪味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和鼻腔,熏得我头晕目眩。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她做出了那个代表“停止”的词。
那条内裤在我嘴里停留了半个来回,便被她取出来,扔在了地上。
她扶着我,走到客厅中央的一张椅子前坐下。我的双手被反拷在椅背上,双脚也被绑在了凳子腿上,大腿张开动弹不得。她蹲在我面前,目光与我平齐,说:“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我是不是得给你‘幸’福?接下来,我会一直让你保持在悬崖边上,但什么时候跳下去,得听我的。如果你听话,最后会很爽很爽哦。”
她说这是我昨天很棒的奖励。
也是我四十次寸止地狱和那一天忘了数多少次高潮的开始。
起初两次,她只是用手。我能清晰地看到她专注的神情,手指在我体内搅动,不时刮过那些敏感的软肉。因为能看见,所以羞耻感比情愫快得多,身体的反应也跟着迟钝。她似乎也察觉到了,于是找来一条布巾,蒙住了我的眼睛。
世界陷入黑暗,感官便被放大了无数倍。她站到我身后,右手重新探入我的下身,左手则伸进文胸,拨弄我的乳首。我很快就到了边缘,下腹像揣着一团火,又像有了第二颗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动。我忍不住挣扎,绷紧的大腿肌肉开始微微发颤。
后来她似乎也累了,便换了个跳蛋塞进来(哎,当时用的还是不带电的)。我在椅子上挣扎扑腾,大腿也一直紧绷着。每当快要失控时,便大声喊她的名字。她会依言停下,等我急促的呼吸稍稍平复,便又重新开启,然后又是一次次加档,一次次判等。到了最后,我的思考能力彻底瓦解,大脑变成了一片混沌的泥潭。在无尽的、濒临崩溃的欲望折磨下,呼喊她的名字,祈求她停下,竟成了我唯一的救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本能——本能地相信那无可言状的最终极乐,于是拧巴的我一边想着挣扎出来,用手给自己解脱,另一边又可笑的用理性期待着来自于她的极端体验的救赎。
于是第四十次,这是她事后跟我说的,她又如约停了下来。我感觉那个冰凉的物件被抽走了。就在我以为这又是一次无望的间歇时,一只手猛地拧住我的胸,另一只手的手指则探进我泥泞不堪的下身,在最敏感的那一点上,狠狠一挠。
那是短暂的失神。等意识回笼时,我感到自己的大腿在剧烈痉挛。她摘下了我的眼罩——那块布巾早已被生理性的泪水浸得湿透。我看见自己的下身,正随着身体的抽搐,喷射出一股股浑浊的液体。椅子上,地板上,一片狼藉,积了一层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爱液的东西。
她在我耳边夸我,说真棒,说我是听话的好孩子,这就是奖励。我脑子一片空白,连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下淌着涎水滴在胸口也无暇顾及。
“接下来,你可以放心的高潮了。”她说着,又将两根手指捅了进去。我条件反射地想夹紧双腿,却被牢牢地绑着。她重新站到我身后,除了责弄我的乳首,还时不时地啃咬我的脖颈和耳垂。我很快便再次缴械。
再往后,一次又一次,我的快感逐渐被酸痛和疲惫所取代。身下也越来越干涩,每一次进入,都像是用砂纸在打磨。到第七次,还是第九次,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身体里像是着了火,又干又疼。她在我体内搅动了许久,我也只是发出一声声细碎的哭叫,再也流不出什么来了。
她这才终于停手。抱着我,轻拍我的后背安慰我,于是我索性又哭了一场。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好吃
ANNCOP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tinker1001:↑知道的哦,我跟男朋友有些手法都是跟她学来的(ANNCOP:↑话说大家觉得我是继续从头一点点记录比较好还是明天现场直播(赛后总结)比较好?赛后总结自然是最好的~~,坐等更新,话说楼主的男朋友知道你找教练这么玩吗?好奇他什么感受😀
我跟她玩的有一点大,不光在glsm中是硬核模式,就算是整个BDSM圈中也算硬核大概
明天想更我和男友的故事了
Akane7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Xingnainai:↑挺有趣😊哥们晚上十点才下班,byd哪个学校都在招生😋
另外谁懂两点钟还没工作完的心酸😌
Akane7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ANNCOP:↑拳馆里,虽然打扫得很光鲜,空气里却总是一股汗臭混着革油的味道。好强的文笔!
声音是沉闷的,拳头或者膝盖击中皮靶,一下,又一下,像湿木头在烧。
抗击打的要义,是绷紧核心,用肌肉筑成一道墙去抵抗,她不厌其烦的用拳头教我,直到那天,她单独把我留下。
她说,忘了那些,现在,试着别抵抗,去接纳。
就在那一次,一记不重的拳落下来,我的小腹深处却像被什么东西惊了一下,起了一阵很奇怪的战栗。
她停了手,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了然。
她说,你很特别。
后来便去了她家。屋子很空,没什么多余的东西。
她让我试着接她的拳,不用格挡,就用身体感受。
那不是拳馆里的练习,更像一种测试,一种问询。
拳点落在肚子上,起初是闷的,然后慢慢散开,变成一片温热的、持续的麻。
她看着我皮肤上泛起的红晕,像水彩在宣纸上洇开。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赤着脚,脚趾干净、修长。我跪在地板上,地板很凉,她的脚心是温的,脚趾在我嘴里,我含糊不清的呜咽着。
她说,你很有天赋。
她说,周末来吧。
我到她家的时候,天刚亮透。她让我撑在地上,用小臂和膝盖。屋里很静,能听到她在我背上吃早饭的声音,筷子划过盘子,很轻。那重量是活的,压着我的肩胛骨,让我觉得很安稳。
她去洗澡,水声哗哗的。她隔着浴室的磨砂玻璃门,问我,要不要把自己交给她?
我几乎没思考,应了一声,好呀。那一声很轻,像是吐出了一直憋着的一口气。
我也洗完了,穿戴整齐地出来。她却让我脱掉,只留下贴身的衣物。她把我抵在墙上,墙壁冰凉。一只手覆上我的胸口,另一只手轻轻捏着我的下巴,膝盖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挤进我的腿间,缓慢地、带着薄茧的布料厮磨。她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说,准备好挨过一天了吗?说我可以叫出来,她爱听。
腿间的热度还没散尽,一记拳就落在了胸口和腹部的交界处。那一瞬间,我好像哑了,身体里所有的声音都被这一拳打了回去。她说,我们先数三十下,你不许绷紧肚子,数给我听。
空气里只有她沉稳的拳风和我的报数声。我努力让腹部松弛下来,像一块海绵。二十八下,我都做得很好,几乎要相信自己驯服了身体的本能。第二十九下,力道陡然加重,像一块石头沉进深水里,我感到肚子里的一切都空了,然后又在一阵晕眩里猛地涌回来。
于是第三十下,我下意识地绷紧了。那一刻我知道,坏了。
她轻笑起来,拍了拍我的肚子。然后,用一条布蒙住了我的眼睛。
世界变成了全然的黑暗,只有声音和触感。我感觉自己手被缚住,吊了起来,脚尖将将离地。一阵细密的、不带力道的击打落在了我的下身,像急促的雨点,不痛,却让我的神经末梢都烧了起来。身体不听使唤地抽动,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在我脱力地颤抖时,她解开了我的裤子。黑暗里,一个精准的、尖锐的痛点自花蒂传来,像有人用指甲掐灭了一颗火星。又是一阵更剧烈的痉挛。
然后,我感觉到她的手,带着薄茧,探了进来。
她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很轻的惊叹,说,还是个孩子啊。
她凑到我耳边,气息是热的,混着沐浴露的清香,牙齿啃咬我的脖子和肩膀,问,要不要我帮你?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好。
那是一个很用力的、捅进来的动作。
她把我的眼罩揭开,我哭得像个孩子,而是因为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名为‘自我’的弦,终于断了。断掉的一瞬间,我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落到实地的、被允许软弱的安稳。她把我抱在怀里,手还在我身体里,用一种很慢的节奏搅动,像是在帮我收拾那些散落一地的碎片,轻声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她把我弄干净,给我穿好衣服,像照顾一个娃娃。然后,她牵着我的手,领我出门吃饭,我的身下传来阵阵嗡鸣。
窗外的阳光很好,街上的行人、车辆,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只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那是第一个值得在这里纪念的上午。
写的很好哎
去她家的路上,心里始终是拧巴的。
那个被内化了的观念,像一根绳索,在我的脑子里打了个死结。男朋友允许了我,可我是否应当允许我自己呢?它让我无法全然地投入,身体向着她,思绪却总想往后退。这种割裂,让最初的体验蒙上了一层灰。
今天没有预设的道具。到了她家,迎接我的是三瓶矿泉水,她看着我一瓶瓶地灌下去,像是在饮驴。然后是洗澡,热水冲刷着身体,却冲不散心里的那个结。
洗完澡,我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她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屋子中央,说,站稳了。她的意图很明显,只要我的腿稍一发软,我的整个重心,便只能交付于她即将探向我身下的那只手。
她的右手上,套了一只黑色的丝质手套。那只手探了下来,带着布料的凉意,轻轻一撑,食指与无名指便拨开了最外层的软肉,中指的指腹则不偏不倚地压上了那颗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小小的突起。那一瞬间,像是有人在我神经的最深处,拨动了一根从未被触碰过的弦,于是我带着尖叫跳了起来。
她笑了一声,带着发现新大陆的惊喜,把那根覆着黑丝的中指重新抵在那里,说:“诶呀,原来你这里还没被开发过呀,那你今天可惨咯。”
原定的计划是带我体验阴蒂责和我当猫猫进行“口舌侍奉”的,可惜被打乱了。她让我跪在地板上,挺直后背。想到男朋友之前在我手下被责弄的时候宛如一条离了水的鱼般蹦跶,我便头皮发麻,意识到了某些惊恐的事将要发生。
“给我舔”,她说。覆着黑丝手套的右手伸到我的嘴前,却又保持着一丝距离。“你的口水,就是你唯一的润滑。不好好舔,待会儿伤到了,我可不管。”她看着我眼神里的哀求,又补充道,“不不不,我不会摘手丝的。你明天就在我这里歇着吧,别想走路了。”
我认命地伸出舌头,在那光滑却又带着织物质感的丝绸上舔舐着。舌尖的触感是粗粝的,我的思绪也开始收紧,飞向跟男友的对话。
舌头上的触感消失,脸颊上却传来一阵清脆的痛感,一记耳光把我从纷乱的思绪中扇了回来。她说:“怎么,还有心事?那就只能这样一直责到你翻着白眼,只会喘气,说不出话为止了哦。”
那一刻,那个拧巴的结,似乎被这一巴掌打松了。一种破罐破摔的冲动涌了上来。我重新站起来,踮着脚,主动将身下最脆弱的地方,送进了她那只比一开始抬得更高的、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里。
那只覆着丝绸的手,像一块干燥的、不断升温的浮石,在我最柔软的地方研磨。更何况,我的膀胱里还装着那三瓶水的重量。我很快就泣不成声,哭喊着求着姐姐慢点,求着姐姐允许我先去排泄。但所有的哀求都被她刻意地忽略了。我当然也不敢真的失禁,怕这会成为她更有力的借口。
在这样残忍的折磨里,高潮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尿意却是永不停歇的潮水。疾痛惨怛中,我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飘向了远方。
这次的巴掌,却是从下身传来的。她显然意识到了我的再次分神,也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分神的源头。
她将我推倒在地,像丢开一件无用的东西。电话的拨号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像一种审判的预告。我听到她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语调说:“你女朋友可真厉害,我正弄着她,她还能想到你。你现在就听着她的声音开始打飞机。要是她比你先高潮,她今天就完了。”
我察觉到不对劲。这不是在玩,她是真的动气了。我瘫在地上站不起来,她便用那只没戴手套的左手,一把揪住我的乳头,硬生生把我往上提。我发出一声惨叫,却也感到身下一阵湿热。
因为害怕被撕裂而强打精神站起来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正大口喘着气,以为她会继续折磨那个可怜的地方,两根手指却弹进了我的阴道,开始用力地挖抠。
之前积累了巨大的、无处宣泄的快感,在这一刻找到了突破口。
我溃不成军。
她对着电话那头,平静地宣布:“她输了。明天你来接她的时候,我教你几个能用在她身上的手法。”
电话被挂断,一只拳头紧随其后落在了我的肚子上。她把我推进卫生间,让我靠墙站着。
“现在,给你长个教训。”
她不再关心其他地方,只用那只戴着黑丝手套的手,死死地盯着那一处,反复地、不知疲倦地,也不管我其他嗷嗷待哺躯体,变着花的摩擦。后来甚至换了手法,时而用两指夹住那颗早已红肿不堪的珠子向外拉扯,时而又用覆着丝的手掌拍一下。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肿了起来,连缩回那层薄皮的庇护都做不到了。
第一次的堤坝溃决之后,浪潮便再也不受控制,一波接着一波,要将我整个人都拍碎在岸上。卫生间里没有钟表,我不知道这场惩罚何时才会结束。嘴里的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只会大喊着姐姐,大喊着对不起,中间夹杂着失声的、不成调的尖叫。我不知道自己高潮了多少次,因为到了最后,整个下身连带着小腹都在剧烈地痉挛,我也早已彻底失禁。她的手上,我们的腿上,卫生间的地砖上,流淌着一片分不清是汗、是爱液、是尿、还是涎水的液体。
她终于停下了。痛感退去后,留下的是一片麻木的、过载烧毁后的寂静。我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双腿无力地岔开。她只是朝那里轻轻吹一口气,就能引得我一声无助的轻呼。
她甩了甩右手的手腕,站起身,说她累了,不想再弄我了。她问我知道错了吗?我当然知道。
她一只脚踩在我的胸口上,脚趾轻轻玩弄着我的乳头,问我,那么,该怎么办呢?
“请……哈……姐姐……责罚……”
“下次来,踢你的骚逼,好不好啊?”
我再也撑不住了,胡乱地点着头道着谢,便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多。我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叫嚣着酸痛,尤其是双腿之间,连并拢都成了一种酷刑。她坐在床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温柔的向我揭露了最后的一层诡计——之前的生气都是装的。“不过你还是要专心哦,我可爱的前女友”,她随后又补充道。
她说,她能感觉到我心里那道墙,那个拧巴的结。如果不把我逼到绝境,不让我真的感到害怕,那道墙就永远不会倒塌。她需要我把脑子里那些关于“应不应该”的杂音都丢掉,然后才能完完全全地,只属于这里,只感受当下。
她的话,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原来我所有的挣扎与分神,她都看在眼里。她不是在惩罚我的不专心,而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帮我打碎那个困住我的、名为“自我”的牢笼。我还是连腿都闭不上,但我知道,在听完她这番话的这一刻,我终于可以放心地哭了。
一夜无言
那个被内化了的观念,像一根绳索,在我的脑子里打了个死结。男朋友允许了我,可我是否应当允许我自己呢?它让我无法全然地投入,身体向着她,思绪却总想往后退。这种割裂,让最初的体验蒙上了一层灰。
今天没有预设的道具。到了她家,迎接我的是三瓶矿泉水,她看着我一瓶瓶地灌下去,像是在饮驴。然后是洗澡,热水冲刷着身体,却冲不散心里的那个结。
洗完澡,我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她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屋子中央,说,站稳了。她的意图很明显,只要我的腿稍一发软,我的整个重心,便只能交付于她即将探向我身下的那只手。
她的右手上,套了一只黑色的丝质手套。那只手探了下来,带着布料的凉意,轻轻一撑,食指与无名指便拨开了最外层的软肉,中指的指腹则不偏不倚地压上了那颗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小小的突起。那一瞬间,像是有人在我神经的最深处,拨动了一根从未被触碰过的弦,于是我带着尖叫跳了起来。
她笑了一声,带着发现新大陆的惊喜,把那根覆着黑丝的中指重新抵在那里,说:“诶呀,原来你这里还没被开发过呀,那你今天可惨咯。”
原定的计划是带我体验阴蒂责和我当猫猫进行“口舌侍奉”的,可惜被打乱了。她让我跪在地板上,挺直后背。想到男朋友之前在我手下被责弄的时候宛如一条离了水的鱼般蹦跶,我便头皮发麻,意识到了某些惊恐的事将要发生。
“给我舔”,她说。覆着黑丝手套的右手伸到我的嘴前,却又保持着一丝距离。“你的口水,就是你唯一的润滑。不好好舔,待会儿伤到了,我可不管。”她看着我眼神里的哀求,又补充道,“不不不,我不会摘手丝的。你明天就在我这里歇着吧,别想走路了。”
我认命地伸出舌头,在那光滑却又带着织物质感的丝绸上舔舐着。舌尖的触感是粗粝的,我的思绪也开始收紧,飞向跟男友的对话。
舌头上的触感消失,脸颊上却传来一阵清脆的痛感,一记耳光把我从纷乱的思绪中扇了回来。她说:“怎么,还有心事?那就只能这样一直责到你翻着白眼,只会喘气,说不出话为止了哦。”
那一刻,那个拧巴的结,似乎被这一巴掌打松了。一种破罐破摔的冲动涌了上来。我重新站起来,踮着脚,主动将身下最脆弱的地方,送进了她那只比一开始抬得更高的、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里。
那只覆着丝绸的手,像一块干燥的、不断升温的浮石,在我最柔软的地方研磨。更何况,我的膀胱里还装着那三瓶水的重量。我很快就泣不成声,哭喊着求着姐姐慢点,求着姐姐允许我先去排泄。但所有的哀求都被她刻意地忽略了。我当然也不敢真的失禁,怕这会成为她更有力的借口。
在这样残忍的折磨里,高潮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尿意却是永不停歇的潮水。疾痛惨怛中,我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飘向了远方。
这次的巴掌,却是从下身传来的。她显然意识到了我的再次分神,也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分神的源头。
她将我推倒在地,像丢开一件无用的东西。电话的拨号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像一种审判的预告。我听到她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语调说:“你女朋友可真厉害,我正弄着她,她还能想到你。你现在就听着她的声音开始打飞机。要是她比你先高潮,她今天就完了。”
我察觉到不对劲。这不是在玩,她是真的动气了。我瘫在地上站不起来,她便用那只没戴手套的左手,一把揪住我的乳头,硬生生把我往上提。我发出一声惨叫,却也感到身下一阵湿热。
因为害怕被撕裂而强打精神站起来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正大口喘着气,以为她会继续折磨那个可怜的地方,两根手指却弹进了我的阴道,开始用力地挖抠。
之前积累了巨大的、无处宣泄的快感,在这一刻找到了突破口。
我溃不成军。
她对着电话那头,平静地宣布:“她输了。明天你来接她的时候,我教你几个能用在她身上的手法。”
电话被挂断,一只拳头紧随其后落在了我的肚子上。她把我推进卫生间,让我靠墙站着。
“现在,给你长个教训。”
她不再关心其他地方,只用那只戴着黑丝手套的手,死死地盯着那一处,反复地、不知疲倦地,也不管我其他嗷嗷待哺躯体,变着花的摩擦。后来甚至换了手法,时而用两指夹住那颗早已红肿不堪的珠子向外拉扯,时而又用覆着丝的手掌拍一下。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肿了起来,连缩回那层薄皮的庇护都做不到了。
第一次的堤坝溃决之后,浪潮便再也不受控制,一波接着一波,要将我整个人都拍碎在岸上。卫生间里没有钟表,我不知道这场惩罚何时才会结束。嘴里的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只会大喊着姐姐,大喊着对不起,中间夹杂着失声的、不成调的尖叫。我不知道自己高潮了多少次,因为到了最后,整个下身连带着小腹都在剧烈地痉挛,我也早已彻底失禁。她的手上,我们的腿上,卫生间的地砖上,流淌着一片分不清是汗、是爱液、是尿、还是涎水的液体。
她终于停下了。痛感退去后,留下的是一片麻木的、过载烧毁后的寂静。我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双腿无力地岔开。她只是朝那里轻轻吹一口气,就能引得我一声无助的轻呼。
她甩了甩右手的手腕,站起身,说她累了,不想再弄我了。她问我知道错了吗?我当然知道。
她一只脚踩在我的胸口上,脚趾轻轻玩弄着我的乳头,问我,那么,该怎么办呢?
“请……哈……姐姐……责罚……”
“下次来,踢你的骚逼,好不好啊?”
我再也撑不住了,胡乱地点着头道着谢,便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多。我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叫嚣着酸痛,尤其是双腿之间,连并拢都成了一种酷刑。她坐在床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温柔的向我揭露了最后的一层诡计——之前的生气都是装的。“不过你还是要专心哦,我可爱的前女友”,她随后又补充道。
她说,她能感觉到我心里那道墙,那个拧巴的结。如果不把我逼到绝境,不让我真的感到害怕,那道墙就永远不会倒塌。她需要我把脑子里那些关于“应不应该”的杂音都丢掉,然后才能完完全全地,只属于这里,只感受当下。
她的话,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原来我所有的挣扎与分神,她都看在眼里。她不是在惩罚我的不专心,而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帮我打碎那个困住我的、名为“自我”的牢笼。我还是连腿都闭不上,但我知道,在听完她这番话的这一刻,我终于可以放心地哭了。
一夜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