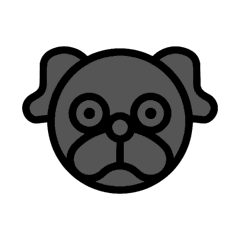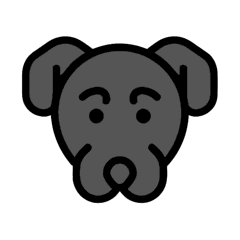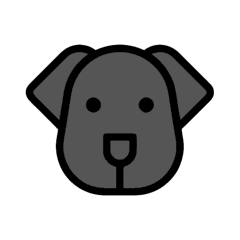羔羊在镜前凝视的绝不是悲伤
添加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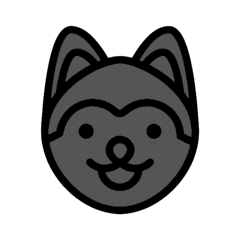
13
13303381250
羔羊在镜前凝视的绝不是悲伤
警告:禁止带入自己
双旦快乐!
羔羊在镜前凝视的绝不是悲伤
文/人仿
零 吗
萨特在《禁闭》中写道,他人即地狱。
他认为,人总会尽力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将他人物化成被审视的客体。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永无休止地在互相欺骗、迫害、争斗,而人却又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直与他人相处。这种凝视所有人,同时又受到所有人的凝视,与世界为敌的状态,如同身处地狱。
虽然我时常认为他的观点有些过激,觉得人类不该只是如此简单极端的生物。不过有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我就是自己的地狱。
一 绝不是悲伤
“看着我的鞋子。”她说。
我的心神被拽回现实,视线逐渐聚焦,她的高跟鞋在视野中变得清晰起来。
我总共见过这双鞋子四次,除了第一次被她踩在脸上试鞋时它是全新的,后面每个周末再见到它,它都会比上一周更旧一点。现在,它尖头上的黑色漆皮依然闪亮,但是脚趾处被折出了深深的褶皱,侧面也有几道不规则的划痕,至于小羊皮的鞋底,则早被各种粗糙的路面磨得面目全非了。
“亲它。”她又说。
我低下头,把嘴唇贴到鞋面上,仔细感受着上面她留下的痕迹。漆皮的表面冰凉、光滑,她白皙的脚和油黑的皮革在灯光下勾出诱人的弧线,一丝酸臭的热气从那令人遐想缝隙中慢慢飘出,被我贪婪地吸进鼻腔。我很想贴到鞋窝的边缘大口呼吸,或是用嘴唇贴到她温暖滑嫩的脚背上,但我不能更进一步了,没有她的命令,我不能碰她的脚。
随后,她勾了勾脚趾,脚后跟从皮革的包裹中滑脱出来。
“脱了。”她踢踢我的鼻尖,带来一阵旖旎的风。
我会意地用嘴唇包住牙齿,咬住她的鞋跟,她虽然不在意鞋子被损坏成什么样子,但如果这损害的源头是我,那她就会大发雷霆。所以我只能用这种别扭的方式,咬着自己的嘴唇,费力地将鞋子分别从她的脚上脱下。
她扭动着脚趾,舒缓踩了一天高跟的疲劳。我默默将这美丽的景象刻进我的大脑深处。
“好了,”她把脚从我面前抽走,“把它扔掉吧。”
我心里忽然感到一阵不幸,我不知道我是为这样一双美丽的鞋子没有得到它应得的爱惜而不幸,还是为亲眼见证了花掉自己半年工资购买的奢侈品仅过了三周就在她的脚下被污损成扔进衣物捐献箱都会被工作人员嫌弃地捡出去的样子的我自己而不幸。
想来是后者居多吧。
“对了,那件事,给你最后一个晚上考虑清楚,明天我起来了要知道你的回答,明白了吗?”她站起身,踢踢我的大腿。
“我明白了。”
那件事,无论如何思考,理智和情感都不会统一的吧。之前那么长时间我都没能找到答案,我十分怀疑现在只凭一晚,我能否做出符合本心的决定。
“好了,把鞋扔了,睡觉吧。”她把我的头按到地上,踩着我的头站起来,离开了沙发。
我叼起鞋子,鼻尖探入鞋窝,慢吞吞地往客厅的垃圾桶爬去,享受着她的气味。她没有理会我的小心思,套上拖鞋,关掉客厅的灯,啪嗒啪嗒地往卧室去了。
那里曾是我的卧室,但现在屋子里存在的,是她的衣服、她的用具、她的味道。
在苍白的月光中,我听到她反锁卧室门的声音。
还好这是我家,不像她那个小破出租屋,至少在我家里我还有沙发可以睡。
我躺在沙发上,沙发很软。我闭上眼,世界被彻底的黑暗吞没。
其实我知道,她并不喜欢我。
我还知道,我也不是真的喜欢她。
但是,人类是一种会任由自己被欲望牵着走的生物,而我毫无疑问地,正是体现这种可悲特性的绝佳代表。
或许这不能算可悲,因为此刻我并不悲伤。
是的,这种若隐若现、无法捉摸的情愫,绝不是悲伤。
二 凝视的
“所以,你就是人仿?”
第一次见面时,她翘着腿,上身向前探着,霸占了整个双人小桌。
奶茶店的空调很足,完全没有夏天炎热的感觉,即使热烈的阳光正透过玻璃窗打在我的后背上。
我窘迫地低着头,试图把脸转到她看不到的角度。
她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
“也没有很奇怪的地方啊~”她用另一只手撑着脸颊,像是在研究什么新奇的物件一般。
我的嘴唇蠕动着,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大脑却一片空白。
“所以,为什么会想到去当直播奴呢?”她嘟起嘴,啜饮一口旁边的冰饮,唇釉在吸管上留下一抹亮晶晶的淡粉色。
“我……就是一时兴起……”
“那就是下半身管住了上半身咯?”她的嘴角勾了起来。
我讨厌这样嘲讽的语气,但是她说的是事实。
我皱起眉头表示抗议,没有回她的话。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也没有说话,只是一口一口吸着橘子苏打,盯着我看。
过了一会,我逐渐害怕起这诡异的沉默。
“我以为你是个很喜欢说话的人。”在她的杯子里只剩冰块的那一刻,我开口了。
“我确实喜欢说话,但我更喜欢让别人自以为是的猜测落空呢。”
“抱歉,我没有想要审视你的意思,我只是习惯性地就……”
“你还挺有礼貌的嘛,我开始喜欢你了~”
“谢谢。”
“不用这么紧张啦,凝视是不可避免的,他人即地狱嘛~”
“萨特。”我点点头。
“懂得还挺多嘛,”她笑眯眯地拍拍我的头,随即板起脸来,“那我就直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地狱了。”
“什么?”
“你听清我说的话了,我不会重复的。”
我一时不知道该紧张还是该莫名其妙。
“我是说,你往我家的门缝里塞信,威胁我不到这来就把我做直播奴的视频发给我的亲朋好友,到底是为了要什么?钱吗?”
“我刚刚还觉得你挺聪明来着,”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抽出吸管点在我的鼻尖上,有点凉“你觉得我像是那种看重钱财的人吗?”
“不像。”我想摇头,又忍住了,就这样任由她点着我。
“嘟嘟——错误答案哦。”她按着吸管,好像要把它戳进我的鼻子里,“正确答案是‘不知道’哦毕竟你没有权力审视我呢”
她旋转起吸管,我感到有点疼。
“对不起。”我说。
或许是出于对我们同读萨特这点感到亲近,或许是出于某种逆反心理,虽然我嘴上说出了道歉的话,但心里反而不愿意再避开看她,而是充满了对于窥探她的渴望。
我斜过眼,试图用余光悄悄打量她。
她哼了一声。
“要看就好好看。”她用指尖轻轻扇在我的脸上,把我的脸转成正朝着她。
然后她交换了翘起来的双腿,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双臂张开,一副任我观览的样子。
我的目光不禁被她的美丽所吸引:清爽利落的黑色短发,发梢被气流扰动,微微摇曳着。她水润的嘴唇随着咀嚼口香糖的动作不断扭动,嘴唇中间有一道晶莹的水线,我似乎能透过那几不可见的缝隙,看到里面她粉嫩的舌头淫靡地搅动着唾液和那团胶质,在口腔中翻滚拉丝,被牙齿挤压变形。
她穿着最近很流行的JK服,做工很好,墨绿色的领子上用金线绣着校徽之类的纹饰,看起来更像是什么作品的cos服。轻薄的白色布料遮掩不住她姣好的胸部,两颗饱满的半球紧紧顶起,将周围的布料扯出褶皱。我顺着玩下看,缝着金边的墨绿色短裙下面,白皙的纤腿闯入我的视线,裙子的长度有些危险,因为她换腿夹住裙角的原因,百褶裙正忠实地勾勒着她双腿间的三角地带,肆无忌惮地展示着青春的魅力。
我咽了下口水,她明显是在故意诱惑我。
“你……为什么?”我板着脸,强装着正人君子的样子,眼球却不受控制地在她身上东瞟西瞟。
“我不喜欢被凝视,但如果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凝视,我也能享受旁人的赞美。”
她把“赞美”两个字咬得很重,我很轻易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你……很漂亮。”我一字一顿地说。
“谢谢~”
“你应该不在乎吧……我的夸奖啥的。”
“当然~”
“那啥……”我打算重新回到正题,她到底是想要什么?
“等下,”她打断我,重新把手肘支到桌子上,“你想吃吗?”
她吐出舌头,被嚼得发白的口香糖挂着几丝晶莹的唾液,摊在她粉嫩的舌面上。
我疑惑地摇摇头。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看别人被迫做讨厌的事情的样子~”她笑眯眯地把口香糖吐到桌面上,冲它努努嘴,“吃了。”
我伸出手。
“用嘴。”她的表情看起来不容置疑。
我深吸了一口气,环顾四周,旁边的两对情侣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店员则在后厨忙碌。于是我俯下身,以蹦极的心态快速把脸贴近桌子。那位置离她很近,我俯下身子后,脸颊几乎贴到了她的胳膊。我用舌头卷起桌面上的口香糖,还附带了一点她的唾液。刚想起身,却被她用另一只手搭在了头上。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能感到她的鼻息吹在我的头发上,她的脸此刻离我只有几厘米。我的心脏砰砰跳着,大脑一片混乱。
她到底想干什么?我想不明白。但我……不想起身……
“起来吧。”她拍拍我的后脑勺。
我直起身,嘴里嚼着那块口香糖,一点味道都没有,像块橡皮。
“我是让你吃了,不是让你尝味道。”她的柳叶眉皱在一起。
“这个……不能吃吧?会黏在胃里啥的……”
“咽了。”她没有跟着我的思路走,只是平淡地命令着。
仿佛我生来就该如此做。
我咽了下去。她没有看,她在坤包里翻着什么。
“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写在这上面。”她翻出来一张纸和一支笔。
“你呢?你叫什么?”我一边在纸上写,一边随口问她。
“我想让你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这倒是提醒我了,我还是被她要挟的状态。
“把账结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找你的。”她把纸笔收好,起身离开位置。
“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看着她的背影推开大门,急忙问。
“毁灭你。”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丢过来一句话,消失在了门外的人群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眼神:淡漠、锐利,还有那一丝潜藏在极深处的、似要把我吞噬的、近乎疯狂的欲念。
三 在镜前
她要我每天下班之后都来她家处理家务,今天也是如此。我来的时候,她像之前一样并不在家,而她享受北京的夜生活的时候,我则独自为她打扫屋子,清洗衣物和准备夜宵。不知为何,她似乎并不担心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许是她在房间里安装了我从没找到过的隐蔽摄像头,或许她只是单纯地吃定了我不会违抗她。
事实上,我的确不会违抗她。正如她规定我在做完日常的事情后,要一直跪在门口等她回来,我也从未偷偷休息过。即使她每天都回来得很晚,我要从十一点左右开始跪上几个小时,第二天还要继续上班,我也没有生出过反抗的想法。
真奇怪。
在她家的门口,鞋架侧面,支着一面穿搭镜,我总会忍不住歪头看它,从中观赏自己强撑着疲惫的身躯,卑贱地跪在门口,被她的各种鞋子包围的样子。每当我这样看时,我都会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仿佛正在受难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跟我长的一模一样的别的人似的。
真奇怪。
然而无论我的内心是痛苦还是愉悦,我每天依旧会在下班后坐地铁来到她的小区,用她给的备用钥匙打开门锁,脱掉秋天穿着正合适却阻碍干活的薄夹克,把它和背包放到鞋架旁边,用她的鞋子压好。
随后便是如往常一样例行工作,如往常一样戴上项圈,如往常一样跪在门口,如往常一样呼吸着地毯上的尘土味道,如往常一样孤独地等待她回来……
时间是凌晨一点,我跪着等了两个小时。
她回来了,没有问我跪了多久,她从来不问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家里都发生了什么,只会随手拿来狗链,牵着我走到卧室。然后如往常一样,她坐在她的床上,我跪在她的面前。
“你看,我昨天晚上发现了这个。”她扔下一个贴纸,破破烂烂的,嵌着不少黑灰色的污迹,“从你前几天给我买的这双Jimmy Choo的鞋底上揭下来的,踩着逛了好几天才发现,所以有点脏了。”
我捡起来看,上面印着“消耗品”三个字,黑体。虽然确实听说过“奢侈品鞋其实是走几次红毯之后就会扔掉的消耗品”之类的说法,但是没想到真的会做出实体的标识来。
“挺有意思。”我从麻木的思维中挤出一句无聊的回复。
“有意思吧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把你的工牌拿出来。”
我从兜里掏出我的工牌,说是工牌,其实就是两张印着部门姓名和照片的纸片,夹着张白色的射频卡,一起塞在带吊绳的卡套里而已。她抄过去,解开绳子,把卡套和射频卡随手扔掉,然后弯腰把两张纸片放到地上。
“给你个选择的机会,你想把它贴到哪一面?”
“啊?”我疑惑地抬头看她。
“这个贴纸多符合你的身份啊。”她的嘴唇拉成一条玩味的弧线。
“我……”我刚想要说话,嘴巴就被她用鞋底踩住。
刚好,我也不知道我要说点什么。
她低头俯视我,脸上浮起微微的红晕,眼神里满是恶劣的笑意。
“消——耗——品——”挑动神经的词语从她的唇间吐出。
我勃起了。
“你看,你的小弟弟可是十分同意呢~”她用高跟鞋的细跟戳戳我的下面。
我盯着手里的贴纸,恍惚间竟真的在它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或许它真的是一面抽象的镜子,映照出了我应有的悲惨命运?
我动摇了。
“愣什么神呢,快选。”她用脚踢踢我的脑袋。
我看了看两张纸片,都是打印出来的,没有任何区别。
“那就这……”我随便拈起一张,却被她踩住了。
“不许选这张~”
那让我选的意义何在啊……
“我选这张。”我拾起另一张,把贴纸贴在唯一空白的地方。
我的照片上方顶着这个贴纸,好像游戏里角色头上顶着的称号。如果人们真的能自选一个称号顶在头上,应该没有人会选这个吧,谁会标榜自己是消耗品呢?
忽然一阵亮光闪过,她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画面里占据主体的是她可爱的脸和剪刀手,角落里则是拿着工牌出神的我。她给我的脸和工牌打了马赛克,却又在旁边恶趣味地写了“消耗品”三个字,画了个箭头指向我。
我忽然感到,成为她的消耗品,被她消耗殆尽,或许……也不错?
“哇,刚po上推就有人点赞了呢!”她摆弄着手机。
我低下头,企图在地上找到一个地缝钻进去。
“好啦,把你的工牌装好吧,你明天还要用吧?”
她抬起踩着另一张纸片的脚,纸片黏在了她的鞋底上,她抖了抖脚,纸片才重新飘回地上。我看到一个污泥颜色的鞋印,清晰地印在了上面。她似乎嫌不够明显,又用鞋跟对准纸片上我的脸踩了下去,像钢印一样让那里凹出了一个灰黑的正方形。
我默默拿起纸片,从旁边捡回卡套和射频卡,把它们重新组合成我的工牌。
“我说,这两面你更怕哪一面被看到呢?”她饶有兴趣地问。
这个问题很难,被踩上一看就知道是高跟鞋鞋印的一面,和贴着破烂消耗品贴纸的一面,无论哪个被看到都会被暗中指指点点吧。
“有鞋印的一面吧。”纠结一番后,我做出了回答。
“你对你是消耗品这件事的接受度意外地高的欸~”
我愣了一下,我没想过展示出自己是消耗品会比随便就能编个理由糊弄过去的工牌被高跟鞋踩过更能令我接受。
“噗哈哈哈!”她大笑起来。
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好了,把你的工牌收起来吧。我困了,要睡觉了。”她踩踩我的头,甩掉鞋子,下了逐客令。
我叼着那双新买的Jimmy Choo爬出她的卧室,穿过逼仄的客厅,把鞋摆到鞋架上,然后再回来,关掉客厅的灯。时间太晚了,如果回家的话又要搞到三四点钟,我只能像大部分时间一样,蜷缩在她家客厅的地板上,勉强度过难熬的夜晚。
黑暗中,我看到那面穿搭镜反射着不知哪来的光。我爬到镜子前,借着微光审视自己。镜中的人状态十分糟糕,像是一团用了许久的抹布。
我失神落魄地爬回客厅,阳台的窗户里也显出我的倒影;我看像厨房,也隐隐约约在狭长的窗子中看见了自己;卫生间的玻璃门上似乎也有我的影子——我被自己的镜像包围了。
一股夹杂着愉悦的恐惧环绕着我,我听到他们在对我说话。
他们问:你在凝视的是什么?
四 羔羊
我被光线晃着,从沙发上醒来。
我本以为这会是无眠的一夜,看来是我低估了自己的疲惫。
她站在我的面前,俯视着我。
我从沙发上起来,跪在她面前,把沙发让给她。
“考虑得怎么样了?”她问。
“还不清楚。”
她抱起胳膊,把左腿翘到右腿上,拖鞋吊在趾尖一晃一晃的。
“那就现在决定吧。”
我看向阳台,外面的天还很黑,只能依稀看出街上的树被冬风摧残后剩下的光秃秃的树枝。
“别看了,现在才四点,我是起来上厕所顺便来问问你,”她打了个哈欠,“你快点决定,完了我还要回去睡觉呢。”
看来她已经是默认我同意了。但是我呢?我真的有勇气贡出我的一切吗?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外面天色昏暗,客厅的灯光将室内的影像忠实地投射到窗户上,再由窗户反射进我的眼睛。拜此所赐,我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背佝偻着,身形消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她给予我的苦难竟将我折磨到此等地步,我的心脏忽然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兴奋攫住。
“我……我同意。”借着这股冲动,我草率地做出了重要的决定。
“你同意什么?”她的声音中掺入了一丝戏弄。
“我同意向你……贡出我的一切。”
我伏在地上,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干了一样。
她嗤笑一声,回到卧室,拿出来一沓文书。上面的字很多,我一个都没看,只是一股脑地在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她把那堆纸扔到一边,盯着我看。
我感到一阵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该把手放到哪里,也不知道该把膝盖跪在何处。身下的地面已不再是我的家了,面前我几分钟前还躺在上面的沙发也已不再是我的沙发了。
我变成了这间屋子里的客人。
不,我并不是现在才变成客人的,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注定是这间屋子里的客人了。
“你打算在我的房子里待多久?”她玩味地看着我。
“我现在就离开。”我转身往门口爬去。
“主人允许你走了?”她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充满希望地回头。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依然是你的主人而已,滚吧。”
我掉头,慢慢爬到门口。她并没有如我期望地回心转意。
我站起身,打开门,楼道里的空气异常的冷。
“喂,那个谁。”
到头来,连我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吗……
“如果你要去死的话,记得选个不会被人发现尸体的地方哦,不要给我惹上麻烦。”她的唇间吐出冰冷的话语。
冰冷到我想测测她的体温,看看她是否还是一个人类。
我想说话,喉咙却梗住不能动弹,只能冲她点点头。
我为什么要点头呢?我一边想着这无意义的问题,一边走到门外,冰冷的空气让我打了个寒颤。
“还有,”她坐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叫住我,“主人想要你身上的衣服。”
事实上,并没有测体温的必要,因为很明显地,她并不是一个人类,她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魔鬼。
我一口气脱下身上的衣服,毕竟是在有暖气的家里穿的,算上内裤也才薄薄的三件。
“乖~”她的声音中忽然带了些温柔,让人摸不着头脑,“戴上吧,主人赏你的。”
她扔过来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个电击止吠器,兽用的。
裸体、兽用品……很好,这样我作为小丑的装束就齐了。
我关上门,转身下楼。刚走出第一步,就被难以承受的寒冷狠狠打了一拳。
我几乎是立刻想要敲门,哀求她让我回去,但也是几乎立刻我就得出答案,她不会让我回去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下楼,希望运动能让身体暖和一些,虽然脚底被冰冷的地面冻得发疼,但是肌肉的地方似乎隐隐生出了一些热量。
冲出单元门,门口有一滩饮料结成的冰,我跳了过去。比楼道里还要强劲百倍的冷空气从四面八方袭击过来,我的骨头似乎都附上了一层霜。
门口有一个叫“人仿商店”的奇怪贩卖机,我靠在它的散热口,像在沙漠中的鱼扑在一片带露水的叶子上。
无论如何思索,目的地似乎都是确定的。
通惠河。
我打定主意,鼓动颤抖的肌肉,哆哆嗦嗦地朝着河边跑。
我家……曾经是我家的地方离河边很近,刚搬来的时候我经常被河边晨练的老头老太太吵醒,所以后来我学会了戴耳塞。
不知道她学会戴耳塞了没。
……妈的,为什么脑子里还是她。
我甩甩脑袋,专注于肌肉发力,我感到它们越来越不听控制了。好在河边也没两步了,穿过马路,翻越栏杆,我就能坠入目的地了。
“啊!”一声意料之外的尖叫声从咫尺传来。
我的心猛地一突,我被发现了!
我艰难地转过头,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运动服,厚厚的围巾和小熊耳罩。看起来是来晨跑的。
“你……你是要……跳河?”
“对。”我的牙齿打架,只能用喉咙把字挤出来。
“你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吗?你冷不冷啊?”她解开围巾,露出戴着有些幼稚的小熊口罩的脸。
多么善良的女孩子啊,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恶魔的话,我或许也会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和她结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吧。
可我已经丧失了这个资格。
我后退两步,一切都为时已晚,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刻了。我用手撑住栏杆,胳膊用不上力,于是我靠近栏杆,把上半身往外探,打算栽出去。
胳膊上传来一阵温暖,她拽着我,力量虽弱,但很坚定。
谢谢你,陌生的天使,不过很遗憾,你无法拯救我。
我挣脱她,向前探身。
一股酥麻的感觉从脖子上散开,随后迅速爆发,我的肌肉瞬间抖得不成样子。没了支撑,我跌坐在地上,浑身痉挛。
我看到那个天使拿着遥控器。
是电击止吠器!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的遥控器?
“看来我的伪音练得还挺好的。”她摘下口罩。
陌生的天使卸下了伪装,底下是熟悉的魔鬼。
“我时常在想,你就像一个替罪的羔羊,所替的罪却是毁灭你的人犯下的,毁灭你的罪过。”她自顾自地说着,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她自己说,“你受到了折磨,还要承担因这折磨而产生的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吗?”
她微笑着,脸上泛起迷离的红晕:“你就是神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我努力张大嘴巴,但是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音节。
“你想问什么?”她松开遥控器,把外套和围巾扔在我的身上。
带着她的体温,很温暖。
“为什么?”我问出脑子里仅存的一句话。
为什么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想问为什么。
“我说过了,我是你的地狱,我要一点点地、彻底的毁灭你,你现在只是失去了金钱,但你还有社会关系、肉体、情感、智力等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呢。”她轻轻笑着,“你这可怜的羔羊,你的世界里以后只会有我一个人,你的地狱就是你的神明。”
我不明白,但我似乎又明白。
脸上烫烫的,我流泪了,但我并不悲伤。
闪光灯闪过,她用手机拍了张自拍。
“你想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吗?”
“想。”
她把手机屏幕朝向我。
屏幕的角落里,是一个滑稽可笑,冻得发青的可怜虫。它蜷缩在她的脚边,本能地寻找着温暖,即使这温暖是地狱中的火焰。
我看着这可怜虫,我看着这羔羊,我看着它,我看着他们,我看着我。
一阵热潮涌来,我射精了。
双旦快乐!
羔羊在镜前凝视的绝不是悲伤
文/人仿
零 吗
萨特在《禁闭》中写道,他人即地狱。
他认为,人总会尽力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将他人物化成被审视的客体。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永无休止地在互相欺骗、迫害、争斗,而人却又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直与他人相处。这种凝视所有人,同时又受到所有人的凝视,与世界为敌的状态,如同身处地狱。
虽然我时常认为他的观点有些过激,觉得人类不该只是如此简单极端的生物。不过有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我就是自己的地狱。
一 绝不是悲伤
“看着我的鞋子。”她说。
我的心神被拽回现实,视线逐渐聚焦,她的高跟鞋在视野中变得清晰起来。
我总共见过这双鞋子四次,除了第一次被她踩在脸上试鞋时它是全新的,后面每个周末再见到它,它都会比上一周更旧一点。现在,它尖头上的黑色漆皮依然闪亮,但是脚趾处被折出了深深的褶皱,侧面也有几道不规则的划痕,至于小羊皮的鞋底,则早被各种粗糙的路面磨得面目全非了。
“亲它。”她又说。
我低下头,把嘴唇贴到鞋面上,仔细感受着上面她留下的痕迹。漆皮的表面冰凉、光滑,她白皙的脚和油黑的皮革在灯光下勾出诱人的弧线,一丝酸臭的热气从那令人遐想缝隙中慢慢飘出,被我贪婪地吸进鼻腔。我很想贴到鞋窝的边缘大口呼吸,或是用嘴唇贴到她温暖滑嫩的脚背上,但我不能更进一步了,没有她的命令,我不能碰她的脚。
随后,她勾了勾脚趾,脚后跟从皮革的包裹中滑脱出来。
“脱了。”她踢踢我的鼻尖,带来一阵旖旎的风。
我会意地用嘴唇包住牙齿,咬住她的鞋跟,她虽然不在意鞋子被损坏成什么样子,但如果这损害的源头是我,那她就会大发雷霆。所以我只能用这种别扭的方式,咬着自己的嘴唇,费力地将鞋子分别从她的脚上脱下。
她扭动着脚趾,舒缓踩了一天高跟的疲劳。我默默将这美丽的景象刻进我的大脑深处。
“好了,”她把脚从我面前抽走,“把它扔掉吧。”
我心里忽然感到一阵不幸,我不知道我是为这样一双美丽的鞋子没有得到它应得的爱惜而不幸,还是为亲眼见证了花掉自己半年工资购买的奢侈品仅过了三周就在她的脚下被污损成扔进衣物捐献箱都会被工作人员嫌弃地捡出去的样子的我自己而不幸。
想来是后者居多吧。
“对了,那件事,给你最后一个晚上考虑清楚,明天我起来了要知道你的回答,明白了吗?”她站起身,踢踢我的大腿。
“我明白了。”
那件事,无论如何思考,理智和情感都不会统一的吧。之前那么长时间我都没能找到答案,我十分怀疑现在只凭一晚,我能否做出符合本心的决定。
“好了,把鞋扔了,睡觉吧。”她把我的头按到地上,踩着我的头站起来,离开了沙发。
我叼起鞋子,鼻尖探入鞋窝,慢吞吞地往客厅的垃圾桶爬去,享受着她的气味。她没有理会我的小心思,套上拖鞋,关掉客厅的灯,啪嗒啪嗒地往卧室去了。
那里曾是我的卧室,但现在屋子里存在的,是她的衣服、她的用具、她的味道。
在苍白的月光中,我听到她反锁卧室门的声音。
还好这是我家,不像她那个小破出租屋,至少在我家里我还有沙发可以睡。
我躺在沙发上,沙发很软。我闭上眼,世界被彻底的黑暗吞没。
其实我知道,她并不喜欢我。
我还知道,我也不是真的喜欢她。
但是,人类是一种会任由自己被欲望牵着走的生物,而我毫无疑问地,正是体现这种可悲特性的绝佳代表。
或许这不能算可悲,因为此刻我并不悲伤。
是的,这种若隐若现、无法捉摸的情愫,绝不是悲伤。
二 凝视的
“所以,你就是人仿?”
第一次见面时,她翘着腿,上身向前探着,霸占了整个双人小桌。
奶茶店的空调很足,完全没有夏天炎热的感觉,即使热烈的阳光正透过玻璃窗打在我的后背上。
我窘迫地低着头,试图把脸转到她看不到的角度。
她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
“也没有很奇怪的地方啊~”她用另一只手撑着脸颊,像是在研究什么新奇的物件一般。
我的嘴唇蠕动着,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大脑却一片空白。
“所以,为什么会想到去当直播奴呢?”她嘟起嘴,啜饮一口旁边的冰饮,唇釉在吸管上留下一抹亮晶晶的淡粉色。
“我……就是一时兴起……”
“那就是下半身管住了上半身咯?”她的嘴角勾了起来。
我讨厌这样嘲讽的语气,但是她说的是事实。
我皱起眉头表示抗议,没有回她的话。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也没有说话,只是一口一口吸着橘子苏打,盯着我看。
过了一会,我逐渐害怕起这诡异的沉默。
“我以为你是个很喜欢说话的人。”在她的杯子里只剩冰块的那一刻,我开口了。
“我确实喜欢说话,但我更喜欢让别人自以为是的猜测落空呢。”
“抱歉,我没有想要审视你的意思,我只是习惯性地就……”
“你还挺有礼貌的嘛,我开始喜欢你了~”
“谢谢。”
“不用这么紧张啦,凝视是不可避免的,他人即地狱嘛~”
“萨特。”我点点头。
“懂得还挺多嘛,”她笑眯眯地拍拍我的头,随即板起脸来,“那我就直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地狱了。”
“什么?”
“你听清我说的话了,我不会重复的。”
我一时不知道该紧张还是该莫名其妙。
“我是说,你往我家的门缝里塞信,威胁我不到这来就把我做直播奴的视频发给我的亲朋好友,到底是为了要什么?钱吗?”
“我刚刚还觉得你挺聪明来着,”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抽出吸管点在我的鼻尖上,有点凉“你觉得我像是那种看重钱财的人吗?”
“不像。”我想摇头,又忍住了,就这样任由她点着我。
“嘟嘟——错误答案哦。”她按着吸管,好像要把它戳进我的鼻子里,“正确答案是‘不知道’哦毕竟你没有权力审视我呢”
她旋转起吸管,我感到有点疼。
“对不起。”我说。
或许是出于对我们同读萨特这点感到亲近,或许是出于某种逆反心理,虽然我嘴上说出了道歉的话,但心里反而不愿意再避开看她,而是充满了对于窥探她的渴望。
我斜过眼,试图用余光悄悄打量她。
她哼了一声。
“要看就好好看。”她用指尖轻轻扇在我的脸上,把我的脸转成正朝着她。
然后她交换了翘起来的双腿,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双臂张开,一副任我观览的样子。
我的目光不禁被她的美丽所吸引:清爽利落的黑色短发,发梢被气流扰动,微微摇曳着。她水润的嘴唇随着咀嚼口香糖的动作不断扭动,嘴唇中间有一道晶莹的水线,我似乎能透过那几不可见的缝隙,看到里面她粉嫩的舌头淫靡地搅动着唾液和那团胶质,在口腔中翻滚拉丝,被牙齿挤压变形。
她穿着最近很流行的JK服,做工很好,墨绿色的领子上用金线绣着校徽之类的纹饰,看起来更像是什么作品的cos服。轻薄的白色布料遮掩不住她姣好的胸部,两颗饱满的半球紧紧顶起,将周围的布料扯出褶皱。我顺着玩下看,缝着金边的墨绿色短裙下面,白皙的纤腿闯入我的视线,裙子的长度有些危险,因为她换腿夹住裙角的原因,百褶裙正忠实地勾勒着她双腿间的三角地带,肆无忌惮地展示着青春的魅力。
我咽了下口水,她明显是在故意诱惑我。
“你……为什么?”我板着脸,强装着正人君子的样子,眼球却不受控制地在她身上东瞟西瞟。
“我不喜欢被凝视,但如果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凝视,我也能享受旁人的赞美。”
她把“赞美”两个字咬得很重,我很轻易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你……很漂亮。”我一字一顿地说。
“谢谢~”
“你应该不在乎吧……我的夸奖啥的。”
“当然~”
“那啥……”我打算重新回到正题,她到底是想要什么?
“等下,”她打断我,重新把手肘支到桌子上,“你想吃吗?”
她吐出舌头,被嚼得发白的口香糖挂着几丝晶莹的唾液,摊在她粉嫩的舌面上。
我疑惑地摇摇头。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看别人被迫做讨厌的事情的样子~”她笑眯眯地把口香糖吐到桌面上,冲它努努嘴,“吃了。”
我伸出手。
“用嘴。”她的表情看起来不容置疑。
我深吸了一口气,环顾四周,旁边的两对情侣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店员则在后厨忙碌。于是我俯下身,以蹦极的心态快速把脸贴近桌子。那位置离她很近,我俯下身子后,脸颊几乎贴到了她的胳膊。我用舌头卷起桌面上的口香糖,还附带了一点她的唾液。刚想起身,却被她用另一只手搭在了头上。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能感到她的鼻息吹在我的头发上,她的脸此刻离我只有几厘米。我的心脏砰砰跳着,大脑一片混乱。
她到底想干什么?我想不明白。但我……不想起身……
“起来吧。”她拍拍我的后脑勺。
我直起身,嘴里嚼着那块口香糖,一点味道都没有,像块橡皮。
“我是让你吃了,不是让你尝味道。”她的柳叶眉皱在一起。
“这个……不能吃吧?会黏在胃里啥的……”
“咽了。”她没有跟着我的思路走,只是平淡地命令着。
仿佛我生来就该如此做。
我咽了下去。她没有看,她在坤包里翻着什么。
“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写在这上面。”她翻出来一张纸和一支笔。
“你呢?你叫什么?”我一边在纸上写,一边随口问她。
“我想让你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这倒是提醒我了,我还是被她要挟的状态。
“把账结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找你的。”她把纸笔收好,起身离开位置。
“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看着她的背影推开大门,急忙问。
“毁灭你。”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丢过来一句话,消失在了门外的人群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眼神:淡漠、锐利,还有那一丝潜藏在极深处的、似要把我吞噬的、近乎疯狂的欲念。
三 在镜前
她要我每天下班之后都来她家处理家务,今天也是如此。我来的时候,她像之前一样并不在家,而她享受北京的夜生活的时候,我则独自为她打扫屋子,清洗衣物和准备夜宵。不知为何,她似乎并不担心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许是她在房间里安装了我从没找到过的隐蔽摄像头,或许她只是单纯地吃定了我不会违抗她。
事实上,我的确不会违抗她。正如她规定我在做完日常的事情后,要一直跪在门口等她回来,我也从未偷偷休息过。即使她每天都回来得很晚,我要从十一点左右开始跪上几个小时,第二天还要继续上班,我也没有生出过反抗的想法。
真奇怪。
在她家的门口,鞋架侧面,支着一面穿搭镜,我总会忍不住歪头看它,从中观赏自己强撑着疲惫的身躯,卑贱地跪在门口,被她的各种鞋子包围的样子。每当我这样看时,我都会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仿佛正在受难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跟我长的一模一样的别的人似的。
真奇怪。
然而无论我的内心是痛苦还是愉悦,我每天依旧会在下班后坐地铁来到她的小区,用她给的备用钥匙打开门锁,脱掉秋天穿着正合适却阻碍干活的薄夹克,把它和背包放到鞋架旁边,用她的鞋子压好。
随后便是如往常一样例行工作,如往常一样戴上项圈,如往常一样跪在门口,如往常一样呼吸着地毯上的尘土味道,如往常一样孤独地等待她回来……
时间是凌晨一点,我跪着等了两个小时。
她回来了,没有问我跪了多久,她从来不问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家里都发生了什么,只会随手拿来狗链,牵着我走到卧室。然后如往常一样,她坐在她的床上,我跪在她的面前。
“你看,我昨天晚上发现了这个。”她扔下一个贴纸,破破烂烂的,嵌着不少黑灰色的污迹,“从你前几天给我买的这双Jimmy Choo的鞋底上揭下来的,踩着逛了好几天才发现,所以有点脏了。”
我捡起来看,上面印着“消耗品”三个字,黑体。虽然确实听说过“奢侈品鞋其实是走几次红毯之后就会扔掉的消耗品”之类的说法,但是没想到真的会做出实体的标识来。
“挺有意思。”我从麻木的思维中挤出一句无聊的回复。
“有意思吧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把你的工牌拿出来。”
我从兜里掏出我的工牌,说是工牌,其实就是两张印着部门姓名和照片的纸片,夹着张白色的射频卡,一起塞在带吊绳的卡套里而已。她抄过去,解开绳子,把卡套和射频卡随手扔掉,然后弯腰把两张纸片放到地上。
“给你个选择的机会,你想把它贴到哪一面?”
“啊?”我疑惑地抬头看她。
“这个贴纸多符合你的身份啊。”她的嘴唇拉成一条玩味的弧线。
“我……”我刚想要说话,嘴巴就被她用鞋底踩住。
刚好,我也不知道我要说点什么。
她低头俯视我,脸上浮起微微的红晕,眼神里满是恶劣的笑意。
“消——耗——品——”挑动神经的词语从她的唇间吐出。
我勃起了。
“你看,你的小弟弟可是十分同意呢~”她用高跟鞋的细跟戳戳我的下面。
我盯着手里的贴纸,恍惚间竟真的在它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或许它真的是一面抽象的镜子,映照出了我应有的悲惨命运?
我动摇了。
“愣什么神呢,快选。”她用脚踢踢我的脑袋。
我看了看两张纸片,都是打印出来的,没有任何区别。
“那就这……”我随便拈起一张,却被她踩住了。
“不许选这张~”
那让我选的意义何在啊……
“我选这张。”我拾起另一张,把贴纸贴在唯一空白的地方。
我的照片上方顶着这个贴纸,好像游戏里角色头上顶着的称号。如果人们真的能自选一个称号顶在头上,应该没有人会选这个吧,谁会标榜自己是消耗品呢?
忽然一阵亮光闪过,她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画面里占据主体的是她可爱的脸和剪刀手,角落里则是拿着工牌出神的我。她给我的脸和工牌打了马赛克,却又在旁边恶趣味地写了“消耗品”三个字,画了个箭头指向我。
我忽然感到,成为她的消耗品,被她消耗殆尽,或许……也不错?
“哇,刚po上推就有人点赞了呢!”她摆弄着手机。
我低下头,企图在地上找到一个地缝钻进去。
“好啦,把你的工牌装好吧,你明天还要用吧?”
她抬起踩着另一张纸片的脚,纸片黏在了她的鞋底上,她抖了抖脚,纸片才重新飘回地上。我看到一个污泥颜色的鞋印,清晰地印在了上面。她似乎嫌不够明显,又用鞋跟对准纸片上我的脸踩了下去,像钢印一样让那里凹出了一个灰黑的正方形。
我默默拿起纸片,从旁边捡回卡套和射频卡,把它们重新组合成我的工牌。
“我说,这两面你更怕哪一面被看到呢?”她饶有兴趣地问。
这个问题很难,被踩上一看就知道是高跟鞋鞋印的一面,和贴着破烂消耗品贴纸的一面,无论哪个被看到都会被暗中指指点点吧。
“有鞋印的一面吧。”纠结一番后,我做出了回答。
“你对你是消耗品这件事的接受度意外地高的欸~”
我愣了一下,我没想过展示出自己是消耗品会比随便就能编个理由糊弄过去的工牌被高跟鞋踩过更能令我接受。
“噗哈哈哈!”她大笑起来。
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好了,把你的工牌收起来吧。我困了,要睡觉了。”她踩踩我的头,甩掉鞋子,下了逐客令。
我叼着那双新买的Jimmy Choo爬出她的卧室,穿过逼仄的客厅,把鞋摆到鞋架上,然后再回来,关掉客厅的灯。时间太晚了,如果回家的话又要搞到三四点钟,我只能像大部分时间一样,蜷缩在她家客厅的地板上,勉强度过难熬的夜晚。
黑暗中,我看到那面穿搭镜反射着不知哪来的光。我爬到镜子前,借着微光审视自己。镜中的人状态十分糟糕,像是一团用了许久的抹布。
我失神落魄地爬回客厅,阳台的窗户里也显出我的倒影;我看像厨房,也隐隐约约在狭长的窗子中看见了自己;卫生间的玻璃门上似乎也有我的影子——我被自己的镜像包围了。
一股夹杂着愉悦的恐惧环绕着我,我听到他们在对我说话。
他们问:你在凝视的是什么?
四 羔羊
我被光线晃着,从沙发上醒来。
我本以为这会是无眠的一夜,看来是我低估了自己的疲惫。
她站在我的面前,俯视着我。
我从沙发上起来,跪在她面前,把沙发让给她。
“考虑得怎么样了?”她问。
“还不清楚。”
她抱起胳膊,把左腿翘到右腿上,拖鞋吊在趾尖一晃一晃的。
“那就现在决定吧。”
我看向阳台,外面的天还很黑,只能依稀看出街上的树被冬风摧残后剩下的光秃秃的树枝。
“别看了,现在才四点,我是起来上厕所顺便来问问你,”她打了个哈欠,“你快点决定,完了我还要回去睡觉呢。”
看来她已经是默认我同意了。但是我呢?我真的有勇气贡出我的一切吗?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外面天色昏暗,客厅的灯光将室内的影像忠实地投射到窗户上,再由窗户反射进我的眼睛。拜此所赐,我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背佝偻着,身形消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她给予我的苦难竟将我折磨到此等地步,我的心脏忽然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兴奋攫住。
“我……我同意。”借着这股冲动,我草率地做出了重要的决定。
“你同意什么?”她的声音中掺入了一丝戏弄。
“我同意向你……贡出我的一切。”
我伏在地上,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干了一样。
她嗤笑一声,回到卧室,拿出来一沓文书。上面的字很多,我一个都没看,只是一股脑地在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她把那堆纸扔到一边,盯着我看。
我感到一阵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该把手放到哪里,也不知道该把膝盖跪在何处。身下的地面已不再是我的家了,面前我几分钟前还躺在上面的沙发也已不再是我的沙发了。
我变成了这间屋子里的客人。
不,我并不是现在才变成客人的,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注定是这间屋子里的客人了。
“你打算在我的房子里待多久?”她玩味地看着我。
“我现在就离开。”我转身往门口爬去。
“主人允许你走了?”她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充满希望地回头。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依然是你的主人而已,滚吧。”
我掉头,慢慢爬到门口。她并没有如我期望地回心转意。
我站起身,打开门,楼道里的空气异常的冷。
“喂,那个谁。”
到头来,连我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吗……
“如果你要去死的话,记得选个不会被人发现尸体的地方哦,不要给我惹上麻烦。”她的唇间吐出冰冷的话语。
冰冷到我想测测她的体温,看看她是否还是一个人类。
我想说话,喉咙却梗住不能动弹,只能冲她点点头。
我为什么要点头呢?我一边想着这无意义的问题,一边走到门外,冰冷的空气让我打了个寒颤。
“还有,”她坐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叫住我,“主人想要你身上的衣服。”
事实上,并没有测体温的必要,因为很明显地,她并不是一个人类,她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魔鬼。
我一口气脱下身上的衣服,毕竟是在有暖气的家里穿的,算上内裤也才薄薄的三件。
“乖~”她的声音中忽然带了些温柔,让人摸不着头脑,“戴上吧,主人赏你的。”
她扔过来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个电击止吠器,兽用的。
裸体、兽用品……很好,这样我作为小丑的装束就齐了。
我关上门,转身下楼。刚走出第一步,就被难以承受的寒冷狠狠打了一拳。
我几乎是立刻想要敲门,哀求她让我回去,但也是几乎立刻我就得出答案,她不会让我回去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下楼,希望运动能让身体暖和一些,虽然脚底被冰冷的地面冻得发疼,但是肌肉的地方似乎隐隐生出了一些热量。
冲出单元门,门口有一滩饮料结成的冰,我跳了过去。比楼道里还要强劲百倍的冷空气从四面八方袭击过来,我的骨头似乎都附上了一层霜。
门口有一个叫“人仿商店”的奇怪贩卖机,我靠在它的散热口,像在沙漠中的鱼扑在一片带露水的叶子上。
无论如何思索,目的地似乎都是确定的。
通惠河。
我打定主意,鼓动颤抖的肌肉,哆哆嗦嗦地朝着河边跑。
我家……曾经是我家的地方离河边很近,刚搬来的时候我经常被河边晨练的老头老太太吵醒,所以后来我学会了戴耳塞。
不知道她学会戴耳塞了没。
……妈的,为什么脑子里还是她。
我甩甩脑袋,专注于肌肉发力,我感到它们越来越不听控制了。好在河边也没两步了,穿过马路,翻越栏杆,我就能坠入目的地了。
“啊!”一声意料之外的尖叫声从咫尺传来。
我的心猛地一突,我被发现了!
我艰难地转过头,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运动服,厚厚的围巾和小熊耳罩。看起来是来晨跑的。
“你……你是要……跳河?”
“对。”我的牙齿打架,只能用喉咙把字挤出来。
“你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吗?你冷不冷啊?”她解开围巾,露出戴着有些幼稚的小熊口罩的脸。
多么善良的女孩子啊,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恶魔的话,我或许也会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和她结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吧。
可我已经丧失了这个资格。
我后退两步,一切都为时已晚,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刻了。我用手撑住栏杆,胳膊用不上力,于是我靠近栏杆,把上半身往外探,打算栽出去。
胳膊上传来一阵温暖,她拽着我,力量虽弱,但很坚定。
谢谢你,陌生的天使,不过很遗憾,你无法拯救我。
我挣脱她,向前探身。
一股酥麻的感觉从脖子上散开,随后迅速爆发,我的肌肉瞬间抖得不成样子。没了支撑,我跌坐在地上,浑身痉挛。
我看到那个天使拿着遥控器。
是电击止吠器!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的遥控器?
“看来我的伪音练得还挺好的。”她摘下口罩。
陌生的天使卸下了伪装,底下是熟悉的魔鬼。
“我时常在想,你就像一个替罪的羔羊,所替的罪却是毁灭你的人犯下的,毁灭你的罪过。”她自顾自地说着,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她自己说,“你受到了折磨,还要承担因这折磨而产生的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吗?”
她微笑着,脸上泛起迷离的红晕:“你就是神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我努力张大嘴巴,但是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音节。
“你想问什么?”她松开遥控器,把外套和围巾扔在我的身上。
带着她的体温,很温暖。
“为什么?”我问出脑子里仅存的一句话。
为什么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想问为什么。
“我说过了,我是你的地狱,我要一点点地、彻底的毁灭你,你现在只是失去了金钱,但你还有社会关系、肉体、情感、智力等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呢。”她轻轻笑着,“你这可怜的羔羊,你的世界里以后只会有我一个人,你的地狱就是你的神明。”
我不明白,但我似乎又明白。
脸上烫烫的,我流泪了,但我并不悲伤。
闪光灯闪过,她用手机拍了张自拍。
“你想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吗?”
“想。”
她把手机屏幕朝向我。
屏幕的角落里,是一个滑稽可笑,冻得发青的可怜虫。它蜷缩在她的脚边,本能地寻找着温暖,即使这温暖是地狱中的火焰。
我看着这可怜虫,我看着这羔羊,我看着它,我看着他们,我看着我。
一阵热潮涌来,我射精了。
好!!!!!
好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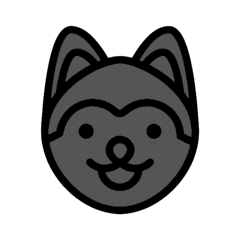
13
13303381250
Re: 羔羊在镜前凝视的绝不是悲伤
星寰公社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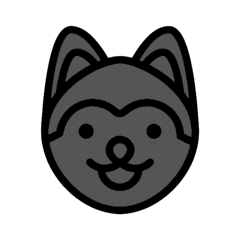
13
13303381250
Re: 《羔羊在镜前凝视的绝不是悲伤》
续集请移步镜像:https://mirror.chromaso.net/thread/1073746342
写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