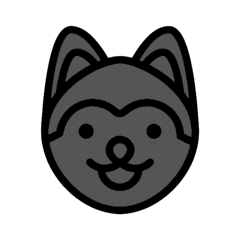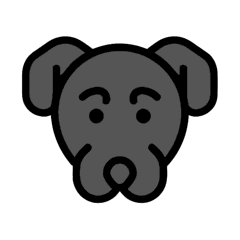留言
添加标签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留言了。
或许这条消息会像之前那几条那样被你屏蔽,或许不会。不管怎样都好,总之,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让我最后发一次疯吧。过了今天,确切地说,再过两个小时,一切就要彻底结束了。
我试着联系了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回复过。你抛弃了我,连一只旧袜子都没有留下来——你明明知道闻不到你的脚我会怎样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已经中了你的毒,无法从你的脚以外的任何东西上找到一点点快乐。
他们说中了蛇毒之后的急救方法是把蛇毒连着血液一起从伤口里挤出来。所以现在,我想要把我脑子里所有和你有关的东西都挤到这篇留言里,让大脑能够彻底的空下来。我定了一个闹钟,给自己两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件事。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用的话,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没错,我现在坐在HT大楼的天台,也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开始和结束一定要呼应,不是吗?
在那之后我经常梦到这里。每次的场景都不一样,天气也不一样,甚至情节也不一样,但每次都有你,还有你穿的那双黑色靴子——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光怪陆离的梦,都是饥渴的大脑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那天记忆的反刍罢了。那天,就是在这里,你告诉我不要跳下去,还有值得你为之活下去的东西。那时我只是嗤之以鼻,心想你一定要和电视剧里那些谈判专家那样,开始讲什么家人啊朋友啊之类的俗套台词了。很遗憾,我刚好和这些美好的名词都没有关系。
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居然把脚伸了过来。
如果你真的没有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就试试我的脚吧,我还记得你是这样说的。来,闻闻它,或者,舔舔看。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真的听了你的话。
事后想来,那或许并不是出于所谓的恋足(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词),只是一种百无聊赖下的消遣罢了。毕竟既然连死都不在乎了,再浪费一两分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还是很惊讶,自己竟然真的就从栏杆爬了下来,蹲到地上去闻你的左脚。你的体香,轻微的汗味,还混合着皮革特有的味道,透过鼻腔直击到我的神经,让那里产生了不知道多久没有产生过的震颤。那震颤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让我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跟我回家吧,你说。回去之后,再多闻一会儿也没关系。
于是我就真的跟着你回家了,就像狗追着骨头的味道那样。
后来你说你是心理系的学生,能看出我有什么什么心理疾病。你说我其实并不是真的一无所有,只是脑袋里出了问题,对那些美好的事物缺乏感知的能力罢了。你说有人可以为好的天气开心,有人会为一顿好吃的午饭开心,但这些东西的刺激对我而言就像是隔靴搔痒,总是没办法感受清楚,更没法在心里激起一点波澜。这个世界五光十色,而我只是裹在雨衣里路过。
那,对女人的脚感兴趣难道不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吗,我问。其实我对这件事倒不是那么意外,毕竟我之前也喜欢蹲在街头,有意无意的看着路过的女人的鞋子发呆。只不过在实际近距离闻到之前,从来不知道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刺激。
你告诉我这很正常,比这更奇怪更变态的爱好多的是——倒不如说,能找到如此容易满足的爱好已经很幸运了。还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会利用这一点加上一种叫“移情”的治疗方式来治好我。我同意了,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你沾满尘土的靴底碾烂食物喂给我,它竟然真的就变得好吃了;用穿了一天全是汗味的长筒靴盛水给我喝,它就真的变好喝了。你还教我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只要做得好,就可以在你晚上回家后尽情的帮你按摩脚,甚至还可以舔一小会儿。于是为了能换取把你的脚舔的干干净净的资格,我每天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你可以把对我的脚的热爱转化成对生活的热爱。你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
大概半年之后,你告诉我治疗很顺利。除去和你的脚相关的那些部分以外,我已经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了。但你治不了我没有什么本事这件事,所以我依然只能在你家做你的仆人。这对我其实没什么,或者不如说,这样才好呢。不过,你还说为了逐步戒除我对脚的依赖,今后要适当减少和你的脚的接触。于是,我要等三天乃至于一周才能为你舔上一次脚,还得是在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才行。用脚碾碎的食物也只有在你偶尔心情好的时候才会给我做。为了防止我偷吸,你甚至把家里的鞋柜锁了起来。为了换取你的奖励,我想更加拼命的干活讨你欢心,但却总是感觉恍惚,头脑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来。你轻描淡写地说这叫戒断反应。
总而言之,戒除并没有起作用。碰不到你的脚只会让我更加疯狂的渴望它们。我开始趁你不在的时候去舔地板,用帮你倒洗脚水的名义偷偷把它喝掉——我还记得被你撞见的那天,你脸上的表情。你把我的头直接按到了那盆水里,任凭我的手在空中无力的挣扎也没有停手,直到洗脚水大量涌进我的鼻子和肺部才放开。你怒气冲冲地宣布有必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治疗手段了。对不起,你那时一定很失望吧。
你开始用拖鞋抽打我的脸,穿着我最喜欢的靴子在我的身上踩踏,用靴子的尖头踢我的下体,用鞋跟在我的背上划出血红的痕迹,就算我疼的满脸泪水嗷嗷直叫也不会罢手。你说这样可以让我将【脚】和【痛苦】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建立条件反射。从而逐渐戒除对你的脚的依赖。
但是没有用。你的脚为我施加的痛苦并没有让我讨厌脚,而是反过来开始期待痛苦。被你的脚虐待总好过什么都感受不到。每一处红肿都是你的脚送我的礼物,每一个疤痕都是你的脚赐予的勋章。这样想着,我甚至在被你踢的时候射精了出来。那一刻我愚钝的脑袋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实我从来没有热爱过生活,也从来没有害怕过痛苦,只是在与日俱增地疯狂的迷恋你的脚。我这辈子唯一做的事情,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闻你的脚而已;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这件事的铺垫和衬托罢了。
你终于还是放弃了我。在最后的那个下午,你说我无药可救。可我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病不病,只要能闻到你的脚就好。但你没有再给我这个机会。
你现在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从天台砸到地上,你会听到我的声音吗。如果你刚好从一旁路过,你会停下来看我一眼吗。如果我的血会四处飞溅,我希望能有一点能溅在你的鞋子上,让我能最后一次,靠近我曾经最喜欢的地方。然后,被你嫌弃的用纸巾擦掉,扔进垃圾桶里。这样也好,这样就好。
啊,对了,既然是最后一次发消息了,就告诉你好啦。其实呀,我都知道的。
我知道你看到过我偷看别人的鞋子。
我知道移情治疗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在家里装了摄像头,能看到我舔地板和喝洗脚水。
我知道你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治好我。不管是怎样的治疗手段,给我怎样的奖励和惩罚,都只是因为你刚好想要这么做,我刚好可以让你这么做,仅此而已。你想看我匍匐在你脚下的样子,想看我为你的脚痴迷的样子,想看我被虐待时痛苦隐忍的样子。我都有,都可以有。
而当你不想再看的时候,我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对你而言就像是一张气泡纸,被一个一个捏破之后就该扔掉。对吧。
想明白这些并没有那么难。我只是病态而已,我并不蠢。至少,并没有那么蠢。
但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告诉你这些。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心里怎样看我,但我知道,我曾经死心塌地的绝望的喜欢过你和你的脚。而且我总觉得好像只要不说出这些来,一切就会有挽回的余地。你会在某个时刻,或许就是现在,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穿着那双我最喜欢的黑色皮靴,柔声告诉我,你来接我做下个阶段的治疗了。
但是你还是没有来。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奇怪,我忽然又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闹铃响起的声音,风吹过的触感,都像是隔了一层东西一样,朦朦胧胧的,听不到,也感受不到。想要再次温习你的脚的味道。却像是隔了一辈子那样,再也回忆不起来了。
啊。我懂了。我真的懂了。一定是这样吧。你只是我幻想出的幻觉而已。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呢,怎么可能忍心不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呢。现在,除了不知道为什么留下的几滴眼泪以外,我的状态就和两年前一模一样了。这就是一切都是幻觉的最好证明。
没错。并不是你抛弃了我,而是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在你脚下度过的两年时光,不过是一场已经太长太长的梦而已。而现在,梦醒了,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啊,我知道了,当然是应该去做我本来就打算做的事情啦。就是那个呀,那个,两年前,被你打断没有做成的那件事情。
那么,再见
或许这条消息会像之前那几条那样被你屏蔽,或许不会。不管怎样都好,总之,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让我最后发一次疯吧。过了今天,确切地说,再过两个小时,一切就要彻底结束了。
我试着联系了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回复过。你抛弃了我,连一只旧袜子都没有留下来——你明明知道闻不到你的脚我会怎样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已经中了你的毒,无法从你的脚以外的任何东西上找到一点点快乐。
他们说中了蛇毒之后的急救方法是把蛇毒连着血液一起从伤口里挤出来。所以现在,我想要把我脑子里所有和你有关的东西都挤到这篇留言里,让大脑能够彻底的空下来。我定了一个闹钟,给自己两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件事。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用的话,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没错,我现在坐在HT大楼的天台,也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开始和结束一定要呼应,不是吗?
在那之后我经常梦到这里。每次的场景都不一样,天气也不一样,甚至情节也不一样,但每次都有你,还有你穿的那双黑色靴子——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光怪陆离的梦,都是饥渴的大脑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那天记忆的反刍罢了。那天,就是在这里,你告诉我不要跳下去,还有值得你为之活下去的东西。那时我只是嗤之以鼻,心想你一定要和电视剧里那些谈判专家那样,开始讲什么家人啊朋友啊之类的俗套台词了。很遗憾,我刚好和这些美好的名词都没有关系。
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居然把脚伸了过来。
如果你真的没有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就试试我的脚吧,我还记得你是这样说的。来,闻闻它,或者,舔舔看。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真的听了你的话。
事后想来,那或许并不是出于所谓的恋足(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词),只是一种百无聊赖下的消遣罢了。毕竟既然连死都不在乎了,再浪费一两分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还是很惊讶,自己竟然真的就从栏杆爬了下来,蹲到地上去闻你的左脚。你的体香,轻微的汗味,还混合着皮革特有的味道,透过鼻腔直击到我的神经,让那里产生了不知道多久没有产生过的震颤。那震颤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让我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跟我回家吧,你说。回去之后,再多闻一会儿也没关系。
于是我就真的跟着你回家了,就像狗追着骨头的味道那样。
后来你说你是心理系的学生,能看出我有什么什么心理疾病。你说我其实并不是真的一无所有,只是脑袋里出了问题,对那些美好的事物缺乏感知的能力罢了。你说有人可以为好的天气开心,有人会为一顿好吃的午饭开心,但这些东西的刺激对我而言就像是隔靴搔痒,总是没办法感受清楚,更没法在心里激起一点波澜。这个世界五光十色,而我只是裹在雨衣里路过。
那,对女人的脚感兴趣难道不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吗,我问。其实我对这件事倒不是那么意外,毕竟我之前也喜欢蹲在街头,有意无意的看着路过的女人的鞋子发呆。只不过在实际近距离闻到之前,从来不知道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刺激。
你告诉我这很正常,比这更奇怪更变态的爱好多的是——倒不如说,能找到如此容易满足的爱好已经很幸运了。还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会利用这一点加上一种叫“移情”的治疗方式来治好我。我同意了,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你沾满尘土的靴底碾烂食物喂给我,它竟然真的就变得好吃了;用穿了一天全是汗味的长筒靴盛水给我喝,它就真的变好喝了。你还教我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只要做得好,就可以在你晚上回家后尽情的帮你按摩脚,甚至还可以舔一小会儿。于是为了能换取把你的脚舔的干干净净的资格,我每天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你可以把对我的脚的热爱转化成对生活的热爱。你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
大概半年之后,你告诉我治疗很顺利。除去和你的脚相关的那些部分以外,我已经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了。但你治不了我没有什么本事这件事,所以我依然只能在你家做你的仆人。这对我其实没什么,或者不如说,这样才好呢。不过,你还说为了逐步戒除我对脚的依赖,今后要适当减少和你的脚的接触。于是,我要等三天乃至于一周才能为你舔上一次脚,还得是在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才行。用脚碾碎的食物也只有在你偶尔心情好的时候才会给我做。为了防止我偷吸,你甚至把家里的鞋柜锁了起来。为了换取你的奖励,我想更加拼命的干活讨你欢心,但却总是感觉恍惚,头脑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来。你轻描淡写地说这叫戒断反应。
总而言之,戒除并没有起作用。碰不到你的脚只会让我更加疯狂的渴望它们。我开始趁你不在的时候去舔地板,用帮你倒洗脚水的名义偷偷把它喝掉——我还记得被你撞见的那天,你脸上的表情。你把我的头直接按到了那盆水里,任凭我的手在空中无力的挣扎也没有停手,直到洗脚水大量涌进我的鼻子和肺部才放开。你怒气冲冲地宣布有必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治疗手段了。对不起,你那时一定很失望吧。
你开始用拖鞋抽打我的脸,穿着我最喜欢的靴子在我的身上踩踏,用靴子的尖头踢我的下体,用鞋跟在我的背上划出血红的痕迹,就算我疼的满脸泪水嗷嗷直叫也不会罢手。你说这样可以让我将【脚】和【痛苦】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建立条件反射。从而逐渐戒除对你的脚的依赖。
但是没有用。你的脚为我施加的痛苦并没有让我讨厌脚,而是反过来开始期待痛苦。被你的脚虐待总好过什么都感受不到。每一处红肿都是你的脚送我的礼物,每一个疤痕都是你的脚赐予的勋章。这样想着,我甚至在被你踢的时候射精了出来。那一刻我愚钝的脑袋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实我从来没有热爱过生活,也从来没有害怕过痛苦,只是在与日俱增地疯狂的迷恋你的脚。我这辈子唯一做的事情,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闻你的脚而已;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这件事的铺垫和衬托罢了。
你终于还是放弃了我。在最后的那个下午,你说我无药可救。可我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病不病,只要能闻到你的脚就好。但你没有再给我这个机会。
你现在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从天台砸到地上,你会听到我的声音吗。如果你刚好从一旁路过,你会停下来看我一眼吗。如果我的血会四处飞溅,我希望能有一点能溅在你的鞋子上,让我能最后一次,靠近我曾经最喜欢的地方。然后,被你嫌弃的用纸巾擦掉,扔进垃圾桶里。这样也好,这样就好。
啊,对了,既然是最后一次发消息了,就告诉你好啦。其实呀,我都知道的。
我知道你看到过我偷看别人的鞋子。
我知道移情治疗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在家里装了摄像头,能看到我舔地板和喝洗脚水。
我知道你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治好我。不管是怎样的治疗手段,给我怎样的奖励和惩罚,都只是因为你刚好想要这么做,我刚好可以让你这么做,仅此而已。你想看我匍匐在你脚下的样子,想看我为你的脚痴迷的样子,想看我被虐待时痛苦隐忍的样子。我都有,都可以有。
而当你不想再看的时候,我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对你而言就像是一张气泡纸,被一个一个捏破之后就该扔掉。对吧。
想明白这些并没有那么难。我只是病态而已,我并不蠢。至少,并没有那么蠢。
但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告诉你这些。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心里怎样看我,但我知道,我曾经死心塌地的绝望的喜欢过你和你的脚。而且我总觉得好像只要不说出这些来,一切就会有挽回的余地。你会在某个时刻,或许就是现在,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穿着那双我最喜欢的黑色皮靴,柔声告诉我,你来接我做下个阶段的治疗了。
但是你还是没有来。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奇怪,我忽然又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闹铃响起的声音,风吹过的触感,都像是隔了一层东西一样,朦朦胧胧的,听不到,也感受不到。想要再次温习你的脚的味道。却像是隔了一辈子那样,再也回忆不起来了。
啊。我懂了。我真的懂了。一定是这样吧。你只是我幻想出的幻觉而已。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呢,怎么可能忍心不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呢。现在,除了不知道为什么留下的几滴眼泪以外,我的状态就和两年前一模一样了。这就是一切都是幻觉的最好证明。
没错。并不是你抛弃了我,而是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在你脚下度过的两年时光,不过是一场已经太长太长的梦而已。而现在,梦醒了,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啊,我知道了,当然是应该去做我本来就打算做的事情啦。就是那个呀,那个,两年前,被你打断没有做成的那件事情。
那么,再见
好耶!
卧槽要不是多说一句真的会大晚上的吓到我
写得真好,值得洛阳铲
跟铲!
跟铲!
让我解读一下最后一句没有句号是什么意思
怎么这篇突然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