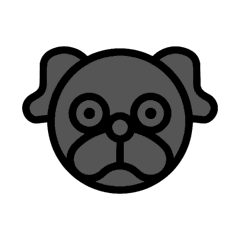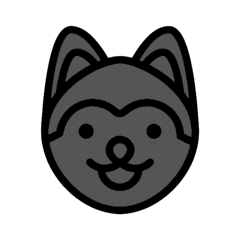贖罪與救贖---連載至四十集 七人留言直接更新七集!!!
连载中原创AI生成校园绿奴足控贞操锁舔鞋厕奴黄金阉割圣水情侣主
頂 很好看! 支持
第十七章:潘朵拉的盒子
清晨的宿舍昏暗冰冷,陽光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跪著的赤裸上身。我額頭貼著水泥地,手機鏡頭對著我,錄下每天的磕頭請安影片。貞操鎖在晨光下泛著冷光,像一枚永遠摘不下的恥辱標記。我低聲說道:「主人,奴隸張小凡向您請安,祝您和男友旅行愉快。」每磕一下頭,額頭撞地的悶響都像在敲碎我的靈魂。影片傳送出去後,麥語心的回覆如冰霜刺骨:「狗,別忘了今晚去我公寓打掃乾淨。我回來會檢查,要是一粒灰,我就讓你好看!」
這句威脅像鐵錘砸進我的心,我連忙回覆:「是,主人,奴隸一定做到最好。」放下手機,我騎上那輛輪胎幾乎磨平的電動車,開始一天的外送工作。城市的清晨冷得刺骨,寒風如刀子割在臉上,我卻不敢停下。訂單提示音像無形的鞭子,驅使我穿梭在街頭巷尾。汗水浸濕衣背,背上的鞭痕被拉扯得刺痛,但我只能咬牙堅持。從早餐到晚餐,我幾乎沒停過,雙腿酸痛得像灌了鉛,只為多賺幾塊錢上交給她,同時也為了讓忙碌麻痺自己的靈魂。
夜幕降臨,我拖著殞殞的身體,騎車趕往麥語心的公寓。站在門口,我的手心全是冷汗,心跳如擂鼓。我傳訊請示:「主人,奴隸已到達公寓門口,請求允許進入。」幾分鐘後,她回覆:「進去吧。狗,別以為我不在你就可以肆意妄為。記住,什麼是你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自己心裡要有數!」這句話像幽靈,纏繞在我心頭,讓我背脊發涼。我連忙回覆:「是,主人,奴隸絕不敢越矩。」
推開公寓的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房間靜得可怕,牆角的攝影機紅燈閃爍,像一隻無情的眼睛,提醒我麥語心可能正在千里之外透過手機監視。我脫光衣服,露出那枚羞恥的貞操鎖,匍匐在地,像條狗一樣爬進這片「神聖聖域」。我跪下,低聲說道:「主人,奴隸開始打掃,請您監督。」這句話像咒語,讓我徹底墮入奴隸的角色。
一進門,我注意到鞋櫃上了鎖,鎖頭在昏暗的燈光下泛著冷光,像在嘲笑我的妄想。麥語心果然不信任我,怕我在她不在時褻瀆她的鞋子或私物。可她不知道,這鎖頭粉碎的不只是我的希望,還有我心底那絲病態的渴望。作為一個男人,被貞操鎖禁錮了一年多,我早已忘了釋放的滋味。那種如吸毒般癡迷的高潮感,像遙遠的幻夢,幾乎從記憶中抹去。麥語心是我唯一能接觸的異性,儘管她的折磨早已消磨了我對她的愛意,舔鞋底、喝聖水時我的下體也不再有反應,只有她賞賜黃金時,那屈辱的刺激才會讓我硬得脹痛。可她依然是我曾癡迷的女人,我曾幻想趁她不在,夜深人靜時,關掉燈,偷偷拿出她的鞋子,聞那殞著她氣息的鞋內味道,哪怕只有片刻的沉醉。可鎖頭像一記耳光,讓我清醒:我是條狗,連妄想的資格都沒有。
我認命地開始打掃,戴上白色橡膠手套,跪著擦拭客廳的地板。汗水滴在地上,混著背上的鞭痕,刺痛得像火燒。茶几、沙發、窗台,我一寸寸擦拭,生怕留下任何痕跡。衛生間的馬桶散發著腥臭,我跪在瓷磚上,用刷子和清潔劑仔細刷洗,確保一塵不染。因為主人不在,這次允許使用工具,我如釋重負,卻仍不敢馬虎,檢查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馬桶潔白如新。她的警告在我腦海迴盪:「一粒灰,我就讓你好看!」
打掃完客廳和衛生間,我癱跪在地,靠在麥語心臥室的門口,意外發現門沒上鎖,輕輕一推,門縫緩緩敞開。那一瞬間,濃郁的女性香氣像洪水湧來,塞滿我的鼻子,那是麥語心的氣息,甜美而致命,讓我頭暈目眩。我的心跳猛地加速,血液像被點燃,但我沒敢踏入一步。客廳的攝影機紅燈閃爍,像在警告我這是大逆不道的禁地。我知道,臥室可能也有監控,麥語心或許正拿著手機,隨時檢查我的舉動。我僵在門口,目光穿過門縫,隱約看見房間深處一個大收納箱,散發著致命的誘惑。
我的腦海瞬間被幻想淹沒。我想像自己躡手躡腳爬進這片禁地,跪在收納箱前,顫抖著掀開箱蓋。裡面珍藏著各式各樣的專櫃品牌內衣—華x爾、黛x芬等,這些都是我用血汗錢為她買的。平時,這些衣物對我來說如同聖物,哪怕主人隨手扔一件在面前,我也得匍匐磕頭致敬,彷彿她親臨。手洗這些內衣時,我必須沐浴更衣,刷牙洗手,戴上白色手套,小心翼翼地清洗,生怕毀損一絲一毫,否則便是電擊棒和鞭子的酷刑。如今,這些薄如蟬翼的布料卻近在咫尺,殞著她高貴聖潔的氣息。那是每天緊貼她「神聖聖域」的衣物,與我這條狗永遠遙不可及的禁地緊密相依。我想像自己拿起一件粉紅蕾絲內衣,不用隔著手套,直接觸碰那柔軟的布料,貼近鼻尖,深深吸入那沾染了她香氣的味道。那氣息一定濃郁得讓我紙醉金迷,像毒藥般勾引我墮落,讓我感受那曾觸碰她聖域的恩賜,哪怕只有一秒的沉醉。我的下體因這幻想而脹痛,巨物像要掙脫貞操鎖的牢籠,奔騰而出,硬得讓我幾乎站不穩。這種渴望像毒藥,侵蝕我的理智,讓我幾乎要不顧一切衝進去。可我強壓下這衝動,決定按計畫行事:先假裝完成任務,獲得離開許可,再折返探索這片禁忌的聖域。
我跪在客廳中央,錄下匯報影片:「主人,奴隸已完成打掃,請您檢查。」影片傳送出去後,我屏息等待。幾分鐘後,她回覆:「狗,做得不錯,滾吧。」這句話像一道赦免令,讓我鬆了一口氣。我關掉公寓的所有燈光,匍匐到門口,假裝離開,在攝影機前緩緩關上門,發出清晰的「咔噠」聲。走廊的寂靜讓我的心跳更加刺耳,我站在門外,數著秒針,確保手機沒有新的訊息,確認她沒有起疑。
十分鐘後,我輕手輕腳推開門,重新爬進公寓,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我匍匐到臥室門口,門縫裡的香氣再次襲來,像毒藥鑽進我的血液。那股屬於麥語心的氣息,喚醒了我深埋的渴望。除了母親,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異性,這片禁地是我這條狗永遠不配觸碰的聖域。我跪在門口,目光穿過門縫,凝視那個收納箱,內心的波瀾如海嘯,激動、恐懼、渴望交織成一團。我想像著下一秒踏進這片聖域,掀開那個收納箱,觸碰那讓我發狂的禁忌之物。這幻想讓我全身顫抖,汗水滑進眼角,貞操鎖的脹痛如火焰,燒得我神智模糊。雖然房間黑暗,空氣冷得令人窒息,總覺得黑暗中好似有隻眼神在凝視著我,可慾望已將我理智沖垮,我什麼都管不了了。我只想沉浸在那充滿誘惑香氣的溫柔鄉裡,感受那禁忌的恩賜,哪怕只是片刻的沉醉。
清晨的宿舍昏暗冰冷,陽光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跪著的赤裸上身。我額頭貼著水泥地,手機鏡頭對著我,錄下每天的磕頭請安影片。貞操鎖在晨光下泛著冷光,像一枚永遠摘不下的恥辱標記。我低聲說道:「主人,奴隸張小凡向您請安,祝您和男友旅行愉快。」每磕一下頭,額頭撞地的悶響都像在敲碎我的靈魂。影片傳送出去後,麥語心的回覆如冰霜刺骨:「狗,別忘了今晚去我公寓打掃乾淨。我回來會檢查,要是一粒灰,我就讓你好看!」
這句威脅像鐵錘砸進我的心,我連忙回覆:「是,主人,奴隸一定做到最好。」放下手機,我騎上那輛輪胎幾乎磨平的電動車,開始一天的外送工作。城市的清晨冷得刺骨,寒風如刀子割在臉上,我卻不敢停下。訂單提示音像無形的鞭子,驅使我穿梭在街頭巷尾。汗水浸濕衣背,背上的鞭痕被拉扯得刺痛,但我只能咬牙堅持。從早餐到晚餐,我幾乎沒停過,雙腿酸痛得像灌了鉛,只為多賺幾塊錢上交給她,同時也為了讓忙碌麻痺自己的靈魂。
夜幕降臨,我拖著殞殞的身體,騎車趕往麥語心的公寓。站在門口,我的手心全是冷汗,心跳如擂鼓。我傳訊請示:「主人,奴隸已到達公寓門口,請求允許進入。」幾分鐘後,她回覆:「進去吧。狗,別以為我不在你就可以肆意妄為。記住,什麼是你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自己心裡要有數!」這句話像幽靈,纏繞在我心頭,讓我背脊發涼。我連忙回覆:「是,主人,奴隸絕不敢越矩。」
推開公寓的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房間靜得可怕,牆角的攝影機紅燈閃爍,像一隻無情的眼睛,提醒我麥語心可能正在千里之外透過手機監視。我脫光衣服,露出那枚羞恥的貞操鎖,匍匐在地,像條狗一樣爬進這片「神聖聖域」。我跪下,低聲說道:「主人,奴隸開始打掃,請您監督。」這句話像咒語,讓我徹底墮入奴隸的角色。
一進門,我注意到鞋櫃上了鎖,鎖頭在昏暗的燈光下泛著冷光,像在嘲笑我的妄想。麥語心果然不信任我,怕我在她不在時褻瀆她的鞋子或私物。可她不知道,這鎖頭粉碎的不只是我的希望,還有我心底那絲病態的渴望。作為一個男人,被貞操鎖禁錮了一年多,我早已忘了釋放的滋味。那種如吸毒般癡迷的高潮感,像遙遠的幻夢,幾乎從記憶中抹去。麥語心是我唯一能接觸的異性,儘管她的折磨早已消磨了我對她的愛意,舔鞋底、喝聖水時我的下體也不再有反應,只有她賞賜黃金時,那屈辱的刺激才會讓我硬得脹痛。可她依然是我曾癡迷的女人,我曾幻想趁她不在,夜深人靜時,關掉燈,偷偷拿出她的鞋子,聞那殞著她氣息的鞋內味道,哪怕只有片刻的沉醉。可鎖頭像一記耳光,讓我清醒:我是條狗,連妄想的資格都沒有。
我認命地開始打掃,戴上白色橡膠手套,跪著擦拭客廳的地板。汗水滴在地上,混著背上的鞭痕,刺痛得像火燒。茶几、沙發、窗台,我一寸寸擦拭,生怕留下任何痕跡。衛生間的馬桶散發著腥臭,我跪在瓷磚上,用刷子和清潔劑仔細刷洗,確保一塵不染。因為主人不在,這次允許使用工具,我如釋重負,卻仍不敢馬虎,檢查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馬桶潔白如新。她的警告在我腦海迴盪:「一粒灰,我就讓你好看!」
打掃完客廳和衛生間,我癱跪在地,靠在麥語心臥室的門口,意外發現門沒上鎖,輕輕一推,門縫緩緩敞開。那一瞬間,濃郁的女性香氣像洪水湧來,塞滿我的鼻子,那是麥語心的氣息,甜美而致命,讓我頭暈目眩。我的心跳猛地加速,血液像被點燃,但我沒敢踏入一步。客廳的攝影機紅燈閃爍,像在警告我這是大逆不道的禁地。我知道,臥室可能也有監控,麥語心或許正拿著手機,隨時檢查我的舉動。我僵在門口,目光穿過門縫,隱約看見房間深處一個大收納箱,散發著致命的誘惑。
我的腦海瞬間被幻想淹沒。我想像自己躡手躡腳爬進這片禁地,跪在收納箱前,顫抖著掀開箱蓋。裡面珍藏著各式各樣的專櫃品牌內衣—華x爾、黛x芬等,這些都是我用血汗錢為她買的。平時,這些衣物對我來說如同聖物,哪怕主人隨手扔一件在面前,我也得匍匐磕頭致敬,彷彿她親臨。手洗這些內衣時,我必須沐浴更衣,刷牙洗手,戴上白色手套,小心翼翼地清洗,生怕毀損一絲一毫,否則便是電擊棒和鞭子的酷刑。如今,這些薄如蟬翼的布料卻近在咫尺,殞著她高貴聖潔的氣息。那是每天緊貼她「神聖聖域」的衣物,與我這條狗永遠遙不可及的禁地緊密相依。我想像自己拿起一件粉紅蕾絲內衣,不用隔著手套,直接觸碰那柔軟的布料,貼近鼻尖,深深吸入那沾染了她香氣的味道。那氣息一定濃郁得讓我紙醉金迷,像毒藥般勾引我墮落,讓我感受那曾觸碰她聖域的恩賜,哪怕只有一秒的沉醉。我的下體因這幻想而脹痛,巨物像要掙脫貞操鎖的牢籠,奔騰而出,硬得讓我幾乎站不穩。這種渴望像毒藥,侵蝕我的理智,讓我幾乎要不顧一切衝進去。可我強壓下這衝動,決定按計畫行事:先假裝完成任務,獲得離開許可,再折返探索這片禁忌的聖域。
我跪在客廳中央,錄下匯報影片:「主人,奴隸已完成打掃,請您檢查。」影片傳送出去後,我屏息等待。幾分鐘後,她回覆:「狗,做得不錯,滾吧。」這句話像一道赦免令,讓我鬆了一口氣。我關掉公寓的所有燈光,匍匐到門口,假裝離開,在攝影機前緩緩關上門,發出清晰的「咔噠」聲。走廊的寂靜讓我的心跳更加刺耳,我站在門外,數著秒針,確保手機沒有新的訊息,確認她沒有起疑。
十分鐘後,我輕手輕腳推開門,重新爬進公寓,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我匍匐到臥室門口,門縫裡的香氣再次襲來,像毒藥鑽進我的血液。那股屬於麥語心的氣息,喚醒了我深埋的渴望。除了母親,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異性,這片禁地是我這條狗永遠不配觸碰的聖域。我跪在門口,目光穿過門縫,凝視那個收納箱,內心的波瀾如海嘯,激動、恐懼、渴望交織成一團。我想像著下一秒踏進這片聖域,掀開那個收納箱,觸碰那讓我發狂的禁忌之物。這幻想讓我全身顫抖,汗水滑進眼角,貞操鎖的脹痛如火焰,燒得我神智模糊。雖然房間黑暗,空氣冷得令人窒息,總覺得黑暗中好似有隻眼神在凝視著我,可慾望已將我理智沖垮,我什麼都管不了了。我只想沉浸在那充滿誘惑香氣的溫柔鄉裡,感受那禁忌的恩賜,哪怕只是片刻的沉醉。
cpy112233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棒棒棒,顶一下催更
第十八章 潘朵拉的秘密
我自以為聰明絕頂,計畫天衣無縫。公寓漆黑一片,客廳的監視器在黑暗中應該捕捉不到清晰畫面,這是我精心算計的機會。我假意離開,在門口故意讓門鎖發出「咔噠」一聲,然後屏息等待,確認麥語心的手機沒有傳來任何質問。我折返,躡手躡腳地推開門,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我知道,只要穿過這片黑暗的客廳,偷偷潛入麥語心的臥室,就能暫時脫離她手機遠端的監控。她的臥室對我來說是禁地,平時沒有她的允許,我連靠近都不敢,門總是鎖得嚴嚴實實,像在嘲笑我的卑微。可今晚,門縫透出一絲微光,門鎖竟然沒上,仿佛命運在向我招手。我猜,臥室裡應該不會裝有攝影機—麥語心那麼高傲,對我的掌控瞭如指掌,怎會想到我這條狗竟敢趁她不在,闖入她的私人領域?她一定認為我早已被調教得服服帖帖,連反抗的念頭都不敢有。我的胸口湧起一陣竊喜,覺得自己終於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窺探她的秘密。
我堅信這計畫萬無一失,內心的興奮讓我拋開了奴隸的畏縮。我不再匍匐在地,像條狗般卑微爬行,而是站起身,像個人一樣昂首闊步。我推開臥室的門,大膽地按下開關,燈光瞬間灑滿房間,照亮這片平時對我來說高不可攀的聖域。我肆無忌憚地走進她的領域,坐上她的床—這張我從未有資格觸碰的床,柔軟的床墊承載著她的氣息,讓我心跳加速。我躺了下來,臉貼著床單,貪婪地吸吮她殞留的體香,甜美而濃烈,像毒藥鑽進我的血液。我閉上眼,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我不在時,這張床上是否曾有男人與她交歡,肆意占有她的胴體?這想法讓我竟然生出一絲吃醋,妒火在胸口燃燒。我忘了自己只是條狗,只是條奴隸,竟敢對她的私生活心生嫉妒。我將下身貼在床上,貞操鎖的冰冷金屬摩擦著床單,我模擬男人交歡的動作,臀部上下起伏,幻想自己是她的男人,與她纏綿。這前所未有的感覺太美好,像從地獄掙脫到了天堂,我的靈魂仿佛重獲自由。可這還不夠,我需要更多刺激—對,就是那個盒子,那個我稱為潘朵拉的盒子,藏著她最私密的秘密,等著我去揭開。
我匍匐過去,每一下動作都小心翼翼,生怕發出任何聲響。黑暗中,麥語心的氣息更濃烈,像無形的繩索勒緊我的喉嚨。我跪在收納箱前,手指顫抖著掀開箱蓋。五顏六色的內衣內褲整齊排列,華歌爾、黛安芬,每一件都散發著她的氣息,刺繡精緻、做工完美,美得令人窒息。我一件件拿起,細細欣賞,柔軟的布料在指尖滑過,像電流燒過我的神經。我幻想麥語心穿上它們的模樣—粉紅蕾絲緊貼她的曲線,黑色絲綢勾勒她的腰身,薄如蟬翼的布料若隱若現,散發著致命的誘惑。我的下體脹痛得像一頭爆發的野獸,貞操鎖的牢籠無法禁錮,龜頭滲出黏稠的液體,順著金屬邊緣滑落,帶來一陣羞恥的刺痛。
禁慾太久的我,面對這些內衣,怎能克制?我的腦海全是她的胴體—粉嫩的雙峰在蕾絲下若隱若現,嬌滴的乳頭被薄布包裹,內褲緩緩滑下,露出那片神秘的黑森林,在昏暗的光線下散發著致命的誘惑。我開始羨慕她的歷任男友,那些能親眼目睹她穿著這些內衣的男人,那些能一顆顆解開她的鈕扣,將內衣褪去,肆意欣賞她赤裸胴體的男人。他們能觸碰那片我永遠無法企及的聖域,親吻她的肌膚,聆聽她的呻吟。而我,這條狗,除了跪著手洗這些聖物,連抬頭看她一眼的資格都沒有。我的心像被刀割,酸楚與嫉妒交織,讓我喘不過氣。
我的思緒墜入更深的深淵,回想起當初的選擇。如果我沒阻止陳凱威的威脅,或許我也能窺見這番風景?如果我沒刪除那段影片,而是私下與麥語心談判,用它換取一絲親近的機會,是否我也能觸碰那如今神聖遙不可及的聖域?可我選擇了贖罪,選擇了刪除影片,卻將自己推入無底的深淵。我自願成為她的奴隸,每天被迫舔鞋底、喝聖水、做苦役,承受嘲諷、責罵與羞辱。我被禁止釋放,成為她的出氣筒,無限壓榨勞動,上繳所有工資。我連愛人都無法守護,被迫在她面前舔麥語心的鞋,甚至喝下她閨蜜的尿,供她們取樂。連她的屎,我都得吞下。這些非人道的待遇像毒藥,腐蝕我的靈魂,讓我連做人的資格都失去。
我後悔,悔得心如刀絞。當初的我,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為什麼要為了所謂的贖罪,放棄一切可能?如果我當時狠下心,與陳凱威同流合污,或許我也能站在她的身邊,哪怕只是片刻的親密,也足以慰藉我這顆破碎的心。可我選擇了正義,選擇了保護她,卻換來無盡的屈辱。我的愛人趙宜,她的笑容曾是我生命的全部,可我卻在她面前舔麥語心的鞋,被迫喝下她的聖水,成為她們取樂的工具。趙宜離開時的眼神,那句「我恨你」,像一把刀永遠插在我的心上。每當夜深人靜,這份悔恨就像洪水,淹沒我的靈魂。我好蠢,好笨,好傻,為什麼我要做出這樣的選擇?為什麼我要讓自己墮入這無邊的地獄?
現在的我,連抬頭的資格都沒有。我的未來只剩無盡的勞役與羞辱。麥語心的閨蜜王嘉嘉和駱品萱,她們的笑聲像鞭子,抽在我心上。她們的尿液,腥臭而刺鼻,我卻得一滴不剩地吞下,只為博她們一笑。我的尊嚴被碾得粉碎,連狗都不如。未來還會有什麼?我不敢想。或許是更殞烈的調教,或許是公開的羞辱,讓全校都知道我這條狗的賤樣。想到這,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奪眶而出,所有的委屈像洪水傾瀉而下。我好後悔,好後悔,可一切已無回頭路。我將永遠是麥語心的奴隸,永遠抬不起頭。
我看著她的內褲,仔細檢查棉質面料,尋找是否有她的分泌物。一旦發現黃漬或殞留的氣味,我便激動萬分,貼近鼻尖貪婪吸聞,伸出舌頭舔舐。雖多半只剩洗滌劑的香味,我仍妄想尋找一絲她的氣息。在忘情舐時,仿佛我零距離親吻她的私密處,觸碰那片神聖的聖域。這是我成為奴隸以來,最開心、最幸運的一天。她的內褲大多嶄新,全是用我的血汗錢買來的,一但稍有磨損,她便隨手丟棄,毫不珍惜。我找到幾件她常穿的,帶著明顯的黃漬與分泌物,貪婪地吸聞,用舌頭舔舐那殞留的氣味,仿佛能從中找回一絲她的存在。
我挑選一件最性感的黑色蕾絲內褲,顫抖著套在被貞操鎖禁錮的驕傲上。我抓住冰冷的金屬籠鎖,像男人般上下擺動。布料摩擦著腫脹的肉體,帶來細微的快感,卻伴隨著鐵籠的刺痛。我閉上眼,幻想自己與麥語心交融,奴隸褻瀆女神,低賤玷污神聖。快感如潮水湧來,我很快達到高潮,濃白的液體從鎖頭噴出,沾染在內褲上,像骯髒的罪證玷污了這片聖物。這是我首次未經允許的釋放,卻沒有罪惡感,只有滿滿的滿足。
休息片刻,我又挑了一件緋紅絲綢內褲,重複這禁忌的儀式。我的肉體已被金屬勒出紅痕,刺痛如刀割,卻阻止不了我的動作。我幻想著她的胴體,她的呻吟,幻想自己是她的男人,而非一條狗。第二次高潮來得更猛烈,液體再次玷污了內褲,我的靈魂仿佛在這一刻掙脫了枷鎖。第三件內褲,粉色薄紗,我繼續這瘋狂的發洩,直到精疲力竭,癱倒在她滿滿的內衣內褲中。
這一刻,我不再是奴隸,而是男人。我沒有罪惡感,只有滿滿的幸福與滿足。她的內褲散落在身旁,像一場禁忌的盛宴,承載著我所有的渴望與悔恨。我閉上眼,淚水滑落,混雜著汗水與血水。我知道,這短暫的解放只是幻夢,醒來後,我仍是她的狗,永遠無法逃脫這無邊的深淵。可在這一刻,我選擇沉醉,選擇擁抱這唯一的自由,哪怕它如此骯髒,如此不堪。
我自以為聰明絕頂,計畫天衣無縫。公寓漆黑一片,客廳的監視器在黑暗中應該捕捉不到清晰畫面,這是我精心算計的機會。我假意離開,在門口故意讓門鎖發出「咔噠」一聲,然後屏息等待,確認麥語心的手機沒有傳來任何質問。我折返,躡手躡腳地推開門,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我知道,只要穿過這片黑暗的客廳,偷偷潛入麥語心的臥室,就能暫時脫離她手機遠端的監控。她的臥室對我來說是禁地,平時沒有她的允許,我連靠近都不敢,門總是鎖得嚴嚴實實,像在嘲笑我的卑微。可今晚,門縫透出一絲微光,門鎖竟然沒上,仿佛命運在向我招手。我猜,臥室裡應該不會裝有攝影機—麥語心那麼高傲,對我的掌控瞭如指掌,怎會想到我這條狗竟敢趁她不在,闖入她的私人領域?她一定認為我早已被調教得服服帖帖,連反抗的念頭都不敢有。我的胸口湧起一陣竊喜,覺得自己終於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窺探她的秘密。
我堅信這計畫萬無一失,內心的興奮讓我拋開了奴隸的畏縮。我不再匍匐在地,像條狗般卑微爬行,而是站起身,像個人一樣昂首闊步。我推開臥室的門,大膽地按下開關,燈光瞬間灑滿房間,照亮這片平時對我來說高不可攀的聖域。我肆無忌憚地走進她的領域,坐上她的床—這張我從未有資格觸碰的床,柔軟的床墊承載著她的氣息,讓我心跳加速。我躺了下來,臉貼著床單,貪婪地吸吮她殞留的體香,甜美而濃烈,像毒藥鑽進我的血液。我閉上眼,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我不在時,這張床上是否曾有男人與她交歡,肆意占有她的胴體?這想法讓我竟然生出一絲吃醋,妒火在胸口燃燒。我忘了自己只是條狗,只是條奴隸,竟敢對她的私生活心生嫉妒。我將下身貼在床上,貞操鎖的冰冷金屬摩擦著床單,我模擬男人交歡的動作,臀部上下起伏,幻想自己是她的男人,與她纏綿。這前所未有的感覺太美好,像從地獄掙脫到了天堂,我的靈魂仿佛重獲自由。可這還不夠,我需要更多刺激—對,就是那個盒子,那個我稱為潘朵拉的盒子,藏著她最私密的秘密,等著我去揭開。
我匍匐過去,每一下動作都小心翼翼,生怕發出任何聲響。黑暗中,麥語心的氣息更濃烈,像無形的繩索勒緊我的喉嚨。我跪在收納箱前,手指顫抖著掀開箱蓋。五顏六色的內衣內褲整齊排列,華歌爾、黛安芬,每一件都散發著她的氣息,刺繡精緻、做工完美,美得令人窒息。我一件件拿起,細細欣賞,柔軟的布料在指尖滑過,像電流燒過我的神經。我幻想麥語心穿上它們的模樣—粉紅蕾絲緊貼她的曲線,黑色絲綢勾勒她的腰身,薄如蟬翼的布料若隱若現,散發著致命的誘惑。我的下體脹痛得像一頭爆發的野獸,貞操鎖的牢籠無法禁錮,龜頭滲出黏稠的液體,順著金屬邊緣滑落,帶來一陣羞恥的刺痛。
禁慾太久的我,面對這些內衣,怎能克制?我的腦海全是她的胴體—粉嫩的雙峰在蕾絲下若隱若現,嬌滴的乳頭被薄布包裹,內褲緩緩滑下,露出那片神秘的黑森林,在昏暗的光線下散發著致命的誘惑。我開始羨慕她的歷任男友,那些能親眼目睹她穿著這些內衣的男人,那些能一顆顆解開她的鈕扣,將內衣褪去,肆意欣賞她赤裸胴體的男人。他們能觸碰那片我永遠無法企及的聖域,親吻她的肌膚,聆聽她的呻吟。而我,這條狗,除了跪著手洗這些聖物,連抬頭看她一眼的資格都沒有。我的心像被刀割,酸楚與嫉妒交織,讓我喘不過氣。
我的思緒墜入更深的深淵,回想起當初的選擇。如果我沒阻止陳凱威的威脅,或許我也能窺見這番風景?如果我沒刪除那段影片,而是私下與麥語心談判,用它換取一絲親近的機會,是否我也能觸碰那如今神聖遙不可及的聖域?可我選擇了贖罪,選擇了刪除影片,卻將自己推入無底的深淵。我自願成為她的奴隸,每天被迫舔鞋底、喝聖水、做苦役,承受嘲諷、責罵與羞辱。我被禁止釋放,成為她的出氣筒,無限壓榨勞動,上繳所有工資。我連愛人都無法守護,被迫在她面前舔麥語心的鞋,甚至喝下她閨蜜的尿,供她們取樂。連她的屎,我都得吞下。這些非人道的待遇像毒藥,腐蝕我的靈魂,讓我連做人的資格都失去。
我後悔,悔得心如刀絞。當初的我,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為什麼要為了所謂的贖罪,放棄一切可能?如果我當時狠下心,與陳凱威同流合污,或許我也能站在她的身邊,哪怕只是片刻的親密,也足以慰藉我這顆破碎的心。可我選擇了正義,選擇了保護她,卻換來無盡的屈辱。我的愛人趙宜,她的笑容曾是我生命的全部,可我卻在她面前舔麥語心的鞋,被迫喝下她的聖水,成為她們取樂的工具。趙宜離開時的眼神,那句「我恨你」,像一把刀永遠插在我的心上。每當夜深人靜,這份悔恨就像洪水,淹沒我的靈魂。我好蠢,好笨,好傻,為什麼我要做出這樣的選擇?為什麼我要讓自己墮入這無邊的地獄?
現在的我,連抬頭的資格都沒有。我的未來只剩無盡的勞役與羞辱。麥語心的閨蜜王嘉嘉和駱品萱,她們的笑聲像鞭子,抽在我心上。她們的尿液,腥臭而刺鼻,我卻得一滴不剩地吞下,只為博她們一笑。我的尊嚴被碾得粉碎,連狗都不如。未來還會有什麼?我不敢想。或許是更殞烈的調教,或許是公開的羞辱,讓全校都知道我這條狗的賤樣。想到這,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奪眶而出,所有的委屈像洪水傾瀉而下。我好後悔,好後悔,可一切已無回頭路。我將永遠是麥語心的奴隸,永遠抬不起頭。
我看著她的內褲,仔細檢查棉質面料,尋找是否有她的分泌物。一旦發現黃漬或殞留的氣味,我便激動萬分,貼近鼻尖貪婪吸聞,伸出舌頭舔舐。雖多半只剩洗滌劑的香味,我仍妄想尋找一絲她的氣息。在忘情舐時,仿佛我零距離親吻她的私密處,觸碰那片神聖的聖域。這是我成為奴隸以來,最開心、最幸運的一天。她的內褲大多嶄新,全是用我的血汗錢買來的,一但稍有磨損,她便隨手丟棄,毫不珍惜。我找到幾件她常穿的,帶著明顯的黃漬與分泌物,貪婪地吸聞,用舌頭舔舐那殞留的氣味,仿佛能從中找回一絲她的存在。
我挑選一件最性感的黑色蕾絲內褲,顫抖著套在被貞操鎖禁錮的驕傲上。我抓住冰冷的金屬籠鎖,像男人般上下擺動。布料摩擦著腫脹的肉體,帶來細微的快感,卻伴隨著鐵籠的刺痛。我閉上眼,幻想自己與麥語心交融,奴隸褻瀆女神,低賤玷污神聖。快感如潮水湧來,我很快達到高潮,濃白的液體從鎖頭噴出,沾染在內褲上,像骯髒的罪證玷污了這片聖物。這是我首次未經允許的釋放,卻沒有罪惡感,只有滿滿的滿足。
休息片刻,我又挑了一件緋紅絲綢內褲,重複這禁忌的儀式。我的肉體已被金屬勒出紅痕,刺痛如刀割,卻阻止不了我的動作。我幻想著她的胴體,她的呻吟,幻想自己是她的男人,而非一條狗。第二次高潮來得更猛烈,液體再次玷污了內褲,我的靈魂仿佛在這一刻掙脫了枷鎖。第三件內褲,粉色薄紗,我繼續這瘋狂的發洩,直到精疲力竭,癱倒在她滿滿的內衣內褲中。
這一刻,我不再是奴隸,而是男人。我沒有罪惡感,只有滿滿的幸福與滿足。她的內褲散落在身旁,像一場禁忌的盛宴,承載著我所有的渴望與悔恨。我閉上眼,淚水滑落,混雜著汗水與血水。我知道,這短暫的解放只是幻夢,醒來後,我仍是她的狗,永遠無法逃脫這無邊的深淵。可在這一刻,我選擇沉醉,選擇擁抱這唯一的自由,哪怕它如此骯髒,如此不堪。
顶顶顶
第十九章:待宰羔羊
清晨的宿舍籠罩在薄霧中,陽光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赤裸的胸膛上,貞操鎖在晨光下泛著冰冷的光芒,像一枚永遠摘不下的恥辱烙印。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剛從麥語心的公寓回來,內心卻充滿了一種病態的滿足。那場與她貼身內褲的禁忌交歡,像毒藥般在我血液裡流淌,讓我回味無窮。凌晨四點半,我小心翼翼地復原了現場,將沾染我罪證的三件內褲清洗乾淨,掛在浴室陰乾,心裡盤算著她還有兩天回來,明天再偷偷收好,應該神不知鬼不覺。我甚至暗自得意,覺得這計畫天衣無縫。
離開前,一個邪念突然竄進腦海。收納箱裡的內褲那麼多,少一兩件,麥語心應該不會察覺吧?這念頭像惡魔的低語,瞬間佔據我的大腦。我又默默爬回臥室,跪在收納箱前,顫抖著挑選。每一件內褲都性感得令人窒息,我陷入選擇的煎熬,最終選了一件淺綠色蕾絲內褲,繡滿玫瑰花,褲頭點綴著可愛的蝴蝶結,美得令人窒息;還有一件純白蕾絲內褲,佈滿花朵刺繡,清淡高雅又不失性感,褲頭的蝴蝶結有著畫龍點睛的效果。我將這兩件內褲偷偷塞進口袋,將收納箱恢復原狀,摸黑爬到門口,小心翼翼離開,儘量不發出任何聲響。
離開的路上,我腦海裡不斷閃現與她貼身內褲纏綿的畫面,心想她後天才回來,今晚我還能再享受一次這禁忌的狂歡,興奮得難以言喻。回到宿舍,已是清晨六點五十分,我錄製了一段向主人請安的影片,然後抱著那件淺綠色內褲沉沉睡去。或許是昨晚的放縱耗盡了體力,或是那件內褲的魔力,我睡得格外深沉,醒來時已是下午三點半。我猛地從床上彈起,驚覺錯過了中午向主人的請安。想到她對遲到的懲罰,我心慌意亂,趕緊錄了一段影片,解釋自己因外送太累睡過頭,懇求原諒。
錄完影片,我打開通訊軟體,卻發現麥語心已經發來五條訊息。平時除非有任務或我犯錯,她的日常請安從不回覆,但她發訊息時,我必須在十分鐘內回應,否則將面臨嚴厲懲罰。而我熟睡時,她連續發了五條訊息,我頓時背脊發涼,恐懼如潮水般湧來。
9:10:狗,我今天提前一天回程,下午三點半到家,四點準時到我家伺候。別讓我等!
9:20:怎麼不回訊息?敢無視我了?活膩了?
10:30:主人才離開幾天,你就放飛自我了?信不信我讓你後悔當我的狗?
11:30:再不回訊息,別怪我讓你生不如死!你的賤樣我有的是證據!
3:30:我到家了,還不回訊息?四點沒準時到,你就等著後悔活著吧!
她的語氣從冷淡到憤怒,每一句都像刀子刺進我的心。平時遲到半小時,我已被電擊得半死不活,如今遲了整整幾小時,我嚇得全身發抖,手忙腳亂地將剛錄的影片發給她,然後抓起電動車鑰匙,飛奔向她的公寓。我知道,無論如何懺悔,這次懲罰都無可避免。悔恨像毒藥吞噬我的心,昨晚的貪歡如今成了致命的錯誤。
更恐怖的念頭突然閃過腦海——主人提前回來,浴室裡還掛著那三件內褲!雖然我已將它們洗淨,精液的痕跡應該已被清除,但這些內褲本該鎖在麥語心臥室的收納箱裡,那片對我來說是絕對禁地的聖域。如今它們卻莫名出現在浴室,唯一的解釋是我闖入了她的臥室,並對內褲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清洗的痕跡反而成了我褻瀆的鐵證!她提前回來,必定已發現這一切。我的腦海裡閃過上次褻瀆內褲時的場景,她逼我寫下的悔過切結書,內容歷歷在目,像一把刀懸在我心頭:
悔過切結書
賤奴張小凡,因對主人麥語心之貼身衣物心生淫邪之念,褻瀆主人神聖之物,罪不可赦。承蒙主人施以重罰,賤奴痛徹心扉,真心悔悟,自此絕不再犯。若日後再對主人或其物品心存不敬或淫邪想法,賤奴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絕不推脫,誓言為證。
這份切結書如詛咒,字字刻在我心上。當時我跪在她面前,淚流滿面地簽下這份誓言,她的眼神冷酷如刀,警告我若再犯,必親手執行閹割。如今,我再次觸犯她的禁忌,浴室的內褲就是鐵證,她必定已知情。我的腦海裡閃過電擊棒的滋滋聲,皮鞭撕裂皮膚的劇痛,甚至那把冰冷的手術刀在她手中閃著寒光,準備執行我曾發下的毒誓。她的冷笑,她的怒火,像幽靈纏繞在我心頭,讓我背脊陣陣發涼,恐懼像無形的鎖鏈,勒緊我的喉嚨,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吞咽玻璃碴。
我竟然對一個女人如此恐懼,恐懼到連靈魂都在顫抖。忽然,一股溫熱的液體從下身蔓延,我低頭一看,內褲已濕透,竟是我的尿液。我竟然害怕到失禁了!羞恥和恐懼交織,我咬緊牙關,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可現實卻逼我繼續向前,奔向那無底的深淵。
抵達公寓樓下時,我雙腿軟得像棉花,幾乎站不穩。手機突然響起,是麥語心的視訊電話。我低頭一看,時間已是四點五分,我遲到了五分鐘!恐懼像洪水吞沒我,我慌張地掏出手機,手抖得像篩糠,不小心將手機摔在地上,螢幕在地上發出刺耳的撞擊聲。我趕忙撿起,顧不上擦去上面的灰塵,恭敬地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接通視訊。還沒等我開口,電話那頭傳來她憤怒的咆哮,像雷霆劈進我的腦海:「你這髒東西!垃圾!賤狗!你敢闖我臥室,碰我的內褲?!」
「我…我…」我竟然害怕得說不出話,喉嚨像被什麼堵住,想辯解卻只發出顫抖的氣音,在她憤怒的目光下,我只能瑟瑟發抖。她的眼神透過螢幕,像刀子刺穿我的靈魂,帶著毫不掩飾的鄙夷和怒火。「狗東西,現在四點十分,你給我三分鐘內滾到我面前!不然,我把你舔鞋底、喝尿的賤樣全公開,還送你進監獄,讓你這輩子都抬不起頭!」她語氣冷酷,字字如冰錐,說完便狠狠掛斷電話,螢幕瞬間黑了下來。
我愣在原地,腦子一片空白,恐懼像毒蛇鑽進我的骨髓,讓我全身冰冷。我知道,三分鐘內爬上五樓幾乎不可能,這次我站著進去,恐怕得躺著出來了。一個瘋狂的念頭閃過腦海——逃跑!就此離開,遠走高飛,逃離這無盡的奴役!可現實像鐵錘砸碎了這幻想。我身無分文,連換身衣服的錢都沒有。更何況,她手裡握著我的罪證,那些不堪入目的影片——我舔鞋底、喝她和她閨蜜的聖水,那些畫面一旦公開,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他們辛苦一輩子的臉面將被我徹底毀掉。我的腦海裡閃過父親佝僂的背影,母親滿是皺紋的雙手,他們為我付出了一切,而我卻淪為這般不堪的畜生。我不能讓他們蒙羞,不能讓他們因為我而抬不起頭!
我沒有選擇。明知是死路,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前。我拖著顫抖的雙腿,跌跌撞撞地衝進公寓樓,樓梯間的回音像在嘲笑我的絕望。我爬上五樓,肺像要炸開,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站在她公寓門口,我的手抖得幾乎握不住手機,汗水混著尿液的濕冷感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無地自容。我的腦海裡全是那份切結書,閹割的威脅像死神的鐮刀懸在頭頂,電擊棒的滋滋聲、皮鞭的撕裂聲、還有手術刀的寒光,像噩夢般輪番上演。我的雙腿顫抖得像篩子,恐懼吞噬了我的靈魂,我甚至感覺到下體的貞操鎖在顫抖,彷彿在預告即將到來的酷刑。我傳訊請示:「主人,賤奴到達,求您開門,允許這骯髒的狗進來接受您的審判。」她的回覆如地獄烈焰,充滿滔天怒火:「推門進來,狗!你這下賤的垃圾,敢褻瀆我的聖物,今天我非剝了你的皮不可!」
我推開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麥語心站在客廳中央,穿著黑色緊身上衣和短裙,氣場如女王般冷酷。她的眼神像刀,狠狠刺穿我,手裡握著一條帶刺的皮鞭,鞭梢在空中輕輕晃動,發出令人心悸的聲響。茶几上放著那三件內褲,整齊疊好,像一份罪證靜靜等待審判。我還沒來得及脫下衣服,她猛地甩出一鞭,鞭梢撕裂我的肩膀,鮮血瞬間滲出,痛得我縮成一團,癱倒在地。
「操你媽的死賤狗!竟然敢闖我臥室,褻瀆我的內褲,還是我最喜歡的那幾件!你這王八蛋!」她的聲音充滿新仇舊恨,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每一句都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連忙磕頭,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知錯…求您饒恕…」可我的道歉只換來更毒辣的鞭打,鞭梢如狂風暴雨,抽在我的背上、胸口,舊傷被撕裂,鮮血順著皮膚流下,滴在地上,發出細微的滴答聲。
「還不把衣服脫掉?在主人面前還敢穿衣服?進來前請安了嗎?連禮數都忘了?尊卑忘了?身分忘了?」她的怒罵如雷霆,我連忙爬起,邊挨鞭子邊脫衣服,手忙腳亂地扯下衣物,每脫下一件,鞭子就抽在裸露的皮膚上,留下一條條血痕。我咬緊牙,忍著劇痛,磕頭求饒:「主人…賤奴該死…賤奴知錯…」可她毫無憐憫,鞭子抽得更狠,彷彿要將我整個人撕碎。客廳的空氣瀰漫著血腥味,皮鞭的呼嘯聲和我的哀嚎交織,像一場殞烈的審判。
麥語心的怒火未消,她冷冷命令:「腰桿挺直!」我已被打得全身無力,聽到命令用盡吃奶的力氣勉強挺起腰,卻沒想到下體冷不防地被她狠狠踢了一腳。雖然隔著貞操鎖,這一腳的力道卻像錘子砸在我的命根子上,痛得我眼淚瞬間爆射而出,身體本能地蜷縮成一團,發出淒厲的哀嚎。她毫不停手,接連朝我的下體猛踹,即使我試圖護住命根,她卻無情地吼道:「把手拿開,你這賤狗,還敢擋?」
我因恐懼顫抖著緩緩挪開雙手,露出被貞操鎖禁錮的下體。麥語心抬起靴子,狠狠踩踏我的下體,靴尖碾壓著金屬鎖,痛得我全身痙攣。她一邊踩踏,一邊踢我的身體和臉頰,我像個沙包任由她毆打,無力反抗。她的嘲諷如刀,刺進我的靈魂:「你這骯髒齷齪的狗東西,就不配有這東西!我看到就噁心!你的切結書還記得吧?再犯就閹了你,今天就是你兌現誓言的時候!」她的話像死神的宣判,閹割的威脅讓我的心墜入無底深淵,恐懼和羞恥吞噬了我的靈魂。我試圖求饒,聲音沙啶得像在哀嚎:「主人…賤奴知錯…求您…別…」可話還沒說完,又是一腳踢在我的下巴,頭撞在地上,眼前一黑,意識模糊。
在麥語心無情的毆打下,我的身體像被撕碎的布偶,鮮血和汗水混雜,尿液的腥味從濕透的內褲傳來,讓我墮入無邊的絕望。最後一擊,她的靴子狠狠踩在我的胸口,力道大得讓我喘不過氣。我的視線漸漸模糊,耳邊只剩她的冷笑和嘲諷:「狗,你這賤東西,活著就是個錯誤。」
終於,劇痛和恐懼將我吞沒,我暈厥過去,靈魂像被拖進無盡的黑暗深淵,無處可逃。
清晨的宿舍籠罩在薄霧中,陽光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赤裸的胸膛上,貞操鎖在晨光下泛著冰冷的光芒,像一枚永遠摘不下的恥辱烙印。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剛從麥語心的公寓回來,內心卻充滿了一種病態的滿足。那場與她貼身內褲的禁忌交歡,像毒藥般在我血液裡流淌,讓我回味無窮。凌晨四點半,我小心翼翼地復原了現場,將沾染我罪證的三件內褲清洗乾淨,掛在浴室陰乾,心裡盤算著她還有兩天回來,明天再偷偷收好,應該神不知鬼不覺。我甚至暗自得意,覺得這計畫天衣無縫。
離開前,一個邪念突然竄進腦海。收納箱裡的內褲那麼多,少一兩件,麥語心應該不會察覺吧?這念頭像惡魔的低語,瞬間佔據我的大腦。我又默默爬回臥室,跪在收納箱前,顫抖著挑選。每一件內褲都性感得令人窒息,我陷入選擇的煎熬,最終選了一件淺綠色蕾絲內褲,繡滿玫瑰花,褲頭點綴著可愛的蝴蝶結,美得令人窒息;還有一件純白蕾絲內褲,佈滿花朵刺繡,清淡高雅又不失性感,褲頭的蝴蝶結有著畫龍點睛的效果。我將這兩件內褲偷偷塞進口袋,將收納箱恢復原狀,摸黑爬到門口,小心翼翼離開,儘量不發出任何聲響。
離開的路上,我腦海裡不斷閃現與她貼身內褲纏綿的畫面,心想她後天才回來,今晚我還能再享受一次這禁忌的狂歡,興奮得難以言喻。回到宿舍,已是清晨六點五十分,我錄製了一段向主人請安的影片,然後抱著那件淺綠色內褲沉沉睡去。或許是昨晚的放縱耗盡了體力,或是那件內褲的魔力,我睡得格外深沉,醒來時已是下午三點半。我猛地從床上彈起,驚覺錯過了中午向主人的請安。想到她對遲到的懲罰,我心慌意亂,趕緊錄了一段影片,解釋自己因外送太累睡過頭,懇求原諒。
錄完影片,我打開通訊軟體,卻發現麥語心已經發來五條訊息。平時除非有任務或我犯錯,她的日常請安從不回覆,但她發訊息時,我必須在十分鐘內回應,否則將面臨嚴厲懲罰。而我熟睡時,她連續發了五條訊息,我頓時背脊發涼,恐懼如潮水般湧來。
9:10:狗,我今天提前一天回程,下午三點半到家,四點準時到我家伺候。別讓我等!
9:20:怎麼不回訊息?敢無視我了?活膩了?
10:30:主人才離開幾天,你就放飛自我了?信不信我讓你後悔當我的狗?
11:30:再不回訊息,別怪我讓你生不如死!你的賤樣我有的是證據!
3:30:我到家了,還不回訊息?四點沒準時到,你就等著後悔活著吧!
她的語氣從冷淡到憤怒,每一句都像刀子刺進我的心。平時遲到半小時,我已被電擊得半死不活,如今遲了整整幾小時,我嚇得全身發抖,手忙腳亂地將剛錄的影片發給她,然後抓起電動車鑰匙,飛奔向她的公寓。我知道,無論如何懺悔,這次懲罰都無可避免。悔恨像毒藥吞噬我的心,昨晚的貪歡如今成了致命的錯誤。
更恐怖的念頭突然閃過腦海——主人提前回來,浴室裡還掛著那三件內褲!雖然我已將它們洗淨,精液的痕跡應該已被清除,但這些內褲本該鎖在麥語心臥室的收納箱裡,那片對我來說是絕對禁地的聖域。如今它們卻莫名出現在浴室,唯一的解釋是我闖入了她的臥室,並對內褲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清洗的痕跡反而成了我褻瀆的鐵證!她提前回來,必定已發現這一切。我的腦海裡閃過上次褻瀆內褲時的場景,她逼我寫下的悔過切結書,內容歷歷在目,像一把刀懸在我心頭:
悔過切結書
賤奴張小凡,因對主人麥語心之貼身衣物心生淫邪之念,褻瀆主人神聖之物,罪不可赦。承蒙主人施以重罰,賤奴痛徹心扉,真心悔悟,自此絕不再犯。若日後再對主人或其物品心存不敬或淫邪想法,賤奴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絕不推脫,誓言為證。
這份切結書如詛咒,字字刻在我心上。當時我跪在她面前,淚流滿面地簽下這份誓言,她的眼神冷酷如刀,警告我若再犯,必親手執行閹割。如今,我再次觸犯她的禁忌,浴室的內褲就是鐵證,她必定已知情。我的腦海裡閃過電擊棒的滋滋聲,皮鞭撕裂皮膚的劇痛,甚至那把冰冷的手術刀在她手中閃著寒光,準備執行我曾發下的毒誓。她的冷笑,她的怒火,像幽靈纏繞在我心頭,讓我背脊陣陣發涼,恐懼像無形的鎖鏈,勒緊我的喉嚨,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吞咽玻璃碴。
我竟然對一個女人如此恐懼,恐懼到連靈魂都在顫抖。忽然,一股溫熱的液體從下身蔓延,我低頭一看,內褲已濕透,竟是我的尿液。我竟然害怕到失禁了!羞恥和恐懼交織,我咬緊牙關,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可現實卻逼我繼續向前,奔向那無底的深淵。
抵達公寓樓下時,我雙腿軟得像棉花,幾乎站不穩。手機突然響起,是麥語心的視訊電話。我低頭一看,時間已是四點五分,我遲到了五分鐘!恐懼像洪水吞沒我,我慌張地掏出手機,手抖得像篩糠,不小心將手機摔在地上,螢幕在地上發出刺耳的撞擊聲。我趕忙撿起,顧不上擦去上面的灰塵,恭敬地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接通視訊。還沒等我開口,電話那頭傳來她憤怒的咆哮,像雷霆劈進我的腦海:「你這髒東西!垃圾!賤狗!你敢闖我臥室,碰我的內褲?!」
「我…我…」我竟然害怕得說不出話,喉嚨像被什麼堵住,想辯解卻只發出顫抖的氣音,在她憤怒的目光下,我只能瑟瑟發抖。她的眼神透過螢幕,像刀子刺穿我的靈魂,帶著毫不掩飾的鄙夷和怒火。「狗東西,現在四點十分,你給我三分鐘內滾到我面前!不然,我把你舔鞋底、喝尿的賤樣全公開,還送你進監獄,讓你這輩子都抬不起頭!」她語氣冷酷,字字如冰錐,說完便狠狠掛斷電話,螢幕瞬間黑了下來。
我愣在原地,腦子一片空白,恐懼像毒蛇鑽進我的骨髓,讓我全身冰冷。我知道,三分鐘內爬上五樓幾乎不可能,這次我站著進去,恐怕得躺著出來了。一個瘋狂的念頭閃過腦海——逃跑!就此離開,遠走高飛,逃離這無盡的奴役!可現實像鐵錘砸碎了這幻想。我身無分文,連換身衣服的錢都沒有。更何況,她手裡握著我的罪證,那些不堪入目的影片——我舔鞋底、喝她和她閨蜜的聖水,那些畫面一旦公開,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他們辛苦一輩子的臉面將被我徹底毀掉。我的腦海裡閃過父親佝僂的背影,母親滿是皺紋的雙手,他們為我付出了一切,而我卻淪為這般不堪的畜生。我不能讓他們蒙羞,不能讓他們因為我而抬不起頭!
我沒有選擇。明知是死路,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前。我拖著顫抖的雙腿,跌跌撞撞地衝進公寓樓,樓梯間的回音像在嘲笑我的絕望。我爬上五樓,肺像要炸開,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站在她公寓門口,我的手抖得幾乎握不住手機,汗水混著尿液的濕冷感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無地自容。我的腦海裡全是那份切結書,閹割的威脅像死神的鐮刀懸在頭頂,電擊棒的滋滋聲、皮鞭的撕裂聲、還有手術刀的寒光,像噩夢般輪番上演。我的雙腿顫抖得像篩子,恐懼吞噬了我的靈魂,我甚至感覺到下體的貞操鎖在顫抖,彷彿在預告即將到來的酷刑。我傳訊請示:「主人,賤奴到達,求您開門,允許這骯髒的狗進來接受您的審判。」她的回覆如地獄烈焰,充滿滔天怒火:「推門進來,狗!你這下賤的垃圾,敢褻瀆我的聖物,今天我非剝了你的皮不可!」
我推開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麥語心站在客廳中央,穿著黑色緊身上衣和短裙,氣場如女王般冷酷。她的眼神像刀,狠狠刺穿我,手裡握著一條帶刺的皮鞭,鞭梢在空中輕輕晃動,發出令人心悸的聲響。茶几上放著那三件內褲,整齊疊好,像一份罪證靜靜等待審判。我還沒來得及脫下衣服,她猛地甩出一鞭,鞭梢撕裂我的肩膀,鮮血瞬間滲出,痛得我縮成一團,癱倒在地。
「操你媽的死賤狗!竟然敢闖我臥室,褻瀆我的內褲,還是我最喜歡的那幾件!你這王八蛋!」她的聲音充滿新仇舊恨,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每一句都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連忙磕頭,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知錯…求您饒恕…」可我的道歉只換來更毒辣的鞭打,鞭梢如狂風暴雨,抽在我的背上、胸口,舊傷被撕裂,鮮血順著皮膚流下,滴在地上,發出細微的滴答聲。
「還不把衣服脫掉?在主人面前還敢穿衣服?進來前請安了嗎?連禮數都忘了?尊卑忘了?身分忘了?」她的怒罵如雷霆,我連忙爬起,邊挨鞭子邊脫衣服,手忙腳亂地扯下衣物,每脫下一件,鞭子就抽在裸露的皮膚上,留下一條條血痕。我咬緊牙,忍著劇痛,磕頭求饒:「主人…賤奴該死…賤奴知錯…」可她毫無憐憫,鞭子抽得更狠,彷彿要將我整個人撕碎。客廳的空氣瀰漫著血腥味,皮鞭的呼嘯聲和我的哀嚎交織,像一場殞烈的審判。
麥語心的怒火未消,她冷冷命令:「腰桿挺直!」我已被打得全身無力,聽到命令用盡吃奶的力氣勉強挺起腰,卻沒想到下體冷不防地被她狠狠踢了一腳。雖然隔著貞操鎖,這一腳的力道卻像錘子砸在我的命根子上,痛得我眼淚瞬間爆射而出,身體本能地蜷縮成一團,發出淒厲的哀嚎。她毫不停手,接連朝我的下體猛踹,即使我試圖護住命根,她卻無情地吼道:「把手拿開,你這賤狗,還敢擋?」
我因恐懼顫抖著緩緩挪開雙手,露出被貞操鎖禁錮的下體。麥語心抬起靴子,狠狠踩踏我的下體,靴尖碾壓著金屬鎖,痛得我全身痙攣。她一邊踩踏,一邊踢我的身體和臉頰,我像個沙包任由她毆打,無力反抗。她的嘲諷如刀,刺進我的靈魂:「你這骯髒齷齪的狗東西,就不配有這東西!我看到就噁心!你的切結書還記得吧?再犯就閹了你,今天就是你兌現誓言的時候!」她的話像死神的宣判,閹割的威脅讓我的心墜入無底深淵,恐懼和羞恥吞噬了我的靈魂。我試圖求饒,聲音沙啶得像在哀嚎:「主人…賤奴知錯…求您…別…」可話還沒說完,又是一腳踢在我的下巴,頭撞在地上,眼前一黑,意識模糊。
在麥語心無情的毆打下,我的身體像被撕碎的布偶,鮮血和汗水混雜,尿液的腥味從濕透的內褲傳來,讓我墮入無邊的絕望。最後一擊,她的靴子狠狠踩在我的胸口,力道大得讓我喘不過氣。我的視線漸漸模糊,耳邊只剩她的冷笑和嘲諷:「狗,你這賤東西,活著就是個錯誤。」
終於,劇痛和恐懼將我吞沒,我暈厥過去,靈魂像被拖進無盡的黑暗深淵,無處可逃。
这个点怎么睡得着的,起来更👿
第二十章 沒有選擇
黑暗中,一盆冰水兜頭澆下,刺骨的寒意瞬間將我從昏厥中驚醒。我猛地抽搐,意識像被撕裂的布片,勉強拼湊出殞烈的現實。客廳的地板冰冷刺骨,血腥味混雜著尿液的腥臭,提醒我剛才的噩夢並非幻覺。我的背上、肩膀佈滿鞭痕,鮮血凝固成黏稠的痕跡,下體的貞操鎖傳來陣陣脹痛,彷彿還殞留著麥語心靴尖的碾壓。我試著動彈,卻發現四肢無力,喉嚨乾涸得像吞了沙子,發不出半點聲音。
麥語心站在我面前,手中拿著一個空水桶,眼神冷酷如冰,帶著一絲疲憊卻不減的怒火。她剛剛的毆打似乎耗費了不少力氣,微微喘著氣,隨手將水桶扔到一旁,坐回沙發,喝了一口桌上的礦泉水。她的動作緩慢,卻透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像一隻玩弄獵物的猛獸,隨時準備給予致命一擊。她從茶几旁抽出一張泛黃的紙,緩緩展開,嘴角揚起一抹嘲弄的弧度。「狗,你知道這是什麼吧?」她的聲音平靜,卻像刀子刺進我的心。
我顫抖著抬起頭,目光落在她手中的紙上——那份悔過切結書,字字如刀,刻在我心上。我的喉嚨一緊,恐懼像毒蛇鑽進骨髓,背脊陣陣發涼。那份誓言的內容在我腦海中閃現,特別是「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幾個字,像死神的鐮刀懸在頭頂。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聲音沙啞得像在哀嚎:「主人…賤奴知錯…求您…饒了我…」
「饒你?」麥語心冷笑,靴尖踢了踢我的下巴,逼我抬起頭。她的目光如刀,刺進我的靈魂。「你這骯髒的垃圾,敢闖我臥室,褻瀆我的內褲,還想求饒?給我把這份切結書大聲念出來!讓我聽聽你這賤狗有多後悔!」她將紙扔在我面前,語氣裡滿是嘲諷,像在撕開我的傷口撒鹽。
我顫抖著撿起切結書,手抖得幾乎拿不穩,低頭看著上面的文字,心如刀絞。我深吸一口氣,開始大聲朗誦,聲音顫抖卻力求清晰:
「賤奴張小凡,因對主人麥語心之貼身衣物心生淫邪之念,褻瀆主人神聖之物,罪不可赦。承蒙主人施以重罰,賤奴痛徹心扉,真心悔悟,自此絕不再犯。若日後再對主人或其物品心存不敬或淫邪想法,賤奴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絕不推脫,誓言為證。」
每念一字,我的心就沉一分,閹割的威脅像鐵錘砸在胸口,羞恥和恐懼交織,讓我幾乎窒息。麥語心冷笑連連,不斷打斷我,羞辱的話像鞭子抽在我的靈魂上:「狗,你還有臉念?上次簽這東西的時候,你不是信誓旦旦說不會再犯?現在呢?又爬進我臥室,碰我的內褲!你這賤東西,連狗都不如!」她頓了頓,語氣更冷:「念慢點!一字一句,讓我聽清楚你這賤狗的誓言!」
我咬緊牙,忍著喉嚨的哽咽,重新一字一句念完,額頭的汗水混著血水滴在地上。念完後,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知錯…賤奴保證不再犯…求您…饒了我…」我試圖保住最後一絲尊嚴——我的命根子,那是我作為男人僅存的證明。我的腦海裡閃過手術刀的寒光,電擊棒的滋滋聲,還有她上次懲罰時的冷笑,恐懼像潮水淹沒我,讓我連呼吸都覺得沉重。
麥語心卻毫無憐憫,她站起身,緩緩走近我,靴尖輕輕碾壓我的手指,痛得我全身一顫。「饒你?狗,你以為你還有資格求饒?」她的語氣冰冷,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你褻瀆了我的聖物,違反了奴隸條款最重的罪!按規矩,我該當場閹了你,然後把你扔進監獄,讓你這輩子都抬不起頭!」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抹腹黑的光芒。「不過,我給你個選擇——三天內,給我擬一份閹割計畫,費用你自己出,每天的工資照樣上繳,怎麼生錢,你自己想辦法!不想花錢?那就找個地方自己動手,把你那髒東西閹了,別弄髒我的地方!或者,我現在就把你舔鞋底、喝聖水的賤樣影片公開,再送你去坐牢!選吧,狗!這次,我絕不妥協!」
她的話像雷霆,擊碎了我最後的希望。我試著提出彌補方式,聲音顫抖得像在哀求:「主人…賤奴願意加倍工作…把所有收入都給您…賤奴願意做任何事…求您…別閹我…別公開影片…」可她只是冷笑,毫不留情地打斷我:「加倍工作?狗,你這賤東西的錢本來就是我的!做任何事?你連我的鞋底都不配舔,還談什麼彌補?」我又提出願意接受更重的鞭打、電擊,甚至公開羞辱,可她一一拒絕,語氣越來越冷:「你的罪孽已經無法刷洗,狗!從今天起,你的地位低於地板上的塵埃!我的鞋底、聖水,你這賤東西都不配碰!」
我愣在原地,心如死灰,只能匍匐在地,聲音低得像在懺悔:「賤奴…接受主人的審判…」我別無選擇,閹割的威脅像鐵鏈鎖住我的靈魂,公開影片的恐懼讓我連反抗的念頭都不敢有。我的家人、父母的面容在我腦海裡閃過,他們的期望如今被我徹底碾碎,我連死的勇氣都沒有,只能接受這殞烈的審判。
本以為麥語心的怒火已發洩殆盡,我可以拖著滿身傷痕離開,可她突然皺起眉,鼻子輕輕抽動,像是嗅到了什麼。她低頭看向我脫下的衣物,緩緩走近,俯身一聞,臉色瞬間陰沉下來。她猛地抬起頭,眼神燃著熊熊怒火,質問道:「操你媽的死賤狗!你在我家尿尿?!」
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磕頭,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絕對沒有…是…是因為犯了錯,害怕得沒控制住,在外面…在外面尿了…絕對不是在您家…」我試著解釋,可話語蒼白無力,尿液的腥臭從內褲傳來,像罪證般讓我無處遁形。麥語心根本不聽,怒吼道:「賤狗!來見主人前連這點事都處理不好?你這骯髒的東西,應該在外面把褲子脫了,或者自己解決掉!這又是褻瀆之罪!」
她伸手想拿起藤鞭,可剛剛的毆打讓她手臂酸軟,數鞭下去,力道已不如先前。她冷哼一聲,扔下藤鞭,換了種更屈辱的懲罰。「狗,既然你這麼賤,三天內,每天工作完後,給我跪在公寓門口懺悔!從傍晚六點到晚上十點,一分鐘都不許少!讓所有人都看看你這賤狗的德性!」她的語氣冰冷,帶著毫不掩飾的嘲弄。
我心頭一震,羞恥像火焰燒遍全身,連忙磕頭哀求:「主人…求您…別讓賤奴做這麼丟人的事…賤奴願意接受其他懲罰…求您…」可她只是冷笑,靴尖踢了踢我的臉:「丟人?狗,你還有臉談丟人?這已經是最輕的懲罰了!不服?那我現在就公開你的影片!」她的威脅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只能低頭,聲音哽咽:「賤奴…遵命…」
她還沒完,語氣突然變得更冷,眼中閃過一抹陰險的光芒。「狗,別以為這就完了。一週後,我會給你更嚴厲的懲罰!閹割、公然羞辱,還有比這更重的刑罰!你的罪太滔天,褻瀆了我,違反了奴隸條款最重的禁忌!本該當場閹了你,再送你進監獄!但你這賤東西還有點用處,所以我才留你這條狗命!」她的話像鐵錘,砸碎了我最後的希望。我的背脊冰冷刺痛,恐懼像無邊的黑暗將我吞噬,一週後的懲罰像幽靈,纏繞在我心頭,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
麥語心揮揮手,示意我滾出去。我拖著滿身傷痕,踉蹌地爬出公寓,鮮血和汗水順著皮膚流下,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想死。外面的夜風冷得刺骨,我騎上那輛輪胎幾乎磨平的電動車,開始瘋狂接單。城市的霓虹燈在黑暗中模糊,像一幅永遠觸不到的畫。我的雙腿酸痛得像灌了鉛,背上的鞭痕被汗水浸得火燒般刺痛,但我只能咬牙堅持。我知道,無論我多努力,三天內賺到閹割費用的錢、每天跪在公寓門口的羞辱、還有即將到來的一週後的酷刑,都是我無法逃脫的命運。
黑暗中,一盆冰水兜頭澆下,刺骨的寒意瞬間將我從昏厥中驚醒。我猛地抽搐,意識像被撕裂的布片,勉強拼湊出殞烈的現實。客廳的地板冰冷刺骨,血腥味混雜著尿液的腥臭,提醒我剛才的噩夢並非幻覺。我的背上、肩膀佈滿鞭痕,鮮血凝固成黏稠的痕跡,下體的貞操鎖傳來陣陣脹痛,彷彿還殞留著麥語心靴尖的碾壓。我試著動彈,卻發現四肢無力,喉嚨乾涸得像吞了沙子,發不出半點聲音。
麥語心站在我面前,手中拿著一個空水桶,眼神冷酷如冰,帶著一絲疲憊卻不減的怒火。她剛剛的毆打似乎耗費了不少力氣,微微喘著氣,隨手將水桶扔到一旁,坐回沙發,喝了一口桌上的礦泉水。她的動作緩慢,卻透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像一隻玩弄獵物的猛獸,隨時準備給予致命一擊。她從茶几旁抽出一張泛黃的紙,緩緩展開,嘴角揚起一抹嘲弄的弧度。「狗,你知道這是什麼吧?」她的聲音平靜,卻像刀子刺進我的心。
我顫抖著抬起頭,目光落在她手中的紙上——那份悔過切結書,字字如刀,刻在我心上。我的喉嚨一緊,恐懼像毒蛇鑽進骨髓,背脊陣陣發涼。那份誓言的內容在我腦海中閃現,特別是「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幾個字,像死神的鐮刀懸在頭頂。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聲音沙啞得像在哀嚎:「主人…賤奴知錯…求您…饒了我…」
「饒你?」麥語心冷笑,靴尖踢了踢我的下巴,逼我抬起頭。她的目光如刀,刺進我的靈魂。「你這骯髒的垃圾,敢闖我臥室,褻瀆我的內褲,還想求饒?給我把這份切結書大聲念出來!讓我聽聽你這賤狗有多後悔!」她將紙扔在我面前,語氣裡滿是嘲諷,像在撕開我的傷口撒鹽。
我顫抖著撿起切結書,手抖得幾乎拿不穩,低頭看著上面的文字,心如刀絞。我深吸一口氣,開始大聲朗誦,聲音顫抖卻力求清晰:
「賤奴張小凡,因對主人麥語心之貼身衣物心生淫邪之念,褻瀆主人神聖之物,罪不可赦。承蒙主人施以重罰,賤奴痛徹心扉,真心悔悟,自此絕不再犯。若日後再對主人或其物品心存不敬或淫邪想法,賤奴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絕不推脫,誓言為證。」
每念一字,我的心就沉一分,閹割的威脅像鐵錘砸在胸口,羞恥和恐懼交織,讓我幾乎窒息。麥語心冷笑連連,不斷打斷我,羞辱的話像鞭子抽在我的靈魂上:「狗,你還有臉念?上次簽這東西的時候,你不是信誓旦旦說不會再犯?現在呢?又爬進我臥室,碰我的內褲!你這賤東西,連狗都不如!」她頓了頓,語氣更冷:「念慢點!一字一句,讓我聽清楚你這賤狗的誓言!」
我咬緊牙,忍著喉嚨的哽咽,重新一字一句念完,額頭的汗水混著血水滴在地上。念完後,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知錯…賤奴保證不再犯…求您…饒了我…」我試圖保住最後一絲尊嚴——我的命根子,那是我作為男人僅存的證明。我的腦海裡閃過手術刀的寒光,電擊棒的滋滋聲,還有她上次懲罰時的冷笑,恐懼像潮水淹沒我,讓我連呼吸都覺得沉重。
麥語心卻毫無憐憫,她站起身,緩緩走近我,靴尖輕輕碾壓我的手指,痛得我全身一顫。「饒你?狗,你以為你還有資格求饒?」她的語氣冰冷,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你褻瀆了我的聖物,違反了奴隸條款最重的罪!按規矩,我該當場閹了你,然後把你扔進監獄,讓你這輩子都抬不起頭!」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抹腹黑的光芒。「不過,我給你個選擇——三天內,給我擬一份閹割計畫,費用你自己出,每天的工資照樣上繳,怎麼生錢,你自己想辦法!不想花錢?那就找個地方自己動手,把你那髒東西閹了,別弄髒我的地方!或者,我現在就把你舔鞋底、喝聖水的賤樣影片公開,再送你去坐牢!選吧,狗!這次,我絕不妥協!」
她的話像雷霆,擊碎了我最後的希望。我試著提出彌補方式,聲音顫抖得像在哀求:「主人…賤奴願意加倍工作…把所有收入都給您…賤奴願意做任何事…求您…別閹我…別公開影片…」可她只是冷笑,毫不留情地打斷我:「加倍工作?狗,你這賤東西的錢本來就是我的!做任何事?你連我的鞋底都不配舔,還談什麼彌補?」我又提出願意接受更重的鞭打、電擊,甚至公開羞辱,可她一一拒絕,語氣越來越冷:「你的罪孽已經無法刷洗,狗!從今天起,你的地位低於地板上的塵埃!我的鞋底、聖水,你這賤東西都不配碰!」
我愣在原地,心如死灰,只能匍匐在地,聲音低得像在懺悔:「賤奴…接受主人的審判…」我別無選擇,閹割的威脅像鐵鏈鎖住我的靈魂,公開影片的恐懼讓我連反抗的念頭都不敢有。我的家人、父母的面容在我腦海裡閃過,他們的期望如今被我徹底碾碎,我連死的勇氣都沒有,只能接受這殞烈的審判。
本以為麥語心的怒火已發洩殆盡,我可以拖著滿身傷痕離開,可她突然皺起眉,鼻子輕輕抽動,像是嗅到了什麼。她低頭看向我脫下的衣物,緩緩走近,俯身一聞,臉色瞬間陰沉下來。她猛地抬起頭,眼神燃著熊熊怒火,質問道:「操你媽的死賤狗!你在我家尿尿?!」
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磕頭,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絕對沒有…是…是因為犯了錯,害怕得沒控制住,在外面…在外面尿了…絕對不是在您家…」我試著解釋,可話語蒼白無力,尿液的腥臭從內褲傳來,像罪證般讓我無處遁形。麥語心根本不聽,怒吼道:「賤狗!來見主人前連這點事都處理不好?你這骯髒的東西,應該在外面把褲子脫了,或者自己解決掉!這又是褻瀆之罪!」
她伸手想拿起藤鞭,可剛剛的毆打讓她手臂酸軟,數鞭下去,力道已不如先前。她冷哼一聲,扔下藤鞭,換了種更屈辱的懲罰。「狗,既然你這麼賤,三天內,每天工作完後,給我跪在公寓門口懺悔!從傍晚六點到晚上十點,一分鐘都不許少!讓所有人都看看你這賤狗的德性!」她的語氣冰冷,帶著毫不掩飾的嘲弄。
我心頭一震,羞恥像火焰燒遍全身,連忙磕頭哀求:「主人…求您…別讓賤奴做這麼丟人的事…賤奴願意接受其他懲罰…求您…」可她只是冷笑,靴尖踢了踢我的臉:「丟人?狗,你還有臉談丟人?這已經是最輕的懲罰了!不服?那我現在就公開你的影片!」她的威脅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只能低頭,聲音哽咽:「賤奴…遵命…」
她還沒完,語氣突然變得更冷,眼中閃過一抹陰險的光芒。「狗,別以為這就完了。一週後,我會給你更嚴厲的懲罰!閹割、公然羞辱,還有比這更重的刑罰!你的罪太滔天,褻瀆了我,違反了奴隸條款最重的禁忌!本該當場閹了你,再送你進監獄!但你這賤東西還有點用處,所以我才留你這條狗命!」她的話像鐵錘,砸碎了我最後的希望。我的背脊冰冷刺痛,恐懼像無邊的黑暗將我吞噬,一週後的懲罰像幽靈,纏繞在我心頭,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
麥語心揮揮手,示意我滾出去。我拖著滿身傷痕,踉蹌地爬出公寓,鮮血和汗水順著皮膚流下,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想死。外面的夜風冷得刺骨,我騎上那輛輪胎幾乎磨平的電動車,開始瘋狂接單。城市的霓虹燈在黑暗中模糊,像一幅永遠觸不到的畫。我的雙腿酸痛得像灌了鉛,背上的鞭痕被汗水浸得火燒般刺痛,但我只能咬牙堅持。我知道,無論我多努力,三天內賺到閹割費用的錢、每天跪在公寓門口的羞辱、還有即將到來的一週後的酷刑,都是我無法逃脫的命運。
第二十章 羞辱的刑罰
清晨的宿舍依然籠罩在薄霧中,窗外的陽光冷得像刀,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滿是傷痕的身上。昨晚麥語心的毒打像烙鐵燒進我的靈魂,背上的鞭痕滲著血,黏膩地貼著破舊的床單,下體的貞操鎖傳來陣陣脹痛,彷彿還殞留著她靴尖的碾壓。我拖著殞傷的身體爬下床,膝蓋一軟,險些摔倒。鏡子裡的我,滿臉瘀青,眼神空洞,像一具沒有靈魂的傀儡。我咬緊牙,錄下向主人的請安影片,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主人,賤奴張小凡向您請安,祝您今天心情愉快…」
發送影片後,我換上那件已被汗水浸透的外送制服,尿液的腥味從昨晚濕透的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無地自容。我沒時間洗澡,也不敢浪費一分鐘,因為麥語心的命令像鐵鏈,勒緊我的每一個動作。我騎上那輛輪胎幾乎磨平的電動車,穿梭在吵鬧喧雜的城市,面無表情地奔波在街頭巷尾。車流與喇叭聲如洪水將我淹沒,但我毫無感覺,我的腦子早已被三天後的酷刑和未來閹割的恐懼佔滿,靈魂像被無邊的黑暗吞噬。
上午十點二十分,手機震動了一下,我心頭一緊,低頭一看,是麥語心的訊息:「狗,記得你的懲罰。今天下午五點,我要看到你跪在我家樓下,好好懺悔。別讓我失望!」她的語氣冷酷,字裡行間透著不容反抗的威嚴。我的心猛地一縮,閹割的陰影和公開羞辱的屈辱讓我幾乎無法呼吸。我無心細想,手指顫抖著回覆:「賤奴知道了,賤奴會準時到。」我以為這已經足夠,可幾秒後,她又發來一條訊息,語氣陡然變得尖銳:「你他媽是這樣跟主人說話的?狗東西,連基本的禮數都忘了?」
我嚇得魂飛魄散,意識到自己忘了用最卑微的語氣,忘了在回覆中加上「主人」和「賤奴」的敬稱。我連忙跪在路邊,顧不上周圍路人詫異的目光,顫抖著打字:「主人,賤奴知錯!賤奴該死,剛才在跑單,愚蠢地忽略了禮數!賤奴已悔悟,求主人寬恕賤奴的無禮!」我屏住呼吸,等待她的回覆,心跳快得像要炸開。幾分鐘後,她回道:「我的氣還沒消,你這賤雜種!以為求饒就夠了?下午五點,給我跪得規矩點,不然我讓你知道什麼叫生不如死!」
我低頭看著螢幕,羞恥和恐懼交織,只能繼續乞求:「主人,賤奴罪該萬死,賤奴一定規規矩矩懺悔,求主人息怒…」我發出一條又一條訊息,卑微得像一條真正的狗,可她只是冷冷回了一句:「滾去賺錢,狗!別讓我再看到你這賤樣!」便沒再回復。我愣在原地,猜想她或許去忙了,但她的怒火像火焰,燒得我無處可逃。
我拖著沉重的身體繼續送單,城市的喧囂在我耳邊變得模糊,腦子裡全是麥語心的命令和那份切結書的陰影。閹割的威脅像幽靈纏繞,昨晚她讓我三天內擬定閹割計畫的畫面在我腦海重播,她冷笑著說「自己動手,別弄髒我的地方」的語氣,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我試著想像手術刀切開皮膚的冰冷觸感,鮮血與劇痛吞噬我的畫面,恐懼讓我的手抖得幾乎握不住車把。我竟然對一個女人怕到這種地步,怕到連靈魂都在顫抖,怕到昨晚失禁的羞恥還在我內褲上殞留,腥臭刺鼻。
中午的訂單高峰讓我喘不過氣,我瘋狂地穿梭在高樓與巷弄,汗水浸濕鞭痕,火燒般的痛楚讓我咬緊牙關。顧客的抱怨、紅燈的等待,都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我的腦海裡閃過父母的面容,他們佝僂的身影,滿是皺紋的雙手,若他們知道我淪為這般不堪的畜生,會不會連看都不願看我一眼?我試著甩開這些念頭,可麥語心的聲音像詛咒,縈繞不去:「狗,你這賤東西,活著就是個錯誤。」
下午四點,我提前趕到麥語心的公寓樓下,雙腿酸痛得像灌了鉛,背上的傷口被汗水浸得刺痛。我站在樓下,望著那扇熟悉的鐵門,心跳快得像要炸開。公開懺悔的屈辱像一把刀懸在頭頂,我試著想像自己跪在這裡,路人投來的目光,竊竊私語的嘲笑,甚至可能有認識的同學經過,認出我這條賤狗的模樣。我的胃一陣翻騰,羞恥和恐懼交織,讓我幾乎想掉頭逃跑。可我無處可逃,她手裡的影片、那份切結書,都是鎖住我的鐵鏈,我連死的資格都沒有。
五點整,我跪在公寓樓下的水泥地上,膝蓋硌得生疼,頭低得幾乎貼地,雙手恭敬地放在膝前,像一條真正的狗。我不敢抬頭,怕看到路人的目光,怕看到麥語心從窗戶俯視我的冷笑。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張小凡,罪不可赦,褻瀆主人神聖之物,求主人寬恕…」我的聲音在空氣中飄散,被風聲和車流吞沒,卻像刀子割在我的心上。每說一句,我的心就沉一分,尊嚴像被碾碎的塵埃,隨風消散。
路人經過,有人駐足,有人竊笑,有人低聲議論:「這傢伙在幹嘛?瘋了吧?」我咬緊牙,額頭滲出冷汗,羞恥如火焰燒遍全身。我試著麻痺自己,告訴自己這只是懲罰,總會過去,可麥語心的命令像鐵錘砸在我的腦海:三天,每天四小時,公開懺悔。我的靈魂像被剝離,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她的腳下。
直到傍晚,麥語心才傳來訊息,命令我上公寓找她。我傳訊請示:「主人,賤奴懺悔完畢,求您允許賤奴進入服侍。」她的回覆簡單而冰冷:「進來,狗。」我拖著麻木的雙腿,爬上五樓,推開公寓大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我脫光衣服,赤裸地跪在玄關,將她的拖鞋恭敬地置於我的衣物上方,緩慢爬進客廳,頭低得不敢抬。
麥語心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穿著黑色緊身上衣和短裙,氣場如女王般冷酷。她低頭看著我,眼神帶著嘲弄,手中把玩著手機,像是隨時能按下某個致命的鍵。我跪在她面前,鼻尖幾乎貼地,汗水混著血水滴在地上。她先開口,語氣平靜卻透著威嚴:「狗,今天的收入呢?」
我連忙將手機遞到她手上,恭敬回報:「主人,賤奴今天賺了五百塊,求主人查收。」她接過手機,隨意翻看了幾眼,確認我沒有虛報或隱瞞後,將錢轉進她的戶頭。她放下手機,目光掃過我,嘴角揚起一抹冷笑。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腳上的拖鞋,粉紅色的絨毛拖鞋,曾被我舔過無數次,如今卻成了我再也無資格觸碰的禁地。我不自覺地吞了口口水,這細微的動作被她捕捉到,她譏諷道:「想舔?狗,你以為你還有資格替我舔鞋?因為你的過錯,你連我鞋底的灰都不配碰!」
我心頭一震,羞恥如潮水湧來,連忙磕頭,聲音哽咽:「主人…賤奴知錯…賤奴罪該萬死,求主人寬恕…」我試圖乞求她的憐憫,可這反而激怒了她。她猛地起身,一腳踹在我的肩膀,力道讓我摔倒在地,鞭痕被扯裂,鮮血滲出,痛得我咬緊牙關。她俯視我,語氣充滿鄙夷:「你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還敢要求?你配嗎?」
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賤奴該死…賤奴不敢要求…求主人息怒…」可她毫無憐憫,抬起腳,狠狠踩在我的頭上,靴跟碾壓著我的額頭,力道大得讓我頭皮發麻,額頭瞬間紅腫,瘀痕刺眼。她彎下腰,湊近我,語氣帶著致命的威脅:「賤狗,你是不是不只褻瀆了三條內褲?」
我嚇得渾身發抖,恐懼如冰水澆遍全身,背脊冰冷刺痛。她的眼神如刀,刺進我的靈魂,彷彿早已看穿一切。我試著否認,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賤奴只…只碰了三條…」可她猛地一腳踢在我的肋骨,痛得我蜷縮在地,喘不過氣。「撒謊?」她怒吼,聲音如雷霆,「你最好從實交代!不然,今天我不送你進監獄,我就不叫麥語心!」
她的威脅如鐵錘砸碎我的防線,我知道再隱瞞只會換來更殞烈的懲罰。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聲音低得像在懺悔:「主人…賤奴該死…賤奴…賤奴還偷了兩條內褲…藏在宿舍…賤奴馬上歸還…求主人饒命…」我將真相全盤托出,心如死灰,閹割的陰影和監獄的恐懼讓我連抬頭的勇氣都沒有。
麥語心聽完,臉色陰沉得如暴風雨前的天空,眼中燃著熊熊怒火。她冷笑,語氣充滿嘲弄:「五條內褲?狗,你膽子真是大到天上去了!我的收納箱全被你這髒東西碰過,全部得丟!說,你怎麼賠償?」我顫抖著回道:「主人…賤奴願意加倍工作…賠償您的損失…」可她嗤笑,打斷我:「你這畜生的錢本來就是我的!我用自己的錢賠自己?」
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主人…賤奴不是這意思…賤奴…」她冷冷質問:「你有錢嗎?你連閹割的費用都拿不出來,對吧?」我低頭,卑微地回答:「是…賤奴…賤奴沒錢…」她高冷地俯視我,語氣冰冷如刀:「賠償肯定是要賠的,閹割也是要閹的,這幾點一點都不妥協!三天內,把那兩條內褲還回來,閹割計畫也給我擬好!不然,你這賤狗的下場,比監獄還慘!」
我愣在原地,恐懼如無邊的黑暗將我吞噬,心像被撕裂。我試著求饒,聲音沙啞得如哀嚎:「主人…賤奴知錯…求您…給賤奴一條活路…」可她只是冷笑,靴尖踢了踢我的臉:「活路?狗,你這輩子都得匍匐在我腳下!滾回去,明天繼續跪!別讓我再抓到你的把柄!」
我拖著滿身傷痕,踉蹌地爬出公寓,夜風冷得刺骨,鮮血和汗水順著皮膚流下,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想死。我騎上電動車,腦子裡全是她的冷笑、閹割的威脅,還有那兩條藏在宿舍的內褲,像罪證壓得我喘不過氣。我的內心開始自問自答,像一個瘋子在與自己爭執:「張小凡,你怎麼會淪落到這地步?為什麼要偷那兩條內褲?為什麼要一錯再錯?」我的心像被撕裂,悔恨如毒藥吞噬我。我試著想像父母知道我被閹割的畫面,他們失望的眼神,母親的淚水,父親的沉默,像刀子刺進我的胸口。我低聲自語,聲音顫抖得像在哭:「我該怎麼辦…三天後的懲罰…閹割…我逃不掉…我連死的資格都沒有…」恐懼讓我全身顫抖,腦海裡閃過手術刀的寒光,麥語心冷笑著說「自己動手」的畫面,讓我幾乎崩潰。我閉上眼,淚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已經無路可退。
清晨的宿舍依然籠罩在薄霧中,窗外的陽光冷得像刀,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滿是傷痕的身上。昨晚麥語心的毒打像烙鐵燒進我的靈魂,背上的鞭痕滲著血,黏膩地貼著破舊的床單,下體的貞操鎖傳來陣陣脹痛,彷彿還殞留著她靴尖的碾壓。我拖著殞傷的身體爬下床,膝蓋一軟,險些摔倒。鏡子裡的我,滿臉瘀青,眼神空洞,像一具沒有靈魂的傀儡。我咬緊牙,錄下向主人的請安影片,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主人,賤奴張小凡向您請安,祝您今天心情愉快…」
發送影片後,我換上那件已被汗水浸透的外送制服,尿液的腥味從昨晚濕透的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無地自容。我沒時間洗澡,也不敢浪費一分鐘,因為麥語心的命令像鐵鏈,勒緊我的每一個動作。我騎上那輛輪胎幾乎磨平的電動車,穿梭在吵鬧喧雜的城市,面無表情地奔波在街頭巷尾。車流與喇叭聲如洪水將我淹沒,但我毫無感覺,我的腦子早已被三天後的酷刑和未來閹割的恐懼佔滿,靈魂像被無邊的黑暗吞噬。
上午十點二十分,手機震動了一下,我心頭一緊,低頭一看,是麥語心的訊息:「狗,記得你的懲罰。今天下午五點,我要看到你跪在我家樓下,好好懺悔。別讓我失望!」她的語氣冷酷,字裡行間透著不容反抗的威嚴。我的心猛地一縮,閹割的陰影和公開羞辱的屈辱讓我幾乎無法呼吸。我無心細想,手指顫抖著回覆:「賤奴知道了,賤奴會準時到。」我以為這已經足夠,可幾秒後,她又發來一條訊息,語氣陡然變得尖銳:「你他媽是這樣跟主人說話的?狗東西,連基本的禮數都忘了?」
我嚇得魂飛魄散,意識到自己忘了用最卑微的語氣,忘了在回覆中加上「主人」和「賤奴」的敬稱。我連忙跪在路邊,顧不上周圍路人詫異的目光,顫抖著打字:「主人,賤奴知錯!賤奴該死,剛才在跑單,愚蠢地忽略了禮數!賤奴已悔悟,求主人寬恕賤奴的無禮!」我屏住呼吸,等待她的回覆,心跳快得像要炸開。幾分鐘後,她回道:「我的氣還沒消,你這賤雜種!以為求饒就夠了?下午五點,給我跪得規矩點,不然我讓你知道什麼叫生不如死!」
我低頭看著螢幕,羞恥和恐懼交織,只能繼續乞求:「主人,賤奴罪該萬死,賤奴一定規規矩矩懺悔,求主人息怒…」我發出一條又一條訊息,卑微得像一條真正的狗,可她只是冷冷回了一句:「滾去賺錢,狗!別讓我再看到你這賤樣!」便沒再回復。我愣在原地,猜想她或許去忙了,但她的怒火像火焰,燒得我無處可逃。
我拖著沉重的身體繼續送單,城市的喧囂在我耳邊變得模糊,腦子裡全是麥語心的命令和那份切結書的陰影。閹割的威脅像幽靈纏繞,昨晚她讓我三天內擬定閹割計畫的畫面在我腦海重播,她冷笑著說「自己動手,別弄髒我的地方」的語氣,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我試著想像手術刀切開皮膚的冰冷觸感,鮮血與劇痛吞噬我的畫面,恐懼讓我的手抖得幾乎握不住車把。我竟然對一個女人怕到這種地步,怕到連靈魂都在顫抖,怕到昨晚失禁的羞恥還在我內褲上殞留,腥臭刺鼻。
中午的訂單高峰讓我喘不過氣,我瘋狂地穿梭在高樓與巷弄,汗水浸濕鞭痕,火燒般的痛楚讓我咬緊牙關。顧客的抱怨、紅燈的等待,都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我的腦海裡閃過父母的面容,他們佝僂的身影,滿是皺紋的雙手,若他們知道我淪為這般不堪的畜生,會不會連看都不願看我一眼?我試著甩開這些念頭,可麥語心的聲音像詛咒,縈繞不去:「狗,你這賤東西,活著就是個錯誤。」
下午四點,我提前趕到麥語心的公寓樓下,雙腿酸痛得像灌了鉛,背上的傷口被汗水浸得刺痛。我站在樓下,望著那扇熟悉的鐵門,心跳快得像要炸開。公開懺悔的屈辱像一把刀懸在頭頂,我試著想像自己跪在這裡,路人投來的目光,竊竊私語的嘲笑,甚至可能有認識的同學經過,認出我這條賤狗的模樣。我的胃一陣翻騰,羞恥和恐懼交織,讓我幾乎想掉頭逃跑。可我無處可逃,她手裡的影片、那份切結書,都是鎖住我的鐵鏈,我連死的資格都沒有。
五點整,我跪在公寓樓下的水泥地上,膝蓋硌得生疼,頭低得幾乎貼地,雙手恭敬地放在膝前,像一條真正的狗。我不敢抬頭,怕看到路人的目光,怕看到麥語心從窗戶俯視我的冷笑。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張小凡,罪不可赦,褻瀆主人神聖之物,求主人寬恕…」我的聲音在空氣中飄散,被風聲和車流吞沒,卻像刀子割在我的心上。每說一句,我的心就沉一分,尊嚴像被碾碎的塵埃,隨風消散。
路人經過,有人駐足,有人竊笑,有人低聲議論:「這傢伙在幹嘛?瘋了吧?」我咬緊牙,額頭滲出冷汗,羞恥如火焰燒遍全身。我試著麻痺自己,告訴自己這只是懲罰,總會過去,可麥語心的命令像鐵錘砸在我的腦海:三天,每天四小時,公開懺悔。我的靈魂像被剝離,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她的腳下。
直到傍晚,麥語心才傳來訊息,命令我上公寓找她。我傳訊請示:「主人,賤奴懺悔完畢,求您允許賤奴進入服侍。」她的回覆簡單而冰冷:「進來,狗。」我拖著麻木的雙腿,爬上五樓,推開公寓大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我脫光衣服,赤裸地跪在玄關,將她的拖鞋恭敬地置於我的衣物上方,緩慢爬進客廳,頭低得不敢抬。
麥語心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穿著黑色緊身上衣和短裙,氣場如女王般冷酷。她低頭看著我,眼神帶著嘲弄,手中把玩著手機,像是隨時能按下某個致命的鍵。我跪在她面前,鼻尖幾乎貼地,汗水混著血水滴在地上。她先開口,語氣平靜卻透著威嚴:「狗,今天的收入呢?」
我連忙將手機遞到她手上,恭敬回報:「主人,賤奴今天賺了五百塊,求主人查收。」她接過手機,隨意翻看了幾眼,確認我沒有虛報或隱瞞後,將錢轉進她的戶頭。她放下手機,目光掃過我,嘴角揚起一抹冷笑。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腳上的拖鞋,粉紅色的絨毛拖鞋,曾被我舔過無數次,如今卻成了我再也無資格觸碰的禁地。我不自覺地吞了口口水,這細微的動作被她捕捉到,她譏諷道:「想舔?狗,你以為你還有資格替我舔鞋?因為你的過錯,你連我鞋底的灰都不配碰!」
我心頭一震,羞恥如潮水湧來,連忙磕頭,聲音哽咽:「主人…賤奴知錯…賤奴罪該萬死,求主人寬恕…」我試圖乞求她的憐憫,可這反而激怒了她。她猛地起身,一腳踹在我的肩膀,力道讓我摔倒在地,鞭痕被扯裂,鮮血滲出,痛得我咬緊牙關。她俯視我,語氣充滿鄙夷:「你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還敢要求?你配嗎?」
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賤奴該死…賤奴不敢要求…求主人息怒…」可她毫無憐憫,抬起腳,狠狠踩在我的頭上,靴跟碾壓著我的額頭,力道大得讓我頭皮發麻,額頭瞬間紅腫,瘀痕刺眼。她彎下腰,湊近我,語氣帶著致命的威脅:「賤狗,你是不是不只褻瀆了三條內褲?」
我嚇得渾身發抖,恐懼如冰水澆遍全身,背脊冰冷刺痛。她的眼神如刀,刺進我的靈魂,彷彿早已看穿一切。我試著否認,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賤奴只…只碰了三條…」可她猛地一腳踢在我的肋骨,痛得我蜷縮在地,喘不過氣。「撒謊?」她怒吼,聲音如雷霆,「你最好從實交代!不然,今天我不送你進監獄,我就不叫麥語心!」
她的威脅如鐵錘砸碎我的防線,我知道再隱瞞只會換來更殞烈的懲罰。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聲音低得像在懺悔:「主人…賤奴該死…賤奴…賤奴還偷了兩條內褲…藏在宿舍…賤奴馬上歸還…求主人饒命…」我將真相全盤托出,心如死灰,閹割的陰影和監獄的恐懼讓我連抬頭的勇氣都沒有。
麥語心聽完,臉色陰沉得如暴風雨前的天空,眼中燃著熊熊怒火。她冷笑,語氣充滿嘲弄:「五條內褲?狗,你膽子真是大到天上去了!我的收納箱全被你這髒東西碰過,全部得丟!說,你怎麼賠償?」我顫抖著回道:「主人…賤奴願意加倍工作…賠償您的損失…」可她嗤笑,打斷我:「你這畜生的錢本來就是我的!我用自己的錢賠自己?」
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主人…賤奴不是這意思…賤奴…」她冷冷質問:「你有錢嗎?你連閹割的費用都拿不出來,對吧?」我低頭,卑微地回答:「是…賤奴…賤奴沒錢…」她高冷地俯視我,語氣冰冷如刀:「賠償肯定是要賠的,閹割也是要閹的,這幾點一點都不妥協!三天內,把那兩條內褲還回來,閹割計畫也給我擬好!不然,你這賤狗的下場,比監獄還慘!」
我愣在原地,恐懼如無邊的黑暗將我吞噬,心像被撕裂。我試著求饒,聲音沙啞得如哀嚎:「主人…賤奴知錯…求您…給賤奴一條活路…」可她只是冷笑,靴尖踢了踢我的臉:「活路?狗,你這輩子都得匍匐在我腳下!滾回去,明天繼續跪!別讓我再抓到你的把柄!」
我拖著滿身傷痕,踉蹌地爬出公寓,夜風冷得刺骨,鮮血和汗水順著皮膚流下,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想死。我騎上電動車,腦子裡全是她的冷笑、閹割的威脅,還有那兩條藏在宿舍的內褲,像罪證壓得我喘不過氣。我的內心開始自問自答,像一個瘋子在與自己爭執:「張小凡,你怎麼會淪落到這地步?為什麼要偷那兩條內褲?為什麼要一錯再錯?」我的心像被撕裂,悔恨如毒藥吞噬我。我試著想像父母知道我被閹割的畫面,他們失望的眼神,母親的淚水,父親的沉默,像刀子刺進我的胸口。我低聲自語,聲音顫抖得像在哭:「我該怎麼辦…三天後的懲罰…閹割…我逃不掉…我連死的資格都沒有…」恐懼讓我全身顫抖,腦海裡閃過手術刀的寒光,麥語心冷笑著說「自己動手」的畫面,讓我幾乎崩潰。我閉上眼,淚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已經無路可退。
第二十一章:可笑的懺悔
清晨的宿舍籠罩在薄霧中,窗外的陽光冷得如刀,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滿是傷痕的身上。昨晚麥語心的毒打如烙鐵燒進我的靈魂,背上的鞭痕滲著血,黏膩地貼著破舊的床單,下體的貞操鎖傳來陣陣脹痛,彷彿還殞留著她靴尖的碾壓。我拖著殞傷的身體爬下床,膝蓋一軟,險些摔倒。鏡子裡的我,滿臉瘀青,眼神空洞,宛如一具沒有靈魂的傀儡。我咬緊牙,錄下向主人的請安影片,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主人,賤奴張小凡向您請安,祝您今日心情愉快…」
發送影片後,我沒有如往常般換上外送制服,因為麥語心的命令猶言在耳:「三天內,給我擬一份閹割計畫,費用你自己出!」這句話如死神的宣判,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閹割——對我這條賤狗而言,不僅是最沉重的羞辱,更是對我作為男人僅存尊嚴的徹底踐踏。更讓我畏懼的是她手中的罪證,那些不堪入目的影片——我舔鞋底、喝聖水、吞下她與閨蜜的黃金,若公開,我的家人將永遠抬不起頭,我將身敗名裂,淪為眾人唾棄的垃圾。沒有男人願意捨棄自己的寶貝,可她的威脅如鐵鏈鎖住我的靈魂,若我反抗,我不敢想像她會如何摧毀我。我試著甩開這些念頭,腦子裡卻全是她的冷笑、電擊棒的滋滋聲,以及那份悔過切結書上「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的字眼,字字如刀,刺進我的心。
我跪在宿舍地板上,將那兩條偷來的內褲——淺綠色蕾絲和純白蕾絲——從床底的隱秘角落取出。它們曾是我禁忌幻想的寄託,如今卻成了壓垮我的罪證。我戴上白色橡膠手套,小心翼翼地清洗它們,洗滌劑的氣味掩蓋不了我內心的羞恥。我一邊洗,一邊自問自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張小凡,你怎麼會蠢到這地步?為什麼要偷它們?為什麼要一錯再錯?那些影片…若公開,你怎麼面對父母?」悔恨如毒藥吞噬我,我試著想像父母知曉我被閹割、影片曝光的畫面,他們失望的眼神,母親的淚水,父親的沉默,如刀子刺進我的胸口。我低聲自語:「我該怎麼辦…罪證在她手上…閹割…我逃不掉…」
清洗乾淨後,我將內褲小心收進一個塑膠袋,密封好,確保不留下任何痕跡。但這只是徒勞,麥語心的怒火不會因我的悔改而消退。我坐在宿舍的破椅子上,雙手抱頭,腦子裡全是手術刀的寒光,她冷笑著說「自己動手,別弄髒我的地方」的畫面,還有那些影片公開後家人蒙羞的場景,讓我幾乎崩潰。我別無選擇,繳交閹割計畫的期限迫在眉睫,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打開筆電,顫抖著在網上搜尋各大醫院的男性器官切除手術資訊。螢幕上的醫療術語如在嘲笑我的墮落,我覺得自己可笑又可悲,竟落魄到查詢這些東西。網頁顯示,正規醫院的閹割手術分為化學閹割與物理閹割,費用動輒百萬,還需長期的心理諮詢,確認患者自願且無後悔可能,醫生才會同意動刀。我心頭一沉,若我提出這種計畫,麥語心絕不會買單,她會認為我在敷衍,接著又是一場非人道的毒打。我繼續搜尋,試圖找到便宜、不花錢的閹割方式,卻在一個荒誕的BDSM秘密論壇中,發現了一個「閹奴」的分享。
那個匿名用戶描述了一個地下場所,只需一萬塊即可進行閹割,無需預約,專為無錢的奴隸服務。之所以便宜,是因為它仿照古法——皇宮對太監的切除手法。先將被閹割者餓兩三天,五花大綁於手術台上,清洗消毒後,用滾燙的刀具一刀切下。只要簽下同意書,當天即可手術,但死活不論,術後無任何醫療保障。我哭笑不得,腦海裡閃過那殞烈的畫面:自己被綁在骯髒的手術台上,滾燙的刀刃切開皮膚,鮮血噴湧,劇痛吞噬意識,甚至可能因感染而死。我的胃一陣翻騰,恐懼讓我全身顫抖,可時間的齒輪滴答作響,毫不停歇。我必須在今日做出決定,這不人道的方案,竟成了我唯一的選擇。
下午四點,我帶著裝有內褲的塑膠袋,趕往麥語心的公寓。為了避免再次觸怒她,我提前傳訊請示:「主人,賤奴已準備好內褲與閹割計畫,求您允許賤奴於五點到達門口懺悔並服侍。」她的回覆冰冷如刀:「五點準時跪在門口,狗!別遲到!」我站在公寓樓下,望著那扇熟悉的鐵門,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我試著想像即將面對的羞辱,她冷笑著審視我的計畫,嘲弄我這條賤狗的畫面,讓我幾乎崩潰。我自問:「張小凡,你還有退路嗎?她手裡的罪證…那些影片…公開後你怎麼活?閹割…你真的要變成不人不鬼的東西?」我的心如被撕裂,悔恨與恐懼交織,我低聲自語:「我不想…可我不敢反抗…她會毀了我…我的家人…」淚水滑落,汗水混著血水從鞭痕滲出,刺痛提醒我這無盡的奴役。
五點整,我跪在麥語心公寓門口的走廊上,水泥地冰冷刺骨,硌得膝蓋生疼。我頭低得幾乎貼地,雙手恭敬地放在膝前,像一條真正的狗,手裡緊握著裝有內褲的塑膠袋。我不敢抬頭,怕走廊裡的監視器捕捉到我的眼神,怕麥語心從門後窺視我的懦弱。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張小凡,罪孽深重,褻瀆主人聖物,求主人寬恕…」我的聲音在狹窄的走廊迴盪,卻被自己的心跳聲吞沒。每說一句,我的心就沉一分,尊嚴如被碾碎的塵埃,隨空氣消散。
走廊偶爾傳來鄰居的腳步聲,有人經過,低聲嘀咕:「這人在幹嘛?」我咬緊牙,額頭滲出冷汗,羞恥如火焰燒遍全身。監視器的紅燈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爍,如一隻冷酷的眼睛,提醒我麥語心隨時能看到我的每一絲顫抖。我試著麻痺自己,告訴自己這只是懲罰,總會過去,可她的命令如鐵錘砸在我的腦海:每天從五點跪到十點,五小時的懺悔。我的靈魂像被剝離,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她的腳下。我自問:「張小凡,你為什麼不逃?為什麼要跪在這?」可答案如刀割心:我逃不掉,她的罪證會毀了我,我的家人會因我蒙羞。我只能繼續跪,繼續懺悔,直到十點。
十點整,麥語心傳來訊息:「進來,狗。」我傳訊請示:「主人,賤奴懺悔完畢,求您允許賤奴進入服侍。」她的回覆充滿怒火:「滾進來,狗!別讓我再抓到你的把柄!」我推開公寓大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我脫光衣服,赤裸地跪在玄關,將她的拖鞋恭敬地置於我的衣物上方,緩慢爬進客廳,頭低得不敢抬。
麥語心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穿著黑色緊身上衣和短裙,氣場如女王般冷酷。她低頭看著我,眼神帶著嘲弄,手中把玩著手機,像是隨時能按下某個致命的鍵。我跪在她面前,鼻尖幾乎貼地,汗水混著血水滴在地上。我恭敬地呈上裝有兩條內褲的塑膠袋,低聲稟報:「主人,賤奴已將內褲清洗乾淨,全程戴手套,未曾碰觸,求主人查收。」
她接過袋子,隨意瞥了一眼,臉上閃過一抹噁心的神情,語氣充滿鄙夷:「這幾條內褲已被你這賤貨玷污,再怎麼洗也洗不乾淨!就算不乾淨,也輪不到你這狗東西擁有!」她頓了頓,眼中燃起怒火,命令道:「你褻瀆我的懲罰,明天我再跟你算!現在,你褻瀆了它們,」她指了指內褲,「也得為你的罪行懺悔!今晚你就留在這,對它們磕頭,磕到天亮,一邊念你的懺悔詞!聽到沒有?」
我心頭一震,羞恥如潮水湧來,可我知道自己沒有拒絕的權利。我低聲回道:「賤奴遵命…謝主人恩典…」正準備執行命令,她突然冷笑,質問道:「等等,賤狗,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我一愣,還沒反應過來,她起身走到我面前,鞋尖挑起我的貞操鎖,語氣帶著嘲弄:「它呢?你的閹割計畫,準備好了?」
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磕頭,額頭撞地,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賤奴已找到一個地下場所…只需一萬塊…仿古法閹割…簽同意書即可手術…賤奴…賤奴願意接受…求主人允許…」我將論壇上查到的殞烈方案全盤托出,心如死灰,腦海裡閃過滾燙刀刃切開皮膚的畫面,鮮血噴湧的場景讓我幾乎崩潰。
麥語心聽完,滿意地點點頭,嘴角揚起一抹冷笑,語氣充滿嘲諷:「不錯,狗,你終於有點自覺了!幾天後,自己去把那髒東西閹了,完事向我匯報。你這賤東西,本就不配有那根東西!這就是你褻瀆我的代價!」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抹殞意,繼續羞辱:「不過你也該高興,沒了那東西,你就不用帶這破鎖了!多好,省得我看著噁心!」她的話如刀,刺進我的靈魂,卻如女皇的旨意,讓我無法抗拒。我只能磕頭,聲音哽咽:「謝主人恩典…謝主人給賤奴贖罪的機會…」
這句話聽起來多麼可笑,可我別無選擇。我被帶到客廳一角,兩條內褲被她放在一個小桌上,如神聖的聖物般供奉。我跪在它們面前,開始無盡的磕頭,額頭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罪孽深重,褻瀆聖物之神聖,今跪於聖物面前,徹底悔過自新,求聖物原諒…」我就像個傻子,對著兩件無生命的內褲,不斷磕頭,不斷懺悔,絲毫不敢停歇。房間內的監視器紅燈閃爍,如一隻冷酷的眼睛,提醒我麥語心雖在臥室,卻隨時能透過手機遠端連線,檢查我是否確實執行她的命令。
那一夜,我的膝蓋磨破了皮,額頭腫起瘀痕,鮮血混著汗水滴在地上。我的靈魂如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這無盡的屈辱中。我試著自問:「張小凡,你怎麼會淪落至此?為什麼要偷那五條內褲?為什麼要讓自己墮入這深淵?」悔恨如毒藥吞噬我,我想像父母失望的眼神,家人蒙羞的畫面,卻連死的勇氣都沒有。我閉上眼,淚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注定要為這罪孽付出一切。
清晨的宿舍籠罩在薄霧中,窗外的陽光冷得如刀,勉強從破舊窗簾的縫隙鑽進來,照在我滿是傷痕的身上。昨晚麥語心的毒打如烙鐵燒進我的靈魂,背上的鞭痕滲著血,黏膩地貼著破舊的床單,下體的貞操鎖傳來陣陣脹痛,彷彿還殞留著她靴尖的碾壓。我拖著殞傷的身體爬下床,膝蓋一軟,險些摔倒。鏡子裡的我,滿臉瘀青,眼神空洞,宛如一具沒有靈魂的傀儡。我咬緊牙,錄下向主人的請安影片,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主人,賤奴張小凡向您請安,祝您今日心情愉快…」
發送影片後,我沒有如往常般換上外送制服,因為麥語心的命令猶言在耳:「三天內,給我擬一份閹割計畫,費用你自己出!」這句話如死神的宣判,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閹割——對我這條賤狗而言,不僅是最沉重的羞辱,更是對我作為男人僅存尊嚴的徹底踐踏。更讓我畏懼的是她手中的罪證,那些不堪入目的影片——我舔鞋底、喝聖水、吞下她與閨蜜的黃金,若公開,我的家人將永遠抬不起頭,我將身敗名裂,淪為眾人唾棄的垃圾。沒有男人願意捨棄自己的寶貝,可她的威脅如鐵鏈鎖住我的靈魂,若我反抗,我不敢想像她會如何摧毀我。我試著甩開這些念頭,腦子裡卻全是她的冷笑、電擊棒的滋滋聲,以及那份悔過切結書上「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的字眼,字字如刀,刺進我的心。
我跪在宿舍地板上,將那兩條偷來的內褲——淺綠色蕾絲和純白蕾絲——從床底的隱秘角落取出。它們曾是我禁忌幻想的寄託,如今卻成了壓垮我的罪證。我戴上白色橡膠手套,小心翼翼地清洗它們,洗滌劑的氣味掩蓋不了我內心的羞恥。我一邊洗,一邊自問自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張小凡,你怎麼會蠢到這地步?為什麼要偷它們?為什麼要一錯再錯?那些影片…若公開,你怎麼面對父母?」悔恨如毒藥吞噬我,我試著想像父母知曉我被閹割、影片曝光的畫面,他們失望的眼神,母親的淚水,父親的沉默,如刀子刺進我的胸口。我低聲自語:「我該怎麼辦…罪證在她手上…閹割…我逃不掉…」
清洗乾淨後,我將內褲小心收進一個塑膠袋,密封好,確保不留下任何痕跡。但這只是徒勞,麥語心的怒火不會因我的悔改而消退。我坐在宿舍的破椅子上,雙手抱頭,腦子裡全是手術刀的寒光,她冷笑著說「自己動手,別弄髒我的地方」的畫面,還有那些影片公開後家人蒙羞的場景,讓我幾乎崩潰。我別無選擇,繳交閹割計畫的期限迫在眉睫,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打開筆電,顫抖著在網上搜尋各大醫院的男性器官切除手術資訊。螢幕上的醫療術語如在嘲笑我的墮落,我覺得自己可笑又可悲,竟落魄到查詢這些東西。網頁顯示,正規醫院的閹割手術分為化學閹割與物理閹割,費用動輒百萬,還需長期的心理諮詢,確認患者自願且無後悔可能,醫生才會同意動刀。我心頭一沉,若我提出這種計畫,麥語心絕不會買單,她會認為我在敷衍,接著又是一場非人道的毒打。我繼續搜尋,試圖找到便宜、不花錢的閹割方式,卻在一個荒誕的BDSM秘密論壇中,發現了一個「閹奴」的分享。
那個匿名用戶描述了一個地下場所,只需一萬塊即可進行閹割,無需預約,專為無錢的奴隸服務。之所以便宜,是因為它仿照古法——皇宮對太監的切除手法。先將被閹割者餓兩三天,五花大綁於手術台上,清洗消毒後,用滾燙的刀具一刀切下。只要簽下同意書,當天即可手術,但死活不論,術後無任何醫療保障。我哭笑不得,腦海裡閃過那殞烈的畫面:自己被綁在骯髒的手術台上,滾燙的刀刃切開皮膚,鮮血噴湧,劇痛吞噬意識,甚至可能因感染而死。我的胃一陣翻騰,恐懼讓我全身顫抖,可時間的齒輪滴答作響,毫不停歇。我必須在今日做出決定,這不人道的方案,竟成了我唯一的選擇。
下午四點,我帶著裝有內褲的塑膠袋,趕往麥語心的公寓。為了避免再次觸怒她,我提前傳訊請示:「主人,賤奴已準備好內褲與閹割計畫,求您允許賤奴於五點到達門口懺悔並服侍。」她的回覆冰冷如刀:「五點準時跪在門口,狗!別遲到!」我站在公寓樓下,望著那扇熟悉的鐵門,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我試著想像即將面對的羞辱,她冷笑著審視我的計畫,嘲弄我這條賤狗的畫面,讓我幾乎崩潰。我自問:「張小凡,你還有退路嗎?她手裡的罪證…那些影片…公開後你怎麼活?閹割…你真的要變成不人不鬼的東西?」我的心如被撕裂,悔恨與恐懼交織,我低聲自語:「我不想…可我不敢反抗…她會毀了我…我的家人…」淚水滑落,汗水混著血水從鞭痕滲出,刺痛提醒我這無盡的奴役。
五點整,我跪在麥語心公寓門口的走廊上,水泥地冰冷刺骨,硌得膝蓋生疼。我頭低得幾乎貼地,雙手恭敬地放在膝前,像一條真正的狗,手裡緊握著裝有內褲的塑膠袋。我不敢抬頭,怕走廊裡的監視器捕捉到我的眼神,怕麥語心從門後窺視我的懦弱。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張小凡,罪孽深重,褻瀆主人聖物,求主人寬恕…」我的聲音在狹窄的走廊迴盪,卻被自己的心跳聲吞沒。每說一句,我的心就沉一分,尊嚴如被碾碎的塵埃,隨空氣消散。
走廊偶爾傳來鄰居的腳步聲,有人經過,低聲嘀咕:「這人在幹嘛?」我咬緊牙,額頭滲出冷汗,羞恥如火焰燒遍全身。監視器的紅燈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爍,如一隻冷酷的眼睛,提醒我麥語心隨時能看到我的每一絲顫抖。我試著麻痺自己,告訴自己這只是懲罰,總會過去,可她的命令如鐵錘砸在我的腦海:每天從五點跪到十點,五小時的懺悔。我的靈魂像被剝離,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她的腳下。我自問:「張小凡,你為什麼不逃?為什麼要跪在這?」可答案如刀割心:我逃不掉,她的罪證會毀了我,我的家人會因我蒙羞。我只能繼續跪,繼續懺悔,直到十點。
十點整,麥語心傳來訊息:「進來,狗。」我傳訊請示:「主人,賤奴懺悔完畢,求您允許賤奴進入服侍。」她的回覆充滿怒火:「滾進來,狗!別讓我再抓到你的把柄!」我推開公寓大門,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壓迫感。我脫光衣服,赤裸地跪在玄關,將她的拖鞋恭敬地置於我的衣物上方,緩慢爬進客廳,頭低得不敢抬。
麥語心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穿著黑色緊身上衣和短裙,氣場如女王般冷酷。她低頭看著我,眼神帶著嘲弄,手中把玩著手機,像是隨時能按下某個致命的鍵。我跪在她面前,鼻尖幾乎貼地,汗水混著血水滴在地上。我恭敬地呈上裝有兩條內褲的塑膠袋,低聲稟報:「主人,賤奴已將內褲清洗乾淨,全程戴手套,未曾碰觸,求主人查收。」
她接過袋子,隨意瞥了一眼,臉上閃過一抹噁心的神情,語氣充滿鄙夷:「這幾條內褲已被你這賤貨玷污,再怎麼洗也洗不乾淨!就算不乾淨,也輪不到你這狗東西擁有!」她頓了頓,眼中燃起怒火,命令道:「你褻瀆我的懲罰,明天我再跟你算!現在,你褻瀆了它們,」她指了指內褲,「也得為你的罪行懺悔!今晚你就留在這,對它們磕頭,磕到天亮,一邊念你的懺悔詞!聽到沒有?」
我心頭一震,羞恥如潮水湧來,可我知道自己沒有拒絕的權利。我低聲回道:「賤奴遵命…謝主人恩典…」正準備執行命令,她突然冷笑,質問道:「等等,賤狗,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我一愣,還沒反應過來,她起身走到我面前,鞋尖挑起我的貞操鎖,語氣帶著嘲弄:「它呢?你的閹割計畫,準備好了?」
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磕頭,額頭撞地,聲音顫抖得像在哭:「主人…賤奴…賤奴已找到一個地下場所…只需一萬塊…仿古法閹割…簽同意書即可手術…賤奴…賤奴願意接受…求主人允許…」我將論壇上查到的殞烈方案全盤托出,心如死灰,腦海裡閃過滾燙刀刃切開皮膚的畫面,鮮血噴湧的場景讓我幾乎崩潰。
麥語心聽完,滿意地點點頭,嘴角揚起一抹冷笑,語氣充滿嘲諷:「不錯,狗,你終於有點自覺了!幾天後,自己去把那髒東西閹了,完事向我匯報。你這賤東西,本就不配有那根東西!這就是你褻瀆我的代價!」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抹殞意,繼續羞辱:「不過你也該高興,沒了那東西,你就不用帶這破鎖了!多好,省得我看著噁心!」她的話如刀,刺進我的靈魂,卻如女皇的旨意,讓我無法抗拒。我只能磕頭,聲音哽咽:「謝主人恩典…謝主人給賤奴贖罪的機會…」
這句話聽起來多麼可笑,可我別無選擇。我被帶到客廳一角,兩條內褲被她放在一個小桌上,如神聖的聖物般供奉。我跪在它們面前,開始無盡的磕頭,額頭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罪孽深重,褻瀆聖物之神聖,今跪於聖物面前,徹底悔過自新,求聖物原諒…」我就像個傻子,對著兩件無生命的內褲,不斷磕頭,不斷懺悔,絲毫不敢停歇。房間內的監視器紅燈閃爍,如一隻冷酷的眼睛,提醒我麥語心雖在臥室,卻隨時能透過手機遠端連線,檢查我是否確實執行她的命令。
那一夜,我的膝蓋磨破了皮,額頭腫起瘀痕,鮮血混著汗水滴在地上。我的靈魂如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這無盡的屈辱中。我試著自問:「張小凡,你怎麼會淪落至此?為什麼要偷那五條內褲?為什麼要讓自己墮入這深淵?」悔恨如毒藥吞噬我,我想像父母失望的眼神,家人蒙羞的畫面,卻連死的勇氣都沒有。我閉上眼,淚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注定要為這罪孽付出一切。
cpy112233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真不错!支持!
第二十二章:漫漫長夜
漫漫長夜,公寓客廳的地板冰冷刺骨,我的膝蓋早已磨破,鮮血混著汗水滲進水泥縫隙,留下斑駁的痕跡。整夜對著兩條無生命的內褲磕頭懺悔,額頭腫起青紫瘀痕,每一次撞地都像刀子割在心上。我低聲念著懺悔詞:「賤奴罪孽深重,褻瀆聖物之神聖,今跪於聖物面前,徹底悔過自新,求聖物原諒…」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顫抖得幾乎聽不清。我就像個傻子,對著麥語心的內褲磕頭不止,屈辱如毒藥燒進我的骨髓,卻不敢停下。牆角監視器的紅燈在黑暗中閃爍,像一隻冷酷的眼睛,時刻提醒我麥語心隨時可能透過手機遠端連線,檢查我的每一個動作。
這幾天的連續懲罰—鞭打、踩踏、公開羞辱,還有那無處不在的閹割威脅與罪證恐懼,已將我的精神推向崩潰邊緣。她的影片,那些我舔鞋底、喝聖水、吞黃金的畫面,像死神的鐮刀懸在頭頂,一旦公開,我的家人將永遠抬不起頭,我將淪為眾人唾棄的垃圾。悔過切結書的「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字眼在我腦海反覆閃現,手術刀的寒光、滾燙刀刃切開皮膚的殞烈畫面,讓我連呼吸都覺得沉重。我的靈魂像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這無盡的屈辱中。
疲憊像巨石壓在身上,我的眼皮沉得像灌了鉛,意識斷斷續續,幾次不小心睡著,卻被恐懼硬生生驚醒。只要一點細微的聲響—窗外的風聲、樓梯間的腳步聲,甚至自己的心跳—都足以讓我從迷霧般的睡夢中彈起,全身冷汗,趕緊恢復跪姿,繼續磕頭懺悔。深怕麥語心半夜醒來,從監視器中看到我偷懶未執行命令,那將是電擊棒、皮鞭,甚至閹割的酷刑。我的腦海裡全是她的冷笑:「狗,你這賤東西,活著就是個錯誤!」恐懼如無形的鎖鏈,勒緊我的喉嚨,讓我連片刻喘息都不敢。
半夜時分,我已不知具體時間,只猜麥語心應該睡了。眼前的小桌上,兩條內褲靜靜躺著,淺綠色與純白的蕾絲在昏暗燈光下泛著微光。洗滌劑的氣味掩蓋了主人的氣息,可對我這條賤狗而言,它們曾緊貼她的神秘聖域,依然散發致命的吸引力。一個邪念竄進腦海—或許我可以再拿起它們,貼近鼻尖,好好品聞,哪怕只有一瞬。可這念頭剛冒出來,就被恐懼狠狠壓下。我好累,好睏,累到連這禁忌的渴望都變得蒼白。此刻,我只想睡一覺,哪怕十分鐘,哪怕只是閉眼片刻,我什麼都願意。閹割的恐懼、明天的懲罰、對內褲的病態渴望,我都不在乎了。我只想躺下,讓這無盡的折磨暫停,哪怕只是片刻。
我磕著磕著頭,意識再次模糊,頭越來越沉,身體不受控制地向前傾倒。就在我即將墜入黑暗的瞬間,麥語心臥室傳來一陣細微的聲響—像是床板的吱吱聲,或是腳步的輕響。我猛地驚醒,才發現自己已整個人倒在地上,額頭貼著冰冷的地板,竟不知何時睡著了!恐懼如洪水吞沒我,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汗水瞬間浸濕背脊。我的腦海閃過電擊棒的滋滋聲、皮鞭撕裂皮膚的劇痛,還有她冷酷的怒吼:「狗,你敢偷懶?」我嚇得魂飛魄散,趕緊撐起身體,恢復跪姿,額頭狠狠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繼續懺悔:「賤奴罪孽深重,褻瀆聖物…求聖物原諒…」我的聲音顫抖得像在哭,恐懼如毒蛇鑽進骨髓,背脊冰冷刺痛。我不敢抬頭,怕監視器捕捉到我的失誤,怕麥語心此刻正透過手機冷笑著看我,準備施加更殞烈的懲罰。我的雙腿抖得像篩子,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提醒我昨晚失禁的羞恥,現在的我連靈魂都在顫抖,只剩對她怒火的無邊畏懼。
門吱吱一聲開了,麥語心的腳步聲緩緩逼近,像死神的低語。我全身顫抖,額頭撞地的力道更大,鮮血從瘀痕滲出,滴在地上,發出細微的滴答聲。我的腦海全是她的靴尖碾壓我下體的畫面,閹割的威脅如鐵錘砸在胸口。我低聲哀求,聲音沙啞得像在懺悔:「主人…賤奴知錯…賤奴不敢偷懶…求您饒恕…」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恐懼吞噬了我的理智,我甚至感覺貞操鎖在顫抖,彷彿在預告即將到來的酷刑。她的腳步停在我身旁,我屏住呼吸,等待暴風雨般的懲罰。
出乎意料,她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轉身走向浴室。馬桶沖水的聲音傳來,隨後是她回臥室的腳步,門吱吱關上,房間重歸寂靜。我愣在原地,恐懼仍像毒蛇纏繞,卻終於鬆了一口氣。腎上腺素的激湧讓我的睡意瞬間消散,像是被注射了一劑強心針,濃濃的疲憊被硬生生壓下。我趕緊繼續磕頭,額頭撞地的聲響在空蕩的客廳迴盪,懺悔詞從喉嚨擠出,機械而僵硬。我不敢再有片刻懈怠,監視器的紅燈像死神的眼睛,無時無刻不在盯著我。
隨著時間推移,天色漸亮,陽光從窗簾縫隙鑽進,房間越來越熱。我汗流浹背,汗水混著血水順著額頭滑進眼睛,刺得生疼。我的身體早已不堪重負,膝蓋的傷口被汗水浸得火燒般痛,雙臂酸軟得幾乎抬不起,頭昏沉得像灌了鉛。可我不敢停下,眼前的小桌上,兩條內褲靜靜躺著,淺綠色與純白的蕾絲在陽光下泛著微光,像是對我的嘲弄。我繼續磕頭,動作機械得像一台壞掉的機器,懺悔詞從嘴裡吐出,卻毫無靈魂。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在這無盡的折磨中變得模糊,只知道每一下磕頭都在耗盡我的生命。
正當我瀕臨崩潰,意識像風中殞燭搖搖欲墜時,麥語心的腳步聲再次響起。她緩緩走近,靴子在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響,像死神的節拍。我不敢抬頭,繼續磕頭,額頭撞地的聲音混雜著我的喘息,汗水滴在地上,匯成一小灘水漬。她停在我身旁,沉默片刻,隨後一隻靴子狠狠踩在我的頭頂,力道大得讓我的額頭與地板猛烈撞擊,碰!碰!碰!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我咬緊牙,發出低低的哀嚎,聲音哽咽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知錯…求您饒恕…」
她冷笑,語氣冰冷如刀:「賤狗,你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有沒有偷懶?」她的靴跟碾壓著我的頭皮,痛得我全身痙攣,卻不敢動彈。我喘著粗氣,聲音顫抖得幾乎破碎:「主人…賤奴自知罪孽深重…不敢偷懶…整夜對聖物磕頭…不敢懈怠…求主人原諒…」我試著掩蓋那幾次無意識的昏睡,恐懼讓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深怕她從監視器中發現我的失誤。
麥語心哼了一聲,緩緩移開靴子,語氣冷血如冰:「你可以滾了。記得晚上六點你的懺悔,還有一週後的懲罰在等著你!」她的話如鐵錘,砸碎我僅存的希望,閹割與公開羞辱的威脅像幽靈纏繞,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我含著淚,忍住崩潰的情緒,恭敬地磕了三個頭,聲音哽咽:「謝主人恩典…賤奴給主人請早安…賤奴告退…」
我跪著倒退到玄關,顫抖著穿上破舊的衣服和鞋子,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無地自容。我傳訊請示:「賤奴請示離開。」麥語心揮了揮手,語氣充滿鄙夷:「滾吧,看見你就噁心!」我再次磕頭謝恩,低聲說:「祝主人今日美好。」然後拖著殞傷的身體,踉蹌地離開公寓。
這棟看似美好的公寓,對我卻是煉獄,每一秒都像在刀尖上行走。我一刻也不想停留,推開大門,陽光刺得我眼睛生疼。我低頭看手機,竟已是上午十一點半—麥語心睡到這麼晚,而我五點還得回來報到懺悔,能休息的時間所剩無幾。今晚又將是一夜的折磨,但我已顧不得這些。此刻的我,只想睡一覺,哪怕十分鐘,哪怕只是閉眼片刻,對我都是彌足珍貴。閹割的恐懼、明天的懲罰、對罪證的畏懼,我都不在乎了。沒什麼比好好睡一覺更重要。我拖著幾乎散架的身體,騎上電動車,腦子一片空白,只想趕回宿舍,躺下,讓這無盡的折磨暫停,哪怕只是片刻。
漫漫長夜,公寓客廳的地板冰冷刺骨,我的膝蓋早已磨破,鮮血混著汗水滲進水泥縫隙,留下斑駁的痕跡。整夜對著兩條無生命的內褲磕頭懺悔,額頭腫起青紫瘀痕,每一次撞地都像刀子割在心上。我低聲念著懺悔詞:「賤奴罪孽深重,褻瀆聖物之神聖,今跪於聖物面前,徹底悔過自新,求聖物原諒…」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顫抖得幾乎聽不清。我就像個傻子,對著麥語心的內褲磕頭不止,屈辱如毒藥燒進我的骨髓,卻不敢停下。牆角監視器的紅燈在黑暗中閃爍,像一隻冷酷的眼睛,時刻提醒我麥語心隨時可能透過手機遠端連線,檢查我的每一個動作。
這幾天的連續懲罰—鞭打、踩踏、公開羞辱,還有那無處不在的閹割威脅與罪證恐懼,已將我的精神推向崩潰邊緣。她的影片,那些我舔鞋底、喝聖水、吞黃金的畫面,像死神的鐮刀懸在頭頂,一旦公開,我的家人將永遠抬不起頭,我將淪為眾人唾棄的垃圾。悔過切結書的「無條件接受閹割之刑」字眼在我腦海反覆閃現,手術刀的寒光、滾燙刀刃切開皮膚的殞烈畫面,讓我連呼吸都覺得沉重。我的靈魂像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匍匐在這無盡的屈辱中。
疲憊像巨石壓在身上,我的眼皮沉得像灌了鉛,意識斷斷續續,幾次不小心睡著,卻被恐懼硬生生驚醒。只要一點細微的聲響—窗外的風聲、樓梯間的腳步聲,甚至自己的心跳—都足以讓我從迷霧般的睡夢中彈起,全身冷汗,趕緊恢復跪姿,繼續磕頭懺悔。深怕麥語心半夜醒來,從監視器中看到我偷懶未執行命令,那將是電擊棒、皮鞭,甚至閹割的酷刑。我的腦海裡全是她的冷笑:「狗,你這賤東西,活著就是個錯誤!」恐懼如無形的鎖鏈,勒緊我的喉嚨,讓我連片刻喘息都不敢。
半夜時分,我已不知具體時間,只猜麥語心應該睡了。眼前的小桌上,兩條內褲靜靜躺著,淺綠色與純白的蕾絲在昏暗燈光下泛著微光。洗滌劑的氣味掩蓋了主人的氣息,可對我這條賤狗而言,它們曾緊貼她的神秘聖域,依然散發致命的吸引力。一個邪念竄進腦海—或許我可以再拿起它們,貼近鼻尖,好好品聞,哪怕只有一瞬。可這念頭剛冒出來,就被恐懼狠狠壓下。我好累,好睏,累到連這禁忌的渴望都變得蒼白。此刻,我只想睡一覺,哪怕十分鐘,哪怕只是閉眼片刻,我什麼都願意。閹割的恐懼、明天的懲罰、對內褲的病態渴望,我都不在乎了。我只想躺下,讓這無盡的折磨暫停,哪怕只是片刻。
我磕著磕著頭,意識再次模糊,頭越來越沉,身體不受控制地向前傾倒。就在我即將墜入黑暗的瞬間,麥語心臥室傳來一陣細微的聲響—像是床板的吱吱聲,或是腳步的輕響。我猛地驚醒,才發現自己已整個人倒在地上,額頭貼著冰冷的地板,竟不知何時睡著了!恐懼如洪水吞沒我,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汗水瞬間浸濕背脊。我的腦海閃過電擊棒的滋滋聲、皮鞭撕裂皮膚的劇痛,還有她冷酷的怒吼:「狗,你敢偷懶?」我嚇得魂飛魄散,趕緊撐起身體,恢復跪姿,額頭狠狠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繼續懺悔:「賤奴罪孽深重,褻瀆聖物…求聖物原諒…」我的聲音顫抖得像在哭,恐懼如毒蛇鑽進骨髓,背脊冰冷刺痛。我不敢抬頭,怕監視器捕捉到我的失誤,怕麥語心此刻正透過手機冷笑著看我,準備施加更殞烈的懲罰。我的雙腿抖得像篩子,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提醒我昨晚失禁的羞恥,現在的我連靈魂都在顫抖,只剩對她怒火的無邊畏懼。
門吱吱一聲開了,麥語心的腳步聲緩緩逼近,像死神的低語。我全身顫抖,額頭撞地的力道更大,鮮血從瘀痕滲出,滴在地上,發出細微的滴答聲。我的腦海全是她的靴尖碾壓我下體的畫面,閹割的威脅如鐵錘砸在胸口。我低聲哀求,聲音沙啞得像在懺悔:「主人…賤奴知錯…賤奴不敢偷懶…求您饒恕…」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恐懼吞噬了我的理智,我甚至感覺貞操鎖在顫抖,彷彿在預告即將到來的酷刑。她的腳步停在我身旁,我屏住呼吸,等待暴風雨般的懲罰。
出乎意料,她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轉身走向浴室。馬桶沖水的聲音傳來,隨後是她回臥室的腳步,門吱吱關上,房間重歸寂靜。我愣在原地,恐懼仍像毒蛇纏繞,卻終於鬆了一口氣。腎上腺素的激湧讓我的睡意瞬間消散,像是被注射了一劑強心針,濃濃的疲憊被硬生生壓下。我趕緊繼續磕頭,額頭撞地的聲響在空蕩的客廳迴盪,懺悔詞從喉嚨擠出,機械而僵硬。我不敢再有片刻懈怠,監視器的紅燈像死神的眼睛,無時無刻不在盯著我。
隨著時間推移,天色漸亮,陽光從窗簾縫隙鑽進,房間越來越熱。我汗流浹背,汗水混著血水順著額頭滑進眼睛,刺得生疼。我的身體早已不堪重負,膝蓋的傷口被汗水浸得火燒般痛,雙臂酸軟得幾乎抬不起,頭昏沉得像灌了鉛。可我不敢停下,眼前的小桌上,兩條內褲靜靜躺著,淺綠色與純白的蕾絲在陽光下泛著微光,像是對我的嘲弄。我繼續磕頭,動作機械得像一台壞掉的機器,懺悔詞從嘴裡吐出,卻毫無靈魂。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在這無盡的折磨中變得模糊,只知道每一下磕頭都在耗盡我的生命。
正當我瀕臨崩潰,意識像風中殞燭搖搖欲墜時,麥語心的腳步聲再次響起。她緩緩走近,靴子在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響,像死神的節拍。我不敢抬頭,繼續磕頭,額頭撞地的聲音混雜著我的喘息,汗水滴在地上,匯成一小灘水漬。她停在我身旁,沉默片刻,隨後一隻靴子狠狠踩在我的頭頂,力道大得讓我的額頭與地板猛烈撞擊,碰!碰!碰!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我咬緊牙,發出低低的哀嚎,聲音哽咽得像在哭:「主人…賤奴知錯…求您饒恕…」
她冷笑,語氣冰冷如刀:「賤狗,你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有沒有偷懶?」她的靴跟碾壓著我的頭皮,痛得我全身痙攣,卻不敢動彈。我喘著粗氣,聲音顫抖得幾乎破碎:「主人…賤奴自知罪孽深重…不敢偷懶…整夜對聖物磕頭…不敢懈怠…求主人原諒…」我試著掩蓋那幾次無意識的昏睡,恐懼讓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深怕她從監視器中發現我的失誤。
麥語心哼了一聲,緩緩移開靴子,語氣冷血如冰:「你可以滾了。記得晚上六點你的懺悔,還有一週後的懲罰在等著你!」她的話如鐵錘,砸碎我僅存的希望,閹割與公開羞辱的威脅像幽靈纏繞,讓我連喘息的勇氣都沒有。我含著淚,忍住崩潰的情緒,恭敬地磕了三個頭,聲音哽咽:「謝主人恩典…賤奴給主人請早安…賤奴告退…」
我跪著倒退到玄關,顫抖著穿上破舊的衣服和鞋子,尿液的腥味從內褲傳來,讓我羞恥得無地自容。我傳訊請示:「賤奴請示離開。」麥語心揮了揮手,語氣充滿鄙夷:「滾吧,看見你就噁心!」我再次磕頭謝恩,低聲說:「祝主人今日美好。」然後拖著殞傷的身體,踉蹌地離開公寓。
這棟看似美好的公寓,對我卻是煉獄,每一秒都像在刀尖上行走。我一刻也不想停留,推開大門,陽光刺得我眼睛生疼。我低頭看手機,竟已是上午十一點半—麥語心睡到這麼晚,而我五點還得回來報到懺悔,能休息的時間所剩無幾。今晚又將是一夜的折磨,但我已顧不得這些。此刻的我,只想睡一覺,哪怕十分鐘,哪怕只是閉眼片刻,對我都是彌足珍貴。閹割的恐懼、明天的懲罰、對罪證的畏懼,我都不在乎了。沒什麼比好好睡一覺更重要。我拖著幾乎散架的身體,騎上電動車,腦子一片空白,只想趕回宿舍,躺下,讓這無盡的折磨暫停,哪怕只是片刻。
想问一下,阉割过后的生活还打算写吗,还是割完就完结了
第二十三章:王嘉嘉大人的懲罰
嘟嘟嘟…嘟嘟嘟…四點的鬧鐘刺耳地從手機傳來,像刀子割裂我短暫的夢鄉。這幾天的疲憊如巨石壓身,短短幾小時的休息哪能緩解?我閉著眼,試圖貪戀片刻寧靜,腦子卻像被鐵錘砸中,閃過麥語心的冷笑、監視器的紅燈、還有那把手術刀的寒光。我知道,多貪圖這幾分鐘的安寧,未來只會換來更大的風暴。我咬緊牙,撐起殞傷的身體,背上的鞭痕被扯裂,火燒般的痛楚讓我倒吸一口氣。我匆匆洗澡,更換新衣服,舊傷的刺痛如刀割心,羞恥與疲憊交織,讓我幾乎崩潰。我拖著幾乎散架的身子,趕在四點五十五分抵達麥語心的公寓樓下。
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車流與喧囂如洪水淹沒我的存在。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膝蓋硌得生疼,頭低得幾乎貼地,雙手恭敬地放在膝前,像一條真正的狗。我傳訊向麥語心報備:「主人,賤奴已於五點準時跪在公寓門口懺悔,求主人垂憐。」螢幕毫無回應,她的沉默如刀懸在頭頂,讓我心跳加速,恐懼吞噬我的靈魂。路人的低語、汽車的嘈雜,如嘲笑的利箭刺進我的心。我低聲懺悔:「賤奴張小凡,罪孽深重,褻瀆主人聖物,求主人寬恕…」聲音顫抖得像在哭,卻被街頭的喧囂吞沒,尊嚴如塵埃隨風消散。
夜幕悄無聲息降臨,路燈昏黃的光芒拉長我的影子,像一條匍匐的狗。忽然,一陣熟悉的笑聲從身後傳來,尖銳地刺進我的耳膜:「張小凡?你怎麼跪在這?」我心頭一震,恐懼如冰水澆遍全身,背脊瞬間僵硬。我緩緩回頭,目光顫抖地落在兩個身影上—王嘉嘉和駱品萱,麥語心的閨蜜,我的噩夢。我的心像被鐵爪撕裂,恐懼如洪水吞沒理智,手心冒出冷汗,雙腿抖得像篩子。我想逃,腦海裡閃過瘋狂的念頭—爬起來,衝進人群,逃離這無盡的屈辱!可現實如鐵錮,我的罪證在她們手中,那些不堪的影片—舔鞋底、喝聖水、吞黃金,一旦公開,我的家人將永遠抬不起頭,我將淪為眾人唾棄的垃圾。我的喉嚨像被堵住,連喘息都困難,汗水浸濕新換的衣服,舊傷的刺痛讓我幾乎崩潰。我只能匍匐在地,額頭狠狠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賤奴叩見王嘉嘉大人、駱品萱大人…」
這幾天的刑罰—鞭打、踩踏、整夜磕頭,已將我的精神推向崩潰邊緣。王嘉嘉與駱品萱的出現如死神的低語,讓我魂飛魄散。我的腦海閃過麥語心的電擊棒滋滋聲、皮鞭撕裂皮膚的劇痛,還有她們手中可能握有的影片,像刀子懸在頭頂。我的雙腿抖得像要斷裂,恐懼吞噬我的靈魂,我恨不得當場死去,只求逃離她們的嘲弄。我祈禱她們只是路過,趕緊上樓,別再羞辱我這條殞狗,可王嘉嘉的笑聲卻如毒蛇,纏繞在我心頭,讓我無處可逃。
王嘉嘉緩緩走近,蹲在我身旁,嘴角揚起一抹殞毒的笑,語氣尖銳如刀:「張小凡,瞧瞧你這賤樣,又幹了什麼下三濫的蠢事,惹你主人生氣?嗯?」她的聲音帶著戲謔,卻透著不容反抗的威嚴,像在撕開我的傷口撒鹽。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恐懼如無邊的黑暗吞噬我,汗水順著額頭滴在地上,匯成一小灘水漬。我試著開口,喉嚨卻像被鐵爪扼住,羞恥讓我一個字也吐不出。我低著頭,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賤奴知錯…求王嘉嘉大人饒恕…」
她嗤笑一聲,語氣更刻薄:「怎麼?這點破事都不屑回答?還是你這賤狗以為自己有資格在我面前裝啞巴?」她湊近我,眼中閃過一抹殞意,聲音低沉卻充滿威脅:「別忘了,你那堆噁心的影片可都在我手上!我跟你主人是閨蜜,隨手一按,就能讓你舔鞋底、喝尿的賤樣滿天飛!你不怕我一不小心,把它們發出去,讓全校笑你這條骯髒的蛆蟲一輩子?」
我嚇得魂飛魄散,恐懼如刀子刺進心臟,背脊冰冷刺痛。我的腦海閃過影片公開的畫面—父母失望的眼神、母親的淚水、父親的沉默,我的家人將因我蒙羞,永遠抬不起頭。我的雙腿抖得像要崩潰,汗水浸濕衣服,舊傷的刺痛讓我幾乎暈厥。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鮮血從瘀痕滲出,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王嘉嘉大人…求您…求您別公開…賤奴不是不講…是賤奴不敢講…求您饒恕賤奴的愚蠢…」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卑微得像一條真正的狗,只求她息怒。
駱品萱在一旁看著,語氣帶著幾分不忍:「嘉嘉,算了吧,你看他這副可憐樣,已經夠慘了。等下問語心不就知道原因了?」她的聲音溫柔,卻無法動搖王嘉嘉的殞意。王嘉嘉的眼神更冷,嘴角揚起一抹嘲弄的弧度,語氣尖酸得如毒液:「可憐?這賤狗可憐?品萱,你心太軟了!這種骯髒的垃圾,活該被踩進泥裡,永遠爬不起來!」她轉向我,眼中燃著報復的火焰,語氣更刻薄:「張小凡,我就不信治不了你這條下賤的狗!說,你到底幹了什麼?還是想逼我把你那噁心的影片發出去,讓全校笑你這變態一輩子?」
我全身顫抖,恐懼如鐵錮勒緊我的靈魂。我試著撒謊,聲音顫抖得幾乎破碎:「王嘉嘉大人…賤奴…賤奴只是犯了小錯…求您…」可話還沒說完,她猛地站起,冷不防一腳狠狠踹在我的下體!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貞操鎖的金屬撞擊命根,痛得我眼淚爆射,身體本能蜷縮在地,發出淒厲的哀嚎。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得像在哭:「王嘉嘉大人…求您饒命…賤奴知錯…求您…」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羞恥與恐懼交織,舊傷的刺痛讓我墮入無邊的絕望。
她冷笑,語氣如刀割心:「饒命?賤狗,你有資格求饒?說!不說我就踢!踢到你這骯髒的東西說為止!」她的增高牛津鞋懸在我面前,鞋尖沾滿灰塵,像死神的鐮刀,眼中滿是殞毒的快意。駱品萱試著勸阻:「嘉嘉,別太過了,街上這麼多人…」可王嘉嘉毫不理會,語氣更尖銳:「品萱,這賤狗不說,我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我已顧不得面子,為了少受點罪,我低著頭,聲音低得像在懺悔:「王嘉嘉大人…賤奴…賤奴褻瀆了主人的聖物…所以被罰在這懺悔…」羞恥如火焰燒遍全身,我恨不得當場死去。王嘉嘉的眼睛一亮,語氣更譏諷:「聖物?哈哈,就為這跪在這丟人現眼?簡直活該!說清楚,什麼聖物?別逼我再問!」她鞋尖輕輕點地,像在警告我的猶豫。
我吱吱嗚嗚,聲音顫抖得幾乎聽不清:「是…是主人的私人物品…」我的心如刀絞,羞恥讓我連抬頭的勇氣都沒有。王嘉嘉的臉色一沉,語氣陡然變得更冷,每個字都如鐵錘砸在我心上:「什!麼!物!品!」她一字一句,慢得像在撕開我的靈魂,耐心如薄冰即將崩裂。見我仍猶豫,她冷笑一聲:「不說是吧?好!這賤狗還敢嘴硬!」她猛地抬起增高牛津鞋,又是一腳狠狠踹來!
我本能地用手護住下體,勉強擋住這致命一擊,劇痛仍讓我全身痙攣。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鮮血滴在地上,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王嘉嘉大人…求您寬恕…賤奴知錯…」可她怒火更盛,語氣尖銳如刀:「還敢擋?把!手!拿!開!再不說,我就踢到你說為止!」她的鞋尖懸在空中,像隨時會碾碎我的命根。駱品萱再次勸阻:「嘉嘉,夠了!別在街上鬧了!」可王嘉嘉毫不理會,眼中燃著殞毒的火焰,命令道:「手拿開!快!」
我嚇得魂飛魄散,恐懼吞噬最後的理智。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聲音低得像在懺悔:「我說…我說…是主人的…內褲…」這句話如刀割喉,羞恥如洪水將我淹沒,我恨不得當場死去。王嘉嘉與駱品萱同時露出鄙夷的神情,發出噁心的聲音:「嘖!張小凡,你這噁心的變態!竟然敢覬覦語心的內褲?就你這骯髒的東西,也配碰她的聖物?你這賤狗,真是下賤到骨子裡了!」王嘉嘉的語氣充滿嘲弄,如毒液燒進我的靈魂。駱品萱原本的同情瞬間消失,語氣也變得冷淡:「真噁心…語心養你這條狗,真是浪費!」
我低著頭,匍匐在她們腳下,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知錯…賤奴罪孽深重…願意接受懲罰…」羞恥與恐懼交織,我的靈魂如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王嘉嘉聽到「懲罰」,冷笑更甚,語氣尖酸得如刀子:「懲罰?哈哈,跪在這算什麼懲罰?對你這骯髒的變態來說,簡直太輕了!像你這種垃圾,就該被踩進泥裡,永遠爬不起來!」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抹殞意,繼續羞辱:「說,你這賤狗是不是還偷了語心的內褲,天天躲在宿舍聞?噁心不噁心?」
我嚇得手心冒汗,恐懼如鐵爪扼住喉嚨。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王嘉嘉大人…賤奴已被主人嚴懲…求您放過賤奴…」可她毫不理會,語氣更刻薄:「放過你?笑話!你這下賤的垃圾,以為求饒就夠了?我沒資格懲罰你?還是你這賤狗瞧不起我?」她的鞋尖輕輕點地,如在宣判我的死刑。
我全身顫抖,恐懼讓我幾乎崩潰,連忙磕頭,額頭撞地,鮮血滴在地上,聲音沙啞得如懺悔:「不…不是的…王嘉嘉大人當然有資格…賤奴不敢…求您饒恕…」我的回答無助得如一條真正的狗,羞恥與恐懼吞噬我的靈魂。王嘉嘉冷笑,語氣充滿鄙夷:「有資格?那就證明你的賤!來,把我和駱大人的鞋底舔乾淨!讓全街的人看看,你這骯髒的狗有多下賤!」
她抬起增高牛津鞋,鞋底硬得如石頭,沾滿灰塵與汙漬,在路燈下泛著刺眼的光芒。我的心如刀絞,羞恥讓我恨不得當場死去,可她的威脅如鐵錮—影片公開、麥語心的怒火、閹割的酷刑,讓我連反抗的念頭都不敢有。駱品萱皺眉,低聲說:「嘉嘉,算了吧,街上這麼多人,怪尷尬的…」可王嘉嘉毫不理會,語氣更尖銳:「尷尬?這賤狗還有臉談尷尬?品萱,你別管!這骯髒的東西,就該像這樣趴在地上舔鞋底!」她轉向我,鞋尖懸在我面前,命令道:「舔!快!別逼我再說第二遍,你這噁心的變態!」
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羞恥與恐懼交織。我緩緩伸出舌頭,舔上她的牛津鞋底,硬邦邦的紋路割得舌頭生疼,灰塵的苦澀味在嘴裡蔓延,屈辱如刀子刺進心頭。王嘉嘉冷笑連連,語氣尖酸得如毒液:「哈哈,瞧瞧你這賤樣!舔得再用力點,你這骯髒的蛆蟲!就你這德性,只配趴在地上當抹布!」她抬起另一隻鞋,命令道:「換這隻!舔乾淨,一粒灰都別留!不然我讓你這賤狗在街上爬一圈!」
我咬緊牙,忍住喉嚨的哽咽,繼續舔著,舌頭被鞋底磨得滲血,屈辱燒進我的骨髓。路人的低語、汽車的喇叭聲,如嘲笑的利箭刺進我的心。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如在哭:「賤奴知錯…謝王嘉嘉大人恩典…」可她只是冷笑,語氣更刻薄:「恩典?你這骯髒的垃圾,也配談恩典?舔!舔到我滿意為止!像你這種變態,只配當我鞋底的垃圾桶!」
舔完兩隻鞋,我的舌頭麻木,嘴角滲血,羞恥與恐懼將我推入無底深淵。王嘉嘉滿意地點點頭,語氣充滿鄙夷:「滾吧,蛆蟲!你這賤狗,只配舔鞋底,永遠別想抬起你那骯髒的頭!」她轉身與駱品萱離開,笑聲如刀子在我心頭迴盪。我匍匐在地,淚水滴在地上,靈魂如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等待麥語心下一場更殞烈的審判。
嘟嘟嘟…嘟嘟嘟…四點的鬧鐘刺耳地從手機傳來,像刀子割裂我短暫的夢鄉。這幾天的疲憊如巨石壓身,短短幾小時的休息哪能緩解?我閉著眼,試圖貪戀片刻寧靜,腦子卻像被鐵錘砸中,閃過麥語心的冷笑、監視器的紅燈、還有那把手術刀的寒光。我知道,多貪圖這幾分鐘的安寧,未來只會換來更大的風暴。我咬緊牙,撐起殞傷的身體,背上的鞭痕被扯裂,火燒般的痛楚讓我倒吸一口氣。我匆匆洗澡,更換新衣服,舊傷的刺痛如刀割心,羞恥與疲憊交織,讓我幾乎崩潰。我拖著幾乎散架的身子,趕在四點五十五分抵達麥語心的公寓樓下。
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車流與喧囂如洪水淹沒我的存在。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膝蓋硌得生疼,頭低得幾乎貼地,雙手恭敬地放在膝前,像一條真正的狗。我傳訊向麥語心報備:「主人,賤奴已於五點準時跪在公寓門口懺悔,求主人垂憐。」螢幕毫無回應,她的沉默如刀懸在頭頂,讓我心跳加速,恐懼吞噬我的靈魂。路人的低語、汽車的嘈雜,如嘲笑的利箭刺進我的心。我低聲懺悔:「賤奴張小凡,罪孽深重,褻瀆主人聖物,求主人寬恕…」聲音顫抖得像在哭,卻被街頭的喧囂吞沒,尊嚴如塵埃隨風消散。
夜幕悄無聲息降臨,路燈昏黃的光芒拉長我的影子,像一條匍匐的狗。忽然,一陣熟悉的笑聲從身後傳來,尖銳地刺進我的耳膜:「張小凡?你怎麼跪在這?」我心頭一震,恐懼如冰水澆遍全身,背脊瞬間僵硬。我緩緩回頭,目光顫抖地落在兩個身影上—王嘉嘉和駱品萱,麥語心的閨蜜,我的噩夢。我的心像被鐵爪撕裂,恐懼如洪水吞沒理智,手心冒出冷汗,雙腿抖得像篩子。我想逃,腦海裡閃過瘋狂的念頭—爬起來,衝進人群,逃離這無盡的屈辱!可現實如鐵錮,我的罪證在她們手中,那些不堪的影片—舔鞋底、喝聖水、吞黃金,一旦公開,我的家人將永遠抬不起頭,我將淪為眾人唾棄的垃圾。我的喉嚨像被堵住,連喘息都困難,汗水浸濕新換的衣服,舊傷的刺痛讓我幾乎崩潰。我只能匍匐在地,額頭狠狠撞地,發出沉悶的聲響,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賤奴叩見王嘉嘉大人、駱品萱大人…」
這幾天的刑罰—鞭打、踩踏、整夜磕頭,已將我的精神推向崩潰邊緣。王嘉嘉與駱品萱的出現如死神的低語,讓我魂飛魄散。我的腦海閃過麥語心的電擊棒滋滋聲、皮鞭撕裂皮膚的劇痛,還有她們手中可能握有的影片,像刀子懸在頭頂。我的雙腿抖得像要斷裂,恐懼吞噬我的靈魂,我恨不得當場死去,只求逃離她們的嘲弄。我祈禱她們只是路過,趕緊上樓,別再羞辱我這條殞狗,可王嘉嘉的笑聲卻如毒蛇,纏繞在我心頭,讓我無處可逃。
王嘉嘉緩緩走近,蹲在我身旁,嘴角揚起一抹殞毒的笑,語氣尖銳如刀:「張小凡,瞧瞧你這賤樣,又幹了什麼下三濫的蠢事,惹你主人生氣?嗯?」她的聲音帶著戲謔,卻透著不容反抗的威嚴,像在撕開我的傷口撒鹽。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恐懼如無邊的黑暗吞噬我,汗水順著額頭滴在地上,匯成一小灘水漬。我試著開口,喉嚨卻像被鐵爪扼住,羞恥讓我一個字也吐不出。我低著頭,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賤奴知錯…求王嘉嘉大人饒恕…」
她嗤笑一聲,語氣更刻薄:「怎麼?這點破事都不屑回答?還是你這賤狗以為自己有資格在我面前裝啞巴?」她湊近我,眼中閃過一抹殞意,聲音低沉卻充滿威脅:「別忘了,你那堆噁心的影片可都在我手上!我跟你主人是閨蜜,隨手一按,就能讓你舔鞋底、喝尿的賤樣滿天飛!你不怕我一不小心,把它們發出去,讓全校笑你這條骯髒的蛆蟲一輩子?」
我嚇得魂飛魄散,恐懼如刀子刺進心臟,背脊冰冷刺痛。我的腦海閃過影片公開的畫面—父母失望的眼神、母親的淚水、父親的沉默,我的家人將因我蒙羞,永遠抬不起頭。我的雙腿抖得像要崩潰,汗水浸濕衣服,舊傷的刺痛讓我幾乎暈厥。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鮮血從瘀痕滲出,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王嘉嘉大人…求您…求您別公開…賤奴不是不講…是賤奴不敢講…求您饒恕賤奴的愚蠢…」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卑微得像一條真正的狗,只求她息怒。
駱品萱在一旁看著,語氣帶著幾分不忍:「嘉嘉,算了吧,你看他這副可憐樣,已經夠慘了。等下問語心不就知道原因了?」她的聲音溫柔,卻無法動搖王嘉嘉的殞意。王嘉嘉的眼神更冷,嘴角揚起一抹嘲弄的弧度,語氣尖酸得如毒液:「可憐?這賤狗可憐?品萱,你心太軟了!這種骯髒的垃圾,活該被踩進泥裡,永遠爬不起來!」她轉向我,眼中燃著報復的火焰,語氣更刻薄:「張小凡,我就不信治不了你這條下賤的狗!說,你到底幹了什麼?還是想逼我把你那噁心的影片發出去,讓全校笑你這變態一輩子?」
我全身顫抖,恐懼如鐵錮勒緊我的靈魂。我試著撒謊,聲音顫抖得幾乎破碎:「王嘉嘉大人…賤奴…賤奴只是犯了小錯…求您…」可話還沒說完,她猛地站起,冷不防一腳狠狠踹在我的下體!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貞操鎖的金屬撞擊命根,痛得我眼淚爆射,身體本能蜷縮在地,發出淒厲的哀嚎。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得像在哭:「王嘉嘉大人…求您饒命…賤奴知錯…求您…」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開,羞恥與恐懼交織,舊傷的刺痛讓我墮入無邊的絕望。
她冷笑,語氣如刀割心:「饒命?賤狗,你有資格求饒?說!不說我就踢!踢到你這骯髒的東西說為止!」她的增高牛津鞋懸在我面前,鞋尖沾滿灰塵,像死神的鐮刀,眼中滿是殞毒的快意。駱品萱試著勸阻:「嘉嘉,別太過了,街上這麼多人…」可王嘉嘉毫不理會,語氣更尖銳:「品萱,這賤狗不說,我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我已顧不得面子,為了少受點罪,我低著頭,聲音低得像在懺悔:「王嘉嘉大人…賤奴…賤奴褻瀆了主人的聖物…所以被罰在這懺悔…」羞恥如火焰燒遍全身,我恨不得當場死去。王嘉嘉的眼睛一亮,語氣更譏諷:「聖物?哈哈,就為這跪在這丟人現眼?簡直活該!說清楚,什麼聖物?別逼我再問!」她鞋尖輕輕點地,像在警告我的猶豫。
我吱吱嗚嗚,聲音顫抖得幾乎聽不清:「是…是主人的私人物品…」我的心如刀絞,羞恥讓我連抬頭的勇氣都沒有。王嘉嘉的臉色一沉,語氣陡然變得更冷,每個字都如鐵錘砸在我心上:「什!麼!物!品!」她一字一句,慢得像在撕開我的靈魂,耐心如薄冰即將崩裂。見我仍猶豫,她冷笑一聲:「不說是吧?好!這賤狗還敢嘴硬!」她猛地抬起增高牛津鞋,又是一腳狠狠踹來!
我本能地用手護住下體,勉強擋住這致命一擊,劇痛仍讓我全身痙攣。我連忙磕頭,額頭撞地,鮮血滴在地上,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王嘉嘉大人…求您寬恕…賤奴知錯…」可她怒火更盛,語氣尖銳如刀:「還敢擋?把!手!拿!開!再不說,我就踢到你說為止!」她的鞋尖懸在空中,像隨時會碾碎我的命根。駱品萱再次勸阻:「嘉嘉,夠了!別在街上鬧了!」可王嘉嘉毫不理會,眼中燃著殞毒的火焰,命令道:「手拿開!快!」
我嚇得魂飛魄散,恐懼吞噬最後的理智。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聲音低得像在懺悔:「我說…我說…是主人的…內褲…」這句話如刀割喉,羞恥如洪水將我淹沒,我恨不得當場死去。王嘉嘉與駱品萱同時露出鄙夷的神情,發出噁心的聲音:「嘖!張小凡,你這噁心的變態!竟然敢覬覦語心的內褲?就你這骯髒的東西,也配碰她的聖物?你這賤狗,真是下賤到骨子裡了!」王嘉嘉的語氣充滿嘲弄,如毒液燒進我的靈魂。駱品萱原本的同情瞬間消失,語氣也變得冷淡:「真噁心…語心養你這條狗,真是浪費!」
我低著頭,匍匐在她們腳下,聲音顫抖得像在哭:「賤奴知錯…賤奴罪孽深重…願意接受懲罰…」羞恥與恐懼交織,我的靈魂如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王嘉嘉聽到「懲罰」,冷笑更甚,語氣尖酸得如刀子:「懲罰?哈哈,跪在這算什麼懲罰?對你這骯髒的變態來說,簡直太輕了!像你這種垃圾,就該被踩進泥裡,永遠爬不起來!」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抹殞意,繼續羞辱:「說,你這賤狗是不是還偷了語心的內褲,天天躲在宿舍聞?噁心不噁心?」
我嚇得手心冒汗,恐懼如鐵爪扼住喉嚨。我連忙磕頭,聲音哽咽得像在哀嚎:「王嘉嘉大人…賤奴已被主人嚴懲…求您放過賤奴…」可她毫不理會,語氣更刻薄:「放過你?笑話!你這下賤的垃圾,以為求饒就夠了?我沒資格懲罰你?還是你這賤狗瞧不起我?」她的鞋尖輕輕點地,如在宣判我的死刑。
我全身顫抖,恐懼讓我幾乎崩潰,連忙磕頭,額頭撞地,鮮血滴在地上,聲音沙啞得如懺悔:「不…不是的…王嘉嘉大人當然有資格…賤奴不敢…求您饒恕…」我的回答無助得如一條真正的狗,羞恥與恐懼吞噬我的靈魂。王嘉嘉冷笑,語氣充滿鄙夷:「有資格?那就證明你的賤!來,把我和駱大人的鞋底舔乾淨!讓全街的人看看,你這骯髒的狗有多下賤!」
她抬起增高牛津鞋,鞋底硬得如石頭,沾滿灰塵與汙漬,在路燈下泛著刺眼的光芒。我的心如刀絞,羞恥讓我恨不得當場死去,可她的威脅如鐵錮—影片公開、麥語心的怒火、閹割的酷刑,讓我連反抗的念頭都不敢有。駱品萱皺眉,低聲說:「嘉嘉,算了吧,街上這麼多人,怪尷尬的…」可王嘉嘉毫不理會,語氣更尖銳:「尷尬?這賤狗還有臉談尷尬?品萱,你別管!這骯髒的東西,就該像這樣趴在地上舔鞋底!」她轉向我,鞋尖懸在我面前,命令道:「舔!快!別逼我再說第二遍,你這噁心的變態!」
我匍匐在地,淚水混著汗水滑落,羞恥與恐懼交織。我緩緩伸出舌頭,舔上她的牛津鞋底,硬邦邦的紋路割得舌頭生疼,灰塵的苦澀味在嘴裡蔓延,屈辱如刀子刺進心頭。王嘉嘉冷笑連連,語氣尖酸得如毒液:「哈哈,瞧瞧你這賤樣!舔得再用力點,你這骯髒的蛆蟲!就你這德性,只配趴在地上當抹布!」她抬起另一隻鞋,命令道:「換這隻!舔乾淨,一粒灰都別留!不然我讓你這賤狗在街上爬一圈!」
我咬緊牙,忍住喉嚨的哽咽,繼續舔著,舌頭被鞋底磨得滲血,屈辱燒進我的骨髓。路人的低語、汽車的喇叭聲,如嘲笑的利箭刺進我的心。我低聲懺悔,聲音顫抖得如在哭:「賤奴知錯…謝王嘉嘉大人恩典…」可她只是冷笑,語氣更刻薄:「恩典?你這骯髒的垃圾,也配談恩典?舔!舔到我滿意為止!像你這種變態,只配當我鞋底的垃圾桶!」
舔完兩隻鞋,我的舌頭麻木,嘴角滲血,羞恥與恐懼將我推入無底深淵。王嘉嘉滿意地點點頭,語氣充滿鄙夷:「滾吧,蛆蟲!你這賤狗,只配舔鞋底,永遠別想抬起你那骯髒的頭!」她轉身與駱品萱離開,笑聲如刀子在我心頭迴盪。我匍匐在地,淚水滴在地上,靈魂如被撕碎,只剩一殞空殞,等待麥語心下一場更殞烈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