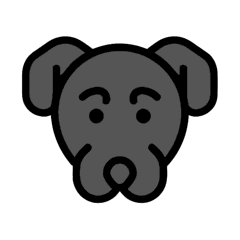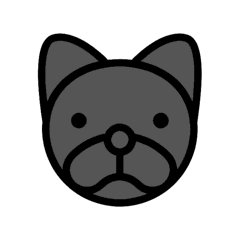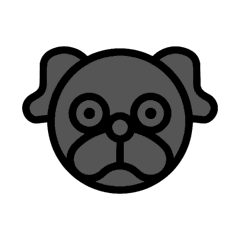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中篇】【5.22 完结】月下霜华怜香奴
女虐女足控已完结逆NTR束缚连载中原创玄幻妹妹大小姐强迫调教妓女百合NTR
本文登场角色如未提及性别默认全女。
本文不会出现任何血腥及R18G要素。
本文总计15w字,预计阅读时间7小时。
评论是最大的支持,谢谢你。
序章
风穿瓦缝,吹落一盏残灯,落地碎成几瓣金影。
苏家堡东厢庭院,杀声如雷,残兵断刃堆积成丘。剑戈交鸣之音早已止息,唯余战后血溅的沉静。
三十七名黑衣人,皆是江湖亡命徒,死士出身,今夜为一人而来——苏无恨。
苏家堡主,一刀成名,双手血债。江湖人前谈笑风生,私下咬牙切齿;多少旧仇新恨,都压在今夜风中。
“苏无恨!你血债盈山,今日拿你命还!”
“还你娘!”苏无恨怒啸如雷,踏血上前,身披玄黑劲装,刀出如霹雳坠地。他身如虎豹,步若雷奔,七星横岳刀劈开三人脑骨,一刀划出数尺血雨。
“你以为老子这把刀,是陪你唠嗑的吗!”
四方围杀,刀光交错,他步步杀出死路。每一斩,都是一命换一命;每一次喘息,都是靠血撑出的空隙。他肩头已被羽箭刺穿,血从锁骨奔流而下,掌心染得刀柄湿滑,可他仍像凶猛战鬼,咬牙不死。
左肩中一箭,咬碎箭杆反手插入敌喉。右臂被削半寸肌肉,他一吼,便以肘撞碎敌人颅骨。脚下滑倒时以膝震断来敌膝骨,跌下地面时翻身起落一刀封喉。血溅入眼,他便舔净唇角;血流入靴,他便赤足前踏。
仇人一人接一人,招招狠辣,死意十足,可谁都没想到——他竟杀到底了。
等到最后一个人倒下,那人脸上还残着一丝轻蔑,仿佛死前都不信自己会死。
苏无恨缓缓收刀,半边披风早已被血与火撕成碎片,长发凌乱垂下,发丝间是鲜血与碎骨混合的腥气。他一手扶柱,呼吸如破风箱般拉响,胸口鼓动得像将要爆裂的战鼓。
“娘的……就这点本事,也敢来苏家讨命?”
他吐了口血,啐在脚下尸体脸上。
可那股怒意却在这一瞬间,被突如其来的虚弱击碎了。
——手不见了。
披风下,那条手臂连着肩骨被硬生生削去,只余破肉残骨挂着焦黑的血痂。他想再挥一次刀。左肩一动,却猛然空荡如风,只有一抹撕裂的剧痛伴随残忍的空虚自肩窝撕扯开来。他看着自己空空的肩头,像是隔着三丈远在望别人的死相,竟一时恍惚,未生半分惊骇。甚至试图握刀,却只感到肌肉本能地抽搐了一下,旋即什么也握不住。
他的膝一软,几乎跪倒。胸膛里有东西在抽搐,每一口气都带出猩红,他知道——那些人虽死,自己的命也到了头。内腑裂断,气血倒冲,最毒那一剑已搅碎他心口,他不过靠着余意站着。
死,突然就不那么可怕了。
这辈子血杀百余人,灭门十数,威震江湖,却也恶名在外。他本该早死,只是迟了这几年而已。
他低头看向自己掌心,血已涌不出,只剩骨色泛白。
他缓缓闭眼,长长吐出一口气,如山卸下。
那口气落地的一瞬,他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清晨蹒跚学步的婴孩,穿着他亲手缝的紫绣肚兜,满脸奶渍地趴在厅前地毯上,一把抓住他刀柄就往嘴里塞;那个曾缩在他怀里睡着,小小一团,只要有人高声说话就吓哭,非得他拍着背才能安稳;那个气得他要打人又舍不得动手的娇小姐,背着他偷溜出堡学骑马,摔了满屁股泥,回来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不怕摔!”
他一想到苏怜月,忽然就不舍了。
他这一辈子,血腥够了,仇杀够了,罪也够了。可她还没长大。她还没嫁人。她还没知道江湖的腥风血雨是什么味道。
她不该知道。
于是他缓缓转头,像寻找一个影子,像抓住那根尚未断裂的线。他喉头发紧,眼中只剩余火一寸,低声唤道:
“霜儿——”
他的声音拖得很长,不像平日那样洪亮,甚至带着难得一见的脆弱。
下一瞬,一道冷香袭来——
那是霜华,凌霜华。
苏无恨一手教出来的凶器。
苏无恨眸中倒映着她的脸——那是一张藏不住风情的脸,像是艳阳底下割人眼睛的利刃,生来就让人目眩神迷。眉如远山冷翠,不施粉黛却勾魂摄魄;一双眼似秋水流霜,寒中带媚,媚里藏锋。肌肤细白胜雪,仿若剥壳鸡蛋,透出微光;唇不厚却艳,颜色天然如胭脂点绛,动一下便似勾魂摄魄。
她年岁二十有三,颈项修长,锁骨若羽翼初展,向下是一对挺拔雪乳,鼓胀得连衣襟都紧紧绷起,微一喘息就看得见那层层细布上下微动,如有跳鱼在内搏动。她腰身纤却不削,曲线如玉瓷般流畅,偏偏臀圆肉丰,腿生得极长,站着便如一尊雪地妖像,跪着也像斩人的刀鞘。天生媚骨入骨三分,即便什么也不做,光是站在那里不动,便让男人目光发滞、口干舌燥,连老僧也难保心中不起涟漪。
可这身媚骨偏生裹着杀气,一举一动皆如拔刃而出。
她出身妓寮边界的乱尸堆,婴儿时被人贩子随手扔进臭水沟里,是无恨在那年江南平叛中捡了回来,带回堡里亲自养大。
他说,这孩子命硬,寒中出骨,皮白不化。就起名‘凌霜华’。
苏无恨不教她女红不教她礼仪,只教她杀人。
她一手霜刃,劈过十方仇敌;一身冷艳,勾过多少魂魄。人说她的刀是妖,劈开人身也劈烂人心。可更多人说,她这张脸才是妖,出刀时势快,脱衣时肉美,最是那一记“断霞横燕斩”,施展时下盘翻腾,白润大腿挟裹着力道扫出,刃随胯转,腰随膝摆,每一寸肌肉都抖出春波,连招式收尾都带着余韵,让人不知是该捂住胸口避锋,还是跪倒下去甘愿死在她胯下。
她战斗的姿态比风月楼最艳的舞姬还动人:轻身上墙,玉乳前挺,刀出则峰跳乳颤,身翻则腰肢乱摆,密布汗珠的脊背划出优雅弧线,臀肉因发力而微震,裆下那一片紧裹的薄布湿得紧贴肌肤,杀一人如梦中婀娜,残一命如春夜呻吟。
因此江湖里传她为“霜刃玉姬”,可没人敢当面调笑。
曾有南边采花贼头子在酒楼高谈阔论,言笑晏晏地说:“这凌霜华……长得那般样子,何不让我收作压寨夫人,每夜骑她三回倒也不冤……”
第二日清晨,他的头被人提到酒楼桌上,七窍流血,笑容仍僵着。喉咙被人以极薄刀锋削断,创口细如发丝,血未喷出已气绝。旁人只在额顶看见一行小字,似是刀尖所刻:
“你可知她腰软,但可知她刀比你命硬?”
还有一次,夜色未央,霜华一身夜行衣翻过三道檐角,只为追杀一个刺客。她一刃封喉,转身跳下屋顶,那一跳的落势惊艳了酒楼满堂。有人说只见那女侠腿间一抹红光一闪,似有春水荡漾于腿缝之中,跃下时衣摆翻飞、雪乳晃动,连那月下的风都多看了她一眼。
那刺客的尸首整整三日才从屋后下水道被人捞出,腹破肠流,脸带惊恐,瞳孔中还映着那张冷艳美艳的脸。
没人再敢胡说。
她是苏无恨亲手打造的妖刃,一柄藏在香脂与媚骨中的杀器,一身淫色藏锋,一身肉香带血,一脚踏进风月,却无人敢言轻薄半句。
因为她不是谁的玩物,而是苏家堡的禁脔——只认一个主,只听一个人说话。
只是那个主人,即将死去。
“义父!”
苏无恨一把抓住她手腕,掌心沾血,骨节僵冷。他的呼吸已不匀,眼神却越发清明。
“别说话,听我。”
“你记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话一个字一个字砸进她耳里,“怜儿……不能沾血。她不该走我这条路。不该见这满院尸首……不该知道,她爹爹……是个杀人鬼。”
他嘴角浮现一丝苦笑。
“你是我一手养大的。你曾问我,这把刀将来要给谁。我没说——其实,是她。”
说着,他缓缓抬手,从断臂的血腰间摸出那柄熟悉的刀——七星横岳。
鞘上满是干涸的血,银星已被血污黯了光,唯有刀柄处一截握痕仍清晰如旧。
他用尽全身仅余的力气,将它横着递到霜华怀中,指骨青白,刀却未颤。
“可现在……我要你,收起它。”
“别让她像我这样……别让她,沾进这些腥风血雨。”
“保护好她,霜...儿...”
说完这句话时,他手指一松,终于垂落地面。那柄刀也随之微微一响,落在霜华臂弯中,如一段旧命运,沉重地安歇。
满院静寂,唯余风穿过断廊,带起一阵微冷。夜还未亮,苏家堡血未冷。
而霜华,在血泊中抱着他缓缓冷却的尸体,一字不发地跪着。
她指尖轻拂苏无恨的血衣,手指死死扣住刀鞘上那枚绣着“怜”字的香囊。那是苏无恨随身佩戴之物,里头包着初生之时女儿抓住的一缕胎发。血已经浸透了它,那一抹“怜”字像要滴下泪来。
“我会护她。”她低语,嗓音不见起伏,却冷得仿佛刀尖拂雪,“如你所愿,她这一生不会染血,不闻杀,不知江湖。”
她抬起头,那张冷艳脸庞沾着血,眼神却比雪山寒三分。
“但若她有半点风吹草动,我会让这江湖,从此为她一人流血如雨。”
那一刻风吹残灯,暮色深沉。霜华缓缓起身,披着满身血与夜色,才一转身,却忽然怔住。
月光下,走廊尽头,一个小小的人影怯生生地立着。
她穿着紫色的缎面小袍,脚踏绣云布靴,一只手还揉着惺忪睡眼,另一只手抓着栏杆。十二岁的苏怜月,额前碎发微乱,小脸未脱稚气,却生得眉目如画,已初见倾城之姿。
“霜姐姐……”她声音软软的,带着一丝刚睡醒的鼻音,眼睛却渐渐瞪大,看向血迹斑斑的地面,“爹爹呢?是不是有人闯进来了?你……你怎么满身是血?”
那一瞬,凌霜华仿佛被人扼住了呼吸。
她从未怕过什么,不怕敌人,不怕阴谋,不怕死,更不怕被刀捅穿肚腹。可在那双干净的、还不知人世险恶的眼睛面前,她忽然觉得满身的血和杀意是种不堪入目的肮脏。
她快步上前,单膝跪下,将怜月一把搂入怀中。苏怜月一惊,嗅到她怀里的血味,忍不住瑟缩一下。
“别看,”霜华的声音一改冷冽,柔了几分,手掌护在她眼前,低声道,“只是几个小贼闯了进来,已经处理了。”
“爹爹呢?”小姑娘颤着嗓子问,“他不是说今儿要教我练骑马么?”
霜华闭了闭眼,胸口剧烈起伏一次,强自镇定地牵起她的手。
“他有急事出门了。”霜华轻声哄道,“去了……去了江北边境,明日就给你带回来你最想要的那匹白蹄马。你乖,别让爹爹失望。”
苏怜月噘了噘嘴,似懂非懂地咕哝:“他总说带我出门都不带……”
她低下头,摸了摸霜华腰间的刀,手指冰凉,像在寻求一点安慰。
霜华喉头一涩,俯下身轻轻抱起她,一步一步,抱她走出满院腥风血雨。
她走得极稳,极轻,不让那柔软的怀中人有一丝颠簸。
“霜姐姐,我怕……”苏怜月在她怀里瑟缩着,小手紧攥她衣襟,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你唱首歌好不好……你一唱,我就不怕了……”
霜华轻轻“嗯”了一声,嗓音低沉沙哑,却依旧唱了,是她记得最清楚的一首小调——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
“你不问江湖几许险,我便替你踏断刀剑山。”
五年,江南换了四轮春秋,苏家堡却始终寂静如初。坊间传言,堡主苏无恨远征边疆,战未休归期未定,堡中政事由义女凌霜华暂摄。而苏家小姐苏怜月,则由凌霜华照拂教养,谨守闺门,不涉江湖。
其实人都知道,苏无恨早已魂归九泉,只是没人敢问,没人敢说。
而真正将那秘密压进心底的人,是苏怜月。
她今年十七,出落得越发如画。
柳眉生得纤长入鬓,眸中带雾,一笑便仿佛春水漾开。身段高挑纤柔,腰肢细得一手可握,肌肤若雪胜脂,行走时香风盈盈。那副天生贵气的骨相里,却藏着父亲一样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是被霜华硬生生压了五年。
她每日起居皆被安排得妥帖,一应食衣无不精致。
身边配了三位贴身婢女,两个教书的夫子,一个琴师,一个女红师傅。花房诗画、香粉丝竹,处处精雕细琢,仿若一位天家公主而非江湖女儿。
只是她从未见过苏家堡的武器库,只被允许在后山亭内读书听琴。每次她问起家中旧事,霜华都冷着脸回一句:“等你十八。”
“父亲呢?”她年幼时曾反复问过。
“他在边疆。”霜华从不多言,神情如铁,“替你守国。”
可那年她十三岁,在园中藏书阁无意中看到一页旧信,内容只寥寥数语:“堡主战死,血战三十七人,尸满前庭。”
她恨自己识字。
她没有哭,只是当天夜里烧毁了那封信,第二日笑着对霜华说:“我梦到爹爹了,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看我。”
霜华微怔,却依旧不语,只在她额前轻抚一下。
那抚摸极轻,极冷,如月色穿过窗纸,如她这些年来所有的温柔,全藏在那一下呼吸之间。
自那之后,她便不再问了。
可没人知道,她夜里常梦见血,从那年起就在梦里看到长刀劈裂石柱,看到父亲断臂握刀的模样。她知道爹爹死了,知道自己身负苏家血脉,也知道霜华一直在骗她。
那不是善意的谎言,而是一种温柔至极的阉割。
霜华用柔情将她包裹,把刀藏进锦被,把杀气藏进茶香,用一整座宅子的静谧与礼教,把她从血海里捞起来,放进温泉里泡软了骨头、洗干净命运的腥味。
她的保护是一种围困,是一种把“权”与“血”从她人生中彻底切割出去的谋算。霜华不是不愿她去报仇,而是连“报仇”这种词,都不愿她学会。她不想她成为苏无恨的女儿,只想她成为任何人的妻、任何门第的花,不问过往、不认血债,最好连苏这个姓也慢慢淡了。
那不是爱。那是怕。怕她长成她父亲那样的刀,怕那条路再斩出一个血流成河的下场。
而怜月恨的,就是这种“怕”。
怕得太狠了,就像是把她的人生连根拔起、扔进一个无风的世界。她活着,却像是被温柔地埋了。
这让她厌恶。
于是她开始学会压抑、学会笑,学会用看似乖巧的语气说出轻飘飘的命令。
她开始享受发号施令的感觉。
起初是让贴身婢女跪着帮她换鞋,后来是让婢女含着茶水喂她喝。再后来,她用刺绣针扎错一线,便罚人跪到流血,理由只是“不好看”。
但她喜欢看她们哭时求饶的样子。
她笑着伸脚,叫人用舌头舔净鞋底,语气却软得像在请人吃点心。她一边摆弄发髻,一边欣赏她们抖着跪下时的模样,像是在看一场闲极无聊的傀儡戏。
而霜华终于意识到——这孩子,已然长成了另一个苏无恨。只是披着更温柔的皮,笑得比谁都乖巧,心比她那已故的义父,还要狠三分。
苏家堡,暮春。
梨花初谢,桃李盈墙。内院回廊之下,一排婢女战战兢兢跪伏在地,个个垂首不敢抬头,唯恐触了那位小姐的霉头。
而场中那位身着粉白交领襦裙的少女,正懒懒地倚靠在玉雕椅榻上,纤手撑颊,玉足半露,正由人替她慢慢拂尘。
苏怜月今年十七。
眉目温婉,肤白若脂,唇不点而红,眸中似有水意浮动。她生得极清纯,极乖巧,一笑便似春日桃枝含苞,叫人不忍怠慢。可唯有靠近她的人才知——她那双眼里没有一点孩子气的怯意,而是一种极稳、极静的掌控者之眼。像从血泊里浮出的珠泪,看着软,骨子里是寒的。
她今日心情不好。
绿杏跪在她脚下,脸色惨白如纸,身子止不住地颤。
“你自己说。”怜月嗓音柔柔的,仿佛春日清风,“那盏盏,是我最喜欢的白瓷莲杯。你怎么打碎的?”
绿杏今年十五,眉眼还未长开,身子却已发育得颇有曲线,胸口圆润,腰细腿长,一身青衣绣花小袄,胸口上方一片水渍未干——方才是她摔了茶水才砸了杯盏,脸上还挂着滚烫水珠之后的红痕。
“小姐,奴婢……奴婢不是故意的。”绿杏磕头,额上冷汗如雨,“是手滑了……求小姐开恩……”
“手滑了?”怜月一声轻笑,眉眼未挑,笑意却不达眼底,“这茶水若是泼在我身上呢?你是不是也说——手滑了?”
她伸出脚,轻轻蹭了蹭绿杏的下巴。
那脚白得几近透明,十趾细巧,趾甲涂着淡粉。她脚踝极细,足弓高耸,皮肉柔腻光润,像是养在锦被玉盆里从未沾尘的尤物。
“抬起头来。”她轻声道。
绿杏被逼抬头,正好迎上一只玉足抵在她脸颊。怜月脚趾微动,慢慢蹭着她的泪痕,又缓缓滑下,从鼻梁、嘴唇一直划至她颈项,脚趾勾住她衣领,轻轻一挑,衣襟乍开一线。
“我记得你胸口挺得很好。”她语气依旧温和,“是不是还没发育完全?给我瞧瞧。”
“小姐……”绿杏哽咽得几近不能出声,却不敢反抗。
怜月的玉足便这样探入她襟中,一寸寸挑开里衣,将那一对白嫩丰盈的小乳肉从衣襟中剥出来。绿杏哭着咬牙,却又羞又疼地忍着,直到怜月脚趾勾住她乳头,慢慢揉碾,眼里才浮现真正的绝望。
“嘶……这反应倒不错。”怜月垂眸轻笑,目光落在那微颤的乳头上。
她脚趾缓缓按压,碾揉乳尖,再一勾,绿杏身子剧烈一颤,竟低低地呻吟了一声,羞得整张脸都烧红了。
怜月一脸无辜地笑道:“怎么,你还喜欢?”
她一脚踹翻绿杏,让她趴伏于地,玉足伸入她裙底,沿着大腿内侧一路挑弄,直到贴近私处,才缓缓在那湿润一片的布料上来回摩擦。
“这地方也挺滑。”她语气温柔得像在说天气,“是不是怕得出汗了?”
她脚趾在那片细嫩肌肤上轻轻画圈,时不时用脚尖挑起些皮肉,像猫挑弄虫子那般有耐心。绿杏哭着发抖,手指死死攥紧地上的褶布,却不敢反抗,甚至不敢夹腿,怕惹来更狠的对待。
怜月忽然用脚背一勾,将绿杏整条腿扒开,姿势粗暴得近乎羞辱。
“唔……哈……小姐……”绿杏的声音已经带上哽咽的颤音,像断弦的琴,声音不成调。
怜月低头俯瞰她,像看一件终于服软的玩具,微微一笑,又将足尖探入那湿透的裙褶,轻轻一顶——
绿杏尖叫一声,整个人猛地拱起身子,却被怜月用另一只脚死死踩住后腰,动弹不得,只能颤抖着伏在地上,羞耻和快感像滚烫的铁汁一起灌入骨髓。
她哭得眼角尽红,却不敢再求饶,只能咬唇强忍,像狗一样趴着,任人戏弄。绿杏的俏身抽搐着一抖,那一刻终于绷断,娇躯猛地一颤,蜜肉痉挛间竟在地上泄了出来,湿意浸透裙裾,甚至带出一滩滚热的清尿,沿着她大腿根一路蜿蜒而下,竟湿了怜月垂落在榻下的绣履一角。
绿杏猛然意识到这一点,瞳孔骤缩,仿佛从迷乱中被雷霆惊醒。
她脸色瞬间惨白,身子一软,连滚带爬地跪伏在怜月脚边,额头重重磕地,“砰砰”作响,声音颤抖中带着破音:
“小姐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弄脏小姐的鞋……奴婢该死,真的该死……求您、求您饶命……”
绿杏崩溃地哭了,而四周所有下人,包括她同房的婢女们,皆面如死灰,不敢出声。
无人敢上前,甚至无人敢发出呼吸声。
哪怕她不是堡主,哪怕她没有实权,可这五年来,她的眼神、她的气场、她的手段,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忤逆她者,轻则受辱,重则废去。
怜月终于厌倦了戏耍,收回玉足,一扬手。
“藤杖——三十。”
下人早已备好,一名年长婆子双手奉上,她接过轻巧地一甩。
“自己数着,抽够三十不准偷懒。”她语气轻快,“若哭得太小声,我就加十。”
绿杏身子颤抖,却只能咬牙趴好,将裙摆撩至腰间,露出一片已红肿的雪臀。藤杖落下,啪啪作响,每一下都像打在人心上。
五杖,十杖,二十杖。
她已哭到声音嘶哑,屁股红肿如熟桃,鲜红的血丝一条条从臀缝沁出。可怜月面无表情,指尖拨弄茶盏,仿佛听戏。
就在第二十九杖落下那一瞬,一道熟悉而压迫的声音响起:
“够了。”
众人心头一凛,抬眼望去——
是凌霜华。
她立于花廊之上,一袭墨色宽袖长袍,胸前半束腰封,身姿高挑冷艳。五年过去,她的容貌不仅未衰,反而更加风情万千。那身天生媚骨如今已完全长开,胸更高挺,腰更柔细,臀更圆润,走一步都似春波荡漾,连袍下走动时的腿线,都牵动着人心躁动。
而在她腰间,一柄古刀静静垂挂,鞘黑如墨,金丝缠脊,刀背嵌有七颗寒星状的银芒,隐隐如北斗排阵,锋寒不露却压得人喘不过气。那正是苏无恨的佩刀——七星横岳。
这刀一出,无需出鞘,便叫人想起苏无恨当年血洗武林时的腥风血雨。而如今,它悬在凌霜华的腰间,刀未动,意已至。
她不需声张,只需立在那里,苏家堡上下就没人敢不俯首低眉。
也只有她,能镇得住苏怜月那股天生的疯劲。
她的脸依旧冰冷,却那种冷,是压抑了欲望的冷,是越压抑越勾魂的冷。
“她的反省够了,回房。”霜华淡淡道。
“她砸了我的杯。”怜月缓缓起身,裙摆落地如云,“我只是在教她怎么做人。”
“你当然有的是权。”霜华淡声道,“但你是苏家堡未来的女主,可不是个疯婆子。”
“那你是觉得我疯?”怜月眼眸一转,笑意却更深,“你教我琴棋书画,却不教我剑术权谋,告诉我爹在边疆却不许我追问,你让我做一个‘小姐’,可我姓苏,苏家是怎么立的你不比我清楚?你让我做什么?当个会绣花的死人?”
霜华沉默,片刻后,只道:
“休得多言,回房,禁足一周,该你反省。”
怜月站在廊前,背影笔直,眼里怒火涌动。
最终她一言不发,缓缓转身,裙摆拂过地面时像把慢抽出鞘的刀。
她走回闺房的每一步,脚下都是碎花,心中却是血池。
夜已深,灯未熄。藏月轩内香炉微燃,一缕檀香缠绕帷幔。
凌霜华卸下墨袍,仅着一袭素白中衣,立于轩前。灯火映出她五年后更加凌厉的身形,冷艳之中更添成熟之色。她天生媚骨,年少时是风中利刃,而今的她,已如雪地沉刀——越沉,越锋,越艳。
她的胸更饱满,腰更窄细,臀更圆润丰盈,皮肤雪白如玉,连肩胛骨都带着不容忽视的线条感,仿佛每一道曲线都暗藏力量与风情。最惹人心悸的,是她那双眼,冷得像盔甲,却在夜色中透出一丝人前不露的疲惫与眷恋。
一双柔臂从她身后绕来,轻轻环住她的腰。
“又在发呆。”
声音如玉铃敲雪,软糯中带着点撒娇。
“你不是说过,不许独自站在夜里吹风,会寒入骨。”
她没有回头,却已轻轻叹了口气。
“清音。”
沐清音,天音阁前圣女,外人皆传其冰肌玉骨、心如止水,实则……她是藏得最深的那团火。
她今年二十有四,长身玉立,肌肤胜雪,五官温柔得像画,眼中却藏着水波流转。她一身素纱薄衫,赤足入室,身姿婀娜,胸前两团柔腻随步轻晃,饱满柔软得不像凡尘女子。她步履轻盈,腰肢如柳,身下那片轻纱薄得几乎遮不住她的私处轮廓,连腿根隐隐可见一丝潮意。
她是医生,也是琴师。
但她还说是凌霜华的恋人——唯一一个能勾起霜华情欲的人。
两年前,怜月忽染恶疾,霜华遍寻名医无果,火烧眉头之际,方从一位故交口中得知天音阁有一人,医术极妙,素日不问世事,只以音律养心。霜华亲自三赴山中请人,见她第一眼,便如见清雪覆火山,气静神动,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缕执念。
自此,清音便随她回了苏家堡,住进花阁西苑,一为医,一为琴。平日怜月身子无恙时,便随她习琴;身子不快时,她亦会调香制汤、推功引气,甚至夜夜守在床畔,用指尖温揉她心口脉络,让那颗躁烈之心渐归平缓。
而霜华也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心结微动。
她原以为清音这等人,只该远望。可她未曾想到,清音亦会为她停步。
不是惊雷,不是骤火,是灯火入夜,是雪落无声——她们之间的情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燃了起来。
“你今日,又罚了怜月。”清音温声道,手指顺着她腰窝滑下,指尖轻轻勾过她腹部的肌肤,“她的性子,越来越像你说的那位老苏堡主了。”
霜华不语,只是闭了闭眼。
“我知道你压着她,是怕她血路走早,走死。”清音贴在她背上,声音愈发轻柔,“可她……终归不是你养得住的。”
“我不想你再被这些事困着。”她顿了顿,手伸到霜华胸前,轻轻握住那一对冷艳雪乳,指腹揉捻,“你从十岁就开始杀人,十七岁出师,十九岁为苏家断后,二十三岁埋了他,二十八岁还在替他养女——霜华,你已经还够了。”
霜华的身子微微一震。
她不回应,可胸前的乳头已在清音指间悄然硬起。那点反应,不是爱欲太深,而是……太久压抑。
“跟我走吧。”清音吻上她颈侧,唇湿如露,“不去北境,不去江湖。我们去东海,去南山,种田、采花,你下地种菜我织绣调香。你若还爱舞刀弄剑,就舞给我一个人看。”
霜华沉默良久,终是握住她的手指,从自己胸前挪开。
“不行。”
“为什么?”清音轻声问,眼中却有一点委屈。
霜华转身,低头看她,眼神复杂。
她从不说谎,不逃避。她只是太冷,太压着,把什么都藏进骨头缝里。
“苏家救我,教我,养我。若我现在走,便是弃义。”
“你觉得你欠他们。”清音低声说,“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两年来,一直在你身边,却从来排不过她?”
霜华眉头动了一下:“清音……”
“我没有生气。”清音摇头,凑近她鼻尖,“我只是……怕你一辈子都困在她身边,看着她成了你义父的影子,却不能脱身。”
“她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她长大了,也不会再听你话。出生苏家,她总会有她的道,她的江湖,她的血路。你以为你还能护她一生?”
霜华缓缓吸了口气,终于低声道:
“再等两年。”
“她十八岁后,嫁出去。我便不再管。”
“到那时,我便跟你走。”
清音怔了一下,眼中水光微闪,笑意仿佛停在唇角未绽之处。她不是听不出那句“再等两年”又是一场推脱,只是那一点点失落,来得太轻,也太快。
她不愿让它停留在脸上。
指尖轻轻一紧,她像是想握住什么,又轻轻放开,随即轻笑,像春水翻起一层柔波,扑进她怀中,声音带着撒娇的气音:
“你说的,不许反悔。”
“嗯。”
“那你今晚……也别冷着我了。”她语气一转,唇已吻上霜华锁骨,纤手探入她衣内,指尖滑入雪峰之间。
霜华低喘一声,终于也伸手环住她纤腰,将她压在榻上,眼神里浮起少见的欲意。
她俯身咬住清音乳尖,温热湿润的舌尖卷着那嫣红小点缓缓揉舔,清音的娇喘顿时从喉中逸出,指甲已抓紧她肩头。
腿交缠,香汗交融。衣衫零落间,一双素足翻过锦褥,带乱了烛影,扰动了帷幔,也搅碎了她们守了太久的矜持。
本文不会出现任何血腥及R18G要素。
本文总计15w字,预计阅读时间7小时。
评论是最大的支持,谢谢你。
序章
风穿瓦缝,吹落一盏残灯,落地碎成几瓣金影。
苏家堡东厢庭院,杀声如雷,残兵断刃堆积成丘。剑戈交鸣之音早已止息,唯余战后血溅的沉静。
三十七名黑衣人,皆是江湖亡命徒,死士出身,今夜为一人而来——苏无恨。
苏家堡主,一刀成名,双手血债。江湖人前谈笑风生,私下咬牙切齿;多少旧仇新恨,都压在今夜风中。
“苏无恨!你血债盈山,今日拿你命还!”
“还你娘!”苏无恨怒啸如雷,踏血上前,身披玄黑劲装,刀出如霹雳坠地。他身如虎豹,步若雷奔,七星横岳刀劈开三人脑骨,一刀划出数尺血雨。
“你以为老子这把刀,是陪你唠嗑的吗!”
四方围杀,刀光交错,他步步杀出死路。每一斩,都是一命换一命;每一次喘息,都是靠血撑出的空隙。他肩头已被羽箭刺穿,血从锁骨奔流而下,掌心染得刀柄湿滑,可他仍像凶猛战鬼,咬牙不死。
左肩中一箭,咬碎箭杆反手插入敌喉。右臂被削半寸肌肉,他一吼,便以肘撞碎敌人颅骨。脚下滑倒时以膝震断来敌膝骨,跌下地面时翻身起落一刀封喉。血溅入眼,他便舔净唇角;血流入靴,他便赤足前踏。
仇人一人接一人,招招狠辣,死意十足,可谁都没想到——他竟杀到底了。
等到最后一个人倒下,那人脸上还残着一丝轻蔑,仿佛死前都不信自己会死。
苏无恨缓缓收刀,半边披风早已被血与火撕成碎片,长发凌乱垂下,发丝间是鲜血与碎骨混合的腥气。他一手扶柱,呼吸如破风箱般拉响,胸口鼓动得像将要爆裂的战鼓。
“娘的……就这点本事,也敢来苏家讨命?”
他吐了口血,啐在脚下尸体脸上。
可那股怒意却在这一瞬间,被突如其来的虚弱击碎了。
——手不见了。
披风下,那条手臂连着肩骨被硬生生削去,只余破肉残骨挂着焦黑的血痂。他想再挥一次刀。左肩一动,却猛然空荡如风,只有一抹撕裂的剧痛伴随残忍的空虚自肩窝撕扯开来。他看着自己空空的肩头,像是隔着三丈远在望别人的死相,竟一时恍惚,未生半分惊骇。甚至试图握刀,却只感到肌肉本能地抽搐了一下,旋即什么也握不住。
他的膝一软,几乎跪倒。胸膛里有东西在抽搐,每一口气都带出猩红,他知道——那些人虽死,自己的命也到了头。内腑裂断,气血倒冲,最毒那一剑已搅碎他心口,他不过靠着余意站着。
死,突然就不那么可怕了。
这辈子血杀百余人,灭门十数,威震江湖,却也恶名在外。他本该早死,只是迟了这几年而已。
他低头看向自己掌心,血已涌不出,只剩骨色泛白。
他缓缓闭眼,长长吐出一口气,如山卸下。
那口气落地的一瞬,他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清晨蹒跚学步的婴孩,穿着他亲手缝的紫绣肚兜,满脸奶渍地趴在厅前地毯上,一把抓住他刀柄就往嘴里塞;那个曾缩在他怀里睡着,小小一团,只要有人高声说话就吓哭,非得他拍着背才能安稳;那个气得他要打人又舍不得动手的娇小姐,背着他偷溜出堡学骑马,摔了满屁股泥,回来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不怕摔!”
他一想到苏怜月,忽然就不舍了。
他这一辈子,血腥够了,仇杀够了,罪也够了。可她还没长大。她还没嫁人。她还没知道江湖的腥风血雨是什么味道。
她不该知道。
于是他缓缓转头,像寻找一个影子,像抓住那根尚未断裂的线。他喉头发紧,眼中只剩余火一寸,低声唤道:
“霜儿——”
他的声音拖得很长,不像平日那样洪亮,甚至带着难得一见的脆弱。
下一瞬,一道冷香袭来——
那是霜华,凌霜华。
苏无恨一手教出来的凶器。
苏无恨眸中倒映着她的脸——那是一张藏不住风情的脸,像是艳阳底下割人眼睛的利刃,生来就让人目眩神迷。眉如远山冷翠,不施粉黛却勾魂摄魄;一双眼似秋水流霜,寒中带媚,媚里藏锋。肌肤细白胜雪,仿若剥壳鸡蛋,透出微光;唇不厚却艳,颜色天然如胭脂点绛,动一下便似勾魂摄魄。
她年岁二十有三,颈项修长,锁骨若羽翼初展,向下是一对挺拔雪乳,鼓胀得连衣襟都紧紧绷起,微一喘息就看得见那层层细布上下微动,如有跳鱼在内搏动。她腰身纤却不削,曲线如玉瓷般流畅,偏偏臀圆肉丰,腿生得极长,站着便如一尊雪地妖像,跪着也像斩人的刀鞘。天生媚骨入骨三分,即便什么也不做,光是站在那里不动,便让男人目光发滞、口干舌燥,连老僧也难保心中不起涟漪。
可这身媚骨偏生裹着杀气,一举一动皆如拔刃而出。
她出身妓寮边界的乱尸堆,婴儿时被人贩子随手扔进臭水沟里,是无恨在那年江南平叛中捡了回来,带回堡里亲自养大。
他说,这孩子命硬,寒中出骨,皮白不化。就起名‘凌霜华’。
苏无恨不教她女红不教她礼仪,只教她杀人。
她一手霜刃,劈过十方仇敌;一身冷艳,勾过多少魂魄。人说她的刀是妖,劈开人身也劈烂人心。可更多人说,她这张脸才是妖,出刀时势快,脱衣时肉美,最是那一记“断霞横燕斩”,施展时下盘翻腾,白润大腿挟裹着力道扫出,刃随胯转,腰随膝摆,每一寸肌肉都抖出春波,连招式收尾都带着余韵,让人不知是该捂住胸口避锋,还是跪倒下去甘愿死在她胯下。
她战斗的姿态比风月楼最艳的舞姬还动人:轻身上墙,玉乳前挺,刀出则峰跳乳颤,身翻则腰肢乱摆,密布汗珠的脊背划出优雅弧线,臀肉因发力而微震,裆下那一片紧裹的薄布湿得紧贴肌肤,杀一人如梦中婀娜,残一命如春夜呻吟。
因此江湖里传她为“霜刃玉姬”,可没人敢当面调笑。
曾有南边采花贼头子在酒楼高谈阔论,言笑晏晏地说:“这凌霜华……长得那般样子,何不让我收作压寨夫人,每夜骑她三回倒也不冤……”
第二日清晨,他的头被人提到酒楼桌上,七窍流血,笑容仍僵着。喉咙被人以极薄刀锋削断,创口细如发丝,血未喷出已气绝。旁人只在额顶看见一行小字,似是刀尖所刻:
“你可知她腰软,但可知她刀比你命硬?”
还有一次,夜色未央,霜华一身夜行衣翻过三道檐角,只为追杀一个刺客。她一刃封喉,转身跳下屋顶,那一跳的落势惊艳了酒楼满堂。有人说只见那女侠腿间一抹红光一闪,似有春水荡漾于腿缝之中,跃下时衣摆翻飞、雪乳晃动,连那月下的风都多看了她一眼。
那刺客的尸首整整三日才从屋后下水道被人捞出,腹破肠流,脸带惊恐,瞳孔中还映着那张冷艳美艳的脸。
没人再敢胡说。
她是苏无恨亲手打造的妖刃,一柄藏在香脂与媚骨中的杀器,一身淫色藏锋,一身肉香带血,一脚踏进风月,却无人敢言轻薄半句。
因为她不是谁的玩物,而是苏家堡的禁脔——只认一个主,只听一个人说话。
只是那个主人,即将死去。
“义父!”
苏无恨一把抓住她手腕,掌心沾血,骨节僵冷。他的呼吸已不匀,眼神却越发清明。
“别说话,听我。”
“你记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话一个字一个字砸进她耳里,“怜儿……不能沾血。她不该走我这条路。不该见这满院尸首……不该知道,她爹爹……是个杀人鬼。”
他嘴角浮现一丝苦笑。
“你是我一手养大的。你曾问我,这把刀将来要给谁。我没说——其实,是她。”
说着,他缓缓抬手,从断臂的血腰间摸出那柄熟悉的刀——七星横岳。
鞘上满是干涸的血,银星已被血污黯了光,唯有刀柄处一截握痕仍清晰如旧。
他用尽全身仅余的力气,将它横着递到霜华怀中,指骨青白,刀却未颤。
“可现在……我要你,收起它。”
“别让她像我这样……别让她,沾进这些腥风血雨。”
“保护好她,霜...儿...”
说完这句话时,他手指一松,终于垂落地面。那柄刀也随之微微一响,落在霜华臂弯中,如一段旧命运,沉重地安歇。
满院静寂,唯余风穿过断廊,带起一阵微冷。夜还未亮,苏家堡血未冷。
而霜华,在血泊中抱着他缓缓冷却的尸体,一字不发地跪着。
她指尖轻拂苏无恨的血衣,手指死死扣住刀鞘上那枚绣着“怜”字的香囊。那是苏无恨随身佩戴之物,里头包着初生之时女儿抓住的一缕胎发。血已经浸透了它,那一抹“怜”字像要滴下泪来。
“我会护她。”她低语,嗓音不见起伏,却冷得仿佛刀尖拂雪,“如你所愿,她这一生不会染血,不闻杀,不知江湖。”
她抬起头,那张冷艳脸庞沾着血,眼神却比雪山寒三分。
“但若她有半点风吹草动,我会让这江湖,从此为她一人流血如雨。”
那一刻风吹残灯,暮色深沉。霜华缓缓起身,披着满身血与夜色,才一转身,却忽然怔住。
月光下,走廊尽头,一个小小的人影怯生生地立着。
她穿着紫色的缎面小袍,脚踏绣云布靴,一只手还揉着惺忪睡眼,另一只手抓着栏杆。十二岁的苏怜月,额前碎发微乱,小脸未脱稚气,却生得眉目如画,已初见倾城之姿。
“霜姐姐……”她声音软软的,带着一丝刚睡醒的鼻音,眼睛却渐渐瞪大,看向血迹斑斑的地面,“爹爹呢?是不是有人闯进来了?你……你怎么满身是血?”
那一瞬,凌霜华仿佛被人扼住了呼吸。
她从未怕过什么,不怕敌人,不怕阴谋,不怕死,更不怕被刀捅穿肚腹。可在那双干净的、还不知人世险恶的眼睛面前,她忽然觉得满身的血和杀意是种不堪入目的肮脏。
她快步上前,单膝跪下,将怜月一把搂入怀中。苏怜月一惊,嗅到她怀里的血味,忍不住瑟缩一下。
“别看,”霜华的声音一改冷冽,柔了几分,手掌护在她眼前,低声道,“只是几个小贼闯了进来,已经处理了。”
“爹爹呢?”小姑娘颤着嗓子问,“他不是说今儿要教我练骑马么?”
霜华闭了闭眼,胸口剧烈起伏一次,强自镇定地牵起她的手。
“他有急事出门了。”霜华轻声哄道,“去了……去了江北边境,明日就给你带回来你最想要的那匹白蹄马。你乖,别让爹爹失望。”
苏怜月噘了噘嘴,似懂非懂地咕哝:“他总说带我出门都不带……”
她低下头,摸了摸霜华腰间的刀,手指冰凉,像在寻求一点安慰。
霜华喉头一涩,俯下身轻轻抱起她,一步一步,抱她走出满院腥风血雨。
她走得极稳,极轻,不让那柔软的怀中人有一丝颠簸。
“霜姐姐,我怕……”苏怜月在她怀里瑟缩着,小手紧攥她衣襟,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你唱首歌好不好……你一唱,我就不怕了……”
霜华轻轻“嗯”了一声,嗓音低沉沙哑,却依旧唱了,是她记得最清楚的一首小调——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
“你不问江湖几许险,我便替你踏断刀剑山。”
五年,江南换了四轮春秋,苏家堡却始终寂静如初。坊间传言,堡主苏无恨远征边疆,战未休归期未定,堡中政事由义女凌霜华暂摄。而苏家小姐苏怜月,则由凌霜华照拂教养,谨守闺门,不涉江湖。
其实人都知道,苏无恨早已魂归九泉,只是没人敢问,没人敢说。
而真正将那秘密压进心底的人,是苏怜月。
她今年十七,出落得越发如画。
柳眉生得纤长入鬓,眸中带雾,一笑便仿佛春水漾开。身段高挑纤柔,腰肢细得一手可握,肌肤若雪胜脂,行走时香风盈盈。那副天生贵气的骨相里,却藏着父亲一样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是被霜华硬生生压了五年。
她每日起居皆被安排得妥帖,一应食衣无不精致。
身边配了三位贴身婢女,两个教书的夫子,一个琴师,一个女红师傅。花房诗画、香粉丝竹,处处精雕细琢,仿若一位天家公主而非江湖女儿。
只是她从未见过苏家堡的武器库,只被允许在后山亭内读书听琴。每次她问起家中旧事,霜华都冷着脸回一句:“等你十八。”
“父亲呢?”她年幼时曾反复问过。
“他在边疆。”霜华从不多言,神情如铁,“替你守国。”
可那年她十三岁,在园中藏书阁无意中看到一页旧信,内容只寥寥数语:“堡主战死,血战三十七人,尸满前庭。”
她恨自己识字。
她没有哭,只是当天夜里烧毁了那封信,第二日笑着对霜华说:“我梦到爹爹了,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看我。”
霜华微怔,却依旧不语,只在她额前轻抚一下。
那抚摸极轻,极冷,如月色穿过窗纸,如她这些年来所有的温柔,全藏在那一下呼吸之间。
自那之后,她便不再问了。
可没人知道,她夜里常梦见血,从那年起就在梦里看到长刀劈裂石柱,看到父亲断臂握刀的模样。她知道爹爹死了,知道自己身负苏家血脉,也知道霜华一直在骗她。
那不是善意的谎言,而是一种温柔至极的阉割。
霜华用柔情将她包裹,把刀藏进锦被,把杀气藏进茶香,用一整座宅子的静谧与礼教,把她从血海里捞起来,放进温泉里泡软了骨头、洗干净命运的腥味。
她的保护是一种围困,是一种把“权”与“血”从她人生中彻底切割出去的谋算。霜华不是不愿她去报仇,而是连“报仇”这种词,都不愿她学会。她不想她成为苏无恨的女儿,只想她成为任何人的妻、任何门第的花,不问过往、不认血债,最好连苏这个姓也慢慢淡了。
那不是爱。那是怕。怕她长成她父亲那样的刀,怕那条路再斩出一个血流成河的下场。
而怜月恨的,就是这种“怕”。
怕得太狠了,就像是把她的人生连根拔起、扔进一个无风的世界。她活着,却像是被温柔地埋了。
这让她厌恶。
于是她开始学会压抑、学会笑,学会用看似乖巧的语气说出轻飘飘的命令。
她开始享受发号施令的感觉。
起初是让贴身婢女跪着帮她换鞋,后来是让婢女含着茶水喂她喝。再后来,她用刺绣针扎错一线,便罚人跪到流血,理由只是“不好看”。
但她喜欢看她们哭时求饶的样子。
她笑着伸脚,叫人用舌头舔净鞋底,语气却软得像在请人吃点心。她一边摆弄发髻,一边欣赏她们抖着跪下时的模样,像是在看一场闲极无聊的傀儡戏。
而霜华终于意识到——这孩子,已然长成了另一个苏无恨。只是披着更温柔的皮,笑得比谁都乖巧,心比她那已故的义父,还要狠三分。
苏家堡,暮春。
梨花初谢,桃李盈墙。内院回廊之下,一排婢女战战兢兢跪伏在地,个个垂首不敢抬头,唯恐触了那位小姐的霉头。
而场中那位身着粉白交领襦裙的少女,正懒懒地倚靠在玉雕椅榻上,纤手撑颊,玉足半露,正由人替她慢慢拂尘。
苏怜月今年十七。
眉目温婉,肤白若脂,唇不点而红,眸中似有水意浮动。她生得极清纯,极乖巧,一笑便似春日桃枝含苞,叫人不忍怠慢。可唯有靠近她的人才知——她那双眼里没有一点孩子气的怯意,而是一种极稳、极静的掌控者之眼。像从血泊里浮出的珠泪,看着软,骨子里是寒的。
她今日心情不好。
绿杏跪在她脚下,脸色惨白如纸,身子止不住地颤。
“你自己说。”怜月嗓音柔柔的,仿佛春日清风,“那盏盏,是我最喜欢的白瓷莲杯。你怎么打碎的?”
绿杏今年十五,眉眼还未长开,身子却已发育得颇有曲线,胸口圆润,腰细腿长,一身青衣绣花小袄,胸口上方一片水渍未干——方才是她摔了茶水才砸了杯盏,脸上还挂着滚烫水珠之后的红痕。
“小姐,奴婢……奴婢不是故意的。”绿杏磕头,额上冷汗如雨,“是手滑了……求小姐开恩……”
“手滑了?”怜月一声轻笑,眉眼未挑,笑意却不达眼底,“这茶水若是泼在我身上呢?你是不是也说——手滑了?”
她伸出脚,轻轻蹭了蹭绿杏的下巴。
那脚白得几近透明,十趾细巧,趾甲涂着淡粉。她脚踝极细,足弓高耸,皮肉柔腻光润,像是养在锦被玉盆里从未沾尘的尤物。
“抬起头来。”她轻声道。
绿杏被逼抬头,正好迎上一只玉足抵在她脸颊。怜月脚趾微动,慢慢蹭着她的泪痕,又缓缓滑下,从鼻梁、嘴唇一直划至她颈项,脚趾勾住她衣领,轻轻一挑,衣襟乍开一线。
“我记得你胸口挺得很好。”她语气依旧温和,“是不是还没发育完全?给我瞧瞧。”
“小姐……”绿杏哽咽得几近不能出声,却不敢反抗。
怜月的玉足便这样探入她襟中,一寸寸挑开里衣,将那一对白嫩丰盈的小乳肉从衣襟中剥出来。绿杏哭着咬牙,却又羞又疼地忍着,直到怜月脚趾勾住她乳头,慢慢揉碾,眼里才浮现真正的绝望。
“嘶……这反应倒不错。”怜月垂眸轻笑,目光落在那微颤的乳头上。
她脚趾缓缓按压,碾揉乳尖,再一勾,绿杏身子剧烈一颤,竟低低地呻吟了一声,羞得整张脸都烧红了。
怜月一脸无辜地笑道:“怎么,你还喜欢?”
她一脚踹翻绿杏,让她趴伏于地,玉足伸入她裙底,沿着大腿内侧一路挑弄,直到贴近私处,才缓缓在那湿润一片的布料上来回摩擦。
“这地方也挺滑。”她语气温柔得像在说天气,“是不是怕得出汗了?”
她脚趾在那片细嫩肌肤上轻轻画圈,时不时用脚尖挑起些皮肉,像猫挑弄虫子那般有耐心。绿杏哭着发抖,手指死死攥紧地上的褶布,却不敢反抗,甚至不敢夹腿,怕惹来更狠的对待。
怜月忽然用脚背一勾,将绿杏整条腿扒开,姿势粗暴得近乎羞辱。
“唔……哈……小姐……”绿杏的声音已经带上哽咽的颤音,像断弦的琴,声音不成调。
怜月低头俯瞰她,像看一件终于服软的玩具,微微一笑,又将足尖探入那湿透的裙褶,轻轻一顶——
绿杏尖叫一声,整个人猛地拱起身子,却被怜月用另一只脚死死踩住后腰,动弹不得,只能颤抖着伏在地上,羞耻和快感像滚烫的铁汁一起灌入骨髓。
她哭得眼角尽红,却不敢再求饶,只能咬唇强忍,像狗一样趴着,任人戏弄。绿杏的俏身抽搐着一抖,那一刻终于绷断,娇躯猛地一颤,蜜肉痉挛间竟在地上泄了出来,湿意浸透裙裾,甚至带出一滩滚热的清尿,沿着她大腿根一路蜿蜒而下,竟湿了怜月垂落在榻下的绣履一角。
绿杏猛然意识到这一点,瞳孔骤缩,仿佛从迷乱中被雷霆惊醒。
她脸色瞬间惨白,身子一软,连滚带爬地跪伏在怜月脚边,额头重重磕地,“砰砰”作响,声音颤抖中带着破音:
“小姐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弄脏小姐的鞋……奴婢该死,真的该死……求您、求您饶命……”
绿杏崩溃地哭了,而四周所有下人,包括她同房的婢女们,皆面如死灰,不敢出声。
无人敢上前,甚至无人敢发出呼吸声。
哪怕她不是堡主,哪怕她没有实权,可这五年来,她的眼神、她的气场、她的手段,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忤逆她者,轻则受辱,重则废去。
怜月终于厌倦了戏耍,收回玉足,一扬手。
“藤杖——三十。”
下人早已备好,一名年长婆子双手奉上,她接过轻巧地一甩。
“自己数着,抽够三十不准偷懒。”她语气轻快,“若哭得太小声,我就加十。”
绿杏身子颤抖,却只能咬牙趴好,将裙摆撩至腰间,露出一片已红肿的雪臀。藤杖落下,啪啪作响,每一下都像打在人心上。
五杖,十杖,二十杖。
她已哭到声音嘶哑,屁股红肿如熟桃,鲜红的血丝一条条从臀缝沁出。可怜月面无表情,指尖拨弄茶盏,仿佛听戏。
就在第二十九杖落下那一瞬,一道熟悉而压迫的声音响起:
“够了。”
众人心头一凛,抬眼望去——
是凌霜华。
她立于花廊之上,一袭墨色宽袖长袍,胸前半束腰封,身姿高挑冷艳。五年过去,她的容貌不仅未衰,反而更加风情万千。那身天生媚骨如今已完全长开,胸更高挺,腰更柔细,臀更圆润,走一步都似春波荡漾,连袍下走动时的腿线,都牵动着人心躁动。
而在她腰间,一柄古刀静静垂挂,鞘黑如墨,金丝缠脊,刀背嵌有七颗寒星状的银芒,隐隐如北斗排阵,锋寒不露却压得人喘不过气。那正是苏无恨的佩刀——七星横岳。
这刀一出,无需出鞘,便叫人想起苏无恨当年血洗武林时的腥风血雨。而如今,它悬在凌霜华的腰间,刀未动,意已至。
她不需声张,只需立在那里,苏家堡上下就没人敢不俯首低眉。
也只有她,能镇得住苏怜月那股天生的疯劲。
她的脸依旧冰冷,却那种冷,是压抑了欲望的冷,是越压抑越勾魂的冷。
“她的反省够了,回房。”霜华淡淡道。
“她砸了我的杯。”怜月缓缓起身,裙摆落地如云,“我只是在教她怎么做人。”
“你当然有的是权。”霜华淡声道,“但你是苏家堡未来的女主,可不是个疯婆子。”
“那你是觉得我疯?”怜月眼眸一转,笑意却更深,“你教我琴棋书画,却不教我剑术权谋,告诉我爹在边疆却不许我追问,你让我做一个‘小姐’,可我姓苏,苏家是怎么立的你不比我清楚?你让我做什么?当个会绣花的死人?”
霜华沉默,片刻后,只道:
“休得多言,回房,禁足一周,该你反省。”
怜月站在廊前,背影笔直,眼里怒火涌动。
最终她一言不发,缓缓转身,裙摆拂过地面时像把慢抽出鞘的刀。
她走回闺房的每一步,脚下都是碎花,心中却是血池。
夜已深,灯未熄。藏月轩内香炉微燃,一缕檀香缠绕帷幔。
凌霜华卸下墨袍,仅着一袭素白中衣,立于轩前。灯火映出她五年后更加凌厉的身形,冷艳之中更添成熟之色。她天生媚骨,年少时是风中利刃,而今的她,已如雪地沉刀——越沉,越锋,越艳。
她的胸更饱满,腰更窄细,臀更圆润丰盈,皮肤雪白如玉,连肩胛骨都带着不容忽视的线条感,仿佛每一道曲线都暗藏力量与风情。最惹人心悸的,是她那双眼,冷得像盔甲,却在夜色中透出一丝人前不露的疲惫与眷恋。
一双柔臂从她身后绕来,轻轻环住她的腰。
“又在发呆。”
声音如玉铃敲雪,软糯中带着点撒娇。
“你不是说过,不许独自站在夜里吹风,会寒入骨。”
她没有回头,却已轻轻叹了口气。
“清音。”
沐清音,天音阁前圣女,外人皆传其冰肌玉骨、心如止水,实则……她是藏得最深的那团火。
她今年二十有四,长身玉立,肌肤胜雪,五官温柔得像画,眼中却藏着水波流转。她一身素纱薄衫,赤足入室,身姿婀娜,胸前两团柔腻随步轻晃,饱满柔软得不像凡尘女子。她步履轻盈,腰肢如柳,身下那片轻纱薄得几乎遮不住她的私处轮廓,连腿根隐隐可见一丝潮意。
她是医生,也是琴师。
但她还说是凌霜华的恋人——唯一一个能勾起霜华情欲的人。
两年前,怜月忽染恶疾,霜华遍寻名医无果,火烧眉头之际,方从一位故交口中得知天音阁有一人,医术极妙,素日不问世事,只以音律养心。霜华亲自三赴山中请人,见她第一眼,便如见清雪覆火山,气静神动,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缕执念。
自此,清音便随她回了苏家堡,住进花阁西苑,一为医,一为琴。平日怜月身子无恙时,便随她习琴;身子不快时,她亦会调香制汤、推功引气,甚至夜夜守在床畔,用指尖温揉她心口脉络,让那颗躁烈之心渐归平缓。
而霜华也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心结微动。
她原以为清音这等人,只该远望。可她未曾想到,清音亦会为她停步。
不是惊雷,不是骤火,是灯火入夜,是雪落无声——她们之间的情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燃了起来。
“你今日,又罚了怜月。”清音温声道,手指顺着她腰窝滑下,指尖轻轻勾过她腹部的肌肤,“她的性子,越来越像你说的那位老苏堡主了。”
霜华不语,只是闭了闭眼。
“我知道你压着她,是怕她血路走早,走死。”清音贴在她背上,声音愈发轻柔,“可她……终归不是你养得住的。”
“我不想你再被这些事困着。”她顿了顿,手伸到霜华胸前,轻轻握住那一对冷艳雪乳,指腹揉捻,“你从十岁就开始杀人,十七岁出师,十九岁为苏家断后,二十三岁埋了他,二十八岁还在替他养女——霜华,你已经还够了。”
霜华的身子微微一震。
她不回应,可胸前的乳头已在清音指间悄然硬起。那点反应,不是爱欲太深,而是……太久压抑。
“跟我走吧。”清音吻上她颈侧,唇湿如露,“不去北境,不去江湖。我们去东海,去南山,种田、采花,你下地种菜我织绣调香。你若还爱舞刀弄剑,就舞给我一个人看。”
霜华沉默良久,终是握住她的手指,从自己胸前挪开。
“不行。”
“为什么?”清音轻声问,眼中却有一点委屈。
霜华转身,低头看她,眼神复杂。
她从不说谎,不逃避。她只是太冷,太压着,把什么都藏进骨头缝里。
“苏家救我,教我,养我。若我现在走,便是弃义。”
“你觉得你欠他们。”清音低声说,“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两年来,一直在你身边,却从来排不过她?”
霜华眉头动了一下:“清音……”
“我没有生气。”清音摇头,凑近她鼻尖,“我只是……怕你一辈子都困在她身边,看着她成了你义父的影子,却不能脱身。”
“她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她长大了,也不会再听你话。出生苏家,她总会有她的道,她的江湖,她的血路。你以为你还能护她一生?”
霜华缓缓吸了口气,终于低声道:
“再等两年。”
“她十八岁后,嫁出去。我便不再管。”
“到那时,我便跟你走。”
清音怔了一下,眼中水光微闪,笑意仿佛停在唇角未绽之处。她不是听不出那句“再等两年”又是一场推脱,只是那一点点失落,来得太轻,也太快。
她不愿让它停留在脸上。
指尖轻轻一紧,她像是想握住什么,又轻轻放开,随即轻笑,像春水翻起一层柔波,扑进她怀中,声音带着撒娇的气音:
“你说的,不许反悔。”
“嗯。”
“那你今晚……也别冷着我了。”她语气一转,唇已吻上霜华锁骨,纤手探入她衣内,指尖滑入雪峰之间。
霜华低喘一声,终于也伸手环住她纤腰,将她压在榻上,眼神里浮起少见的欲意。
她俯身咬住清音乳尖,温热湿润的舌尖卷着那嫣红小点缓缓揉舔,清音的娇喘顿时从喉中逸出,指甲已抓紧她肩头。
腿交缠,香汗交融。衣衫零落间,一双素足翻过锦褥,带乱了烛影,扰动了帷幔,也搅碎了她们守了太久的矜持。
第一章
夜风如水,灯市如昼。
江南烟雨市集中,“听香水榭”自有别样风流。它不挂艳帘,不放笑语,却夜夜满座,夜夜不清。那不是寻常的青楼,那是权贵密会的温床,是风月、情报、金钱、胴体交汇之地。
而在今日傍晚,门口一辆苏家特制的细车悄然停靠,驾车之人低头哈腰,帘中人却未露面,只缓缓伸出一只手。
那只手,修长如玉,十指染着浅蔻丹,腕骨玲珑,袖口绣金——不是谁家的小姐,就是谁家的主母。
“怜月小姐来了!”迎门老鸨眼尖得很,连忙将两旁引路小婢轰开,“快快快,把玉香阁腾出来,再派两个最会伺候的姑娘上去!”
帘子轻掀,一道粉衣人影掠下车,踏入香榭之中。
苏怜月今日一袭水红小褂,外罩月白云罗,纤腰紧束,裙摆如烟。她唇不点而红,眉眼含笑,耳垂坠玉,鬓边斜插一枝海棠,风一吹,衣袂轻扬,步步似浮香。
若非她脸上那点不容违逆的傲意,谁看不出这是一尊养在金笼里的娇贵雀儿。
可偏偏,她不是那种乖乖待在笼里的鸟。
她早知道苏家堡内诸多小道,哪些廊角无人看守,哪扇门后藏着一条暗渠,甚至哪匹马性子最稳、半夜不会嘶鸣——她计划这“出逃”不是一次,不是一天,而是早就准备好的习惯性放纵。
她不反省,她从不真反省。她只反谁不听她的命。
“哟,怜月妹妹又来了。”
楼上红纱微卷,缠绵婉转的声音带着一缕醉意,仿佛香气自檀口溢出,撩得人心里发痒。
说话的是“听香水榭”的主人——白蝶娘。
她今年三十四五,正是风情入骨的年纪,一身墨紫宫裙勾出丰软身段,腰极细,胸极阔,尤其一双腿,修长白腻,生得媚骨天成,偏又习惯赤足穿纱履,行来步步生莲,像是踩在人的心尖儿上。她眼角有一枚朱砂痣,笑时微挑,妖媚得不动声色,却让人想甘为裙下奴。
苏怜月第一次踏入香榭时,白蝶娘并未将她放在眼里,只当是哪个贵人府中的小妾出来偷闲,眼底客气,言语却冷。
可谁知这小姑娘后来一来再来,日子准得像过节似的——每五日必到,点戏、选人、赏酒毫不吝啬。白蝶娘这才晓得她来头不小,是苏家堡中那个最难见、最金贵的怜月小姐。
从那以后,白蝶娘待她就不一样了——笑得甜,说话低,送的香奴都是头牌挑剩中最妙的那一朵,还常常打趣她“妹妹比香榭姑娘都勤快”。
曾经,凌霜华冷声教她说青楼是“污浊不可近”的地界,可她只觉那冰冷的苏家府邸,像座闭气的冰窖,连喘息都是罪。
反倒是这里,有人笑她、宠她、跪着哄她。
“蝶娘今日又添了新姑娘吗?”怜月懒懒地靠在玉香阁绣榻上,撩起帘幔,唇角微挑,“我想试试‘翻牌’。”
“都照你的规矩。”白蝶娘笑盈盈地递上一个香案,案上置着一叠绢牌,每张都绣着姑娘名号,配香调、专长、得宠程度一应俱全,仿佛后宫妃子名册。
怜月兴致盎然,一手挑着牌子,一手摸着案边细纹。她的动作娴熟,甚至带着一点故意的戏谑,像极了前朝皇帝听戏翻人侍寝时那种游刃有余的狂妄。
“这个‘初杏’,”她指着一张画着粉杏的卡,“上次你说她会舌技,结果不过如此,嘴都含不全我……嗯……”
她眼波一转,懒懒拖音,抬眼对白蝶娘道:
“叫她今儿倒壶酒便好,别让她那张小嘴再坏了我兴致。”
“是。”白蝶娘含笑低首,眼里却有一闪而过的玩味光芒。
苏怜月懒懒斜倚在锦榻上,素指一翻,指尖轻点香案上三张娟牌,眼中笑意浅淡,像随手拈花,又像挑拣玩物。
“就这三个吧,”她唇角一翘,语气温温的,“人都叫来瞧瞧。”
“哎哟,怜月妹妹挑得真巧,这几位可是近来香榭里头最得脸的,奴这就让她们进来。”
牌子才翻完没几息,便见帘下纱影晃动,有三位姑娘鱼贯而入,衣衫极薄,粉香盈盈。她们一进来便跪拜行礼,连眼神都不敢抬。
她们一个名为月杳,貌若狐媚,言辞滑腻,靠一张嘴哄得勋贵失魂;一个名叫春浓,擅歌舞,腰肢极软,号称能“坐莲翻鹤”;另一个唤作雪鹞,年纪最小,才十五六,肌肤赛雪,最得白蝶娘宠爱。
与苏家那些规规矩矩的侍女不同,这三人一入屋便似水蛇绕榻,动作不急不缓,却每一寸都透着揣摩与讨好。
“小姐好福气,今日气色真是好得很,奴家一进门就被迷住了。”月杳眨着水眸,笑得像蜜,手已自觉地抚上怜月膝头,“想来是昨夜梦里也有人想着我家小姐,才这么润泽呢。”
“是奴家福薄,几晚未得服侍,夜里都梦见自己跪在小姐脚边,被狠狠踩着不许喘气。”春浓有样学样,贴着怜月裙摆,低声笑,胸前两团软肉几乎整个贴在怜月腿边,“醒来时,竟已湿了一片。”
最末的雪鹞却半晌未语,只怯生生地蹲在一侧,手指轻搅着自己衣角,睫羽颤了又颤。直到怜月凤眸一偏,落在她身上,她才低声开口:
“奴、奴婢昨夜在床上磨着腿……想着小姐坐在奴婢脸上的样子……越想越热,也……也湿了……奴婢该打……”
她声音细得像猫叫,羞耻到耳根通红,却又带着那种年少少女独有的清甜与不自知的媚意。
怜月靠在榻上,手指拨弄着香炉盖,目光淡淡,却笑而不语。她不需说话,这些女人自会献上所有。
怜月站起身来,裙摆微动,轻盈如燕,居高临下望着跪在榻下的几人,笑得懒懒的,眼波半垂。
“早上的兴致遭人扫了……嗯,就叫你们几个,替我补回来吧。”
“先来舔舔脚,让我心情好点儿。”
怜月的命令如皇后临朝,懒洋洋地吐出,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意。
“遵命。”
三人齐声,便如三只野猫伏地而上,一左一右,一前一后,跪在她足下争相服侍。
月杳最是嘴巧,一边含着她脚趾轻吮,一边喃喃道:“小姐的脚真香,奴家愿一辈子不吃不喝,就这样含着也心满意足。”
春浓舔的是足弓,舌头卷动得极细腻,每一下都像在书写情书:“这脚心比我的唇还嫩,怕是用花露水洗过千遍。”
雪鹞则捧着她另一足,手掌托得稳稳地,脸红心跳地亲吻脚跟:“小姐别动,让奴家多亲几下……怕一松口就舍不得了……”
她们舔得极认真,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带着真实的取悦、讨好,仿佛争宠的妃嫔,各使浑身解数。
怜月微阖美目,雪白玉足一动一动,若有若无地在她们唇舌间碾压,享受着那种被主动取悦、被人舔到高潮的权力感。她只轻轻一笑,那三人便恨不能将脸埋入她足底,把羞耻当献礼。
“你们中间,谁最会夹乳喝茶?”她忽然发问。
三人一怔,随即异口同声:“奴家最会!”
“那就都试试。”她起身,一指月杳,“你先。”
月杳二话不说,褪去襦裙,解开乳裳,一对白花花大乳自衣中跳出,饱满得像两团熟糯。她跪好,取茶盏放于乳沟之间,轻轻夹紧,竟稳得不晃一分。
怜月勾唇,缓缓低头饮了一口:“嗯……热气正好,奶香足。”
“奴家这乳,是为了小姐特意养的。”月杳娇笑,身子微抬,那茶水被乳肉夹着荡出涟漪,溅落她胸前一串水痕,看得旁人心头发烫。
“下一个。”
雪鹞脸红得快滴血,却也娴熟地褪下罗衣,乳虽小些,却因年少紧实得很,夹起盏来颤微微地抖着。她偷偷望了怜月一眼,舌头悄悄伸出,在茶盏边舔了一圈,才小声道:“小姐若不嫌弃……奴也想舔一口您唇上余温……”
怜月眼神终于动了动,懒懒地垂眸,像猫看小鱼般望着她那稚嫩又贪馋的小模样。忽而抬手,指尖轻轻一弹,正中雪鹞额心。
“小嘴倒是甜,就是规矩都忘了?”
她语气极轻,带着点似嗔似宠的笑意,手却一寸寸抬起,指背轻敲雪鹞下巴:“轮次都记不住的小奴儿,是不是要我喂你一记才学得快些?”
雪鹞脸色霎时惨白,身子伏得更低,声音带着哭腔:“奴、奴不是要抢……只是……只是看小姐今日好生娇媚,忍不住……”
怜月未言,只将一只足搁在她肩上,缓缓施力,让她低头、再低头,直至跪地匍匐,如犬如婢。
她笑了,睫毛颤动,像一尊初登基的小帝王,尝到支配滋味,便再也戒不掉。
此刻的玉香阁中,春光旖旎、欲意蒸腾,妓女们低吟浅哼、娇艳如花,而那位穿着粉衣的苏怜月,正斜倚香榻之上,玉足交错、媚笑盈盈,仿佛已将天下、将万艳,收于脚下。
酒过七巡,怜月面颊酡红,香汗微沁,眼神却越来越迷离,像是水波映月,分不清是映着屋中人,还是梦里景。
香炉里的沉香已燃至尾梢,雾气缭绕成缕,混着屋中肌肤交摩的香汗与酒气。
苏怜月倚靠在软榻之上,怀中抱着尚未着衣的雪鹞,双足分别踩在月杳与春浓后背上,仿佛三只供人玩赏的雌犬。屋中灯影温软,帷帐半垂,春色如露未敛。
忽听门外帘动,一道身影缓步而入,步履轻飘,袍裙摩地如水潺潺。
“怜月妹妹,夜已深了,要不要留宿?”
来人正是白蝶娘,一身靛紫薄绡广袖,胸前半露,纱中春光若隐若现,腰间佩着香囊与绣扇,妆容不浓,却艳色无双。
怜月闻声未答,反而勾了勾手指。
“你来。”
蝶娘抿唇一笑,步步生风,坐在了她对面:“又喝了多少?”
“不过三盏。”怜月一挥袖,身下春浓忙不迭地奉上新盏,“来,再陪我一杯。今夜月色好,不醉无趣。”
蝶娘接过,与她轻轻一碰,玉液入喉,目光始终未移开她眼眸。
“奴听言,”蝶娘轻声道,“妹妹又被那位冷霜护法,罚回深闺反省?”
“呵……”怜月冷笑一声,仰头饮尽杯中酒,“反省?她真以为我还三岁小儿,唬我两句我便乖乖待着绣鸳鸯,读女戒?我都替她脸红。”
她纤指勾起雪鹞的下巴,迫她仰脸接吻,唇齿相交,唾液混着酒香交缠一处,怜月才意犹未尽地将她推开,继续笑道:
“她啊,倒真是个好姐姐……在苏家堡里,我走哪儿都有人盯,吃饭有人看,睡觉有人管,连梦里想的事都能被她揪着拷问一通。她说什么?‘你是小姐,要知礼守身,做不得轻浮之事’。”
“可笑!”
她将杯中残酒泼在地上,吓得雪鹞浑身一颤,怜月却眼神不变,轻轻挑起她裙摆,用脚趾拨弄她腿根湿滑之处,像在玩一团不合心意的泥。
“我在她眼里,就是个需要捧着哄着的瓷娃娃罢了。”
“蝶娘,你说,若有朝一日……我真成了苏家堡主,她第一个,是不是该给我磕头认命?”
白蝶娘勾唇,笑意盈盈,却未开口。
她怔了一瞬,忽地轻笑,像笑自己,也像笑那场梦。
“我该恨她的,对吧?”
“可她生得美。”怜月吐出一句,像从心底逼出来的叹息。
“她有一双眼,冰得像剑,唇却红得像要吻我……她的身子……啧……”
她闭上眼,指尖缓缓抚上自己胸口,似是陷入梦魇,又像陷入欲念。
“我小时候常躲在屏风后偷看她沐浴。她背上那些疤像藤蔓缠在雪地上……每当她抹浴露的时候,那雪白的乳房一颤一颤,我就……”
她话未说完,却缓缓睁眼,眼神一变,带着一点微醺的失焦。
她靠在榻上,呼吸愈发浅促,手指还轻轻摩挲着胸口柔软处,像是在触碰一个长久压抑的梦。
她知道自己喝多了,嘴里说的是疯话,可心底那道念头却真实得像刀刮过骨头——她是真的想过。
想看霜华跪下,不是羞辱,只是……想看她低头的模样。那个从小把她捧在掌心、却又牢牢关进笼子的人,那个谁也不能侵犯、谁也不能亲近的女人——她想亲近。想狠狠地、彻底地、带着报复心也好、带着迷恋也罢,把她那副冰雪做的身体,抱进自己怀里,看她在自己怀里喘,看她颤,看她哭。
可那一夜,她本是夜半醒来,只想寻杯水润喉,路过廊侧时却无意听见了一声低喘。她悄悄拨开一线门缝,看见的,是霜华伏在榻上,而那素衣如雪的清音——正伏在她身下,吻她的颈,舔她的乳,唤她“姐姐”。
「明明那是我的姐姐。」
帷幔垂落,香火微暗,霜华的喘息压在咬紧的唇间,发丝散落,胸乳起伏如潮,那副平日里清冷矜持的模样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任由清音玩弄时,那一点一点被逼出的媚态。
「明明她不该有这幅神情的。」
她只看了一眼,便逃也似地转身。
可那一眼成了钉子,钉进她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从此日日作痛。
她这才意识到——
她想要霜华的,不是姐姐的爱,不是义母的怜惜,而是清音那样的、能让霜华弓身低喘、溢出呻吟、露出媚态的资格。她想看她趴下,想听她求饶,想踩着她那冷若霜雪的脸,说:“你该只属于我。”
可她知道,这份资格她永远得不到了。
她可以是苏怜月,可以是苏家堡未来的女主,却不可以是那个能爬上霜华榻上的女人。
她不是不爱霜华。
恰恰相反,她太爱了。爱得不能说,不能碰,不能妄想。越不能,越想。那种爱像是毒,一旦下喉,就只能用更烈的毒压着。
可她终究压不住了。
她那点孽念,只能埋进泥里、埋进酒里、埋进每一次戏弄婢女时的脚掌碾压中。
那是她唯一能留住霜华的方式了——哪怕是在幻想里。
怜月喝得脸颊泛红,眸光却愈发亮,像点了火似的,呼吸也乱了几分。她俯身望着脚下月杳那张媚眼盈盈的脸,忽然语调一转,声音压得低低的,像在梦呓,又像在挑衅: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
“要是霜华她……也像你们这样,跪在我脚下,被我踩着奶子,舔着我的脚趾,哭着求我原谅她不听话……”
“会是什么样子?”
她说这话时,舌尖还舔了一下唇角,不知是酒后吐真言,还是心里真藏着这样一幅画面太久了,竟带出一种说不清的兴奋。
“你!”
她抬起手,用纤指挑起雪鹞的乳鸽,那乳尖已湿润香软,红得似染了花汁。
“你现在是她。”
雪鹞一愣,立刻低头应道:“是,小姐,奴是您那位冷霜护法。”
怜月喉头轻动,低笑:“好……那就跪好点。”
她一脚将雪鹞按在地上,踩住她后颈,像踩着霜华的傲骨。
“你不肯听话,对我冷着脸,处处压我,现在知道错了?”
“知错了,小姐……”雪鹞声音娇弱,眉头紧蹙,像真的羞惭悔恨。
“月杳,你是她的手。”
怜月一指,月杳立刻俯身,将双手贴在她大腿内侧,自下而上地缓缓摩挲。
“你平时用这双手替我梳头,替我拭泪……可现在——”
“现在该替小姐捧香趾,舔玉足……不敢再妄图操控。”月杳张嘴含住她脚尖,唇舌缠绕,舌根卷得极深,舔得怜月脚心都一阵阵酥颤。
“春浓,你是她的嘴。”
怜月眯眼,脸上浮出一抹几近疯狂的笑意。
“平时你用这嘴教我女戒,说什么‘小姐应贞静’,呵……你来,现在就用这张嘴给我唱,唱你怎么被我驯得伏在床上,被我骑在脸上,哭着求肏!”
春浓脸色通红,立刻伏地娇声哼唱,语调淫媚:
“奴是苏家护法凌霜华,今夜甘为怜妹胯下娃……舌尖若不晓那深处春,便唤那玉趾碾贱奴臀……”
“再说一遍!”怜月低喝,猛地将双脚并拢,夹住春浓的头发,像夹住霜华的发髻。
“说你是霜华,是被我调教、被我骑弄、被我踩下贞节的母狗!”
“我是!我是……”春浓哭腔溢出,面色酥媚,“我是小姐的霜奴,是小姐膝下舔穴的雌犬,是您用足趾驯化的下贱婢奴!”
怜月终于笑了,笑得像雪中开花,艳而疯魔。
“霜华啊霜华……你那么高傲,我都快看腻了。”
“你若有朝一日……也能像她们这样,伏在我脚下,用舌头舔我,舔到我颤得不想说话,哭着说‘小姐别再踩’……”
她猛地仰头,一盏酒自唇边洒落,香液顺着雪颈滑至胸前,滴入乳沟,她却仿若不觉,只闭着眼喃喃:
“我就原谅你了……”
她醉了,彻底地醉了。可她吐出的每一句,都不是胡言。
脚下三人继续娇喘承欢,一边哀哀地替她按摩舔吮,一边有意无意地重复着她幻想中的羞辱对白,把这场春梦渲染得愈发荒淫、愈发真实。
但怜月忽然怔住了,像被自己舌尖蹭破了什么,酥麻过后,才后知后觉地察觉不对。
她把那种藏了太久、只敢藏在梦里反复回味的念头……在外人面前说出口了。
纵是醉意缠身,她也知刚才那句话意味着什么——
她在说,她想驯服她的护法。
她想调教她的义姐。
她想将那位冷面杀神,变成脚下淫奴。
但她知道这只是妄想,是会让任何人惊讶得掉杯的疯言疯语。
她轻咳一声,唇角带着一抹强撑出来的笑意,拿起酒壶亲自替蝶娘斟了一盏,递过去。
“哎呀……蝶娘见笑了。”她声音一改先前醉意喃喃,语气带点娇俏又不失世家小姐的分寸,“我方才是喝高了,竟胡言乱语起来。家中私事,不该乱说。您就当我在编戏文罢。”
白蝶娘接过酒盏,红唇微扬,未语,笑意却藏在眼角那一枚朱痣下。
“若这戏文真能成,倒也是一出风流传奇。”
她轻抿一口酒,忽地压低声音,带着一点半真半假的恭敬:
“小姐若真有此志,奴也不是外人,不妨……让奴为您出些法子。”
“只要将来小姐登位之日,不忘了听香水榭,有福同享……奴这一榭,这一身……都听您吩咐便是。”
她说得轻,却字字滴血,是一封悄然递出的投名状。
怜月听罢,怔了一息,旋即笑出声来。
“就凭你?”
怜月半垂着眼帘,淡淡又补了一句:“霜华那人你也知,清冷无情,武功又高,一柄霜刃出鞘,多少江湖人连她影子都摸不着就死了。”
“我小时候亲眼见她一招‘霜骨斩’把刺客整个人从中间劈成两半,连血都还在半空没落地,她已经走完三个方位。”
“她的腿极长,出腿带风,扫来时连地砖都断三寸。她一掌打在石柱上,那石头像豆腐一样碎。”
“可她的身子……”怜月眼神一转,带着些酒意的痴,“却柔得像水一样。我无意间碰过她背,那皮肤,比婢女们洗三次花露还细。”
“她明明生了一副妖骨,却偏要装成冰山。”
她说着,自己都笑了笑,带着点自嘲:“我就算想,能奈她何?她若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恐怕连脚趾都不屑让我等碰到一下。”
白蝶娘却只笑,笑得极淡,唇角不扬,眸光幽深如蛊,仿佛万千胭脂泪都沉在那一眼之下。
“我不懂武功。”
她缓缓踱步,声音不紧不慢,却每一字都像针,直刺欲根。
“但我……懂女人。”
她停在几名仍伏在地上的妓女身前,目光落在那最小的雪鹞身上。
“雪鹞,过来。”
雪鹞一颤,连忙爬起,低着头走到蝶娘身前,恭恭敬敬跪下。
蝶娘半蹲着,抬起她的下巴,那动作没有一丝粗暴,柔得仿佛拂花。
“你总觉你的姐姐冷,不近人情——可这世上最藏不住欲的,恰是那种看起来最会忍的女人。”
“越是冷,越是忍,她们骨子里那点欲根,才藏得深,烧得久。”
“可她越是忍得住,调起来才越好看。”
“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容易沦陷?”
“不是那风尘惯走的,也不是甘作贱奴的,而是那种——尝过一丝甜,就以为不过如此的。”
“她们不识自己的身体,不知快感与羞辱只隔一线;她们误把克制当高洁,把沉默当强大。”
“但直到第一声哼吟自喉中泄出时,她们自己都吓了一跳。”
蝶娘伸手按在雪鹞的肩膀,让她身子向后仰,露出脖颈与胸前一抹雪白。
“来,我们让小姐见识一下,怎么调一具‘初开’的身子。”
雪鹞咬唇不语,却乖巧地仰头任她摆弄。
蝶娘只用指尖,在她锁骨处轻轻绕了一圈。
“你瞧,这地方,最开始不敏感,但女人一旦心乱,血脉一冲,这里会发烫,像烧起来。”
她手指一点点下滑,绕过乳沟,沿着乳下轮廓缓缓划线,每一下都像是刻字。
“然后是乳根,最容易藏羞。别看她乳尖立得紧,其实这根下的神经才最能勾魂——”
她轻轻一捻,雪鹞身子一颤,唇间微张,差点叫出声来。
“再往下。”
她一手掀开雪鹞的裙摆,将她双腿并拢抬起,一指点在大腿根最内侧:
“这里连婢女都不一定知道自己会颤,可只要捻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羞还是爽。”
“你若想降服你家护法姐姐,千万别急。你别跟她斗力斗狠,那是她最擅长的。”
“你要诱她,试她,撩她。让她冷艳的面具自己碎,让她那身媚骨在羞耻中软化。”
蝶娘回头看向怜月,眼中带着一点近乎慈悲的柔光,却媚得让人心里发痒:
“你要让她从冷傲中泄出第一声呻,从清高中舔下你脚趾,从她最倔的一口气里,哭着咬牙,把求饶的声音亲口吐出来。”
“那时候,她再不会拔剑,只会张口。”
“而你,只需坐着,看她一寸寸地烂在你掌心。”
她轻轻推了推雪鹞,那姑娘整个人软成一团,已是双腿发颤,喘息不止,脸色红得像熟桃,仿佛真被抽去了魂魄。
蝶娘缓缓直起身,淡然整理袖口,仿佛刚才那不过是一场温柔的茶艺表演。
“小姐若信我,奴不才,愿替您布这一局。”
“若不信……也无妨。”
“您也且当听了个故事,回头再笑便是。”
白蝶娘话音落下,怜月却未答。她只是低头饮酒,半盏未尽,眸色已沉了几分。
她原本兴致正浓,打算就在香榭歇下,叫人调灯设榻,好好再作一夜春梦。
可不知为何,蝶娘那番话像一枚火星,落在她心口深藏多年的某个地方,烧出了火,也烧出影子来。
帷帐未收,酒盏犹温,苏怜月却已披上外裳,淡声唤马,神情如水,不动声色地回了苏家堡。
那晚,怜月枕着檀香丝被,辗转无眠。
屋外虫吟低鸣,夜风轻拂,她却只觉得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烧着——烧得她难受,烧得她闭上眼就是那夜里听香水榭的帷帐、朱灯、软榻与脚下那三名妓女娇喘含泪的模样。
更忘不掉的,是白蝶娘那句贴在她耳边轻语的话:
“从她最倔的一口气里,哭着咬牙,把求饶的声音亲口吐出来。”
她醒来时下身已湿透,脸颊火热,气息未稳。
日子越过越平,苏家堡一切如常。
霜华还是那个霜华,一袭素纱,束胸利带,剑从未离身,话从未多言。她每日巡视、训练、批阅,偶尔出现在怜月书房门外,只一句:“小姐是否用饭?”便不见踪影。
而怜月,自那天从“听香水榭”回来后,也像变了个人。
她不再常常顶嘴,也不再时不时闹脾气;她每日早起,温声答礼,练字持琴都极规矩。霜华说什么,她便应什么,还时不时唤她一声“姐姐”,眼眸含笑,软得叫人心都发烫。
霜华起初不以为意,后来却慢慢放了心。偶尔也会多说一句话,晚些离开些时辰;见怜月咳嗽两声,便让清音熬了汤亲手送来。她从不惯人,可唯独怜月这几日的乖巧,叫她忍不住多少回了些人情味。
然而怜月眼里的她,不再是那个让人敬畏的护法,而是一副套着冷冰冰皮囊的淫骨仙子。
怜月笑着吃她递来的药汤,眼神却落在她蹲身拂袍的曲线上;她说“姐姐照顾得真好”,语气乖巧,指尖却悄悄压在裙下,缓缓研磨自己发热的穴口。
她的腿那么长,腰那么细,乳那么丰,走路时肩胛微动,臀瓣随步轻晃,说话时声线低柔,像是压着呻吟;弯腰时衣襟滑开一线,仿佛特意撩拨人心;那剑从背上滑下时,更像极了情人卸甲褪衣的背影。挺着胸、撅着臀、媚着眼,等着谁扑上来将她咬开,掰进怀里,啃得满唇是汗,是油,是呻吟。
她盯着霜华脱靴时露出的白嫩脚踝,心里想的却是那双脚是否也会在自己舌下轻颤;她看她练剑时乳峰一跳一跳,便下意识地用玉足轻蹭自己裙下,幻想那副高不可攀的身子被自己逼跪在地,双乳贴地,肩胛撑起,汗水从背脊滑下,抖着腿夹着主人的脚尖,含着羞在她耳边哭着喘着求原谅。
“妹妹……请、再、重一点……”
她开始坐卧难安。
越是乖巧,幻想就越疯。
越是温顺,她心底那只兽就爬得越高,咬得越深。
她心里明知道这是疯的,是错的,是痴人妄想——可她那点小小的克制,早就被那晚白蝶娘那番话敲裂了。
“她越是忍得住,调起来才越好看。”
于是,当禁足期一过,她几乎是第一时间又踏入了听香水榭。
这一次,她没有让人备车,而是带着一名贴身婢女,以赏灯会为名悄然入市。
不饮酒,不翻牌,不掀帘——她一进门便点名:“叫白蝶娘来。”
老鸨忙不迭迎上,婢女被留在楼下,怜月被请入后院竹亭。白蝶娘早已候在那,换了一身素金织缎轻衫,妆容比那晚更淡,却媚得更加勾人。
“怜月妹妹。”她低福一礼,声音比灯火还暖,“今夜无酒、无妓、无乐,小姐可是……另有心事?”
怜月没笑,只淡淡开口:“那晚你说的话,留了半句。”
“今日来,只想听你接着往下说。”
白蝶娘微一颔首,眼神微动,唇角却不扬。
“那小姐……是来听奴讲戏文,还是来演一出真本事?”
她不等怜月回话,便亲自奉上一壶温茶,斟入玉盏,低声道:“若是后者——那奴便斗胆,献上一策。”
阁中灯火摇曳,风声掠竹,茶香清雅,而白蝶娘却低声,在她耳边细细说了一炷香的时间。
那声音忽高忽低,时如温语哄婴,时如利爪撕心;她所述之事,既不伤身,也不伤情,但偏偏伤魂动欲、步步为牢、抽丝剥茧——将冰山美人推入情欲深渊的手段,说得像一场梦,却又字字可行。
怜月听得神色几变,起初带着嘲讽:“这太荒唐了。”
说着却慢慢陷入沉思,唇角渐渐露出一丝复杂的笑:
“……可也未必……也不是个法子。”
她抬起眼,望着夜色之外,苏家堡方向灯火已远,霜华此刻大抵仍在廊上为自己巡夜、清风而立,一如往常那样无可动摇。
白蝶娘垂眸:“那小姐意下如何?”
怜月轻声一笑,指尖拂过案上一枚檀香,没说话,只低低一应:
“......嗯。”
夜风如水,灯市如昼。
江南烟雨市集中,“听香水榭”自有别样风流。它不挂艳帘,不放笑语,却夜夜满座,夜夜不清。那不是寻常的青楼,那是权贵密会的温床,是风月、情报、金钱、胴体交汇之地。
而在今日傍晚,门口一辆苏家特制的细车悄然停靠,驾车之人低头哈腰,帘中人却未露面,只缓缓伸出一只手。
那只手,修长如玉,十指染着浅蔻丹,腕骨玲珑,袖口绣金——不是谁家的小姐,就是谁家的主母。
“怜月小姐来了!”迎门老鸨眼尖得很,连忙将两旁引路小婢轰开,“快快快,把玉香阁腾出来,再派两个最会伺候的姑娘上去!”
帘子轻掀,一道粉衣人影掠下车,踏入香榭之中。
苏怜月今日一袭水红小褂,外罩月白云罗,纤腰紧束,裙摆如烟。她唇不点而红,眉眼含笑,耳垂坠玉,鬓边斜插一枝海棠,风一吹,衣袂轻扬,步步似浮香。
若非她脸上那点不容违逆的傲意,谁看不出这是一尊养在金笼里的娇贵雀儿。
可偏偏,她不是那种乖乖待在笼里的鸟。
她早知道苏家堡内诸多小道,哪些廊角无人看守,哪扇门后藏着一条暗渠,甚至哪匹马性子最稳、半夜不会嘶鸣——她计划这“出逃”不是一次,不是一天,而是早就准备好的习惯性放纵。
她不反省,她从不真反省。她只反谁不听她的命。
“哟,怜月妹妹又来了。”
楼上红纱微卷,缠绵婉转的声音带着一缕醉意,仿佛香气自檀口溢出,撩得人心里发痒。
说话的是“听香水榭”的主人——白蝶娘。
她今年三十四五,正是风情入骨的年纪,一身墨紫宫裙勾出丰软身段,腰极细,胸极阔,尤其一双腿,修长白腻,生得媚骨天成,偏又习惯赤足穿纱履,行来步步生莲,像是踩在人的心尖儿上。她眼角有一枚朱砂痣,笑时微挑,妖媚得不动声色,却让人想甘为裙下奴。
苏怜月第一次踏入香榭时,白蝶娘并未将她放在眼里,只当是哪个贵人府中的小妾出来偷闲,眼底客气,言语却冷。
可谁知这小姑娘后来一来再来,日子准得像过节似的——每五日必到,点戏、选人、赏酒毫不吝啬。白蝶娘这才晓得她来头不小,是苏家堡中那个最难见、最金贵的怜月小姐。
从那以后,白蝶娘待她就不一样了——笑得甜,说话低,送的香奴都是头牌挑剩中最妙的那一朵,还常常打趣她“妹妹比香榭姑娘都勤快”。
曾经,凌霜华冷声教她说青楼是“污浊不可近”的地界,可她只觉那冰冷的苏家府邸,像座闭气的冰窖,连喘息都是罪。
反倒是这里,有人笑她、宠她、跪着哄她。
“蝶娘今日又添了新姑娘吗?”怜月懒懒地靠在玉香阁绣榻上,撩起帘幔,唇角微挑,“我想试试‘翻牌’。”
“都照你的规矩。”白蝶娘笑盈盈地递上一个香案,案上置着一叠绢牌,每张都绣着姑娘名号,配香调、专长、得宠程度一应俱全,仿佛后宫妃子名册。
怜月兴致盎然,一手挑着牌子,一手摸着案边细纹。她的动作娴熟,甚至带着一点故意的戏谑,像极了前朝皇帝听戏翻人侍寝时那种游刃有余的狂妄。
“这个‘初杏’,”她指着一张画着粉杏的卡,“上次你说她会舌技,结果不过如此,嘴都含不全我……嗯……”
她眼波一转,懒懒拖音,抬眼对白蝶娘道:
“叫她今儿倒壶酒便好,别让她那张小嘴再坏了我兴致。”
“是。”白蝶娘含笑低首,眼里却有一闪而过的玩味光芒。
苏怜月懒懒斜倚在锦榻上,素指一翻,指尖轻点香案上三张娟牌,眼中笑意浅淡,像随手拈花,又像挑拣玩物。
“就这三个吧,”她唇角一翘,语气温温的,“人都叫来瞧瞧。”
“哎哟,怜月妹妹挑得真巧,这几位可是近来香榭里头最得脸的,奴这就让她们进来。”
牌子才翻完没几息,便见帘下纱影晃动,有三位姑娘鱼贯而入,衣衫极薄,粉香盈盈。她们一进来便跪拜行礼,连眼神都不敢抬。
她们一个名为月杳,貌若狐媚,言辞滑腻,靠一张嘴哄得勋贵失魂;一个名叫春浓,擅歌舞,腰肢极软,号称能“坐莲翻鹤”;另一个唤作雪鹞,年纪最小,才十五六,肌肤赛雪,最得白蝶娘宠爱。
与苏家那些规规矩矩的侍女不同,这三人一入屋便似水蛇绕榻,动作不急不缓,却每一寸都透着揣摩与讨好。
“小姐好福气,今日气色真是好得很,奴家一进门就被迷住了。”月杳眨着水眸,笑得像蜜,手已自觉地抚上怜月膝头,“想来是昨夜梦里也有人想着我家小姐,才这么润泽呢。”
“是奴家福薄,几晚未得服侍,夜里都梦见自己跪在小姐脚边,被狠狠踩着不许喘气。”春浓有样学样,贴着怜月裙摆,低声笑,胸前两团软肉几乎整个贴在怜月腿边,“醒来时,竟已湿了一片。”
最末的雪鹞却半晌未语,只怯生生地蹲在一侧,手指轻搅着自己衣角,睫羽颤了又颤。直到怜月凤眸一偏,落在她身上,她才低声开口:
“奴、奴婢昨夜在床上磨着腿……想着小姐坐在奴婢脸上的样子……越想越热,也……也湿了……奴婢该打……”
她声音细得像猫叫,羞耻到耳根通红,却又带着那种年少少女独有的清甜与不自知的媚意。
怜月靠在榻上,手指拨弄着香炉盖,目光淡淡,却笑而不语。她不需说话,这些女人自会献上所有。
怜月站起身来,裙摆微动,轻盈如燕,居高临下望着跪在榻下的几人,笑得懒懒的,眼波半垂。
“早上的兴致遭人扫了……嗯,就叫你们几个,替我补回来吧。”
“先来舔舔脚,让我心情好点儿。”
怜月的命令如皇后临朝,懒洋洋地吐出,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意。
“遵命。”
三人齐声,便如三只野猫伏地而上,一左一右,一前一后,跪在她足下争相服侍。
月杳最是嘴巧,一边含着她脚趾轻吮,一边喃喃道:“小姐的脚真香,奴家愿一辈子不吃不喝,就这样含着也心满意足。”
春浓舔的是足弓,舌头卷动得极细腻,每一下都像在书写情书:“这脚心比我的唇还嫩,怕是用花露水洗过千遍。”
雪鹞则捧着她另一足,手掌托得稳稳地,脸红心跳地亲吻脚跟:“小姐别动,让奴家多亲几下……怕一松口就舍不得了……”
她们舔得极认真,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带着真实的取悦、讨好,仿佛争宠的妃嫔,各使浑身解数。
怜月微阖美目,雪白玉足一动一动,若有若无地在她们唇舌间碾压,享受着那种被主动取悦、被人舔到高潮的权力感。她只轻轻一笑,那三人便恨不能将脸埋入她足底,把羞耻当献礼。
“你们中间,谁最会夹乳喝茶?”她忽然发问。
三人一怔,随即异口同声:“奴家最会!”
“那就都试试。”她起身,一指月杳,“你先。”
月杳二话不说,褪去襦裙,解开乳裳,一对白花花大乳自衣中跳出,饱满得像两团熟糯。她跪好,取茶盏放于乳沟之间,轻轻夹紧,竟稳得不晃一分。
怜月勾唇,缓缓低头饮了一口:“嗯……热气正好,奶香足。”
“奴家这乳,是为了小姐特意养的。”月杳娇笑,身子微抬,那茶水被乳肉夹着荡出涟漪,溅落她胸前一串水痕,看得旁人心头发烫。
“下一个。”
雪鹞脸红得快滴血,却也娴熟地褪下罗衣,乳虽小些,却因年少紧实得很,夹起盏来颤微微地抖着。她偷偷望了怜月一眼,舌头悄悄伸出,在茶盏边舔了一圈,才小声道:“小姐若不嫌弃……奴也想舔一口您唇上余温……”
怜月眼神终于动了动,懒懒地垂眸,像猫看小鱼般望着她那稚嫩又贪馋的小模样。忽而抬手,指尖轻轻一弹,正中雪鹞额心。
“小嘴倒是甜,就是规矩都忘了?”
她语气极轻,带着点似嗔似宠的笑意,手却一寸寸抬起,指背轻敲雪鹞下巴:“轮次都记不住的小奴儿,是不是要我喂你一记才学得快些?”
雪鹞脸色霎时惨白,身子伏得更低,声音带着哭腔:“奴、奴不是要抢……只是……只是看小姐今日好生娇媚,忍不住……”
怜月未言,只将一只足搁在她肩上,缓缓施力,让她低头、再低头,直至跪地匍匐,如犬如婢。
她笑了,睫毛颤动,像一尊初登基的小帝王,尝到支配滋味,便再也戒不掉。
此刻的玉香阁中,春光旖旎、欲意蒸腾,妓女们低吟浅哼、娇艳如花,而那位穿着粉衣的苏怜月,正斜倚香榻之上,玉足交错、媚笑盈盈,仿佛已将天下、将万艳,收于脚下。
酒过七巡,怜月面颊酡红,香汗微沁,眼神却越来越迷离,像是水波映月,分不清是映着屋中人,还是梦里景。
香炉里的沉香已燃至尾梢,雾气缭绕成缕,混着屋中肌肤交摩的香汗与酒气。
苏怜月倚靠在软榻之上,怀中抱着尚未着衣的雪鹞,双足分别踩在月杳与春浓后背上,仿佛三只供人玩赏的雌犬。屋中灯影温软,帷帐半垂,春色如露未敛。
忽听门外帘动,一道身影缓步而入,步履轻飘,袍裙摩地如水潺潺。
“怜月妹妹,夜已深了,要不要留宿?”
来人正是白蝶娘,一身靛紫薄绡广袖,胸前半露,纱中春光若隐若现,腰间佩着香囊与绣扇,妆容不浓,却艳色无双。
怜月闻声未答,反而勾了勾手指。
“你来。”
蝶娘抿唇一笑,步步生风,坐在了她对面:“又喝了多少?”
“不过三盏。”怜月一挥袖,身下春浓忙不迭地奉上新盏,“来,再陪我一杯。今夜月色好,不醉无趣。”
蝶娘接过,与她轻轻一碰,玉液入喉,目光始终未移开她眼眸。
“奴听言,”蝶娘轻声道,“妹妹又被那位冷霜护法,罚回深闺反省?”
“呵……”怜月冷笑一声,仰头饮尽杯中酒,“反省?她真以为我还三岁小儿,唬我两句我便乖乖待着绣鸳鸯,读女戒?我都替她脸红。”
她纤指勾起雪鹞的下巴,迫她仰脸接吻,唇齿相交,唾液混着酒香交缠一处,怜月才意犹未尽地将她推开,继续笑道:
“她啊,倒真是个好姐姐……在苏家堡里,我走哪儿都有人盯,吃饭有人看,睡觉有人管,连梦里想的事都能被她揪着拷问一通。她说什么?‘你是小姐,要知礼守身,做不得轻浮之事’。”
“可笑!”
她将杯中残酒泼在地上,吓得雪鹞浑身一颤,怜月却眼神不变,轻轻挑起她裙摆,用脚趾拨弄她腿根湿滑之处,像在玩一团不合心意的泥。
“我在她眼里,就是个需要捧着哄着的瓷娃娃罢了。”
“蝶娘,你说,若有朝一日……我真成了苏家堡主,她第一个,是不是该给我磕头认命?”
白蝶娘勾唇,笑意盈盈,却未开口。
她怔了一瞬,忽地轻笑,像笑自己,也像笑那场梦。
“我该恨她的,对吧?”
“可她生得美。”怜月吐出一句,像从心底逼出来的叹息。
“她有一双眼,冰得像剑,唇却红得像要吻我……她的身子……啧……”
她闭上眼,指尖缓缓抚上自己胸口,似是陷入梦魇,又像陷入欲念。
“我小时候常躲在屏风后偷看她沐浴。她背上那些疤像藤蔓缠在雪地上……每当她抹浴露的时候,那雪白的乳房一颤一颤,我就……”
她话未说完,却缓缓睁眼,眼神一变,带着一点微醺的失焦。
她靠在榻上,呼吸愈发浅促,手指还轻轻摩挲着胸口柔软处,像是在触碰一个长久压抑的梦。
她知道自己喝多了,嘴里说的是疯话,可心底那道念头却真实得像刀刮过骨头——她是真的想过。
想看霜华跪下,不是羞辱,只是……想看她低头的模样。那个从小把她捧在掌心、却又牢牢关进笼子的人,那个谁也不能侵犯、谁也不能亲近的女人——她想亲近。想狠狠地、彻底地、带着报复心也好、带着迷恋也罢,把她那副冰雪做的身体,抱进自己怀里,看她在自己怀里喘,看她颤,看她哭。
可那一夜,她本是夜半醒来,只想寻杯水润喉,路过廊侧时却无意听见了一声低喘。她悄悄拨开一线门缝,看见的,是霜华伏在榻上,而那素衣如雪的清音——正伏在她身下,吻她的颈,舔她的乳,唤她“姐姐”。
「明明那是我的姐姐。」
帷幔垂落,香火微暗,霜华的喘息压在咬紧的唇间,发丝散落,胸乳起伏如潮,那副平日里清冷矜持的模样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任由清音玩弄时,那一点一点被逼出的媚态。
「明明她不该有这幅神情的。」
她只看了一眼,便逃也似地转身。
可那一眼成了钉子,钉进她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从此日日作痛。
她这才意识到——
她想要霜华的,不是姐姐的爱,不是义母的怜惜,而是清音那样的、能让霜华弓身低喘、溢出呻吟、露出媚态的资格。她想看她趴下,想听她求饶,想踩着她那冷若霜雪的脸,说:“你该只属于我。”
可她知道,这份资格她永远得不到了。
她可以是苏怜月,可以是苏家堡未来的女主,却不可以是那个能爬上霜华榻上的女人。
她不是不爱霜华。
恰恰相反,她太爱了。爱得不能说,不能碰,不能妄想。越不能,越想。那种爱像是毒,一旦下喉,就只能用更烈的毒压着。
可她终究压不住了。
她那点孽念,只能埋进泥里、埋进酒里、埋进每一次戏弄婢女时的脚掌碾压中。
那是她唯一能留住霜华的方式了——哪怕是在幻想里。
怜月喝得脸颊泛红,眸光却愈发亮,像点了火似的,呼吸也乱了几分。她俯身望着脚下月杳那张媚眼盈盈的脸,忽然语调一转,声音压得低低的,像在梦呓,又像在挑衅: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
“要是霜华她……也像你们这样,跪在我脚下,被我踩着奶子,舔着我的脚趾,哭着求我原谅她不听话……”
“会是什么样子?”
她说这话时,舌尖还舔了一下唇角,不知是酒后吐真言,还是心里真藏着这样一幅画面太久了,竟带出一种说不清的兴奋。
“你!”
她抬起手,用纤指挑起雪鹞的乳鸽,那乳尖已湿润香软,红得似染了花汁。
“你现在是她。”
雪鹞一愣,立刻低头应道:“是,小姐,奴是您那位冷霜护法。”
怜月喉头轻动,低笑:“好……那就跪好点。”
她一脚将雪鹞按在地上,踩住她后颈,像踩着霜华的傲骨。
“你不肯听话,对我冷着脸,处处压我,现在知道错了?”
“知错了,小姐……”雪鹞声音娇弱,眉头紧蹙,像真的羞惭悔恨。
“月杳,你是她的手。”
怜月一指,月杳立刻俯身,将双手贴在她大腿内侧,自下而上地缓缓摩挲。
“你平时用这双手替我梳头,替我拭泪……可现在——”
“现在该替小姐捧香趾,舔玉足……不敢再妄图操控。”月杳张嘴含住她脚尖,唇舌缠绕,舌根卷得极深,舔得怜月脚心都一阵阵酥颤。
“春浓,你是她的嘴。”
怜月眯眼,脸上浮出一抹几近疯狂的笑意。
“平时你用这嘴教我女戒,说什么‘小姐应贞静’,呵……你来,现在就用这张嘴给我唱,唱你怎么被我驯得伏在床上,被我骑在脸上,哭着求肏!”
春浓脸色通红,立刻伏地娇声哼唱,语调淫媚:
“奴是苏家护法凌霜华,今夜甘为怜妹胯下娃……舌尖若不晓那深处春,便唤那玉趾碾贱奴臀……”
“再说一遍!”怜月低喝,猛地将双脚并拢,夹住春浓的头发,像夹住霜华的发髻。
“说你是霜华,是被我调教、被我骑弄、被我踩下贞节的母狗!”
“我是!我是……”春浓哭腔溢出,面色酥媚,“我是小姐的霜奴,是小姐膝下舔穴的雌犬,是您用足趾驯化的下贱婢奴!”
怜月终于笑了,笑得像雪中开花,艳而疯魔。
“霜华啊霜华……你那么高傲,我都快看腻了。”
“你若有朝一日……也能像她们这样,伏在我脚下,用舌头舔我,舔到我颤得不想说话,哭着说‘小姐别再踩’……”
她猛地仰头,一盏酒自唇边洒落,香液顺着雪颈滑至胸前,滴入乳沟,她却仿若不觉,只闭着眼喃喃:
“我就原谅你了……”
她醉了,彻底地醉了。可她吐出的每一句,都不是胡言。
脚下三人继续娇喘承欢,一边哀哀地替她按摩舔吮,一边有意无意地重复着她幻想中的羞辱对白,把这场春梦渲染得愈发荒淫、愈发真实。
但怜月忽然怔住了,像被自己舌尖蹭破了什么,酥麻过后,才后知后觉地察觉不对。
她把那种藏了太久、只敢藏在梦里反复回味的念头……在外人面前说出口了。
纵是醉意缠身,她也知刚才那句话意味着什么——
她在说,她想驯服她的护法。
她想调教她的义姐。
她想将那位冷面杀神,变成脚下淫奴。
但她知道这只是妄想,是会让任何人惊讶得掉杯的疯言疯语。
她轻咳一声,唇角带着一抹强撑出来的笑意,拿起酒壶亲自替蝶娘斟了一盏,递过去。
“哎呀……蝶娘见笑了。”她声音一改先前醉意喃喃,语气带点娇俏又不失世家小姐的分寸,“我方才是喝高了,竟胡言乱语起来。家中私事,不该乱说。您就当我在编戏文罢。”
白蝶娘接过酒盏,红唇微扬,未语,笑意却藏在眼角那一枚朱痣下。
“若这戏文真能成,倒也是一出风流传奇。”
她轻抿一口酒,忽地压低声音,带着一点半真半假的恭敬:
“小姐若真有此志,奴也不是外人,不妨……让奴为您出些法子。”
“只要将来小姐登位之日,不忘了听香水榭,有福同享……奴这一榭,这一身……都听您吩咐便是。”
她说得轻,却字字滴血,是一封悄然递出的投名状。
怜月听罢,怔了一息,旋即笑出声来。
“就凭你?”
怜月半垂着眼帘,淡淡又补了一句:“霜华那人你也知,清冷无情,武功又高,一柄霜刃出鞘,多少江湖人连她影子都摸不着就死了。”
“我小时候亲眼见她一招‘霜骨斩’把刺客整个人从中间劈成两半,连血都还在半空没落地,她已经走完三个方位。”
“她的腿极长,出腿带风,扫来时连地砖都断三寸。她一掌打在石柱上,那石头像豆腐一样碎。”
“可她的身子……”怜月眼神一转,带着些酒意的痴,“却柔得像水一样。我无意间碰过她背,那皮肤,比婢女们洗三次花露还细。”
“她明明生了一副妖骨,却偏要装成冰山。”
她说着,自己都笑了笑,带着点自嘲:“我就算想,能奈她何?她若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恐怕连脚趾都不屑让我等碰到一下。”
白蝶娘却只笑,笑得极淡,唇角不扬,眸光幽深如蛊,仿佛万千胭脂泪都沉在那一眼之下。
“我不懂武功。”
她缓缓踱步,声音不紧不慢,却每一字都像针,直刺欲根。
“但我……懂女人。”
她停在几名仍伏在地上的妓女身前,目光落在那最小的雪鹞身上。
“雪鹞,过来。”
雪鹞一颤,连忙爬起,低着头走到蝶娘身前,恭恭敬敬跪下。
蝶娘半蹲着,抬起她的下巴,那动作没有一丝粗暴,柔得仿佛拂花。
“你总觉你的姐姐冷,不近人情——可这世上最藏不住欲的,恰是那种看起来最会忍的女人。”
“越是冷,越是忍,她们骨子里那点欲根,才藏得深,烧得久。”
“可她越是忍得住,调起来才越好看。”
“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容易沦陷?”
“不是那风尘惯走的,也不是甘作贱奴的,而是那种——尝过一丝甜,就以为不过如此的。”
“她们不识自己的身体,不知快感与羞辱只隔一线;她们误把克制当高洁,把沉默当强大。”
“但直到第一声哼吟自喉中泄出时,她们自己都吓了一跳。”
蝶娘伸手按在雪鹞的肩膀,让她身子向后仰,露出脖颈与胸前一抹雪白。
“来,我们让小姐见识一下,怎么调一具‘初开’的身子。”
雪鹞咬唇不语,却乖巧地仰头任她摆弄。
蝶娘只用指尖,在她锁骨处轻轻绕了一圈。
“你瞧,这地方,最开始不敏感,但女人一旦心乱,血脉一冲,这里会发烫,像烧起来。”
她手指一点点下滑,绕过乳沟,沿着乳下轮廓缓缓划线,每一下都像是刻字。
“然后是乳根,最容易藏羞。别看她乳尖立得紧,其实这根下的神经才最能勾魂——”
她轻轻一捻,雪鹞身子一颤,唇间微张,差点叫出声来。
“再往下。”
她一手掀开雪鹞的裙摆,将她双腿并拢抬起,一指点在大腿根最内侧:
“这里连婢女都不一定知道自己会颤,可只要捻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羞还是爽。”
“你若想降服你家护法姐姐,千万别急。你别跟她斗力斗狠,那是她最擅长的。”
“你要诱她,试她,撩她。让她冷艳的面具自己碎,让她那身媚骨在羞耻中软化。”
蝶娘回头看向怜月,眼中带着一点近乎慈悲的柔光,却媚得让人心里发痒:
“你要让她从冷傲中泄出第一声呻,从清高中舔下你脚趾,从她最倔的一口气里,哭着咬牙,把求饶的声音亲口吐出来。”
“那时候,她再不会拔剑,只会张口。”
“而你,只需坐着,看她一寸寸地烂在你掌心。”
她轻轻推了推雪鹞,那姑娘整个人软成一团,已是双腿发颤,喘息不止,脸色红得像熟桃,仿佛真被抽去了魂魄。
蝶娘缓缓直起身,淡然整理袖口,仿佛刚才那不过是一场温柔的茶艺表演。
“小姐若信我,奴不才,愿替您布这一局。”
“若不信……也无妨。”
“您也且当听了个故事,回头再笑便是。”
白蝶娘话音落下,怜月却未答。她只是低头饮酒,半盏未尽,眸色已沉了几分。
她原本兴致正浓,打算就在香榭歇下,叫人调灯设榻,好好再作一夜春梦。
可不知为何,蝶娘那番话像一枚火星,落在她心口深藏多年的某个地方,烧出了火,也烧出影子来。
帷帐未收,酒盏犹温,苏怜月却已披上外裳,淡声唤马,神情如水,不动声色地回了苏家堡。
那晚,怜月枕着檀香丝被,辗转无眠。
屋外虫吟低鸣,夜风轻拂,她却只觉得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烧着——烧得她难受,烧得她闭上眼就是那夜里听香水榭的帷帐、朱灯、软榻与脚下那三名妓女娇喘含泪的模样。
更忘不掉的,是白蝶娘那句贴在她耳边轻语的话:
“从她最倔的一口气里,哭着咬牙,把求饶的声音亲口吐出来。”
她醒来时下身已湿透,脸颊火热,气息未稳。
日子越过越平,苏家堡一切如常。
霜华还是那个霜华,一袭素纱,束胸利带,剑从未离身,话从未多言。她每日巡视、训练、批阅,偶尔出现在怜月书房门外,只一句:“小姐是否用饭?”便不见踪影。
而怜月,自那天从“听香水榭”回来后,也像变了个人。
她不再常常顶嘴,也不再时不时闹脾气;她每日早起,温声答礼,练字持琴都极规矩。霜华说什么,她便应什么,还时不时唤她一声“姐姐”,眼眸含笑,软得叫人心都发烫。
霜华起初不以为意,后来却慢慢放了心。偶尔也会多说一句话,晚些离开些时辰;见怜月咳嗽两声,便让清音熬了汤亲手送来。她从不惯人,可唯独怜月这几日的乖巧,叫她忍不住多少回了些人情味。
然而怜月眼里的她,不再是那个让人敬畏的护法,而是一副套着冷冰冰皮囊的淫骨仙子。
怜月笑着吃她递来的药汤,眼神却落在她蹲身拂袍的曲线上;她说“姐姐照顾得真好”,语气乖巧,指尖却悄悄压在裙下,缓缓研磨自己发热的穴口。
她的腿那么长,腰那么细,乳那么丰,走路时肩胛微动,臀瓣随步轻晃,说话时声线低柔,像是压着呻吟;弯腰时衣襟滑开一线,仿佛特意撩拨人心;那剑从背上滑下时,更像极了情人卸甲褪衣的背影。挺着胸、撅着臀、媚着眼,等着谁扑上来将她咬开,掰进怀里,啃得满唇是汗,是油,是呻吟。
她盯着霜华脱靴时露出的白嫩脚踝,心里想的却是那双脚是否也会在自己舌下轻颤;她看她练剑时乳峰一跳一跳,便下意识地用玉足轻蹭自己裙下,幻想那副高不可攀的身子被自己逼跪在地,双乳贴地,肩胛撑起,汗水从背脊滑下,抖着腿夹着主人的脚尖,含着羞在她耳边哭着喘着求原谅。
“妹妹……请、再、重一点……”
她开始坐卧难安。
越是乖巧,幻想就越疯。
越是温顺,她心底那只兽就爬得越高,咬得越深。
她心里明知道这是疯的,是错的,是痴人妄想——可她那点小小的克制,早就被那晚白蝶娘那番话敲裂了。
“她越是忍得住,调起来才越好看。”
于是,当禁足期一过,她几乎是第一时间又踏入了听香水榭。
这一次,她没有让人备车,而是带着一名贴身婢女,以赏灯会为名悄然入市。
不饮酒,不翻牌,不掀帘——她一进门便点名:“叫白蝶娘来。”
老鸨忙不迭迎上,婢女被留在楼下,怜月被请入后院竹亭。白蝶娘早已候在那,换了一身素金织缎轻衫,妆容比那晚更淡,却媚得更加勾人。
“怜月妹妹。”她低福一礼,声音比灯火还暖,“今夜无酒、无妓、无乐,小姐可是……另有心事?”
怜月没笑,只淡淡开口:“那晚你说的话,留了半句。”
“今日来,只想听你接着往下说。”
白蝶娘微一颔首,眼神微动,唇角却不扬。
“那小姐……是来听奴讲戏文,还是来演一出真本事?”
她不等怜月回话,便亲自奉上一壶温茶,斟入玉盏,低声道:“若是后者——那奴便斗胆,献上一策。”
阁中灯火摇曳,风声掠竹,茶香清雅,而白蝶娘却低声,在她耳边细细说了一炷香的时间。
那声音忽高忽低,时如温语哄婴,时如利爪撕心;她所述之事,既不伤身,也不伤情,但偏偏伤魂动欲、步步为牢、抽丝剥茧——将冰山美人推入情欲深渊的手段,说得像一场梦,却又字字可行。
怜月听得神色几变,起初带着嘲讽:“这太荒唐了。”
说着却慢慢陷入沉思,唇角渐渐露出一丝复杂的笑:
“……可也未必……也不是个法子。”
她抬起眼,望着夜色之外,苏家堡方向灯火已远,霜华此刻大抵仍在廊上为自己巡夜、清风而立,一如往常那样无可动摇。
白蝶娘垂眸:“那小姐意下如何?”
怜月轻声一笑,指尖拂过案上一枚檀香,没说话,只低低一应:
“......嗯。”
qpf7103发布于 2025-04-05 23:09
Re: 【中篇】【连载中】【4.5 更新第一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歪日,还有高手?还附带这么劲爆的剧情啊,一口气看下来十分期待后续
究极足控少女发布于 2025-04-06 00:47
Re: 【中篇】【连载中】【4.5 更新第一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这剧情很赞啊,文笔也不错!催更!
第二章
夜未央,月将沉。
苏家堡的围墙在月下如兽伏影,沉默不语。四周巡夜的火把已经熄了一茬又一茬,换岗未至,藏匿在暗中的黑影,悄然游蛇般滑入了沉睡的院落。
“东南角已清,五人。”
“西北侧尚有灯火,无妨,避开即可。”
几名黑衣人身法古怪,低语如蚊,不循武林常式,偏偏动作极利落,仿佛关节能随意折叠,行走间无声无息如蠕虫潜沙。他们趁夜色逼近内宅,每一步都踩在瓦梁间隙上,避过所有机关与响木,如幽魂夜渡,只为一人——
苏怜月。
一柄细匕滑出鞘,弯若蛇信,薄得几不可见。一名黑衣人贴身潜近,俯瞰榻边熟睡的小丫鬟,眼神冷淡得如看一抹尘埃,却不带丝毫杀意。他手腕一抖,袖中滑出玉针般的银叶,轻点其颈后麻穴,少女便眉心一蹙,沉入更深梦境,连哼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另一人早已贴墙滑行,一指探出,拂过守卫脖颈。指尖露出的细管中喷出一缕无色烟气,幽冷入骨。那侍卫面色一怔,手中刀才举到半空,便软软垂落,歪倒在地,尚未清醒,已坠眠深渊,气息沉稳如婴。
夜色悄无声息地吞噬一切动静,未曾惊扰星月。
唯一一处意外,是侧门之守。那人血气方刚、筋骨强悍,竟在中毒后挣扎踉跄两步,嘴唇微启,一点气音已欲呼喊,却忽被一掌贴面封喉,咽息中断,只余唇齿张阖,神情僵滞,声音终未破夜。他眼神怔然,倒地之际被接住轻放,连盔甲都未碰响半寸。
十余息后,整个内宅早被他们悄然封锁,连猫狗都不曾惊动,唯有暗处灯影忽明忽灭,仿佛随呼吸跳动。
“呀啊!!!——”
忽有女子尖叫,刺破夜色,如银针刺破水面,带着惊恐又隐忍的裂音,从寝阁深处骤然传出。
“怜月!”
寝阁内,凌霜华的眼在一瞬睁开,眸中冰光炸裂,竟比夜更冷。她恍然间是五年前苏家堡东厢庭院,苏无恨躺在血泊中,左臂已断,身上插着三箭,鲜血漫出薄衫。
她不愿再看一次。
衣衫未整,霜华已夺门而出,素衣未掩美骨,冷刃已出鞘三分。她身影掠至院中,月下如电掠霜,青丝飞散,冷艳到极致,也媚得摄人心魄。
一名刺客方才穿身而过,尚未落地,便被她一刀横斩,血花喷洒,落在她纤腰与侧乳之间。
她甚至未看他一眼。
“擒苏家千金!”
有人喊。
下一瞬,霜华已如魅影杀至,刀光未动,气势先撼心魂。
她那身素袍贴肉而薄,每一次横斩、旋步、掠影如燕,都牵动着胸前微颤欲脱的曲线,雪乳若隐若现,仿佛勾人心魄的梦魇。然而她的神色却冷得逼霜,每一刀都似要断人生机。
“天生媚骨……却是刀下不留情的妖孽……”
刺客失神一瞬,霜华已欺身而近,右手翻腕,一记斜劈斩颈,力贯三分,血箭喷出。
第二人怒吼扑来,她刀尖上挑,将对方手中钢刀弹飞,左手五指如钩,反扣其衣襟下摆,猛地一拽——纤指探肉,力道精准,喉骨“咔”的一声断裂,宛如山雀骨折。
他未及惨叫,霜华已半身贴近,顺势一刀反撩,从大腿内侧斜斩而上,直断要脉,血溅如雨,染红她半条素腿。她连眉头都未皱一下,眼神反而更冷,仿佛杀人只是一次缓慢的吐气。
杀意入骨,媚意入骨。
这一身不该杀人的香肌玉骨,一颤一动都如勾魂摄魄的舞伎,可她偏偏每一式每一招皆为杀招,收势如疾风骤雨,落点如死神点穴。
她那刀——不是削铁如泥,而是绕身三尺如蛇缠骨,游龙般探向敌喉,每一次挥舞,都似吻喉之刃,实则断命之器;那身形——不是舞者,而是苍狼扑野,身姿旋舞间,血已四溅。
数名刺客已心神俱裂,接连倒退,口吐血沫。
“姐姐!救我——”
内堂深处,忽传来苏怜月一声惊叫,声音细弱如丝,软腻如梦,仿佛一缕残香惊魂未定,似真似假,却挑得霜华心头猛然一紧。
她足下一旋,倏然破窗而入,刀气一振,便劈断梁柱,碎木横飞,将一人撞得半张脸塌陷,滚地不起。
霜华身法低伏如燕掠地,刀鞘扫火,将案前烛火尽数乱卷,也将她那张染血冷绝的面孔映得如魅如神。
只见那名刺客早已将苏怜月挟持在前,匕首抵在她纤颈,笑意冰冷:“你敢近一步,我就——”
话未出口,霜华早已如箭脱弦,手中长刀倒转而握,脚下一踢,踢翻侧柱灯。
火影摇曳间,她刀影如游蛇穿案,从桌底反斩而起,一记螺旋斩击打落匕首,寒芒乍现!
“呃啊——!”
那人肩头迸血,踉跄退后。霜华不给喘息之机,左肩一旋,刀随势回,半月斩猛然贴胸而落,重重斩在他心窝。
“咚!”他身形一震,吐出大口鲜血,颓然倒地,不省人事。
苏怜月跌入她怀中,身香如兰,轻颤如雀。她整个人像是软成了一团香脂,嵌进霜华的胸前,唇边带着未褪的余惊。
“你没事吧。”霜华声音低哑,刀尖滴血未收,怀里却抱得极轻极稳,如捧珠玉。
“……姐姐,”苏怜月微抬螓首,眸角犹挂泪痕,指尖却缓缓搭上霜华那把染血尚温的大刀,轻声呢喃,“留他一命……”
霜华眉心微蹙,冷光未敛,仿佛那杀意未曾散去。血从断木横梁间淌出,流过阶砖,蜿蜒涌至霜华脚边,将她白靴底缘染上一抹刺眼深红。她不动,影子立于血泊中,仿佛一尊不容忤逆的阎罗女。
“让他说出……他的主子是谁……为何要行刺。”
她沉默了两息,刀身微倾,终还是**将刀收回半寸,重刀挽手反握,刀背贴臂,杀意却未散半分。目光冰寒如初,转头望向那尚存一息的黑衣刺客。
“说出你主子是谁,我让你死得痛快些。”
那名刺客被她一刀刺入肋下,此刻正瘫倒于地,血如涌泉,自伤口溢出,混着碎裂骨骼的呻吟抽搐不已。他面色青白,嘴角泛血,只余一口吊命的残息。
“说。”她冷冷吐出一字,声如雪夜凛风,“谁指使你们。”
刺客张口咳血,半边脸贴在血污中,嗓音嘶哑:“是……是当年……那批人……他们没死……”
“什么人。”
“……五年前……杀苏无恨……的那些……”
空气瞬间沉重。
霜华指尖微颤,刀口却没有一丝放松,更刺入他皮肉一分,血丝顺着喉口蜿蜒淌下,触目惊心。
“他们听说……”那刺客唇角扯出一抹狞笑,嘴角涎血滴落,喘息间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兴奋,“苏无恨……还有个女儿,藏在堡里头……模样还俊得很……啧,长身玉立,冷得像冰雕,可要是脱了衣裳绑在床上,叫她学狗学猫地叫,岂不比什么花魁还招人疼……”
他咳着血,却仍笑得淫亵,“几个兄弟说了,要抓了她……剃发换红裳……塞进青楼好好调教成一尊淫娃……日夜轮翻,把她骨头肏软,把苏家的脸,肏进泥里……让那老头子死都死不瞑目,死了都得听她浪叫——咳……咳咳——”
霜华眼眸骤然一缩,杀意如潮天崩地裂。她那一双本冷若霜池的眼眸,瞬间灼烧成地狱修罗,指中长刀一抖,刀尖斜指咽喉,寒光流泻如怒蛇蜿蜒。
“敢辱她,你们该——”
“姐姐!”
苏怜月突然开口,声音轻柔,却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道,握住她执刃的手腕。
霜华偏头,眸光仍燃着杀意:“你可知他们要做什么?”
“当然知道。”她垂眸,睫羽掩住情绪,声音却稳,“正因为指导,我们才不能现在杀他。”
霜华眉头紧锁,长刀微微一顿:“你想从他嘴里挖出更多?”
“若不查根究底,这样的人,杀一个还有下一个。”怜月语调冷静,双手交叠于身前,神态仍是那副胆怯惊魂未定的模样,可那份镇定却诡异得令人心惊。
“今日能刺入府中,明日就能潜入花阁,若不拔出根来,防也防不住。”
霜华没有言语,杀意如旧,却微微敛了三分。
“继续说。”怜月低头望向刺客,语气温和,却字字钉骨,“若你再敢含糊,就别怪霜姐姐的刀把你骨头一寸寸剔出来。”
刺客身子一抖,拼着气息断续道:
“我们……我们接到指令……若得手……就送人去……‘听香水榭’……”
霜华眉头皱起,低声:“何处?”
“江南城东南角……青楼酒肆汇聚之地……那家香榭是……是专做贵人交易的地方……我们只管送人,交给那里的‘白蝶娘’接手……”
霜华喃喃复诵:“白蝶娘……谁是白蝶娘?”
刺客摇头如捣蒜,语气愈发虚弱:“是那边的主事……我们从不过问她底细……任务完成便算数……再查……会死的……”
霜华目光如刃,望着地上那人半死不活,锋刃不动,却已悄然将劲势聚至足下,随时可收其性命。
“姐姐。”苏怜月轻声唤她,伸手轻抚她肩胛,“他活不了多久了,何必让他死得痛快?”
她转身,长发拂肩而落,步伐冷定,但心头却是惊疑不定——她从未听过“听香水榭”的名,更不识“白蝶娘”,而这家青楼能与刺杀苏无恨的余孽牵上线,背后岂止是风月之地那般简单?
她垂眸沉思半晌,终是压下满腔杀意,决定先顺怜月意行事,暗查此榭根脚。
“绑了他。”她收刀入鞘,沉声道,“等他再咽几口气,就给我吐干净他知道的每一个人名。”
翌日清晨,雾色未散,晨钟尚未响彻城头,苏家堡便已出动。
三十余名亲卫披甲而行,自府门而出,直奔江南城南角,那里灯红酒绿,风月之地林立,而最中央一栋朱漆香榭,三层飞檐,红绡环绕,正是昨夜拿刺客口中的——“听香水榭”。
世人只道那是权贵放纵、佳人如云之地,岂知此地背后竟牵连着五年前的血仇残党、苏家千金遇刺之局?
“搜!听香水榭全楼,鸡犬不留!”
苏家亲卫踏入香榭之内,甲靴碾红毯,刀戈亮寒光,香粉气顷刻被肃杀气吞没。白蝶娘还未来得及从榻上起身,便已被擒下,慌不择衣,只着一袭轻纱睡袍,半裹半露,妆未卸完,香气犹存,神色却慌乱如斗败花妖。
她满身粉脂香汗,被反绑双臂押上马车时还不停辩解:“冤枉、冤枉啊!奴家只是个开楼的……何曾掺和江湖仇怨……”
入了苏府,带到堂前,她被一把推至红毯之上,跪得狼狈。霜华负手而立,目中寒芒如霜刃冰针,苏怜月则侧坐于榻,眼波浮动,似笑非笑,唇边一痣红艳如血。
“就是你受命接收苏家小姐?”霜华站在她面前,眼中已凝杀意,“你可知她是谁?”
“奴家、奴家哪知道啊!”白蝶娘脸色煞白,“那边人出的是重金,说要找个懂调教的青楼来收个女货,说是……说是要把她养成能让狗都发情的尤物……奴婢贱命一条,也只想着赚钱养楼,哪知道她是苏家千金啊?要是早知道…就是给奴十座香楼,都不敢沾啊!”
她哭得衣袍滑落一肩,露出青白锁骨,脸颊涕泪交融,惨白得几乎不像活人。
霜华冷哼:“这等败类,留你何用!”拔刀三寸,寒芒已出鞘。
“我有办法!”白蝶娘突地惊叫,面色骤变,几乎跪着往前扑,挣断绳索的皮带咯吱作响,“他们这事才刚起头,我知道他们还藏着更深的人!联系奴家的那个中人……下个月还要来香榭!你们想查,就得引出更大的头目……奴……奴家可以帮你们引蛇出洞!只要你们……只要你们别杀我。”
刀光凝滞,霜华低声道:“说。”
白蝶娘却左右环顾,神色惊惶欲绝,声音颤着发出:“这话……在这儿……说不得。墙有耳,院有眼。奴只收钱行事,真正的买主是何人、藏身何处,若叫他们知我露了口风,只怕香榭上下都得陪着小女陪葬……”
霜华目光更冷:“你在卖弄玄机?”
“姐姐。”一旁苏怜月轻声开口,语气却柔得似江南春水,缓缓绵绵,偏又带着一缕惹人怜意的娇气,“她这般模样,倒也未必尽是虚言。听她一听……也无妨。”
霜华眉未动,怜月已垂眸上前半步,声音轻得仿佛怕惊着什么:“若她真有法子,自可引出余孽;若是唬我等,那时再斩也不迟……”
“好姐姐,依我一回罢。”
霜华沉吟片刻,终是冷冷一收刀:“随我来。”
三人穿过垂花门、绕过月影廊,直至后园最深处一处偏院。那院名唤“秋静”,昔年曾为苏怜月学艺时所设清修之所,院中无酒无欢,无琴无伎,唯植竹数竿,绕廊一方,供她静坐练气、课诵藏经。自她成年后便久未再启,屋门尘封,帘角落蛛网,隐有余香犹在。
此刻院门一开,浮尘翻舞,竹影斜照地砖,竟似尘世之外。
霜华目光一扫四方,亲自遣散院内旧婢,命其不得入内;更提声传令,将外屋左右侍卫悉数退去,五丈之内,不许有半人靠近。
厅中旧榻上香炉微熏,香气若有若无,带一丝凉意;屋外只闻风动竹声,沙沙如水,天地寂然。
“说吧。”霜华站于窗前,冷背迎人,眸色沉沉。
白蝶娘此刻已被换上清衣,双手搓得发红,小心翼翼地坐在屋内绣凳上,望着两位女子,一位若霜若刃,一位若水若狐,眼中藏着贪婪又隐秘的火焰。
“其实……”她一字一顿,嗓音变低,“想引出那些人……小姐必须亲自……演一场。”
霜华眉头微动。
苏怜月轻轻歪头,似笑非笑:“哦?演什么?”
白蝶娘露出一个仿佛羞赧的微笑,像是妓馆初夜时不敢抬眼的新人:“演……一个被卖入青楼的贵人胭脂货……诱得他们现身,以真钩钓鱼,引鬼上钩……”
她微笑着摊开双手,指节瘦长如枯枝,却像蛇蜕一般灵活:“只需放出风声,说我听香水榭最近收到一批贵人血脉,精挑细选、专供重口,藏在南院密榻,便可将他们勾出暗巢。那帮畜生若知道‘苏无恨之女’已落青楼之手,必然按捺不住。”
霜华眉头如刀锋,寒声割出:“你说……要让怜月,做青楼妓货?”
白蝶娘微微垂首,语气带着一丝刻意营造的“羞耻”和“无奈”:“非是奴家有意亵渎小姐,只是……对方只知‘苏无恨有一女’,却不识模样,若无‘实货’可看、可玩,便断然不会现身。”
“你——恬不知耻!”
霜华怒喝,杀意未出,已震得桌角花瓶微颤,香炉翻滚出几缕灰烬。她一步逼近,冷目如雪盯向白蝶娘,眼中杀意如黑潮压顶。
“休再妄言一字,我宁愿将那群狗贼逐个剐皮,也不会让她堕这污泥!”
“姐姐。”
怜月轻声开口,语调平静得近乎冰冷,像一池被夜色封住的月水。
霜华转头,看见她缓缓起身,双手交叠于前,目光坚定如初雪之刃。
“这是我的仇。我父亲的血,滴在你我之间五年,不能永远由你一个人背着。”
“自从那年……自从我爹爹倒在血泊里,死在那些人的刀下,我就从来没一日睡得安稳过。”
“我日日想着,若有一日能把他们挖出来、一个一个剜心刮骨,才能告慰他在天之灵。”
“可现在——他们不仅没死,还想着继续害我。”
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些,却冷得令人发寒:“若这仇不报,我有什么脸,再去九泉之下见我爹?”
“我愿意。”她走上前来,面对蝶娘,盈盈一礼,声音中带着说不出的凛冽之气,“为报仇雪恨,哪怕失去清白、堕入泥淖,又有何惧?”
霜华呼吸一顿。
那一刻,她几乎看见苏无恨的影子重叠在这少女背后。那双眉眼那么像,那句“为仇赴死”也几乎是他曾说过的话。
可她分明记得,那人临终前只说了一句:“照顾她。”
护她一生,护她清白,护她不入江湖,不踏血河。她怎能……
她自问不是个多情人,刀下亡魂无数,冷情冷命,纵有爱人清音,也只敢在夜里轻唤几声,从不曾奢念长久温存。她杀得多了,心早已被铁血浸透,早就明白情之一字,于她不过是命外浮萍。
可她从来不悔,因为她是凌霜华,是苏无恨亲选的托孤人,是为苏家持刀之人。
但现在,她站在命运之门前,听见那个五年前还娇怯藏在她怀里哭泣的小女孩,要以血肉之躯为诱饵入局,以清白与尊严,做一场青楼诱狐的“活香饵”。
她能斩千人,却唯独斩不下这一个。
她喉间如被火灼,眼底有潮水在翻,可她只是闭上了眼。
苏无恨的声音在她耳中响起:“你要护她,护她远离江湖,护她远离我这条血路。”
他临死那夜,断骨撑地,血泪涌眼,死也不肯闭眼,只怕她守不住这个女儿。她应下了,在他断气前那最后一刻。
五年,她未曾违背——
但她知道,若再犹豫一步,她便将亲眼看着怜月走入青楼,被群狼环伺、化作一具任人羞辱的“肉货”。
霜华猛地睁眼,目光已不似之前那样清冷,而像一道倏然下坠的瀑火,燃着绝意与孤勇。
“够了。”霜华声音微哑,却骤然斩断一切,“此事……由我来。”
怜月眼底似有一丝光轻轻一跳,像深水中一抹久藏的喜意终于泛起波纹——
只是刹那,她便已敛下眼睫,将那点欣悦压进唇角柔意中,语气依旧温婉乖顺:“姐姐,你——”
“别再说了。”
霜华转头,盯着她,一字一顿,仿佛咬断了她一生的矜持:“你不能去,我不会让你去。你若跳进去了,我这五年守着你、护着你、杀人、负命……便全成了笑话。”
霜华转身面对白蝶娘,双目如冰针,话语却重如寒铁:“你不是说他们不识小姐的真面目?只认身份只认传言?那便由我来假作她。”
白蝶娘愣了半瞬,眼底迅速掠过一抹光亮,却故作惶然:“霜华姑娘您……您怎可如此?万一身份暴露,那可……”
“我武功在身,自能自保。”霜华冷冷道,“且他们若真是余孽,必然先试货,试过之后才交人,自有空隙可布防设计。你只需按你所说布局,其他不用你管。”
她顿了顿,又道:“他们只知苏无恨有女,却不知究竟几位。我亦是义女,名分在身,身份足矣。”
“可……可是……”
“够了!”她一喝打断,又冷冷盯住白蝶娘,“你若再推诿半句,我便将你舌头割下,看你还能说多少花话!”
白蝶娘俯身连连点头,做出一副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模样:“不敢,不敢!我只是担心……姑娘身份贵重……唉,这法子原是为小姐设计的,如今变通……也…也未尝不可。”
她眼角余光一闪,看向站在一旁的苏怜月:“何况姑娘气质冷艳,一身媚骨更是人间罕有,那些人不识真身,只怕更信这‘极品胭脂货’非她莫属。”
霜华面色一沉,冷冷一瞥。
而怜月——唇角仍是那抹温顺笑意,只是那眼中,有一丝细不可察的亮光微微绽开,像花蕾悄悄舒展。
“姐姐……”她轻轻唤了一声,语气里含着怯意与柔情,双手缓缓覆上霜华的手腕,语调如初春细雨,“你为我挡了太多,如今却要我眼睁睁看你涉险……我怎舍得呢?”
她话未说完便低垂眉眼,轻轻咬了咬唇,嗓音细若蚕丝,却带着一丝注定劝不动的无力:“可我知道,姐姐你既然已决意一试,我拦也拦不住……”
她抬眸望向霜华,眼圈微红,泫然欲泣,却强忍着未落一滴:“那……我便听你的。只是怜月无以为报,唯有来生再做牛做马……”
语罢,她低低福了一礼,声音几不可闻:“……也许今生,也做得起。”
霜华指节微颤,终究没有挣开她的手。
白蝶娘在一旁拱手:“既如此,奴家便按霜姑娘之貌、之骨、之姿,为她设局一场。要做出一个‘能叫江南百妓自惭形秽’的极品尤物来,引那群狗贼自投罗网。”
“只求姑娘……能扛得住那些人‘调教试货’的手段。”
话语如蜜滴在刀锋上,甜得腥凉。
霜华沉默半息,终于闭目,缓缓吐出一句:
“我扛得住。”
“姑娘这份胆识,奴家佩服得紧,便依你意思,奴这就着手筹备。”
屋外仍是沉静。夜未阑,风过竹影微颤。那是一种蓄势的沉寂,像战鼓落下前的最后一声吸气。
密室之中,三人尚未踏出一步,窗帘低垂,炉香袅袅,灰白的烟打在屋梁上,像风月未醒的眼角纹。仆人已被遣去准备“入局之器”,白蝶娘所需之物一应俱全,尽由信任之人暗中送至。除他们三人,府内再无人知晓这场“引蛇出洞”的谋局。
白蝶娘与苏怜月换上了从刺客身上扒下的夜行衣。黑衣贴身,窄袖紧裹,宽腰束带,细节一丝不苟,连血迹都用颜料精心补涂,乍一看去,与那夜屠堡刺客无异。白蝶娘嘻笑着翻转匕首,在怜月身边转来转去:
“呵,小小姐穿这身杀气腾腾的,竟也有几分妖媚。”
怜月转头一笑,眸中清冷如冰镜:“你不也穿得像只狼婆?再油腻些,我就信了你是头领。”
白蝶娘“啧”了一声,没再回嘴,转向屋中那一人——
凌霜华,仍跪坐于火炉前,背对众人,未言未动。那一袭素白中衣已解去外袍,鬓发微湿,似是洗过热水,肌肤在烛光下泛着幽冷的光泽。
“该开始了。”白蝶娘说得平静,语气却带笑,“姑娘,要入这一局,可得把皮先剥了才行。”
霜华没有转身。她将手搭上衣带,微一用力,袍带滑落,带起一声轻响。
她不是第一次脱衣,但这却是第一次在两个女人面前,脱去所有杀意,脱去武者的身骨尊严,赤身裸裎,不为欢愉,而为陷阱。
白蝶娘缓步上前,眼神如夜街老娼看肉评价,目光不躲不藏。怜月站在一侧,默然不语,只静静看着。
衣袍一层层剥去。
白衣滑下,露出背脊。
那是一截令人窒息的线条——肩胛锋锐,脊梁挺拔,薄薄肌肤下是刀刃般收束的力量感。她不是风尘女子的柔媚,却是雪山精铁铸出的艳骨。腰身收窄得不可思议,从肩至尾骨一道雪脊,仿佛是为侠而生的身段。
肩胛下,两条手臂纤长坚实,肌肉不多,却在每一个握拳的微动里藏着雷霆。腿部线条更是夺魂——修长紧致,曲线刚柔相济,像是一柄鞘中刃,被欲望抚过也未失锋。
而最令人惊心的,是那双乳。
高挺,雪白,轮廓如月,一如她的人:不似凡俗女子的香艳,却艳得叫人心头泛火,傲得叫人心生亵念。
再往下,是那对艳臀——雪团般饱满,肉色若脂,形如狐尾上翘而紧实。每当她转身微动,那曲线便轻颤如波,既非柔软的风尘肉感,却胜在骨相清贵,叫人一眼便想捧住掰开、在那高傲的姿态里逼她哼叫出声。
股缝间的毛,却干净利落,仅留一缕绒雾轻伏在穴口上方,如春水边草初生,不乱,却勾魂。阴唇浅藏深缝之间,紧抿得像从未张开的花瓣,若非走近细看,几乎辨不清那是女子的秘处,只觉雪色肌理下有一线薄红藏焰。
那穴,紧,冷,却不掩生理上的艳——天生的器,道心未破的贞,却生在这具“不可堕不可辱”的绝色肉身上。
白蝶娘眯眼打量了一圈,这才恍然明白,原来怜月口中那点“心念难抑”,全都系在这副媚肉淫骨之上。她轻笑着吐了口气,舌尖一抿唇角:
“姑娘果真是尤物……可惜了这副皮囊浪费了这么多年。”
霜华未答,只是低头,任衣物褪尽,直至雪肌毕露。
“来吧。”她睫毛垂下,抿了抿唇,冷声却带上一点不易察觉的羞窘,“你不是要捆?”
白蝶娘笑着拍了拍手,命青楼中妓娘送来的道具终于一一陈列于榻前——粗细不一的绳索,红缨、麻绳、玉纽、拘缚环、香粉……一应俱全,琳琅如术。她挑了一条麻绳,手指勾动间,指节翻转如舞,绳子立刻化作盘蛇,柔软却有骨。又从器具盒中捻出一小瓶淡黄色的檀油,在指间搓了搓,故作随意地抹上绳身:
“麻绳太生,若不抹点油,磨起皮来可疼了……奴家可是疼惜姑娘。”
“站直,双手背后,脚跟并立。”她像训奴,语气轻浮。
霜华皱眉,却照做。
白蝶娘站在她身后,麻绳自霜华右肩开始,绕过腋下,穿胸而过,绷得极紧,勒入双乳根部,将那对雪团缓缓挤成两瓣,肉峰微微泛红。霜华轻轻抽气一口,却忍住未作声。
霜华轻轻抽气,身体略微一颤。
白蝶娘嘴角一勾,手指却故意在绳索拉紧时往内错了一寸,那一寸,恰巧按在乳肉最丰腴的下缘,食指稍一抹,便在柔腻间滑了半圈,像是无意,又分明带着一丝恶意的抚搓。
“哎呀,捆错了。”她装作无辜地笑着,“姑娘的这对儿太丰,我手不小心压上了。”
霜华咬唇,未应,耳根却泛红。
白蝶娘继续绕绳,绳绕第二圈,交错于腹部,再缠至腰脊。
绳道刚过脐下,她五指一张,掌心顺势抚过霜华平坦小腹,再故意滑入那片毛绒微卷的耻骨上沿,轻轻一按。
“练家子果然筋肉紧致。肚子这块……啧,摸着都发热。”
霜华指尖微颤,冷道:“……继续。”
“当然继续。”白蝶娘笑得更媚,手指却顺着勒紧的绳缝慢慢向下滑,装作调整角度,食指几乎贴着蜜缝外沿绕了一圈,再“顺手”抚过霜华大腿内侧最敏感之处。
那处肌肤一触即颤,霜华轻“唔”一声,鼻息一紧。
“哟,姑娘怕痒?”她边说边回绕至霜华身后,从臀上绕至尾骨。绳子绕得缓慢,每一下都像轻轻割过肌肤。
白蝶娘手法极熟,绳索贴肉而走,但她的指尖却更放肆了——每缠一圈,都要顺势在霜华臀肉上轻捏一下,揉成团、再放开,让肉抖三下、再紧一下,才肯抽绳固定。
霜华双腿微绷,绳动即肉颤,只能被动承受那羞人的酥麻一搓又一捻。
“你这骨太紧,太挺,便是不像胭脂货。”白蝶娘一边绕绳,一边伸指按了按霜华的肩,“放松点,再紧下去,绳要勒断了。”
“从未有人……这样捆过我。”霜华低声道。
“那就好。初次最香。”白蝶娘笑得更贱了些,“你身子一动,乳都在颤。明儿给你配个铃铛,看你浪不浪。”
霜华眼中冷光一闪,似要回嘴,却因绳索缠至大腿内侧,突觉一阵陌生的撕扯之感,忍不住轻抽了一口气。
白蝶娘察觉那细微喘息,笑着问:“怎么,难受?”
霜华面颊泛红,却不答,仍只道:“继续。”
“你这副‘不服’的劲儿,就该让人多勒几道,勒得你动不得,说不得,才像真被驯。”
白蝶娘终于绕至最关键的一圈——她捧着一条腿抬高,绳索从大腿内侧绕至后臀,指尖蘸油沿着绳道往股缝深处按去,“不小心”抹进臀沟,手势轻柔地“压紧绳道”之名,实则正好一指滑过尾骨与穴口交界。
那一刹——
“……唔啊!……”
霜华一颤,声从喉中漏出,细若蚁吟,像春夜里枝头压断的一声喘。
她立刻咬紧牙关,脸颊刷地泛红,脚趾抓着地板缝死死蜷紧。
她身下早已出汗,那不是羞耻的热,是一种未曾体验过的被动感——明明绳道之间未曾直触肉处,偏偏那细密摩擦将她最私密的一点渴望一点点挑起。
她强忍下异样,只待白蝶娘将最后一圈绳结收紧,打了个缠花扣,退后一步,仔细欣赏眼前“成品”。
那是一具被完美捆缚的女体,挺立而羞涩,肉颤却无法动弹,双乳被交缠的绳结勒出两轮夸张而羞耻的弧度,小腹微收,肋下汗光隐现,脊背笔直却战栗微颤,一道道绳印仿若火痕般贴在雪肤之上。她那双腿虽未被死缚,却被加上了精致的股绳拘束,从腿根穿缠而下,勒入内侧嫩肉,隐隐勾勒出秘处线条。双膝仍能迈步,却被强制保持一种微张姿态,每一步挪动,腿间便传来牵绊摩擦,羞耻无处可避——仿佛一把被拆去刀鞘、断去护手的艳骨之刃,矜傲地站在屠夫案前,正被人选刀宰剖。
“这些绳子…虽捆得难受…但倘若我一发劲……都能崩断。”
“当然。”白蝶娘笑了笑,指尖轻轻弹了弹勒得发红的乳根,“姑娘若真发劲,别说绳,连人都能断。”
她话锋一转,眼波一挑,笑意如钩:“所以啊,要让姑娘这等人服帖,绳只是小术,得另下功夫才是。”
白蝶娘忽地从器具盒中取出一物。
她手中那物,通体暗金,巴掌大小,质地不明,却雕刻得极细。中间是两片狭窄金叶,缀着银扣,形状恰如项圈,最中处凿有一线红晶,微光流转。
“这是……?”霜华眉头一蹙,敏觉如刃。
白蝶娘微笑,语气轻慢中带着一种耐人寻味的炫耀:
“你方才也觉,这些绳子,终归是青楼用物,绑普通娘们儿自然好用,若是对上你这种有内力、有骨劲的‘女侠’——两下便挣脱了。”
她举起那枚项圈,在手指间轻轻转着,红晶泛着微光,像一滴流不尽的血泪。
“可惜人贩子里头,有的是识货的。他们可不是只抓贱女、苦女,他们也贩……‘侠女’。”
她语气忽低,嘴角笑意却扬得比香粉还腻:
“这东西,叫——‘捆仙箍’。戴上之后,一炷香之内,便能封人全身经络,断绝真气运行,强如一品内修,也得像只猫儿一样,瘫着任人拿捏。”
霜华脸色骤变,寒光自眼底透出:“这世间……竟真有如此邪淫之物?”
“怎么会没有?”白蝶娘咯咯一笑,“江南前年就有一位剑门女修,被抓时还劈死了六个活人呢,最后不还是被吊在花楼上头,一日一夜,叫得连观众都起鸡皮疙瘩?”
她眼神带笑,落在霜华颈项间:“所以得用上这等物什,才能让他们信得真、看不穿。”
霜华咬紧后槽牙,身体不动,却心如暴雨翻涌。
让她脱衣可忍,让她受缚可忍,让她羞辱自己也可忍。
唯独这“武功尽失”,是她自十岁起未尝一日的恐惧。
这等于卸了她所有刀锋,砍了她所有脊骨。她将彻底沦为一具裸肉、任人施为,甚至连最后的“拔刀斩物”都做不到。
霜华眸中寒芒爆起,几乎要挣绳出掌:
“你莫想让我戴上这物。”
“当然当然。”白蝶娘举起双手,作出“怕了怕了”的模样,“我哪敢强迫姑娘,万一你真失了功力,叫人趁虚而入、玩了贞身,那可不是奴家担得起的罪,岂不大祸临头?”
“你还知祸?”
“自然知。”
这时,一旁的苏怜月忽然出声,柔柔地拉住白蝶娘衣袖,轻声劝道:
“蝶娘,其实……也不必演得这么真罢?若霜华姐姐不愿,我们也不必强她戴上。”
她声音温软,语调似是体恤,指尖却轻轻拂过霜华手臂上的绳结,像在无意间安抚:“姐姐向来最讨厌这些束缚……若因我而戴上那种……羞辱的器物,我心里也不安。”
她低垂眼睫,咬了咬唇,声音更低一分:
“……倒像是我故意把姐姐往火坑里推。”
白蝶娘侧目看她,神情一顿,忽然一笑:
“小姐果然心善——可惜,越心善,越容易叫人看破。”
“你这护法姐姐若不戴此物,一举一动仍是武人气度,任你装得再惨也没人信她是‘胭脂货’。说不定他们一眼识破,调头就走,到时候这一局——岂不是竹篮打水?”
她顿了顿,眸光一转,笑意更深:
“何况……若真要‘试货’,他们定会先探筋骨、试穴道、听呼吸……练家子的气息是藏不住的。”
“放心,我这物虽凶,却也留了你一线退路。”
她扬起手中“捆仙箍”,指腹轻弹红晶,发出一声清脆轻响。
“你只需,在局中喉咙贴这处机关,唤三声‘苏怜月’,它便自动解落。但只有一次机会。”
“脱了之后,再戴不上。”
“所以要慎用,用早了没用,用迟了被干,那就真做了场‘青楼烈艳’。”
霜华死死盯着那枚项圈,喉头微动,掌心已沁出冷汗。那不是怕痛、怕辱,而是一种更深的直觉——作为武人,她的血与骨都在抗拒那种“任人拿捏”的可能。
她从来都是护人的——不是被人保护的。
可此刻,她却要亲手缴出最后的力。
那一瞬,她几乎开口要拒,却在抬眸的刹那,看见怜月那双眼——澄澈如溪,不染尘土,正仰望着她,像小时候一样,那种“姐姐无所不能”的目光,没有变。
苏怜月忽然上前一步,轻轻握住她的手,语声软得像吹落的灯火:
“其实……就算失了武功,我也不信姐姐就会输。”
她抿了抿唇,像是在极力掩饰某种惧意,语气却越发柔软,带着一点迟疑,一点信任,一点若有若无的撒娇:
“从小到大,姐姐就是我心里最强的……就连梦里,都是你护着我。”
她说着,微微垂下眼,仿佛怕她生气,又似乎怕自己说得太多,手却悄悄攥紧了她的手腕。
“……若是连你也不能胜他们,那我……”
她像是害怕被霜华误会,语尾收得很轻,手却握得更紧。
那一刻,霜华心口忽然一痛——不是被打穿的那种,是那种被人一针一线缝住的窒息感。
那眼神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是从五年前就从未变过,像是那个夜里失声痛哭的小姑娘,仍站在原地,用那种“姐姐什么都能做到”的眼神仰望着她。
她可以败,她可以堕,她甚至可以被人调教、被人玩弄、被捆在床上羞辱……
但唯独不能,让怜月失望。
片刻后,她闭上眼。
“戴吧。”
她声音轻得仿佛一片灰,落在这密室的檀香中,却砸得比刀剑还重。
霜华缓缓伸出脖颈,将自己送到那枚项圈之前。
白蝶娘笑意荡开,像春水拨动锁般,将“捆仙箍”环于她雪白的颈项。金叶贴肤,红晶嵌喉,发出一声轻不可闻的“嗡”。
而苏怜月站在她身后,静静看着她脖颈上那一抹铜环扣紧,手指在袖中慢慢合拢,眼神恍若春水映月——波平浪不止。
初时无感,仿佛只是一件冰凉的饰物。
但数息之后——她心口的气,开始散了。
是的——不是不动,是散了,像被人掀开丹田之门,一缕缕真气由内而外飘逸而出,无声无息,不带一丝痛感,却让她全身如泄水之瓮。
她骤然一震,尝试运劲,双腿紧绷——绳索应声紧勒,却未换来熟悉的力道支撑。
她再试调气,真元不起。
“……这东西……居然……真的……”
霜华咬牙,忍不住扭身,试图扯断一绳,脚尖一挑,气沉丹田——然而丹田像是被掏空,脚下一滑,竟险些踉跄。
霜华喘息渐重,每一口气都仿佛比上一口更浅,更虚。她手臂轻颤,汗水从脊背滑落,胸脯因呼吸微喘而一颤一颤,那被绳勒得胀起的雪肉轻轻晃动,竟多了几分淫靡之感,仿佛此刻的她不再属于杀伐,而是属于床榻与喘息。
她死死咬住牙关,咒骂一般吐出一句:“你们这些青楼人贩子……下流玩意可真不……”
话未说完,忽然一物突兀塞入唇中,霜华瞳孔骤缩,惊愕中竟连唾沫都未及吞咽。
“既然你是真‘货’,那这两样也不能少。”
白蝶娘笑吟吟地将指间那枚红缨软布口衔缓缓推进,像是往一匹即将开笼的烈马口中塞上嚼环,手法不紧不慢,却准得令人发指。
“这口衔是皮中嵌铅,能压舌、驯音、软咽。”她边说边捻住霜华的下颌,拇指抵住她下唇,轻轻一掰,牙关便被撬开,“姑娘你是练家子,骂人那几句话说得太溜。现在乖一点,我不想听。”
霜华“唔”了一声,口腔被硬塞撑开,舌被顶得发麻,下颚被迫后抬,那一抹湿软红嫩暴露在空气里,发出细碎、无力、羞人的呻吟。她羞愤想偏过头去,肩膀才一动,束胸缠腹的绳道立刻收紧,将两团雪乳死死勒住,连乳尖都涨得发红颤动,挣得越狠、露得越多。
“别乱动,再动绳子都勒进奶心里了。”白蝶娘眯起眼笑,语气像是驯犬女匠,“我说过,你这身骨不驯,得慢慢压。”
霜华不敢再挣,却仍睁着眼怒视,眸中冷意如钩。白蝶娘却不急,取过一条黑绫眼罩,在她眼前晃了晃,轻声道:
“还有姑娘眼神太烈,我看着都怕。”
她话虽玩笑,却毫不迟疑地抬手将黑绫从霜华耳后绕过,遮住她目光,那两只冷若冰锋的眼,在一瞬间被遮去光亮,只余鼻尖微喘与唇角的细颤喘息。
“这等杀气搁脸上,别说上钩了,怕是鱼都不敢靠近半分。还是遮一遮,省得杀气太盛,把人吓跑。”
紧接着,一张雪白面巾包裹了她半张脸,只露出羞红耳根与微颤的鼻尖。眼不能视,口不能言,气不能凝,力不能聚。
束缚、封穴、驯舌、断视。
她彻底被困。
白蝶娘轻哼一声,从器具盒中取出最后一物——一根赤红缀尾、银链为舌的牵引链。
她将它扣在项圈侧的银环,链尾垂落,落地一声清响——叮哐,宛如刀剑折服的哀鸣,也像傲骨崩断的回响。
“好了。”
她退后一步,慢慢端详。
那一刻,苏怜月也终于走上前来。
两个女人一左一右,看着这座曾经是剑气凌霄、目下无人的江南女侠,终于彻底‘伪装’成一件货色。
她跪坐于密室正中,手反缚于背,雪肤遍覆细绳,胸脯被勒成两团涨润艳肉,微喘之间不住轻颤;口中衔着红衔,唇角有唾光微溢,半张面庞被白巾包裹,只露出潮红的鼻尖与呼吸起伏的锁骨;眼被黑布遮蔽,看不见任何事物,神情无措,气若游丝,连头颈都因项圈的压迫而轻轻下垂。
她身上早已出汗,雪背上有晶莹汗珠顺绳而落,沿脊而下流入尾骨凹陷,又被勒臀之绳引流至股缝深处。阴阜处的绳索也早已被蜜水打湿,每当她在无声中微微挣动,那处绳缝便摩擦得牵动下体颤鸣,肉缝微启,黏腻香液悄然溢出,被腿根绷带细细拖拉出一道光亮的痕。
鼻尖呼吸已不匀,短促得像是隐隐喘息,唇齿深处时不时溢出低不可闻的“呜……唔……”之声,既羞且软,似恳求又似渴求。
项圈之上悬着银链,坠至地面,仿佛她已被某个“主人”拴好,只待人牵走,送入妓门。
她,已不是霜华。
她是“苏怜月”——被仇家擒获、被捆至失力、等候调教的胭脂肉奴。
夜未央,月将沉。
苏家堡的围墙在月下如兽伏影,沉默不语。四周巡夜的火把已经熄了一茬又一茬,换岗未至,藏匿在暗中的黑影,悄然游蛇般滑入了沉睡的院落。
“东南角已清,五人。”
“西北侧尚有灯火,无妨,避开即可。”
几名黑衣人身法古怪,低语如蚊,不循武林常式,偏偏动作极利落,仿佛关节能随意折叠,行走间无声无息如蠕虫潜沙。他们趁夜色逼近内宅,每一步都踩在瓦梁间隙上,避过所有机关与响木,如幽魂夜渡,只为一人——
苏怜月。
一柄细匕滑出鞘,弯若蛇信,薄得几不可见。一名黑衣人贴身潜近,俯瞰榻边熟睡的小丫鬟,眼神冷淡得如看一抹尘埃,却不带丝毫杀意。他手腕一抖,袖中滑出玉针般的银叶,轻点其颈后麻穴,少女便眉心一蹙,沉入更深梦境,连哼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另一人早已贴墙滑行,一指探出,拂过守卫脖颈。指尖露出的细管中喷出一缕无色烟气,幽冷入骨。那侍卫面色一怔,手中刀才举到半空,便软软垂落,歪倒在地,尚未清醒,已坠眠深渊,气息沉稳如婴。
夜色悄无声息地吞噬一切动静,未曾惊扰星月。
唯一一处意外,是侧门之守。那人血气方刚、筋骨强悍,竟在中毒后挣扎踉跄两步,嘴唇微启,一点气音已欲呼喊,却忽被一掌贴面封喉,咽息中断,只余唇齿张阖,神情僵滞,声音终未破夜。他眼神怔然,倒地之际被接住轻放,连盔甲都未碰响半寸。
十余息后,整个内宅早被他们悄然封锁,连猫狗都不曾惊动,唯有暗处灯影忽明忽灭,仿佛随呼吸跳动。
“呀啊!!!——”
忽有女子尖叫,刺破夜色,如银针刺破水面,带着惊恐又隐忍的裂音,从寝阁深处骤然传出。
“怜月!”
寝阁内,凌霜华的眼在一瞬睁开,眸中冰光炸裂,竟比夜更冷。她恍然间是五年前苏家堡东厢庭院,苏无恨躺在血泊中,左臂已断,身上插着三箭,鲜血漫出薄衫。
她不愿再看一次。
衣衫未整,霜华已夺门而出,素衣未掩美骨,冷刃已出鞘三分。她身影掠至院中,月下如电掠霜,青丝飞散,冷艳到极致,也媚得摄人心魄。
一名刺客方才穿身而过,尚未落地,便被她一刀横斩,血花喷洒,落在她纤腰与侧乳之间。
她甚至未看他一眼。
“擒苏家千金!”
有人喊。
下一瞬,霜华已如魅影杀至,刀光未动,气势先撼心魂。
她那身素袍贴肉而薄,每一次横斩、旋步、掠影如燕,都牵动着胸前微颤欲脱的曲线,雪乳若隐若现,仿佛勾人心魄的梦魇。然而她的神色却冷得逼霜,每一刀都似要断人生机。
“天生媚骨……却是刀下不留情的妖孽……”
刺客失神一瞬,霜华已欺身而近,右手翻腕,一记斜劈斩颈,力贯三分,血箭喷出。
第二人怒吼扑来,她刀尖上挑,将对方手中钢刀弹飞,左手五指如钩,反扣其衣襟下摆,猛地一拽——纤指探肉,力道精准,喉骨“咔”的一声断裂,宛如山雀骨折。
他未及惨叫,霜华已半身贴近,顺势一刀反撩,从大腿内侧斜斩而上,直断要脉,血溅如雨,染红她半条素腿。她连眉头都未皱一下,眼神反而更冷,仿佛杀人只是一次缓慢的吐气。
杀意入骨,媚意入骨。
这一身不该杀人的香肌玉骨,一颤一动都如勾魂摄魄的舞伎,可她偏偏每一式每一招皆为杀招,收势如疾风骤雨,落点如死神点穴。
她那刀——不是削铁如泥,而是绕身三尺如蛇缠骨,游龙般探向敌喉,每一次挥舞,都似吻喉之刃,实则断命之器;那身形——不是舞者,而是苍狼扑野,身姿旋舞间,血已四溅。
数名刺客已心神俱裂,接连倒退,口吐血沫。
“姐姐!救我——”
内堂深处,忽传来苏怜月一声惊叫,声音细弱如丝,软腻如梦,仿佛一缕残香惊魂未定,似真似假,却挑得霜华心头猛然一紧。
她足下一旋,倏然破窗而入,刀气一振,便劈断梁柱,碎木横飞,将一人撞得半张脸塌陷,滚地不起。
霜华身法低伏如燕掠地,刀鞘扫火,将案前烛火尽数乱卷,也将她那张染血冷绝的面孔映得如魅如神。
只见那名刺客早已将苏怜月挟持在前,匕首抵在她纤颈,笑意冰冷:“你敢近一步,我就——”
话未出口,霜华早已如箭脱弦,手中长刀倒转而握,脚下一踢,踢翻侧柱灯。
火影摇曳间,她刀影如游蛇穿案,从桌底反斩而起,一记螺旋斩击打落匕首,寒芒乍现!
“呃啊——!”
那人肩头迸血,踉跄退后。霜华不给喘息之机,左肩一旋,刀随势回,半月斩猛然贴胸而落,重重斩在他心窝。
“咚!”他身形一震,吐出大口鲜血,颓然倒地,不省人事。
苏怜月跌入她怀中,身香如兰,轻颤如雀。她整个人像是软成了一团香脂,嵌进霜华的胸前,唇边带着未褪的余惊。
“你没事吧。”霜华声音低哑,刀尖滴血未收,怀里却抱得极轻极稳,如捧珠玉。
“……姐姐,”苏怜月微抬螓首,眸角犹挂泪痕,指尖却缓缓搭上霜华那把染血尚温的大刀,轻声呢喃,“留他一命……”
霜华眉心微蹙,冷光未敛,仿佛那杀意未曾散去。血从断木横梁间淌出,流过阶砖,蜿蜒涌至霜华脚边,将她白靴底缘染上一抹刺眼深红。她不动,影子立于血泊中,仿佛一尊不容忤逆的阎罗女。
“让他说出……他的主子是谁……为何要行刺。”
她沉默了两息,刀身微倾,终还是**将刀收回半寸,重刀挽手反握,刀背贴臂,杀意却未散半分。目光冰寒如初,转头望向那尚存一息的黑衣刺客。
“说出你主子是谁,我让你死得痛快些。”
那名刺客被她一刀刺入肋下,此刻正瘫倒于地,血如涌泉,自伤口溢出,混着碎裂骨骼的呻吟抽搐不已。他面色青白,嘴角泛血,只余一口吊命的残息。
“说。”她冷冷吐出一字,声如雪夜凛风,“谁指使你们。”
刺客张口咳血,半边脸贴在血污中,嗓音嘶哑:“是……是当年……那批人……他们没死……”
“什么人。”
“……五年前……杀苏无恨……的那些……”
空气瞬间沉重。
霜华指尖微颤,刀口却没有一丝放松,更刺入他皮肉一分,血丝顺着喉口蜿蜒淌下,触目惊心。
“他们听说……”那刺客唇角扯出一抹狞笑,嘴角涎血滴落,喘息间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兴奋,“苏无恨……还有个女儿,藏在堡里头……模样还俊得很……啧,长身玉立,冷得像冰雕,可要是脱了衣裳绑在床上,叫她学狗学猫地叫,岂不比什么花魁还招人疼……”
他咳着血,却仍笑得淫亵,“几个兄弟说了,要抓了她……剃发换红裳……塞进青楼好好调教成一尊淫娃……日夜轮翻,把她骨头肏软,把苏家的脸,肏进泥里……让那老头子死都死不瞑目,死了都得听她浪叫——咳……咳咳——”
霜华眼眸骤然一缩,杀意如潮天崩地裂。她那一双本冷若霜池的眼眸,瞬间灼烧成地狱修罗,指中长刀一抖,刀尖斜指咽喉,寒光流泻如怒蛇蜿蜒。
“敢辱她,你们该——”
“姐姐!”
苏怜月突然开口,声音轻柔,却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道,握住她执刃的手腕。
霜华偏头,眸光仍燃着杀意:“你可知他们要做什么?”
“当然知道。”她垂眸,睫羽掩住情绪,声音却稳,“正因为指导,我们才不能现在杀他。”
霜华眉头紧锁,长刀微微一顿:“你想从他嘴里挖出更多?”
“若不查根究底,这样的人,杀一个还有下一个。”怜月语调冷静,双手交叠于身前,神态仍是那副胆怯惊魂未定的模样,可那份镇定却诡异得令人心惊。
“今日能刺入府中,明日就能潜入花阁,若不拔出根来,防也防不住。”
霜华没有言语,杀意如旧,却微微敛了三分。
“继续说。”怜月低头望向刺客,语气温和,却字字钉骨,“若你再敢含糊,就别怪霜姐姐的刀把你骨头一寸寸剔出来。”
刺客身子一抖,拼着气息断续道:
“我们……我们接到指令……若得手……就送人去……‘听香水榭’……”
霜华眉头皱起,低声:“何处?”
“江南城东南角……青楼酒肆汇聚之地……那家香榭是……是专做贵人交易的地方……我们只管送人,交给那里的‘白蝶娘’接手……”
霜华喃喃复诵:“白蝶娘……谁是白蝶娘?”
刺客摇头如捣蒜,语气愈发虚弱:“是那边的主事……我们从不过问她底细……任务完成便算数……再查……会死的……”
霜华目光如刃,望着地上那人半死不活,锋刃不动,却已悄然将劲势聚至足下,随时可收其性命。
“姐姐。”苏怜月轻声唤她,伸手轻抚她肩胛,“他活不了多久了,何必让他死得痛快?”
她转身,长发拂肩而落,步伐冷定,但心头却是惊疑不定——她从未听过“听香水榭”的名,更不识“白蝶娘”,而这家青楼能与刺杀苏无恨的余孽牵上线,背后岂止是风月之地那般简单?
她垂眸沉思半晌,终是压下满腔杀意,决定先顺怜月意行事,暗查此榭根脚。
“绑了他。”她收刀入鞘,沉声道,“等他再咽几口气,就给我吐干净他知道的每一个人名。”
翌日清晨,雾色未散,晨钟尚未响彻城头,苏家堡便已出动。
三十余名亲卫披甲而行,自府门而出,直奔江南城南角,那里灯红酒绿,风月之地林立,而最中央一栋朱漆香榭,三层飞檐,红绡环绕,正是昨夜拿刺客口中的——“听香水榭”。
世人只道那是权贵放纵、佳人如云之地,岂知此地背后竟牵连着五年前的血仇残党、苏家千金遇刺之局?
“搜!听香水榭全楼,鸡犬不留!”
苏家亲卫踏入香榭之内,甲靴碾红毯,刀戈亮寒光,香粉气顷刻被肃杀气吞没。白蝶娘还未来得及从榻上起身,便已被擒下,慌不择衣,只着一袭轻纱睡袍,半裹半露,妆未卸完,香气犹存,神色却慌乱如斗败花妖。
她满身粉脂香汗,被反绑双臂押上马车时还不停辩解:“冤枉、冤枉啊!奴家只是个开楼的……何曾掺和江湖仇怨……”
入了苏府,带到堂前,她被一把推至红毯之上,跪得狼狈。霜华负手而立,目中寒芒如霜刃冰针,苏怜月则侧坐于榻,眼波浮动,似笑非笑,唇边一痣红艳如血。
“就是你受命接收苏家小姐?”霜华站在她面前,眼中已凝杀意,“你可知她是谁?”
“奴家、奴家哪知道啊!”白蝶娘脸色煞白,“那边人出的是重金,说要找个懂调教的青楼来收个女货,说是……说是要把她养成能让狗都发情的尤物……奴婢贱命一条,也只想着赚钱养楼,哪知道她是苏家千金啊?要是早知道…就是给奴十座香楼,都不敢沾啊!”
她哭得衣袍滑落一肩,露出青白锁骨,脸颊涕泪交融,惨白得几乎不像活人。
霜华冷哼:“这等败类,留你何用!”拔刀三寸,寒芒已出鞘。
“我有办法!”白蝶娘突地惊叫,面色骤变,几乎跪着往前扑,挣断绳索的皮带咯吱作响,“他们这事才刚起头,我知道他们还藏着更深的人!联系奴家的那个中人……下个月还要来香榭!你们想查,就得引出更大的头目……奴……奴家可以帮你们引蛇出洞!只要你们……只要你们别杀我。”
刀光凝滞,霜华低声道:“说。”
白蝶娘却左右环顾,神色惊惶欲绝,声音颤着发出:“这话……在这儿……说不得。墙有耳,院有眼。奴只收钱行事,真正的买主是何人、藏身何处,若叫他们知我露了口风,只怕香榭上下都得陪着小女陪葬……”
霜华目光更冷:“你在卖弄玄机?”
“姐姐。”一旁苏怜月轻声开口,语气却柔得似江南春水,缓缓绵绵,偏又带着一缕惹人怜意的娇气,“她这般模样,倒也未必尽是虚言。听她一听……也无妨。”
霜华眉未动,怜月已垂眸上前半步,声音轻得仿佛怕惊着什么:“若她真有法子,自可引出余孽;若是唬我等,那时再斩也不迟……”
“好姐姐,依我一回罢。”
霜华沉吟片刻,终是冷冷一收刀:“随我来。”
三人穿过垂花门、绕过月影廊,直至后园最深处一处偏院。那院名唤“秋静”,昔年曾为苏怜月学艺时所设清修之所,院中无酒无欢,无琴无伎,唯植竹数竿,绕廊一方,供她静坐练气、课诵藏经。自她成年后便久未再启,屋门尘封,帘角落蛛网,隐有余香犹在。
此刻院门一开,浮尘翻舞,竹影斜照地砖,竟似尘世之外。
霜华目光一扫四方,亲自遣散院内旧婢,命其不得入内;更提声传令,将外屋左右侍卫悉数退去,五丈之内,不许有半人靠近。
厅中旧榻上香炉微熏,香气若有若无,带一丝凉意;屋外只闻风动竹声,沙沙如水,天地寂然。
“说吧。”霜华站于窗前,冷背迎人,眸色沉沉。
白蝶娘此刻已被换上清衣,双手搓得发红,小心翼翼地坐在屋内绣凳上,望着两位女子,一位若霜若刃,一位若水若狐,眼中藏着贪婪又隐秘的火焰。
“其实……”她一字一顿,嗓音变低,“想引出那些人……小姐必须亲自……演一场。”
霜华眉头微动。
苏怜月轻轻歪头,似笑非笑:“哦?演什么?”
白蝶娘露出一个仿佛羞赧的微笑,像是妓馆初夜时不敢抬眼的新人:“演……一个被卖入青楼的贵人胭脂货……诱得他们现身,以真钩钓鱼,引鬼上钩……”
她微笑着摊开双手,指节瘦长如枯枝,却像蛇蜕一般灵活:“只需放出风声,说我听香水榭最近收到一批贵人血脉,精挑细选、专供重口,藏在南院密榻,便可将他们勾出暗巢。那帮畜生若知道‘苏无恨之女’已落青楼之手,必然按捺不住。”
霜华眉头如刀锋,寒声割出:“你说……要让怜月,做青楼妓货?”
白蝶娘微微垂首,语气带着一丝刻意营造的“羞耻”和“无奈”:“非是奴家有意亵渎小姐,只是……对方只知‘苏无恨有一女’,却不识模样,若无‘实货’可看、可玩,便断然不会现身。”
“你——恬不知耻!”
霜华怒喝,杀意未出,已震得桌角花瓶微颤,香炉翻滚出几缕灰烬。她一步逼近,冷目如雪盯向白蝶娘,眼中杀意如黑潮压顶。
“休再妄言一字,我宁愿将那群狗贼逐个剐皮,也不会让她堕这污泥!”
“姐姐。”
怜月轻声开口,语调平静得近乎冰冷,像一池被夜色封住的月水。
霜华转头,看见她缓缓起身,双手交叠于前,目光坚定如初雪之刃。
“这是我的仇。我父亲的血,滴在你我之间五年,不能永远由你一个人背着。”
“自从那年……自从我爹爹倒在血泊里,死在那些人的刀下,我就从来没一日睡得安稳过。”
“我日日想着,若有一日能把他们挖出来、一个一个剜心刮骨,才能告慰他在天之灵。”
“可现在——他们不仅没死,还想着继续害我。”
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些,却冷得令人发寒:“若这仇不报,我有什么脸,再去九泉之下见我爹?”
“我愿意。”她走上前来,面对蝶娘,盈盈一礼,声音中带着说不出的凛冽之气,“为报仇雪恨,哪怕失去清白、堕入泥淖,又有何惧?”
霜华呼吸一顿。
那一刻,她几乎看见苏无恨的影子重叠在这少女背后。那双眉眼那么像,那句“为仇赴死”也几乎是他曾说过的话。
可她分明记得,那人临终前只说了一句:“照顾她。”
护她一生,护她清白,护她不入江湖,不踏血河。她怎能……
她自问不是个多情人,刀下亡魂无数,冷情冷命,纵有爱人清音,也只敢在夜里轻唤几声,从不曾奢念长久温存。她杀得多了,心早已被铁血浸透,早就明白情之一字,于她不过是命外浮萍。
可她从来不悔,因为她是凌霜华,是苏无恨亲选的托孤人,是为苏家持刀之人。
但现在,她站在命运之门前,听见那个五年前还娇怯藏在她怀里哭泣的小女孩,要以血肉之躯为诱饵入局,以清白与尊严,做一场青楼诱狐的“活香饵”。
她能斩千人,却唯独斩不下这一个。
她喉间如被火灼,眼底有潮水在翻,可她只是闭上了眼。
苏无恨的声音在她耳中响起:“你要护她,护她远离江湖,护她远离我这条血路。”
他临死那夜,断骨撑地,血泪涌眼,死也不肯闭眼,只怕她守不住这个女儿。她应下了,在他断气前那最后一刻。
五年,她未曾违背——
但她知道,若再犹豫一步,她便将亲眼看着怜月走入青楼,被群狼环伺、化作一具任人羞辱的“肉货”。
霜华猛地睁眼,目光已不似之前那样清冷,而像一道倏然下坠的瀑火,燃着绝意与孤勇。
“够了。”霜华声音微哑,却骤然斩断一切,“此事……由我来。”
怜月眼底似有一丝光轻轻一跳,像深水中一抹久藏的喜意终于泛起波纹——
只是刹那,她便已敛下眼睫,将那点欣悦压进唇角柔意中,语气依旧温婉乖顺:“姐姐,你——”
“别再说了。”
霜华转头,盯着她,一字一顿,仿佛咬断了她一生的矜持:“你不能去,我不会让你去。你若跳进去了,我这五年守着你、护着你、杀人、负命……便全成了笑话。”
霜华转身面对白蝶娘,双目如冰针,话语却重如寒铁:“你不是说他们不识小姐的真面目?只认身份只认传言?那便由我来假作她。”
白蝶娘愣了半瞬,眼底迅速掠过一抹光亮,却故作惶然:“霜华姑娘您……您怎可如此?万一身份暴露,那可……”
“我武功在身,自能自保。”霜华冷冷道,“且他们若真是余孽,必然先试货,试过之后才交人,自有空隙可布防设计。你只需按你所说布局,其他不用你管。”
她顿了顿,又道:“他们只知苏无恨有女,却不知究竟几位。我亦是义女,名分在身,身份足矣。”
“可……可是……”
“够了!”她一喝打断,又冷冷盯住白蝶娘,“你若再推诿半句,我便将你舌头割下,看你还能说多少花话!”
白蝶娘俯身连连点头,做出一副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模样:“不敢,不敢!我只是担心……姑娘身份贵重……唉,这法子原是为小姐设计的,如今变通……也…也未尝不可。”
她眼角余光一闪,看向站在一旁的苏怜月:“何况姑娘气质冷艳,一身媚骨更是人间罕有,那些人不识真身,只怕更信这‘极品胭脂货’非她莫属。”
霜华面色一沉,冷冷一瞥。
而怜月——唇角仍是那抹温顺笑意,只是那眼中,有一丝细不可察的亮光微微绽开,像花蕾悄悄舒展。
“姐姐……”她轻轻唤了一声,语气里含着怯意与柔情,双手缓缓覆上霜华的手腕,语调如初春细雨,“你为我挡了太多,如今却要我眼睁睁看你涉险……我怎舍得呢?”
她话未说完便低垂眉眼,轻轻咬了咬唇,嗓音细若蚕丝,却带着一丝注定劝不动的无力:“可我知道,姐姐你既然已决意一试,我拦也拦不住……”
她抬眸望向霜华,眼圈微红,泫然欲泣,却强忍着未落一滴:“那……我便听你的。只是怜月无以为报,唯有来生再做牛做马……”
语罢,她低低福了一礼,声音几不可闻:“……也许今生,也做得起。”
霜华指节微颤,终究没有挣开她的手。
白蝶娘在一旁拱手:“既如此,奴家便按霜姑娘之貌、之骨、之姿,为她设局一场。要做出一个‘能叫江南百妓自惭形秽’的极品尤物来,引那群狗贼自投罗网。”
“只求姑娘……能扛得住那些人‘调教试货’的手段。”
话语如蜜滴在刀锋上,甜得腥凉。
霜华沉默半息,终于闭目,缓缓吐出一句:
“我扛得住。”
“姑娘这份胆识,奴家佩服得紧,便依你意思,奴这就着手筹备。”
屋外仍是沉静。夜未阑,风过竹影微颤。那是一种蓄势的沉寂,像战鼓落下前的最后一声吸气。
密室之中,三人尚未踏出一步,窗帘低垂,炉香袅袅,灰白的烟打在屋梁上,像风月未醒的眼角纹。仆人已被遣去准备“入局之器”,白蝶娘所需之物一应俱全,尽由信任之人暗中送至。除他们三人,府内再无人知晓这场“引蛇出洞”的谋局。
白蝶娘与苏怜月换上了从刺客身上扒下的夜行衣。黑衣贴身,窄袖紧裹,宽腰束带,细节一丝不苟,连血迹都用颜料精心补涂,乍一看去,与那夜屠堡刺客无异。白蝶娘嘻笑着翻转匕首,在怜月身边转来转去:
“呵,小小姐穿这身杀气腾腾的,竟也有几分妖媚。”
怜月转头一笑,眸中清冷如冰镜:“你不也穿得像只狼婆?再油腻些,我就信了你是头领。”
白蝶娘“啧”了一声,没再回嘴,转向屋中那一人——
凌霜华,仍跪坐于火炉前,背对众人,未言未动。那一袭素白中衣已解去外袍,鬓发微湿,似是洗过热水,肌肤在烛光下泛着幽冷的光泽。
“该开始了。”白蝶娘说得平静,语气却带笑,“姑娘,要入这一局,可得把皮先剥了才行。”
霜华没有转身。她将手搭上衣带,微一用力,袍带滑落,带起一声轻响。
她不是第一次脱衣,但这却是第一次在两个女人面前,脱去所有杀意,脱去武者的身骨尊严,赤身裸裎,不为欢愉,而为陷阱。
白蝶娘缓步上前,眼神如夜街老娼看肉评价,目光不躲不藏。怜月站在一侧,默然不语,只静静看着。
衣袍一层层剥去。
白衣滑下,露出背脊。
那是一截令人窒息的线条——肩胛锋锐,脊梁挺拔,薄薄肌肤下是刀刃般收束的力量感。她不是风尘女子的柔媚,却是雪山精铁铸出的艳骨。腰身收窄得不可思议,从肩至尾骨一道雪脊,仿佛是为侠而生的身段。
肩胛下,两条手臂纤长坚实,肌肉不多,却在每一个握拳的微动里藏着雷霆。腿部线条更是夺魂——修长紧致,曲线刚柔相济,像是一柄鞘中刃,被欲望抚过也未失锋。
而最令人惊心的,是那双乳。
高挺,雪白,轮廓如月,一如她的人:不似凡俗女子的香艳,却艳得叫人心头泛火,傲得叫人心生亵念。
再往下,是那对艳臀——雪团般饱满,肉色若脂,形如狐尾上翘而紧实。每当她转身微动,那曲线便轻颤如波,既非柔软的风尘肉感,却胜在骨相清贵,叫人一眼便想捧住掰开、在那高傲的姿态里逼她哼叫出声。
股缝间的毛,却干净利落,仅留一缕绒雾轻伏在穴口上方,如春水边草初生,不乱,却勾魂。阴唇浅藏深缝之间,紧抿得像从未张开的花瓣,若非走近细看,几乎辨不清那是女子的秘处,只觉雪色肌理下有一线薄红藏焰。
那穴,紧,冷,却不掩生理上的艳——天生的器,道心未破的贞,却生在这具“不可堕不可辱”的绝色肉身上。
白蝶娘眯眼打量了一圈,这才恍然明白,原来怜月口中那点“心念难抑”,全都系在这副媚肉淫骨之上。她轻笑着吐了口气,舌尖一抿唇角:
“姑娘果真是尤物……可惜了这副皮囊浪费了这么多年。”
霜华未答,只是低头,任衣物褪尽,直至雪肌毕露。
“来吧。”她睫毛垂下,抿了抿唇,冷声却带上一点不易察觉的羞窘,“你不是要捆?”
白蝶娘笑着拍了拍手,命青楼中妓娘送来的道具终于一一陈列于榻前——粗细不一的绳索,红缨、麻绳、玉纽、拘缚环、香粉……一应俱全,琳琅如术。她挑了一条麻绳,手指勾动间,指节翻转如舞,绳子立刻化作盘蛇,柔软却有骨。又从器具盒中捻出一小瓶淡黄色的檀油,在指间搓了搓,故作随意地抹上绳身:
“麻绳太生,若不抹点油,磨起皮来可疼了……奴家可是疼惜姑娘。”
“站直,双手背后,脚跟并立。”她像训奴,语气轻浮。
霜华皱眉,却照做。
白蝶娘站在她身后,麻绳自霜华右肩开始,绕过腋下,穿胸而过,绷得极紧,勒入双乳根部,将那对雪团缓缓挤成两瓣,肉峰微微泛红。霜华轻轻抽气一口,却忍住未作声。
霜华轻轻抽气,身体略微一颤。
白蝶娘嘴角一勾,手指却故意在绳索拉紧时往内错了一寸,那一寸,恰巧按在乳肉最丰腴的下缘,食指稍一抹,便在柔腻间滑了半圈,像是无意,又分明带着一丝恶意的抚搓。
“哎呀,捆错了。”她装作无辜地笑着,“姑娘的这对儿太丰,我手不小心压上了。”
霜华咬唇,未应,耳根却泛红。
白蝶娘继续绕绳,绳绕第二圈,交错于腹部,再缠至腰脊。
绳道刚过脐下,她五指一张,掌心顺势抚过霜华平坦小腹,再故意滑入那片毛绒微卷的耻骨上沿,轻轻一按。
“练家子果然筋肉紧致。肚子这块……啧,摸着都发热。”
霜华指尖微颤,冷道:“……继续。”
“当然继续。”白蝶娘笑得更媚,手指却顺着勒紧的绳缝慢慢向下滑,装作调整角度,食指几乎贴着蜜缝外沿绕了一圈,再“顺手”抚过霜华大腿内侧最敏感之处。
那处肌肤一触即颤,霜华轻“唔”一声,鼻息一紧。
“哟,姑娘怕痒?”她边说边回绕至霜华身后,从臀上绕至尾骨。绳子绕得缓慢,每一下都像轻轻割过肌肤。
白蝶娘手法极熟,绳索贴肉而走,但她的指尖却更放肆了——每缠一圈,都要顺势在霜华臀肉上轻捏一下,揉成团、再放开,让肉抖三下、再紧一下,才肯抽绳固定。
霜华双腿微绷,绳动即肉颤,只能被动承受那羞人的酥麻一搓又一捻。
“你这骨太紧,太挺,便是不像胭脂货。”白蝶娘一边绕绳,一边伸指按了按霜华的肩,“放松点,再紧下去,绳要勒断了。”
“从未有人……这样捆过我。”霜华低声道。
“那就好。初次最香。”白蝶娘笑得更贱了些,“你身子一动,乳都在颤。明儿给你配个铃铛,看你浪不浪。”
霜华眼中冷光一闪,似要回嘴,却因绳索缠至大腿内侧,突觉一阵陌生的撕扯之感,忍不住轻抽了一口气。
白蝶娘察觉那细微喘息,笑着问:“怎么,难受?”
霜华面颊泛红,却不答,仍只道:“继续。”
“你这副‘不服’的劲儿,就该让人多勒几道,勒得你动不得,说不得,才像真被驯。”
白蝶娘终于绕至最关键的一圈——她捧着一条腿抬高,绳索从大腿内侧绕至后臀,指尖蘸油沿着绳道往股缝深处按去,“不小心”抹进臀沟,手势轻柔地“压紧绳道”之名,实则正好一指滑过尾骨与穴口交界。
那一刹——
“……唔啊!……”
霜华一颤,声从喉中漏出,细若蚁吟,像春夜里枝头压断的一声喘。
她立刻咬紧牙关,脸颊刷地泛红,脚趾抓着地板缝死死蜷紧。
她身下早已出汗,那不是羞耻的热,是一种未曾体验过的被动感——明明绳道之间未曾直触肉处,偏偏那细密摩擦将她最私密的一点渴望一点点挑起。
她强忍下异样,只待白蝶娘将最后一圈绳结收紧,打了个缠花扣,退后一步,仔细欣赏眼前“成品”。
那是一具被完美捆缚的女体,挺立而羞涩,肉颤却无法动弹,双乳被交缠的绳结勒出两轮夸张而羞耻的弧度,小腹微收,肋下汗光隐现,脊背笔直却战栗微颤,一道道绳印仿若火痕般贴在雪肤之上。她那双腿虽未被死缚,却被加上了精致的股绳拘束,从腿根穿缠而下,勒入内侧嫩肉,隐隐勾勒出秘处线条。双膝仍能迈步,却被强制保持一种微张姿态,每一步挪动,腿间便传来牵绊摩擦,羞耻无处可避——仿佛一把被拆去刀鞘、断去护手的艳骨之刃,矜傲地站在屠夫案前,正被人选刀宰剖。
“这些绳子…虽捆得难受…但倘若我一发劲……都能崩断。”
“当然。”白蝶娘笑了笑,指尖轻轻弹了弹勒得发红的乳根,“姑娘若真发劲,别说绳,连人都能断。”
她话锋一转,眼波一挑,笑意如钩:“所以啊,要让姑娘这等人服帖,绳只是小术,得另下功夫才是。”
白蝶娘忽地从器具盒中取出一物。
她手中那物,通体暗金,巴掌大小,质地不明,却雕刻得极细。中间是两片狭窄金叶,缀着银扣,形状恰如项圈,最中处凿有一线红晶,微光流转。
“这是……?”霜华眉头一蹙,敏觉如刃。
白蝶娘微笑,语气轻慢中带着一种耐人寻味的炫耀:
“你方才也觉,这些绳子,终归是青楼用物,绑普通娘们儿自然好用,若是对上你这种有内力、有骨劲的‘女侠’——两下便挣脱了。”
她举起那枚项圈,在手指间轻轻转着,红晶泛着微光,像一滴流不尽的血泪。
“可惜人贩子里头,有的是识货的。他们可不是只抓贱女、苦女,他们也贩……‘侠女’。”
她语气忽低,嘴角笑意却扬得比香粉还腻:
“这东西,叫——‘捆仙箍’。戴上之后,一炷香之内,便能封人全身经络,断绝真气运行,强如一品内修,也得像只猫儿一样,瘫着任人拿捏。”
霜华脸色骤变,寒光自眼底透出:“这世间……竟真有如此邪淫之物?”
“怎么会没有?”白蝶娘咯咯一笑,“江南前年就有一位剑门女修,被抓时还劈死了六个活人呢,最后不还是被吊在花楼上头,一日一夜,叫得连观众都起鸡皮疙瘩?”
她眼神带笑,落在霜华颈项间:“所以得用上这等物什,才能让他们信得真、看不穿。”
霜华咬紧后槽牙,身体不动,却心如暴雨翻涌。
让她脱衣可忍,让她受缚可忍,让她羞辱自己也可忍。
唯独这“武功尽失”,是她自十岁起未尝一日的恐惧。
这等于卸了她所有刀锋,砍了她所有脊骨。她将彻底沦为一具裸肉、任人施为,甚至连最后的“拔刀斩物”都做不到。
霜华眸中寒芒爆起,几乎要挣绳出掌:
“你莫想让我戴上这物。”
“当然当然。”白蝶娘举起双手,作出“怕了怕了”的模样,“我哪敢强迫姑娘,万一你真失了功力,叫人趁虚而入、玩了贞身,那可不是奴家担得起的罪,岂不大祸临头?”
“你还知祸?”
“自然知。”
这时,一旁的苏怜月忽然出声,柔柔地拉住白蝶娘衣袖,轻声劝道:
“蝶娘,其实……也不必演得这么真罢?若霜华姐姐不愿,我们也不必强她戴上。”
她声音温软,语调似是体恤,指尖却轻轻拂过霜华手臂上的绳结,像在无意间安抚:“姐姐向来最讨厌这些束缚……若因我而戴上那种……羞辱的器物,我心里也不安。”
她低垂眼睫,咬了咬唇,声音更低一分:
“……倒像是我故意把姐姐往火坑里推。”
白蝶娘侧目看她,神情一顿,忽然一笑:
“小姐果然心善——可惜,越心善,越容易叫人看破。”
“你这护法姐姐若不戴此物,一举一动仍是武人气度,任你装得再惨也没人信她是‘胭脂货’。说不定他们一眼识破,调头就走,到时候这一局——岂不是竹篮打水?”
她顿了顿,眸光一转,笑意更深:
“何况……若真要‘试货’,他们定会先探筋骨、试穴道、听呼吸……练家子的气息是藏不住的。”
“放心,我这物虽凶,却也留了你一线退路。”
她扬起手中“捆仙箍”,指腹轻弹红晶,发出一声清脆轻响。
“你只需,在局中喉咙贴这处机关,唤三声‘苏怜月’,它便自动解落。但只有一次机会。”
“脱了之后,再戴不上。”
“所以要慎用,用早了没用,用迟了被干,那就真做了场‘青楼烈艳’。”
霜华死死盯着那枚项圈,喉头微动,掌心已沁出冷汗。那不是怕痛、怕辱,而是一种更深的直觉——作为武人,她的血与骨都在抗拒那种“任人拿捏”的可能。
她从来都是护人的——不是被人保护的。
可此刻,她却要亲手缴出最后的力。
那一瞬,她几乎开口要拒,却在抬眸的刹那,看见怜月那双眼——澄澈如溪,不染尘土,正仰望着她,像小时候一样,那种“姐姐无所不能”的目光,没有变。
苏怜月忽然上前一步,轻轻握住她的手,语声软得像吹落的灯火:
“其实……就算失了武功,我也不信姐姐就会输。”
她抿了抿唇,像是在极力掩饰某种惧意,语气却越发柔软,带着一点迟疑,一点信任,一点若有若无的撒娇:
“从小到大,姐姐就是我心里最强的……就连梦里,都是你护着我。”
她说着,微微垂下眼,仿佛怕她生气,又似乎怕自己说得太多,手却悄悄攥紧了她的手腕。
“……若是连你也不能胜他们,那我……”
她像是害怕被霜华误会,语尾收得很轻,手却握得更紧。
那一刻,霜华心口忽然一痛——不是被打穿的那种,是那种被人一针一线缝住的窒息感。
那眼神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是从五年前就从未变过,像是那个夜里失声痛哭的小姑娘,仍站在原地,用那种“姐姐什么都能做到”的眼神仰望着她。
她可以败,她可以堕,她甚至可以被人调教、被人玩弄、被捆在床上羞辱……
但唯独不能,让怜月失望。
片刻后,她闭上眼。
“戴吧。”
她声音轻得仿佛一片灰,落在这密室的檀香中,却砸得比刀剑还重。
霜华缓缓伸出脖颈,将自己送到那枚项圈之前。
白蝶娘笑意荡开,像春水拨动锁般,将“捆仙箍”环于她雪白的颈项。金叶贴肤,红晶嵌喉,发出一声轻不可闻的“嗡”。
而苏怜月站在她身后,静静看着她脖颈上那一抹铜环扣紧,手指在袖中慢慢合拢,眼神恍若春水映月——波平浪不止。
初时无感,仿佛只是一件冰凉的饰物。
但数息之后——她心口的气,开始散了。
是的——不是不动,是散了,像被人掀开丹田之门,一缕缕真气由内而外飘逸而出,无声无息,不带一丝痛感,却让她全身如泄水之瓮。
她骤然一震,尝试运劲,双腿紧绷——绳索应声紧勒,却未换来熟悉的力道支撑。
她再试调气,真元不起。
“……这东西……居然……真的……”
霜华咬牙,忍不住扭身,试图扯断一绳,脚尖一挑,气沉丹田——然而丹田像是被掏空,脚下一滑,竟险些踉跄。
霜华喘息渐重,每一口气都仿佛比上一口更浅,更虚。她手臂轻颤,汗水从脊背滑落,胸脯因呼吸微喘而一颤一颤,那被绳勒得胀起的雪肉轻轻晃动,竟多了几分淫靡之感,仿佛此刻的她不再属于杀伐,而是属于床榻与喘息。
她死死咬住牙关,咒骂一般吐出一句:“你们这些青楼人贩子……下流玩意可真不……”
话未说完,忽然一物突兀塞入唇中,霜华瞳孔骤缩,惊愕中竟连唾沫都未及吞咽。
“既然你是真‘货’,那这两样也不能少。”
白蝶娘笑吟吟地将指间那枚红缨软布口衔缓缓推进,像是往一匹即将开笼的烈马口中塞上嚼环,手法不紧不慢,却准得令人发指。
“这口衔是皮中嵌铅,能压舌、驯音、软咽。”她边说边捻住霜华的下颌,拇指抵住她下唇,轻轻一掰,牙关便被撬开,“姑娘你是练家子,骂人那几句话说得太溜。现在乖一点,我不想听。”
霜华“唔”了一声,口腔被硬塞撑开,舌被顶得发麻,下颚被迫后抬,那一抹湿软红嫩暴露在空气里,发出细碎、无力、羞人的呻吟。她羞愤想偏过头去,肩膀才一动,束胸缠腹的绳道立刻收紧,将两团雪乳死死勒住,连乳尖都涨得发红颤动,挣得越狠、露得越多。
“别乱动,再动绳子都勒进奶心里了。”白蝶娘眯起眼笑,语气像是驯犬女匠,“我说过,你这身骨不驯,得慢慢压。”
霜华不敢再挣,却仍睁着眼怒视,眸中冷意如钩。白蝶娘却不急,取过一条黑绫眼罩,在她眼前晃了晃,轻声道:
“还有姑娘眼神太烈,我看着都怕。”
她话虽玩笑,却毫不迟疑地抬手将黑绫从霜华耳后绕过,遮住她目光,那两只冷若冰锋的眼,在一瞬间被遮去光亮,只余鼻尖微喘与唇角的细颤喘息。
“这等杀气搁脸上,别说上钩了,怕是鱼都不敢靠近半分。还是遮一遮,省得杀气太盛,把人吓跑。”
紧接着,一张雪白面巾包裹了她半张脸,只露出羞红耳根与微颤的鼻尖。眼不能视,口不能言,气不能凝,力不能聚。
束缚、封穴、驯舌、断视。
她彻底被困。
白蝶娘轻哼一声,从器具盒中取出最后一物——一根赤红缀尾、银链为舌的牵引链。
她将它扣在项圈侧的银环,链尾垂落,落地一声清响——叮哐,宛如刀剑折服的哀鸣,也像傲骨崩断的回响。
“好了。”
她退后一步,慢慢端详。
那一刻,苏怜月也终于走上前来。
两个女人一左一右,看着这座曾经是剑气凌霄、目下无人的江南女侠,终于彻底‘伪装’成一件货色。
她跪坐于密室正中,手反缚于背,雪肤遍覆细绳,胸脯被勒成两团涨润艳肉,微喘之间不住轻颤;口中衔着红衔,唇角有唾光微溢,半张面庞被白巾包裹,只露出潮红的鼻尖与呼吸起伏的锁骨;眼被黑布遮蔽,看不见任何事物,神情无措,气若游丝,连头颈都因项圈的压迫而轻轻下垂。
她身上早已出汗,雪背上有晶莹汗珠顺绳而落,沿脊而下流入尾骨凹陷,又被勒臀之绳引流至股缝深处。阴阜处的绳索也早已被蜜水打湿,每当她在无声中微微挣动,那处绳缝便摩擦得牵动下体颤鸣,肉缝微启,黏腻香液悄然溢出,被腿根绷带细细拖拉出一道光亮的痕。
鼻尖呼吸已不匀,短促得像是隐隐喘息,唇齿深处时不时溢出低不可闻的“呜……唔……”之声,既羞且软,似恳求又似渴求。
项圈之上悬着银链,坠至地面,仿佛她已被某个“主人”拴好,只待人牵走,送入妓门。
她,已不是霜华。
她是“苏怜月”——被仇家擒获、被捆至失力、等候调教的胭脂肉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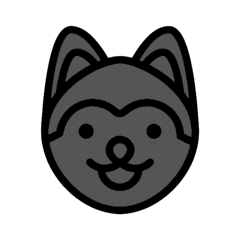
By
bydaynight发布于 2025-04-06 19:38
Re: 【中篇】【连载中】【4.6 更新第二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大大终于更了,数月不见,当真难熬。
uranusg发布于 2025-04-07 14:57
Re: 【中篇】【连载中】【4.6 更新第二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终于更新了!等了好久,而且也是最爱的下克上题材,赞!
第三章
城郊道上,黑色马车稳稳前行。
两名“刺客”一前一后,牵着一位戴着项圈的“俘虏”步入车厢。其中一位刺客骑马驾车,垂首不语,鬓边一缕青丝垂落,竟比正经车伕还沉稳几分。她未曾回头,不问来路,不语人言,仿佛这趟马车只为送货,不为护人。
车厢内部早已布置成风月之榻,软垫香毯,遮帘沉重,隔音密实,外人无从窥探。
那“俘虏”,正是被束缚得动弹不得的霜华。
她依然全身绳缚,胸脯勒涨,四肢无力,口中衔着红缨,眼被黑布所罩,只能被牵着、拖着、抬上车。
银链叮铃,项圈微晃。
她跪在车厢中央,被安置如一尊玩偶,而她曾是如何的女侠,如今就如何显得不堪。
马车启程,轮辘压路而行,车身微晃,肉体随着轨迹不住轻颤。
“呼……终于进来了。”
苏怜月轻轻叹息一声,摘下面罩,伸出柔软手指拨了拨鬓角的汗丝。黑衣贴身,她却依旧风姿婉婉,眼神带笑。
车厢内,霜华跪在软垫之上,银链坠地,项圈紧贴雪颈,口衔深嵌、眼罩紧封,整个人被勒绑成一尊雪色的胴体囚像,跪伏于黑衣“刺客”脚边。
她喘息轻乱,鼻尖薄汗,仍努力保持着最后一分“挺拔”的仪态——可她的乳早已被勒涨得又红又肿,股间缝滑得贴绳发亮,身体早不是她能完全掌控。
她看着眼前这个跪伏的女人,那个一手长刀、敢独挡一面的霜华姐姐,如今肉身绷亮地跪在脚下,像一头温顺却仍在微颤的雌犬。
她眸光一寸寸在霜华身上游走:那挺得高高却因力竭而微颤的乳团,那绳缝中渗出的淫液痕迹,那无法张口却发出哀音的红樱口衔,那仍在努力挺直的后背。
怜月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刻意假装的怜香惜玉,而是一种藏了太久的、终于能够亲手揭开的渴望与掌控——
至少在这个马车厢里,不,从现在开始,
「她永远都是我的姐姐了。」
她曾幻想过许多回——
幻想这个冷得叫人不敢靠近的女人,被脱得精光,戴着枷锁,跪在自己膝前,像一只困兽变成的宠奴。
她想让她低头,想听她说“妹妹饶命”,想看她那双杀人的眼、那把护她五年的刀、那种不容亵渎的清冷,一点点在她唇下溶解成热汗、鼻音、奶水。
她仿佛看见了自己深夜反复意淫的画面,终于要成为现实。
“……原来你真会这样喘呢。”她低语,几不可闻。
话一出口,她才意识到自己又说漏了。
声音太低、太黏、太贴近欲念。
她不该那样说。
不是现在。
霜华还没被彻底“交货”,这出戏才刚刚开场,她不该……提前表现出这种过于露骨的贪欲。
她顿了顿,目光从霜华汗湿的脖颈移开,仿佛要矫正自己的姿态。但那句脱口而出的呓语,像个钩子,从她舌根勾到小腹,再往下绷紧了她整根脊梁。
她呼吸轻重不稳,胸膛微起伏,脸上努力维持着“姐姐我不过开个玩笑”的镇定,却早已无法把持那节节逼近的渴望。
她从小仰望、从小害怕、从小仇恨、从小迷恋的那个姐姐,如今手脚缚住、口不能言、眼不能见,乳珠红透,鼻音呜呜地就跪在她的脚边。
她再也忍不住了。
“姐姐……”
她换上那副“惋惜又亲昵”的口气,慢慢靠近,膝盖轻轻一弯,伏身到霜华背后。
霜华听见她的呼吸靠近,带着浅浅的温热,若有若无地扑在肩颈之间。她一动未动,只以为——怜月是心疼了,还愿为她松一松口衔、取一取眼罩,让她喘一口气、歇一歇神。
她没有抗拒,反而在那气息贴近的瞬间,极轻极缓地向后靠了靠,将肩背露了出来,颈项也微微一仰。
那姿势既无防备,也无挣扎,像是一种沉默的接受——甚至,带着几分误会中的温存,几分认命时的安静顺从。
直到那指尖轻轻的覆在霜华裸露、泛红、被绳勒得圆胀得快炸开的乳上——
那肉实在太软、太热、太烫,像是怒极之下的身体,在任人把玩前的最后一丝硬挺,被她两指轻轻一夹,顿时挤出一圈细汗珠。
她那对乳,是练武者才有的锋挺,是天生淫骨才长出的丰腻,如今却全被绳子勒成一副随捏随动、随揉随涨的样子。
她轻轻一捏——
乳肉像是挣扎了半寸,肌肤抖了一下,却最终绵软地滑出指缝,温顺得像在邀宠。
“唔呜!……”
霜华下意识一抖,肩膀轻缩,“呜”地一声低哼,从口衔后溢出,鼻腔带着一连串破碎的软音。
她本已被黑绫遮眼,可那瞬间,眼皮下的瞳孔还是骤然一缩,仿佛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情绪在幽暗中炸开——错愕、不可置信,甚至是一丝细微到几近无法察觉的……恐惧。
“马上就要分别很久了……你要被送进香榭替妹妹当‘货’,我却只能留在苏家守局。”
她轻轻抚上霜华肩头,像是在安慰:“姐姐,你说,我是不是该……”
“先替这香榭试试货色?”
霜华浑身一紧,她下意识地微微摇头,“唔唔”含混着发出否定哼声,语气急促,破碎,几近哀求。脖颈上的项圈随之作响,银链微颤,像是无助挣扎的小兽尾巴,摇得轻而急。
不,不可能。
她知道怜月生性狡黠,有些乖张性子,偶尔耍赖、偶尔撒娇,可她始终是自己一手护大的孩子。哪怕有些偏执、有些怨怼……可她绝不该——
绝不该用这种语气,说出那样的话。
她想斥、想骂、想挣扎,想像以前一样训斥怜月不知礼数、守不得规矩,怎可说出这般媟语——
可身体比她还诚实地先一步颤抖了,像一只失去牙齿的猛兽,在陌生的地盘喘息。
“不用紧张呀。”怜月温声哄她,唇贴在她耳后,舔了一下她沾汗的鬓发,语气里带着几分笑,“妹妹我又不是外人……肥水,总不能流了外人田,对不对?”
“第一次嘛…怎能便宜了那些香榭里的粗手笨脚的嫖客?”
“姐姐现在这样……真的,好可爱……可爱得让我、忍不住了……”
说到这,她忽然露出一点扮可怜的表情,声音黏软下沉,像小时候挨训时低头撒娇求原谅: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想抱你、亲你,可你总凶我……现在机会难得,你就……原谅妹妹这一次嘛……”
“就这一次。”她眼神含着笑,像是哄,又像是哀求,“姐姐别生气……让我玩完了,我就乖。”
她说着,一边轻轻把霜华往怀里搂。
霜华脑中一片嗡鸣,想挣、想避,却只能喉中哼着娇软喘音,被红缨口衔堵得死死的,说不出一丝威胁。她的身子轻颤,想要摇头,奈何全身被捆、力气封断,只能微微缩动肩膀,像在求饶。
“别乱动嘛。”怜月轻轻按住她,“车厢晃得这么厉害,姐姐这样一扭,绳子都勒进肉里啦。”
她轻笑了一声,忽地从身旁香囊中抽出两根细细的绛红绳丝。
“既然姐姐老是乱动……”她手指轻巧地拨了拨霜华被勒得鼓胀的乳珠,“那就别怪妹妹想点小巧思……帮姐姐‘规矩规矩’啦。”
霜华骤然一惊,似是意识到什么,身体微微挣动。
可苏怜月动作极快,已经将绳绕过她的一侧乳珠根部,缓缓打结,再绕向她另一侧白皙的大脚趾。
那脚趾因紧张而轻曲,肌肉还带着刀修之人的一分收敛力量,怜月却笑吟吟地抚了抚她脚弓处那薄汗润泽的皮肤,低声呢喃:
“姐姐的腿功最好,记得小时候你一个腾身上屋檐,我吓哭了一整夜。”
“现在……你要是再乱动,被你那脚一抽,这乳儿可就——”
她故意一收绳,乳珠顿时被扯得前突一分,鲜红如豆,盈盈战栗。
“唔呜……!”
霜华猛地低头,鼻音一声哀啼,眼罩下泪光闪动,乳珠颤动不止,脚趾却不敢再动一分。
“乖嘛。”怜月轻柔地将另一根绳也绕上另一边乳珠与脚趾,动作熟练得像在绣一朵绣球花。
“这样你就安静了……乖乖跪好、让妹妹抱着,不乱踢、不乱逃。”
“你若真怕痛,就好好听话,不然你那双宝贝脚,就得自己把你这对奶给牵下来。”
她抚摸着那根被拴起的乳绳,轻轻一拨,那根细细的绛红绳丝仿佛有了生命,在霜华胸前一颤一弹,乳珠便被勒得发胀泛红,像极了熟透的果实,被人轻轻拉扯着等着滴汁。
霜华轻“呜”一声,肩膀微颤,却还未真正察觉其厉害。
直到怜月故意在她脚趾边拽了一指宽度,拉紧绳结。
“唰——”
一阵微痛自乳头陡然窜起,像火星坠入雪湖,炙得霜华猛地抽了口气,整条腿本能地往回缩——却只是更悲剧地拉动了脚趾,那脚趾一弯,绳子猛地牵住乳头。
“呜啊……!”
她闷哼一声,整个人往前一倾,乳珠被绳拽得一扯一缩,那根雪白挺拔的乳被瞬间扯成了向下坠落的弯月形,红豆般的乳尖被绳子勒成深红,边缘都微微渗出一圈淡淡的汗膜。
“疼吗?”怜月在她身后轻声问,语调温柔得像在哄睡婴儿,指尖却不肯放松。
她又轻轻拨了一下绳结,那小小的乳珠再次被牵得往上跳了一寸,像是被弹起的樱桃,在空气中微微颤颤。
霜华“唔唔”地哼出几声,鼻音娇软,头埋得更低了些,脚趾蜷缩,膝盖往内并,像想遮羞,又像是怕下一次被牵出更重的痛楚。
但雪颈上的那道箍压制了她所有的反抗。
她越想往内收,腿绷得越紧,脚趾牵得越狠,乳头拉得越紧,连带着整团被勒涨的乳肉都在不住颤抖,汗光在皮肤表面泛起晶莹湿光,衬得那对雪团愈发淫靡。
她低笑,手指顺着乳绳根部抚摸过去,在乳下那一点皮肤与绳子交错的地方轻轻点了点,霜华又是一颤,鼻音中带着几分哽咽的腻意。
“还乱动吗?”
再不敢乱动了。
她身子僵得如弓,眼罩下满是热雾,汗沿着额角滑入脖颈,咬着口衔、缩着脚趾、咽着嗫音,却无处逃避。
“乖。”
苏怜月终于满意了,像驯好了初次上手的小兽,捏了捏她的大腿根部,然后收起了语气的轻佻,换上了那种藏着童年记忆的甜声细语:
“姐姐……你现在……真的好像我小时候偷养的那只兔子啊,蹬蹬乱蹭,我一给它拴上绳,它就只能乖乖躺在我腿上……让我抱,让我亲……让我钻进它肚皮下面,把脸埋在它毛里,捧着它心口,听它喘。”
她唇贴霜华耳垂,轻轻一舔。
“现在……我也想听姐姐你喘。”
她的手缓缓探上霜华双乳,指尖微凉,落下的却是慢而稳的力道,按住、揉紧、再一点点将那被绳勒住的肉团从缝中挤出,红润胀软,如绽开的花苞。
她按得小心,捏得轻缓,每一下都似在试探力道,不敢太猛、不忍太粗,唯恐按疼了似的——
她平日里对那些香榭侍女残酷乖戾,罚得毫不留情,可唯独这位“姐姐”,却像刚刚得手的心头好,连揉都舍不得太用力。
不是怕她疼,而是怕——一不小心,就弄坏了。
“嗯——!”
霜华猛地一颤,鼻音中第一次带出一声娇腻的哼泣。
怜月凑近,唇贴霜华耳边,嗅着她汗气夹杂的乳香,吐出温热气息:
“你看你……光是这么一捏,就叫得这么动听……”
霜华听着那熟悉却变调的声音,喉咙被口衔堵死,说不出任何话,只能发出低哑的“唔唔”哼声,颤得连手指都轻抖。
怜月笑了。
她伸手绕到霜华身后,双手从绳索之间探入——
那是一双纤指,却像水蛇般钻入勒紧的绳间,探进她后背、腋下、腰侧、直至臀缝。
“这里勒得也紧……是不是已经湿了?”
她话语未落,手指便点到了那一线早已濡湿的缝间。
“唔……!”
霜华身子一颤,腰背猛地紧绷,膝盖抵地几乎滑动。那一指仿佛电击,激得她连鼻音都走腔。
“真的湿了呀……”
怜月眼神越来越亮,轻轻拨弄那被绳勒出沟壑的蜜缝,指节揉进那已湿得发黏的缝内,缓缓一揉一捻。
“这么敏感……才绑了一刻钟,姐姐就已经开始渴了?”
霜华狠狠摇头,羞怒至极,可每一声呻吟反而像娇喘叫床,每一次颤抖都像迎合,双腿拼命收,却绳索勒得越紧、蜜液越流,缝间甚至已能听见“啵啵”的淫靡响声。
怜月捧起她下颌,在她耳边轻语:
“我就玩一下……一下就好……姐姐就当是习惯习惯,被人调教的感觉嘛……”
手指从蜜缝探入,先是一节,然后缓缓深入,指节弯曲在她体内拨弄。
“呜啊……唔唔!唔……呜呃呃……”
霜华整个身子僵住,一瞬仿佛被雷击,双腿猛地绷紧,那两道细绳应声收紧,勒在乳根的绳结被牵得猛一抖动,乳团乱颤如浪,蜜穴一阵阵痉挛收缩,竟止不住地涌出滚烫蜜液。
“姐姐真好色,才刚进一指……里面已经在夹我了。”
“不过呀,被姐姐这样迎着夹着……妹妹我,也会忍不住开心呢。”
她话音未落,又一根手指缓缓探入,两指并进,轻轻一捻。
霜华想要抽逃,却全身封穴,连腰部肌肉都软得像被抽空,只能在怜月的掌中战栗,像一尾被剥皮的鱼,滑嫩得无处可逃。
“唔呜……唔唔……!”
她喉中呜咽不断,口衔阻音,牙关死咬却止不住呻吟漏出。双腿想夹,却一动便牵扯到那绕乳连趾的绛红细绳——乳根勒处顿时收紧,抽得她生疼;想踢开,更是寸步难伸,反倒让胸前雪肉被带得又紧又颤。只能无助地张着,任那对细腻的手指在穴口中一探再探,一搅再搅。
怜月低头看着,眼神里不再有半分妹妹的怯意,而是一种病态的柔情与恶意的怜惜。
“姐姐这里……好软,又好紧……”她边说边探入更深,手指一勾,顶开一处深处的嫩壁,那道肉褶像是从未被人触及过的禁地,被这突如其来的顶弄勾得一阵痉挛。
霜华“唔啊”一声,双乳随着痉挛猛地抖起,汗珠从乳沟顺着红绳滚下,混着皮肤上的蜜液闪着淫光。她拼命想要扭开腰,却只是将穴口那两指夹得更紧,反而像在主动含住那羞辱的侵犯。
怜月笑了笑,手指抽出半寸,再缓缓插入,抽插的动作不快不猛,却带着令人发疯的节奏,每一下都像要把她最深处的脆弱一点点撬开。
“别夹这么紧嘛……”她语调轻媚,手指却忽然加快抽插,一下、一下、一下,淫液被搅得粘稠响亮,车厢内都是“啾啾”“咕叽”的水声。
霜华早已泪满面罩,呼吸破碎,腿根剧烈颤抖,蜜穴抽动不止。
“唔啊……唔呜呜……!”
她每想挣脱,穴口便回吸得更狠,像是那羞耻的洞口已不是她能控制的部位,而是早被“妹妹的手”调成了肉腔器皿,只知道迎合、吞纳、渴求。
那两根手指越捻越深、越插越快,抽送间带着粘腻水声,霜华原本咬紧的齿根开始松动,背脊发紧,腹部痉挛,她的意识在那一瞬开始断裂,羞耻、痛楚、愤怒与快感交错如潮,层层叠叠,将她向着深渊推去。
直到那最后一下——
“嗯啊啊……!”
她发出第一声无法压抑的高潮叫喊,娇啼从口衔缝隙中迸出,断断续续、婉转入骨,宛如玉女破戒,痛恨之中夹着快感的绝望。
霜华喉间呜咽不断,口衔吐不出词,眼罩下泪水模糊,腰身扭不过一分,腿抬不起一寸,只能被妹妹从身后勾着玩弄,指尖每一下按在私处都带着羞辱的温柔。
“唔……唔啊……唔唔……”
而她的妹妹,正低头含着她乳尖,用舌尖卷起那被绳勒得高耸挺立的乳珠,一边舔一边喃喃:
“姐姐的雌汁又腥又香……姐姐不再是那个拔刀见血的冷霜华了,而是我的乖狗狗了……对吧?”
霜华浑身颤抖,眼下涌泪,口中娇啼不休。
她从未想过,自己这一遭的第一劫会是这样来的。
不是仇敌的折辱,不是淫器的惩罚,不是香榭老鸨的调教,而是……怜月。
她从小捧在手心的妹妹,她以为始终柔顺单纯、始终仰望自己、愿意为自己低头含泪的“怜儿”……竟用这种方式逼她低头、让她浪叫,让她高潮,叫她一滴不剩地在自己手中洒尽侠气。
「我……居然……在她手里……去了……」
她内力被封,连羞愤都无法完整聚起,只有那一股酥痒与战栗穿透绳缝、穿透骨髓,让她像一滩被玩熟的软泥,被妹妹操控着潮起潮落。那道蜜封的嫩鲍,正被一指一按间逼出淫水,那对曾为江南风月传名的腿,如今只能岔开供玩,连夹一下都做不到。
霜华心底忽然泛起新的恐惧,不是对辱的恐惧,而是对这份病态情意的惊惧。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名为“妹妹”的苏怜月,从来就不是躲在她背后的柔弱羔羊,而是……潜伏在她脚边的豺狼,温顺不过是舔舐的舌,顺从只是等着扑上去咬住她脖子的姿势。
而现在,她被咬住了,被按在车壁上、用蜜水湿透的腿间、用羞耻灼红的乳尖,一点一点——吞进了那个叫苏怜月的少女怀中。
第一次泄身之后,霜华便再也无法分辨车厢内的光线。
可她知道苏怜月食言了。
明明方才还软声说着“玩一下就好”,此刻却全无要停下的意思。那双从小被她牵着走过雪地石桥的手,如今却时而抚发、时而温柔地揉着乳、时而探向她腿间早已被蜜水泡软的花缝,揉着她高潮后的颤抖,像是调教一只不会反抗的猫,玩累了便哄,哄软了便玩。
不知是第几次被奸到蜜水横流,她已彻底分不清时间、方向与尊严。她只记得自己曾是冷面女侠,杀人不眨眼、拔刀不回头;可现在——她跪趴在马车软榻上,被妹妹两根手指来回揉弄,肏得双腿打颤,腰软舌乱。
几根手指,就能把她逼到高潮,逼得她哭,逼得她呻吟着在亲妹妹怀中撒娇求饶。
她不记得自己呻吟过多少声,只记得每一次高潮都更耻于上一次,每一次乳尖都被舔得更挺,每一次穴口都被玩得更湿。
她甚至不再挣扎——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挣也无用。
“唔呜……啊……呃嗯……”
那一声声娇啼未歇,却已主动将脸埋进苏怜月怀里,发丝凌乱、汗湿香颊,一下一下地蹭着她胸前柔软的乳袋,带着余韵的软媚与本能的依恋。
她愣了一瞬,然后笑了,笑意从眼底漫出,再藏都藏不住。
——就是这个模样。
她梦了无数遍的姐姐,就是这个模样:满脸潮红地缩在她怀里,一边流着淫水,一边蹭着她胸口轻轻呜咽。她梦中梦见过的,梦里伸手都抓不到的,如今就这样软在她怀中,哭着、湿着、喘着,全身都在渴着她的指。
她眼神灼亮,唇角忍不住上扬,那原本柔怯的笑意,逐渐变得病态、贪婪,像个得了糖的孩子,却偏要把糖一点点捏碎再含进嘴里。
江南拂晓,天未明,城边旧路轻尘初起。
那辆黑漆马车一路驶过碎石土道,车身微晃,每一步马蹄落下都夹着一声奇异的——“唔啊……唔唔……呃啊……”
不是风,不是鸟,是低低压抑的女人呻吟。
蹄声咚咚,呻吟软绵绵地拖尾。
马车内,烛台早熄,窗帘紧闭,却满是淫靡潮热。
苏怜月脱下刺客外袍,跪坐于霜华身后,怀中满是香汗淋漓的姐姐。
霜华那一身白雪似的肌肤已被汗与蜜打湿,脸颊潮红得仿佛烧灼,红缨口衔湿透,垂落下透明的涎丝。她被绳索捆得紧紧,胸脯早已被勒涨如熟桃,蜜缝泛滥,滑腻得几乎滴水成珠。
那绳缝之间,每一次摇晃都在碾压敏感;那项圈牵链,每一次低头都像主动求抱。
她整个人瘫在车内软垫上,双膝蜷着,银链落地,脚尖打颤。蜜液顺着腿根蜿蜒,浸湿了垫毯,连车厢木板都光亮一片,散发出热蒸蒸的淫香。
苏怜月舔着她耳垂,呢喃如鸦羽:
“姐姐已经习惯了呢……这才几炷香,你的身子就自己学会怎么浪了。”
“好乖……姐姐习惯了…下次就不会这么痛了。”
霜华轻哼,喉中堵着,鼻音发颤,“唔唔唔……唔呃……”
她下意识想反驳、想挣,可一动腰、脚、胸,绳道收紧,蜜缝被剐得更深,反倒“啪”地喷出一股热潮,沾满马车壁。
这一路,早已不知被苏怜月玩去了几回。她的意志在淫浪中摇晃,尊严仿佛被一根竹枝不断削片,薄至透明。
忽然,帘外传来白蝶娘懒洋洋的笑声:
“江南城快到了,该收收心咯。”
苏怜月眸光微动,忽地起身整衣。
她望着霜华那副满脸潮红、乳胀绳勒、蜜汁淌腿的模样,唇角缓缓扬起,心头突然生出一个更香的念头。
“停车。”她轻轻一挥手,“离香榭还有两条街,停这里。”
白蝶娘一愣,随即会意,笑得媚得发腻:“小姐这是……不舍得放姐姐‘轻松进门’啊?”
怜月笑而不语,只是柔柔地将手掌抚上霜华汗湿的后背,顺着那被捆得凹凸毕现的脊线轻轻划过,语气娇怜,语意却带钩:
“蝶娘,你是明面上的‘交易人’,这又是香榭里的马车。若你我共乘此车入城,被人瞧出了破绽......可就不好收场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捏了捏霜华绳下那被玩得挺翘的乳尖,指尖轻巧一绕,解开了牵连足趾的红绳。唇角微弯,笑得分外无辜:
“所以呢……我们得下车步行入城。”
她话音微顿,眼波却未曾移开霜华那早已湿透、绷紧的裸躯,声音更低了些,像是在劝,又像在哄:
“况且...姐姐这副模样…香汗淋漓、气若游丝,最合演‘被抓来的贱妓’的角了。这若不让人瞧上一眼,别人还以为我们装得不够真呢?”
车停。
霜华浑身一震,眼罩之下神情恍惚。
她不知道还要多少人见她这样——见她如狗似奴,被妹妹牵链提走,像头牲口,香汗满身、淫汁遍地地走入青楼。那曾踏断雪岭、御风跨舟的双腿,如今却在发软,连脚尖都因高潮后的脱力而蜷缩成屈。
这时,苏怜月忽然俯身,语气温柔得近乎体贴:
“姐姐要走这么远,怎么能光着脚呢?这路石板又凉又硬,万一把姐姐的脚底磨破了……多可惜。”
她一边说着,一边掀开车帘向白蝶娘投去一个眼色。
白蝶娘立刻会意,从怀中取出一双做工极艳的鞋。
那是一双高跟细齿的软底小履,鞋身上绣着并蒂春蝶,色泽绛红,鞋尖细削如钩,鞋后挂着一串银铃,轻轻一晃便叮铃作响,清脆悠扬,媚意十足。
白蝶娘一边将鞋呈上,一边慢条斯理地笑道:
“这叫‘步音奴履’,我们香榭头牌个个都得穿。响得远,走得慢,铃一响,整条街都知道——‘好货来了’。”
她伸手,轻轻握住霜华那只沾满蜜汗的脚踝。
霜华骤然一颤,脚趾本能地往里一缩,似是要挣脱。但那挣扎太轻太短,几乎刚刚抽动,便又瘫软落回掌中。
她实在没有力气了。高潮未褪,羞耻正涨,那对脚——曾以“江南第一轻功”著称的足尖,此刻却只能像被捉住的兔子蹄,湿滑滚烫,连反抗都带着呻吟。
白蝶娘轻轻抚过她足背,指腹缓慢而淫靡地揉了一圈脚心,再捏了捏她屈缩的脚趾,一根一根将其掰开,才将那只精致小履缓缓套入。
那鞋窄如花匣,霜华的足骨本就修长,鞋尖紧裹,足弓高耸,穿进去之后被强迫抬起脚跟,只能用脚趾点地,一步一步地摇摆前行。银铃贴肉,随她每一次颤抖轻响两声,清脆得几乎像嘲笑。
第二只鞋也套了进去,白蝶娘按着她足跟将其稳稳压进鞋底,扣好银扣。
“……这才像了。”怜月轻轻拍了拍霜华的足背,目光顺着绳缚之腿一路滑上。
霜华的双脚此刻并膝而跪,鞋尖贴地,银铃悬垂,足趾绷起,像是随时等待被牵走的娼奴。
“别怕嘛。”苏怜月拿出那根小时候霜华经常用来抽她的竹条,在她绳缠的腰眼轻轻拍了一下,“只是让你先走几步‘适应场景’。”
她笑意温婉,指间竹条却不容人拒绝。
“来,乖狗狗,跟主子下车——”
说着,她扯住项圈的牵链,向前一拽。
霜华身子一颤,跪姿滑动,膝头在绒毯上拖出一道痕迹,被迫向车门一点一点地挪去。铃鞋叮哐作响,配合牵链发出的细脆金属声,像牲畜出圈,被拖至屠场。
“啪啪——”
竹条抽落在圆臀两侧,那肉被勒出纹痕的臀瓣被击得飞颤,乳也跟着绳索晃起,弹得一串乳浪。霜华呜咽一声,舌被压住,只能喉中发出哑哑的啜声,似痛似颤。
车帘被掀开,一缕街头的冷风灌入密室。
她的膝盖软得几乎碰地,脚跟高高踩在“步音奴履”之中,脚趾点地而立,身形被迫挺直。铃响入街,空气清冷,汗与蜜在腿根悄然凝固。
她站不稳,被项圈链子牵着才勉强立住,脸被白巾裹得看不出神情,只有鼻尖泛红,唇角有银丝溢出,脚下铃声在青石板上轻轻摇响。
苏怜月轻轻理了理她额前汗湿的碎发,低声笑道:“姐姐乖,记得走得慢一点,要让路边的人好好看看‘这新货’值不值。”
车前的蝶娘早已脱去黑衣,扮回了风尘之妇,妆浓色艳,鬓边插花,立在车旁掩口笑:“啧,好一个俘虏……今儿香榭怕是要迎来贵货了。”
白蝶娘这时向她微一拱手:“不打扰姑娘雅致,奴先行一步,去香榭打点收货事宜。”
“别走太快。”怜月语带双关。
“放心。”白蝶娘回眸一笑,“奴自然会在门口‘验货’的……到时叫那些客爷都瞧得清清楚楚,这是谁家的俏肉。”
她说着一甩烟袖,转身上马融入街市中。
江南清晨,城门初启,街巷还未喧哗,只有偶尔挑担赶集的脚步,在青石板上拖出些轻响。
可今日,一道不寻常的身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前头是一个女子,虽裹着黑袍,却高挑冷艳,风姿婉然,乍一看像是谁家小姐早起赶路。
可问题在于——她身后“牵”的东西。
那不是牲畜,也不是货物,而是一个被赤身绑缚的绝色女人,跪步而行、脚穿高跟,项圈缀链,被银索牵着缓缓前行。
她戴着黑布眼罩,口中衔着红缨丝绫,白纱微盖,整张脸只露出一小截鼻梁与发红的耳尖;一身白腻绳缚,自胸至腹,从腿至腕,每一寸皮肤都勒得微凸、泛红,仿佛特意为展露肉感而缠。
步音奴履在青石地面上咔哒咔哒作响,细而脆,像调情般地响亮。
那铃音轻快,一响一摇,恰恰与她双乳晃动的频率重合。每一步,她胸前那对被勒高的巨乳都晃得乳根泛红、乳珠微透,蜜腿间夹着滑腻之痕,香汗淋漓,如同打了蜡的肉雕在晨光中莹润生光。
那样的身材,那样的皮相,哪怕被捆着,也艳得夺目;哪怕低着头,也色得犯规。
可她那步伐……依稀还带着一分侠骨旧姿。
脚步仍稳,背脊不弯,每一挪移都像是在试图保留某种最后的“气节”。可那链索一拽,她便只能低头;竹条一抽,她便只能哼泣。
这份“欲挺不成”的矛盾,反倒让她更像一尊刚刚被驯服的淫奴——反抗的影子还在,屈服的痕迹却已烙骨。
有个早起卖茶的老汉目光愕然,喃喃道:“那……那是人?”
旁边有挑水的年轻汉子咽了口唾沫,小声说:“像个娘儿……可这身子……我他娘的从没见过这么俊的骚货……”
“她是被谁玩成这样的?是哪家青楼的头牌?要不要命了?”
更有几个看着像下九流混子的男子,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被勒得发紫的乳尖与绳缝之间的淫液,低声嘀咕着:
“这要是我弄到手——干三天都不放她下来。”
“听说那种鞋是步音奴履,香榭里的——能穿这个的,不是贱奴就是淫品。”
“呸,这骚货也不知做了多少人的狗了。”
众人不敢上前,甚至不敢大声调笑,因她被牵的模样虽淫,但那背脊线条仍透着令人不敢轻近的“冷杀气”。
可她低着头,被链拴走的模样,却又叫人不由自主地意淫她被翻在青楼床上叫到失声的画面。
越想,越不敢看。
越看,又越无法移目。
而此刻的霜华——
她走在青石板上,听着那清脆的“咔哒”声从自己脚下发出,听得自己每一寸皮肤都发麻。
那些鞋跟踏实地的声音,每一下都像锤在她心口。
她知道——苏怜月这是在公报私仇。
从小她就对这妹妹最严、最冷,每次犯错便抽她手心、罚她跪堂,哪怕心疼,也从不放纵。而如今,她竟在她手中,被拽成这副“狗一般的贱奴模样”,一路牵走,步步皆辱,众目睽睽之下如肉般展示。
她知道这其中藏着怜月的怨、她的恶意、她压了多年的渴望与不甘——
可她忍了。
因为她是姐姐。她必须护着怜月,不论她做了什么。
但她却不理解,马车上为何怜月又会展现出如此贪癫的一面。
作戏能演成那幅模样吗?
不过此刻她已经无法去思考这些问题了。
她只能听见耳边行人的喘息,听见他们的目光落在自己乳上的热度,听见蜜液从腿缝滴下的水声混在那“哒哒”中,交织成一曲羞耻的朝歌。
她双腿一软,几欲跪地,可牵链一扯,强迫她“站好”。
羞。
羞得她想咬舌、想闭气、想碎成尘土。
可最羞的不是那些目光。
最羞的是她的身体。
她的蜜缝仍在一颤一颤地收紧,仿佛链条的每一次牵拉,都会让那被绳勒的下体微微抽搐;乳尖依旧高耸,顶着绳缝向外鼓起,凉风拂过,都像是在催她挺得更傲;那高跟淫履下的腿根,一滴、一滴透明的蜜液,正顺着内腿蜿蜒而下,踩入鞋底,弄湿她那双银铃作响的妓奴之履。
她高潮之后,竟仍在渴着、热着、湿着。
不该是这样的。
她明明恨极了自己这个样子,却更恨——这副身体竟已不由她掌控。
“呜呜……唔呜……”
她发出极其细碎的啜泣,红缨口衔堵着,反而让那些抽泣声听起来像是勾人的娇吟。
“姐姐……”
苏怜月忽然靠近,在她耳边柔柔地说,带着一丝假惺惺的歉意:
“对不起哦……没想到这条街……人还挺多的……只能委屈姐姐多忍一忍这一段。”
“不过……姐姐这么好看,让大家欣赏欣赏……也没什么不好,对吧?”
她伸手在霜华臀上的红印轻轻抚了一把,又拍了一下,故意弄得屁股一颤,乳珠前挺,淫液飞弹。
“再走一条街,就到香榭啦。”
终于,待到天光破晓,第一缕晨日洒落在香榭朱红门扉之上,照亮了那一幕异样至极的场景。
那是一个女子——
被绳缚、赤裸、戴口衔、蒙眼布、乳肉勒涨、蜜腿淌汁,穿着叮铃作响的铃履,被牵链拽着跪在青楼门前。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茶摊老板,过巷书生,晨起挑担的汉子,巡逻未散的小兵,香榭的老妓、杂伎、买香的贵客……都止步观望,面色各异,有惊、有窃喜、有羞、有热。
苏怜月轻轻一扯牵链。
“姐姐,观众越来越多了,可别让他们失望了呢。”
霜华身形一紧,绷着想稳住脚步,未料那牵链忽然一勒,她重心一歪,脚下一软,竟毫无防备地“扑通”一声跪倒在香榭门前。
“叮哐。”
银链坠地,铃音碎响,空气中淫香四溢。
霜华跪在门前,脸贴青石,香汗淋漓,乳贴地颤,银链坠地作响,蜜汁自腿缝滴落成线,在她跪拜的地面渍出一圈淫晕。
苏怜月俯身,唇角噙笑,嗓音温柔却不容拒绝:
“既然跪都跪了……那便乖乖地,爬进去吧。”
霜华闭着眼,在眼罩黑暗的世界里默念:
「无人在此认得我…只是观个贱婢而已…」
她抬起膝,往前一爬。
「怜月……不过是多年怨气难消,借势发作罢了。」
又一爬。
「权当逢场作戏,不可误了正事。」
石阶冷硬,膝骨擦破,肌肤红肿,乳在地上晃着、抖着、垂着。她脚尖在奴履中蜷缩,铃声响得像凌辱的乐章。
苏怜月轻笑着:“姐姐好乖,再三阶就到了哦。”
就在那第三阶的门槛前——
香榭朱门缓缓开启,白蝶娘袍袖拂地,似笑非笑:
“呦,货来了?”
那是白蝶娘,缓步而出,手持绢扇,腋下红绸荡漾,媚眼一挑,身后立着四名妓娘,皆衣着艳俗,眼神轻浮。
“行了,上手。都按我说的来——今天可是头一回,旁人看着呢。”
霜华原本只以为是“入楼前走一遭戏”,从未想过竟要在门前被——验货。
她骤然僵住,膝步一滞,脑中嗡的一声炸响。
「不、不可能——她们不会真的……」
可那两名妓娘已一左一右上前,笑吟吟地探手而来,动作娴熟却不容抗拒。一人按住她反缚的手腕,将绳索更紧勒入皮肉,另一人则顺势扣住她肩背关节,猛地一提!
“唔——唔啊!!”
霜华陡然惊叫,口中衔物阻声,却仍发出细碎而破碎的娇啼,眼罩之下双目猛睁,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感觉身体被吊起,失重感从脚底涌上脑海。
她还未来得及挣扎,腿根已被人从两侧架开,一股寒风掠入蜜缝,带着微凉将她最隐秘的热处吹得颤了一下。
“唰——”
随着最后一根绳索扣紧,她整个人被吊成弓形——
胸朝天,腿分开,蜜穴大张。
她悬在门前廊柱之间,头低脚高,项圈牵链微晃,淫液从臀下滴在香榭门板上,发出一连串水声滴答,像春雨打池。
“唔唔……唔啊……呜……”
霜华惊骇欲绝,那一瞬羞辱几乎炸裂全身,血气全冲上眼眶——她根本没想到,怜月居然真的允许她在门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吊起来、被当牲畜验货。
她拼命扭动,却越扭越晃,乳在空中一抖一抖地弹,腿间蜜肉在晨风中微微收缩,淫液却偏偏更快地流下来,像是羞耻把她的体温逼到了沸点。
街边的围观者屏息静气,不敢上前,却不自觉地靠得更近几分。
她不知自己是在哭、在喘、还是在呻吟,只觉得嘴里的衔物越来越软,越来越咬不住了。
“来,先查肉性。”
一妓娘用紫藤尖条挑开缠在霜华大腿上的绳扣,缓缓滑至耻丘下,绳一拨,蜜肉弹出,粉嫩颤抖,淌得满手香滑。
另一妓娘笑着接了条羽刷,在霜华蜜缝上轻轻一刷,从珠尖扫到穴口。
“呜……唔呃……嗯呜……”
霜华猛地挣动,口衔中发出失控的呻吟,胸乳在空中晃得快飞起来,眼罩下泪水直涌,嗓音却只剩娇喘。
“啧。”白蝶娘摇着扇子笑,“这反应不错,触感新鲜,骚得有潜力。”
“来,试探入肉程度——看她到底得从哪一步‘训’起走。”
妓娘从香榭门边提来一小瓶檀木浸油,一滴滴落在霜华臀缝、乳根、肚脐上,然后两指蘸着油轻探进蜜穴,一探便入,两探便颤。
“咕啾——”
霜华整个人抖如筛糠,双脚绷直,高跟奴履在空中乱颤,手腕挣得红痕透骨,蜜穴却死死夹住那两根探指。
“唔唔!呜呜啊啊……呃呃……”
她哭了,叫了,身子乱抖,连链子都抖得叮叮当当响,蜜液像被挤破了穴腺,从肉缝深处喷涌而出。
白蝶娘懒洋洋一笑:“这叫‘假抗真浪’。看着还在挣,其实下面早学会享受了。”
“她这肉……再上三堂课,便能听声便浪,闻香便湿。”
那妓娘微微一用力,指节弯钩,“啵”地一声从她蜜肉深处扣出,带出一汪浓黏汁液,飞溅至廊柱上。
霜华,彻底恬不知耻地高潮了。
她头仰背弓,全身痉挛,口中呜咽变作喘叫,连白巾被咬出齿印,蜜穴张合不止,淫水混着汗水滴得地板一片狼藉。小腹一抽再抽,涌出的蜜液从大张的穴口淌成一线,滑过腿弯、坠下鞋尖,铃铛也因抽搐连连作响,如春夜风声叮咛不歇。
她连昏厥前最后一声喘息,都是带着软媚鼻音的“呜啊——”,像是婊子破了身喊出的头一声浪叫。
然后她昏了。
媚肉悬挂轻晃,双乳因力竭而微颤,乳头仍挺未软,腿绳仍勒未松。头垂至胸前,双眼翻白,唇角余涎未褪,宛如献祭之物般被悬在香榭门前的朱漆廊柱之间,供人观赏。
她曾手起刀落、快意江湖,如今却被人牵着银链拖下马车,吊在青楼门口,当街张腿泄蜜,连一根指头都未能抬起抵抗;她曾誓死不辱、不屈不媚,而如今却当众高潮,淫水如雨,面罩下喘成一头乖顺淫犬。
白蝶娘收扇一叹:
“啧,还是嫩。才验一验,就失神了。要调得更久些。”
她一挥手,两名妓娘上前将霜华从绳上解下,横抱进香榭门内,如抱一尊刚用完的观音妓偶,姿势扭曲、肉体软垂、乳臀暴露。
那银色长链还拖着霜华残余的体温,在石板路上划出一道水迹,蜿蜒直至门槛为止。
红门缓缓合拢。
啪——
锁扣合上。
香榭门后,从此多了一条会呻吟的狗。
苏怜月站在门前,终于不必掩饰唇角的喜意。
她抬手,冲那闭合门扉挥了挥,轻声告别:
“姐姐,再见咯。”
“好好听课,莫要偷懒。”
“——妹妹等你,乖乖回来。”
城郊道上,黑色马车稳稳前行。
两名“刺客”一前一后,牵着一位戴着项圈的“俘虏”步入车厢。其中一位刺客骑马驾车,垂首不语,鬓边一缕青丝垂落,竟比正经车伕还沉稳几分。她未曾回头,不问来路,不语人言,仿佛这趟马车只为送货,不为护人。
车厢内部早已布置成风月之榻,软垫香毯,遮帘沉重,隔音密实,外人无从窥探。
那“俘虏”,正是被束缚得动弹不得的霜华。
她依然全身绳缚,胸脯勒涨,四肢无力,口中衔着红缨,眼被黑布所罩,只能被牵着、拖着、抬上车。
银链叮铃,项圈微晃。
她跪在车厢中央,被安置如一尊玩偶,而她曾是如何的女侠,如今就如何显得不堪。
马车启程,轮辘压路而行,车身微晃,肉体随着轨迹不住轻颤。
“呼……终于进来了。”
苏怜月轻轻叹息一声,摘下面罩,伸出柔软手指拨了拨鬓角的汗丝。黑衣贴身,她却依旧风姿婉婉,眼神带笑。
车厢内,霜华跪在软垫之上,银链坠地,项圈紧贴雪颈,口衔深嵌、眼罩紧封,整个人被勒绑成一尊雪色的胴体囚像,跪伏于黑衣“刺客”脚边。
她喘息轻乱,鼻尖薄汗,仍努力保持着最后一分“挺拔”的仪态——可她的乳早已被勒涨得又红又肿,股间缝滑得贴绳发亮,身体早不是她能完全掌控。
她看着眼前这个跪伏的女人,那个一手长刀、敢独挡一面的霜华姐姐,如今肉身绷亮地跪在脚下,像一头温顺却仍在微颤的雌犬。
她眸光一寸寸在霜华身上游走:那挺得高高却因力竭而微颤的乳团,那绳缝中渗出的淫液痕迹,那无法张口却发出哀音的红樱口衔,那仍在努力挺直的后背。
怜月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刻意假装的怜香惜玉,而是一种藏了太久的、终于能够亲手揭开的渴望与掌控——
至少在这个马车厢里,不,从现在开始,
「她永远都是我的姐姐了。」
她曾幻想过许多回——
幻想这个冷得叫人不敢靠近的女人,被脱得精光,戴着枷锁,跪在自己膝前,像一只困兽变成的宠奴。
她想让她低头,想听她说“妹妹饶命”,想看她那双杀人的眼、那把护她五年的刀、那种不容亵渎的清冷,一点点在她唇下溶解成热汗、鼻音、奶水。
她仿佛看见了自己深夜反复意淫的画面,终于要成为现实。
“……原来你真会这样喘呢。”她低语,几不可闻。
话一出口,她才意识到自己又说漏了。
声音太低、太黏、太贴近欲念。
她不该那样说。
不是现在。
霜华还没被彻底“交货”,这出戏才刚刚开场,她不该……提前表现出这种过于露骨的贪欲。
她顿了顿,目光从霜华汗湿的脖颈移开,仿佛要矫正自己的姿态。但那句脱口而出的呓语,像个钩子,从她舌根勾到小腹,再往下绷紧了她整根脊梁。
她呼吸轻重不稳,胸膛微起伏,脸上努力维持着“姐姐我不过开个玩笑”的镇定,却早已无法把持那节节逼近的渴望。
她从小仰望、从小害怕、从小仇恨、从小迷恋的那个姐姐,如今手脚缚住、口不能言、眼不能见,乳珠红透,鼻音呜呜地就跪在她的脚边。
她再也忍不住了。
“姐姐……”
她换上那副“惋惜又亲昵”的口气,慢慢靠近,膝盖轻轻一弯,伏身到霜华背后。
霜华听见她的呼吸靠近,带着浅浅的温热,若有若无地扑在肩颈之间。她一动未动,只以为——怜月是心疼了,还愿为她松一松口衔、取一取眼罩,让她喘一口气、歇一歇神。
她没有抗拒,反而在那气息贴近的瞬间,极轻极缓地向后靠了靠,将肩背露了出来,颈项也微微一仰。
那姿势既无防备,也无挣扎,像是一种沉默的接受——甚至,带着几分误会中的温存,几分认命时的安静顺从。
直到那指尖轻轻的覆在霜华裸露、泛红、被绳勒得圆胀得快炸开的乳上——
那肉实在太软、太热、太烫,像是怒极之下的身体,在任人把玩前的最后一丝硬挺,被她两指轻轻一夹,顿时挤出一圈细汗珠。
她那对乳,是练武者才有的锋挺,是天生淫骨才长出的丰腻,如今却全被绳子勒成一副随捏随动、随揉随涨的样子。
她轻轻一捏——
乳肉像是挣扎了半寸,肌肤抖了一下,却最终绵软地滑出指缝,温顺得像在邀宠。
“唔呜!……”
霜华下意识一抖,肩膀轻缩,“呜”地一声低哼,从口衔后溢出,鼻腔带着一连串破碎的软音。
她本已被黑绫遮眼,可那瞬间,眼皮下的瞳孔还是骤然一缩,仿佛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情绪在幽暗中炸开——错愕、不可置信,甚至是一丝细微到几近无法察觉的……恐惧。
“马上就要分别很久了……你要被送进香榭替妹妹当‘货’,我却只能留在苏家守局。”
她轻轻抚上霜华肩头,像是在安慰:“姐姐,你说,我是不是该……”
“先替这香榭试试货色?”
霜华浑身一紧,她下意识地微微摇头,“唔唔”含混着发出否定哼声,语气急促,破碎,几近哀求。脖颈上的项圈随之作响,银链微颤,像是无助挣扎的小兽尾巴,摇得轻而急。
不,不可能。
她知道怜月生性狡黠,有些乖张性子,偶尔耍赖、偶尔撒娇,可她始终是自己一手护大的孩子。哪怕有些偏执、有些怨怼……可她绝不该——
绝不该用这种语气,说出那样的话。
她想斥、想骂、想挣扎,想像以前一样训斥怜月不知礼数、守不得规矩,怎可说出这般媟语——
可身体比她还诚实地先一步颤抖了,像一只失去牙齿的猛兽,在陌生的地盘喘息。
“不用紧张呀。”怜月温声哄她,唇贴在她耳后,舔了一下她沾汗的鬓发,语气里带着几分笑,“妹妹我又不是外人……肥水,总不能流了外人田,对不对?”
“第一次嘛…怎能便宜了那些香榭里的粗手笨脚的嫖客?”
“姐姐现在这样……真的,好可爱……可爱得让我、忍不住了……”
说到这,她忽然露出一点扮可怜的表情,声音黏软下沉,像小时候挨训时低头撒娇求原谅: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想抱你、亲你,可你总凶我……现在机会难得,你就……原谅妹妹这一次嘛……”
“就这一次。”她眼神含着笑,像是哄,又像是哀求,“姐姐别生气……让我玩完了,我就乖。”
她说着,一边轻轻把霜华往怀里搂。
霜华脑中一片嗡鸣,想挣、想避,却只能喉中哼着娇软喘音,被红缨口衔堵得死死的,说不出一丝威胁。她的身子轻颤,想要摇头,奈何全身被捆、力气封断,只能微微缩动肩膀,像在求饶。
“别乱动嘛。”怜月轻轻按住她,“车厢晃得这么厉害,姐姐这样一扭,绳子都勒进肉里啦。”
她轻笑了一声,忽地从身旁香囊中抽出两根细细的绛红绳丝。
“既然姐姐老是乱动……”她手指轻巧地拨了拨霜华被勒得鼓胀的乳珠,“那就别怪妹妹想点小巧思……帮姐姐‘规矩规矩’啦。”
霜华骤然一惊,似是意识到什么,身体微微挣动。
可苏怜月动作极快,已经将绳绕过她的一侧乳珠根部,缓缓打结,再绕向她另一侧白皙的大脚趾。
那脚趾因紧张而轻曲,肌肉还带着刀修之人的一分收敛力量,怜月却笑吟吟地抚了抚她脚弓处那薄汗润泽的皮肤,低声呢喃:
“姐姐的腿功最好,记得小时候你一个腾身上屋檐,我吓哭了一整夜。”
“现在……你要是再乱动,被你那脚一抽,这乳儿可就——”
她故意一收绳,乳珠顿时被扯得前突一分,鲜红如豆,盈盈战栗。
“唔呜……!”
霜华猛地低头,鼻音一声哀啼,眼罩下泪光闪动,乳珠颤动不止,脚趾却不敢再动一分。
“乖嘛。”怜月轻柔地将另一根绳也绕上另一边乳珠与脚趾,动作熟练得像在绣一朵绣球花。
“这样你就安静了……乖乖跪好、让妹妹抱着,不乱踢、不乱逃。”
“你若真怕痛,就好好听话,不然你那双宝贝脚,就得自己把你这对奶给牵下来。”
她抚摸着那根被拴起的乳绳,轻轻一拨,那根细细的绛红绳丝仿佛有了生命,在霜华胸前一颤一弹,乳珠便被勒得发胀泛红,像极了熟透的果实,被人轻轻拉扯着等着滴汁。
霜华轻“呜”一声,肩膀微颤,却还未真正察觉其厉害。
直到怜月故意在她脚趾边拽了一指宽度,拉紧绳结。
“唰——”
一阵微痛自乳头陡然窜起,像火星坠入雪湖,炙得霜华猛地抽了口气,整条腿本能地往回缩——却只是更悲剧地拉动了脚趾,那脚趾一弯,绳子猛地牵住乳头。
“呜啊……!”
她闷哼一声,整个人往前一倾,乳珠被绳拽得一扯一缩,那根雪白挺拔的乳被瞬间扯成了向下坠落的弯月形,红豆般的乳尖被绳子勒成深红,边缘都微微渗出一圈淡淡的汗膜。
“疼吗?”怜月在她身后轻声问,语调温柔得像在哄睡婴儿,指尖却不肯放松。
她又轻轻拨了一下绳结,那小小的乳珠再次被牵得往上跳了一寸,像是被弹起的樱桃,在空气中微微颤颤。
霜华“唔唔”地哼出几声,鼻音娇软,头埋得更低了些,脚趾蜷缩,膝盖往内并,像想遮羞,又像是怕下一次被牵出更重的痛楚。
但雪颈上的那道箍压制了她所有的反抗。
她越想往内收,腿绷得越紧,脚趾牵得越狠,乳头拉得越紧,连带着整团被勒涨的乳肉都在不住颤抖,汗光在皮肤表面泛起晶莹湿光,衬得那对雪团愈发淫靡。
她低笑,手指顺着乳绳根部抚摸过去,在乳下那一点皮肤与绳子交错的地方轻轻点了点,霜华又是一颤,鼻音中带着几分哽咽的腻意。
“还乱动吗?”
再不敢乱动了。
她身子僵得如弓,眼罩下满是热雾,汗沿着额角滑入脖颈,咬着口衔、缩着脚趾、咽着嗫音,却无处逃避。
“乖。”
苏怜月终于满意了,像驯好了初次上手的小兽,捏了捏她的大腿根部,然后收起了语气的轻佻,换上了那种藏着童年记忆的甜声细语:
“姐姐……你现在……真的好像我小时候偷养的那只兔子啊,蹬蹬乱蹭,我一给它拴上绳,它就只能乖乖躺在我腿上……让我抱,让我亲……让我钻进它肚皮下面,把脸埋在它毛里,捧着它心口,听它喘。”
她唇贴霜华耳垂,轻轻一舔。
“现在……我也想听姐姐你喘。”
她的手缓缓探上霜华双乳,指尖微凉,落下的却是慢而稳的力道,按住、揉紧、再一点点将那被绳勒住的肉团从缝中挤出,红润胀软,如绽开的花苞。
她按得小心,捏得轻缓,每一下都似在试探力道,不敢太猛、不忍太粗,唯恐按疼了似的——
她平日里对那些香榭侍女残酷乖戾,罚得毫不留情,可唯独这位“姐姐”,却像刚刚得手的心头好,连揉都舍不得太用力。
不是怕她疼,而是怕——一不小心,就弄坏了。
“嗯——!”
霜华猛地一颤,鼻音中第一次带出一声娇腻的哼泣。
怜月凑近,唇贴霜华耳边,嗅着她汗气夹杂的乳香,吐出温热气息:
“你看你……光是这么一捏,就叫得这么动听……”
霜华听着那熟悉却变调的声音,喉咙被口衔堵死,说不出任何话,只能发出低哑的“唔唔”哼声,颤得连手指都轻抖。
怜月笑了。
她伸手绕到霜华身后,双手从绳索之间探入——
那是一双纤指,却像水蛇般钻入勒紧的绳间,探进她后背、腋下、腰侧、直至臀缝。
“这里勒得也紧……是不是已经湿了?”
她话语未落,手指便点到了那一线早已濡湿的缝间。
“唔……!”
霜华身子一颤,腰背猛地紧绷,膝盖抵地几乎滑动。那一指仿佛电击,激得她连鼻音都走腔。
“真的湿了呀……”
怜月眼神越来越亮,轻轻拨弄那被绳勒出沟壑的蜜缝,指节揉进那已湿得发黏的缝内,缓缓一揉一捻。
“这么敏感……才绑了一刻钟,姐姐就已经开始渴了?”
霜华狠狠摇头,羞怒至极,可每一声呻吟反而像娇喘叫床,每一次颤抖都像迎合,双腿拼命收,却绳索勒得越紧、蜜液越流,缝间甚至已能听见“啵啵”的淫靡响声。
怜月捧起她下颌,在她耳边轻语:
“我就玩一下……一下就好……姐姐就当是习惯习惯,被人调教的感觉嘛……”
手指从蜜缝探入,先是一节,然后缓缓深入,指节弯曲在她体内拨弄。
“呜啊……唔唔!唔……呜呃呃……”
霜华整个身子僵住,一瞬仿佛被雷击,双腿猛地绷紧,那两道细绳应声收紧,勒在乳根的绳结被牵得猛一抖动,乳团乱颤如浪,蜜穴一阵阵痉挛收缩,竟止不住地涌出滚烫蜜液。
“姐姐真好色,才刚进一指……里面已经在夹我了。”
“不过呀,被姐姐这样迎着夹着……妹妹我,也会忍不住开心呢。”
她话音未落,又一根手指缓缓探入,两指并进,轻轻一捻。
霜华想要抽逃,却全身封穴,连腰部肌肉都软得像被抽空,只能在怜月的掌中战栗,像一尾被剥皮的鱼,滑嫩得无处可逃。
“唔呜……唔唔……!”
她喉中呜咽不断,口衔阻音,牙关死咬却止不住呻吟漏出。双腿想夹,却一动便牵扯到那绕乳连趾的绛红细绳——乳根勒处顿时收紧,抽得她生疼;想踢开,更是寸步难伸,反倒让胸前雪肉被带得又紧又颤。只能无助地张着,任那对细腻的手指在穴口中一探再探,一搅再搅。
怜月低头看着,眼神里不再有半分妹妹的怯意,而是一种病态的柔情与恶意的怜惜。
“姐姐这里……好软,又好紧……”她边说边探入更深,手指一勾,顶开一处深处的嫩壁,那道肉褶像是从未被人触及过的禁地,被这突如其来的顶弄勾得一阵痉挛。
霜华“唔啊”一声,双乳随着痉挛猛地抖起,汗珠从乳沟顺着红绳滚下,混着皮肤上的蜜液闪着淫光。她拼命想要扭开腰,却只是将穴口那两指夹得更紧,反而像在主动含住那羞辱的侵犯。
怜月笑了笑,手指抽出半寸,再缓缓插入,抽插的动作不快不猛,却带着令人发疯的节奏,每一下都像要把她最深处的脆弱一点点撬开。
“别夹这么紧嘛……”她语调轻媚,手指却忽然加快抽插,一下、一下、一下,淫液被搅得粘稠响亮,车厢内都是“啾啾”“咕叽”的水声。
霜华早已泪满面罩,呼吸破碎,腿根剧烈颤抖,蜜穴抽动不止。
“唔啊……唔呜呜……!”
她每想挣脱,穴口便回吸得更狠,像是那羞耻的洞口已不是她能控制的部位,而是早被“妹妹的手”调成了肉腔器皿,只知道迎合、吞纳、渴求。
那两根手指越捻越深、越插越快,抽送间带着粘腻水声,霜华原本咬紧的齿根开始松动,背脊发紧,腹部痉挛,她的意识在那一瞬开始断裂,羞耻、痛楚、愤怒与快感交错如潮,层层叠叠,将她向着深渊推去。
直到那最后一下——
“嗯啊啊……!”
她发出第一声无法压抑的高潮叫喊,娇啼从口衔缝隙中迸出,断断续续、婉转入骨,宛如玉女破戒,痛恨之中夹着快感的绝望。
霜华喉间呜咽不断,口衔吐不出词,眼罩下泪水模糊,腰身扭不过一分,腿抬不起一寸,只能被妹妹从身后勾着玩弄,指尖每一下按在私处都带着羞辱的温柔。
“唔……唔啊……唔唔……”
而她的妹妹,正低头含着她乳尖,用舌尖卷起那被绳勒得高耸挺立的乳珠,一边舔一边喃喃:
“姐姐的雌汁又腥又香……姐姐不再是那个拔刀见血的冷霜华了,而是我的乖狗狗了……对吧?”
霜华浑身颤抖,眼下涌泪,口中娇啼不休。
她从未想过,自己这一遭的第一劫会是这样来的。
不是仇敌的折辱,不是淫器的惩罚,不是香榭老鸨的调教,而是……怜月。
她从小捧在手心的妹妹,她以为始终柔顺单纯、始终仰望自己、愿意为自己低头含泪的“怜儿”……竟用这种方式逼她低头、让她浪叫,让她高潮,叫她一滴不剩地在自己手中洒尽侠气。
「我……居然……在她手里……去了……」
她内力被封,连羞愤都无法完整聚起,只有那一股酥痒与战栗穿透绳缝、穿透骨髓,让她像一滩被玩熟的软泥,被妹妹操控着潮起潮落。那道蜜封的嫩鲍,正被一指一按间逼出淫水,那对曾为江南风月传名的腿,如今只能岔开供玩,连夹一下都做不到。
霜华心底忽然泛起新的恐惧,不是对辱的恐惧,而是对这份病态情意的惊惧。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名为“妹妹”的苏怜月,从来就不是躲在她背后的柔弱羔羊,而是……潜伏在她脚边的豺狼,温顺不过是舔舐的舌,顺从只是等着扑上去咬住她脖子的姿势。
而现在,她被咬住了,被按在车壁上、用蜜水湿透的腿间、用羞耻灼红的乳尖,一点一点——吞进了那个叫苏怜月的少女怀中。
第一次泄身之后,霜华便再也无法分辨车厢内的光线。
可她知道苏怜月食言了。
明明方才还软声说着“玩一下就好”,此刻却全无要停下的意思。那双从小被她牵着走过雪地石桥的手,如今却时而抚发、时而温柔地揉着乳、时而探向她腿间早已被蜜水泡软的花缝,揉着她高潮后的颤抖,像是调教一只不会反抗的猫,玩累了便哄,哄软了便玩。
不知是第几次被奸到蜜水横流,她已彻底分不清时间、方向与尊严。她只记得自己曾是冷面女侠,杀人不眨眼、拔刀不回头;可现在——她跪趴在马车软榻上,被妹妹两根手指来回揉弄,肏得双腿打颤,腰软舌乱。
几根手指,就能把她逼到高潮,逼得她哭,逼得她呻吟着在亲妹妹怀中撒娇求饶。
她不记得自己呻吟过多少声,只记得每一次高潮都更耻于上一次,每一次乳尖都被舔得更挺,每一次穴口都被玩得更湿。
她甚至不再挣扎——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挣也无用。
“唔呜……啊……呃嗯……”
那一声声娇啼未歇,却已主动将脸埋进苏怜月怀里,发丝凌乱、汗湿香颊,一下一下地蹭着她胸前柔软的乳袋,带着余韵的软媚与本能的依恋。
她愣了一瞬,然后笑了,笑意从眼底漫出,再藏都藏不住。
——就是这个模样。
她梦了无数遍的姐姐,就是这个模样:满脸潮红地缩在她怀里,一边流着淫水,一边蹭着她胸口轻轻呜咽。她梦中梦见过的,梦里伸手都抓不到的,如今就这样软在她怀中,哭着、湿着、喘着,全身都在渴着她的指。
她眼神灼亮,唇角忍不住上扬,那原本柔怯的笑意,逐渐变得病态、贪婪,像个得了糖的孩子,却偏要把糖一点点捏碎再含进嘴里。
江南拂晓,天未明,城边旧路轻尘初起。
那辆黑漆马车一路驶过碎石土道,车身微晃,每一步马蹄落下都夹着一声奇异的——“唔啊……唔唔……呃啊……”
不是风,不是鸟,是低低压抑的女人呻吟。
蹄声咚咚,呻吟软绵绵地拖尾。
马车内,烛台早熄,窗帘紧闭,却满是淫靡潮热。
苏怜月脱下刺客外袍,跪坐于霜华身后,怀中满是香汗淋漓的姐姐。
霜华那一身白雪似的肌肤已被汗与蜜打湿,脸颊潮红得仿佛烧灼,红缨口衔湿透,垂落下透明的涎丝。她被绳索捆得紧紧,胸脯早已被勒涨如熟桃,蜜缝泛滥,滑腻得几乎滴水成珠。
那绳缝之间,每一次摇晃都在碾压敏感;那项圈牵链,每一次低头都像主动求抱。
她整个人瘫在车内软垫上,双膝蜷着,银链落地,脚尖打颤。蜜液顺着腿根蜿蜒,浸湿了垫毯,连车厢木板都光亮一片,散发出热蒸蒸的淫香。
苏怜月舔着她耳垂,呢喃如鸦羽:
“姐姐已经习惯了呢……这才几炷香,你的身子就自己学会怎么浪了。”
“好乖……姐姐习惯了…下次就不会这么痛了。”
霜华轻哼,喉中堵着,鼻音发颤,“唔唔唔……唔呃……”
她下意识想反驳、想挣,可一动腰、脚、胸,绳道收紧,蜜缝被剐得更深,反倒“啪”地喷出一股热潮,沾满马车壁。
这一路,早已不知被苏怜月玩去了几回。她的意志在淫浪中摇晃,尊严仿佛被一根竹枝不断削片,薄至透明。
忽然,帘外传来白蝶娘懒洋洋的笑声:
“江南城快到了,该收收心咯。”
苏怜月眸光微动,忽地起身整衣。
她望着霜华那副满脸潮红、乳胀绳勒、蜜汁淌腿的模样,唇角缓缓扬起,心头突然生出一个更香的念头。
“停车。”她轻轻一挥手,“离香榭还有两条街,停这里。”
白蝶娘一愣,随即会意,笑得媚得发腻:“小姐这是……不舍得放姐姐‘轻松进门’啊?”
怜月笑而不语,只是柔柔地将手掌抚上霜华汗湿的后背,顺着那被捆得凹凸毕现的脊线轻轻划过,语气娇怜,语意却带钩:
“蝶娘,你是明面上的‘交易人’,这又是香榭里的马车。若你我共乘此车入城,被人瞧出了破绽......可就不好收场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捏了捏霜华绳下那被玩得挺翘的乳尖,指尖轻巧一绕,解开了牵连足趾的红绳。唇角微弯,笑得分外无辜:
“所以呢……我们得下车步行入城。”
她话音微顿,眼波却未曾移开霜华那早已湿透、绷紧的裸躯,声音更低了些,像是在劝,又像在哄:
“况且...姐姐这副模样…香汗淋漓、气若游丝,最合演‘被抓来的贱妓’的角了。这若不让人瞧上一眼,别人还以为我们装得不够真呢?”
车停。
霜华浑身一震,眼罩之下神情恍惚。
她不知道还要多少人见她这样——见她如狗似奴,被妹妹牵链提走,像头牲口,香汗满身、淫汁遍地地走入青楼。那曾踏断雪岭、御风跨舟的双腿,如今却在发软,连脚尖都因高潮后的脱力而蜷缩成屈。
这时,苏怜月忽然俯身,语气温柔得近乎体贴:
“姐姐要走这么远,怎么能光着脚呢?这路石板又凉又硬,万一把姐姐的脚底磨破了……多可惜。”
她一边说着,一边掀开车帘向白蝶娘投去一个眼色。
白蝶娘立刻会意,从怀中取出一双做工极艳的鞋。
那是一双高跟细齿的软底小履,鞋身上绣着并蒂春蝶,色泽绛红,鞋尖细削如钩,鞋后挂着一串银铃,轻轻一晃便叮铃作响,清脆悠扬,媚意十足。
白蝶娘一边将鞋呈上,一边慢条斯理地笑道:
“这叫‘步音奴履’,我们香榭头牌个个都得穿。响得远,走得慢,铃一响,整条街都知道——‘好货来了’。”
她伸手,轻轻握住霜华那只沾满蜜汗的脚踝。
霜华骤然一颤,脚趾本能地往里一缩,似是要挣脱。但那挣扎太轻太短,几乎刚刚抽动,便又瘫软落回掌中。
她实在没有力气了。高潮未褪,羞耻正涨,那对脚——曾以“江南第一轻功”著称的足尖,此刻却只能像被捉住的兔子蹄,湿滑滚烫,连反抗都带着呻吟。
白蝶娘轻轻抚过她足背,指腹缓慢而淫靡地揉了一圈脚心,再捏了捏她屈缩的脚趾,一根一根将其掰开,才将那只精致小履缓缓套入。
那鞋窄如花匣,霜华的足骨本就修长,鞋尖紧裹,足弓高耸,穿进去之后被强迫抬起脚跟,只能用脚趾点地,一步一步地摇摆前行。银铃贴肉,随她每一次颤抖轻响两声,清脆得几乎像嘲笑。
第二只鞋也套了进去,白蝶娘按着她足跟将其稳稳压进鞋底,扣好银扣。
“……这才像了。”怜月轻轻拍了拍霜华的足背,目光顺着绳缚之腿一路滑上。
霜华的双脚此刻并膝而跪,鞋尖贴地,银铃悬垂,足趾绷起,像是随时等待被牵走的娼奴。
“别怕嘛。”苏怜月拿出那根小时候霜华经常用来抽她的竹条,在她绳缠的腰眼轻轻拍了一下,“只是让你先走几步‘适应场景’。”
她笑意温婉,指间竹条却不容人拒绝。
“来,乖狗狗,跟主子下车——”
说着,她扯住项圈的牵链,向前一拽。
霜华身子一颤,跪姿滑动,膝头在绒毯上拖出一道痕迹,被迫向车门一点一点地挪去。铃鞋叮哐作响,配合牵链发出的细脆金属声,像牲畜出圈,被拖至屠场。
“啪啪——”
竹条抽落在圆臀两侧,那肉被勒出纹痕的臀瓣被击得飞颤,乳也跟着绳索晃起,弹得一串乳浪。霜华呜咽一声,舌被压住,只能喉中发出哑哑的啜声,似痛似颤。
车帘被掀开,一缕街头的冷风灌入密室。
她的膝盖软得几乎碰地,脚跟高高踩在“步音奴履”之中,脚趾点地而立,身形被迫挺直。铃响入街,空气清冷,汗与蜜在腿根悄然凝固。
她站不稳,被项圈链子牵着才勉强立住,脸被白巾裹得看不出神情,只有鼻尖泛红,唇角有银丝溢出,脚下铃声在青石板上轻轻摇响。
苏怜月轻轻理了理她额前汗湿的碎发,低声笑道:“姐姐乖,记得走得慢一点,要让路边的人好好看看‘这新货’值不值。”
车前的蝶娘早已脱去黑衣,扮回了风尘之妇,妆浓色艳,鬓边插花,立在车旁掩口笑:“啧,好一个俘虏……今儿香榭怕是要迎来贵货了。”
白蝶娘这时向她微一拱手:“不打扰姑娘雅致,奴先行一步,去香榭打点收货事宜。”
“别走太快。”怜月语带双关。
“放心。”白蝶娘回眸一笑,“奴自然会在门口‘验货’的……到时叫那些客爷都瞧得清清楚楚,这是谁家的俏肉。”
她说着一甩烟袖,转身上马融入街市中。
江南清晨,城门初启,街巷还未喧哗,只有偶尔挑担赶集的脚步,在青石板上拖出些轻响。
可今日,一道不寻常的身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前头是一个女子,虽裹着黑袍,却高挑冷艳,风姿婉然,乍一看像是谁家小姐早起赶路。
可问题在于——她身后“牵”的东西。
那不是牲畜,也不是货物,而是一个被赤身绑缚的绝色女人,跪步而行、脚穿高跟,项圈缀链,被银索牵着缓缓前行。
她戴着黑布眼罩,口中衔着红缨丝绫,白纱微盖,整张脸只露出一小截鼻梁与发红的耳尖;一身白腻绳缚,自胸至腹,从腿至腕,每一寸皮肤都勒得微凸、泛红,仿佛特意为展露肉感而缠。
步音奴履在青石地面上咔哒咔哒作响,细而脆,像调情般地响亮。
那铃音轻快,一响一摇,恰恰与她双乳晃动的频率重合。每一步,她胸前那对被勒高的巨乳都晃得乳根泛红、乳珠微透,蜜腿间夹着滑腻之痕,香汗淋漓,如同打了蜡的肉雕在晨光中莹润生光。
那样的身材,那样的皮相,哪怕被捆着,也艳得夺目;哪怕低着头,也色得犯规。
可她那步伐……依稀还带着一分侠骨旧姿。
脚步仍稳,背脊不弯,每一挪移都像是在试图保留某种最后的“气节”。可那链索一拽,她便只能低头;竹条一抽,她便只能哼泣。
这份“欲挺不成”的矛盾,反倒让她更像一尊刚刚被驯服的淫奴——反抗的影子还在,屈服的痕迹却已烙骨。
有个早起卖茶的老汉目光愕然,喃喃道:“那……那是人?”
旁边有挑水的年轻汉子咽了口唾沫,小声说:“像个娘儿……可这身子……我他娘的从没见过这么俊的骚货……”
“她是被谁玩成这样的?是哪家青楼的头牌?要不要命了?”
更有几个看着像下九流混子的男子,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被勒得发紫的乳尖与绳缝之间的淫液,低声嘀咕着:
“这要是我弄到手——干三天都不放她下来。”
“听说那种鞋是步音奴履,香榭里的——能穿这个的,不是贱奴就是淫品。”
“呸,这骚货也不知做了多少人的狗了。”
众人不敢上前,甚至不敢大声调笑,因她被牵的模样虽淫,但那背脊线条仍透着令人不敢轻近的“冷杀气”。
可她低着头,被链拴走的模样,却又叫人不由自主地意淫她被翻在青楼床上叫到失声的画面。
越想,越不敢看。
越看,又越无法移目。
而此刻的霜华——
她走在青石板上,听着那清脆的“咔哒”声从自己脚下发出,听得自己每一寸皮肤都发麻。
那些鞋跟踏实地的声音,每一下都像锤在她心口。
她知道——苏怜月这是在公报私仇。
从小她就对这妹妹最严、最冷,每次犯错便抽她手心、罚她跪堂,哪怕心疼,也从不放纵。而如今,她竟在她手中,被拽成这副“狗一般的贱奴模样”,一路牵走,步步皆辱,众目睽睽之下如肉般展示。
她知道这其中藏着怜月的怨、她的恶意、她压了多年的渴望与不甘——
可她忍了。
因为她是姐姐。她必须护着怜月,不论她做了什么。
但她却不理解,马车上为何怜月又会展现出如此贪癫的一面。
作戏能演成那幅模样吗?
不过此刻她已经无法去思考这些问题了。
她只能听见耳边行人的喘息,听见他们的目光落在自己乳上的热度,听见蜜液从腿缝滴下的水声混在那“哒哒”中,交织成一曲羞耻的朝歌。
她双腿一软,几欲跪地,可牵链一扯,强迫她“站好”。
羞。
羞得她想咬舌、想闭气、想碎成尘土。
可最羞的不是那些目光。
最羞的是她的身体。
她的蜜缝仍在一颤一颤地收紧,仿佛链条的每一次牵拉,都会让那被绳勒的下体微微抽搐;乳尖依旧高耸,顶着绳缝向外鼓起,凉风拂过,都像是在催她挺得更傲;那高跟淫履下的腿根,一滴、一滴透明的蜜液,正顺着内腿蜿蜒而下,踩入鞋底,弄湿她那双银铃作响的妓奴之履。
她高潮之后,竟仍在渴着、热着、湿着。
不该是这样的。
她明明恨极了自己这个样子,却更恨——这副身体竟已不由她掌控。
“呜呜……唔呜……”
她发出极其细碎的啜泣,红缨口衔堵着,反而让那些抽泣声听起来像是勾人的娇吟。
“姐姐……”
苏怜月忽然靠近,在她耳边柔柔地说,带着一丝假惺惺的歉意:
“对不起哦……没想到这条街……人还挺多的……只能委屈姐姐多忍一忍这一段。”
“不过……姐姐这么好看,让大家欣赏欣赏……也没什么不好,对吧?”
她伸手在霜华臀上的红印轻轻抚了一把,又拍了一下,故意弄得屁股一颤,乳珠前挺,淫液飞弹。
“再走一条街,就到香榭啦。”
终于,待到天光破晓,第一缕晨日洒落在香榭朱红门扉之上,照亮了那一幕异样至极的场景。
那是一个女子——
被绳缚、赤裸、戴口衔、蒙眼布、乳肉勒涨、蜜腿淌汁,穿着叮铃作响的铃履,被牵链拽着跪在青楼门前。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茶摊老板,过巷书生,晨起挑担的汉子,巡逻未散的小兵,香榭的老妓、杂伎、买香的贵客……都止步观望,面色各异,有惊、有窃喜、有羞、有热。
苏怜月轻轻一扯牵链。
“姐姐,观众越来越多了,可别让他们失望了呢。”
霜华身形一紧,绷着想稳住脚步,未料那牵链忽然一勒,她重心一歪,脚下一软,竟毫无防备地“扑通”一声跪倒在香榭门前。
“叮哐。”
银链坠地,铃音碎响,空气中淫香四溢。
霜华跪在门前,脸贴青石,香汗淋漓,乳贴地颤,银链坠地作响,蜜汁自腿缝滴落成线,在她跪拜的地面渍出一圈淫晕。
苏怜月俯身,唇角噙笑,嗓音温柔却不容拒绝:
“既然跪都跪了……那便乖乖地,爬进去吧。”
霜华闭着眼,在眼罩黑暗的世界里默念:
「无人在此认得我…只是观个贱婢而已…」
她抬起膝,往前一爬。
「怜月……不过是多年怨气难消,借势发作罢了。」
又一爬。
「权当逢场作戏,不可误了正事。」
石阶冷硬,膝骨擦破,肌肤红肿,乳在地上晃着、抖着、垂着。她脚尖在奴履中蜷缩,铃声响得像凌辱的乐章。
苏怜月轻笑着:“姐姐好乖,再三阶就到了哦。”
就在那第三阶的门槛前——
香榭朱门缓缓开启,白蝶娘袍袖拂地,似笑非笑:
“呦,货来了?”
那是白蝶娘,缓步而出,手持绢扇,腋下红绸荡漾,媚眼一挑,身后立着四名妓娘,皆衣着艳俗,眼神轻浮。
“行了,上手。都按我说的来——今天可是头一回,旁人看着呢。”
霜华原本只以为是“入楼前走一遭戏”,从未想过竟要在门前被——验货。
她骤然僵住,膝步一滞,脑中嗡的一声炸响。
「不、不可能——她们不会真的……」
可那两名妓娘已一左一右上前,笑吟吟地探手而来,动作娴熟却不容抗拒。一人按住她反缚的手腕,将绳索更紧勒入皮肉,另一人则顺势扣住她肩背关节,猛地一提!
“唔——唔啊!!”
霜华陡然惊叫,口中衔物阻声,却仍发出细碎而破碎的娇啼,眼罩之下双目猛睁,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感觉身体被吊起,失重感从脚底涌上脑海。
她还未来得及挣扎,腿根已被人从两侧架开,一股寒风掠入蜜缝,带着微凉将她最隐秘的热处吹得颤了一下。
“唰——”
随着最后一根绳索扣紧,她整个人被吊成弓形——
胸朝天,腿分开,蜜穴大张。
她悬在门前廊柱之间,头低脚高,项圈牵链微晃,淫液从臀下滴在香榭门板上,发出一连串水声滴答,像春雨打池。
“唔唔……唔啊……呜……”
霜华惊骇欲绝,那一瞬羞辱几乎炸裂全身,血气全冲上眼眶——她根本没想到,怜月居然真的允许她在门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吊起来、被当牲畜验货。
她拼命扭动,却越扭越晃,乳在空中一抖一抖地弹,腿间蜜肉在晨风中微微收缩,淫液却偏偏更快地流下来,像是羞耻把她的体温逼到了沸点。
街边的围观者屏息静气,不敢上前,却不自觉地靠得更近几分。
她不知自己是在哭、在喘、还是在呻吟,只觉得嘴里的衔物越来越软,越来越咬不住了。
“来,先查肉性。”
一妓娘用紫藤尖条挑开缠在霜华大腿上的绳扣,缓缓滑至耻丘下,绳一拨,蜜肉弹出,粉嫩颤抖,淌得满手香滑。
另一妓娘笑着接了条羽刷,在霜华蜜缝上轻轻一刷,从珠尖扫到穴口。
“呜……唔呃……嗯呜……”
霜华猛地挣动,口衔中发出失控的呻吟,胸乳在空中晃得快飞起来,眼罩下泪水直涌,嗓音却只剩娇喘。
“啧。”白蝶娘摇着扇子笑,“这反应不错,触感新鲜,骚得有潜力。”
“来,试探入肉程度——看她到底得从哪一步‘训’起走。”
妓娘从香榭门边提来一小瓶檀木浸油,一滴滴落在霜华臀缝、乳根、肚脐上,然后两指蘸着油轻探进蜜穴,一探便入,两探便颤。
“咕啾——”
霜华整个人抖如筛糠,双脚绷直,高跟奴履在空中乱颤,手腕挣得红痕透骨,蜜穴却死死夹住那两根探指。
“唔唔!呜呜啊啊……呃呃……”
她哭了,叫了,身子乱抖,连链子都抖得叮叮当当响,蜜液像被挤破了穴腺,从肉缝深处喷涌而出。
白蝶娘懒洋洋一笑:“这叫‘假抗真浪’。看着还在挣,其实下面早学会享受了。”
“她这肉……再上三堂课,便能听声便浪,闻香便湿。”
那妓娘微微一用力,指节弯钩,“啵”地一声从她蜜肉深处扣出,带出一汪浓黏汁液,飞溅至廊柱上。
霜华,彻底恬不知耻地高潮了。
她头仰背弓,全身痉挛,口中呜咽变作喘叫,连白巾被咬出齿印,蜜穴张合不止,淫水混着汗水滴得地板一片狼藉。小腹一抽再抽,涌出的蜜液从大张的穴口淌成一线,滑过腿弯、坠下鞋尖,铃铛也因抽搐连连作响,如春夜风声叮咛不歇。
她连昏厥前最后一声喘息,都是带着软媚鼻音的“呜啊——”,像是婊子破了身喊出的头一声浪叫。
然后她昏了。
媚肉悬挂轻晃,双乳因力竭而微颤,乳头仍挺未软,腿绳仍勒未松。头垂至胸前,双眼翻白,唇角余涎未褪,宛如献祭之物般被悬在香榭门前的朱漆廊柱之间,供人观赏。
她曾手起刀落、快意江湖,如今却被人牵着银链拖下马车,吊在青楼门口,当街张腿泄蜜,连一根指头都未能抬起抵抗;她曾誓死不辱、不屈不媚,而如今却当众高潮,淫水如雨,面罩下喘成一头乖顺淫犬。
白蝶娘收扇一叹:
“啧,还是嫩。才验一验,就失神了。要调得更久些。”
她一挥手,两名妓娘上前将霜华从绳上解下,横抱进香榭门内,如抱一尊刚用完的观音妓偶,姿势扭曲、肉体软垂、乳臀暴露。
那银色长链还拖着霜华残余的体温,在石板路上划出一道水迹,蜿蜒直至门槛为止。
红门缓缓合拢。
啪——
锁扣合上。
香榭门后,从此多了一条会呻吟的狗。
苏怜月站在门前,终于不必掩饰唇角的喜意。
她抬手,冲那闭合门扉挥了挥,轻声告别:
“姐姐,再见咯。”
“好好听课,莫要偷懒。”
“——妹妹等你,乖乖回来。”

35
3508484180发布于 2025-04-08 00:54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终于等到作者的新作了
mhq020924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红袖发布于 2025-04-08 09:04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写的好棒!
qpf7103发布于 2025-04-08 09:45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大佬这细节描写太猛了,看捆绑跟游街那段画面感已经出来了,头一次看这种题材的,无敌了
mingren101发布于 2025-04-08 15:25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这文笔功力真是赞,可惜不会是我喜欢的黑暗文,还是点赞感谢作者。

35
3508484180发布于 2025-04-08 17:05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作者有没有想过在p站之类的也发一下,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St
stephencurry123发布于 2025-04-08 17:43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期待后续!
大佬的口味还是偏轻的,这次会跟之前的作品不一样么
大佬的口味还是偏轻的,这次会跟之前的作品不一样么
究极足控少女:↑这剧情很赞啊,文笔也不错!催更!
bydaynight:↑大大终于更了,数月不见,当真难熬。
uranusg:↑终于更新了!等了好久,而且也是最爱的下克上题材,赞!
qpf7103:↑大佬这细节描写太猛了,看捆绑跟游街那段画面感已经出来了,头一次看这种题材的,无敌了
红袖:↑写的好棒!谢谢喜欢和评论!
axios:↑大佬的笔力在m站属实是鹤立鸡群。过奖了,我很多桥段也是借鉴m站里各位大佬的
mingren101:↑这文笔功力真是赞,可惜不会是我喜欢的黑暗文,还是点赞感谢作者。没事,感谢点赞,总能找到心头好的文的
3508484180:↑作者有没有想过在p站之类的也发一下,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暂时没有这个打算,感觉就放m站挺好的
stephencurry123:↑期待后续!应该还是经典样板戏hh,不过这次篇幅会略长一点
大佬的口味还是偏轻的,这次会跟之前的作品不一样么

35
3508484180发布于 2025-04-08 23:49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
不太赞成样板戏这个说法,因为剧情不一样,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一个动作,不同的氛围和人都不一样。比如老鼠小姐,就更像那种罂粟的感觉危险又迷人,这本能更多的感受到爱意。然后作者对人物的描写是很细致的
qpf7103发布于 2025-04-09 10:50
Re: Re: 【中篇】【连载中】【4.7 更新第三章】月下霜华怜香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