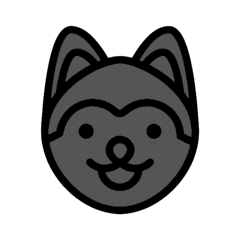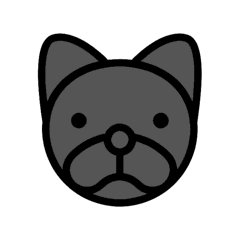皇城秘事番外:烬(短篇完结)100%坏女人,纯BE
袜控短篇原创虐杀窒息气味血腥大小姐
阅前提醒:
本文包含100%坏女人,纯BE,包括且不限于踩踏,血腥,鞭打,气味,窒息等,无法接受请立即关闭。
「来,第一只」
轻轻覆住口鼻处的柔暖裹挟着融融煦煦的温热,依偎拥抱着竭力呼吸的面庞。轻薄如羽的湿润袜身将能吸进体内的气体,截留得只剩寥寥无几的残缕。急促翕动的鼻翼竭力的妄图从细密紧致的细小缝隙中吸入丝丝缕缕,汲取那少得可怜的新鲜空气。
经过潮湿袜身过滤的气味是阿烬已经闻过无数次的味道,是独属于主人的气息,是主人褪下长靴中悄然萦绕的芬芳 ,是混合着皮革的醇厚与主人身上清幽体香的独特韵味,是无需任何额外动作,仅仅是嗅到一丝便能让心底的欲望不可遏制地涨立起来的味道。
阿烬已经记不清曾有多少次,仅是闻着这魂牵梦绕的气味,便让自己双腿酥软沉溺其中。但在主人的“赏赐”并未“许可”的情况下,自己作为爱宠做出逾越赏赐的行为便是重罪。
「第二只」
为了能捕捉到那哪怕最细微、如风中残烛般珍贵的一丝空气,在口鼻处那如薄纱般轻柔的袜身,深深凹陷进阿烬的口腔,即便如此挣扎吸气,进入体内的气体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增加。身侧旧伤似被冰冷寒针插入的刺痛,随着胸廓每一次极其微弱的颤动而扩大。每一丝试图扩张胸廓的努力,都如同撕裂一般疼痛,让阿烬根本无法获取更多赖以活命的氧气。
凭借着侧一侧头的力道,那近乎封死呼吸的袜身便会顺着脸颊滑落,让阿烬重新呼吸到甜美的空气。但是阿烬不敢,也不能,身为 “玩宠” 没有说 “不” 的权利,主人的一切行为都是 “赏赐”。
那被砌死在寝宫楠木椅下面的上一任 “玩宠”便是最好的例子,阿烬不知道那玩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被挑断四肢挖去眼睛,封死在楠木椅下石窟中的那人,“金汁玉液”这唯一赖以生存的食物,也要看主人的心情才能赏赐。
「姐姐要加第三只嘛?」
那娇俏却又透着几分骄纵的声音突兀地响起,这个声音阿烬很熟悉,那是在公主府宴席上传菜时慌乱间打破了瓷瓶时,主人身旁那位王府小姐的声音。
“这莽撞小厮倒也有几分姿色”身穿锦服的王府小姐勾起了自己的跪地磕头的面庞,也正是因此话语,阿烬撞进了主人的视线。
在画舫上阿烬也曾见过这位王府小姐的身影,仅仅是为了向姐妹展示新得的鞭子,便将玩宠生生抽至断气,那凄厉的场景仿佛还在阿烬眼前闪回。还有那偎依在主人耳边,想借阿烬给自己玩两天的说辞,眼神中满是令阿烬心悸的火热。
「第三只也盖上好了」
主人的轻润语气在耳边响起,交叠着盖在脸上的汗湿薄袜却似千钧巨山,每一丝试图钻进鼻腔的空气都被袜身无情截留,能进入身体的空气稀薄得几近于无。汹涌如潮水般的强烈窒息让身体不得不昂起头,仿佛如此便能抢夺一丝活命的空气般。然而越是吸气,那薄袜与口鼻的贴合便越是紧密。挣扎、颤抖,哪怕是幅度更大的动作都不会让带着主人气味与体温的潮湿薄袜有丝毫的移动。
阿烬这名字是外府管事起的。幼时家里被烧,父母双亡的自己在六岁那年流浪到皇城,在冰天雪地中即将冻死之际,是主人将他带到了府里。正巧那天赶上倒炭炉,管事见他可怜,也就单取了个 “烬” 字。
现在喉管中愈发强烈的灼烧感却真似吞炭般,不仅仅是喉管,袜身传来的主人气味让阿烬的身体也似被炭火灼烧般,四肢止不住地发抖,在窒息与欲望的双重折磨下,挺立的情欲不自知的向外留着暖流。但阿烬即便满心渴望抬手拿下脸上这薄袜,也不可能做到。因为自己那无法弥补的过错,主人的惩罚让阿烬早就失去了控制手指的能力,那个待他如同亲儿子一般的老管事,也因阿烬而丢了性命。
透过织物越来越少的空气让缺氧带来的幻觉逐渐实质化,已然充溢着主人幽兰般气味的身体,似是让阿烬眼前的场景又回到了在主人寝宫里接受断指惩罚那天。
金线绣制的繁杂花纹在黑色绸缎长靴上熠熠生辉,看着细长的雕花鞋跟轻轻踏上了手指。金属雕花的鞋跟以指节为支点,缓慢的左右转动,皮肉被剥离所渗出的血液顺着指节侧方淌下,紧接着便是筋膜与坚韧的肌腱,圆弧鞋跟锋利的边缘仅旋蹍半圈便将粘附血肉的洁白肌腱切断,脆弱的骨关节失去肌腱的约束牵引,在公主逐渐施加的力度面前,发出一阵阵心悸的碎裂声后,被下沉的靴根蹍成碎裂的骨片,而这仅是一个指节。
不到一刻钟,左手小指指骨便从关节处被彻底踩断,三节血肉模糊的断指带着丝丝缕缕的肉末与猩红色的血迹,一点点渗进绒毯的绒毛间隙,和地面铺设的绒毯融为一体。寝宫内只有轻微的骨骼碎裂声与男孩的低沉闷哼。
浓重的夜色如墨,从雕花窗棂的缝隙拼命挤入。随着主人重新坐回到楠木椅上,强忍着断指处传来剧痛的阿烬,身体颤抖着靠近面前轻抬的靴子,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舔舐着自己的血迹。靴底那些藏匿在细微缝隙中的碎骨,也被舌尖如寻觅至宝般,一点一点地舔出。
手掌渗出的鲜血连带着一波又一波的痛楚,就在主人轻抬起另一只靴子示意阿烬继续时,眼前宛如被蒙上黑布的身体却是如天旋地转般向前栽倒,晕了过去。
但随即被满是荆棘铁刺的鞭子继而抽醒的阿烬,意识还混沌在剧痛的泥沼之中,迷迷糊糊间,对上了主人方才还有几分欣赏,如今却寒若冰霜的眼眸。那双眼睛冷意彻骨,残存的迷糊也被驱赶得一干二净。
身后的侍卫长扬起手中的鞭子再次狠狠抽在阿烬身上。“啪” 的一声脆响,皮开肉绽,血珠飞溅,阿烬的后背瞬间绽开一道道血痕,挣扎着想要继续舔舐主人靴子的阿烬,却见主人已将轻抬的长靴收回,站起身冷冷地看着自己。
“机会只有一次,子不教父之过,那外府老奴也不必活了”
冷淡声音一字一句都似重锤,狠狠砸在阿烬心上。拼命磕头为管事求饶的阿烬,额头撞击地面发出 “砰砰” 闷响,但不多时却被主人继续踩在手指上的鞋跟制止。
“你的命是本宫赏的,用本宫的东西去抵那老奴的命,你胆子很大呢”
主人的语调慢悠悠,恰似春风轻柔婉转,却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与狠厉,一字一句仿若冰锥,直直刺入阿烬的心房。身姿优雅地端坐在楠木椅上的主人,华美锦袍如流淌的云霞,随着她细微的动作轻轻摆动,泛出粼粼光泽。玉手轻轻搭在扶手上,指尖蔻丹如血,那微微抬起的下巴,尽显高贵冷艳,宛如画卷中不可亵渎的神女。
细细的指骨对于金属靴根毫无抵御之力,莲足轻点长靴轻抬,主人缓缓碾碎自己手指的模样,以及靴面上精致的刺绣在烛光下闪烁着金银丝线的光芒,每一寸靴面的纹理,每一道金属配饰的光泽,都深深烙印在阿烬的脑海。
十指俱碎的痛苦几乎将阿烬的意识撕扯得支离破碎,却又被恐惧死死拽回现实。一次次触碰靴底的舌尖,直至完全舔干净靴底那满是血肉和骨片的混合物后,主人脸上的冷意才显得不那么阴沉。
「姐姐你这小奴很能忍呢,第三条都没怎么挣扎」
王府小姐那娇柔却又透着几分玩味的声音,如同一把锐利的钩子,将阿烬从痛苦与恐惧交织的幻觉中硬生生地拽了出来。恍惚间,似乎还能感觉到纤细修长的手指,如冰冷的蛇信,轻轻划过自己胸口。因为无法吸入空气,那被薄袜遮挡住的视野也愈发模糊,夜色暗潮般漆黑的边缘一点一点地向视野中聚拢。
王府小姐,阿烬确是见过几次。犹记画舫那次自己一言不发地跪在主人身边,低垂着头,听闻了王府小姐几日便换一个玩宠的牢骚,那语气就像是在谈论一件稀松平常的衣物,随意满不在乎。又想起了王府小姐抚摸着自己脸颊的狂热眼神,那目光中近乎病态的欲望,让阿烬的脊背瞬间发凉。幸好主人当场拒绝了将阿烬出借的请求。
画舫整晚,阿烬都保持着跪地的姿势,膝盖早已麻木不堪。但阿烬却无疑是幸运的,只是作为观众眼睁睁地看着画舫那隔音优良的船舱里,上演着一幕幕令人胆寒的场景,而不是作为台上的人。相比那根将自己后背抽带出血肉的荆刺皮鞭,王府小姐带来的那根鞭子上在船舱烛火下闪着寒光的金属刃钉,显然不是为了 “惩罚” 。那根鞭子,更像是从地狱深渊捞出的凶器,每一道刃钉都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下身被金属牢笼固定的男孩,惊恐的双眼瞪得滚圆,身体却被王府小姐身边的侍卫如拎小鸡般,架上了船舱里的刑架。这艘专为王公贵族预备的玩乐之处,设施可谓齐全。那男孩被架起腿后,仍止不住地发颤,双腿像筛糠一般,每一块肌肉都在痉挛,那是对即将到来的痛苦最本能的抗拒。当长鞭带着呼啸声抽下,阿烬似乎能看到空气都被抽得扭曲,男孩的身体瞬间弓起,脸上的痛苦扭曲到极致。嘴巴大张却只能发出近乎无声的丝缕气音。
阿烬听王府小姐所言才知道,这男孩因为聒噪,上船前就被毒哑,平日里总是偎依着要开锁释放,毕竟喂了他数十日的情物,今日也是打算试试鞭子,顺便看看这男孩能不能释放出来。
寒光的金属刃钉鞭高高扬起,长鞭狠狠抽在男孩身上,一道从脖颈至下肋的鞭痕豁然出现,皮肉翻卷,白骨森森,那刃钉上挂着的血肉还在令人毛骨悚然地抽搐,似在痛苦地呻吟,诉说着痛苦与绝望。
紧接着,又是一鞭,快如闪电,重重落在男孩裸露的前胸上,创口从胸廓撕裂至小腹。而三鞭下去,男孩的身体已是像抽断筋脉的泥人,瘫倒在刑架上,没了一丝生气,曾经鲜活的生命就此消逝,只留下一具不似人形的躯壳。阿烬听着那长鞭抽打空气发出的破空声响,不忍看向那男孩,只能低下头双手死死攥着地上的丝绒地毯,靠着指缝间被勒出深深的红印,强忍着恐惧与血腥气息带来的反胃。
“什么嘛,根本没有释放出来,费我这么多力气,真该死”
柳眉轻蹙,生气地嘟着嫣红小嘴的王府小姐,走到已然面目全非、完全没有人形的刑架前,用靴尖拨弄着地上那滩触目惊心的血肉,毕竟眼前这血腥的场景只是一场令她不悦的调教罢了。
紧接着鱼贯而入的画舫私兵动作麻利、神色冷漠,三两下便将血肉骨骼和浸渍着黏稠血液的毛毯打包带走,没有丝毫与迟疑,就如同清理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刹那间,一个活生生的人,曾经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这世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没留下一丝存在过的痕迹,空气中那刺鼻的血腥气,随着江风的呼啸,也渐渐消散于无形。
原本血迹斑斑、仿若修罗场的船舱,顷刻间便已恢复一新,奢华的装饰、精美的摆件,一切都整洁如初。不经意间,主人漫不经心地轻轻瞥过阿烬的眼神却也扯出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这奴锁了也乖巧,再盖一只也无妨」
主人那冷淡至极的声音悠然响起。话音未落,阿烬脸上堆叠的织物便又被无情地加厚一层,本就如发丝般细微、十不存一的透气缝隙,此刻被那袜身捂得更加严实。
即便不顾胸肋的伤势,竭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将丝毫空气吸进胸口。喉管处传来的剧烈灼烧感,如火蛇般顺着气管迅猛滑进肺中,所到之处将五脏六腑都灼烧得疼痛难忍。主人的气味也仿佛凝固在气管中一样,宛如实质化的将整个呼吸道死死堵住,就如同被主人的高贵玉足插入喉管一样,完全感觉不到任何气流交换的感觉。
清晨强令阿烬吃下的性药所带来的燥热感,此刻在窒息的催化下,犹如火上浇油,让体内原本就汹涌的灼热火欲愈加旺盛。自觉绵软得如同烂泥的四肢,实际却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着,意识也渐渐模糊,如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恍惚间眼前的黑暗中似出现了些许闪烁的星光,那是死亡临近的征兆。
「姐姐你看他已经开始发抽了,真的能忍到释放吗?」
「那便是没这福分,白生了这张脸面」
「嘻嘻,果然姐姐不愿将这小奴借我玩是因为这样貌呢」
王府小姐那娇柔却又透着几分残忍的嬉笑在阿烬耳中显得格外刺耳。阿烬听主人和侍卫长聊过一些事,主人每次听到 “皇子” 一词时,面色都阴沉的可怕。如若不是自己和那位皇子长相相仿,冬日濒死之时也不会引得那载着主人的皇府马车停下。自己早就死在冬日里,和那些流浪在街巷的孩童一样,落个被野狗分食,尸骨全无的下场。
王府小姐曾在临下画舫之际,贴近阿烬耳畔说过,阿烬这模样在公主姐姐手中活不长久,自己还是比较中意阿烬的。当时只觉恶寒的阿烬并未说话,因为自己相比那些主人曾经的小奴已经幸运很多。
能吸到的空气近乎与无,口中事先被塞入袜子的阿烬连伸出舌头都做不到,因为窒息而逐渐干涸的喉咙只能尝到来自主人薄袜上那丝丝缕缕清幽咸味入喉,甚至自己的四肢也渐渐无法感受到,冰冷的感觉逐渐向自己的身体集中,就像浸入冰水中一样,意识也愈发模糊。深埋在身体骨髓里的求生本能,妄图驱使阿烬抬起那仿佛灌了铅的手臂。然而阿烬并不知道刚刚四肢震颤时,主人早已吩咐侍卫将自己的手脚铐死在桌案上。
「怪不得刚才西苑猎场那会儿,姐姐说要奖励这小奴,吸着围猎后的汗湿袜子闷死,也是福份」
娇柔却又透着几分玩味至极的声音传来,王府小姐眼角扫过阿烬形同死物的身躯,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此时的阿烬,双耳就像被塞入了千万只蜂鸣的小虫,外界的一切声响尽皆被这汹涌的噪音无情淹没。偶尔有几缕话音如风中残丝般飘入,脑海中却根本拼凑不出完整语句,想理解更是奢望。
木桌上阿烬宛如一条脱水濒死的鱼,胸腹急剧起伏,拼尽全力扭动身躯,妄图从那密不透风的禁锢中挣得一丝氧气。可脸上那薄袜,若牢墙般将生的希望彻底断绝。早已将那金属小笼顶起多时的下身,不受控制地滴落着的似稀薄米汤般的液体。
公主莲步轻移,手中拿着最后一双刚刚褪下裸足的薄袜,轻轻覆于剧烈颤抖的阿烬面庞之上。
「五」
「四」
「三」
「二」
「一」
阿烬生命最后的气力勉强听着主人倒计时,但那允许释放的命令却久久未入耳。溢出的米清汁液中却似是掺上了一丝丝纯白,看着已经止不住溢着浆液的男孩,公主俯身朱唇轻启。
「烧了那占地旧屋才有猎场,今日这赏赐也算是你全家性命求来的」
不知是因为听闻身世缘由而不甘挣扎,亦或是临死前混合着高潮与求生欲的无意义震颤,木桌上箍住男孩四肢的铁链激烈的发出阵阵声响。被枷锁强行支开的双腿在将死高潮下,徒然无用的妄图交叠着,随着下身最后一丝颤动后便彻底陷入了死寂。双腿间那锁着下身的小巧金属笼,却还在顺着大腿边不停滴落的凝乳般浓稠纯白的液体。
「好可惜,原以为会看到姐姐用长靴踩呢」
「不过贱奴罢了,脏了靴子」
「只是觉得窒息不过瘾嘛,还是带血的合我胃口」
「南宫妹妹倒是教育起本宫来了?」
(完)
本文包含100%坏女人,纯BE,包括且不限于踩踏,血腥,鞭打,气味,窒息等,无法接受请立即关闭。
「来,第一只」
轻轻覆住口鼻处的柔暖裹挟着融融煦煦的温热,依偎拥抱着竭力呼吸的面庞。轻薄如羽的湿润袜身将能吸进体内的气体,截留得只剩寥寥无几的残缕。急促翕动的鼻翼竭力的妄图从细密紧致的细小缝隙中吸入丝丝缕缕,汲取那少得可怜的新鲜空气。
经过潮湿袜身过滤的气味是阿烬已经闻过无数次的味道,是独属于主人的气息,是主人褪下长靴中悄然萦绕的芬芳 ,是混合着皮革的醇厚与主人身上清幽体香的独特韵味,是无需任何额外动作,仅仅是嗅到一丝便能让心底的欲望不可遏制地涨立起来的味道。
阿烬已经记不清曾有多少次,仅是闻着这魂牵梦绕的气味,便让自己双腿酥软沉溺其中。但在主人的“赏赐”并未“许可”的情况下,自己作为爱宠做出逾越赏赐的行为便是重罪。
「第二只」
为了能捕捉到那哪怕最细微、如风中残烛般珍贵的一丝空气,在口鼻处那如薄纱般轻柔的袜身,深深凹陷进阿烬的口腔,即便如此挣扎吸气,进入体内的气体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增加。身侧旧伤似被冰冷寒针插入的刺痛,随着胸廓每一次极其微弱的颤动而扩大。每一丝试图扩张胸廓的努力,都如同撕裂一般疼痛,让阿烬根本无法获取更多赖以活命的氧气。
凭借着侧一侧头的力道,那近乎封死呼吸的袜身便会顺着脸颊滑落,让阿烬重新呼吸到甜美的空气。但是阿烬不敢,也不能,身为 “玩宠” 没有说 “不” 的权利,主人的一切行为都是 “赏赐”。
那被砌死在寝宫楠木椅下面的上一任 “玩宠”便是最好的例子,阿烬不知道那玩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被挑断四肢挖去眼睛,封死在楠木椅下石窟中的那人,“金汁玉液”这唯一赖以生存的食物,也要看主人的心情才能赏赐。
「姐姐要加第三只嘛?」
那娇俏却又透着几分骄纵的声音突兀地响起,这个声音阿烬很熟悉,那是在公主府宴席上传菜时慌乱间打破了瓷瓶时,主人身旁那位王府小姐的声音。
“这莽撞小厮倒也有几分姿色”身穿锦服的王府小姐勾起了自己的跪地磕头的面庞,也正是因此话语,阿烬撞进了主人的视线。
在画舫上阿烬也曾见过这位王府小姐的身影,仅仅是为了向姐妹展示新得的鞭子,便将玩宠生生抽至断气,那凄厉的场景仿佛还在阿烬眼前闪回。还有那偎依在主人耳边,想借阿烬给自己玩两天的说辞,眼神中满是令阿烬心悸的火热。
「第三只也盖上好了」
主人的轻润语气在耳边响起,交叠着盖在脸上的汗湿薄袜却似千钧巨山,每一丝试图钻进鼻腔的空气都被袜身无情截留,能进入身体的空气稀薄得几近于无。汹涌如潮水般的强烈窒息让身体不得不昂起头,仿佛如此便能抢夺一丝活命的空气般。然而越是吸气,那薄袜与口鼻的贴合便越是紧密。挣扎、颤抖,哪怕是幅度更大的动作都不会让带着主人气味与体温的潮湿薄袜有丝毫的移动。
阿烬这名字是外府管事起的。幼时家里被烧,父母双亡的自己在六岁那年流浪到皇城,在冰天雪地中即将冻死之际,是主人将他带到了府里。正巧那天赶上倒炭炉,管事见他可怜,也就单取了个 “烬” 字。
现在喉管中愈发强烈的灼烧感却真似吞炭般,不仅仅是喉管,袜身传来的主人气味让阿烬的身体也似被炭火灼烧般,四肢止不住地发抖,在窒息与欲望的双重折磨下,挺立的情欲不自知的向外留着暖流。但阿烬即便满心渴望抬手拿下脸上这薄袜,也不可能做到。因为自己那无法弥补的过错,主人的惩罚让阿烬早就失去了控制手指的能力,那个待他如同亲儿子一般的老管事,也因阿烬而丢了性命。
透过织物越来越少的空气让缺氧带来的幻觉逐渐实质化,已然充溢着主人幽兰般气味的身体,似是让阿烬眼前的场景又回到了在主人寝宫里接受断指惩罚那天。
金线绣制的繁杂花纹在黑色绸缎长靴上熠熠生辉,看着细长的雕花鞋跟轻轻踏上了手指。金属雕花的鞋跟以指节为支点,缓慢的左右转动,皮肉被剥离所渗出的血液顺着指节侧方淌下,紧接着便是筋膜与坚韧的肌腱,圆弧鞋跟锋利的边缘仅旋蹍半圈便将粘附血肉的洁白肌腱切断,脆弱的骨关节失去肌腱的约束牵引,在公主逐渐施加的力度面前,发出一阵阵心悸的碎裂声后,被下沉的靴根蹍成碎裂的骨片,而这仅是一个指节。
不到一刻钟,左手小指指骨便从关节处被彻底踩断,三节血肉模糊的断指带着丝丝缕缕的肉末与猩红色的血迹,一点点渗进绒毯的绒毛间隙,和地面铺设的绒毯融为一体。寝宫内只有轻微的骨骼碎裂声与男孩的低沉闷哼。
浓重的夜色如墨,从雕花窗棂的缝隙拼命挤入。随着主人重新坐回到楠木椅上,强忍着断指处传来剧痛的阿烬,身体颤抖着靠近面前轻抬的靴子,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舔舐着自己的血迹。靴底那些藏匿在细微缝隙中的碎骨,也被舌尖如寻觅至宝般,一点一点地舔出。
手掌渗出的鲜血连带着一波又一波的痛楚,就在主人轻抬起另一只靴子示意阿烬继续时,眼前宛如被蒙上黑布的身体却是如天旋地转般向前栽倒,晕了过去。
但随即被满是荆棘铁刺的鞭子继而抽醒的阿烬,意识还混沌在剧痛的泥沼之中,迷迷糊糊间,对上了主人方才还有几分欣赏,如今却寒若冰霜的眼眸。那双眼睛冷意彻骨,残存的迷糊也被驱赶得一干二净。
身后的侍卫长扬起手中的鞭子再次狠狠抽在阿烬身上。“啪” 的一声脆响,皮开肉绽,血珠飞溅,阿烬的后背瞬间绽开一道道血痕,挣扎着想要继续舔舐主人靴子的阿烬,却见主人已将轻抬的长靴收回,站起身冷冷地看着自己。
“机会只有一次,子不教父之过,那外府老奴也不必活了”
冷淡声音一字一句都似重锤,狠狠砸在阿烬心上。拼命磕头为管事求饶的阿烬,额头撞击地面发出 “砰砰” 闷响,但不多时却被主人继续踩在手指上的鞋跟制止。
“你的命是本宫赏的,用本宫的东西去抵那老奴的命,你胆子很大呢”
主人的语调慢悠悠,恰似春风轻柔婉转,却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与狠厉,一字一句仿若冰锥,直直刺入阿烬的心房。身姿优雅地端坐在楠木椅上的主人,华美锦袍如流淌的云霞,随着她细微的动作轻轻摆动,泛出粼粼光泽。玉手轻轻搭在扶手上,指尖蔻丹如血,那微微抬起的下巴,尽显高贵冷艳,宛如画卷中不可亵渎的神女。
细细的指骨对于金属靴根毫无抵御之力,莲足轻点长靴轻抬,主人缓缓碾碎自己手指的模样,以及靴面上精致的刺绣在烛光下闪烁着金银丝线的光芒,每一寸靴面的纹理,每一道金属配饰的光泽,都深深烙印在阿烬的脑海。
十指俱碎的痛苦几乎将阿烬的意识撕扯得支离破碎,却又被恐惧死死拽回现实。一次次触碰靴底的舌尖,直至完全舔干净靴底那满是血肉和骨片的混合物后,主人脸上的冷意才显得不那么阴沉。
「姐姐你这小奴很能忍呢,第三条都没怎么挣扎」
王府小姐那娇柔却又透着几分玩味的声音,如同一把锐利的钩子,将阿烬从痛苦与恐惧交织的幻觉中硬生生地拽了出来。恍惚间,似乎还能感觉到纤细修长的手指,如冰冷的蛇信,轻轻划过自己胸口。因为无法吸入空气,那被薄袜遮挡住的视野也愈发模糊,夜色暗潮般漆黑的边缘一点一点地向视野中聚拢。
王府小姐,阿烬确是见过几次。犹记画舫那次自己一言不发地跪在主人身边,低垂着头,听闻了王府小姐几日便换一个玩宠的牢骚,那语气就像是在谈论一件稀松平常的衣物,随意满不在乎。又想起了王府小姐抚摸着自己脸颊的狂热眼神,那目光中近乎病态的欲望,让阿烬的脊背瞬间发凉。幸好主人当场拒绝了将阿烬出借的请求。
画舫整晚,阿烬都保持着跪地的姿势,膝盖早已麻木不堪。但阿烬却无疑是幸运的,只是作为观众眼睁睁地看着画舫那隔音优良的船舱里,上演着一幕幕令人胆寒的场景,而不是作为台上的人。相比那根将自己后背抽带出血肉的荆刺皮鞭,王府小姐带来的那根鞭子上在船舱烛火下闪着寒光的金属刃钉,显然不是为了 “惩罚” 。那根鞭子,更像是从地狱深渊捞出的凶器,每一道刃钉都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下身被金属牢笼固定的男孩,惊恐的双眼瞪得滚圆,身体却被王府小姐身边的侍卫如拎小鸡般,架上了船舱里的刑架。这艘专为王公贵族预备的玩乐之处,设施可谓齐全。那男孩被架起腿后,仍止不住地发颤,双腿像筛糠一般,每一块肌肉都在痉挛,那是对即将到来的痛苦最本能的抗拒。当长鞭带着呼啸声抽下,阿烬似乎能看到空气都被抽得扭曲,男孩的身体瞬间弓起,脸上的痛苦扭曲到极致。嘴巴大张却只能发出近乎无声的丝缕气音。
阿烬听王府小姐所言才知道,这男孩因为聒噪,上船前就被毒哑,平日里总是偎依着要开锁释放,毕竟喂了他数十日的情物,今日也是打算试试鞭子,顺便看看这男孩能不能释放出来。
寒光的金属刃钉鞭高高扬起,长鞭狠狠抽在男孩身上,一道从脖颈至下肋的鞭痕豁然出现,皮肉翻卷,白骨森森,那刃钉上挂着的血肉还在令人毛骨悚然地抽搐,似在痛苦地呻吟,诉说着痛苦与绝望。
紧接着,又是一鞭,快如闪电,重重落在男孩裸露的前胸上,创口从胸廓撕裂至小腹。而三鞭下去,男孩的身体已是像抽断筋脉的泥人,瘫倒在刑架上,没了一丝生气,曾经鲜活的生命就此消逝,只留下一具不似人形的躯壳。阿烬听着那长鞭抽打空气发出的破空声响,不忍看向那男孩,只能低下头双手死死攥着地上的丝绒地毯,靠着指缝间被勒出深深的红印,强忍着恐惧与血腥气息带来的反胃。
“什么嘛,根本没有释放出来,费我这么多力气,真该死”
柳眉轻蹙,生气地嘟着嫣红小嘴的王府小姐,走到已然面目全非、完全没有人形的刑架前,用靴尖拨弄着地上那滩触目惊心的血肉,毕竟眼前这血腥的场景只是一场令她不悦的调教罢了。
紧接着鱼贯而入的画舫私兵动作麻利、神色冷漠,三两下便将血肉骨骼和浸渍着黏稠血液的毛毯打包带走,没有丝毫与迟疑,就如同清理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刹那间,一个活生生的人,曾经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这世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没留下一丝存在过的痕迹,空气中那刺鼻的血腥气,随着江风的呼啸,也渐渐消散于无形。
原本血迹斑斑、仿若修罗场的船舱,顷刻间便已恢复一新,奢华的装饰、精美的摆件,一切都整洁如初。不经意间,主人漫不经心地轻轻瞥过阿烬的眼神却也扯出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这奴锁了也乖巧,再盖一只也无妨」
主人那冷淡至极的声音悠然响起。话音未落,阿烬脸上堆叠的织物便又被无情地加厚一层,本就如发丝般细微、十不存一的透气缝隙,此刻被那袜身捂得更加严实。
即便不顾胸肋的伤势,竭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将丝毫空气吸进胸口。喉管处传来的剧烈灼烧感,如火蛇般顺着气管迅猛滑进肺中,所到之处将五脏六腑都灼烧得疼痛难忍。主人的气味也仿佛凝固在气管中一样,宛如实质化的将整个呼吸道死死堵住,就如同被主人的高贵玉足插入喉管一样,完全感觉不到任何气流交换的感觉。
清晨强令阿烬吃下的性药所带来的燥热感,此刻在窒息的催化下,犹如火上浇油,让体内原本就汹涌的灼热火欲愈加旺盛。自觉绵软得如同烂泥的四肢,实际却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着,意识也渐渐模糊,如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恍惚间眼前的黑暗中似出现了些许闪烁的星光,那是死亡临近的征兆。
「姐姐你看他已经开始发抽了,真的能忍到释放吗?」
「那便是没这福分,白生了这张脸面」
「嘻嘻,果然姐姐不愿将这小奴借我玩是因为这样貌呢」
王府小姐那娇柔却又透着几分残忍的嬉笑在阿烬耳中显得格外刺耳。阿烬听主人和侍卫长聊过一些事,主人每次听到 “皇子” 一词时,面色都阴沉的可怕。如若不是自己和那位皇子长相相仿,冬日濒死之时也不会引得那载着主人的皇府马车停下。自己早就死在冬日里,和那些流浪在街巷的孩童一样,落个被野狗分食,尸骨全无的下场。
王府小姐曾在临下画舫之际,贴近阿烬耳畔说过,阿烬这模样在公主姐姐手中活不长久,自己还是比较中意阿烬的。当时只觉恶寒的阿烬并未说话,因为自己相比那些主人曾经的小奴已经幸运很多。
能吸到的空气近乎与无,口中事先被塞入袜子的阿烬连伸出舌头都做不到,因为窒息而逐渐干涸的喉咙只能尝到来自主人薄袜上那丝丝缕缕清幽咸味入喉,甚至自己的四肢也渐渐无法感受到,冰冷的感觉逐渐向自己的身体集中,就像浸入冰水中一样,意识也愈发模糊。深埋在身体骨髓里的求生本能,妄图驱使阿烬抬起那仿佛灌了铅的手臂。然而阿烬并不知道刚刚四肢震颤时,主人早已吩咐侍卫将自己的手脚铐死在桌案上。
「怪不得刚才西苑猎场那会儿,姐姐说要奖励这小奴,吸着围猎后的汗湿袜子闷死,也是福份」
娇柔却又透着几分玩味至极的声音传来,王府小姐眼角扫过阿烬形同死物的身躯,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此时的阿烬,双耳就像被塞入了千万只蜂鸣的小虫,外界的一切声响尽皆被这汹涌的噪音无情淹没。偶尔有几缕话音如风中残丝般飘入,脑海中却根本拼凑不出完整语句,想理解更是奢望。
木桌上阿烬宛如一条脱水濒死的鱼,胸腹急剧起伏,拼尽全力扭动身躯,妄图从那密不透风的禁锢中挣得一丝氧气。可脸上那薄袜,若牢墙般将生的希望彻底断绝。早已将那金属小笼顶起多时的下身,不受控制地滴落着的似稀薄米汤般的液体。
公主莲步轻移,手中拿着最后一双刚刚褪下裸足的薄袜,轻轻覆于剧烈颤抖的阿烬面庞之上。
「五」
「四」
「三」
「二」
「一」
阿烬生命最后的气力勉强听着主人倒计时,但那允许释放的命令却久久未入耳。溢出的米清汁液中却似是掺上了一丝丝纯白,看着已经止不住溢着浆液的男孩,公主俯身朱唇轻启。
「烧了那占地旧屋才有猎场,今日这赏赐也算是你全家性命求来的」
不知是因为听闻身世缘由而不甘挣扎,亦或是临死前混合着高潮与求生欲的无意义震颤,木桌上箍住男孩四肢的铁链激烈的发出阵阵声响。被枷锁强行支开的双腿在将死高潮下,徒然无用的妄图交叠着,随着下身最后一丝颤动后便彻底陷入了死寂。双腿间那锁着下身的小巧金属笼,却还在顺着大腿边不停滴落的凝乳般浓稠纯白的液体。
「好可惜,原以为会看到姐姐用长靴踩呢」
「不过贱奴罢了,脏了靴子」
「只是觉得窒息不过瘾嘛,还是带血的合我胃口」
「南宫妹妹倒是教育起本宫来了?」
(完)
好高贵的女主,社保了
怎么不加大小姐tag,我立刻加上
太棒了,就是太短了
好可惜,超想看长靴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