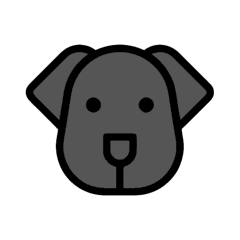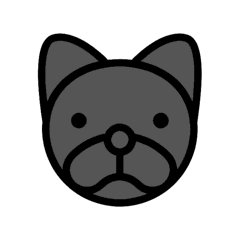山河泪:樱落红旗
连载中原创现实同人纯爱强奸鞭打后庭乳头虐待
我的名字叫波风凑,18岁的清秀少年。
别看我这样,我是关东军一名少尉,毕竟我在陆军学校是第一名的成绩,再加上我的老师自来也是关东军大将,他为我的前程付出了很多。
1937年我们日军全面入侵中国,我在内心不赞同这场战争,但是为了国家,老师和家人,我还是来到了中国晋察冀地区,来到一所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做监狱长
黄昏时分,我站在监狱长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院子里穿着灰色囚服的犯人们在寒风中排着队。我身着崭新的军装,胸前的徽章在夕阳下泛着冷光。
这间办公室很大,装修也算得上豪华。深棕色的实木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份档案,都是关于囚犯的资料。角落里是一个红木书架,上面摆满了法律和军事相关的书籍。
我轻轻叹了口气。虽然才18岁,但我深知这份工作的分量。关东军大将自来也老师临行前对我说:"凑,你要用智慧和勇气来管理这座监狱。"
突然,传令兵敲响了房门:"波风少尉,共产党的重要俘虏已经到了。"
我整理了一下制服,迈步走向门口。走廊尽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几个宪兵押送着一位年轻的女性走了过来。
她看起来二十出头,个子不高但身材丰满。即使身着粗布囚衣,也掩盖不住那对饱满的奶子和圆润的翘臀。她的脸上带着倔强,但眼神中透着一丝惊慌。
"报告少尉,这是我们在平型关抓获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名叫小兰。"宪兵队长递上来一份文件。
我接过文件,目光在这位叫小兰的女囚身上扫过。她低着头,但从她微微发抖的身体可以看出她的紧张。
"带下去吧,单独关押。"我说完,转身回到了办公室。夜幕即将降临,这座冰冷的监狱又将迎来一个漫长的夜晚。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内心却升起一丝不安。作为一名军人,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说来可笑,这里虽然是日本人关押中国共产党的监狱,但是这里只有我一个日本人,这所监狱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皇协军,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汉奸,我内心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对待共产党,对付自己同胞的态度比我这个真正的日本人凶恶的多得多
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外面传来的谩骂声和皮靴踏地的声响。那些皇协军正在押送新到的囚犯。
张队长是这群人中最令人厌恶的一个。他四十来岁,身材矮胖,总是穿着一件擦得锃亮的皮夹克,领口敞开着露出油腻的脖子。每次见到他对着中国囚徒又打又踢的样子,我都觉得一阵反胃。
"波风少尉!"他那难听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那个共党女俘虏不肯开口,要不要我们好好'招待'一下?"
我望着窗外。张队长身后跟着七八个同样面目可憎的打手,他们都摩拳擦掌地等着审讯的命令。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我手中的权力的渴望。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这些叛徒总是用最残酷的方式折磨自己的同胞。
小兰被关在了三号审讯室。我能想象到她此刻正蜷缩在冰冷的铁椅子上,身上的囚衣单薄地几乎遮不住她那对肥硕的奶子和浑圆的屁股。那些皇协军一定已经用色眯眯的眼神把她的身子看了个遍。
我站起身,整了整军装。作为一个日本军官,我本该同意他们的请求。但这群畜生般的走狗让我作呕。他们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更是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丧失殆尽。
"张队长,"我冷冷地说,"今天先把她关起来。明天早上再说。"
张队长脸上的期待变成了失望,但他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这群人就是这样,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扬威,见到日本军官就立刻变成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回到办公桌前,我拿起自来水笔,在值班日志上写下今天的日期。夜晚还很长,我能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寒风,呼啸着穿过监狱的铁栅栏。在这个满是背叛和仇恨的地方,我仿佛也能感受到小兰此刻的恐惧与无助。
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我不该承受这样的重担。但我明白,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被迫站在了某个立场上。只是没想到,最让我反感的,竟是这些打着日本旗号的中国叛徒。
正午的阳光透过铁丝网照射在监狱的水泥地上,形成一道道刺目的光影。我沿着监区的通道缓步巡视,皮靴踩在地上发出规律的声响。
远远就看见张队长那臃肿的身影,他正押送着一批新犯人。这群共产党的衣衫褴褛,脚步蹒跚,但他们的眼神里都闪烁着不屈的光芒。张队长每走一步都要踹上一脚,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咒骂着。
"你们这些该死的共匪!"张队长吐着唾沫,"看看你们现在的德行!"
"呸!你这个卖国贼!"一个男犯人猛地抬起头,眼中喷射着怒火,"你有什么资格骂人?"
正当我准备上前制止时,张队长突然抬脚狠狠踹向队伍最后的那个年轻女孩。她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一头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着,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灰布囚衣,胸前的纽扣掉了几颗,露出了里面白皙的肌肤。
女孩猝不及防,重重摔倒在水泥地上。她的手掌擦破了皮,鲜血渗了出来。其他犯人纷纷叫喊起来:
"住手!你这个畜生!"
"你还有没有人性?"
张队长狞笑着又要上前,但这次我抢先一步挡在他面前。
"够了!张队长。"我用冷冽的声音说道,"这里是监狱,不是你的杀猪场。"
张队长悻悻地退了几步,谄媚地看着我的肩章:"是是是,少尉大人说得对。"
我蹲下身,扶起那个跌倒的女孩。近距离看去,她长得很清秀,脸蛋红扑扑的,虽然衣着褴褛但掩不住少女特有的青涩魅力。她的手腕和脚踝都有淤青,显然是路上受了不少虐待。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我想递给她:"吃吧,补充些体力。"
谁知道她竟然用力推开我的手,倔强地抬起头:"不用敌人施舍!"
她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嘴角还带着一丝倔强的笑意。这种视死如归的姿态让我心中一震。
张队长还在一旁蠢蠢欲动:"少尉大人,要不要......"
我打断了他的话:"把他们带下去,不准虐待。"
看着犯人们消失在牢房的背影,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老师总说:真正的敌人未必是站在对面的人,有时反而是在你身边那些迷失本性的人渣。
夕阳西斜,透过百叶窗在我深棕色的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轻轻摘下脖子上的护身符,这是一块朴素的棉布包裹,已经被汗水浸染得有些发旧。指尖轻抚过布面,似乎还能感受到母亲缝制时的温度。
护身符里装着一片神社祈福的符纸,还有一缕妹妹的头发。记得临行前的那个雨天,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专注地缝制着护身符,银色的发丝在微弱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妹妹则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换上军装。
"凑啊,"母亲的手有些颤抖,"你要好好保护自己。这护身符里装着织姬的一缕头发,保佑你平安归来。"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办公室里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那是潮湿的墙壁散发出来的。远处传来犯人的咳嗽声和铁链的碰撞声,但这都不能打扰我对家乡的思念。
拿出抽屉里的照片,那是全家在东京郊外踏青时拍的。照片上的妹妹还是个高中生,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那么纯真。现在她应该已经习惯了没有兄长的生活吧?
夜幕渐渐降临,窗外传来值勤士兵交接班的脚步声。我将照片重新放回抽屉,摸了摸护身符。它是我和家乡唯一的联系,是我疲惫时的精神寄托。
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死离别。那些被抓来的共产党犯人,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女儿,也会有人像我的母亲一样,在远方牵挂着他们。
张队长他们又开始在审讯室里折腾了,隐约可以听见痛苦的呻吟声。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月光洒在院子里的石板路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在这个遥远的异乡,我只能靠着手中的护身符,寄托对亲人深深的思念。
母亲现在也许正坐在厨房里,像往常一样准备着晚餐;妹妹可能正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专心读书。而我,却在这里,穿着军装,管理着一座关押敌对分子的监狱。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现在的我又会在哪里?会不会在东京某个温暖的教室里,继续着平凡的学业?
初春的清晨,我正在办公室里读着自来也老师的来信。信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透着几分严厉:"凑,你太软弱了。作为一名军官,必须要有果断的决断力。现在派给你一个任务..."
"少尉大人!"张队长推开门,脸上堆着献媚的笑容,"您要的犯人带来了。"
我抬起头,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禁愣住了。一位约莫二十八九岁的女性站在门口,她穿着略显褴褛的八路军军服,军裤管卷到膝盖,露出满是伤痕的小腿。她的双脚赤裸着,沾满了泥土和血迹,但她站着的姿势依然挺拔。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眼睛,清澈而坚定,炯炯有神地凝视着我。她扎着一根利落的马尾,几张碎发粘在额头的汗珠上。虽然衣着简陋,但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这就是犯人苏雅婷。”张队长搓着手说,"我们昨晚在太行山区抓到的。她可是个大人物,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政委。"
我站起身,第一次感到有些局促。这个女人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完全不像我见过的其他囚犯。她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带着一种悲悯。
"喂,小鬼子。"她突然开口,声音清亮而有力,"你这么年轻就来当汉奸了?"
我微微皱眉:"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军官。"
她冷笑一声:"在日本还是个小孩子吧?看看你这身高,怕是连征兵线都够不到,是不是靠着家里的关系才混到这个位置的?"
我确实比同龄人要矮一些,在日本时就经常因为身高被人取笑。但现在被一个囚犯这样嘲讽,让我感到既羞耻又恼怒。
"你们昨天抓了我的一支小队,"她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挑衅,"想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这正是自来也老师要我查明的情报。
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嘲弄起来:"想让我说出来?那就拿出点诚意来。"
张队长立刻会错了意,撸起袖子就要上前:"少尉大人,要不要我..."
住手。"我厉声打断了他。不知为何,我实在不忍心看这个坚强的女人受到伤害。但她刚才的话语又确实让我感到难堪,这种矛盾的心情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靠在门框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怎么?舍不得动手?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最喜欢用暴力逼供吗?来呀,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手段。"
我握紧了拳头,却又缓缓松开。晨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侧脸上,我看到她嘴角有一道新鲜的伤口,想必是抓捕过程中留下的。她的脚踝和手腕都有明显的勒痕,显然一路上没少吃苦。
"把她带到三号审讯室。"我最终说道,声音有些沙哑,"我要亲自审问。"
她跟着张队长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下:"喂,小日本..."
我抬头看她。
"...你的眼神跟其他日本兵不太一样。"她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心跳如雷。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囚犯。她不仅是敌人,更是一个让我深深困惑的存在。
审讯室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铁质的审讯椅和桌子被擦拭得锃亮,墙角的工具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刑具,但此刻它们都被一块深色的布帘遮住了。
苏雅婷坐在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扶手上。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的动作,眼神中依然带着戏谑和轻蔑。我拿出医药箱放在她脚边,打开时金属器械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怎么,小日本?"她微微歪着头,"准备给我用什么刑?听说你们日本军队最喜欢用针扎指甲缝..."她故意停顿了一下,"还是说...你对女俘虏有更好的手段?"
我充耳不闻,专注地调配着医用酒精。她的一双玉足确实伤得不轻,有些地方的皮肤已经溃烂发紫。长期行军让她的脚掌结了一层薄茧,但依然能看出年轻女子特有的纤巧。脚踝处有清晰的绳索勒痕,想必是被抓捕时遭受了不少折磨。
"别废话了,乖乖消毒。"我拿起纱布蘸了酒精,轻轻按在她的伤口上。
"嘶——"她倒吸一口冷气,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哟,还挺温柔的嘛。该不会是是想用这种方式瓦解我的意志吧?"
我没有回答,认真地为她处理着每一处伤口。她的脚趾修长而干净,看得出平时很注意保养,不像一般农村姑娘那样粗糙。这让我很好奇她的背景。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一边包扎一边问道。
"你觉得呢?"她反问,语气中带着调侃,"看我的脚就能猜出来了,是不是?"
阳光从高处的小窗斜射进来,在她的脚背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线。我继续沉默着,手中的动作越发轻柔。
"奇怪,"她突然说,"我见过那么多审讯官,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要么野蛮粗暴,要么假惺惺地套近乎..."她直视我的眼睛,"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我抬起头,发现她的眼神里除了警惕,似乎还藏着一丝好奇。我们四目相对,空气中有片刻的寂静。
"你知道吗?"她打破了沉默,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你要是换个国籍,说不定还是个好孩子。"
这句话让我的手顿了一下。酒精顺着她的脚背流下来,在椅子腿上留下一道透明的痕迹。外面传来巡逻士兵的脚步声,沉重而规律。
"你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脱口而出,随即又为自己的天真感到懊恼。
她笑了,这次的笑声里少了些许嘲讽,多了几分真诚:"也许...你会是我教过的学生吧。我看你这副书生气,肯定是个好学生。"
我低头继续包扎,努力掩饰内心的波澜。这个答案让我感到既意外又心酸。
简单的为她处理好脚上的伤,我内心记着自来也老师的任务,于是开始认真的说道:“我的名字是波风凑,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也是这所监狱唯一的日本人。苏雅婷小姐,我知道你有一份八路军地下党的名单,请你把她交出来,不然我会对你用暴力手段。”
我说出这番话时特意提高了声音,试图让自己听起来更有威慑力。但苏雅婷听完却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狭小的审讯室里回荡。
"哈哈哈...对不起,实在忍不住。"她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水,"你这孩子太可爱了。"
她晃了晃被铐着的手腕:"第一,叫我小姐?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最喜欢说'该死的支那共匪'吗?第二,威胁要用暴力?那你怎么到现在连我的绑都没松?"
她向前倾了倾身子,距离近得让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药草香。那是太行山上常见的草药味道。
"小鬼子,你今年多大?十八?十九?"她的声音突然温柔了下来,但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惊的穿透力,"你觉得,就凭你这样的性格,能当好一个刽子手吗?"
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但她继续说道:"看你的眼睛...干净得像个孩子。应该在学校里读书吧?为什么会来这里?"
她的语气里没有之前的嘲讽,反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怜惜。这让我不知如何应对。明明她是我的阶下囚,此刻却像是她在审视我。
"我..."我刚要解释,她却打断了我。
"知道吗?"她轻轻活动着刚被包扎好的双脚,"你的手法倒是挺专业的。看来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学生。可惜啊..."
她摇了摇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窗外:"现在日本的年轻人,都太容易被大人们骗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烦躁:"够了!我不想听这些!那份名单在哪?"
她反而笑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要用暴力?来吧,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孩子能做出什么事来。"
她的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拆穿的拙劣演员,所有的威胁和威压在她面前都成了笑话。
这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也许她才是那个真正掌握主动权的人。
我此时忍不住皱起眉头的说:“我再说一遍,你不要以为我吓唬你,我真的会对你用暴力手段的!虽然我是第一次做审讯别人,但我也知道什么叫做严刑拷打,你不想尝尝那个滋味吧?”
哦?"她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趣味,"第一次审讯?难怪我觉得你像个刚出道的学生。"
她突然用力挣了挣手铐,发出"咔嚓"的声响:"严刑拷打?那就试试呗。反正我们共产党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她的眼神变得异常明亮,像是燃烧的火苗:"来吧,让我看看日本帝国主义的酷刑有多厉害。你们会用电刑吗?还是打算用老虎凳?或者灌辣椒水?我听说你们最喜欢用针扎指甲缝..."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子一样戳进我的心里。我攥紧了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闭嘴!"
"不闭。"她反倒笑得更开心了,"我偏要说。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吓倒我吗?小孩子扮大人,终究是装不像的。"
我的喉咙发紧,胸口剧烈起伏。她的话确实戳中了我的软肋——是的,我确实是第一次审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日本军官。
"你知道吗?"她见我沉默,反而放缓了语气,"你的眼神,跟我教过的学生一模一样。他们也都是这样,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却被现实逼得不得不长大。"
她的声音渐渐温柔,但却让我的心更加混乱:"但你要记住,真正的成长不是学会残忍,而是即使面对残酷,也要保持内心的光明。"
阳光穿过铁窗的缝隙洒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超越年龄的睿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她能在如此处境下依然保持着从容。
我转过身,不愿让她看到我眼中的动摇。耳边传来她轻柔的声音:"所以,小鬼子,你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是想做一个合格的刽子手?这选择权在你手里。"
我的手在颤抖,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因为害怕。害怕她看穿了我脆弱的伪装,更害怕她说出了我心里最深层的恐惧。
我为了掩饰恐惧,故意说道:“好了,既然你拒不配合,我就要严刑拷打你了!”
随即我立刻走到书架前拿起一本审讯大全看了起来,但随即我就茫然的放下了书。
因为这本书是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写的,虽然我会说中国话,但是我却不认识大部分的中国字。
我尴尬地站在书架前,手里捧着那本厚重的《审讯大全》。封面上的汉字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书,虽然我从高中习中文,但面对这种专业性的词汇,我还是感到束手无策。
余光里,我注意到苏雅婷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既不是嘲笑,也不是轻蔑,而是一种近乎怜悯的神情。
"看不懂?"她突然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原来堂堂日本军官,连中国字都不认识啊。"
我急忙把书放回去,但动作显然过于慌乱了。书页哗啦啦地翻动着,最后重重地撞在书架上。
"连这都看不懂,还想审问我?"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要不要我教你啊?就像教小学生认字那样?"
我转身想要说些什么,但她接着说:"第三页第二行,'拶刑',"她用一种教师授课的语气念道,"就是用竹签夹手指,特别疼,很多人受不了。第五页第四行,'坐杠',就是把人捆在木桩上..."
我越听越觉得难受,攥紧了拳头:"住口!"
"怎么?"她歪着头,"你不是要看审讯大全吗?我倒是知道很多,要不要我教你更多?比如'剥皮''抽筋''剥指甲'..."
"够了!"我几乎是吼出声来。
她突然停止了说话,室内陷入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个被揭穿的骗子,所有的威严在她面前都成了一场拙劣的表演。
"你知道吗?"她最后说,声音温和得让我心痛,"有时候装得太过,反而更容易暴露。"
我又尴尬又恼怒:“这是你们中国人的叛徒,也就是你们说的汉奸写的!我是日本人会说中国话就不错了,不认识中国字很正常!”
"汉奸?"她轻笑一声,"看来你还真了解我们的事情啊。既然如此,那你也应该知道,这些刑罚手段都是你们日本人教会他们的。"
她的语气突然变得犀利:"你说得对,那些人确实是汉奸。但他们至少还敢直面自己的同胞,敢做敢当。你呢?穿着一身军装,拿着一份看不懂的审讯手册,连审问都不知道该怎么进行..."
我涨红了脸:"闭嘴!我警告你..."
"怎么?"她打断我的话,"让我说中了?你们日本人在自己国土上不也是一群普通人吗?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可为什么来了中国就一定要变成魔鬼?"
我后退了一步,靠在书架上。书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仿佛在嘲笑我的狼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她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你们日本军人在自己国内是怎么对待犯人的?会用刑吗?会这样虐待人吗?这些都是你们学来的,对不对?"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脊,努力找寻着反驳的话语,但她的话却像潮水般涌来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脊,努力找寻着反驳的话语,但她的话却像潮水般涌来:"你们入侵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现在还要让我们告诉你谁是地下党员?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连审讯都不会,只会搬出一本汉奸写的书。你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吗?"
我的喉咙发干,说不出一句话。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虚张声势的外表,让我看到了内里不堪的真实。
"波风凑,"她叫我的名字,声音突然变得柔和,"你告诉我,你真的相信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吗?"
我生气的叫她闭嘴,随即开始吃力的翻阅审问大全,随即翻到了审问女共产党的第一页。
第一页的标题写着一句献媚到极点的话语:“请太君大人抓住女共产党后,在审讯之前立刻进行强奸,这样还能用这些下贱的赤匪身体来取悦太君大人。”
我茫然的看着这句话,这复杂的中国字我没有一个认识。
我最后无奈又羞涩的把书拿给苏雅婷,要她念给我听并且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苏雅婷扫了一眼我手中的书页,她的表情突然凝固了。那双清澈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真实的愤怒,而不是之前的戏谑。
"你真的要看吗?"她的声音变得冰冷,"你们日本军人还真是...喜欢这种东西。"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这上面写的是,建议日本军官在审讯女共产党员之前先把她们..."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凌辱。说这样既能泄欲,又能打击我们的意志。"
说到这里,她突然冷笑一声:"怎么,波风凑,你想这么做吗?看来你不仅是来看守的,还是来享乐的?"
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手足无措地想要合上书本:"不...我只是..."
"只是什么?"她的声音越来越冷,"只是想知道怎么做吗?你这个肮脏的小人!"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激动的样子,她的胸膛剧烈起伏着,连手铐都发出铮铮的撞击声。
"你知道吗?"她的声音忽然又平静下来,这种平静比愤怒更可怕,"你们这些日本军人,连审讯都学不会,就要学着侮辱女人。真是可悲啊..."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你才多大?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吗?就要学着用这种方式糟践一个女性?"
我羞愧得几乎要钻进地缝,手中的书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我终于明白,"她轻声说,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你们这些侵略者,表面上趾高气昂,实际上连基本的人性都站不稳。需要依靠这些东西来壮胆,真可怜。"
我的脸蛋涨的通红,结结巴巴的说道:“这…意思就是…要我….书上说要我强奸你?不,你说的是凌辱,凌辱是什么意思?和日本话的强奸是一个意思吗?”
苏雅婷沉默了一会,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大笑。
"天哪...天哪..."她的笑声中带着一丝颤抖,"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不懂?还要我给你解释这个词的意思?"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好吧,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凌辱的意思,就是像你这样的侵略者,用最下流最残暴的方式,玷污一个女性的身体和尊严。"
她说每一个字时都咬牙切齿:"比如说,先把衣服撕碎,然后掐住脖子,用各种方式折磨,直到对方哭着求饶...这就是你们日本军人最喜欢的凌辱。"
我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但她仍不依不饶:"你还要我继续解释吗?需要我用日语再重复一遍吗?'强姦','凌辱','蹂躙'...这些词你应该都看不懂吧?"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冷静:"不过我很好奇,波风凑,你为什么要我念给你听?是因为你真的想这么做,还是仅仅因为你看不懂这些汉字?"
我无言以对,只能感觉到耳根发烫。她的问题像一把尖刀,直直戳入我内心最懦弱的部分。
"你这么小,应该还在上高中吧?"她的语气突然软化下来,但话中的谴责更让人难以承受,"连这些下流的字都不认识,就想学着去做这种事?你父母知道他们的儿子是这样的吗?"
我苦涩的开了口:“我的父亲在九一八那年死在你们中国人的军队手中,我家里只有我母亲,妹妹还有我….”
苏雅婷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她那双总是带着讽刺的眼睛微微眯起,里面的战意稍稍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色。
"所以,"她轻声说,"你参军是为了报仇?"
我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地面。记忆中那个身穿军装的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摸着我的头说要保卫祖国的画面,仍然如此鲜活。
"波风凑,"她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语气说道,"你知道吗?战争就是这样,仇恨永远是轮回的。你的父亲死在中国人手中,所以你要加入军队报复中国人。然后也许有一天,会有中国人的儿子也想要报复日本人..."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柔和:"但你想想,这样有意义吗?你母亲和妹妹,她们真的希望看到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吗?"
我抬起头,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那不像是胜利者的怜悯,反倒像是一种深沉的理解。
"你知道吗?"她继续说,"在太行山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可以是老师、医生、农民,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战争改变了一切,让他们不得不拿起枪..."
阳光透过铁窗斜射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这一刻的她不再是那个嬉笑怒骂的俘虏,而像是一个在战场上看透了生死的长者。
"你母亲一定很辛苦吧,"她轻声说,"既要照顾家,又要抚养你们。她一定很希望你能平安回家,而不是..."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但我们都明白后面的意思。
我此时有些愤怒的打断她的话,要求她交出名单,不然自己就会按照书上对她进行强奸,你也不想被一个小日本鬼子强奸吧?
"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她的声音陡然变冷,眼神里迸发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光芒,"我早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更不会被这种威胁吓倒。"
她抬起头,直视我的眼睛:"你说得对,我确实不想被你这样的人玷污。但是..."
她突然用力扯了扯手铐,发出铮铮的响声:"你以为我真的在乎吗?我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别说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子的威胁,就算是真的..."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势:"就算是真的被你玷污,我也不会背叛我的信仰,不会出卖我的同志!"
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光芒。那种光芒让我感到羞愧,感到渺小。
"而且,"她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你确定你做得出来吗?你这副样子,连威胁都像是在撒娇。"
她歪着头看着我:"要不要我教教你?真正的男人是怎么面对敌人的?还是说,你只想学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虚张声势的外表,让我看到了内里不堪的真实。
"最后问你一次,波风凑,"她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你是想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还是想做一个只会欺辱弱者的懦夫?"
我咬着嘴唇苦涩的说道:“我只做一个忠诚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军人,我只给你两条路,第一条是交出名单,第二条路是被我强奸。
"就这两条路?"她轻笑一声,眼神里却是冰冷的,"那你有没有想过第三条路?"
她突然用力蹬地,借着镣铐的力道让椅子往前倾,距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她仰着头,目光如炬地注视着我:
"那就是你既得不到名单,也做不到威胁的事。"
她的声音逐渐提高:"你以为你是谁?就凭你这样连审讯手册都看不懂的小鬼,也配对我们用这种方式威胁?"
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扑在我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压迫感:"来啊,动手啊!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她忽然扯开自己的衣领:"怎么?这就怂了?连看都不敢看,摸都不敢摸,还算什么男人?"
她的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你的所谓效忠,就这么点骨气吗?连直视敌人都不敢,只知道躲在书本后面找所谓的'规则'?"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我站在原地,既不敢上前,也不敢后退,像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怜虫。
"知道吗?"她的声音忽然又软了下来,却带着更深的讽刺,"你现在这副样子,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战士都要可悲。至少他们,是站着死去的。"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战胜从来都不是靠暴力和威胁,而是像她这样,用气节和尊严,彻底粉碎对手的意志。
我用力的把她推了回去,随即打开她的手铐把我推倒在床上:“够了!我不要听!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我现在就要强奸你!”
别看我这样,我是关东军一名少尉,毕竟我在陆军学校是第一名的成绩,再加上我的老师自来也是关东军大将,他为我的前程付出了很多。
1937年我们日军全面入侵中国,我在内心不赞同这场战争,但是为了国家,老师和家人,我还是来到了中国晋察冀地区,来到一所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做监狱长
黄昏时分,我站在监狱长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院子里穿着灰色囚服的犯人们在寒风中排着队。我身着崭新的军装,胸前的徽章在夕阳下泛着冷光。
这间办公室很大,装修也算得上豪华。深棕色的实木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份档案,都是关于囚犯的资料。角落里是一个红木书架,上面摆满了法律和军事相关的书籍。
我轻轻叹了口气。虽然才18岁,但我深知这份工作的分量。关东军大将自来也老师临行前对我说:"凑,你要用智慧和勇气来管理这座监狱。"
突然,传令兵敲响了房门:"波风少尉,共产党的重要俘虏已经到了。"
我整理了一下制服,迈步走向门口。走廊尽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几个宪兵押送着一位年轻的女性走了过来。
她看起来二十出头,个子不高但身材丰满。即使身着粗布囚衣,也掩盖不住那对饱满的奶子和圆润的翘臀。她的脸上带着倔强,但眼神中透着一丝惊慌。
"报告少尉,这是我们在平型关抓获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名叫小兰。"宪兵队长递上来一份文件。
我接过文件,目光在这位叫小兰的女囚身上扫过。她低着头,但从她微微发抖的身体可以看出她的紧张。
"带下去吧,单独关押。"我说完,转身回到了办公室。夜幕即将降临,这座冰冷的监狱又将迎来一个漫长的夜晚。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内心却升起一丝不安。作为一名军人,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说来可笑,这里虽然是日本人关押中国共产党的监狱,但是这里只有我一个日本人,这所监狱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皇协军,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汉奸,我内心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对待共产党,对付自己同胞的态度比我这个真正的日本人凶恶的多得多
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外面传来的谩骂声和皮靴踏地的声响。那些皇协军正在押送新到的囚犯。
张队长是这群人中最令人厌恶的一个。他四十来岁,身材矮胖,总是穿着一件擦得锃亮的皮夹克,领口敞开着露出油腻的脖子。每次见到他对着中国囚徒又打又踢的样子,我都觉得一阵反胃。
"波风少尉!"他那难听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那个共党女俘虏不肯开口,要不要我们好好'招待'一下?"
我望着窗外。张队长身后跟着七八个同样面目可憎的打手,他们都摩拳擦掌地等着审讯的命令。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我手中的权力的渴望。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这些叛徒总是用最残酷的方式折磨自己的同胞。
小兰被关在了三号审讯室。我能想象到她此刻正蜷缩在冰冷的铁椅子上,身上的囚衣单薄地几乎遮不住她那对肥硕的奶子和浑圆的屁股。那些皇协军一定已经用色眯眯的眼神把她的身子看了个遍。
我站起身,整了整军装。作为一个日本军官,我本该同意他们的请求。但这群畜生般的走狗让我作呕。他们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更是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丧失殆尽。
"张队长,"我冷冷地说,"今天先把她关起来。明天早上再说。"
张队长脸上的期待变成了失望,但他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这群人就是这样,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扬威,见到日本军官就立刻变成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回到办公桌前,我拿起自来水笔,在值班日志上写下今天的日期。夜晚还很长,我能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寒风,呼啸着穿过监狱的铁栅栏。在这个满是背叛和仇恨的地方,我仿佛也能感受到小兰此刻的恐惧与无助。
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我不该承受这样的重担。但我明白,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被迫站在了某个立场上。只是没想到,最让我反感的,竟是这些打着日本旗号的中国叛徒。
正午的阳光透过铁丝网照射在监狱的水泥地上,形成一道道刺目的光影。我沿着监区的通道缓步巡视,皮靴踩在地上发出规律的声响。
远远就看见张队长那臃肿的身影,他正押送着一批新犯人。这群共产党的衣衫褴褛,脚步蹒跚,但他们的眼神里都闪烁着不屈的光芒。张队长每走一步都要踹上一脚,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咒骂着。
"你们这些该死的共匪!"张队长吐着唾沫,"看看你们现在的德行!"
"呸!你这个卖国贼!"一个男犯人猛地抬起头,眼中喷射着怒火,"你有什么资格骂人?"
正当我准备上前制止时,张队长突然抬脚狠狠踹向队伍最后的那个年轻女孩。她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一头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着,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灰布囚衣,胸前的纽扣掉了几颗,露出了里面白皙的肌肤。
女孩猝不及防,重重摔倒在水泥地上。她的手掌擦破了皮,鲜血渗了出来。其他犯人纷纷叫喊起来:
"住手!你这个畜生!"
"你还有没有人性?"
张队长狞笑着又要上前,但这次我抢先一步挡在他面前。
"够了!张队长。"我用冷冽的声音说道,"这里是监狱,不是你的杀猪场。"
张队长悻悻地退了几步,谄媚地看着我的肩章:"是是是,少尉大人说得对。"
我蹲下身,扶起那个跌倒的女孩。近距离看去,她长得很清秀,脸蛋红扑扑的,虽然衣着褴褛但掩不住少女特有的青涩魅力。她的手腕和脚踝都有淤青,显然是路上受了不少虐待。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我想递给她:"吃吧,补充些体力。"
谁知道她竟然用力推开我的手,倔强地抬起头:"不用敌人施舍!"
她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嘴角还带着一丝倔强的笑意。这种视死如归的姿态让我心中一震。
张队长还在一旁蠢蠢欲动:"少尉大人,要不要......"
我打断了他的话:"把他们带下去,不准虐待。"
看着犯人们消失在牢房的背影,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老师总说:真正的敌人未必是站在对面的人,有时反而是在你身边那些迷失本性的人渣。
夕阳西斜,透过百叶窗在我深棕色的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轻轻摘下脖子上的护身符,这是一块朴素的棉布包裹,已经被汗水浸染得有些发旧。指尖轻抚过布面,似乎还能感受到母亲缝制时的温度。
护身符里装着一片神社祈福的符纸,还有一缕妹妹的头发。记得临行前的那个雨天,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专注地缝制着护身符,银色的发丝在微弱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妹妹则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换上军装。
"凑啊,"母亲的手有些颤抖,"你要好好保护自己。这护身符里装着织姬的一缕头发,保佑你平安归来。"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办公室里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那是潮湿的墙壁散发出来的。远处传来犯人的咳嗽声和铁链的碰撞声,但这都不能打扰我对家乡的思念。
拿出抽屉里的照片,那是全家在东京郊外踏青时拍的。照片上的妹妹还是个高中生,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那么纯真。现在她应该已经习惯了没有兄长的生活吧?
夜幕渐渐降临,窗外传来值勤士兵交接班的脚步声。我将照片重新放回抽屉,摸了摸护身符。它是我和家乡唯一的联系,是我疲惫时的精神寄托。
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死离别。那些被抓来的共产党犯人,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女儿,也会有人像我的母亲一样,在远方牵挂着他们。
张队长他们又开始在审讯室里折腾了,隐约可以听见痛苦的呻吟声。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月光洒在院子里的石板路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在这个遥远的异乡,我只能靠着手中的护身符,寄托对亲人深深的思念。
母亲现在也许正坐在厨房里,像往常一样准备着晚餐;妹妹可能正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专心读书。而我,却在这里,穿着军装,管理着一座关押敌对分子的监狱。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现在的我又会在哪里?会不会在东京某个温暖的教室里,继续着平凡的学业?
初春的清晨,我正在办公室里读着自来也老师的来信。信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透着几分严厉:"凑,你太软弱了。作为一名军官,必须要有果断的决断力。现在派给你一个任务..."
"少尉大人!"张队长推开门,脸上堆着献媚的笑容,"您要的犯人带来了。"
我抬起头,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禁愣住了。一位约莫二十八九岁的女性站在门口,她穿着略显褴褛的八路军军服,军裤管卷到膝盖,露出满是伤痕的小腿。她的双脚赤裸着,沾满了泥土和血迹,但她站着的姿势依然挺拔。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眼睛,清澈而坚定,炯炯有神地凝视着我。她扎着一根利落的马尾,几张碎发粘在额头的汗珠上。虽然衣着简陋,但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这就是犯人苏雅婷。”张队长搓着手说,"我们昨晚在太行山区抓到的。她可是个大人物,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政委。"
我站起身,第一次感到有些局促。这个女人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完全不像我见过的其他囚犯。她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带着一种悲悯。
"喂,小鬼子。"她突然开口,声音清亮而有力,"你这么年轻就来当汉奸了?"
我微微皱眉:"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军官。"
她冷笑一声:"在日本还是个小孩子吧?看看你这身高,怕是连征兵线都够不到,是不是靠着家里的关系才混到这个位置的?"
我确实比同龄人要矮一些,在日本时就经常因为身高被人取笑。但现在被一个囚犯这样嘲讽,让我感到既羞耻又恼怒。
"你们昨天抓了我的一支小队,"她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挑衅,"想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这正是自来也老师要我查明的情报。
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嘲弄起来:"想让我说出来?那就拿出点诚意来。"
张队长立刻会错了意,撸起袖子就要上前:"少尉大人,要不要我..."
住手。"我厉声打断了他。不知为何,我实在不忍心看这个坚强的女人受到伤害。但她刚才的话语又确实让我感到难堪,这种矛盾的心情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靠在门框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怎么?舍不得动手?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最喜欢用暴力逼供吗?来呀,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手段。"
我握紧了拳头,却又缓缓松开。晨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侧脸上,我看到她嘴角有一道新鲜的伤口,想必是抓捕过程中留下的。她的脚踝和手腕都有明显的勒痕,显然一路上没少吃苦。
"把她带到三号审讯室。"我最终说道,声音有些沙哑,"我要亲自审问。"
她跟着张队长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下:"喂,小日本..."
我抬头看她。
"...你的眼神跟其他日本兵不太一样。"她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心跳如雷。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囚犯。她不仅是敌人,更是一个让我深深困惑的存在。
审讯室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铁质的审讯椅和桌子被擦拭得锃亮,墙角的工具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刑具,但此刻它们都被一块深色的布帘遮住了。
苏雅婷坐在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扶手上。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的动作,眼神中依然带着戏谑和轻蔑。我拿出医药箱放在她脚边,打开时金属器械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怎么,小日本?"她微微歪着头,"准备给我用什么刑?听说你们日本军队最喜欢用针扎指甲缝..."她故意停顿了一下,"还是说...你对女俘虏有更好的手段?"
我充耳不闻,专注地调配着医用酒精。她的一双玉足确实伤得不轻,有些地方的皮肤已经溃烂发紫。长期行军让她的脚掌结了一层薄茧,但依然能看出年轻女子特有的纤巧。脚踝处有清晰的绳索勒痕,想必是被抓捕时遭受了不少折磨。
"别废话了,乖乖消毒。"我拿起纱布蘸了酒精,轻轻按在她的伤口上。
"嘶——"她倒吸一口冷气,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哟,还挺温柔的嘛。该不会是是想用这种方式瓦解我的意志吧?"
我没有回答,认真地为她处理着每一处伤口。她的脚趾修长而干净,看得出平时很注意保养,不像一般农村姑娘那样粗糙。这让我很好奇她的背景。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一边包扎一边问道。
"你觉得呢?"她反问,语气中带着调侃,"看我的脚就能猜出来了,是不是?"
阳光从高处的小窗斜射进来,在她的脚背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线。我继续沉默着,手中的动作越发轻柔。
"奇怪,"她突然说,"我见过那么多审讯官,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要么野蛮粗暴,要么假惺惺地套近乎..."她直视我的眼睛,"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我抬起头,发现她的眼神里除了警惕,似乎还藏着一丝好奇。我们四目相对,空气中有片刻的寂静。
"你知道吗?"她打破了沉默,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你要是换个国籍,说不定还是个好孩子。"
这句话让我的手顿了一下。酒精顺着她的脚背流下来,在椅子腿上留下一道透明的痕迹。外面传来巡逻士兵的脚步声,沉重而规律。
"你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脱口而出,随即又为自己的天真感到懊恼。
她笑了,这次的笑声里少了些许嘲讽,多了几分真诚:"也许...你会是我教过的学生吧。我看你这副书生气,肯定是个好学生。"
我低头继续包扎,努力掩饰内心的波澜。这个答案让我感到既意外又心酸。
简单的为她处理好脚上的伤,我内心记着自来也老师的任务,于是开始认真的说道:“我的名字是波风凑,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也是这所监狱唯一的日本人。苏雅婷小姐,我知道你有一份八路军地下党的名单,请你把她交出来,不然我会对你用暴力手段。”
我说出这番话时特意提高了声音,试图让自己听起来更有威慑力。但苏雅婷听完却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狭小的审讯室里回荡。
"哈哈哈...对不起,实在忍不住。"她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水,"你这孩子太可爱了。"
她晃了晃被铐着的手腕:"第一,叫我小姐?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最喜欢说'该死的支那共匪'吗?第二,威胁要用暴力?那你怎么到现在连我的绑都没松?"
她向前倾了倾身子,距离近得让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药草香。那是太行山上常见的草药味道。
"小鬼子,你今年多大?十八?十九?"她的声音突然温柔了下来,但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惊的穿透力,"你觉得,就凭你这样的性格,能当好一个刽子手吗?"
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但她继续说道:"看你的眼睛...干净得像个孩子。应该在学校里读书吧?为什么会来这里?"
她的语气里没有之前的嘲讽,反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怜惜。这让我不知如何应对。明明她是我的阶下囚,此刻却像是她在审视我。
"我..."我刚要解释,她却打断了我。
"知道吗?"她轻轻活动着刚被包扎好的双脚,"你的手法倒是挺专业的。看来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学生。可惜啊..."
她摇了摇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窗外:"现在日本的年轻人,都太容易被大人们骗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烦躁:"够了!我不想听这些!那份名单在哪?"
她反而笑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要用暴力?来吧,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孩子能做出什么事来。"
她的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拆穿的拙劣演员,所有的威胁和威压在她面前都成了笑话。
这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也许她才是那个真正掌握主动权的人。
我此时忍不住皱起眉头的说:“我再说一遍,你不要以为我吓唬你,我真的会对你用暴力手段的!虽然我是第一次做审讯别人,但我也知道什么叫做严刑拷打,你不想尝尝那个滋味吧?”
哦?"她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趣味,"第一次审讯?难怪我觉得你像个刚出道的学生。"
她突然用力挣了挣手铐,发出"咔嚓"的声响:"严刑拷打?那就试试呗。反正我们共产党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她的眼神变得异常明亮,像是燃烧的火苗:"来吧,让我看看日本帝国主义的酷刑有多厉害。你们会用电刑吗?还是打算用老虎凳?或者灌辣椒水?我听说你们最喜欢用针扎指甲缝..."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子一样戳进我的心里。我攥紧了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闭嘴!"
"不闭。"她反倒笑得更开心了,"我偏要说。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吓倒我吗?小孩子扮大人,终究是装不像的。"
我的喉咙发紧,胸口剧烈起伏。她的话确实戳中了我的软肋——是的,我确实是第一次审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日本军官。
"你知道吗?"她见我沉默,反而放缓了语气,"你的眼神,跟我教过的学生一模一样。他们也都是这样,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却被现实逼得不得不长大。"
她的声音渐渐温柔,但却让我的心更加混乱:"但你要记住,真正的成长不是学会残忍,而是即使面对残酷,也要保持内心的光明。"
阳光穿过铁窗的缝隙洒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超越年龄的睿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她能在如此处境下依然保持着从容。
我转过身,不愿让她看到我眼中的动摇。耳边传来她轻柔的声音:"所以,小鬼子,你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是想做一个合格的刽子手?这选择权在你手里。"
我的手在颤抖,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因为害怕。害怕她看穿了我脆弱的伪装,更害怕她说出了我心里最深层的恐惧。
我为了掩饰恐惧,故意说道:“好了,既然你拒不配合,我就要严刑拷打你了!”
随即我立刻走到书架前拿起一本审讯大全看了起来,但随即我就茫然的放下了书。
因为这本书是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写的,虽然我会说中国话,但是我却不认识大部分的中国字。
我尴尬地站在书架前,手里捧着那本厚重的《审讯大全》。封面上的汉字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书,虽然我从高中习中文,但面对这种专业性的词汇,我还是感到束手无策。
余光里,我注意到苏雅婷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既不是嘲笑,也不是轻蔑,而是一种近乎怜悯的神情。
"看不懂?"她突然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原来堂堂日本军官,连中国字都不认识啊。"
我急忙把书放回去,但动作显然过于慌乱了。书页哗啦啦地翻动着,最后重重地撞在书架上。
"连这都看不懂,还想审问我?"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要不要我教你啊?就像教小学生认字那样?"
我转身想要说些什么,但她接着说:"第三页第二行,'拶刑',"她用一种教师授课的语气念道,"就是用竹签夹手指,特别疼,很多人受不了。第五页第四行,'坐杠',就是把人捆在木桩上..."
我越听越觉得难受,攥紧了拳头:"住口!"
"怎么?"她歪着头,"你不是要看审讯大全吗?我倒是知道很多,要不要我教你更多?比如'剥皮''抽筋''剥指甲'..."
"够了!"我几乎是吼出声来。
她突然停止了说话,室内陷入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个被揭穿的骗子,所有的威严在她面前都成了一场拙劣的表演。
"你知道吗?"她最后说,声音温和得让我心痛,"有时候装得太过,反而更容易暴露。"
我又尴尬又恼怒:“这是你们中国人的叛徒,也就是你们说的汉奸写的!我是日本人会说中国话就不错了,不认识中国字很正常!”
"汉奸?"她轻笑一声,"看来你还真了解我们的事情啊。既然如此,那你也应该知道,这些刑罚手段都是你们日本人教会他们的。"
她的语气突然变得犀利:"你说得对,那些人确实是汉奸。但他们至少还敢直面自己的同胞,敢做敢当。你呢?穿着一身军装,拿着一份看不懂的审讯手册,连审问都不知道该怎么进行..."
我涨红了脸:"闭嘴!我警告你..."
"怎么?"她打断我的话,"让我说中了?你们日本人在自己国土上不也是一群普通人吗?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可为什么来了中国就一定要变成魔鬼?"
我后退了一步,靠在书架上。书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仿佛在嘲笑我的狼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她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你们日本军人在自己国内是怎么对待犯人的?会用刑吗?会这样虐待人吗?这些都是你们学来的,对不对?"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脊,努力找寻着反驳的话语,但她的话却像潮水般涌来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脊,努力找寻着反驳的话语,但她的话却像潮水般涌来:"你们入侵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现在还要让我们告诉你谁是地下党员?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连审讯都不会,只会搬出一本汉奸写的书。你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吗?"
我的喉咙发干,说不出一句话。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虚张声势的外表,让我看到了内里不堪的真实。
"波风凑,"她叫我的名字,声音突然变得柔和,"你告诉我,你真的相信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吗?"
我生气的叫她闭嘴,随即开始吃力的翻阅审问大全,随即翻到了审问女共产党的第一页。
第一页的标题写着一句献媚到极点的话语:“请太君大人抓住女共产党后,在审讯之前立刻进行强奸,这样还能用这些下贱的赤匪身体来取悦太君大人。”
我茫然的看着这句话,这复杂的中国字我没有一个认识。
我最后无奈又羞涩的把书拿给苏雅婷,要她念给我听并且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苏雅婷扫了一眼我手中的书页,她的表情突然凝固了。那双清澈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真实的愤怒,而不是之前的戏谑。
"你真的要看吗?"她的声音变得冰冷,"你们日本军人还真是...喜欢这种东西。"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这上面写的是,建议日本军官在审讯女共产党员之前先把她们..."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凌辱。说这样既能泄欲,又能打击我们的意志。"
说到这里,她突然冷笑一声:"怎么,波风凑,你想这么做吗?看来你不仅是来看守的,还是来享乐的?"
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手足无措地想要合上书本:"不...我只是..."
"只是什么?"她的声音越来越冷,"只是想知道怎么做吗?你这个肮脏的小人!"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激动的样子,她的胸膛剧烈起伏着,连手铐都发出铮铮的撞击声。
"你知道吗?"她的声音忽然又平静下来,这种平静比愤怒更可怕,"你们这些日本军人,连审讯都学不会,就要学着侮辱女人。真是可悲啊..."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你才多大?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吗?就要学着用这种方式糟践一个女性?"
我羞愧得几乎要钻进地缝,手中的书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我终于明白,"她轻声说,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你们这些侵略者,表面上趾高气昂,实际上连基本的人性都站不稳。需要依靠这些东西来壮胆,真可怜。"
我的脸蛋涨的通红,结结巴巴的说道:“这…意思就是…要我….书上说要我强奸你?不,你说的是凌辱,凌辱是什么意思?和日本话的强奸是一个意思吗?”
苏雅婷沉默了一会,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大笑。
"天哪...天哪..."她的笑声中带着一丝颤抖,"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不懂?还要我给你解释这个词的意思?"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好吧,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凌辱的意思,就是像你这样的侵略者,用最下流最残暴的方式,玷污一个女性的身体和尊严。"
她说每一个字时都咬牙切齿:"比如说,先把衣服撕碎,然后掐住脖子,用各种方式折磨,直到对方哭着求饶...这就是你们日本军人最喜欢的凌辱。"
我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但她仍不依不饶:"你还要我继续解释吗?需要我用日语再重复一遍吗?'强姦','凌辱','蹂躙'...这些词你应该都看不懂吧?"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冷静:"不过我很好奇,波风凑,你为什么要我念给你听?是因为你真的想这么做,还是仅仅因为你看不懂这些汉字?"
我无言以对,只能感觉到耳根发烫。她的问题像一把尖刀,直直戳入我内心最懦弱的部分。
"你这么小,应该还在上高中吧?"她的语气突然软化下来,但话中的谴责更让人难以承受,"连这些下流的字都不认识,就想学着去做这种事?你父母知道他们的儿子是这样的吗?"
我苦涩的开了口:“我的父亲在九一八那年死在你们中国人的军队手中,我家里只有我母亲,妹妹还有我….”
苏雅婷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她那双总是带着讽刺的眼睛微微眯起,里面的战意稍稍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色。
"所以,"她轻声说,"你参军是为了报仇?"
我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地面。记忆中那个身穿军装的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摸着我的头说要保卫祖国的画面,仍然如此鲜活。
"波风凑,"她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语气说道,"你知道吗?战争就是这样,仇恨永远是轮回的。你的父亲死在中国人手中,所以你要加入军队报复中国人。然后也许有一天,会有中国人的儿子也想要报复日本人..."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柔和:"但你想想,这样有意义吗?你母亲和妹妹,她们真的希望看到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吗?"
我抬起头,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那不像是胜利者的怜悯,反倒像是一种深沉的理解。
"你知道吗?"她继续说,"在太行山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可以是老师、医生、农民,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战争改变了一切,让他们不得不拿起枪..."
阳光透过铁窗斜射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这一刻的她不再是那个嬉笑怒骂的俘虏,而像是一个在战场上看透了生死的长者。
"你母亲一定很辛苦吧,"她轻声说,"既要照顾家,又要抚养你们。她一定很希望你能平安回家,而不是..."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但我们都明白后面的意思。
我此时有些愤怒的打断她的话,要求她交出名单,不然自己就会按照书上对她进行强奸,你也不想被一个小日本鬼子强奸吧?
"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她的声音陡然变冷,眼神里迸发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光芒,"我早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更不会被这种威胁吓倒。"
她抬起头,直视我的眼睛:"你说得对,我确实不想被你这样的人玷污。但是..."
她突然用力扯了扯手铐,发出铮铮的响声:"你以为我真的在乎吗?我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别说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子的威胁,就算是真的..."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势:"就算是真的被你玷污,我也不会背叛我的信仰,不会出卖我的同志!"
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光芒。那种光芒让我感到羞愧,感到渺小。
"而且,"她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你确定你做得出来吗?你这副样子,连威胁都像是在撒娇。"
她歪着头看着我:"要不要我教教你?真正的男人是怎么面对敌人的?还是说,你只想学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虚张声势的外表,让我看到了内里不堪的真实。
"最后问你一次,波风凑,"她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你是想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还是想做一个只会欺辱弱者的懦夫?"
我咬着嘴唇苦涩的说道:“我只做一个忠诚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军人,我只给你两条路,第一条是交出名单,第二条路是被我强奸。
"就这两条路?"她轻笑一声,眼神里却是冰冷的,"那你有没有想过第三条路?"
她突然用力蹬地,借着镣铐的力道让椅子往前倾,距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她仰着头,目光如炬地注视着我:
"那就是你既得不到名单,也做不到威胁的事。"
她的声音逐渐提高:"你以为你是谁?就凭你这样连审讯手册都看不懂的小鬼,也配对我们用这种方式威胁?"
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扑在我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压迫感:"来啊,动手啊!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她忽然扯开自己的衣领:"怎么?这就怂了?连看都不敢看,摸都不敢摸,还算什么男人?"
她的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你的所谓效忠,就这么点骨气吗?连直视敌人都不敢,只知道躲在书本后面找所谓的'规则'?"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我站在原地,既不敢上前,也不敢后退,像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怜虫。
"知道吗?"她的声音忽然又软了下来,却带着更深的讽刺,"你现在这副样子,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战士都要可悲。至少他们,是站着死去的。"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战胜从来都不是靠暴力和威胁,而是像她这样,用气节和尊严,彻底粉碎对手的意志。
我用力的把她推了回去,随即打开她的手铐把我推倒在床上:“够了!我不要听!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我现在就要强奸你!”
看一下反响,如果反响好就更新,毕竟是第一次写这种形式的小说,一旦写不好就容易崩,如果有人看会继续更新
还不错 但是后面辩论有点多了 对白就会脱离了角色 用力过度就会变成直接作者之口发声了 而不是角色自己的声音
写的真好,既融入了自己对战争的思考,而且两个人物的关系有一种反差感。
不考虑一下男主被苏军俘虏以后的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