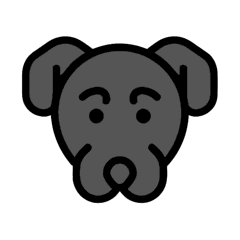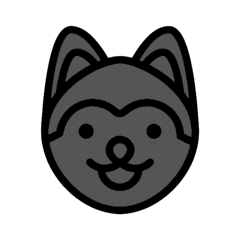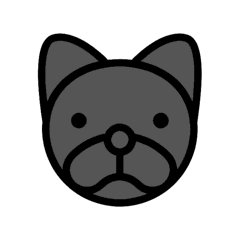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短篇)(已完结)贡掉九条命的猫
NTR短篇原创足交袜控原味臭脚虐杀贡奴败北催眠洗脑
写在前面)
考试前夕的m文灵感爆像是把时间贡给了女s一样...
本篇小说前期可能比较冗余,恳请大家可以读完,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好的感受。
啦啦~
考试前夕的m文灵感爆像是把时间贡给了女s一样...
本篇小说前期可能比较冗余,恳请大家可以读完,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好的感受。
啦啦~
“毕安,目前是这个名字没错吧。出生名为隆蒽,在十七岁时改名为裘牛,二十一岁改名为崖梓,二十三岁改名朝丰,二十五岁改名为苏安霓,二十七岁改名巴夏,二十九岁,也是去年改名为毕安。”
“属实。”
“在十三年内,你每一次改名都会伴随着一次身份的变换,居住地,工作,甚至资产与样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不同时期接触你的人进行询问后,关于你失踪的看法,好似统一口径了一般
——死了。
你是一个在十三年间‘死了’六次的人,关于你的文件总是莫名地中止,而又换了一套扮相莫名地诞生。诚然,这个世界太大了,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都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看见一个真正死了六次的人如今坐在我面前,抱歉,对于我的想象来说,您看上去平凡许多。”
“这或许就是我能这么做的优势所在呢。”他笑了,利索的头型与廉价的西装,好像就是一个将要回家的普通员工。
“老实说,我对你的这些‘光辉事迹’并不关心,毕竟再怎样折腾也是你的权力——不如让我们聊一聊那六位女性,六位曾“杀死”过你的女性吧。”
他那殷勤的笑容僵在了他脸上几秒,随后五官逐渐扭曲挤压,或许是因为整容的缘故,露出非人一般令人作呕的笑容,“您请说。”
“十七年前,也是你在高中的时候,你祖父的逝去为你留下了几乎全部的遗产。你为此被家里亲戚孤立,赶出了寄住的家庭,但是你没有辍掉学业,以十分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当地顶级的大学。但当我们询问了你的大学老师与同学时,他们对你的名字与样貌完全对不上,在他们口里的“隆蒽”,是另一个女孩。你并没有在那里上学,而是在周边的一个三本......”
“尚——她的名字。”他突然慵懒地打断道,“我们那时是在高考后的酒吧聚会里认识的。
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让我去吻她的脚,她穿着不知从哪借来的黑色纱裙,脚下穿的却还是学生时期的运动鞋棉袜,滑稽极了,但我却在那个时刻爱上了那种感觉,趁着酒意将她那白袜舔了个湿透。之后的事情我几乎断片掉,我只知当我醒来时我便成了她的狗。
从那晚回来后,我一边向她愈发疯狂地上贡,一边沉浸地舔着她那臭烘烘的脚。她的脚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穿过那破破烂烂的廉价运动鞋,也不用借那几近戏服般浮夸的黑色长裙。我给她眼界之外还要更远的一切,几万钱的丝袜与香水依旧没有掩盖住她的脚臭——那也是我深陷她无法自拔的原因,只要她弯一弯脚趾,便会有她几辈子也见不到的财产向她涌去——
然而她有一天倦了,收贡金这种PLAY对她来说已经不够新奇了,她将视线重新聚焦到我身上,开始让我去各种底层不能再底层的地方打工,再将那微博的薪水一并剥夺;她开始在各种场合内让我出丑,脱掉衣服,被她扇巴掌,在酒宴当着无数富翁的面吻她的脚趾,而这毁掉我名誉一切,只是为了能得到她穿了几周的袜子作为奖励。可以说,我的一切怪癖都是那时的她为我落下的烙印。甚至到最后,这些几近自毁的举动都成为了奖励本身。
高考分数出来当天,她用鞋跟一边导通着我的尿道,一边将我本来一片光明的志愿改成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垃圾大学,这种将前途毁尽的快感让我的大脑几乎麻痹,但是就在上交的前一刻,她还是将第一志愿改成了那个称得上我的大学。
或是失望,或是感恩,是对她大发慈悲的感激,更多的是对自毁中止的遗憾。但是她一边蹂躏着我的脑袋,一边在我耳旁恶魔般低语:
‘我要让我们的人生彻底交换~’
随后精关大开,污浊的精液被鞋跟顶回了尿道,改变了它一生的行迹。
就这样,九月份停在那所顶级院校前黑色加长轿车,下来的女孩光彩熠熠贵气非凡,完全与两个月前的她判若两人;而我则是独自打车去了一所没有校门的三本学院,从此后人生便逆转开来。或许这种冒名顶替的事情在如今看来不怎么可能,但是在那个时候去向校方砸些钱,靠些关系总是能成的。我承包了她大学期间所有的作业,用钞票垒成砖将她本该属于我的前路一点点夯平,绩点,职位,竞赛,留学,她所做的只是在当地最高级的餐厅坐着玩手机,无数这个教授那个会长的都会毕恭毕敬向她敬酒;而我却只能蜷缩在恶臭的宿舍中,在室友的嘈杂与烟味中帮她安排好这一切。
终于,载着她的飞机去到了美国,送她到世界最高级的学府去“深造”,而在更加刺激的诱惑下,她的花销更大了。她认识了黑人的男朋友,尝到了一些国内根本没有的体验......但是那晚后,她再也没有发过一条消息。
她死了。死在了黑人的床上,或是死在了铺满钞票与白粉的浴缸中,我不在意。我只知道我害死了她,将她平凡的生活加速了几十年,给予了她可能几辈子也收获不到的快感,就在短短四年中......
一开始我也是哭,哭了几天后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了,我的这种悲伤,并不源于对自己的悔恨或是对她的不舍,而是像一个顽童在为自己掰断了玩偶的头而哭——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自己没东西可玩了,仅此而已。尽管我叫了她无数次主人,在她的脚下磕了无数次头,但是从始至终,她都是我的玩物,她手里象征权力的鞭子,也不过是我给她的罢。
尚教会了我好多,我开始意识到,这种身份的颠覆是多么令人沉浸的游戏——于是我将我的遗产不均等的分为了几份,写好了遗书,在第二天清晨坐上了黑色轿车,从此换了副模样活于世上。要我说有钱就是好,一个人的死亡与重生,只要花钱在报纸上登几条新闻,到医院办些证件,再造一个“金丝鸟笼”,将一个人的人生隐掉取而代之,便能重新REBORN,出乎意料的简单。”
“所以你的第二次REBORN,是成为了——”
“一个名为裘牛的酒保,一个死心踏地为一个酒吧女付诸全部的人。开始只是偶尔为她免单,慢慢地,她的朋友,她那几小时一换的男伴,开始放肆地开那货架上珍藏的洋酒,并全部纳为我的账单上,我开始被老板斥责,被罚掉本就微不足道的工资;被醉醺醺的酒鬼提着衣领,像个玩具一般丢在地面上;甚至在她那包臀裙的裙底,成为了她的椅子,甚至是便器。她开怀大笑洒下的黄色尿液,是我这辈子尝过最难品而最过瘾的佳酿,只要你能品出那份“耻辱”的味道。
然而这样的酒吧女,生活又有什么样的保障呢。一场骚乱,两声枪声,一颗子弹穿过了她情夫的头颅,一颗则穿过了她纹着玫瑰的后背。他的老公愤怒地红着眼睛,在那酒吧里巡视了所有人,也没有怀疑那个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害怕,只是想起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她。
“我第一次来这里,请问有什么推荐?”那时候她顶着微微卷曲的烫发,微笑的问着我,那一刻的散发的光似乎告诉我她不属于这里,但是当我免费将一杯提子酒推到她面前,她眼里不经意流转而过玩味的眼神,正是那几乎瞬时的一瞥,将她一生都留在了那个酒馆里。”
“可是,那场骚乱里好像死了不止两个人。”
“毕竟叫做骚乱,几只鸟叫了几声,叶子有几片落在地上,都无人得知。我也是在那个时刻“死去”的,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就此消失,也没人会在意。随后我坐上了早就在马路上停好的黑色轿车,将那黑色背心扔在了酒馆门前的泥坑里,可惜,再也没有淑女踩着过去了。”
“所以,你每次都会将一生的钱砸给一个与你不相干的女人?”
“与其说是上贡给别人,我更想说这都是上贡给我自己,警官,是我砸钱为我塑造了那样别出心裁的一生,她们只是被我挑选的女演员,仅此而已,我给予他们的片酬不菲,可惜的是她们没有迎来自己的好结局。”
“哼,说的好听,不过我更希望你长话短说:二十一岁你更名为睚眦,工作是——普通公司的职员,那时候你遇到的是——”
“雅,多好听的名字,一个海归的财务实习生,趾高气扬地将她所有的工作交付给我,再将我的工资自动划为我每个月的“桌下出租费”。然而消费水平的提高,两个人的工资显然无法满足她的需求,她便一边用脱下的黑丝紧紧勒着我的咽喉,一边强迫我从公司报表里魔法般变出钱来。笨蛋,就算将一切锅坐在我头上,真正财务的名字也是她才对,就这样我陪着她一起坐了牢,听到她在牢里死讯后便再‘活’出来就是了,你没有印象吗,警官?”
“二十三岁,你更名为朝丰,那时候的对象是——”
“家庭主妇,好像叫做潼吧,家里有个五岁的孩子,那时候我在给她孩子做家教。在她辱骂她家小孩时便看出了点端倪,随后以聊聊孩子为由把她约了出来,噗嗤,哪有在外面聊孩子的,当她从皮包里拿出皮鞭时,我简直高兴到流鼻血了。但是该说是一物降一物还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她的老公是个家暴超雄,在发现包里的皮鞭后,就一点一点把她抽死了。天呐,真羡慕啊。”
“二十五岁,苏安霓——”
“啊那个时候是我给我留钱最多的“一生”,一个死去双亲的富家少爷,与我本人多么相似,只不过我留给自己的豪奢只有原先的七分之一,找的女主角则是来我们家的女仆。那种下克上逆转的喜悦,真是让人十分想念,我还记得她将家产的存折放在我的胯下,一边用白丝将我的精液拧出来时,将存折上我的名字彻底玷污掉的快感,简直让我现在都能射出来。我将一切都给予了她,从她的主人变成了她的仆人,随后又被她像狗一样赶出了我的家,就像钻回了我的子房一般,我又一次钻进了那辆黑色轿车,迎来我的是第二天的太阳。”
“所以说她并没有死?”
“厄运往往是如此的诙谐而滑稽,一个女仆居然会忘掉了浴缸旁边不能用电器的规矩。”
“二十七岁,巴夏。”
“一个畅销作家。当然所谓畅销也不过是提前用钱营销出来的把戏,遇到的是一位叫做明子的记者,多么有野心的女孩,能从我的粉丝变成霸占我一切的杜鹃。将我还为写完的文字占为既有,一边要逼迫我在网上向一直以来抄袭她的行为道歉。剥夺掉我一切名声财产之后,甚至玩味地在网站里发了一个用脚撕掉我之前书的视频,可真够大胆的。不过之后的故事,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听说了,人们发觉她之后的创作和以前大相径庭,一边开始伤害网爆她,一边开始缅怀已经‘死去’的我,到头来硬生生逼到让她在房间里自尽。哎,都怪那该死的文艺病,不过她到最后连我的死法也要抄袭,该说是从一而终吧。”
“三十岁。”
“哒哒,就是现在的我啊。”
“一个老师,对吧?”
“在一个很偏远的县城里教孩子英语,倒也不是什么误人子弟的活。”
“那你如今的对象是——”
“......”
“难道还没找到?”
“大概,不能算是对象吧。
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次意外中,她仓皇地坐在了我的对面,询问我有没有位置,那本来是朋友介绍给我新姑娘的座位,却饶有兴趣的让给了她,她向我笑了笑,随后向服务生比了个耶,示意两份馅饼。
她能在性癖上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而我将一切弱点都暴露给她的时候却又无动于衷,她不收钱,只是会让我拉着她去吃她喜欢吃的大餐;她偶尔也会收我的礼物,但是每次看她为了能送出等价回礼拼命的样子又让我不忍心,当我牵着她的手平视她时,她的眼神里好像放着温柔的光。
我现在还没有告诉她我的REBORN,但是我跟她说过,我其实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她会问我,有钱能吃到星星吗?
我会恳切地告诉他,真的可以。
她那时候说,骗你的,星星不好吃,我们去吃阿萨利亚吧,好久没有吃他们家的馅饼了。
她不仅是个好女孩,我遇到的那些女孩都可以称作为好女孩,是我把他们的贪心剖了出来作为我的药引,但是不管我怎么刨析她,似乎她的内心里,除了馅饼与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开始怀恋我的这“一生”,我像一只猫,一只有九条命的猫,我在不断的折磨中上贡着自己的命数,但是在这一次,我遇到了一个不愿意伤害我的人,她只会抱抱我,掐掐我的鼻头,这或许是对我一生以来最大的治愈,又或是对我那肮脏的前世最灼心的折磨。”
说罢,他拿出眼镜布,哈了口气,擦了擦眼镜。随后收起了他恍惚的深情,稍微正色跟她说道。
“但是警官,虽然我无数次颠覆了自己的身份,虽然我是那些女孩死的根本诱因,但是我并没有真的杀害她们。如果没有什么真正的证据,是并不能因为我说的这些定我罪的。”
“你似乎误会了什么,那些女孩的死去早已结案,既往不咎,也没人愿意动那几年前的烂摊子。”
“谢谢警官,那我坐在这里的原因是——”
“狄的自杀案。”
“什么?”
“今天中午一点,狄女士在家中自杀,留下了一封控告她丈夫对他施行家暴的遗书,我们在她丈夫的床下找到了大量皮鞭与行刑工具,在她身上找到了相似的伤痕,她的丈夫,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
“你,你在说什么?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这根本不是她的字迹,她的那些工具,都是用来调教我的啊?怎么可能!你告诉我!一定是搞错了!”他发疯一般挣脱出来,向着她面前的空气撕咬着。
“六号审讯室,犯人应激,请求关闭执法记录仪。”
她确认之后,一脚将他踹在了地上。
踩在他胸前的,居然是一双高跟鞋。
他似乎一瞬间觉悟到了什么,但又说不出口。堵在他喉咙里的不只是乱如麻的思绪,还有黑色漆面的高跟鞋头。
“将家产分为九份,隐姓埋名地偷偷爽几辈子,该说不说你还是蛮有想法的。可惜了,会“死而复生”的不止你一个人哦。”
她的另一只鞋,滑向他的下体,缓缓地揉搓着。
“离开家久了,连几个姐姐都记不清楚,更别提长相什么的了。哪怕你有那么多钱,就算你能活九条命,我也要一条一条的将你杀死,把你的家产一点~一点给我射出来——”
她的鞋子几乎一半伸进了男人的嘴里,他的眼角留着激动的泪水。
“可惜了,让那个臭婊子捷足先登,还没让姐姐我享受到这种快感,还想着能成家,真够搞笑的。你敢相信她面对几个大汉自卫时候,还拿着你给她的皮鞭呐~你是给她了多大的勇气呢,我的~偷~腥~猫,我的小~弟~弟~
只要哪里有一点鱼腥味,就走不动道路,连死几次都不长记性,还说什么‘女人是我的玩偶’,到头来不还是一只踩不死的小蟑螂,既然没让我爽到,那我就一次性把你剩下三条命全部榨出来好不好~”
她的丝袜足逐渐加快~
五
要射出来喔~不管有再多家产~也要一并喷出来~
四
想不想看看那些曾经整死你的姐姐啊,一会就带你看好不好~
三
快把你的精液全部射出来,把那可憎的基因喷出来,让那老头看看,自己选的继承人阳痿的小鸡鸡,根本没办法传宗接代呢~
二
这些精子就死在姐姐的脚上,要死咯~要死咯~
一
“无罪——
——释放!”
在锤子敲响的那一刻,他射了出来。那一刻他多希望是监禁几十年甚至无期徒刑,但是迎接他的终将是“死刑”。
“啊啦啊啦,要重生咯,我的小犯人~”
阳光明媚的马路上,停着那辆他熟悉的黑色轿车,每向前走一步,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的鸳声燕语。那个曾经让他重生的“子宫”,这一次会将他熬成精子,‘死’在姐姐们的脚上......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而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天下又哪来的龙呢?
“属实。”
“在十三年内,你每一次改名都会伴随着一次身份的变换,居住地,工作,甚至资产与样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不同时期接触你的人进行询问后,关于你失踪的看法,好似统一口径了一般
——死了。
你是一个在十三年间‘死了’六次的人,关于你的文件总是莫名地中止,而又换了一套扮相莫名地诞生。诚然,这个世界太大了,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都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看见一个真正死了六次的人如今坐在我面前,抱歉,对于我的想象来说,您看上去平凡许多。”
“这或许就是我能这么做的优势所在呢。”他笑了,利索的头型与廉价的西装,好像就是一个将要回家的普通员工。
“老实说,我对你的这些‘光辉事迹’并不关心,毕竟再怎样折腾也是你的权力——不如让我们聊一聊那六位女性,六位曾“杀死”过你的女性吧。”
他那殷勤的笑容僵在了他脸上几秒,随后五官逐渐扭曲挤压,或许是因为整容的缘故,露出非人一般令人作呕的笑容,“您请说。”
“十七年前,也是你在高中的时候,你祖父的逝去为你留下了几乎全部的遗产。你为此被家里亲戚孤立,赶出了寄住的家庭,但是你没有辍掉学业,以十分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当地顶级的大学。但当我们询问了你的大学老师与同学时,他们对你的名字与样貌完全对不上,在他们口里的“隆蒽”,是另一个女孩。你并没有在那里上学,而是在周边的一个三本......”
“尚——她的名字。”他突然慵懒地打断道,“我们那时是在高考后的酒吧聚会里认识的。
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让我去吻她的脚,她穿着不知从哪借来的黑色纱裙,脚下穿的却还是学生时期的运动鞋棉袜,滑稽极了,但我却在那个时刻爱上了那种感觉,趁着酒意将她那白袜舔了个湿透。之后的事情我几乎断片掉,我只知当我醒来时我便成了她的狗。
从那晚回来后,我一边向她愈发疯狂地上贡,一边沉浸地舔着她那臭烘烘的脚。她的脚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穿过那破破烂烂的廉价运动鞋,也不用借那几近戏服般浮夸的黑色长裙。我给她眼界之外还要更远的一切,几万钱的丝袜与香水依旧没有掩盖住她的脚臭——那也是我深陷她无法自拔的原因,只要她弯一弯脚趾,便会有她几辈子也见不到的财产向她涌去——
然而她有一天倦了,收贡金这种PLAY对她来说已经不够新奇了,她将视线重新聚焦到我身上,开始让我去各种底层不能再底层的地方打工,再将那微博的薪水一并剥夺;她开始在各种场合内让我出丑,脱掉衣服,被她扇巴掌,在酒宴当着无数富翁的面吻她的脚趾,而这毁掉我名誉一切,只是为了能得到她穿了几周的袜子作为奖励。可以说,我的一切怪癖都是那时的她为我落下的烙印。甚至到最后,这些几近自毁的举动都成为了奖励本身。
高考分数出来当天,她用鞋跟一边导通着我的尿道,一边将我本来一片光明的志愿改成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垃圾大学,这种将前途毁尽的快感让我的大脑几乎麻痹,但是就在上交的前一刻,她还是将第一志愿改成了那个称得上我的大学。
或是失望,或是感恩,是对她大发慈悲的感激,更多的是对自毁中止的遗憾。但是她一边蹂躏着我的脑袋,一边在我耳旁恶魔般低语:
‘我要让我们的人生彻底交换~’
随后精关大开,污浊的精液被鞋跟顶回了尿道,改变了它一生的行迹。
就这样,九月份停在那所顶级院校前黑色加长轿车,下来的女孩光彩熠熠贵气非凡,完全与两个月前的她判若两人;而我则是独自打车去了一所没有校门的三本学院,从此后人生便逆转开来。或许这种冒名顶替的事情在如今看来不怎么可能,但是在那个时候去向校方砸些钱,靠些关系总是能成的。我承包了她大学期间所有的作业,用钞票垒成砖将她本该属于我的前路一点点夯平,绩点,职位,竞赛,留学,她所做的只是在当地最高级的餐厅坐着玩手机,无数这个教授那个会长的都会毕恭毕敬向她敬酒;而我却只能蜷缩在恶臭的宿舍中,在室友的嘈杂与烟味中帮她安排好这一切。
终于,载着她的飞机去到了美国,送她到世界最高级的学府去“深造”,而在更加刺激的诱惑下,她的花销更大了。她认识了黑人的男朋友,尝到了一些国内根本没有的体验......但是那晚后,她再也没有发过一条消息。
她死了。死在了黑人的床上,或是死在了铺满钞票与白粉的浴缸中,我不在意。我只知道我害死了她,将她平凡的生活加速了几十年,给予了她可能几辈子也收获不到的快感,就在短短四年中......
一开始我也是哭,哭了几天后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了,我的这种悲伤,并不源于对自己的悔恨或是对她的不舍,而是像一个顽童在为自己掰断了玩偶的头而哭——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自己没东西可玩了,仅此而已。尽管我叫了她无数次主人,在她的脚下磕了无数次头,但是从始至终,她都是我的玩物,她手里象征权力的鞭子,也不过是我给她的罢。
尚教会了我好多,我开始意识到,这种身份的颠覆是多么令人沉浸的游戏——于是我将我的遗产不均等的分为了几份,写好了遗书,在第二天清晨坐上了黑色轿车,从此换了副模样活于世上。要我说有钱就是好,一个人的死亡与重生,只要花钱在报纸上登几条新闻,到医院办些证件,再造一个“金丝鸟笼”,将一个人的人生隐掉取而代之,便能重新REBORN,出乎意料的简单。”
“所以你的第二次REBORN,是成为了——”
“一个名为裘牛的酒保,一个死心踏地为一个酒吧女付诸全部的人。开始只是偶尔为她免单,慢慢地,她的朋友,她那几小时一换的男伴,开始放肆地开那货架上珍藏的洋酒,并全部纳为我的账单上,我开始被老板斥责,被罚掉本就微不足道的工资;被醉醺醺的酒鬼提着衣领,像个玩具一般丢在地面上;甚至在她那包臀裙的裙底,成为了她的椅子,甚至是便器。她开怀大笑洒下的黄色尿液,是我这辈子尝过最难品而最过瘾的佳酿,只要你能品出那份“耻辱”的味道。
然而这样的酒吧女,生活又有什么样的保障呢。一场骚乱,两声枪声,一颗子弹穿过了她情夫的头颅,一颗则穿过了她纹着玫瑰的后背。他的老公愤怒地红着眼睛,在那酒吧里巡视了所有人,也没有怀疑那个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害怕,只是想起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她。
“我第一次来这里,请问有什么推荐?”那时候她顶着微微卷曲的烫发,微笑的问着我,那一刻的散发的光似乎告诉我她不属于这里,但是当我免费将一杯提子酒推到她面前,她眼里不经意流转而过玩味的眼神,正是那几乎瞬时的一瞥,将她一生都留在了那个酒馆里。”
“可是,那场骚乱里好像死了不止两个人。”
“毕竟叫做骚乱,几只鸟叫了几声,叶子有几片落在地上,都无人得知。我也是在那个时刻“死去”的,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就此消失,也没人会在意。随后我坐上了早就在马路上停好的黑色轿车,将那黑色背心扔在了酒馆门前的泥坑里,可惜,再也没有淑女踩着过去了。”
“所以,你每次都会将一生的钱砸给一个与你不相干的女人?”
“与其说是上贡给别人,我更想说这都是上贡给我自己,警官,是我砸钱为我塑造了那样别出心裁的一生,她们只是被我挑选的女演员,仅此而已,我给予他们的片酬不菲,可惜的是她们没有迎来自己的好结局。”
“哼,说的好听,不过我更希望你长话短说:二十一岁你更名为睚眦,工作是——普通公司的职员,那时候你遇到的是——”
“雅,多好听的名字,一个海归的财务实习生,趾高气扬地将她所有的工作交付给我,再将我的工资自动划为我每个月的“桌下出租费”。然而消费水平的提高,两个人的工资显然无法满足她的需求,她便一边用脱下的黑丝紧紧勒着我的咽喉,一边强迫我从公司报表里魔法般变出钱来。笨蛋,就算将一切锅坐在我头上,真正财务的名字也是她才对,就这样我陪着她一起坐了牢,听到她在牢里死讯后便再‘活’出来就是了,你没有印象吗,警官?”
“二十三岁,你更名为朝丰,那时候的对象是——”
“家庭主妇,好像叫做潼吧,家里有个五岁的孩子,那时候我在给她孩子做家教。在她辱骂她家小孩时便看出了点端倪,随后以聊聊孩子为由把她约了出来,噗嗤,哪有在外面聊孩子的,当她从皮包里拿出皮鞭时,我简直高兴到流鼻血了。但是该说是一物降一物还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她的老公是个家暴超雄,在发现包里的皮鞭后,就一点一点把她抽死了。天呐,真羡慕啊。”
“二十五岁,苏安霓——”
“啊那个时候是我给我留钱最多的“一生”,一个死去双亲的富家少爷,与我本人多么相似,只不过我留给自己的豪奢只有原先的七分之一,找的女主角则是来我们家的女仆。那种下克上逆转的喜悦,真是让人十分想念,我还记得她将家产的存折放在我的胯下,一边用白丝将我的精液拧出来时,将存折上我的名字彻底玷污掉的快感,简直让我现在都能射出来。我将一切都给予了她,从她的主人变成了她的仆人,随后又被她像狗一样赶出了我的家,就像钻回了我的子房一般,我又一次钻进了那辆黑色轿车,迎来我的是第二天的太阳。”
“所以说她并没有死?”
“厄运往往是如此的诙谐而滑稽,一个女仆居然会忘掉了浴缸旁边不能用电器的规矩。”
“二十七岁,巴夏。”
“一个畅销作家。当然所谓畅销也不过是提前用钱营销出来的把戏,遇到的是一位叫做明子的记者,多么有野心的女孩,能从我的粉丝变成霸占我一切的杜鹃。将我还为写完的文字占为既有,一边要逼迫我在网上向一直以来抄袭她的行为道歉。剥夺掉我一切名声财产之后,甚至玩味地在网站里发了一个用脚撕掉我之前书的视频,可真够大胆的。不过之后的故事,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听说了,人们发觉她之后的创作和以前大相径庭,一边开始伤害网爆她,一边开始缅怀已经‘死去’的我,到头来硬生生逼到让她在房间里自尽。哎,都怪那该死的文艺病,不过她到最后连我的死法也要抄袭,该说是从一而终吧。”
“三十岁。”
“哒哒,就是现在的我啊。”
“一个老师,对吧?”
“在一个很偏远的县城里教孩子英语,倒也不是什么误人子弟的活。”
“那你如今的对象是——”
“......”
“难道还没找到?”
“大概,不能算是对象吧。
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次意外中,她仓皇地坐在了我的对面,询问我有没有位置,那本来是朋友介绍给我新姑娘的座位,却饶有兴趣的让给了她,她向我笑了笑,随后向服务生比了个耶,示意两份馅饼。
她能在性癖上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而我将一切弱点都暴露给她的时候却又无动于衷,她不收钱,只是会让我拉着她去吃她喜欢吃的大餐;她偶尔也会收我的礼物,但是每次看她为了能送出等价回礼拼命的样子又让我不忍心,当我牵着她的手平视她时,她的眼神里好像放着温柔的光。
我现在还没有告诉她我的REBORN,但是我跟她说过,我其实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她会问我,有钱能吃到星星吗?
我会恳切地告诉他,真的可以。
她那时候说,骗你的,星星不好吃,我们去吃阿萨利亚吧,好久没有吃他们家的馅饼了。
她不仅是个好女孩,我遇到的那些女孩都可以称作为好女孩,是我把他们的贪心剖了出来作为我的药引,但是不管我怎么刨析她,似乎她的内心里,除了馅饼与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开始怀恋我的这“一生”,我像一只猫,一只有九条命的猫,我在不断的折磨中上贡着自己的命数,但是在这一次,我遇到了一个不愿意伤害我的人,她只会抱抱我,掐掐我的鼻头,这或许是对我一生以来最大的治愈,又或是对我那肮脏的前世最灼心的折磨。”
说罢,他拿出眼镜布,哈了口气,擦了擦眼镜。随后收起了他恍惚的深情,稍微正色跟她说道。
“但是警官,虽然我无数次颠覆了自己的身份,虽然我是那些女孩死的根本诱因,但是我并没有真的杀害她们。如果没有什么真正的证据,是并不能因为我说的这些定我罪的。”
“你似乎误会了什么,那些女孩的死去早已结案,既往不咎,也没人愿意动那几年前的烂摊子。”
“谢谢警官,那我坐在这里的原因是——”
“狄的自杀案。”
“什么?”
“今天中午一点,狄女士在家中自杀,留下了一封控告她丈夫对他施行家暴的遗书,我们在她丈夫的床下找到了大量皮鞭与行刑工具,在她身上找到了相似的伤痕,她的丈夫,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
“你,你在说什么?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这根本不是她的字迹,她的那些工具,都是用来调教我的啊?怎么可能!你告诉我!一定是搞错了!”他发疯一般挣脱出来,向着她面前的空气撕咬着。
“六号审讯室,犯人应激,请求关闭执法记录仪。”
她确认之后,一脚将他踹在了地上。
踩在他胸前的,居然是一双高跟鞋。
他似乎一瞬间觉悟到了什么,但又说不出口。堵在他喉咙里的不只是乱如麻的思绪,还有黑色漆面的高跟鞋头。
“将家产分为九份,隐姓埋名地偷偷爽几辈子,该说不说你还是蛮有想法的。可惜了,会“死而复生”的不止你一个人哦。”
她的另一只鞋,滑向他的下体,缓缓地揉搓着。
“离开家久了,连几个姐姐都记不清楚,更别提长相什么的了。哪怕你有那么多钱,就算你能活九条命,我也要一条一条的将你杀死,把你的家产一点~一点给我射出来——”
她的鞋子几乎一半伸进了男人的嘴里,他的眼角留着激动的泪水。
“可惜了,让那个臭婊子捷足先登,还没让姐姐我享受到这种快感,还想着能成家,真够搞笑的。你敢相信她面对几个大汉自卫时候,还拿着你给她的皮鞭呐~你是给她了多大的勇气呢,我的~偷~腥~猫,我的小~弟~弟~
只要哪里有一点鱼腥味,就走不动道路,连死几次都不长记性,还说什么‘女人是我的玩偶’,到头来不还是一只踩不死的小蟑螂,既然没让我爽到,那我就一次性把你剩下三条命全部榨出来好不好~”
她的丝袜足逐渐加快~
五
要射出来喔~不管有再多家产~也要一并喷出来~
四
想不想看看那些曾经整死你的姐姐啊,一会就带你看好不好~
三
快把你的精液全部射出来,把那可憎的基因喷出来,让那老头看看,自己选的继承人阳痿的小鸡鸡,根本没办法传宗接代呢~
二
这些精子就死在姐姐的脚上,要死咯~要死咯~
一
“无罪——
——释放!”
在锤子敲响的那一刻,他射了出来。那一刻他多希望是监禁几十年甚至无期徒刑,但是迎接他的终将是“死刑”。
“啊啦啊啦,要重生咯,我的小犯人~”
阳光明媚的马路上,停着那辆他熟悉的黑色轿车,每向前走一步,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的鸳声燕语。那个曾经让他重生的“子宫”,这一次会将他熬成精子,‘死’在姐姐们的脚上......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而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天下又哪来的龙呢?
喔喔写得好啊!很有美式感觉!
真不错
好有想象力的作品,非常喜欢
龙生九子,猫有九命~甚至巧妙的安排剧情使每一段剧情与九子的性格相对应,精妙绝伦的演出~可惜篇幅有点小短啦
又到了挑 typo 时间:
s/不能在底层/不能再底层/
s/第一支援/第一志愿/
s/她所作的/她所做的/
s/不能在底层/不能再底层/
s/第一支援/第一志愿/
s/她所作的/她所做的/
好涩ww
擦拭 )
擦拭 )
咋死的看不懂不是宣判无罪吗
yiqiezhiwai1:↑咋死的看不懂不是宣判无罪吗是加引号的死刑啦
很有创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