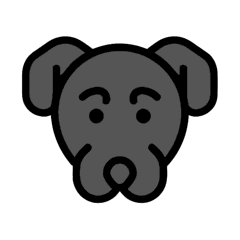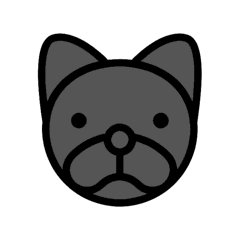此类生物
连载中原创现实纯爱恋物
文/砂糖hobnomi
我叫郁离,一个悲观主义者,座右铭是人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走向庸俗,一条走向毁灭。
这两条路中,后者我走过,孤寂冰冷,旁边的人想拉我一把,我总是会把他们一脚踹开。前者我正走着,燥热拥挤,路上还总有人想踹我一脚,他们可真该死啊。
不过,也有不那么该死的人。譬如她。
她叫向晚。一个女人。我和她结伴而行。
奔现之前,在朋友的眼里我们更像是一对冤家。那时的她强势,说脏话,骂起人来敌友不分,公会里的朋友大多接受过这样的洗礼,却丝毫不影响她一呼百应的地位。大抵是因为她在女性玩家里相对而言过硬的技术水平,以及那不捏不夹浑然天成的御姐音。当然,后者肯定更为重要。而她之所以和我走得最近,究其原因大概并不是因为我游戏玩得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性格互补之类的什么屁话,可能就是单纯因为她骂不过我而已。再后来,我们顺理成章地甜蜜称呼,互点外卖,晚安哄睡,看上去好像有模有样地。而成年人之间玩诸如此类的过家家游戏也有着和小朋友同样的规则,我从没当真过,自然也以为她不会当真的。
同样是游戏罢了。有时若是入戏太深,我的大脑会警觉地刻意提醒自己,用回忆往事的方式。
直到一个不算太冷的夜晚,那女人敲开了我的门。
她穿着那身深红色毛呢大衣,推着同款色系的行李箱,画着她们的职业淡妆,却笑得像个傻子。
没有了手机美颜,即使有做遮瑕,却肯定是不如视频与照片里好看的。可我对她的脸没有太大的兴趣,对她的忽然来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有些心疼即将要发生的一些尽地主之谊的开销。
令我诧异的只有她的眼睛,明明都笑成了月牙形状却闪躲着不敢跟我对视。这不是应该出现在这种时代和这个年纪的害羞。
其实也挺好的,正好让我有机会能多看看感兴趣的地方。
譬如那被厚厚的肉色腿袜包裹着的陡峭臀部,丰满大腿,以及脚上那双锃亮的黑色过膝长靴。
看起来,真是太可口了。
家里没有咖啡,我给她泡了杯我平时喝的那种廉价的立顿伯爵红茶,她接过去喝了口,笑着说有股洗洁精的味道,双手却把那只粉红色的马克杯紧紧握住,就好像不烫似的。
客厅的沙发是单人的,只容得下她一人的屁股。平时不常来客人,也没有准备小凳什么的,我就蹲在她脚边,跟她聊天。
她说自己和家里人吵了架,然后辞职了。
我知道她经常和家里人吵架,尤其是和她爸,根据她往日的描述,是生活在一个由大男子主义父权体系为主旋律的家庭里。但因为吵架这种我眼中的小事而辞职也算挺离奇的,毕竟空姐这种职业还是有不少女生向往而求之不得的。
不过具体的详情我不打算多问,也没有劝解的兴趣。有些东西,送上门的,白给的,品质还不错的。
都摆在你面前了。就别装逼了。
“为什么想着来找我,这种时候不应该去闺蜜家里吗?”我仰起头笑着问她,右手手掌试探性地轻轻在她大腿上拍了拍。毕竟我们名义上也能算是情侣,肉麻甚至僭越的话早就互相说过不少,这样的动作或许也不能算是一种失礼。
丝滑的触感虽短暂却浓烈。其实我早就硬了。当她居高临下望着我的时候,或者更早,从她进门开始,那些臆想中的4i或是dom与sub的桥段便开始冲击着我的大脑,让我不得不花费一些精力去抑制这种情绪,以此来维护自己还算正常的人设和形象。这不是我的错,当虚拟的电子讯号变成实在的肉体时,接受者能体会到的美感是截然不同的。
更何况,她是真的很迷人。
“你知道的,我没有闺蜜。”
她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完全没有一丝惭愧,轻盈的笑眼一会儿俯视着看看脚边的我,一会儿打量着我屋内家徒四壁般的简陋。
当然,我知道的。只是,从前的聊天中获得的那些信息我无法判断是真实的或者只是她的人设。其实想来也是正常的,一个性情爽直口无遮拦的女人,若是真的胸无城府,而不是外宽内深,那的确是很难有同性密友。
她很喜欢把一句话挂嘴边,“女人真麻烦”,不过不知道说这句话有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
若再纠缠着这个话题聊下去,必然是扫兴的。我问她冷不冷,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开始问起了她一路走来的行程。
其实很尬,在虚拟世界中明明以类似夫妻般亲昵的相称,而第一次见面后却冥冥中有种相亲第一次见面的慌乱。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她表现得比我自然,看我蹲了那么久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她又指了指洁净的木地板上被她长靴踩出的那一枚枚深浅不一的泥水鞋印,礼貌地说把我家弄脏了。
这并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大概是想刻意地表现出一些客气和矜持吧。
“没事,一会儿我舔干净就好。”
我是不是在开玩笑其实不重要,只要她觉得是就好。反正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得很自然。
窗外开始淅沥地下起夜雨,我去关窗的时候顺带试着拎了拎她的行李箱,很沉。
悲观主义者,往往想法都现实。又或者说,艰难地爬行在这条通往庸俗的道路上时,路旁的风景都会明示着,暗示着,让你不得不时常去抛弃一些镜花水月的幻想。这些风景有,房贷车贷物业费,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风景,很煞风景。总而言之,我自己活着已是不易,再要“豢养”一个这么“大”的无业女子,那便是万难。
即使她真的很对我胃口。
“等你爸气消了回去好好道个歉,父女俩有什么是说不开的。”
我真没兴趣当个什么化解家庭矛盾的知心姐姐,只是单纯地委婉逐客。她那行李箱实在是太重了,重得我心里发慌。
“我不回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窗外的风雨打穿了玻璃朝我脸上呼来。
“你准备赖上我了?”我还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在说,但不知道表情是否有些扭曲。
“嗯,正有此意。你以为喊你那么久老公白喊了吗?”
“滚。”
我们笑着打闹起来,这种氛围其实已经在虚拟中演练过无数次,所以非但不陌生,甚至十分熟练。只是在她笑得最开心的时候,我轻轻地按了按她的肩膀。
“我养不活你。”
不如直说了吧,反正总得说的。我的身子站得笔直,脸还是笑着。这次换我居高临下地,用肢体语言表达着语境的认真严肃。
“我又不是不去上班。”
她抱起杯子喝了一小口,这次又不敢看我眼睛了。当她说完那句话后,我忽然觉得她这个动作特别可爱。
悲观主义者总爱把一些远近不一的责任通通默认地强加在自己的头上,甚至看不到其中的变化与玄机。在这种一叶障目的状态下,不知道曾经错过了多少本该拥有的美好。
不过这个说法或许太过于乐观了。
她表了这个态,我自然也没有再纠结下去的必要了。我依然对今后的生活并不看好,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说跟着我肯定要吃苦的,她问我家里有土豆吗。我说管够,她说那就没事了。我知道她爱吃土豆,她曾经养的阿拉斯加就叫土豆,我给她取的外号也是土豆。
我甄别不了这种文艺对话的真假,所以心里将其默认为场面话。
我知道自己对她的需求,其实是真是假并不是特别重要。
我挑逗她,随后拥吻,儒雅地品尝着她脖颈与嘴唇里独属于女性的诱人气息,又矛盾地克制着自己的下体与她身体接触的冲动,只是因为在第一次的肉体碰撞中这无疑是失礼的举动。我为自己努力维持着一种平凡的意识形态感到可悲,但这种可悲在现实中又显得无比低级。若是能抛开一切的桎梏,那我只想含着她靴子中被腿袜包裹着的脚趾贪婪舔舐,直到恶心的白色液体从自己那块生殖器中缓缓流出。
仅仅是幻想着,便足够支撑着我把俗套的剧情表演下去了。
更何况,我真的很久没碰过女人了。
窗外的雨停了。我坐在地板上喘气,她说她脚好冷,问我有没有暖脚器或者风暖机之类的东西。遗憾的是,都没有。平时这个时间点我早就睡了,被窝里总是暖和的。
略显尴尬的交流过后,她换上了从行李箱翻出来的睡衣睡裤,坐在沙发上用我给她打的洗脚水烫脚,地板上凌乱地躺着被换下的肉色裤袜和白棉袜。我坐在电脑桌前,用吹风机对准她长靴的靴筒进行着烘干的操作。那里面太冰冷潮湿了,也不知道是她的冷汗还是漏进去的雨水。热风中,蒸腾出的水汽在我的眼镜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白雾。
她说,从来没有男人为她做过这种事,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前男友。
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是从语气能听出来,她那时脸上大概洋溢着一些小女生的幸福表情。
可悲的是,这种反馈,对我而言是刺痛的,像是作弊后考了第一名还被老师夸奖学习努力的情景模拟。
她会将其理解为爱和暖,绝不会想到这种行为真实的动机却是肮脏而变态的。
那个道貌岸然的暖男不过是贪恋那双靴子内体液与皮革的混合气味罢了,他实在是太爱那个味道了,尤其是这双靴子的主人,从通俗审美意义来看,的确能算是个美人。
我虽然自认卑劣,却还是做不到在接受到不属于自己的嘉奖后沾沾自喜,或是顺水推舟,所以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只好岔开话题,问她介不介意睡我的床。当然,我同时明确表示,今晚我不睡了,因为还有三个小时就要出门去上班了。
我能读懂她关上卧室门时脸上的小表情,她大概是把我理解成了不愿意刚见一天就要她身子的正人君子吧。
这次我的刺痛感并不那么强烈,因为我的确认为按时上班比做爱重要,本身已经是通宵的状态,若是再在床上折腾几下,那今天将会更加难熬。
空乘们的私生活我早有耳闻,这大概也是我接纳她的意愿并不那么浓厚的原因之一。若是抛去物质上的因素,遇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又暖又正直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捡到宝了吧。那时的我对她的过往一无所知,思考到这个问题便由衷地想笑。只是多年后跟她聊到当时的想法时,被她罚着跪了半个小时的键盘。
当天空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卧室里刷抖音的声音终于是停了下来。我跟电脑下了四五盘象棋,左下角的时间提醒我该去洗漱了。
这半个夜晚过得实在是折磨,象棋ai软件用它的超强算力花式吊打我,胯下的那根玩意儿不争气地一直挺立着,与牛仔裤做着不死不休的缠斗。
我没有被ai凌虐的癖好,只是想利用高强度的大脑思考来尽量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不去想着有一些足够让我发情的东西就摆放在身旁的地板上,唾手可得。
轻手轻脚地洗漱完后,我把耳朵贴着卧室门,在安静的清晨中能听到里面传出的细微呼吸声。其实有过在她脸上轻吻一口再出门上班的冲动,但不够强烈。
我好困,虽然熬夜与通宵是家常便饭,但与之同时被生殖器折磨却不多见。在决定开门的那一刹那,一小块分裂的意识乖巧地抖出了一滴坏水。
要不先提个神再走吧。
这无疑是个错误的决定,就像是在沙漠中饥渴难耐的人准备灌下一瓶酒精来解渴,后果注定是毁灭性的。
坚持了一夜的自律,在一个瞬间就被击得粉碎,像极了我的人生。
如做贼一般,在自己家里,我蹑手蹑脚地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即使我知道并不存在那种无聊到凌晨六七点拿个望远镜偷窥的人。当屋内失去了所有的光源变得近乎完全的黑暗,甚至在镜中都看不到自己的脸时,我终于有勇气在那双过膝长靴前趴下身体。
说来可笑,温暖的身体在床上躺着,冰冷的鞋子在地上倒着,可某类生物却选择了后者,去作为肉体宣泄的交互对象。
可惜的是,除了那双白色棉袜还有着一丝微咸的口感,其余的物什在离开主人的身体被放置冷却后都失去了味道,只有织物与皮革最为原始的舌尖触感。
想对着靴底的纹路做些清理,但我没有漱口的时间了。
空气是宁静的,它们的主人似乎睡得很熟。我用左臂支撑着身体,右手艰难地解开皮带,拉开裆部的拉链。手掌刚伸进裤裆时是冰冷的,但管不了太多了。所幸的是勉强能做到在伸出舌头舔舐靴面的同时还能用右手以熟练的手法揉搓着自己的阴茎。
以为会至少持续五六分钟,事实上不到十秒便射了,右手甚至还没捂热。
还好,这不是在床上,不然这第一印象怕是留得太差。
不怪我,我真的,太久没碰女人了。
以及,女人的东西。
事实上,在往后的的日子里,这样的清晨还有过不少次。但都不如这般仓促与狼狈了。狼狈得,穿着一条几乎湿透的内裤在公司里行尸走肉般混了一天。
(to be continued)
我叫郁离,一个悲观主义者,座右铭是人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走向庸俗,一条走向毁灭。
这两条路中,后者我走过,孤寂冰冷,旁边的人想拉我一把,我总是会把他们一脚踹开。前者我正走着,燥热拥挤,路上还总有人想踹我一脚,他们可真该死啊。
不过,也有不那么该死的人。譬如她。
她叫向晚。一个女人。我和她结伴而行。
奔现之前,在朋友的眼里我们更像是一对冤家。那时的她强势,说脏话,骂起人来敌友不分,公会里的朋友大多接受过这样的洗礼,却丝毫不影响她一呼百应的地位。大抵是因为她在女性玩家里相对而言过硬的技术水平,以及那不捏不夹浑然天成的御姐音。当然,后者肯定更为重要。而她之所以和我走得最近,究其原因大概并不是因为我游戏玩得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性格互补之类的什么屁话,可能就是单纯因为她骂不过我而已。再后来,我们顺理成章地甜蜜称呼,互点外卖,晚安哄睡,看上去好像有模有样地。而成年人之间玩诸如此类的过家家游戏也有着和小朋友同样的规则,我从没当真过,自然也以为她不会当真的。
同样是游戏罢了。有时若是入戏太深,我的大脑会警觉地刻意提醒自己,用回忆往事的方式。
直到一个不算太冷的夜晚,那女人敲开了我的门。
她穿着那身深红色毛呢大衣,推着同款色系的行李箱,画着她们的职业淡妆,却笑得像个傻子。
没有了手机美颜,即使有做遮瑕,却肯定是不如视频与照片里好看的。可我对她的脸没有太大的兴趣,对她的忽然来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有些心疼即将要发生的一些尽地主之谊的开销。
令我诧异的只有她的眼睛,明明都笑成了月牙形状却闪躲着不敢跟我对视。这不是应该出现在这种时代和这个年纪的害羞。
其实也挺好的,正好让我有机会能多看看感兴趣的地方。
譬如那被厚厚的肉色腿袜包裹着的陡峭臀部,丰满大腿,以及脚上那双锃亮的黑色过膝长靴。
看起来,真是太可口了。
家里没有咖啡,我给她泡了杯我平时喝的那种廉价的立顿伯爵红茶,她接过去喝了口,笑着说有股洗洁精的味道,双手却把那只粉红色的马克杯紧紧握住,就好像不烫似的。
客厅的沙发是单人的,只容得下她一人的屁股。平时不常来客人,也没有准备小凳什么的,我就蹲在她脚边,跟她聊天。
她说自己和家里人吵了架,然后辞职了。
我知道她经常和家里人吵架,尤其是和她爸,根据她往日的描述,是生活在一个由大男子主义父权体系为主旋律的家庭里。但因为吵架这种我眼中的小事而辞职也算挺离奇的,毕竟空姐这种职业还是有不少女生向往而求之不得的。
不过具体的详情我不打算多问,也没有劝解的兴趣。有些东西,送上门的,白给的,品质还不错的。
都摆在你面前了。就别装逼了。
“为什么想着来找我,这种时候不应该去闺蜜家里吗?”我仰起头笑着问她,右手手掌试探性地轻轻在她大腿上拍了拍。毕竟我们名义上也能算是情侣,肉麻甚至僭越的话早就互相说过不少,这样的动作或许也不能算是一种失礼。
丝滑的触感虽短暂却浓烈。其实我早就硬了。当她居高临下望着我的时候,或者更早,从她进门开始,那些臆想中的4i或是dom与sub的桥段便开始冲击着我的大脑,让我不得不花费一些精力去抑制这种情绪,以此来维护自己还算正常的人设和形象。这不是我的错,当虚拟的电子讯号变成实在的肉体时,接受者能体会到的美感是截然不同的。
更何况,她是真的很迷人。
“你知道的,我没有闺蜜。”
她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完全没有一丝惭愧,轻盈的笑眼一会儿俯视着看看脚边的我,一会儿打量着我屋内家徒四壁般的简陋。
当然,我知道的。只是,从前的聊天中获得的那些信息我无法判断是真实的或者只是她的人设。其实想来也是正常的,一个性情爽直口无遮拦的女人,若是真的胸无城府,而不是外宽内深,那的确是很难有同性密友。
她很喜欢把一句话挂嘴边,“女人真麻烦”,不过不知道说这句话有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
若再纠缠着这个话题聊下去,必然是扫兴的。我问她冷不冷,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开始问起了她一路走来的行程。
其实很尬,在虚拟世界中明明以类似夫妻般亲昵的相称,而第一次见面后却冥冥中有种相亲第一次见面的慌乱。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她表现得比我自然,看我蹲了那么久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她又指了指洁净的木地板上被她长靴踩出的那一枚枚深浅不一的泥水鞋印,礼貌地说把我家弄脏了。
这并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大概是想刻意地表现出一些客气和矜持吧。
“没事,一会儿我舔干净就好。”
我是不是在开玩笑其实不重要,只要她觉得是就好。反正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得很自然。
窗外开始淅沥地下起夜雨,我去关窗的时候顺带试着拎了拎她的行李箱,很沉。
悲观主义者,往往想法都现实。又或者说,艰难地爬行在这条通往庸俗的道路上时,路旁的风景都会明示着,暗示着,让你不得不时常去抛弃一些镜花水月的幻想。这些风景有,房贷车贷物业费,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风景,很煞风景。总而言之,我自己活着已是不易,再要“豢养”一个这么“大”的无业女子,那便是万难。
即使她真的很对我胃口。
“等你爸气消了回去好好道个歉,父女俩有什么是说不开的。”
我真没兴趣当个什么化解家庭矛盾的知心姐姐,只是单纯地委婉逐客。她那行李箱实在是太重了,重得我心里发慌。
“我不回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窗外的风雨打穿了玻璃朝我脸上呼来。
“你准备赖上我了?”我还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在说,但不知道表情是否有些扭曲。
“嗯,正有此意。你以为喊你那么久老公白喊了吗?”
“滚。”
我们笑着打闹起来,这种氛围其实已经在虚拟中演练过无数次,所以非但不陌生,甚至十分熟练。只是在她笑得最开心的时候,我轻轻地按了按她的肩膀。
“我养不活你。”
不如直说了吧,反正总得说的。我的身子站得笔直,脸还是笑着。这次换我居高临下地,用肢体语言表达着语境的认真严肃。
“我又不是不去上班。”
她抱起杯子喝了一小口,这次又不敢看我眼睛了。当她说完那句话后,我忽然觉得她这个动作特别可爱。
悲观主义者总爱把一些远近不一的责任通通默认地强加在自己的头上,甚至看不到其中的变化与玄机。在这种一叶障目的状态下,不知道曾经错过了多少本该拥有的美好。
不过这个说法或许太过于乐观了。
她表了这个态,我自然也没有再纠结下去的必要了。我依然对今后的生活并不看好,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说跟着我肯定要吃苦的,她问我家里有土豆吗。我说管够,她说那就没事了。我知道她爱吃土豆,她曾经养的阿拉斯加就叫土豆,我给她取的外号也是土豆。
我甄别不了这种文艺对话的真假,所以心里将其默认为场面话。
我知道自己对她的需求,其实是真是假并不是特别重要。
我挑逗她,随后拥吻,儒雅地品尝着她脖颈与嘴唇里独属于女性的诱人气息,又矛盾地克制着自己的下体与她身体接触的冲动,只是因为在第一次的肉体碰撞中这无疑是失礼的举动。我为自己努力维持着一种平凡的意识形态感到可悲,但这种可悲在现实中又显得无比低级。若是能抛开一切的桎梏,那我只想含着她靴子中被腿袜包裹着的脚趾贪婪舔舐,直到恶心的白色液体从自己那块生殖器中缓缓流出。
仅仅是幻想着,便足够支撑着我把俗套的剧情表演下去了。
更何况,我真的很久没碰过女人了。
窗外的雨停了。我坐在地板上喘气,她说她脚好冷,问我有没有暖脚器或者风暖机之类的东西。遗憾的是,都没有。平时这个时间点我早就睡了,被窝里总是暖和的。
略显尴尬的交流过后,她换上了从行李箱翻出来的睡衣睡裤,坐在沙发上用我给她打的洗脚水烫脚,地板上凌乱地躺着被换下的肉色裤袜和白棉袜。我坐在电脑桌前,用吹风机对准她长靴的靴筒进行着烘干的操作。那里面太冰冷潮湿了,也不知道是她的冷汗还是漏进去的雨水。热风中,蒸腾出的水汽在我的眼镜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白雾。
她说,从来没有男人为她做过这种事,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前男友。
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是从语气能听出来,她那时脸上大概洋溢着一些小女生的幸福表情。
可悲的是,这种反馈,对我而言是刺痛的,像是作弊后考了第一名还被老师夸奖学习努力的情景模拟。
她会将其理解为爱和暖,绝不会想到这种行为真实的动机却是肮脏而变态的。
那个道貌岸然的暖男不过是贪恋那双靴子内体液与皮革的混合气味罢了,他实在是太爱那个味道了,尤其是这双靴子的主人,从通俗审美意义来看,的确能算是个美人。
我虽然自认卑劣,却还是做不到在接受到不属于自己的嘉奖后沾沾自喜,或是顺水推舟,所以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只好岔开话题,问她介不介意睡我的床。当然,我同时明确表示,今晚我不睡了,因为还有三个小时就要出门去上班了。
我能读懂她关上卧室门时脸上的小表情,她大概是把我理解成了不愿意刚见一天就要她身子的正人君子吧。
这次我的刺痛感并不那么强烈,因为我的确认为按时上班比做爱重要,本身已经是通宵的状态,若是再在床上折腾几下,那今天将会更加难熬。
空乘们的私生活我早有耳闻,这大概也是我接纳她的意愿并不那么浓厚的原因之一。若是抛去物质上的因素,遇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又暖又正直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捡到宝了吧。那时的我对她的过往一无所知,思考到这个问题便由衷地想笑。只是多年后跟她聊到当时的想法时,被她罚着跪了半个小时的键盘。
当天空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卧室里刷抖音的声音终于是停了下来。我跟电脑下了四五盘象棋,左下角的时间提醒我该去洗漱了。
这半个夜晚过得实在是折磨,象棋ai软件用它的超强算力花式吊打我,胯下的那根玩意儿不争气地一直挺立着,与牛仔裤做着不死不休的缠斗。
我没有被ai凌虐的癖好,只是想利用高强度的大脑思考来尽量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不去想着有一些足够让我发情的东西就摆放在身旁的地板上,唾手可得。
轻手轻脚地洗漱完后,我把耳朵贴着卧室门,在安静的清晨中能听到里面传出的细微呼吸声。其实有过在她脸上轻吻一口再出门上班的冲动,但不够强烈。
我好困,虽然熬夜与通宵是家常便饭,但与之同时被生殖器折磨却不多见。在决定开门的那一刹那,一小块分裂的意识乖巧地抖出了一滴坏水。
要不先提个神再走吧。
这无疑是个错误的决定,就像是在沙漠中饥渴难耐的人准备灌下一瓶酒精来解渴,后果注定是毁灭性的。
坚持了一夜的自律,在一个瞬间就被击得粉碎,像极了我的人生。
如做贼一般,在自己家里,我蹑手蹑脚地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即使我知道并不存在那种无聊到凌晨六七点拿个望远镜偷窥的人。当屋内失去了所有的光源变得近乎完全的黑暗,甚至在镜中都看不到自己的脸时,我终于有勇气在那双过膝长靴前趴下身体。
说来可笑,温暖的身体在床上躺着,冰冷的鞋子在地上倒着,可某类生物却选择了后者,去作为肉体宣泄的交互对象。
可惜的是,除了那双白色棉袜还有着一丝微咸的口感,其余的物什在离开主人的身体被放置冷却后都失去了味道,只有织物与皮革最为原始的舌尖触感。
想对着靴底的纹路做些清理,但我没有漱口的时间了。
空气是宁静的,它们的主人似乎睡得很熟。我用左臂支撑着身体,右手艰难地解开皮带,拉开裆部的拉链。手掌刚伸进裤裆时是冰冷的,但管不了太多了。所幸的是勉强能做到在伸出舌头舔舐靴面的同时还能用右手以熟练的手法揉搓着自己的阴茎。
以为会至少持续五六分钟,事实上不到十秒便射了,右手甚至还没捂热。
还好,这不是在床上,不然这第一印象怕是留得太差。
不怪我,我真的,太久没碰女人了。
以及,女人的东西。
事实上,在往后的的日子里,这样的清晨还有过不少次。但都不如这般仓促与狼狈了。狼狈得,穿着一条几乎湿透的内裤在公司里行尸走肉般混了一天。
(to be continued)
“我看完以后的首先的感觉是很嫉妒,妈的,写得那么牛比,卧槽”
humulation:↑“我看完以后的首先的感觉是很嫉妒,妈的,写得那么牛比,卧槽”
人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迷妹。
hobnomi:↑果然!我就知道是你!我看的时候就在想怎么这么像海盐!humulation:↑“我看完以后的首先的感觉是很嫉妒,妈的,写得那么牛比,卧槽”humulation老师您好,我是您的黑粉,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特喵的可能根本就没看,然后复制粘贴了柠檬老师的回复。
人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迷妹。
Aieeeeee!甜文!为什么这里会有甜文?!糖尿病犯了(泪
“我看完以后的首先的感觉是很嫉妒,妈的,写得那么牛比,卧槽”
又看一遍,感觉有点重庆森林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