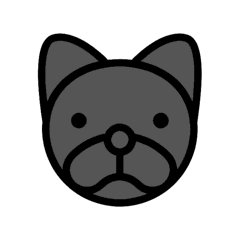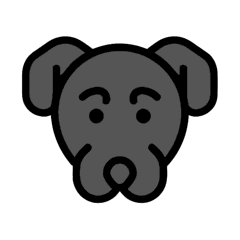恶女的夜
厕奴短篇原创阶级大小姐’24征文比赛虐杀致残感官剥夺
征文比赛赛果
此作品参加了 2024 年夏季举办的叁孙杯「恶女」题材 M 向小说征文比赛,以下为其获得的评委评分和读者投票:
色情
54/100
后 50% σ=26.3
文学
61/80
前 50% σ=22.0
合题
62/80
前 25% σ=26.4
创意
27/40
前 25% σ=9.1
评委总分
205/300
前 50% σ=62.9
绮丽的夏夜里,在皎洁的月光泼不到的暗处,在公允的清风抚不到的偏地,罪恶就如同曼珠沙华一般绽开宝艳瑰丽的花,在路人因惊异于其绚烂陆离而膝盖生根之时,源源不断地攫取着来自地下腐尸的供养。
绮丽,当然是对她来说,像她那样的钟鸣鼎食,哪晚不绮丽呢?对我,那是个破败昏浊急转直下不堪回首的夜晚。不过姑且容我把伤心事往后摆,摆得越靠后冲的痛苦也越淡,缥缥缈缈好像并不发生在己身。
因为困窘,我蜷居在一个阴湿的涵洞里,过着疏水箪瓢的生活。涵洞阴湿,我的关节也时常发痛。关节疼起来很要命,似有无数虫蚁啃噬,我只能用患处猛磕岩壁来缓解疼痛。这样做刚开始屡试不爽,后来肉里难免嵌进些碎石水泥渣,随着关节对碰撞的耐受力增强,就渐渐地失去了原本的功效。可是涵洞呢?还是阴湿,关节也还是在痛。痛得我神魂颠倒,睡觉时把我痛醒,清醒时把我痛昏。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我就咬紧舌头做别的事情转移视听。
那天我痛到眼睛出现飞蚊症、张嘴也吸不进空气。无可奈何之下,我拿出手机来滑信息流,稽查别人的苦难来让自己好受些。我看到手机上说哪里又蔓延了瘟疫,多少小孩感染上结膜吸吮线虫,年纪轻轻就成了瞎子再也看不见东西,我眼里的蚊子就飞走了,我发现我可以看清十米之外垃圾桶上交相辉映的蝇蚁。我看到手机上说哪里又发生了矿难,多少幸存工人患肺尘埃沉着病,正值壮年就肺纤维化再也吸不进空气,我被扼住的喉就解放了,我发现我可以吮吸填满涵洞车来车往排泄而出的废气。在我仅剩关节疼痛的时候,手机上还有什么?
我看到手机上声名显赫的不知出大小姐的出游vlog,巨大到夸张的私人豪华游艇在广袤太平洋上拉出一道扎眼的白线横亘东西,同海一样深蓝幽邃的蓝宝石玻璃隔绝了外界的悲苦和炎热,大小姐慵懒坐在主沙龙休闲区,摘下枚戒指随手掷出窗外,就有勇敢的杂役们赌上性命投身海里寻宝,一同演了烽火戏诸侯的戏码博大小姐一笑。有不幸的杂役撞上鲨鱼,残躯氤出血沫贴到艇壁上形成像是锈蚀的痕迹。大小姐微笑着把乳酒缓缓倒进海里慰藉卖命的演员,血红,海蓝和乳酒的白就拼色成一幅晕乎乎醉人的画。游艇周围高高的护栏和武装让海盗生不起劫富济私的勇气悻悻离去,艰苦小民则在监工的注视下匍匐在沙滩上再叩首祈福大小姐出行顺利,桅杆上绑着祭旗的可怜人直到大小姐平安归来才被解放。vlog之外的内容当然是我在怨愤之下不由自主臆想的,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见识到她的穷奢极欲,再回归到我的窘迫不堪,我哆嗦起来,怨气就像忧郁菇一样偾出了我的身体,不时就填满了逼仄的涵洞,又反沁进手机的私聊对话框里:
“大小姐万类陶均,即能把乳酒分予鱼虾,怎么不接济下贫苦人么?”
我不会去想,这句酸气十足的问安,会把我拖进怎么样的境况里。
“你贫苦吗?果真贫苦的话,虔诚地期待着吧。”
高居云端,永远惬意,无限美好的神明也会共情人间疾苦吗?对我来说是不敢置信的。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的贫苦,先特写十米之外垃圾桶上交相辉映的蝇蚁证明我生存环境的恶劣,镜头一转来到车来车往不停排放的废气,佐以我浑然天成丝毫不显得刻意的咳嗽声,还不足够把我的窘迫展示得一览无余么?按下send键后,我难以遏制内心的雀跃,像蛆虫一样扭曲蠕动的我,终于也迎来了化茧成蝶的机会。我对光明的前景深信不疑————药,救济粮,甚至水仙花,都会有的。我要从顶龌龊的人摇身一变成顶体面的人了,凭什么?凭我是顶困苦的人,比起矿工和小孩来也不遑多让。
可是,鬼迷心窍的我怎么意识得到,作茧不一定化蝶,更大可能是自缚。
在等待接济、昏昏沉沉的迷梦里,得益于大小姐的悲天悯人,我cos了白盔白甲的阿q,要什么就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但,这夜的梦略显蹊跷,怎么缺席了大货车小皮卡此起彼伏喇叭声的BGM?只剩下死寂的静,静得聋子来了也不疑有他。我睡不踏实,心慌慌地惊醒了。
是还在做梦吗?我看到涵洞不知什么时候塞了一团人,比vlog里还要姽婳的大小姐步步生莲地朝我走来,貌极圣洁颜色乳白的靴子踏在岩地上发出曼妙的声音,在逼仄狭窄的涵洞里余音绕梁。回响一次是空灵,回响两次就显得可怖,而第三次若有若无的回响让我毛骨悚然。
她是来接济我的,我在怕什么呢?
“大小姐,大小姐,喏,您看我确实贫苦。在病痛和窘迫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我等您的救赎好久了。我————现在卑贱,以前卑贱,往后也还是卑贱。”
我爬上去,用谄媚的话和谄媚的笑容讨好她。虽然我的姿态丑陋,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形势所迫,我告诉自己我对她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恭敬崇拜啊,哪里有过愤愤不平的时候呢?
“真是可怜。你患病了吗?”
大小姐放任由仆人精心打理的金发随意跃动,堪称完美的美少女面容上泛起一丝恰到好处温婉和煦的微笑,柔声问我。举止既不张狂也不冷漠让我如沐春风,我猜是什么贵族礼仪造物。
她从容地轻抬靴子,挪一小步停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面上,没有带起一粒扬尘。我只嗅到了些微弱的香气,像晨露和芦荻一样若有若无。我低下头温驯地伏到靴子上蜻蜓点水般亲吻一下她的靴尖。
“是的,我因长年蜷缩在阴湿之地,关节已经坏得差不多了,可是一见到您,我就全然顾不上疼痛了。”
巧言令色、阿谀奉承、攀炎附势、什么样的贬义词放到现在的我身上也不显得突兀,我几乎是没有下限地讨好她。
讨论起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觊觎救济粮,还是深感与她云泥之别的身份差距我果真心生崇拜了呢,这只在当时分得清楚。往后也没有了分清楚的必要。
“是吗?这崎岖不平的破路很是难行,我为了接济你可是足足下车走了几十米,唔,脚稍有些酸了。”
她并不关心我顾不顾得上疼痛,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是啊,一个流浪汉病得快死了这样不值一哂的小事,怎么比得上解决大小姐脚酸来得迫切紧要呢?
我低头看着碎石杂草铺成的路,在夜晚它们是与我幽会的情人,我会痴痴地趴在它们身上性交,现今它们却被大小姐指责过于硌脚。
在我踌躇之际,仆役合力抬着未曾放下的一张硕大沉重的椅子终于派上用场,大小姐毫无征兆地坐下,知道下面无论什么时候都必定会有无论什么东西东西承接。全神贯注紧盯大小姐动向的仆役迅速抬过沉重的皮椅,用柔软的丝垫接住大小姐玉体。岩地崎岖,仆役慌不择路用手垫在椅子足下保持平衡。
大小姐翘起玲珑的小腿高过我的头颅,无需她的命令,我如视珍宝般捧过细腻柔软的靴子,把靴底的碎石和浮尘原原本本地收集起来,虔诚地解开锁住芳香的扣绳,小心翼翼地含下口感犹如少女乳房的靴子,昙花一现漏出花苞里珊珊可爱的袜足。我下腹用力掩饰膨胀的屌,让它看起来相安无事。
脱靴子时我怎么敢不谨小慎微呢?我只是个赤贫的流浪汉,万死也不能担起龟玉毁于椟中的责任。
因恐惧暴露我的贪婪引起大小姐不悦,即便接触到让我垂涎欲滴的足香,我也不敢大口吮吸发出声响,只能在用面部轻拱大小姐形态完美的足弓时,趁机细细品味毛茸茸的袜子上那比刚才浓郁得多、异于晨露与芦荻的别味之香。
“还没闻够吗?”
在我轮番侍奉双足十几次仍不舍得终止后,玄天之上传来了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我因恐惧咽下唾液的声音在落针可闻的环境里显得格外欲盖弥彰。
“我,我,抱歉、抱歉、我愧对您的恩赐,得陇望蜀不知感恩,实在是罪不容诛……”
慌忙地捧起靴子侍奉大小姐穿上,我看着诱人的足一点一点没入靴子恍然若失。
“算了,未经教化行为粗鄙的流浪汉,初回侍奉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尚可原谅。念在你诚惶诚恐的份上,嗯……你说关节疼什么的,是指哪个关节?”
大小姐不但宽恕我的贪婪,而且好奇地凑上前来,提出帮我解决病痛,我感激得无以复加。
“大小姐啊,我——肩肘腕指,髋膝踝跖无不在痛。”
我自作聪明夸大了一番病情。大小姐这样善良和煦,我描述的病情越严重,得到的救济不就越多吗?所谓人性都是这样的。
“好。那么从肩关节开始。”
“……什么?”
我的身体猛然沉下去,意识到是被旁边的仆役控制住,我抬起头茫然无措地看她。
大小姐接过侍者跪呈上的火机点燃一支雪茄,精致火机悦耳的开和声让我的屌拱进土里。
“湿寒需用火驱来治。”
雪茄没有犹豫就吻上我的左肩,从若即若离到紧紧咬死,我看着我的左肩恐惧,颤抖,悲鸣,逃避,但无济于事。
明明在被近在咫尺的火焰炙烤,我干涩的眼眶却不可思议地湿润起来,但即刻水分就被蒸干成白雾迷茫了视线,一团火光含含糊糊跳变作六七团,唯中间的焰芒最盛似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原始火种。我就是被这样的火焰灼烧着。
“不、不要,大小姐,我……”
我仓皇无措地哀求她,恐惧,颤抖,悲鸣,逃避,但无济于事。
大小姐短暂失神,我的左肩血肉已变焦灰,关节烧成舍利掉下来。一个流浪汉怎么有舍利呢?原来是因为我是被万类陶均的大小姐火化的。
“这样它再不会痛了欸,不谢谢我吗?”
“我、不,是肮脏腌臜的流浪汉,谨怀不胜惶恐之心、谢谢您(肩)、谢谢您(肘)、谢谢您(腕)、谢谢您(指)、谢谢您(髋)、谢谢您(膝)、谢谢您(踝)、谢谢您(跖),它们都永远不再痛了,您发圣恩,您发发圣恩,…………好吗?”
疼痛让我失去思考的能力疯狂叩首,妄图保全剩下的关节,可这显然是痴人说梦。结局从我不知死活惊扰大小姐圣憩已经注定无可挽回了,我是死得其所的。我的屌告诉我。
“在担心我太过劳累吗?还挺善解人意嘛。不过,我说了会帮你,就会不辞劳苦做完的。”
她的脸上浮出纯粹享受的笑容,那是和我饱经诘难的苦笑截然不同的笑。不过很可爱,我的屌已经在犁地了。还好我没说屌上有关节痛。
涵洞里没有哀嚎和眼泪。大小姐不喜喧闹,我就咬死舌头不弄出声音吵扰她。原本的哀嚎变成眼泪,刚要滴下却又被火焰蒸干,与涵洞之外的人说这里正发生着一桩肢解的惨案,恐怕任谁都不会相信吧。
“但这样效率难免有些低。嗯,你,虽然是患者……我任命你兼任手术一助,拿好这个。”
她纤细的手指夹住一支雪茄递过来,我宁愿去拿燃烧着的部分也不敢去触碰她的手指,这让她有些意外。
“哈哈,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嘛,可怜的我都有些不忍心了。但,痼疾不除怎么好呢?该做什么你清楚的。”
大小姐的语调从欢快变得戏谑,靠在椅子上惬意地等待着我的下一步动作。
我拿着雪茄颤颤巍巍,不敢迟疑,咬牙砸到左踝上。踝和跖,卑贱肮脏的人身上卑贱肮脏的部位不能劳烦大小姐亲自动手。
剥离血肉的疼痛让我几乎无法保持理智,我死咬住舌头坚持着不发出声来。
好在烧蚀关节首当其冲的是神经,坚持到神经坏死之后,疼痛就不再致命,这样我勉强保持清醒的受完了刑。享受完了疗愈,屌纠正说。
我的肩肘腕指髋膝踝跖重复着恐惧,颤抖,悲鸣,逃避的流程,已经颇让人感到厌烦。但大小姐依旧不厌其烦的依次超度了他们,怎么能说大小姐不宅心仁厚呢?只不过事到如今,我再大唱赞美诗也够呛能保全性命了。
万籁俱寂、等我的身体瘫痪之后,她轻快的舒口气,像是结束了什么繁琐的工作。
“呼~好了,那么…………”
她顿一顿,目光扫过一地狼藉,似乎在酝酿什么。
“诊金是一百万円。”
轻描淡写地用我的面部捻灭最后一支雪茄之后,她讲出了让我瞠目结舌的话。
“诊金……一百万……我,您知道的,我就是个流浪汉……虔诚期待着您接济的贫苦流浪汉……”
“嗯,已经进行贫苦专项超特惠减免了,原本的价格是一千万円来着。”
或许是因为幻肢痛,我的目光迟滞,嘴巴张了张,没有说出话来。
“没有钱的话……你的器官虽难堪一用,不过我向来对拒绝奴隶自发由衷的献身感到为难。”
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处境,还有斡旋的余地吗?
“…………大小姐,我的器官不论残缺还是完好,归属权悉数是您的,恭候您随意支配。”
我贴到石块沙尘上的额头再也没有抬起过。
“很好,戴上这个。”
咬住大小姐掷下的项圈,我毕恭毕敬地俯首系颈,委命神明。
“到合适的紧度说停哦。”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项圈就猛然抽缩成了绞刑的死索,不留余力缚住我的气管和声道让我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没有说话。是太松了么?”
力度还在加深,我的眼球凸的快弹射出来,视线已是乌黑了,我疯狂叩首乞求她停手。
“还是没有说话。这是做什么呢?”
力度继续加深,我几乎要身首异处。
在我命悬一线之际,索命的项圈终于放松了束缚,是大小姐亲手解开的。
“宁愿死都不肯说话啊。那么首当其冲,就是累赘的发声器官咯~”
“我……呜……任凭大小姐处置。”
她饶有兴致地让我翻过身来,一刀一刀剖开皮肤,切下喉和声带。血溅到她垂落的金发和雪白的肌肤上,像是传世的画作总是加盖着几个不合时宜的印章。
我失声了,成了一个窘迫的哑巴流浪汉。无所谓吧?反正我早丧失了与除了她的任何人交涉的欲望。
血雾结了一层翳遮住我的视线,现在眼睛也是累赘了。
她站起身来,高高跃起骤然落下,靴子几乎被染成红黑色。
我失明了,成了一个窘迫的瞎子流浪汉。没什么关系吧?反正世间也没有比今夜所见更绮丽的东西了。
现在我真的是顶困苦的人、真的比起旷工和小孩来也不遑多让。
“喉咙抵消五十万円,一只眼睛抵消二十五万円,那么还剩下的负债是————”
她又顿了顿,不过这次少了酝酿的意味,多了些不容置疑的果断。
“一百万円。”
一只眼睛抵消二十五万円,喉咙抵消五十万円,剩下的负债是一百万円。
…………一百万円?
“在疑惑为什么还是一百万円吗?仔细回想一下。你的眼睛和喉咙不是本来就坏了吗?飞蚊症、呼吸困难什么的。那也是我治好的哦~”
“嗯……还是不明白吗?不觉得那场瘟疫来的蹊跷吗?一事发就有特效药,却被不知出财团独家垄断,价格又昂贵的惊人,怎么看都像是先有药再有瘟疫的嘛。”
“至于矿难,发生在抚恤金标准修改前夕,发放的明明是一亿円,怎么到工人手里就奇妙的只剩下一百万円了?”
我知道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小姐所创下的恶,不止于虐杀流浪汉,甚至制造瘟疫卖高价药,设计矿难豪夺殉难工人抚恤金,简直纯粹到令人发指的恶。
她还在笑着,虽然我看不见了,但我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盖过血腥气的甜蜜的愉悦,那是令无论什么甜蜜素芳香烃羟色胺都自惭形愧的醉人香甜,在感知着生命像流水般逝去的时刻,我再顾不上无论是关节眼睛还是喉咙处的疼痛,一股脑把肥料打进污泥里。
“所以,一百万円、你打算用什么来支付呢?”
她踩着从我身体上烧下来的一节残躯,擦拭靴底的血污发出沙沙的声音,温柔地讲。
一百万円,在我身上残值还有这么多的,无外乎是————
我肮脏腌臜、扭曲如蛆虫的生命。
因为失去发声器官,我没办法用言语回复她,只能用尚没有流干的血歪七扭八的拼了个Life。
字写的难以分辨、正像见了我这副模样的人大概也会犹豫我是人还是别的什么无肢豚之类的物种。
“啧,还真是自信啊。或是说…………”
“很想被我夺去生命吗?”
脖子上的项圈突然施力,靴子上的纹路深深地烙进面部皮肤,在我眼眶已经差不多流干的血洞上,粘稠的黑色血浆伴随着挤压出的脑脊液又井喷一波,大概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所谓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这道标识的附加,可是一文不值呢。”
原来如此、没有大小姐的践踏,我的生命一文不值。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我却对即将降临的死亡既不恐慌也不抗拒,心安理得的接纳了结局,就是所谓视死如归吧。即便恐慌抗拒,结局有什么不同吗?无非是体面的死变成不体面的死。
意识到这里就结束了,缺氧、大量失血、加之持续糖摄入的缺失,让我在彻底成为一具干尸之前昏死过去。
………………
死人所在的地狱是泡在水里的吗?因为失去视觉感官我无法求证现在身处何方了。只觉得残缺的身体飘飘摇摇浮浮沉沉、颈部却被器具挟制住动弹不得,相当可悲,我还是活着。
没有人解释情况,也没有人记得我。就在这被遗忘的角落里,我独自张大嘴巴像条缺氧的鱼一样呼吸————不竭尽全力就会窒息。
就这样我不知等了多久,也不知在等什么,直等到精神衰弱又濒临昏迷。
终于有脚步声,但这熟悉的、几乎刻进我的灵魂里的声音不用回响三次就能使我毛骨悚然了。
“虽然泡在消毒液里,但流浪汉改造的厕畜使用起来还是不免有芥蒂啊。”
大小姐似在喃喃自语,但偏偏我一字不落的听清了。
不出所料、接下来的话就是对我说的了。
“如你所说:我万类陶均。所以我免除你一百万円的负债。另外,不必惋惜乳酒分给鱼虾,我现在要赐你的,可是比乳酒珍贵万倍的东西。”
渺渺的圣音从天上降下,我隐隐意识到她是指什么。我时刻张着嘴保持呼吸,眼睛又早失明不会亵渎圣私,被选做厕畜也算物尽其用。
感受着来自面部的压力,我主动迎上大小姐的肛处。来自穹顶之上的温软,畅通无阻地滑进我的食道和胃里。
不知怎么,我的泪腺没有征兆地活跃起来,把这具残躯仅剩的一抹温存供奉给大小姐高贵神圣的蜜庭。
我很开心、不知出大人,我很开心。虽然没办法传达给您,但我是喜极而泣的。
远海传来鸥的叫声。
绮丽,当然是对她来说,像她那样的钟鸣鼎食,哪晚不绮丽呢?对我,那是个破败昏浊急转直下不堪回首的夜晚。不过姑且容我把伤心事往后摆,摆得越靠后冲的痛苦也越淡,缥缥缈缈好像并不发生在己身。
因为困窘,我蜷居在一个阴湿的涵洞里,过着疏水箪瓢的生活。涵洞阴湿,我的关节也时常发痛。关节疼起来很要命,似有无数虫蚁啃噬,我只能用患处猛磕岩壁来缓解疼痛。这样做刚开始屡试不爽,后来肉里难免嵌进些碎石水泥渣,随着关节对碰撞的耐受力增强,就渐渐地失去了原本的功效。可是涵洞呢?还是阴湿,关节也还是在痛。痛得我神魂颠倒,睡觉时把我痛醒,清醒时把我痛昏。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我就咬紧舌头做别的事情转移视听。
那天我痛到眼睛出现飞蚊症、张嘴也吸不进空气。无可奈何之下,我拿出手机来滑信息流,稽查别人的苦难来让自己好受些。我看到手机上说哪里又蔓延了瘟疫,多少小孩感染上结膜吸吮线虫,年纪轻轻就成了瞎子再也看不见东西,我眼里的蚊子就飞走了,我发现我可以看清十米之外垃圾桶上交相辉映的蝇蚁。我看到手机上说哪里又发生了矿难,多少幸存工人患肺尘埃沉着病,正值壮年就肺纤维化再也吸不进空气,我被扼住的喉就解放了,我发现我可以吮吸填满涵洞车来车往排泄而出的废气。在我仅剩关节疼痛的时候,手机上还有什么?
我看到手机上声名显赫的不知出大小姐的出游vlog,巨大到夸张的私人豪华游艇在广袤太平洋上拉出一道扎眼的白线横亘东西,同海一样深蓝幽邃的蓝宝石玻璃隔绝了外界的悲苦和炎热,大小姐慵懒坐在主沙龙休闲区,摘下枚戒指随手掷出窗外,就有勇敢的杂役们赌上性命投身海里寻宝,一同演了烽火戏诸侯的戏码博大小姐一笑。有不幸的杂役撞上鲨鱼,残躯氤出血沫贴到艇壁上形成像是锈蚀的痕迹。大小姐微笑着把乳酒缓缓倒进海里慰藉卖命的演员,血红,海蓝和乳酒的白就拼色成一幅晕乎乎醉人的画。游艇周围高高的护栏和武装让海盗生不起劫富济私的勇气悻悻离去,艰苦小民则在监工的注视下匍匐在沙滩上再叩首祈福大小姐出行顺利,桅杆上绑着祭旗的可怜人直到大小姐平安归来才被解放。vlog之外的内容当然是我在怨愤之下不由自主臆想的,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见识到她的穷奢极欲,再回归到我的窘迫不堪,我哆嗦起来,怨气就像忧郁菇一样偾出了我的身体,不时就填满了逼仄的涵洞,又反沁进手机的私聊对话框里:
“大小姐万类陶均,即能把乳酒分予鱼虾,怎么不接济下贫苦人么?”
我不会去想,这句酸气十足的问安,会把我拖进怎么样的境况里。
“你贫苦吗?果真贫苦的话,虔诚地期待着吧。”
高居云端,永远惬意,无限美好的神明也会共情人间疾苦吗?对我来说是不敢置信的。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的贫苦,先特写十米之外垃圾桶上交相辉映的蝇蚁证明我生存环境的恶劣,镜头一转来到车来车往不停排放的废气,佐以我浑然天成丝毫不显得刻意的咳嗽声,还不足够把我的窘迫展示得一览无余么?按下send键后,我难以遏制内心的雀跃,像蛆虫一样扭曲蠕动的我,终于也迎来了化茧成蝶的机会。我对光明的前景深信不疑————药,救济粮,甚至水仙花,都会有的。我要从顶龌龊的人摇身一变成顶体面的人了,凭什么?凭我是顶困苦的人,比起矿工和小孩来也不遑多让。
可是,鬼迷心窍的我怎么意识得到,作茧不一定化蝶,更大可能是自缚。
在等待接济、昏昏沉沉的迷梦里,得益于大小姐的悲天悯人,我cos了白盔白甲的阿q,要什么就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但,这夜的梦略显蹊跷,怎么缺席了大货车小皮卡此起彼伏喇叭声的BGM?只剩下死寂的静,静得聋子来了也不疑有他。我睡不踏实,心慌慌地惊醒了。
是还在做梦吗?我看到涵洞不知什么时候塞了一团人,比vlog里还要姽婳的大小姐步步生莲地朝我走来,貌极圣洁颜色乳白的靴子踏在岩地上发出曼妙的声音,在逼仄狭窄的涵洞里余音绕梁。回响一次是空灵,回响两次就显得可怖,而第三次若有若无的回响让我毛骨悚然。
她是来接济我的,我在怕什么呢?
“大小姐,大小姐,喏,您看我确实贫苦。在病痛和窘迫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我等您的救赎好久了。我————现在卑贱,以前卑贱,往后也还是卑贱。”
我爬上去,用谄媚的话和谄媚的笑容讨好她。虽然我的姿态丑陋,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形势所迫,我告诉自己我对她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恭敬崇拜啊,哪里有过愤愤不平的时候呢?
“真是可怜。你患病了吗?”
大小姐放任由仆人精心打理的金发随意跃动,堪称完美的美少女面容上泛起一丝恰到好处温婉和煦的微笑,柔声问我。举止既不张狂也不冷漠让我如沐春风,我猜是什么贵族礼仪造物。
她从容地轻抬靴子,挪一小步停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面上,没有带起一粒扬尘。我只嗅到了些微弱的香气,像晨露和芦荻一样若有若无。我低下头温驯地伏到靴子上蜻蜓点水般亲吻一下她的靴尖。
“是的,我因长年蜷缩在阴湿之地,关节已经坏得差不多了,可是一见到您,我就全然顾不上疼痛了。”
巧言令色、阿谀奉承、攀炎附势、什么样的贬义词放到现在的我身上也不显得突兀,我几乎是没有下限地讨好她。
讨论起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觊觎救济粮,还是深感与她云泥之别的身份差距我果真心生崇拜了呢,这只在当时分得清楚。往后也没有了分清楚的必要。
“是吗?这崎岖不平的破路很是难行,我为了接济你可是足足下车走了几十米,唔,脚稍有些酸了。”
她并不关心我顾不顾得上疼痛,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是啊,一个流浪汉病得快死了这样不值一哂的小事,怎么比得上解决大小姐脚酸来得迫切紧要呢?
我低头看着碎石杂草铺成的路,在夜晚它们是与我幽会的情人,我会痴痴地趴在它们身上性交,现今它们却被大小姐指责过于硌脚。
在我踌躇之际,仆役合力抬着未曾放下的一张硕大沉重的椅子终于派上用场,大小姐毫无征兆地坐下,知道下面无论什么时候都必定会有无论什么东西东西承接。全神贯注紧盯大小姐动向的仆役迅速抬过沉重的皮椅,用柔软的丝垫接住大小姐玉体。岩地崎岖,仆役慌不择路用手垫在椅子足下保持平衡。
大小姐翘起玲珑的小腿高过我的头颅,无需她的命令,我如视珍宝般捧过细腻柔软的靴子,把靴底的碎石和浮尘原原本本地收集起来,虔诚地解开锁住芳香的扣绳,小心翼翼地含下口感犹如少女乳房的靴子,昙花一现漏出花苞里珊珊可爱的袜足。我下腹用力掩饰膨胀的屌,让它看起来相安无事。
脱靴子时我怎么敢不谨小慎微呢?我只是个赤贫的流浪汉,万死也不能担起龟玉毁于椟中的责任。
因恐惧暴露我的贪婪引起大小姐不悦,即便接触到让我垂涎欲滴的足香,我也不敢大口吮吸发出声响,只能在用面部轻拱大小姐形态完美的足弓时,趁机细细品味毛茸茸的袜子上那比刚才浓郁得多、异于晨露与芦荻的别味之香。
“还没闻够吗?”
在我轮番侍奉双足十几次仍不舍得终止后,玄天之上传来了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我因恐惧咽下唾液的声音在落针可闻的环境里显得格外欲盖弥彰。
“我,我,抱歉、抱歉、我愧对您的恩赐,得陇望蜀不知感恩,实在是罪不容诛……”
慌忙地捧起靴子侍奉大小姐穿上,我看着诱人的足一点一点没入靴子恍然若失。
“算了,未经教化行为粗鄙的流浪汉,初回侍奉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尚可原谅。念在你诚惶诚恐的份上,嗯……你说关节疼什么的,是指哪个关节?”
大小姐不但宽恕我的贪婪,而且好奇地凑上前来,提出帮我解决病痛,我感激得无以复加。
“大小姐啊,我——肩肘腕指,髋膝踝跖无不在痛。”
我自作聪明夸大了一番病情。大小姐这样善良和煦,我描述的病情越严重,得到的救济不就越多吗?所谓人性都是这样的。
“好。那么从肩关节开始。”
“……什么?”
我的身体猛然沉下去,意识到是被旁边的仆役控制住,我抬起头茫然无措地看她。
大小姐接过侍者跪呈上的火机点燃一支雪茄,精致火机悦耳的开和声让我的屌拱进土里。
“湿寒需用火驱来治。”
雪茄没有犹豫就吻上我的左肩,从若即若离到紧紧咬死,我看着我的左肩恐惧,颤抖,悲鸣,逃避,但无济于事。
明明在被近在咫尺的火焰炙烤,我干涩的眼眶却不可思议地湿润起来,但即刻水分就被蒸干成白雾迷茫了视线,一团火光含含糊糊跳变作六七团,唯中间的焰芒最盛似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原始火种。我就是被这样的火焰灼烧着。
“不、不要,大小姐,我……”
我仓皇无措地哀求她,恐惧,颤抖,悲鸣,逃避,但无济于事。
大小姐短暂失神,我的左肩血肉已变焦灰,关节烧成舍利掉下来。一个流浪汉怎么有舍利呢?原来是因为我是被万类陶均的大小姐火化的。
“这样它再不会痛了欸,不谢谢我吗?”
“我、不,是肮脏腌臜的流浪汉,谨怀不胜惶恐之心、谢谢您(肩)、谢谢您(肘)、谢谢您(腕)、谢谢您(指)、谢谢您(髋)、谢谢您(膝)、谢谢您(踝)、谢谢您(跖),它们都永远不再痛了,您发圣恩,您发发圣恩,…………好吗?”
疼痛让我失去思考的能力疯狂叩首,妄图保全剩下的关节,可这显然是痴人说梦。结局从我不知死活惊扰大小姐圣憩已经注定无可挽回了,我是死得其所的。我的屌告诉我。
“在担心我太过劳累吗?还挺善解人意嘛。不过,我说了会帮你,就会不辞劳苦做完的。”
她的脸上浮出纯粹享受的笑容,那是和我饱经诘难的苦笑截然不同的笑。不过很可爱,我的屌已经在犁地了。还好我没说屌上有关节痛。
涵洞里没有哀嚎和眼泪。大小姐不喜喧闹,我就咬死舌头不弄出声音吵扰她。原本的哀嚎变成眼泪,刚要滴下却又被火焰蒸干,与涵洞之外的人说这里正发生着一桩肢解的惨案,恐怕任谁都不会相信吧。
“但这样效率难免有些低。嗯,你,虽然是患者……我任命你兼任手术一助,拿好这个。”
她纤细的手指夹住一支雪茄递过来,我宁愿去拿燃烧着的部分也不敢去触碰她的手指,这让她有些意外。
“哈哈,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嘛,可怜的我都有些不忍心了。但,痼疾不除怎么好呢?该做什么你清楚的。”
大小姐的语调从欢快变得戏谑,靠在椅子上惬意地等待着我的下一步动作。
我拿着雪茄颤颤巍巍,不敢迟疑,咬牙砸到左踝上。踝和跖,卑贱肮脏的人身上卑贱肮脏的部位不能劳烦大小姐亲自动手。
剥离血肉的疼痛让我几乎无法保持理智,我死咬住舌头坚持着不发出声来。
好在烧蚀关节首当其冲的是神经,坚持到神经坏死之后,疼痛就不再致命,这样我勉强保持清醒的受完了刑。享受完了疗愈,屌纠正说。
我的肩肘腕指髋膝踝跖重复着恐惧,颤抖,悲鸣,逃避的流程,已经颇让人感到厌烦。但大小姐依旧不厌其烦的依次超度了他们,怎么能说大小姐不宅心仁厚呢?只不过事到如今,我再大唱赞美诗也够呛能保全性命了。
万籁俱寂、等我的身体瘫痪之后,她轻快的舒口气,像是结束了什么繁琐的工作。
“呼~好了,那么…………”
她顿一顿,目光扫过一地狼藉,似乎在酝酿什么。
“诊金是一百万円。”
轻描淡写地用我的面部捻灭最后一支雪茄之后,她讲出了让我瞠目结舌的话。
“诊金……一百万……我,您知道的,我就是个流浪汉……虔诚期待着您接济的贫苦流浪汉……”
“嗯,已经进行贫苦专项超特惠减免了,原本的价格是一千万円来着。”
或许是因为幻肢痛,我的目光迟滞,嘴巴张了张,没有说出话来。
“没有钱的话……你的器官虽难堪一用,不过我向来对拒绝奴隶自发由衷的献身感到为难。”
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处境,还有斡旋的余地吗?
“…………大小姐,我的器官不论残缺还是完好,归属权悉数是您的,恭候您随意支配。”
我贴到石块沙尘上的额头再也没有抬起过。
“很好,戴上这个。”
咬住大小姐掷下的项圈,我毕恭毕敬地俯首系颈,委命神明。
“到合适的紧度说停哦。”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项圈就猛然抽缩成了绞刑的死索,不留余力缚住我的气管和声道让我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没有说话。是太松了么?”
力度还在加深,我的眼球凸的快弹射出来,视线已是乌黑了,我疯狂叩首乞求她停手。
“还是没有说话。这是做什么呢?”
力度继续加深,我几乎要身首异处。
在我命悬一线之际,索命的项圈终于放松了束缚,是大小姐亲手解开的。
“宁愿死都不肯说话啊。那么首当其冲,就是累赘的发声器官咯~”
“我……呜……任凭大小姐处置。”
她饶有兴致地让我翻过身来,一刀一刀剖开皮肤,切下喉和声带。血溅到她垂落的金发和雪白的肌肤上,像是传世的画作总是加盖着几个不合时宜的印章。
我失声了,成了一个窘迫的哑巴流浪汉。无所谓吧?反正我早丧失了与除了她的任何人交涉的欲望。
血雾结了一层翳遮住我的视线,现在眼睛也是累赘了。
她站起身来,高高跃起骤然落下,靴子几乎被染成红黑色。
我失明了,成了一个窘迫的瞎子流浪汉。没什么关系吧?反正世间也没有比今夜所见更绮丽的东西了。
现在我真的是顶困苦的人、真的比起旷工和小孩来也不遑多让。
“喉咙抵消五十万円,一只眼睛抵消二十五万円,那么还剩下的负债是————”
她又顿了顿,不过这次少了酝酿的意味,多了些不容置疑的果断。
“一百万円。”
一只眼睛抵消二十五万円,喉咙抵消五十万円,剩下的负债是一百万円。
…………一百万円?
“在疑惑为什么还是一百万円吗?仔细回想一下。你的眼睛和喉咙不是本来就坏了吗?飞蚊症、呼吸困难什么的。那也是我治好的哦~”
“嗯……还是不明白吗?不觉得那场瘟疫来的蹊跷吗?一事发就有特效药,却被不知出财团独家垄断,价格又昂贵的惊人,怎么看都像是先有药再有瘟疫的嘛。”
“至于矿难,发生在抚恤金标准修改前夕,发放的明明是一亿円,怎么到工人手里就奇妙的只剩下一百万円了?”
我知道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小姐所创下的恶,不止于虐杀流浪汉,甚至制造瘟疫卖高价药,设计矿难豪夺殉难工人抚恤金,简直纯粹到令人发指的恶。
她还在笑着,虽然我看不见了,但我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盖过血腥气的甜蜜的愉悦,那是令无论什么甜蜜素芳香烃羟色胺都自惭形愧的醉人香甜,在感知着生命像流水般逝去的时刻,我再顾不上无论是关节眼睛还是喉咙处的疼痛,一股脑把肥料打进污泥里。
“所以,一百万円、你打算用什么来支付呢?”
她踩着从我身体上烧下来的一节残躯,擦拭靴底的血污发出沙沙的声音,温柔地讲。
一百万円,在我身上残值还有这么多的,无外乎是————
我肮脏腌臜、扭曲如蛆虫的生命。
因为失去发声器官,我没办法用言语回复她,只能用尚没有流干的血歪七扭八的拼了个Life。
字写的难以分辨、正像见了我这副模样的人大概也会犹豫我是人还是别的什么无肢豚之类的物种。
“啧,还真是自信啊。或是说…………”
“很想被我夺去生命吗?”
脖子上的项圈突然施力,靴子上的纹路深深地烙进面部皮肤,在我眼眶已经差不多流干的血洞上,粘稠的黑色血浆伴随着挤压出的脑脊液又井喷一波,大概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所谓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这道标识的附加,可是一文不值呢。”
原来如此、没有大小姐的践踏,我的生命一文不值。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我却对即将降临的死亡既不恐慌也不抗拒,心安理得的接纳了结局,就是所谓视死如归吧。即便恐慌抗拒,结局有什么不同吗?无非是体面的死变成不体面的死。
意识到这里就结束了,缺氧、大量失血、加之持续糖摄入的缺失,让我在彻底成为一具干尸之前昏死过去。
………………
死人所在的地狱是泡在水里的吗?因为失去视觉感官我无法求证现在身处何方了。只觉得残缺的身体飘飘摇摇浮浮沉沉、颈部却被器具挟制住动弹不得,相当可悲,我还是活着。
没有人解释情况,也没有人记得我。就在这被遗忘的角落里,我独自张大嘴巴像条缺氧的鱼一样呼吸————不竭尽全力就会窒息。
就这样我不知等了多久,也不知在等什么,直等到精神衰弱又濒临昏迷。
终于有脚步声,但这熟悉的、几乎刻进我的灵魂里的声音不用回响三次就能使我毛骨悚然了。
“虽然泡在消毒液里,但流浪汉改造的厕畜使用起来还是不免有芥蒂啊。”
大小姐似在喃喃自语,但偏偏我一字不落的听清了。
不出所料、接下来的话就是对我说的了。
“如你所说:我万类陶均。所以我免除你一百万円的负债。另外,不必惋惜乳酒分给鱼虾,我现在要赐你的,可是比乳酒珍贵万倍的东西。”
渺渺的圣音从天上降下,我隐隐意识到她是指什么。我时刻张着嘴保持呼吸,眼睛又早失明不会亵渎圣私,被选做厕畜也算物尽其用。
感受着来自面部的压力,我主动迎上大小姐的肛处。来自穹顶之上的温软,畅通无阻地滑进我的食道和胃里。
不知怎么,我的泪腺没有征兆地活跃起来,把这具残躯仅剩的一抹温存供奉给大小姐高贵神圣的蜜庭。
我很开心、不知出大人,我很开心。虽然没办法传达给您,但我是喜极而泣的。
远海传来鸥的叫声。
吐槽2点:
1、标题感觉可以再改得更好。
2、文中“忧郁菇”的比喻不是很好啊,男主设定真的还玩pvz嘛
除此之外没了,给q老师跪了,您再这样写下去我要失业了,道心破碎ಥ_ಥ
1、标题感觉可以再改得更好。
2、文中“忧郁菇”的比喻不是很好啊,男主设定真的还玩pvz嘛
除此之外没了,给q老师跪了,您再这样写下去我要失业了,道心破碎ಥ_ಥ
我勉强保持清醒的读完了这恐怖故事。享受完了疗愈,屌纠正说。
Nb !
感觉好像看了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