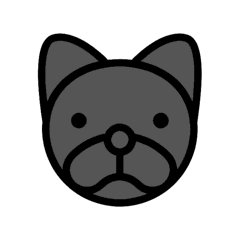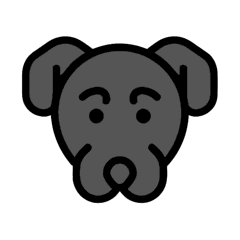讲学家之死
短篇原创现实老师M大小姐NTR
我快死了,在弥留之际写下我的走死路的经历。
那天天气很坏,教室外的天空才下午四点就一片浑黄,路旁的树干隐进这样的环境里不能分辨,风混着沙子掠过寂寥已久的江面发出压抑的鬼哭声,只等暴雨骤然下下来。我在黑板上沙沙的写着,学生在台下寡默无言的听着,各自都是心不在焉。
约莫是临下课的时候,忽有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沉闷,不是打雷,是我的粉笔断了。我习惯拿它从右上往左下滑,但这次由于我心不在焉,拿着它从左下往右上滑了,手感艰涩阻尼又大根本滑不动,它就被我震断了。
我捡起断笔想吹去上面的灰尘接着用,看着断笔却联想到人被拦腰斩断的场面。这死法既不好看又不体面,如果可以选我是最不愿意这样死的。
下课的铃声也比雷声先到,我再次嘱托学生这样坏的天气回家更要小心不要着急,虽然我还没讲完教室的学生就所剩无几了。
但她还在。她是老师们所讨论的特殊的学生。我并不对特定的学生有不同于其他学生的想法和对待,但她确实是特殊的。那个特殊的学生,总是心不在焉总是格格不入,只身的来只身的走,她并不是被孤立的,是她总习惯漠视别人的热情。对无论什么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在别的学生把慌乱的情绪通过空气传播遍教室时,她还是慢条斯理的收拾东西,好像雨永远不会淋到她身上。
我走前多注意了下她时常不聚焦的眼睛。她是漂亮的。因为我是她的老师所以不方便再用别的形容,仅三个字也是多余的赘述。我向来觉得老师和学生不该有什么不发生在教室的交集,当老师对哪个学生发生了异于别的学生的想法时,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是有罪的。
我走到车棚时,天开始闪雷,我把不知道哪个粗心大意的学生丢在棚外的自行车推进去,有车衣的盖上车衣。走到校门口雨开始下,并不想我想的一样一来就是暴雨,它那时下的不是很猛烈。倘若我撑开伞快走几步,应当可以在它变成暴雨前回去。可是,我看见了她。
约莫有一条公序良俗是这么说的,老师该给小自己一辈的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尽管这个学生可能是乖戾不群的。她没有伞而且是学生,我是老师而且有伞,所以我循规蹈矩把伞递过去。我说,雨很快下大我是有教职工宿舍住的,你拿着伞先回去。她说嗯。理所应当的接过伞,若无其事的走开,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她是乖戾不群的学生我早知道的,恐怕说了感谢才可疑吧?我既然把伞给她早有心理打算,感谢不感谢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不该对此感到忿忿。
可是,我看着她走出校门,而后上了一辆车。————————车不是敞篷的,也不是坏了需要推着走,也就是说她没有伞也不会淋雨,尽管这样还是理所应当的收下了我的伞。
雨很快下大了,我本来就湿了也不再在乎湿的透不透。我淋的雨越多身体的温度越低心跳反变得越快了,我不知道这是忿忿致使气血上涌还是身体怕我失温昏死过去所以积极救援,还是另一种隐晦的不可言说的原因,总之它跳的快了。
我要为我的忿忿辩解。我忿忿不是因为我淋雨,而是她明明有车接还要我的伞,明明知道我走路回家还要我的伞,这不是良善和蔼的行径。我经常跟学生讲要做良善和蔼的人,要做良善和蔼的事,可是她全然没有在意。
我的衣服紧粘身上勒出我瘦弱的身形,积水满到小腿,大步淌水行路耗空我的力气,并不遥远的路径如今好像天堑。
但回去就好了,有热水和风机,污水被净水冲刷掉,颤栗被暖风安抚平稳。这样只要一个小时我就又从不体面变回体面了,顺理成章是这样,可是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至于走死路。
下面的就是陈词滥调,不幸的人通用一种不幸。我在我不死气沉沉的时候买了一扇钢门,现在它把我锁死在外,难道是因为我这时死气沉沉吗?我只能用备用钥匙开锁,扎进眼里的玄关有两双鞋,窜进耳蜗的浴室里有钟椎撞击肉槽的声音。他们肆无忌惮到糜烂的淫叫盖过开门声,不理会别的扫兴的事情,就是指我开门进来。
我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结婚十年了描述起来还是含糊其辞。但我知道我和她前五年是貌合神离的,后五年是貌不合神更离的,就是这样从开始就充满了妥协的关系,所以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吧。
我现在是精疲力尽的,就算我不筋疲力尽,凭我孱弱的身躯能抗博那个陌生的男人吗?我不用估计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我拉上门回归暴雨的拥抱。我给学生做过词汇辨析:夺门而去和摔门而去都是走,一个是说兴奋的开门走一个是说愤怒的关门走,两者适用的语境不同不要混淆。我走时推门不兴奋,关门也不愤怒。
也许是我的肾功能不如料想中的强大,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也就和预期大相径庭,像本该硕果累累的树上等一年只结果了一颗苍蝇屎,这怎么能不让人大跌眼镜呢?所以在应该兴奋和愤怒的时候我拿的出出的情绪只有厌倦和茫然。对这样无趣的味同嚼蜡的婚姻,这样无趣的照本宣科的工作,这样无趣的水波不兴的生活我无不感到厌倦。为什么我总要经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呢?我的精力和情绪总在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竭泽而渔,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我渐渐恐惧我一眼可以看到结局的将来。
站在斑马线处,这样急的车流,这样滑的路面,随便哪一辆都能剥离我的性命吧。但我不能死在这里,这个路口离我家太近,我死在这里岂不是给闲人猜忌我的死因是接受不了妻子的出轨吗?这太无趣了,记得有哪个作家死前还有好心情说“自杀不留遗书是最好不过的”,这说法正合适我。
所以我就继续走。我走到不知道哪里不知道是谁的辖区才停下,我一踏上这里的柏油就和我交融,身体也自发瘫软贴在地上认定这是最好的墓地,我也就顺坡下驴打算这样过世了,倒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忽有一双探照大灯毫无征兆的照出我寻死的身姿。上万流明的光照是要帮我烤干衣服吗?可是雨还在下,我岂不成了小学课本上一面放水一面注水的游泳池。
我听到“sensei”的声音,抬头看过去,被探照大灯炙烤我睁不开眼睛,用手遮挡才勉强分辨了坐在后座的她和前排正襟危坐一言不发的司机。
奥,原来是她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看我赴死。不过或许被她碾死也没什么不好,闲人也找不出蛛丝马迹只当我的死是意外。我悔恨我在这时意识还清醒,能理解她的每一句话。
“老师躺在这里,是想寻死吗?”
她打开车门,撑起伞站在台阶上问我。我的视线早被雨水朦胧,大约只见得她绵密的丝袜。
“也许吧。人总归是要死的,早死一会晚死一会我看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吗?何况往后的苦难还更多……”我如此回答她。
“嗯,我并不关心老师的寻死的原因。不过既然老师已经是将死之人了,在死之前能帮我个忙吗?”她打断我的话问我,我都是将死之人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这倒没有什么所谓。”我回答的很慢,正像我的思考。
“把它拿回来。”她微微欠身从鞋子上摘下一个亮晶晶的东西,然后扔到马路对面。
“快点哦,老师。”她对我笑笑,我对此是有些不明所以的,但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也倦怠于思考她的动机。
这样湍急的车流,这样湿滑的路面,制动距离也会比平时长很多。但无所谓,我本来就是要寻死的,我没有犹豫就走过去,爬过护栏在地上摸索着找寻,什么时候我会被车撞死呢?奇怪的是我把东西捡回来了也没有一辆车和我拥抱。
“老师的运气很棒啊。不过它已经掉到水里了。很脏欸,我的鞋子肯定不愿意要了。嗯,那就请老师吃掉吧,反正老师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呵,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我随口吞下那个亮晶晶像是图钉的东西。
“还有另一只鞋子上的,老师不是总在强调秩序和规范,厌恶不协调吗?”她伸出左腿,居高临下对我说。
“用嘴。另外不要弄脏我的鞋子。”我刚伸出手就被她打断,她把我的手掌踩到污水里,我只好用牙齿拔下另一颗图钉装饰品咽下去,我吞了两颗钉子,自然是命不久矣。
“唔,鞋底踩到了垃圾呢,老师跟我过来。”
她撑着伞坐回车里,纤细的小腿垂在半空中摇曳。
“喝掉这些,否则会不消化的。”她指的是从鞋子滴下来的污水,我对于此是无所谓的。
“你是笨蛋吗?这样左面那只就会漏掉了啊。”她指责我的嘴张得不够大不能同时接到两只鞋子滴下来的污水,但其实我的下颌已经张到将近脱臼了。
她把鞋子踩进我的嘴里试图帮我的嘴巴扩容,奈何人是有生理限制的,一番尝试无果后她有些生气。
“真麻烦,你去拿块石头把牙齿磕掉好了。”她一面命令我,一面踩住我的脖子几乎令我窒息,我怔怔往上看着她,试图理解她的意思。
“那会很痛的……”我回复她。
“好吧,像老师这样脆弱的人做不到也正常。那老师该怎么向他们赎罪呢?”她轻轻撩起鞋子掠过我的视线。
赎罪,她是指漏掉了一部分污水的罪孽,这样的逻辑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太复杂了,我是理解不能的。我能做的只是再怔怔的看她。
“唔,还是要我想。这样吧,你吻住我的鞋子,不许咬痛他们!然后帮我从后备箱拿一双新的鞋子。”
她把鞋子脱下,自由落体砸下来,然后收回腿踩在座位上,转头盯着我笨拙的行动。“不许咬痛他们”是指让我用上下唇包裹鞋尖,这样就牙齿就不会接触皮革了,只是要时时用力,不然稍有松懈鞋子就会掉出来。我爬到后备箱,但车的底座竟高到我要站起来才拿的到里面的东西。她要的是什么?里面有礼服、胖次和鞋子。是礼服吗?换起来太繁琐,车内空间不大应该概率渺茫。那么就是胖次了,我把胖次捧过去为我成功赎罪感到满心欢喜。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鞋子!你……”她有些害羞,脸红了半边,夺过胖次藏在身后,偏偏我抱歉不能,我一开口鞋子就会掉下去,所以只能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
我只好再把装鞋子的盒子捧过来,看来我的罪孽又加了一条。
“你太脏了,我自己穿。把他们放到,嗯,胸部吧,我想还比较平坦。躺下。”
她以为我的胸部平坦,实际上也并不平坦,我瘦的琵琶骨一根根显露无疑。但我还是照做了。
“老师这么瘦弱,看来是不能踩在上面穿了,好可惜。”她用鞋尖抚过我的肋骨,发出这样的感慨。但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是个将死之人。她把丝袜提拉到紧紧裹着足部的程度,然后再踏进我胸脯上的盒子。穿好一只鞋子,她忽然注意到我的视线,我确实能看到她裙尾下覆盖着若隐若现的胖次,但我是个老师,而且是将死的老师,我想不出这时候看一个学生胖次的意义。
“不许看!”她用那只穿好的鞋子踏在我鼻梁上方以遮住我的视线,现在我只看得到鞋底上的纹路和印记了。鞋底上上刻着的扭曲的希腊字母,我虽不认得,不过大概就是我生前所见的最后的单词了。
穿好两只鞋子,她让我恢复膝行的姿势,然后蹲下来把空盒子放到我的背上。
“不许掉下来,老师的罪孽还没有赎完,所以要先跟我回家一趟。”她的语气大多是命令,但这次有些请求的意味,她和我对视,我撇开视线不回答她。我不想走,我贪恋这里沥青的滑腻,希冀能够就此弥散在这水雾里茫茫 。
“随便找辆车死在这里的话,老师觉得这是良善和蔼的做法吗?还是说只要是老师的行为,无论怎么样都算良善和蔼?”
“…………”
“跟你走,我还能死成吗?”
她答应会让我得偿所愿,我才跟着她缓缓的爬行。她让司机把车开的很慢,临近天黑的时候才到了一栋庄严肃穆的建筑。我对学生的家境向来是不关心的,我一向觉得有意了解这个当然是别有用心,所以现在见到夸张的城堡也无动于衷,将死之人不会纠结于细枝末节。
“家里只有我和女仆。”她应当是对我说的,但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她让我先洗澡,说遗体倘若不洁牛头马面是不收的,那样就成了孤魂野鬼,所以我只好先洗澡。可是洗完澡我却找不见我的衣服。
“家里没有男性的衣物啊。再说老师都是将死之人了,也没什么好害羞的吧。”她对我这样说,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我洗澡。她说的也不全错,尽管如此,对自己的学生赤身裸体也还是让我感到不自在,身体也有些应激的反应。
“老师怎么对学生发情了~”她凑过来,像抓住我的把柄般,好奇的戳戳我极力掩饰的东西,但越戳它就越兴奋了,好像在向主人邀功一样昂首挺胸。
“这可是比以往大的多的罪孽呢!你这样对得起他们吗?”她用夸张的语气质问我。
“什么?”我楞一会,然后顺着她的视线知道她是指鞋子。
“他们说想和老师接吻。”她接着说。我没有犹豫就趴下去,正欲亲吻她却避开来没有让我接触。
“不是这里,是另一个老师,对学生发情的老师。”我现在知道她是指什么了,我稍稍松手偷看它还丝毫没有要萎靡的迹象。我不愿意把我的丑态暴露出来,它如果没有反应,给她看倒也没什么所谓,可是现在它有反应,就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扰。良善之人就是到死也不愿给人添麻烦,不然我也不会跟她回来。
“我看这不是很合适,因为它不愿意。”
“嗯,我看他分明很愿意嘛,老师不要心口不一。”
她用鞋尖轻轻把我的蘑菇力抵在地上,和缓含蓄的摩挲蘑菇力的头。我的蘑菇力的头是很脆弱敏感的,一接触她的鞋尖就颤颤,尽管她用柔情安抚也无济于事。我的蘑菇力颤抖极力向上生长,奈何被皮革的天穹扼制住动弹不得。小草的所谓生机勃发,怎么度得过压路机带来的灭顶之灾呢?我的蘑菇力的反抗对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刚有起势,即被压回木板肿胀变形。蘑菇力的头还在水深火热,蘑菇力的身体却不明就里发生了什么。快要缴械之际,她终于有空眷顾蘑菇力的身体,从根部滑到头部,再踩住蘑菇力的头使管道闭合让他释放不能。
“让我去……”
我只好用手遮住不洁,向上伸长脖子去哀求她,像一个滑稽的曲颈瓶。
“老师分明犯下了欺骗之罪,却还大言不惭说这种话吗?”
“呜,我错了,我的蘑菇力很想和您的鞋子接吻,请让它去吧”
我把头低下盯住鞋子的亮面,那像乳房一样细腻的鞋子,沾着我基因的鞋子,正和我性交的鞋子,我该恐惧我呼出的浊气污染了他,课本上张屠户那只打过天上文曲星的手终究残疾了,我如此玷污圣物的罪行更加僭越,但我不在乎后果,因为我本来就要死了。
“清理干净。”
她终于轻描淡写的挪开了鞋子,我的蘑菇力才得以缴械疲软下来,我刚恢复正常的思考,转头就不愿承认我曾有过什么异样的想法,我回想一番终究确认了我是遭了迫害才一泻千里的。
我的死节愈发的明晃,我斥责她不要再辱我,我是一心求死的。
“…………好吧,我精通弓术,射艺比起甘蝇飞卫来也不遑多让,请老师去靶场。”甘蝇和飞卫,乃是我课上与学生们提起的两个古时的神射手。
靶场有弓,矢和草靶。草靶中间画着红红的大圆,我比对心脏位置刚好重合应当就万无一失。但真站在这里我又不免怀疑她的弓术,或许不那么精准……倘箭矢透过了身体却没死成怎么样?鸣泣回响在空旷的靶场,拖着骨断筋连的残躯给绿草地染成红色也无人在意,这实在不美观。我嘱托她,万一出了意外要及时给我介错,切记不要让我的哀嚎涌出声道。她提议在我心脏处先剜个红红的大圆来瞄,为防止我身体颤栗移位先用链子固定住四肢,但我这么怕痛怎会答应。
“果然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老师。”
她换上一身纯白的弓道服,足袋踏在细沙上交错开来,缓缓拉开弓弦。弦上的矢,箭头是精钢打的,旁有血槽。箭杆材料是黄檀木,尾部有用以平衡的雕翎。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所以现在的场景就不大和谐有点像大小姐处死犯错的奴隶。不过即便是那样又如何,反正结局一样我总是要死的。
我对纯白素有一种迷恋,因而我的蘑菇力又不合时宜的立了。
我看见她松手,看见流矢飞过来,听见猛烈的撞击声,我的肋骨原来那么坚硬,可以和精钢打出火花,我的心脏原来那么有力,搏动的声音大过钟锥撞击肉槽。我分明看见箭矢垂直长在我的身体,却没有看见红色的喷泉,也没有感受到等同于在身上剜出红色大圆的疼痛。我猜测是我是我的血糖太高以至于血粘稠的像糖浆,所以达不到激流勇射的视觉效果。我的肾上腺素后知后觉开始分泌,隔离了疼痛才让我自在飞花轻似梦。但肾上腺素的功效有那么持久吗?直到我的蘑菇力不立了低头贴到箭杆上我才后知后觉,箭透过了靶子没透过我的身体。假使当时我的蘑菇力没有立,那我现在就没有了蘑菇力。
“没有射中呢。老师该不会被吓到?”她放下弓,快步走过来,戏谑的问我。
虽我没有死成,经此却不愿意再这样死,往往是白受了惊吓却没有成事。
“偌大的建筑,怎么连几块煤炭也没有吗?我为什么死的这么迂回曲折唉。”
“唔,我也想帮老师尽快解脱,但这里确实没有煤炭。不过,老师不是讲过‘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故事吗?马跑的久了不休息,就会暴毙。所以……”
所以我又成了她的马,而且是汗血宝马。为什么是汗血宝马呢?因为我是汉人自然就是汗血,相当浅显的道理。她要我亲吻她的马靴,说这样才能协调马与主人的羁绊,否则就达不到疾行如霹雳弦惊的效果。我不知道这是情趣play还是死亡的先决条件,也不在乎。如果是前者,那我做的类似的事还少吗?
衔铁勒住我的牙齿不能张合,流涎修复铁片在口腔割出的伤口继而与血交融。滚烫的皮肤一接触到冰凉马靴即有刺痛感,沉重的马鞍把我的脊背压瘪。我觉得我负重跑了三公里,其实我才走了三百步就扑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我究竟有没有死,大家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我死了,是被箭射死的,胸口只剩下个红红的大洞不见了心脏。也有说我是被车创死了,或者是劳役太重累死了。但我知道我没有死,我醒来看到壁炉里燃烧的煤炭就开始沮丧了。
我问她,你分明有煤炭,怎么说没有呢?
“有这么样,没有怎么样,反正大家觉得老师已经死了。无论是和老师共事的讲学家,还是老师的妻子都这么说。讣告上大家还称赞老师是良善和蔼的人呢~”
这也算我没有白死。在后来,我又问她,那疾驰的车流怎么一辆都沾不到我身上呢?为什么我吃了钉子却安然无恙呢?
“那条路早就被管控了啊。‘钉子’是巧克力做的。”
“那我记得当时还有车流?”
“我有不止一个司机。他们原本是家父的司机,家父过世后,留下了这座公馆和女仆以及司机们。”她说话时,正看着壁炉里燃烧的煤炭。
“有这样的事情啊……”我感慨道。
那煤炭亮的发光,远远看来质地细腻绵柔,也难怪不仅讲学家而且他父亲都对其消逝的雾气趋之若鹜了。那个侃侃而谈的讲学家确实死了,但我没有时间在他坟前哀默,我新找了个管家的工作。作为公馆里唯一的男性伺候大小姐是极易受到刁难的,好在日子不像讲学家生前一般无趣。
后来我终于有空去讲学家的坟探看,誊抄了不知谁赠与他的奠语:
纵令人寿三百岁,愉逸度世,较之永生无尽之乐趣,亦不过梦幻耳。
唯立心为善者,乃能于圣教中得不可思议之妙趣。
那天天气很坏,教室外的天空才下午四点就一片浑黄,路旁的树干隐进这样的环境里不能分辨,风混着沙子掠过寂寥已久的江面发出压抑的鬼哭声,只等暴雨骤然下下来。我在黑板上沙沙的写着,学生在台下寡默无言的听着,各自都是心不在焉。
约莫是临下课的时候,忽有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沉闷,不是打雷,是我的粉笔断了。我习惯拿它从右上往左下滑,但这次由于我心不在焉,拿着它从左下往右上滑了,手感艰涩阻尼又大根本滑不动,它就被我震断了。
我捡起断笔想吹去上面的灰尘接着用,看着断笔却联想到人被拦腰斩断的场面。这死法既不好看又不体面,如果可以选我是最不愿意这样死的。
下课的铃声也比雷声先到,我再次嘱托学生这样坏的天气回家更要小心不要着急,虽然我还没讲完教室的学生就所剩无几了。
但她还在。她是老师们所讨论的特殊的学生。我并不对特定的学生有不同于其他学生的想法和对待,但她确实是特殊的。那个特殊的学生,总是心不在焉总是格格不入,只身的来只身的走,她并不是被孤立的,是她总习惯漠视别人的热情。对无论什么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在别的学生把慌乱的情绪通过空气传播遍教室时,她还是慢条斯理的收拾东西,好像雨永远不会淋到她身上。
我走前多注意了下她时常不聚焦的眼睛。她是漂亮的。因为我是她的老师所以不方便再用别的形容,仅三个字也是多余的赘述。我向来觉得老师和学生不该有什么不发生在教室的交集,当老师对哪个学生发生了异于别的学生的想法时,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是有罪的。
我走到车棚时,天开始闪雷,我把不知道哪个粗心大意的学生丢在棚外的自行车推进去,有车衣的盖上车衣。走到校门口雨开始下,并不想我想的一样一来就是暴雨,它那时下的不是很猛烈。倘若我撑开伞快走几步,应当可以在它变成暴雨前回去。可是,我看见了她。
约莫有一条公序良俗是这么说的,老师该给小自己一辈的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尽管这个学生可能是乖戾不群的。她没有伞而且是学生,我是老师而且有伞,所以我循规蹈矩把伞递过去。我说,雨很快下大我是有教职工宿舍住的,你拿着伞先回去。她说嗯。理所应当的接过伞,若无其事的走开,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她是乖戾不群的学生我早知道的,恐怕说了感谢才可疑吧?我既然把伞给她早有心理打算,感谢不感谢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不该对此感到忿忿。
可是,我看着她走出校门,而后上了一辆车。————————车不是敞篷的,也不是坏了需要推着走,也就是说她没有伞也不会淋雨,尽管这样还是理所应当的收下了我的伞。
雨很快下大了,我本来就湿了也不再在乎湿的透不透。我淋的雨越多身体的温度越低心跳反变得越快了,我不知道这是忿忿致使气血上涌还是身体怕我失温昏死过去所以积极救援,还是另一种隐晦的不可言说的原因,总之它跳的快了。
我要为我的忿忿辩解。我忿忿不是因为我淋雨,而是她明明有车接还要我的伞,明明知道我走路回家还要我的伞,这不是良善和蔼的行径。我经常跟学生讲要做良善和蔼的人,要做良善和蔼的事,可是她全然没有在意。
我的衣服紧粘身上勒出我瘦弱的身形,积水满到小腿,大步淌水行路耗空我的力气,并不遥远的路径如今好像天堑。
但回去就好了,有热水和风机,污水被净水冲刷掉,颤栗被暖风安抚平稳。这样只要一个小时我就又从不体面变回体面了,顺理成章是这样,可是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至于走死路。
下面的就是陈词滥调,不幸的人通用一种不幸。我在我不死气沉沉的时候买了一扇钢门,现在它把我锁死在外,难道是因为我这时死气沉沉吗?我只能用备用钥匙开锁,扎进眼里的玄关有两双鞋,窜进耳蜗的浴室里有钟椎撞击肉槽的声音。他们肆无忌惮到糜烂的淫叫盖过开门声,不理会别的扫兴的事情,就是指我开门进来。
我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结婚十年了描述起来还是含糊其辞。但我知道我和她前五年是貌合神离的,后五年是貌不合神更离的,就是这样从开始就充满了妥协的关系,所以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吧。
我现在是精疲力尽的,就算我不筋疲力尽,凭我孱弱的身躯能抗博那个陌生的男人吗?我不用估计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我拉上门回归暴雨的拥抱。我给学生做过词汇辨析:夺门而去和摔门而去都是走,一个是说兴奋的开门走一个是说愤怒的关门走,两者适用的语境不同不要混淆。我走时推门不兴奋,关门也不愤怒。
也许是我的肾功能不如料想中的强大,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也就和预期大相径庭,像本该硕果累累的树上等一年只结果了一颗苍蝇屎,这怎么能不让人大跌眼镜呢?所以在应该兴奋和愤怒的时候我拿的出出的情绪只有厌倦和茫然。对这样无趣的味同嚼蜡的婚姻,这样无趣的照本宣科的工作,这样无趣的水波不兴的生活我无不感到厌倦。为什么我总要经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呢?我的精力和情绪总在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竭泽而渔,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我渐渐恐惧我一眼可以看到结局的将来。
站在斑马线处,这样急的车流,这样滑的路面,随便哪一辆都能剥离我的性命吧。但我不能死在这里,这个路口离我家太近,我死在这里岂不是给闲人猜忌我的死因是接受不了妻子的出轨吗?这太无趣了,记得有哪个作家死前还有好心情说“自杀不留遗书是最好不过的”,这说法正合适我。
所以我就继续走。我走到不知道哪里不知道是谁的辖区才停下,我一踏上这里的柏油就和我交融,身体也自发瘫软贴在地上认定这是最好的墓地,我也就顺坡下驴打算这样过世了,倒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忽有一双探照大灯毫无征兆的照出我寻死的身姿。上万流明的光照是要帮我烤干衣服吗?可是雨还在下,我岂不成了小学课本上一面放水一面注水的游泳池。
我听到“sensei”的声音,抬头看过去,被探照大灯炙烤我睁不开眼睛,用手遮挡才勉强分辨了坐在后座的她和前排正襟危坐一言不发的司机。
奥,原来是她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看我赴死。不过或许被她碾死也没什么不好,闲人也找不出蛛丝马迹只当我的死是意外。我悔恨我在这时意识还清醒,能理解她的每一句话。
“老师躺在这里,是想寻死吗?”
她打开车门,撑起伞站在台阶上问我。我的视线早被雨水朦胧,大约只见得她绵密的丝袜。
“也许吧。人总归是要死的,早死一会晚死一会我看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吗?何况往后的苦难还更多……”我如此回答她。
“嗯,我并不关心老师的寻死的原因。不过既然老师已经是将死之人了,在死之前能帮我个忙吗?”她打断我的话问我,我都是将死之人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这倒没有什么所谓。”我回答的很慢,正像我的思考。
“把它拿回来。”她微微欠身从鞋子上摘下一个亮晶晶的东西,然后扔到马路对面。
“快点哦,老师。”她对我笑笑,我对此是有些不明所以的,但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也倦怠于思考她的动机。
这样湍急的车流,这样湿滑的路面,制动距离也会比平时长很多。但无所谓,我本来就是要寻死的,我没有犹豫就走过去,爬过护栏在地上摸索着找寻,什么时候我会被车撞死呢?奇怪的是我把东西捡回来了也没有一辆车和我拥抱。
“老师的运气很棒啊。不过它已经掉到水里了。很脏欸,我的鞋子肯定不愿意要了。嗯,那就请老师吃掉吧,反正老师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呵,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我随口吞下那个亮晶晶像是图钉的东西。
“还有另一只鞋子上的,老师不是总在强调秩序和规范,厌恶不协调吗?”她伸出左腿,居高临下对我说。
“用嘴。另外不要弄脏我的鞋子。”我刚伸出手就被她打断,她把我的手掌踩到污水里,我只好用牙齿拔下另一颗图钉装饰品咽下去,我吞了两颗钉子,自然是命不久矣。
“唔,鞋底踩到了垃圾呢,老师跟我过来。”
她撑着伞坐回车里,纤细的小腿垂在半空中摇曳。
“喝掉这些,否则会不消化的。”她指的是从鞋子滴下来的污水,我对于此是无所谓的。
“你是笨蛋吗?这样左面那只就会漏掉了啊。”她指责我的嘴张得不够大不能同时接到两只鞋子滴下来的污水,但其实我的下颌已经张到将近脱臼了。
她把鞋子踩进我的嘴里试图帮我的嘴巴扩容,奈何人是有生理限制的,一番尝试无果后她有些生气。
“真麻烦,你去拿块石头把牙齿磕掉好了。”她一面命令我,一面踩住我的脖子几乎令我窒息,我怔怔往上看着她,试图理解她的意思。
“那会很痛的……”我回复她。
“好吧,像老师这样脆弱的人做不到也正常。那老师该怎么向他们赎罪呢?”她轻轻撩起鞋子掠过我的视线。
赎罪,她是指漏掉了一部分污水的罪孽,这样的逻辑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太复杂了,我是理解不能的。我能做的只是再怔怔的看她。
“唔,还是要我想。这样吧,你吻住我的鞋子,不许咬痛他们!然后帮我从后备箱拿一双新的鞋子。”
她把鞋子脱下,自由落体砸下来,然后收回腿踩在座位上,转头盯着我笨拙的行动。“不许咬痛他们”是指让我用上下唇包裹鞋尖,这样就牙齿就不会接触皮革了,只是要时时用力,不然稍有松懈鞋子就会掉出来。我爬到后备箱,但车的底座竟高到我要站起来才拿的到里面的东西。她要的是什么?里面有礼服、胖次和鞋子。是礼服吗?换起来太繁琐,车内空间不大应该概率渺茫。那么就是胖次了,我把胖次捧过去为我成功赎罪感到满心欢喜。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鞋子!你……”她有些害羞,脸红了半边,夺过胖次藏在身后,偏偏我抱歉不能,我一开口鞋子就会掉下去,所以只能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
我只好再把装鞋子的盒子捧过来,看来我的罪孽又加了一条。
“你太脏了,我自己穿。把他们放到,嗯,胸部吧,我想还比较平坦。躺下。”
她以为我的胸部平坦,实际上也并不平坦,我瘦的琵琶骨一根根显露无疑。但我还是照做了。
“老师这么瘦弱,看来是不能踩在上面穿了,好可惜。”她用鞋尖抚过我的肋骨,发出这样的感慨。但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是个将死之人。她把丝袜提拉到紧紧裹着足部的程度,然后再踏进我胸脯上的盒子。穿好一只鞋子,她忽然注意到我的视线,我确实能看到她裙尾下覆盖着若隐若现的胖次,但我是个老师,而且是将死的老师,我想不出这时候看一个学生胖次的意义。
“不许看!”她用那只穿好的鞋子踏在我鼻梁上方以遮住我的视线,现在我只看得到鞋底上的纹路和印记了。鞋底上上刻着的扭曲的希腊字母,我虽不认得,不过大概就是我生前所见的最后的单词了。
穿好两只鞋子,她让我恢复膝行的姿势,然后蹲下来把空盒子放到我的背上。
“不许掉下来,老师的罪孽还没有赎完,所以要先跟我回家一趟。”她的语气大多是命令,但这次有些请求的意味,她和我对视,我撇开视线不回答她。我不想走,我贪恋这里沥青的滑腻,希冀能够就此弥散在这水雾里茫茫 。
“随便找辆车死在这里的话,老师觉得这是良善和蔼的做法吗?还是说只要是老师的行为,无论怎么样都算良善和蔼?”
“…………”
“跟你走,我还能死成吗?”
她答应会让我得偿所愿,我才跟着她缓缓的爬行。她让司机把车开的很慢,临近天黑的时候才到了一栋庄严肃穆的建筑。我对学生的家境向来是不关心的,我一向觉得有意了解这个当然是别有用心,所以现在见到夸张的城堡也无动于衷,将死之人不会纠结于细枝末节。
“家里只有我和女仆。”她应当是对我说的,但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她让我先洗澡,说遗体倘若不洁牛头马面是不收的,那样就成了孤魂野鬼,所以我只好先洗澡。可是洗完澡我却找不见我的衣服。
“家里没有男性的衣物啊。再说老师都是将死之人了,也没什么好害羞的吧。”她对我这样说,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我洗澡。她说的也不全错,尽管如此,对自己的学生赤身裸体也还是让我感到不自在,身体也有些应激的反应。
“老师怎么对学生发情了~”她凑过来,像抓住我的把柄般,好奇的戳戳我极力掩饰的东西,但越戳它就越兴奋了,好像在向主人邀功一样昂首挺胸。
“这可是比以往大的多的罪孽呢!你这样对得起他们吗?”她用夸张的语气质问我。
“什么?”我楞一会,然后顺着她的视线知道她是指鞋子。
“他们说想和老师接吻。”她接着说。我没有犹豫就趴下去,正欲亲吻她却避开来没有让我接触。
“不是这里,是另一个老师,对学生发情的老师。”我现在知道她是指什么了,我稍稍松手偷看它还丝毫没有要萎靡的迹象。我不愿意把我的丑态暴露出来,它如果没有反应,给她看倒也没什么所谓,可是现在它有反应,就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扰。良善之人就是到死也不愿给人添麻烦,不然我也不会跟她回来。
“我看这不是很合适,因为它不愿意。”
“嗯,我看他分明很愿意嘛,老师不要心口不一。”
她用鞋尖轻轻把我的蘑菇力抵在地上,和缓含蓄的摩挲蘑菇力的头。我的蘑菇力的头是很脆弱敏感的,一接触她的鞋尖就颤颤,尽管她用柔情安抚也无济于事。我的蘑菇力颤抖极力向上生长,奈何被皮革的天穹扼制住动弹不得。小草的所谓生机勃发,怎么度得过压路机带来的灭顶之灾呢?我的蘑菇力的反抗对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刚有起势,即被压回木板肿胀变形。蘑菇力的头还在水深火热,蘑菇力的身体却不明就里发生了什么。快要缴械之际,她终于有空眷顾蘑菇力的身体,从根部滑到头部,再踩住蘑菇力的头使管道闭合让他释放不能。
“让我去……”
我只好用手遮住不洁,向上伸长脖子去哀求她,像一个滑稽的曲颈瓶。
“老师分明犯下了欺骗之罪,却还大言不惭说这种话吗?”
“呜,我错了,我的蘑菇力很想和您的鞋子接吻,请让它去吧”
我把头低下盯住鞋子的亮面,那像乳房一样细腻的鞋子,沾着我基因的鞋子,正和我性交的鞋子,我该恐惧我呼出的浊气污染了他,课本上张屠户那只打过天上文曲星的手终究残疾了,我如此玷污圣物的罪行更加僭越,但我不在乎后果,因为我本来就要死了。
“清理干净。”
她终于轻描淡写的挪开了鞋子,我的蘑菇力才得以缴械疲软下来,我刚恢复正常的思考,转头就不愿承认我曾有过什么异样的想法,我回想一番终究确认了我是遭了迫害才一泻千里的。
我的死节愈发的明晃,我斥责她不要再辱我,我是一心求死的。
“…………好吧,我精通弓术,射艺比起甘蝇飞卫来也不遑多让,请老师去靶场。”甘蝇和飞卫,乃是我课上与学生们提起的两个古时的神射手。
靶场有弓,矢和草靶。草靶中间画着红红的大圆,我比对心脏位置刚好重合应当就万无一失。但真站在这里我又不免怀疑她的弓术,或许不那么精准……倘箭矢透过了身体却没死成怎么样?鸣泣回响在空旷的靶场,拖着骨断筋连的残躯给绿草地染成红色也无人在意,这实在不美观。我嘱托她,万一出了意外要及时给我介错,切记不要让我的哀嚎涌出声道。她提议在我心脏处先剜个红红的大圆来瞄,为防止我身体颤栗移位先用链子固定住四肢,但我这么怕痛怎会答应。
“果然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老师。”
她换上一身纯白的弓道服,足袋踏在细沙上交错开来,缓缓拉开弓弦。弦上的矢,箭头是精钢打的,旁有血槽。箭杆材料是黄檀木,尾部有用以平衡的雕翎。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所以现在的场景就不大和谐有点像大小姐处死犯错的奴隶。不过即便是那样又如何,反正结局一样我总是要死的。
我对纯白素有一种迷恋,因而我的蘑菇力又不合时宜的立了。
我看见她松手,看见流矢飞过来,听见猛烈的撞击声,我的肋骨原来那么坚硬,可以和精钢打出火花,我的心脏原来那么有力,搏动的声音大过钟锥撞击肉槽。我分明看见箭矢垂直长在我的身体,却没有看见红色的喷泉,也没有感受到等同于在身上剜出红色大圆的疼痛。我猜测是我是我的血糖太高以至于血粘稠的像糖浆,所以达不到激流勇射的视觉效果。我的肾上腺素后知后觉开始分泌,隔离了疼痛才让我自在飞花轻似梦。但肾上腺素的功效有那么持久吗?直到我的蘑菇力不立了低头贴到箭杆上我才后知后觉,箭透过了靶子没透过我的身体。假使当时我的蘑菇力没有立,那我现在就没有了蘑菇力。
“没有射中呢。老师该不会被吓到?”她放下弓,快步走过来,戏谑的问我。
虽我没有死成,经此却不愿意再这样死,往往是白受了惊吓却没有成事。
“偌大的建筑,怎么连几块煤炭也没有吗?我为什么死的这么迂回曲折唉。”
“唔,我也想帮老师尽快解脱,但这里确实没有煤炭。不过,老师不是讲过‘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故事吗?马跑的久了不休息,就会暴毙。所以……”
所以我又成了她的马,而且是汗血宝马。为什么是汗血宝马呢?因为我是汉人自然就是汗血,相当浅显的道理。她要我亲吻她的马靴,说这样才能协调马与主人的羁绊,否则就达不到疾行如霹雳弦惊的效果。我不知道这是情趣play还是死亡的先决条件,也不在乎。如果是前者,那我做的类似的事还少吗?
衔铁勒住我的牙齿不能张合,流涎修复铁片在口腔割出的伤口继而与血交融。滚烫的皮肤一接触到冰凉马靴即有刺痛感,沉重的马鞍把我的脊背压瘪。我觉得我负重跑了三公里,其实我才走了三百步就扑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我究竟有没有死,大家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我死了,是被箭射死的,胸口只剩下个红红的大洞不见了心脏。也有说我是被车创死了,或者是劳役太重累死了。但我知道我没有死,我醒来看到壁炉里燃烧的煤炭就开始沮丧了。
我问她,你分明有煤炭,怎么说没有呢?
“有这么样,没有怎么样,反正大家觉得老师已经死了。无论是和老师共事的讲学家,还是老师的妻子都这么说。讣告上大家还称赞老师是良善和蔼的人呢~”
这也算我没有白死。在后来,我又问她,那疾驰的车流怎么一辆都沾不到我身上呢?为什么我吃了钉子却安然无恙呢?
“那条路早就被管控了啊。‘钉子’是巧克力做的。”
“那我记得当时还有车流?”
“我有不止一个司机。他们原本是家父的司机,家父过世后,留下了这座公馆和女仆以及司机们。”她说话时,正看着壁炉里燃烧的煤炭。
“有这样的事情啊……”我感慨道。
那煤炭亮的发光,远远看来质地细腻绵柔,也难怪不仅讲学家而且他父亲都对其消逝的雾气趋之若鹜了。那个侃侃而谈的讲学家确实死了,但我没有时间在他坟前哀默,我新找了个管家的工作。作为公馆里唯一的男性伺候大小姐是极易受到刁难的,好在日子不像讲学家生前一般无趣。
后来我终于有空去讲学家的坟探看,誊抄了不知谁赠与他的奠语:
纵令人寿三百岁,愉逸度世,较之永生无尽之乐趣,亦不过梦幻耳。
唯立心为善者,乃能于圣教中得不可思议之妙趣。
好看滴
读了一遍,文瘾犯了,又读一遍,再读一遍,最后不知读了多少遍……典故很多,最关键的是!对场景都很贴切!
蘑菇力涩文段hhh黑色幽默也欲罢不能~
把腐儒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拽出来踩,太尽兴了!
精神胜利的讲学家终究是死了,把孔家店里的糟粕全埋回土里罢。
(是女孩子的鞋拯救了他,确信)
蘑菇力涩文段hhh黑色幽默也欲罢不能~
把腐儒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拽出来踩,太尽兴了!
精神胜利的讲学家终究是死了,把孔家店里的糟粕全埋回土里罢。
(是女孩子的鞋拯救了他,确信)
旧坑不填,又挖新坑,写得还这么好,妈的,求求多写几篇
大佬好厉害!
大佬好厉害!学都学不来的。
唉,我看个黄文发泄还要自认不如别人。
q老师太有文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