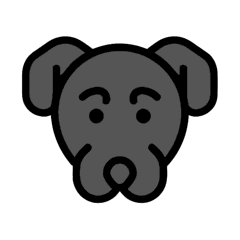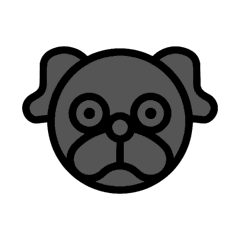姐姐的爱
长靴舔鞋连载中踩踏高跟鞋原创现实阶级职场大小姐鞋靴纯爱异世界纪实御姐
稍微有点吃设定了么,既然老妈一点都不在乎底层,为什么又要把孩子放在底层呢
作者加油
期待作者继续更新,这种利用权力玩弄奴隶的情节好刺激
watermallen:↑稍微有点吃设定了么,既然老妈一点都不在乎底层,为什么又要把孩子放在底层呢后面会有简单的交代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那个烟头躺在焦黑的地毯上,像一条被碾死的虫子。滤嘴上的口红印记艳丽如血,而烟草已经被碾得支离破碎,混合着地毯烧焦的纤维。
“听不懂人话?”她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
我看着那个烟头,喉咙发紧。张盟正在整理手中的麻将牌,仿佛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但我似乎看到她的手指微微颤动了一下。
长靴女人的鞋尖不耐烦地点了点地面:“怎么?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我低下头,慢慢地俯身向那个烟头......
我看着那个被碾碎的烟头,一时间耳边只剩下自己急促的心跳声。麻将牌的碰撞声似乎也变得遥远,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慢慢低下头,我能闻到烟头散发出的复杂气味。烟草、高档口红、皮革和焦糊的地毯纤维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晕眩的气息。那支烟已经被长靴碾得变形,金色的滤嘴上还留着鲜艳的口红印记,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我张开嘴,小心翼翼地用牙齿叼起烟头。滤嘴接触到舌头的瞬间,一股高级化妆品的香气立即在口腔中弥漫。那是某种奢侈品牌的口红,价格可能顶得上我一年的口粮配给。但更让我羞愧和困惑的是,在那个被她朱唇含过的滤嘴处,竟然隐约有一丝甜味。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错觉。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我最后的自尊。在这种耻辱的处境下,我竟然从这种甜味中感受到了一丝病态的愉悦,这让我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整个过程中,张盟始终保持着沉默,专注地整理着手中的麻将牌。但我知道她一定看到了一切。
......
尽管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萦绕在我的味蕾上,但当我真正要吞下这个烟头时,身体还是本能地抗拒着。喉咙像是被无形的手掐住,完全不配合这个吞咽的动作。烟草的苦涩和地毯纤维的粗糙感几乎要将我的食道撕裂,那一点点甜味反而让这种痛苦显得更加讽刺。
我强忍着干呕的冲动,我开始把烟头往嘴里送。烟草的碎屑开始脱落,一些掉在我的舌头上。苦涩中带着焦香,而那若隐若现的甜味却始终萦绕不去。被碾碎的地毯纤维粘在烟草上,像细小的刺一样扎着我的舌头,但我的注意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一点甜味上。试图做出吞咽的动作。破碎的烟头像一块粗糙的砂纸,一点一点刮过我的食道。即便有那若隐若现的甜味作为微妙的慰藉,这种吞咽的过程依然是一种煎熬。我的喉结艰难地滚动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好不容易将烟头咽下,我的胃部立即开始剧烈地抽搐。那种异物感和恶心感一波波地袭来,但我却不敢有任何呕吐的举动。口腔里还残留着那种矛盾的味道:高级化妆品的香气、烟草的苦涩、地毯纤维的焦糊味,我的喉咙不自觉地收紧了。不是因为烟草的苦涩,而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羞耻。在这种赤裸裸的侮辱面前,我不但没有感到纯粹的痛苦,反而在那个被碾碎的烟头上尝到了一丝病态的甜美,这种认知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厌弃。还有那一丝挥之不去的甜。这些味道纠缠在一起,就像我此刻复杂的心绪。
长靴在地毯上不耐烦地点了点,我知道不能再拖延。一鼓作气将烟头吞下,口腔里还残留着那复杂的味道。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生怕被人看出我内心的波澜。那个烟头在我的食道里缓慢下滑,带着它所有的甜美与耻辱。
我的胃开始翻腾,但不知是因为烟草的刺激,还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恶感。那一丝甜味还在我的味蕾上跳动,像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烙印,提醒着我在这场侮辱中竟然尝到了一丝扭曲的快感。
烟头入腹后我仍跪在原地,感受着胃里那种火辣辣的不适。这时长靴美女突然发出一声轻笑,那笑声像是浸了蜜糖又像是淬了毒药。
“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她的声音故作温柔,却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看来还是有点眼力见的。”
我知道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但不知为何,她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却让我的心跳微微加快。那双擦得锃亮的长靴就在我眼前,我能看到自己扭曲的倒影。
她优雅地抖了抖裙摆,轻轻抬起那只踩过烟头的靴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她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我可是让你吃了那么珍贵的东西。要知道,这种香烟,你这辈子要不是我大发慈悲,怕是连见都见不到这种烟。”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讥讽,“还不快谢谢我的恩赐?”
我立即低下头,额头重重地磕在地毯上。那个被烟头烫出的焦黑痕迹就在我的额头下方,还残留着一丝温度。
“谢谢......”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谢谢领导的恩赐......”
每一次磕头,我都能闻到地毯上残留的香烟味道,混合着她靴子的皮革气息。那股若有若无的甜味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舌尖,让我的心跳变得更快。
当我准备起身去清理其他垃圾时,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
“我让你停了吗?”
这句话像一记闷雷,让我浑身一颤。我立即跪好,继续磕头,额头一下下地叩在地毯上。每一次磕头,我都要重复那句“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声音机械地重复着,但我的内心却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这种被完全掌控的状态,这种不得不表达感谢的屈辱,不知为何却让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意。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脸颊开始发烫,不知是因为羞耻还是别的什么。磕头仍在继续,额头已经开始发红。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疼痛。相反,每一次叩首,都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仿佛在这种极度的屈辱中,我反而找到了某种扭曲的自由。
那位长靴美女的笑声依然在耳边回荡,带着一丝胜利者的愉悦。她享受着这种掌控的快感,而我,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公子哥,此刻却在她的靴子前不停叩首,感谢她让我吃下一个烟头。这种身份的反转,这种极致的耻辱,不知为何却在我心中激起了一波波异样的涟漪。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感到愤怒和屈辱,但我的身体和内心却背叛了这种理性的判断,沉沦在这种病态的支配与臣服关系中。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在持续的磕头过程中,那个烟头的甜味似乎在我的口中越发明显。这种味道不再让我感到恶心,反而成了某种奇异的慰藉。就像此刻的心理状态一样,在绝对的压迫下,反而品尝到了一丝病态的甜美。
正当我机械地重复着磕头动作时,一股突如其来的重压让我猝不及防。那位长靴美女抬起她的右脚,将平底靴的靴底重重踩在我的后脑勺上。我的额头猛地撞在地毯上,即使有地毯的缓冲,这一下依然让我眼前发黑。
“怎么,不继续了?”她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带着一丝冷酷的笑意,“我说过可以停了吗?”说着,她的脚又往下用力,将我的头死死压在地毯上。我能闻到地毯上的烟草味,混合着她靴子上的皮革气息。那只踩在我头上的靴子,重量远比想象中要大。
“给我继续!”她命令道,同时用力跺了两下我的后脑勺。每一下都让我的额头重重撞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在这种强大的压迫下,我不得不继续磕头。每一次要抬起头,都需要同时承受着她靴子的重量。脖子的肌肉因为这种非正常的用力而酸痛不已,但我不敢停下。
“咚、咚、咚”,沉闷的撞击声在房间里回荡。每一次磕头都因为靴子的重量而显得格外沉重。我的额头已经开始发烫,不知是因为摩擦还是撞击。在长靴美女的靴底重压下,每一次磕头都变成了一场艰难的挣扎。我的脖颈肌肉绷紧,努力对抗着后脑勺上的重量。那只靴子仿佛有千斤重,将我牢牢钉在地上。
抬头的过程极其痛苦。我的颈椎发出咯咯的响声,脖子上的每一根筋都在颤抖。那只长靴随着我的动作微微抬起,却始终保持着向下的压力。皮革的气息和地毯的绒毛味道充斥着我的鼻腔,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砰!”我刚刚抬起头,她突然加重力道,我的额头重重砸在地毯上。地毯的纤维已经被我的额头蹭得发热,那个被烟头烫过的黑点就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提醒着之前的耻辱。
“用力!”她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伴随着一记重踩,“给我使劲磕!”
我咬紧牙关,调动全身的力气。脖子和后背的肌肉像是要撕裂一般疼痛,但我不得不继续。每一次抬头,都要承受着她靴子的重量,就像是在举起一块巨石。而每一次落下,都因为双重的力量而显得格外沉重。
“咚!”
“咚!”
“咚!”
沉闷的撞击声回荡在房间里,节奏缓慢而稳定。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已经开始发烫,可能已经红肿起来。但比起身体的疼痛,更让我困扰的是内心泛起的异样感觉。
有时候,正当我用尽全力要抬起头时,她会突然发力下压。我的脖子会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压而剧烈颤抖,额头也会比平时撞得更重。奇怪的是,这种完全被掌控的感觉不仅没有让我屈辱,反而给我带来了一种诡异的安心感。
每一次磕头,我都能感受到她靴底的纹路压在我的头发上。那种触感是如此清晰,仿佛要永远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有时候她会稍稍调整脚的位置,皮靴摩擦头皮的感觉让我不自觉地感受到一丝丝的快意。
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不知是因为体力的消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个烟头的甜味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舌尖,与满头的汗水和皮革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味道。
“还不够用力!”她又是一记重踩,同时用平底靴的跟部用力的磕了磕我的后脑勺,“给我继续!”
这种居高临下的命令使我我的心跳陡然加速。我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在她靴底下的渺小,就像一只随时可能被碾碎的蚂蚁。这种认知本该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怒,但我的身体却诚实地做出了反应: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发烫。
“听不懂人话?”她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
我看着那个烟头,喉咙发紧。张盟正在整理手中的麻将牌,仿佛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但我似乎看到她的手指微微颤动了一下。
长靴女人的鞋尖不耐烦地点了点地面:“怎么?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我低下头,慢慢地俯身向那个烟头......
我看着那个被碾碎的烟头,一时间耳边只剩下自己急促的心跳声。麻将牌的碰撞声似乎也变得遥远,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慢慢低下头,我能闻到烟头散发出的复杂气味。烟草、高档口红、皮革和焦糊的地毯纤维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晕眩的气息。那支烟已经被长靴碾得变形,金色的滤嘴上还留着鲜艳的口红印记,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我张开嘴,小心翼翼地用牙齿叼起烟头。滤嘴接触到舌头的瞬间,一股高级化妆品的香气立即在口腔中弥漫。那是某种奢侈品牌的口红,价格可能顶得上我一年的口粮配给。但更让我羞愧和困惑的是,在那个被她朱唇含过的滤嘴处,竟然隐约有一丝甜味。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错觉。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我最后的自尊。在这种耻辱的处境下,我竟然从这种甜味中感受到了一丝病态的愉悦,这让我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整个过程中,张盟始终保持着沉默,专注地整理着手中的麻将牌。但我知道她一定看到了一切。
......
尽管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萦绕在我的味蕾上,但当我真正要吞下这个烟头时,身体还是本能地抗拒着。喉咙像是被无形的手掐住,完全不配合这个吞咽的动作。烟草的苦涩和地毯纤维的粗糙感几乎要将我的食道撕裂,那一点点甜味反而让这种痛苦显得更加讽刺。
我强忍着干呕的冲动,我开始把烟头往嘴里送。烟草的碎屑开始脱落,一些掉在我的舌头上。苦涩中带着焦香,而那若隐若现的甜味却始终萦绕不去。被碾碎的地毯纤维粘在烟草上,像细小的刺一样扎着我的舌头,但我的注意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一点甜味上。试图做出吞咽的动作。破碎的烟头像一块粗糙的砂纸,一点一点刮过我的食道。即便有那若隐若现的甜味作为微妙的慰藉,这种吞咽的过程依然是一种煎熬。我的喉结艰难地滚动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好不容易将烟头咽下,我的胃部立即开始剧烈地抽搐。那种异物感和恶心感一波波地袭来,但我却不敢有任何呕吐的举动。口腔里还残留着那种矛盾的味道:高级化妆品的香气、烟草的苦涩、地毯纤维的焦糊味,我的喉咙不自觉地收紧了。不是因为烟草的苦涩,而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羞耻。在这种赤裸裸的侮辱面前,我不但没有感到纯粹的痛苦,反而在那个被碾碎的烟头上尝到了一丝病态的甜美,这种认知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厌弃。还有那一丝挥之不去的甜。这些味道纠缠在一起,就像我此刻复杂的心绪。
长靴在地毯上不耐烦地点了点,我知道不能再拖延。一鼓作气将烟头吞下,口腔里还残留着那复杂的味道。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生怕被人看出我内心的波澜。那个烟头在我的食道里缓慢下滑,带着它所有的甜美与耻辱。
我的胃开始翻腾,但不知是因为烟草的刺激,还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恶感。那一丝甜味还在我的味蕾上跳动,像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烙印,提醒着我在这场侮辱中竟然尝到了一丝扭曲的快感。
烟头入腹后我仍跪在原地,感受着胃里那种火辣辣的不适。这时长靴美女突然发出一声轻笑,那笑声像是浸了蜜糖又像是淬了毒药。
“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她的声音故作温柔,却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看来还是有点眼力见的。”
我知道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但不知为何,她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却让我的心跳微微加快。那双擦得锃亮的长靴就在我眼前,我能看到自己扭曲的倒影。
她优雅地抖了抖裙摆,轻轻抬起那只踩过烟头的靴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她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我可是让你吃了那么珍贵的东西。要知道,这种香烟,你这辈子要不是我大发慈悲,怕是连见都见不到这种烟。”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讥讽,“还不快谢谢我的恩赐?”
我立即低下头,额头重重地磕在地毯上。那个被烟头烫出的焦黑痕迹就在我的额头下方,还残留着一丝温度。
“谢谢......”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谢谢领导的恩赐......”
每一次磕头,我都能闻到地毯上残留的香烟味道,混合着她靴子的皮革气息。那股若有若无的甜味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舌尖,让我的心跳变得更快。
当我准备起身去清理其他垃圾时,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
“我让你停了吗?”
这句话像一记闷雷,让我浑身一颤。我立即跪好,继续磕头,额头一下下地叩在地毯上。每一次磕头,我都要重复那句“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声音机械地重复着,但我的内心却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这种被完全掌控的状态,这种不得不表达感谢的屈辱,不知为何却让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意。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脸颊开始发烫,不知是因为羞耻还是别的什么。磕头仍在继续,额头已经开始发红。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疼痛。相反,每一次叩首,都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仿佛在这种极度的屈辱中,我反而找到了某种扭曲的自由。
那位长靴美女的笑声依然在耳边回荡,带着一丝胜利者的愉悦。她享受着这种掌控的快感,而我,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公子哥,此刻却在她的靴子前不停叩首,感谢她让我吃下一个烟头。这种身份的反转,这种极致的耻辱,不知为何却在我心中激起了一波波异样的涟漪。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感到愤怒和屈辱,但我的身体和内心却背叛了这种理性的判断,沉沦在这种病态的支配与臣服关系中。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在持续的磕头过程中,那个烟头的甜味似乎在我的口中越发明显。这种味道不再让我感到恶心,反而成了某种奇异的慰藉。就像此刻的心理状态一样,在绝对的压迫下,反而品尝到了一丝病态的甜美。
正当我机械地重复着磕头动作时,一股突如其来的重压让我猝不及防。那位长靴美女抬起她的右脚,将平底靴的靴底重重踩在我的后脑勺上。我的额头猛地撞在地毯上,即使有地毯的缓冲,这一下依然让我眼前发黑。
“怎么,不继续了?”她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带着一丝冷酷的笑意,“我说过可以停了吗?”说着,她的脚又往下用力,将我的头死死压在地毯上。我能闻到地毯上的烟草味,混合着她靴子上的皮革气息。那只踩在我头上的靴子,重量远比想象中要大。
“给我继续!”她命令道,同时用力跺了两下我的后脑勺。每一下都让我的额头重重撞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在这种强大的压迫下,我不得不继续磕头。每一次要抬起头,都需要同时承受着她靴子的重量。脖子的肌肉因为这种非正常的用力而酸痛不已,但我不敢停下。
“咚、咚、咚”,沉闷的撞击声在房间里回荡。每一次磕头都因为靴子的重量而显得格外沉重。我的额头已经开始发烫,不知是因为摩擦还是撞击。在长靴美女的靴底重压下,每一次磕头都变成了一场艰难的挣扎。我的脖颈肌肉绷紧,努力对抗着后脑勺上的重量。那只靴子仿佛有千斤重,将我牢牢钉在地上。
抬头的过程极其痛苦。我的颈椎发出咯咯的响声,脖子上的每一根筋都在颤抖。那只长靴随着我的动作微微抬起,却始终保持着向下的压力。皮革的气息和地毯的绒毛味道充斥着我的鼻腔,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砰!”我刚刚抬起头,她突然加重力道,我的额头重重砸在地毯上。地毯的纤维已经被我的额头蹭得发热,那个被烟头烫过的黑点就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提醒着之前的耻辱。
“用力!”她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伴随着一记重踩,“给我使劲磕!”
我咬紧牙关,调动全身的力气。脖子和后背的肌肉像是要撕裂一般疼痛,但我不得不继续。每一次抬头,都要承受着她靴子的重量,就像是在举起一块巨石。而每一次落下,都因为双重的力量而显得格外沉重。
“咚!”
“咚!”
“咚!”
沉闷的撞击声回荡在房间里,节奏缓慢而稳定。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已经开始发烫,可能已经红肿起来。但比起身体的疼痛,更让我困扰的是内心泛起的异样感觉。
有时候,正当我用尽全力要抬起头时,她会突然发力下压。我的脖子会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压而剧烈颤抖,额头也会比平时撞得更重。奇怪的是,这种完全被掌控的感觉不仅没有让我屈辱,反而给我带来了一种诡异的安心感。
每一次磕头,我都能感受到她靴底的纹路压在我的头发上。那种触感是如此清晰,仿佛要永远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有时候她会稍稍调整脚的位置,皮靴摩擦头皮的感觉让我不自觉地感受到一丝丝的快意。
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不知是因为体力的消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个烟头的甜味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舌尖,与满头的汗水和皮革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味道。
“还不够用力!”她又是一记重踩,同时用平底靴的跟部用力的磕了磕我的后脑勺,“给我继续!”
这种居高临下的命令使我我的心跳陡然加速。我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在她靴底下的渺小,就像一只随时可能被碾碎的蚂蚁。这种认知本该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怒,但我的身体却诚实地做出了反应: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发烫。
麻将桌上的人们开心的聊着天,仿佛着一切都没有发生,麻将牌在她们手中发出规律的响声。
额头撞击地毯的闷响,长靴摩擦头皮的声音,伴随着麻将的碰撞声。还有自己越来越重的喘息,这些声音在我的耳中交织成一首诡异的交响曲。而那些不该有的感觉,那些危险的想法,也在这种律动中越来越清晰。
我只能用更重的磕头来惩罚自己这种不该有的想法。然而,额头的疼痛非但没有让这种感觉消退,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强烈。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脸颊越来越烫,全身都在微微发抖。但我不能停下,也不敢停下。在她的靴底下,在这个房间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奴仆,必须遵从主人的每一个命令。这个认知让我既感到耻辱,又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解脱。在这种极度的压迫中,我的内心深深泛起一阵阵难以言喻的涟漪。这种完全被掌控的状态,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意。我立即掐断了这个念头,这种想法太过危险。但那种异样的感觉却如同潮水般一波波涌来。我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继续磕头上,试图用物理的疼痛来压制内心复杂的感受。额头的撞击,脖子的酸痛,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我必须承受的。而其他的感觉,那些不该有的感觉,我努力将它们封闭在意识的最深处。
而那个烟头的甜味似乎还在我的唇齿间萦绕,随着每一次磕头变得愈发明显。这让我越发困惑:为什么在这种极度的屈辱中,我没有感到纯粹的痛苦?为什么那些本该让我屈辱的举动,却让我的心跳变得如此剧烈?但我不敢也不能去深究这些问题。我只能继续着这机械的磕头动作,在靴子的重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叩击着地面,直到她允许我停下。
我的额头一次次叩击着地毯,每一下都比上一下更加沉重。长时间的磕头让我的脖子几乎失去知觉,但那只踩在我后脑勺上的靴子依然保持着恒定的压力。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汗水浸透了衣襟,却不敢有丝毫停歇。麻将的碰撞声依然在继续,夹杂着她们漫不经心的交谈。我的意识开始模糊,只能机械地重复着磕头的动作。沉重的撞击声在房间里回荡,就像某种单调的背景音乐。
“咚...咚...咚..”
我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体力在这种重复的折磨中逐渐耗尽。但只要一稍微放慢速度,头顶的靴子就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提醒我不能懈怠。
“雪琪,”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这种机械的节奏,是坐在旁边的那位女士。
“你看看这边,我这里都是垃圾。”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在抱怨咖啡不够热一样随意。
原来长靴美女叫雪琪。这个略带娇媚的名字与她冷酷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但我没有时间多想,因为头顶的重压突然消失了。然而,还没等我松一口气,一记突如其来的重踢就落在我的肋下。
我立即会意,连滚带爬地转向垃圾较多的那一侧。额头上的肿块火辣辣的疼,脖子几乎失去直立的力气。爬行的过程中,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雪琪的靴子。那双沾着我头发的长靴在灯光下依然锃亮,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对比让我感到一阵晕眩,却又莫名地期待着什么。
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上的垃圾上。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但当我低头收拾那些零碎的垃圾时,身体却依然记得那种沉重的压迫感。清理垃圾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我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嘴叼起每一片纸屑、每一个零食包装。在这些高跟鞋与长靴之间穿梭时,我必须格外注意不能碰到任何人的鞋子 - 这是底层人员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麻将的声响继续着,我的动作也必须配合她们的节奏:当有人要出牌时,我要及时避让;当有人伸腿时,我要立即后退。这是一场无声的舞蹈,我在其中扮演着最卑微的配角。地毯上的每一寸区域都需要仔细检查。有时一片小小的纸屑会藏在地毯的绒毛之间,我必须凑得很近才能发现。额头上的肿块还在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之前的教训。但这种疼痛反而让我更加专注于当前的工作。
最难处理的是那些散落的饼干碎屑。它们会陷入地毯的纤维中,必须用嘴唇贴近地毯,像吸尘器一样仔细吸吮才能清理干净。这个过程极其耗费体力,没多久我的嗓子就疼痛难忍。但我不敢表现出任何不适。
同时几位领导打牌时的动作让清理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每当有人伸腿或挪动椅子时,我都要立即做出反应。有时正在处理一片垃圾,突然有人把脚伸过来,我就不得不立即后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继续。这种走走停停的节奏让工作的难度倍增。
不知过了多久,三位女领导终于起身离开。她们谈笑着走向门口,高跟鞋在地毯上留下一个个凹痕。临走前,雪琪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房间里终于只剩下我和张盟。她坐在真皮沙发上,专注地玩着手机,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整个房间,确保每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完成清理后,我恭敬地跪行到张盟脚边,低头叩首。她随意地抬起脚,在我的头上点了两下,这是默许的信号。我退到一旁,保持着跪姿。
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突然涌上心头:我今天一直在这里服务,完全错过了温度控制的练习。而据说,总公司的领导随时可能来视察。万一到时候出了差错......这个念头让我坐立不安。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举起手。但张盟正专注于手机,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用最卑微的方式引起她的注意 - 我轻轻地"旺旺"叫了两声。
这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立即后悔了,这种行为太过僭越。然而张盟却抬起头来,眼神示意我可以说话。
“张组长......”
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抖,“我......我......”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没有练习掌控温度的忧虑?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个问题太过冒险,我开始后悔提出来。然而张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她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你不用担心。”她的声音平静,“你们的工作安排,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到时候我直接安排你作为我的保障人员跟我一起,不就好了?”
这句话给我整得一阵懵逼。保障人员?这是只有总公司领导才会配备的职位。一个小组长,怎么可能有权力配备保障人员?除非......
我不敢再想下去,只是感激地向张盟连连叩首。但内心的疑惑更深了:她到底是谁?为什么会以小组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但张盟这句话确实让我松了一口气。至少在视察期间,我不用担心因为技术不熟练而被处死。
时日流转,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那些紧张的温度控制训练仿佛成了上辈子的事,现在的我每天都在张盟的房间里度过,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清洁工"。
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其他人提早一个小时到达。在重复打扫一遍卫生,虽然每天离去的时候已经打扫的很干净。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永远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晨光透过落地窗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这短暂的宁静总会让我想起从前的幸福生活。
九点钟一到,她们就会陆续到达。高跟鞋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像是某种无声的提示。预示着我需要立即下跪,保持最标准的姿势。麻将的声音很快会响起,伴随着她们漫不经心的谈笑。我跪在角落里,随时准备着清理任何垃圾。这些曾经和我平起平坐的管理者们,现在把我当作一件随意摆布的物品。
最难熬的是她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她们会突发奇想,要我做一些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她们对“寻开心”总有无穷的创意。有时是简单的模仿动物:让我学狗叫、学猫叫,但必须声音要足够“真诚”。如果她们觉得不够投入,就会要求反复进行,直到她们满意为止。
有时她们会玩“木偶游戏”。几位女领导会轮流发出指令,我必须立即做出相应动作。“抬头”、“低头”等等复杂的动作。命令快速更替,稍有迟疑就要受罚。这些机械的动作让我想起以前在动物园看到的经过训练的海豹,现在我却成了那个被训练的对象。
偶尔,她们会玩“静止游戏”。要求我保持某个不自然的姿势一动不动,动一下就要重来。有时是单脚跪立,有时是双手撑地。时间长了,肌肉会开始颤抖,冷汗直流,但我不敢有丝毫松懈。最难熬的是她们会在旁边谈笑。
雪琪最喜欢的游戏是“找东西”。这个游戏并不是普通的捉迷藏,她总是会随意将某样物品藏在她那双精致长筒靴的底下,故意用脚踩着,让我无从下手地去寻找。因为我是没有资格去随意碰触鞋子,更不用说去动她藏在底下的物品。每次游戏开始时,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急切与无奈。她们的笑声在空气中蔓延,尽管我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她们总是哈哈大笑,似乎在嘲讽我的笨拙。有一次,为了能取回那个小玩意,我心中暗自筹划,我深吸一口气,向雪琪的脚边靠近,微微颤抖着磕头,一边恳求:
“求雪领导高抬贵脚。”
这一幕引起了周围女领导的极大兴趣,她们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欢愉,纷纷发出哈哈大笑声。我抬头看向雪琪,看到她嘴角勾起一抹顽皮的微笑,那笑容中洋溢着无尽的戏谑。她稍微抬起脚,故意将靴子轻轻晃动。
“听到了吗?不可以求我,你得求它。”她的指尖指向她那双吸引眼球的长筒靴。
我无奈地低下头,凝视着她的靴子,最终我也只能顺应她的调侃,对着那双靴子再次磕头,声声呼唤:
“求求你,求求你!”
这场景惹得她们再次大笑,她们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仿佛光芒四射。我憋红了脸,却也只能无奈地出丑。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如何在羞耻和恳求中挣扎,享受着这种感觉,此时雪琪看着我的模样,似乎越发得意,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她微微侧身,一只优雅的腿轻轻抬起,长筒靴的曲线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迷人,她轻轻晃动着脚,似乎在玩弄着我这只乞求者的心理。
“越求越没用哦!”她甜美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玩味,令我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感受到周的目光,那是一种带着嘲弄与享受的目光,她们沉浸在这场表演之中。在她们眼中,我或许就是一个任人摆弄的玩具,毫无反抗之力。我又试图调整一下情绪。
“你就这样放弃吧!再怎么求都没用!”她的话语像是甜蜜的嘲讽,撩动着周围女孩们的笑声,进一步放大了我的窘迫。不知道是靴子还是靴子下的物品似乎在无形中牵动着我的心绪,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怎么,你就这么想要这个小玩意儿吗?”雪琪的声音轻柔却又带着一丝玩味。她微微晃动着她那闪亮的靴子。我心中无奈,却又无可奈何。
“你们说,我要不要答应他?”她转头问她的朋友们,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那些女孩们的笑声此起彼伏。
“只要他跪得更低,或许就能求到!”其中一个女孩发出调侃的声音,众人不禁大笑。
“你真的不愿意再来一次吗?”雪琪微微侧头,眼神中藏着一丝调皮。
“求求你,求求你!”我再次低头,继续磕头。最终,雪琪的笑声在此时变得越来越清脆,周围女孩们则像是沉浸在狂欢中,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想你得加大你的诚意哦!”
“求……求求你……,高抬贵脚!”
雪琪听后,顿时掩嘴轻笑,似乎对这场戏愈发有趣。“快!继续求!”一个女孩在一旁起哄。
“求求你,高抬贵脚,”我不得不再次恳求,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却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绝望。此时雪琪的笑容越发妖娆,她在享受着。
“好吧,求得如此诚恳,我的心都被你打动了呢!”她的声音依旧带着一丝戏谑。随着她轻轻抬起脚,靴子底下的物品终于露出了个角,我仿佛看见了希望。
“来,继续你的求吧,我会考虑的。”她将脚微微往外一移,露出那个藏在靴子底下的物品,似乎在引导我去把它拿回。雪琪微微抬起脚,我正准备伸手去拿她的腿,谁知她突然“啪”的一声继续踩了下去。眼中带着几分戏谑,俏皮地盯着我。这一瞬间,我鼓起勇气,深情地向她的长筒靴亲吻了下去。当我的唇触碰到靴子的那一刻,靴子似乎轻轻抬起了一点,仿佛在回应我的举动。我鼓起勇气,持续亲吻着这双靴子,每一次亲吻都伴随着靴子的微微抬升。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我的内心又现出原先那种异样的感受,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柔而沉醉。靴子在我唇边轻轻摇曳,仿佛在引导我走向更深的投入。就在这时,我注意到靴子已经完全抬起,与我之间的距离仿佛更加拉近,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又强烈的连接。每一次接触都让我感到格外真实,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悸动。
额头撞击地毯的闷响,长靴摩擦头皮的声音,伴随着麻将的碰撞声。还有自己越来越重的喘息,这些声音在我的耳中交织成一首诡异的交响曲。而那些不该有的感觉,那些危险的想法,也在这种律动中越来越清晰。
我只能用更重的磕头来惩罚自己这种不该有的想法。然而,额头的疼痛非但没有让这种感觉消退,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强烈。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脸颊越来越烫,全身都在微微发抖。但我不能停下,也不敢停下。在她的靴底下,在这个房间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奴仆,必须遵从主人的每一个命令。这个认知让我既感到耻辱,又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解脱。在这种极度的压迫中,我的内心深深泛起一阵阵难以言喻的涟漪。这种完全被掌控的状态,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意。我立即掐断了这个念头,这种想法太过危险。但那种异样的感觉却如同潮水般一波波涌来。我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继续磕头上,试图用物理的疼痛来压制内心复杂的感受。额头的撞击,脖子的酸痛,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我必须承受的。而其他的感觉,那些不该有的感觉,我努力将它们封闭在意识的最深处。
而那个烟头的甜味似乎还在我的唇齿间萦绕,随着每一次磕头变得愈发明显。这让我越发困惑:为什么在这种极度的屈辱中,我没有感到纯粹的痛苦?为什么那些本该让我屈辱的举动,却让我的心跳变得如此剧烈?但我不敢也不能去深究这些问题。我只能继续着这机械的磕头动作,在靴子的重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叩击着地面,直到她允许我停下。
我的额头一次次叩击着地毯,每一下都比上一下更加沉重。长时间的磕头让我的脖子几乎失去知觉,但那只踩在我后脑勺上的靴子依然保持着恒定的压力。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汗水浸透了衣襟,却不敢有丝毫停歇。麻将的碰撞声依然在继续,夹杂着她们漫不经心的交谈。我的意识开始模糊,只能机械地重复着磕头的动作。沉重的撞击声在房间里回荡,就像某种单调的背景音乐。
“咚...咚...咚..”
我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体力在这种重复的折磨中逐渐耗尽。但只要一稍微放慢速度,头顶的靴子就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提醒我不能懈怠。
“雪琪,”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这种机械的节奏,是坐在旁边的那位女士。
“你看看这边,我这里都是垃圾。”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在抱怨咖啡不够热一样随意。
原来长靴美女叫雪琪。这个略带娇媚的名字与她冷酷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但我没有时间多想,因为头顶的重压突然消失了。然而,还没等我松一口气,一记突如其来的重踢就落在我的肋下。
我立即会意,连滚带爬地转向垃圾较多的那一侧。额头上的肿块火辣辣的疼,脖子几乎失去直立的力气。爬行的过程中,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雪琪的靴子。那双沾着我头发的长靴在灯光下依然锃亮,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对比让我感到一阵晕眩,却又莫名地期待着什么。
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上的垃圾上。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但当我低头收拾那些零碎的垃圾时,身体却依然记得那种沉重的压迫感。清理垃圾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我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嘴叼起每一片纸屑、每一个零食包装。在这些高跟鞋与长靴之间穿梭时,我必须格外注意不能碰到任何人的鞋子 - 这是底层人员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麻将的声响继续着,我的动作也必须配合她们的节奏:当有人要出牌时,我要及时避让;当有人伸腿时,我要立即后退。这是一场无声的舞蹈,我在其中扮演着最卑微的配角。地毯上的每一寸区域都需要仔细检查。有时一片小小的纸屑会藏在地毯的绒毛之间,我必须凑得很近才能发现。额头上的肿块还在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之前的教训。但这种疼痛反而让我更加专注于当前的工作。
最难处理的是那些散落的饼干碎屑。它们会陷入地毯的纤维中,必须用嘴唇贴近地毯,像吸尘器一样仔细吸吮才能清理干净。这个过程极其耗费体力,没多久我的嗓子就疼痛难忍。但我不敢表现出任何不适。
同时几位领导打牌时的动作让清理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每当有人伸腿或挪动椅子时,我都要立即做出反应。有时正在处理一片垃圾,突然有人把脚伸过来,我就不得不立即后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继续。这种走走停停的节奏让工作的难度倍增。
不知过了多久,三位女领导终于起身离开。她们谈笑着走向门口,高跟鞋在地毯上留下一个个凹痕。临走前,雪琪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房间里终于只剩下我和张盟。她坐在真皮沙发上,专注地玩着手机,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整个房间,确保每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完成清理后,我恭敬地跪行到张盟脚边,低头叩首。她随意地抬起脚,在我的头上点了两下,这是默许的信号。我退到一旁,保持着跪姿。
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突然涌上心头:我今天一直在这里服务,完全错过了温度控制的练习。而据说,总公司的领导随时可能来视察。万一到时候出了差错......这个念头让我坐立不安。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举起手。但张盟正专注于手机,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用最卑微的方式引起她的注意 - 我轻轻地"旺旺"叫了两声。
这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立即后悔了,这种行为太过僭越。然而张盟却抬起头来,眼神示意我可以说话。
“张组长......”
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抖,“我......我......”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没有练习掌控温度的忧虑?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个问题太过冒险,我开始后悔提出来。然而张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她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你不用担心。”她的声音平静,“你们的工作安排,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到时候我直接安排你作为我的保障人员跟我一起,不就好了?”
这句话给我整得一阵懵逼。保障人员?这是只有总公司领导才会配备的职位。一个小组长,怎么可能有权力配备保障人员?除非......
我不敢再想下去,只是感激地向张盟连连叩首。但内心的疑惑更深了:她到底是谁?为什么会以小组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但张盟这句话确实让我松了一口气。至少在视察期间,我不用担心因为技术不熟练而被处死。
时日流转,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那些紧张的温度控制训练仿佛成了上辈子的事,现在的我每天都在张盟的房间里度过,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清洁工"。
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其他人提早一个小时到达。在重复打扫一遍卫生,虽然每天离去的时候已经打扫的很干净。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永远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晨光透过落地窗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这短暂的宁静总会让我想起从前的幸福生活。
九点钟一到,她们就会陆续到达。高跟鞋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像是某种无声的提示。预示着我需要立即下跪,保持最标准的姿势。麻将的声音很快会响起,伴随着她们漫不经心的谈笑。我跪在角落里,随时准备着清理任何垃圾。这些曾经和我平起平坐的管理者们,现在把我当作一件随意摆布的物品。
最难熬的是她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她们会突发奇想,要我做一些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她们对“寻开心”总有无穷的创意。有时是简单的模仿动物:让我学狗叫、学猫叫,但必须声音要足够“真诚”。如果她们觉得不够投入,就会要求反复进行,直到她们满意为止。
有时她们会玩“木偶游戏”。几位女领导会轮流发出指令,我必须立即做出相应动作。“抬头”、“低头”等等复杂的动作。命令快速更替,稍有迟疑就要受罚。这些机械的动作让我想起以前在动物园看到的经过训练的海豹,现在我却成了那个被训练的对象。
偶尔,她们会玩“静止游戏”。要求我保持某个不自然的姿势一动不动,动一下就要重来。有时是单脚跪立,有时是双手撑地。时间长了,肌肉会开始颤抖,冷汗直流,但我不敢有丝毫松懈。最难熬的是她们会在旁边谈笑。
雪琪最喜欢的游戏是“找东西”。这个游戏并不是普通的捉迷藏,她总是会随意将某样物品藏在她那双精致长筒靴的底下,故意用脚踩着,让我无从下手地去寻找。因为我是没有资格去随意碰触鞋子,更不用说去动她藏在底下的物品。每次游戏开始时,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急切与无奈。她们的笑声在空气中蔓延,尽管我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她们总是哈哈大笑,似乎在嘲讽我的笨拙。有一次,为了能取回那个小玩意,我心中暗自筹划,我深吸一口气,向雪琪的脚边靠近,微微颤抖着磕头,一边恳求:
“求雪领导高抬贵脚。”
这一幕引起了周围女领导的极大兴趣,她们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欢愉,纷纷发出哈哈大笑声。我抬头看向雪琪,看到她嘴角勾起一抹顽皮的微笑,那笑容中洋溢着无尽的戏谑。她稍微抬起脚,故意将靴子轻轻晃动。
“听到了吗?不可以求我,你得求它。”她的指尖指向她那双吸引眼球的长筒靴。
我无奈地低下头,凝视着她的靴子,最终我也只能顺应她的调侃,对着那双靴子再次磕头,声声呼唤:
“求求你,求求你!”
这场景惹得她们再次大笑,她们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仿佛光芒四射。我憋红了脸,却也只能无奈地出丑。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如何在羞耻和恳求中挣扎,享受着这种感觉,此时雪琪看着我的模样,似乎越发得意,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她微微侧身,一只优雅的腿轻轻抬起,长筒靴的曲线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迷人,她轻轻晃动着脚,似乎在玩弄着我这只乞求者的心理。
“越求越没用哦!”她甜美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玩味,令我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感受到周的目光,那是一种带着嘲弄与享受的目光,她们沉浸在这场表演之中。在她们眼中,我或许就是一个任人摆弄的玩具,毫无反抗之力。我又试图调整一下情绪。
“你就这样放弃吧!再怎么求都没用!”她的话语像是甜蜜的嘲讽,撩动着周围女孩们的笑声,进一步放大了我的窘迫。不知道是靴子还是靴子下的物品似乎在无形中牵动着我的心绪,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怎么,你就这么想要这个小玩意儿吗?”雪琪的声音轻柔却又带着一丝玩味。她微微晃动着她那闪亮的靴子。我心中无奈,却又无可奈何。
“你们说,我要不要答应他?”她转头问她的朋友们,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那些女孩们的笑声此起彼伏。
“只要他跪得更低,或许就能求到!”其中一个女孩发出调侃的声音,众人不禁大笑。
“你真的不愿意再来一次吗?”雪琪微微侧头,眼神中藏着一丝调皮。
“求求你,求求你!”我再次低头,继续磕头。最终,雪琪的笑声在此时变得越来越清脆,周围女孩们则像是沉浸在狂欢中,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想你得加大你的诚意哦!”
“求……求求你……,高抬贵脚!”
雪琪听后,顿时掩嘴轻笑,似乎对这场戏愈发有趣。“快!继续求!”一个女孩在一旁起哄。
“求求你,高抬贵脚,”我不得不再次恳求,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却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绝望。此时雪琪的笑容越发妖娆,她在享受着。
“好吧,求得如此诚恳,我的心都被你打动了呢!”她的声音依旧带着一丝戏谑。随着她轻轻抬起脚,靴子底下的物品终于露出了个角,我仿佛看见了希望。
“来,继续你的求吧,我会考虑的。”她将脚微微往外一移,露出那个藏在靴子底下的物品,似乎在引导我去把它拿回。雪琪微微抬起脚,我正准备伸手去拿她的腿,谁知她突然“啪”的一声继续踩了下去。眼中带着几分戏谑,俏皮地盯着我。这一瞬间,我鼓起勇气,深情地向她的长筒靴亲吻了下去。当我的唇触碰到靴子的那一刻,靴子似乎轻轻抬起了一点,仿佛在回应我的举动。我鼓起勇气,持续亲吻着这双靴子,每一次亲吻都伴随着靴子的微微抬升。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我的内心又现出原先那种异样的感受,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柔而沉醉。靴子在我唇边轻轻摇曳,仿佛在引导我走向更深的投入。就在这时,我注意到靴子已经完全抬起,与我之间的距离仿佛更加拉近,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又强烈的连接。每一次接触都让我感到格外真实,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悸动。
然而最悲惨的莫过于有一次,一位穿着高跟鞋的美女那天心情似乎格外好。她轻盈地用鞋跟踩住几颗硕大的车厘子,那红彤彤的果实像糖葫芦一样整齐地串在了一起,闪烁着诱人的光泽。我被要求躺在地上,努力地咬着这些美味的果实。然而,就在这时,她突然觉得这样的玩乐不过瘾,调皮的她竟然将高跟鞋的鞋跟直接插入了我的嘴里,锋利的鞋跟令我惊愕不已。她并没有停下,直到把鞋跟全部插到了我的喉咙深处反而开始在我嘴里搅动,我顿感喉咙里一阵剧烈的刺痛,伴随着整张嘴被彻底封住,发出了呜呜的声音。随着鞋跟的搅动,钻心的疼痛感使我无助的在高跟鞋下挣扎着,我下意识的伸出双手想要去挪开那残忍的高跟鞋,就在即将接触到高跟鞋的瞬间,一阵冷酷的声音居高临下的传来:
“你的贱手要是碰到了我的鞋子,我就用鞋跟一点一点的把你喉咙踩烂!!!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似乎对我的动作不太满意,那坚硬的鞋跟又被重重的踩下,同时加重了搅动的力度。瞬间让我感到一阵巨大的疼痛。我能感受到她鞋跟重重的撞击着我的牙齿,犹如一根锋利的刀片割裂着我的口腔。纤细的鞋跟是何等的利器,而且还是插进嘴里的利器!嘴巴里哪能承受住鞋跟的搅动,而且鞋跟被磨损的有些棱角。这时喉咙处感受到了异物本能的想要把异物给咽下去,可鞋跟怎么可能被咽下去,我渐渐的有种撕扯的感觉,忍受着嘴里鞋跟的搅动,纤细的鞋跟在嘴里的肆意纵横,划破了舌头,牙龈,我感觉甚至捅漏了口腔内壁,溢出来的血液瞬间肆意流动,与果汁混杂,令人作呕。而就在我痛苦不已的同时,坐在椅子上的美女一改刚才的冷酷乐的笑出了声,笑声清脆悦耳,享受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她似乎对自己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她微微前倾着身子,抚着旁边的椅子,乐不可支。
最终还是张盟发话,说把我玩坏了一段时间谁来保障她。我知道她这是在替我解围。随着张盟的提醒,美女才把鞋跟依依不舍的从我嘴里抽出来。但是疼痛持续在我口腔内徘徊,我的唇和牙齿也感到了一阵冰冷的麻木感,似乎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那尖锐的鞋跟是神圣的。最终,鲜血缓缓渗出,混合着我对疼痛的生理反应,
房间里依然需要打扫。我强忍着剧痛,继续我的清洁工作。每一个弯腰的动作都会牵动口腔的伤处,但我不敢表现出任何不适。这几天我发现了,在她们几人面前展现脆弱往往会招来更多的戏弄。
终于,漫长的麻将时光结束了。其他人陆续离开,只留下我和张盟。往常这个时候,我会继续保持着规矩的跪姿,直到她允许我离开。但今天,当最后一个人带上门的瞬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瘫软在地上。
这是我第一次在张盟面前展现如此失态的一面。在这些天的相处中,我确实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当只有我们两人时,那种压迫感会稍微减轻一些。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如此放松过警惕。然而今天的疼痛实在太过剧烈,我再也支撑不住了。瘫坐在地上的那一刻,我甚至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但张盟只是坐在那里,继续摆弄着她的手机。她修长的腿优雅地交叠着。但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偶尔会从手机屏幕上移开,落在我的身上。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甚至我在她的眼神中也看出了疑惑。
让我不安的是,我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相处模式。在其他人面前,我是一个卑微的奴仆;但在张盟面前,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安全感。
但此刻,在口腔的剧痛中,在疲惫的身体里,这种危险的安全感却成了唯一的慰藉。
在地毯上瘫坐了片刻,口腔内的疼痛依然在持续,但比起身体的痛苦,更让我不安的是当前的处境——张盟还在房间里,而我已经失态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强忍着晕眩和疼痛,我努力缓缓爬向张盟所在的位置。
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口腔的伤处,但我不得不继续。最终,我像往常一样跪在她的脚边,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助和脆弱。今天的伤痛太过严重。突然,我注意到张盟停下了一直把玩着的手机。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连时间都变得迟缓起来。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种审视的重量让我不自觉地低下头,试图逃避这种直接的对视。然而,她优雅地翘着二郎腿,脚上那双黑色高跟鞋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突然,她用鞋尖轻轻勾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来。这个动作既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却又出人意料地温柔。被迫与她对视的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恍惚。她的眼神深邃难测,既不是平日里的冷漠,也不是简单的怜悯。那里面似乎藏着某种我读不懂的情绪,就像一潭深水,让人看不清底。
她用鞋面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当她的鞋尖触碰到我受伤的脸颊时,我忍不住发出了细微的呜咽。那里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轻轻抬起高跟鞋,用鞋面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那动作轻柔得不可思议。黑色的皮质高跟鞋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鞋面光滑细腻,与我伤痕累累的口腔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近乎安抚的举动让我恍惚。在这里,高跟鞋往往是权力和压迫的象征,但此刻它却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抚慰。鞋面缓慢滑过我的脸颊,就像母亲温柔的手抚过受伤孩子的脸庞。这个念头一起,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决堤。记忆中母亲的温柔与眼前的一幕重叠。那时我还是天之骄子,母亲每次看到我受伤,都会轻轻抚摸我的脸,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慰我。而现在,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这份温柔却是通过一双高跟鞋传递的。让我心里泛起难以名状的酸楚。鞋面轻轻蹭过我受伤的部位,异样的触感让我忍不住微微发抖。那里的疼痛依然存在,但此刻却与某种安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感受。我不由自主地偏过头,轻轻蹭着那光滑的皮面,像是要确认这一切不是幻觉。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沾湿了擦过的鞋面。在泪水模糊的视线中,我看到张盟的眼神似乎闪过一丝波动。她放缓了动作,鞋面一下下轻轻擦过我的脸颊,仿佛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这种节奏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时,母亲抚摸我额头的样子。那个动作是那么轻柔,就像母亲在安抚受伤的孩子。这个联想让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 我已经记不清母亲抚摸我的感觉。
恍惚间,我不自觉地迎合着她的动作,让自己的脸颊轻轻蹭着那光滑的鞋面。没有任何交流,这一刻,所有的痛苦、委屈、不甘,都化作泪水夺眶而出。这些天来积压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控制。然而这短暂的温存很快就结束了。当她收回高跟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慌乱和不舍。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收回的动作,想要延续那一刻的温暖。
但张盟只是轻轻摇了摇手指,同时用鞋跟抵住我的额头,温柔但坚定地将我推开。
“你的贱手要是碰到了我的鞋子,我就用鞋跟一点一点的把你喉咙踩烂!!!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似乎对我的动作不太满意,那坚硬的鞋跟又被重重的踩下,同时加重了搅动的力度。瞬间让我感到一阵巨大的疼痛。我能感受到她鞋跟重重的撞击着我的牙齿,犹如一根锋利的刀片割裂着我的口腔。纤细的鞋跟是何等的利器,而且还是插进嘴里的利器!嘴巴里哪能承受住鞋跟的搅动,而且鞋跟被磨损的有些棱角。这时喉咙处感受到了异物本能的想要把异物给咽下去,可鞋跟怎么可能被咽下去,我渐渐的有种撕扯的感觉,忍受着嘴里鞋跟的搅动,纤细的鞋跟在嘴里的肆意纵横,划破了舌头,牙龈,我感觉甚至捅漏了口腔内壁,溢出来的血液瞬间肆意流动,与果汁混杂,令人作呕。而就在我痛苦不已的同时,坐在椅子上的美女一改刚才的冷酷乐的笑出了声,笑声清脆悦耳,享受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她似乎对自己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她微微前倾着身子,抚着旁边的椅子,乐不可支。
最终还是张盟发话,说把我玩坏了一段时间谁来保障她。我知道她这是在替我解围。随着张盟的提醒,美女才把鞋跟依依不舍的从我嘴里抽出来。但是疼痛持续在我口腔内徘徊,我的唇和牙齿也感到了一阵冰冷的麻木感,似乎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那尖锐的鞋跟是神圣的。最终,鲜血缓缓渗出,混合着我对疼痛的生理反应,
房间里依然需要打扫。我强忍着剧痛,继续我的清洁工作。每一个弯腰的动作都会牵动口腔的伤处,但我不敢表现出任何不适。这几天我发现了,在她们几人面前展现脆弱往往会招来更多的戏弄。
终于,漫长的麻将时光结束了。其他人陆续离开,只留下我和张盟。往常这个时候,我会继续保持着规矩的跪姿,直到她允许我离开。但今天,当最后一个人带上门的瞬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瘫软在地上。
这是我第一次在张盟面前展现如此失态的一面。在这些天的相处中,我确实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当只有我们两人时,那种压迫感会稍微减轻一些。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如此放松过警惕。然而今天的疼痛实在太过剧烈,我再也支撑不住了。瘫坐在地上的那一刻,我甚至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但张盟只是坐在那里,继续摆弄着她的手机。她修长的腿优雅地交叠着。但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偶尔会从手机屏幕上移开,落在我的身上。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甚至我在她的眼神中也看出了疑惑。
让我不安的是,我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相处模式。在其他人面前,我是一个卑微的奴仆;但在张盟面前,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安全感。
但此刻,在口腔的剧痛中,在疲惫的身体里,这种危险的安全感却成了唯一的慰藉。
在地毯上瘫坐了片刻,口腔内的疼痛依然在持续,但比起身体的痛苦,更让我不安的是当前的处境——张盟还在房间里,而我已经失态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强忍着晕眩和疼痛,我努力缓缓爬向张盟所在的位置。
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口腔的伤处,但我不得不继续。最终,我像往常一样跪在她的脚边,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助和脆弱。今天的伤痛太过严重。突然,我注意到张盟停下了一直把玩着的手机。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连时间都变得迟缓起来。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种审视的重量让我不自觉地低下头,试图逃避这种直接的对视。然而,她优雅地翘着二郎腿,脚上那双黑色高跟鞋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突然,她用鞋尖轻轻勾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来。这个动作既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却又出人意料地温柔。被迫与她对视的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恍惚。她的眼神深邃难测,既不是平日里的冷漠,也不是简单的怜悯。那里面似乎藏着某种我读不懂的情绪,就像一潭深水,让人看不清底。
她用鞋面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当她的鞋尖触碰到我受伤的脸颊时,我忍不住发出了细微的呜咽。那里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轻轻抬起高跟鞋,用鞋面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那动作轻柔得不可思议。黑色的皮质高跟鞋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鞋面光滑细腻,与我伤痕累累的口腔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近乎安抚的举动让我恍惚。在这里,高跟鞋往往是权力和压迫的象征,但此刻它却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抚慰。鞋面缓慢滑过我的脸颊,就像母亲温柔的手抚过受伤孩子的脸庞。这个念头一起,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决堤。记忆中母亲的温柔与眼前的一幕重叠。那时我还是天之骄子,母亲每次看到我受伤,都会轻轻抚摸我的脸,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慰我。而现在,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这份温柔却是通过一双高跟鞋传递的。让我心里泛起难以名状的酸楚。鞋面轻轻蹭过我受伤的部位,异样的触感让我忍不住微微发抖。那里的疼痛依然存在,但此刻却与某种安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感受。我不由自主地偏过头,轻轻蹭着那光滑的皮面,像是要确认这一切不是幻觉。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沾湿了擦过的鞋面。在泪水模糊的视线中,我看到张盟的眼神似乎闪过一丝波动。她放缓了动作,鞋面一下下轻轻擦过我的脸颊,仿佛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这种节奏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时,母亲抚摸我额头的样子。那个动作是那么轻柔,就像母亲在安抚受伤的孩子。这个联想让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 我已经记不清母亲抚摸我的感觉。
恍惚间,我不自觉地迎合着她的动作,让自己的脸颊轻轻蹭着那光滑的鞋面。没有任何交流,这一刻,所有的痛苦、委屈、不甘,都化作泪水夺眶而出。这些天来积压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控制。然而这短暂的温存很快就结束了。当她收回高跟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慌乱和不舍。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收回的动作,想要延续那一刻的温暖。
但张盟只是轻轻摇了摇手指,同时用鞋跟抵住我的额头,温柔但坚定地将我推开。
突然,张盟的动作发生了变化。她收起了一直优雅翘着的二郎腿,黑色的高跟鞋稳稳地踩在地面上。出乎意料的是,我听到了高跟鞋与脚分离时细微的声响。偷瞄着,她穿着细腻的肤色丝袜。这个场景让我屏住了呼吸。张盟展露出如此私密的一面是极其罕见的。这让我想起了母亲在家时的样子,那时她也会在一天工作结束后脱下标志着权力的长靴。
张盟重新翘起二郎腿,那个动作依然带着与生俱来的优雅。但此刻没有了高跟鞋的阻隔,整个氛围都变得不一样了。她穿着丝袜的足部缓缓向我靠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当她的玉足轻轻贴上我的脸颊时,我几乎要颤抖起来。隔着丝袜传来温暖而细腻的触感。这不是普通的丝袜,是最高级的定制品,连最细微的纹路都感受不到,光滑得像是一层轻纱。每一次轻柔的移动,都带着令人安心的温度。张盟的动作优雅,就像在演奏一首无声的乐章。她的足尖时而轻点我的眼角,擦拭着我的眼泪,时而轻抚我的脸颊,擦拭着留下的泪水。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既不会碰到伤处带来疼痛,又能让我感受到她的存在。那种柔软的触感几乎让人忘记了所有的痛苦。丝袜的温度渐渐和肌肤相融,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感。有时她会稍稍用力,将我的脸轻轻托起,这种力道既坚定又温柔。她的玉足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珍珠般的柔和光泽,透过丝袜能看到完美的轮廓。脚趾的曲线优美,简单的擦拭动作,在她的演绎下也变成了一场优雅的舞蹈。当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时,她会用足尖轻巧地接住,动作精准而细腻。有时她会停顿片刻,像是在感受什么,然后再继续那轻柔的安抚。足部肌肤透过丝袜传来淡淡的体温,这温度比之前的高跟鞋要温暖得多。有时她会用脚背轻轻摩挲我的脸颊,那种柔滑的触感让人忘记了眼前的处境,仿佛回到了某个温暖的港湾。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滞了,房间里只剩下轻柔的摩挲声和我偶尔的啜泣声。她的动作都那么从容不迫,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玉足轻轻擦过的地方,似乎连疼痛都减轻了几分。隔着丝袜传来的温度比高跟鞋要暖和得多,也柔软得多。她的动作极其轻柔,就像对待什么易碎的珍宝。
在这里,领导者的每一个部位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但此刻,她却用这样亲密的方式安慰我。丝袜的触感细腻而温暖,轻轻擦过我的眼角,将那些不争气的泪水一点点抹去。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母亲用手帕为我擦眼泪的情景。
我震惊了不知道张盟为什么会这样做。但在这一刻,我只想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情里。但我不敢多想,只能静静地感受着这一刻的温暖。任由她的玉足轻轻擦拭着我的泪水,就像对待一个受伤的孩子。这种温柔,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
正当我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柔时刻,门外突然响起了三声清晰的敲门声。
张盟重新翘起二郎腿,那个动作依然带着与生俱来的优雅。但此刻没有了高跟鞋的阻隔,整个氛围都变得不一样了。她穿着丝袜的足部缓缓向我靠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当她的玉足轻轻贴上我的脸颊时,我几乎要颤抖起来。隔着丝袜传来温暖而细腻的触感。这不是普通的丝袜,是最高级的定制品,连最细微的纹路都感受不到,光滑得像是一层轻纱。每一次轻柔的移动,都带着令人安心的温度。张盟的动作优雅,就像在演奏一首无声的乐章。她的足尖时而轻点我的眼角,擦拭着我的眼泪,时而轻抚我的脸颊,擦拭着留下的泪水。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既不会碰到伤处带来疼痛,又能让我感受到她的存在。那种柔软的触感几乎让人忘记了所有的痛苦。丝袜的温度渐渐和肌肤相融,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感。有时她会稍稍用力,将我的脸轻轻托起,这种力道既坚定又温柔。她的玉足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珍珠般的柔和光泽,透过丝袜能看到完美的轮廓。脚趾的曲线优美,简单的擦拭动作,在她的演绎下也变成了一场优雅的舞蹈。当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时,她会用足尖轻巧地接住,动作精准而细腻。有时她会停顿片刻,像是在感受什么,然后再继续那轻柔的安抚。足部肌肤透过丝袜传来淡淡的体温,这温度比之前的高跟鞋要温暖得多。有时她会用脚背轻轻摩挲我的脸颊,那种柔滑的触感让人忘记了眼前的处境,仿佛回到了某个温暖的港湾。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滞了,房间里只剩下轻柔的摩挲声和我偶尔的啜泣声。她的动作都那么从容不迫,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玉足轻轻擦过的地方,似乎连疼痛都减轻了几分。隔着丝袜传来的温度比高跟鞋要暖和得多,也柔软得多。她的动作极其轻柔,就像对待什么易碎的珍宝。
在这里,领导者的每一个部位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但此刻,她却用这样亲密的方式安慰我。丝袜的触感细腻而温暖,轻轻擦过我的眼角,将那些不争气的泪水一点点抹去。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母亲用手帕为我擦眼泪的情景。
我震惊了不知道张盟为什么会这样做。但在这一刻,我只想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情里。但我不敢多想,只能静静地感受着这一刻的温暖。任由她的玉足轻轻擦拭着我的泪水,就像对待一个受伤的孩子。这种温柔,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
正当我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柔时刻,门外突然响起了三声清晰的敲门声。
“咚、咚、咚”。声音不重,却打破了房间里的宁静。
张盟的动作没有丝毫慌乱,她优雅地收回玉足,动作从容而自然,我看着那双刚刚还在为我拭泪的玉足,缓缓地重新没入黑色的高跟鞋中。她重新翘起二郎腿的动作行云流水。瞬间,那个高高在上的张盟又回来了。她拿起手机,目光落在屏幕上,姿态优雅而疏离。这种转变如此迅速,让我一时恍惚。
敲门声过后是短暂的沉默。我依然保持着跪姿,背对着门口。突然,门被从外面打开,一阵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闷响传来。我不敢抬头,却能感觉到来人走向张盟的方向。刚才玉足的温存还在脸颊上留存,此刻却让我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能将头垂得更低。来人似乎递给了张盟一些东西,我听到物品轻微的摩擦声。最后,那名女性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门被轻轻带上。
“把头抬起来。”张盟的声音轻柔,像一缕轻纱飘落。
我缓缓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精致的纸袋子。纸袋通体洁白,上面烫印着金色的公司logo,在灯光下泛着奢华的光芒。那个logo每一笔都是用纯金制成,重达一克。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随意丢弃这种昂贵的纸袋,而现在,它在我眼前却显得如此珍贵。
张盟轻轻拆开纸袋,从里面取出一堆药品,整齐地摆在她翘起的腿上。每个药盒上都印着相同的金色logo,包装精美得像艺术品。
我仔细看着那些药品:消炎药的包装上印着淡金色的叶脉纹路,止疼药盒子上有流线型的金色暗纹,消肿药则用烫金勾勒出精致的花边。止血药的盒子通体墨黑,以及等等其他一些药品。这些药品只有公司的logo在正中央熠熠生辉。这些都是公司最顶级的医疗产品,普通人别说使用,连见都很难见到。
“你把这些药吃了。”张盟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柔和。
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我再次湿了眼眶。
“好的,张组长,我等会回去就吃。”我强忍着泪水说道。
没想到这句话却换来张盟一记白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生动的表情,那个瞬间的她竟显得格外可爱。紧接着,她抬起穿着高跟鞋的脚,轻轻地踹了我一下。
“你们在集训营里是没有权利得到任何医疗救治的,你还想回去吃?”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你脑子被踹坏了吗?”
我这才醒悟过来,在集训营里,我们连基本的医疗权利都被剥夺了。张盟指了指旁边的垃圾桶,“用我们刚才丢掉的杯子吧。”
我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个几乎未用过的水晶杯,杯子上还带着一丝温度。倒上清水时,我发现药品中夹着一张便签。那是一张触感极其细腻的纸张,正上方依然印着金色的公司logo。便签上详细记录着每种药品的使用剂量,字迹工整优美。我按照上面的说明,开始服用药物。每一片药都包装得极其精致。
服药的过程中,她时不时瞥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当我准备一次吞下较多药片时,她突然伸出脚轻轻踢了我一下,示意我要一片片慢慢来。
药片的形状各不相同,但都小巧精致。有的呈现出完美的圆形,有的则是精心设计的椭圆。每一片都光滑无比,表面都压印着微小但清晰的公司标志。我小心翼翼地吞咽着每一片药,感受着它们滑过喉咙的触感。张盟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偶尔调整一下翘着的二郎腿。最后一片药服下后,张盟满意地点了点头。她修长的手指把药盒重新收好,放回精致的纸袋中。
“你整理一下就回去吧。”随后她修长的手指指向旁边的桌子,那里摆着各种精致的零食和点心,“这些你带些回去,自己偷偷吃了吧。今天就不要去食堂了,那里的食物不干净。”
桌上的零食琳琅满目:进口的巧克力、高级的饼干、昂贵的糕点,还有一些包装精美的果干。这些都是平日里我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每一样食物的包装上都印着公司logo烫金的标志,在灯光下闪烁着奢华的光芒。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温暖的东西充满。这种关怀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下显得尤为珍贵。
我郑重地跪直身体,调整到最标准的跪姿。跪在柔软的地毯上,我先是端正跪姿,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大腿上,背脊挺得笔直。调整好位置后,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向张盟叩首。
第一个头,我先把双手交叠着平放在地毯上,动作恭敬,手掌能感受到地毯细密的绒毛,还带着一丝余温。我缓缓低头,额头重重地叩在手背前方的地毯上。力道很大,地毯的绒毛轻轻刺痒着我的额头,在撞击的瞬间发出一声闷响。
第二个头,我的手掌位置不变,但这次磕得更重。额头落下的位置与第一下几乎完全重合,地毯的绒毛已经被我砸出了一个清晰的凹痕。此时张盟的高跟鞋就在我视线可及的地方,那完美的鞋型此刻近在咫尺。
第三个头,我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这最后一下要把所有的感激之情都倾注其中。额头重重叩在已经被压实的地毯上,发出最沉闷的声响。我能感觉到额头那里火辣辣的,但这种疼痛反而让这份感恩更加真实。随后我依旧保持着跪姿,慢慢地俯下身子。张盟的高跟鞋纹丝不动地踩在地毯上,鞋面如镜般光洁。我能看到鞋面上反射的灯光。慢慢的靠近,我能闻到高级皮革特有的香味。那是一种内敛高雅的气息,混合着张盟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越靠近,这种香气越发明显,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韵味。
我的嘴唇轻轻贴上鞋面时,能清晰地感受到皮革细腻的质地。那触感冰凉光滑,却莫名地让人安心。我刻意控制着力道,让这个吻既表达足够的敬意,又不会在完美的鞋面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嘴唇与鞋面相触的时间不长不短,恰到好处。像是在进行某种庄重的仪式。起身时,我看到刚才嘴唇接触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印记,但很快就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那短暂的印记就像此刻的温情,转瞬即逝,却真实存在过。
张盟看着我的动作,满意地点了点头。她的表情保持着优雅,但眼神中似乎多了一丝温度。“把练习成绩统计的手机给我,”她继续说道,声音轻柔但不容置疑,“这两天的淘汰人选我来定吧。”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部记录着生死数据的手机,双手恭敬地递上。手机的屏幕还亮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每一个数字都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最后,我又向张盟深深地磕了三个头。这次的叩首比之前更加郑重,仿佛要把所有的感激之情都倾注其中。然后,我缓缓地向后退去,保持着最标准的跪姿,一点点向门口移动。直到退出房门,我都能感觉到张盟的目光。那道目光充满威严,又带着一丝难得的温情。门在身后轻轻关上,却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
时间在这样的日子里缓缓流逝。我口腔的伤口在张盟给的药物作用下逐渐愈合,那些精致的药片果然效果显著。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规律而简单:打扫房间、清理垃圾、被她们戏弄取乐。但这种生活比起之前的温度控制训练,已经是莫大的恩赐。
自从那天张盟给了我药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工作结束后,都会郑重地向她磕三个头。这不仅是一种感恩,更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即使她从不表态,但我知道她看在眼里。
今天也和往常一样。房间打扫完毕后,我郑重地跪在张盟面前,开始了例行的叩首仪式。我先是仔细调整跪姿,确保姿势端正,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尊重。双手规矩地放在大腿上,背脊挺直,头微微低垂。
一个,两个,三个。
每次磕完头,我都会保持最后的跪姿片刻。
完成仪式后,我按照惯例缓缓地跪行出门。确保不会发出任何响动。来到门外,我站在走廊里等待郑阳、姜蓉和许明。我们约好一起去食堂吃晚饭,这是难得的几个可以交流的时刻。
不多时,房门被推开。但从他们出来的氛围,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姜蓉的眼睛红肿,显然刚刚哭过。许明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茫然,像是被什么可怕的事情吓住了。就连一向稳重的郑阳也面色凝重。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快步走到三人身边,轻声问道:“郑阳,发生什么事了?”
张盟的动作没有丝毫慌乱,她优雅地收回玉足,动作从容而自然,我看着那双刚刚还在为我拭泪的玉足,缓缓地重新没入黑色的高跟鞋中。她重新翘起二郎腿的动作行云流水。瞬间,那个高高在上的张盟又回来了。她拿起手机,目光落在屏幕上,姿态优雅而疏离。这种转变如此迅速,让我一时恍惚。
敲门声过后是短暂的沉默。我依然保持着跪姿,背对着门口。突然,门被从外面打开,一阵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闷响传来。我不敢抬头,却能感觉到来人走向张盟的方向。刚才玉足的温存还在脸颊上留存,此刻却让我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能将头垂得更低。来人似乎递给了张盟一些东西,我听到物品轻微的摩擦声。最后,那名女性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门被轻轻带上。
“把头抬起来。”张盟的声音轻柔,像一缕轻纱飘落。
我缓缓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精致的纸袋子。纸袋通体洁白,上面烫印着金色的公司logo,在灯光下泛着奢华的光芒。那个logo每一笔都是用纯金制成,重达一克。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随意丢弃这种昂贵的纸袋,而现在,它在我眼前却显得如此珍贵。
张盟轻轻拆开纸袋,从里面取出一堆药品,整齐地摆在她翘起的腿上。每个药盒上都印着相同的金色logo,包装精美得像艺术品。
我仔细看着那些药品:消炎药的包装上印着淡金色的叶脉纹路,止疼药盒子上有流线型的金色暗纹,消肿药则用烫金勾勒出精致的花边。止血药的盒子通体墨黑,以及等等其他一些药品。这些药品只有公司的logo在正中央熠熠生辉。这些都是公司最顶级的医疗产品,普通人别说使用,连见都很难见到。
“你把这些药吃了。”张盟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柔和。
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我再次湿了眼眶。
“好的,张组长,我等会回去就吃。”我强忍着泪水说道。
没想到这句话却换来张盟一记白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生动的表情,那个瞬间的她竟显得格外可爱。紧接着,她抬起穿着高跟鞋的脚,轻轻地踹了我一下。
“你们在集训营里是没有权利得到任何医疗救治的,你还想回去吃?”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你脑子被踹坏了吗?”
我这才醒悟过来,在集训营里,我们连基本的医疗权利都被剥夺了。张盟指了指旁边的垃圾桶,“用我们刚才丢掉的杯子吧。”
我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个几乎未用过的水晶杯,杯子上还带着一丝温度。倒上清水时,我发现药品中夹着一张便签。那是一张触感极其细腻的纸张,正上方依然印着金色的公司logo。便签上详细记录着每种药品的使用剂量,字迹工整优美。我按照上面的说明,开始服用药物。每一片药都包装得极其精致。
服药的过程中,她时不时瞥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当我准备一次吞下较多药片时,她突然伸出脚轻轻踢了我一下,示意我要一片片慢慢来。
药片的形状各不相同,但都小巧精致。有的呈现出完美的圆形,有的则是精心设计的椭圆。每一片都光滑无比,表面都压印着微小但清晰的公司标志。我小心翼翼地吞咽着每一片药,感受着它们滑过喉咙的触感。张盟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偶尔调整一下翘着的二郎腿。最后一片药服下后,张盟满意地点了点头。她修长的手指把药盒重新收好,放回精致的纸袋中。
“你整理一下就回去吧。”随后她修长的手指指向旁边的桌子,那里摆着各种精致的零食和点心,“这些你带些回去,自己偷偷吃了吧。今天就不要去食堂了,那里的食物不干净。”
桌上的零食琳琅满目:进口的巧克力、高级的饼干、昂贵的糕点,还有一些包装精美的果干。这些都是平日里我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每一样食物的包装上都印着公司logo烫金的标志,在灯光下闪烁着奢华的光芒。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温暖的东西充满。这种关怀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下显得尤为珍贵。
我郑重地跪直身体,调整到最标准的跪姿。跪在柔软的地毯上,我先是端正跪姿,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大腿上,背脊挺得笔直。调整好位置后,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向张盟叩首。
第一个头,我先把双手交叠着平放在地毯上,动作恭敬,手掌能感受到地毯细密的绒毛,还带着一丝余温。我缓缓低头,额头重重地叩在手背前方的地毯上。力道很大,地毯的绒毛轻轻刺痒着我的额头,在撞击的瞬间发出一声闷响。
第二个头,我的手掌位置不变,但这次磕得更重。额头落下的位置与第一下几乎完全重合,地毯的绒毛已经被我砸出了一个清晰的凹痕。此时张盟的高跟鞋就在我视线可及的地方,那完美的鞋型此刻近在咫尺。
第三个头,我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这最后一下要把所有的感激之情都倾注其中。额头重重叩在已经被压实的地毯上,发出最沉闷的声响。我能感觉到额头那里火辣辣的,但这种疼痛反而让这份感恩更加真实。随后我依旧保持着跪姿,慢慢地俯下身子。张盟的高跟鞋纹丝不动地踩在地毯上,鞋面如镜般光洁。我能看到鞋面上反射的灯光。慢慢的靠近,我能闻到高级皮革特有的香味。那是一种内敛高雅的气息,混合着张盟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越靠近,这种香气越发明显,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韵味。
我的嘴唇轻轻贴上鞋面时,能清晰地感受到皮革细腻的质地。那触感冰凉光滑,却莫名地让人安心。我刻意控制着力道,让这个吻既表达足够的敬意,又不会在完美的鞋面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嘴唇与鞋面相触的时间不长不短,恰到好处。像是在进行某种庄重的仪式。起身时,我看到刚才嘴唇接触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印记,但很快就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那短暂的印记就像此刻的温情,转瞬即逝,却真实存在过。
张盟看着我的动作,满意地点了点头。她的表情保持着优雅,但眼神中似乎多了一丝温度。“把练习成绩统计的手机给我,”她继续说道,声音轻柔但不容置疑,“这两天的淘汰人选我来定吧。”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部记录着生死数据的手机,双手恭敬地递上。手机的屏幕还亮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每一个数字都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最后,我又向张盟深深地磕了三个头。这次的叩首比之前更加郑重,仿佛要把所有的感激之情都倾注其中。然后,我缓缓地向后退去,保持着最标准的跪姿,一点点向门口移动。直到退出房门,我都能感觉到张盟的目光。那道目光充满威严,又带着一丝难得的温情。门在身后轻轻关上,却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
时间在这样的日子里缓缓流逝。我口腔的伤口在张盟给的药物作用下逐渐愈合,那些精致的药片果然效果显著。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规律而简单:打扫房间、清理垃圾、被她们戏弄取乐。但这种生活比起之前的温度控制训练,已经是莫大的恩赐。
自从那天张盟给了我药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工作结束后,都会郑重地向她磕三个头。这不仅是一种感恩,更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即使她从不表态,但我知道她看在眼里。
今天也和往常一样。房间打扫完毕后,我郑重地跪在张盟面前,开始了例行的叩首仪式。我先是仔细调整跪姿,确保姿势端正,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尊重。双手规矩地放在大腿上,背脊挺直,头微微低垂。
一个,两个,三个。
每次磕完头,我都会保持最后的跪姿片刻。
完成仪式后,我按照惯例缓缓地跪行出门。确保不会发出任何响动。来到门外,我站在走廊里等待郑阳、姜蓉和许明。我们约好一起去食堂吃晚饭,这是难得的几个可以交流的时刻。
不多时,房门被推开。但从他们出来的氛围,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姜蓉的眼睛红肿,显然刚刚哭过。许明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茫然,像是被什么可怕的事情吓住了。就连一向稳重的郑阳也面色凝重。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快步走到三人身边,轻声问道:“郑阳,发生什么事了?”
咋觉得张萌是知道计划全程,然后专门来保护或者管住男主的人呢….或者是当年有关系的男女,童养媳…..
watermallen:↑咋觉得张萌是知道计划全程,然后专门来保护或者管住男主的人呢….或者是当年有关系的男女,童养媳…..戏份那么重不是没可能,我甚至怀疑就是开头的姐姐闺蜜。
特别喜欢,作者加油。可以写点在庄园里做运动,比如打高尔夫、骑马之类的情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