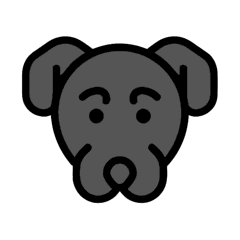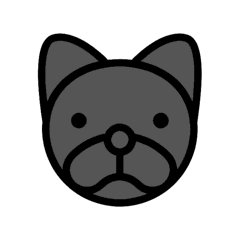《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已完结)
现实已完结逆NTR口舌鞭打长靴吸烟
猴面包🏆笔下封神发布于 2023-11-14 20:28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人老师写得好,更新快点就更好
Crying发布于 2023-11-14 22:11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写的非常细腻啊
1430948575发布于 2023-11-14 23:44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神😭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3-12-09 23:38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后半夜零星来了几个客人,都是网吧里出来买烟的。到了凌晨,送货的厢货来了,我点清货,签了单子,开始把货一件件往库房搬。搬到一半,厢货走了,我才注意到它的后面还停着一辆车,一辆黑色的SUV,打着火,但车灯没开。
等到我搬完货,又熬到早上,煮好茶叶蛋和关东煮,店主过来接班,我出门的时候,我才发现那辆SUV还没走。借着清晨微弱的天光,我看到徐梦正坐在驾驶位上睡觉。
不愧是富贵人家,真不怕烧油啊。我一边想着,一边上去敲她的车窗。她悠悠转醒,打开车内的灯,按下车窗,我看到她的眼眶很红,脸上有浅浅的泪痕。
“早上好。”我说。
“几点了?”她还有些迷离。
“六点半了。”我说,“你不回家吗?”
“不想回。”她靠在真皮椅背上,“你要不要进来说?可暖和了。”
座椅加热的灯亮着,她一定很舒适,我站在寒风中想。这样一想,寒冷忽然也变得色情起来。
“不用了。你接下来打算去哪?”
“你下班后一般去什么地方?”
“网吧。”我有点不好意思。
“走,我跟你去。”
“啊?不好吧?”我忽然有种捡到心碎女大学生的感觉。
“怎么了?”她从副驾的包里掏出DV。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
“没什么,就是里面抽烟的人很多。”我赶忙找了个借口。
“没事,我也抽烟的。”她说。
于是我带着她来到那家我常去的网吧,离便利店不远,也就有个二三十米的样子。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拍。
“来了哥。”一进门,网管就热情的招呼我。
“咱这儿还有富裕的证吗?”我给网管散了一根烟。
“有呢哥,今天带嫂子来玩啊?”网管接过烟,从抽屉里翻了张身份证出来。
“不是。充50吧。”我掏出手机扫码。
“啥不是啊,你看嫂子笑得多开心。”
我慌忙地扭头看她,却正对上DV镜头,心里的期待还没升起就已经破碎。
网吧里只有寥寥几个坚持通宵的人,临近考试周,很多学生都开始临时抱佛脚复习了。我在高配区的角落找了俩座位,清了下桌面上的垃圾,拉开小沙发让她坐下,然后打开机器。
“你一般玩什么游戏?”她透过镜头看我。
“激战2,或者warframe吧。”我看向镜头,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
“你不玩LOL或者CF吗?还有那个什么吃鸡,据说挺火的?”
“吃鸡以前玩,后来号被盗了,被封了,就没再玩。CF和LOL的环境不太好,怕被骂。”
“原来如此。”她挪开DV,“我想拍一些你打游戏的素材,你可以找一些你比较沉浸的游戏玩吗?”
“好的。”我说。
我打开warframe,在新纪之战和第二场梦之间犹豫了一下,最后选了新纪之战。然后我迅速沉浸了进去,直到我追着战甲被放逐到太空,无助地悬浮在茫茫宇宙中,听到中枢cy的那句“Tenno, on your six”时,才回过神来。
“你还挺沉浸的嘛~”她收起DV。
“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进去了。”我挠挠头。
“没事,这样的素材才好。”她说,“而且看到你玩的开心,我也开心。”
“谢谢。”我说,“你不打点什么吗?机器都开了。”
“我剪下片子算了。”她看向显示器,皱了皱眉,“怎么连PR都没有。”
“来网吧的都是来打游戏的。”
“你很喜欢玩游戏吗?”她问。
“还好啦,有些游戏很厉害的,‘第九艺术’可不是白叫的。”
“是吗?”她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
于是我带她打了一上午warframe的战役,她的评价是“故事结构很完整,很有趣”。然后她开车回家,我在网吧睡到晚上。
等到三天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了那副充满活力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等到我搬完货,又熬到早上,煮好茶叶蛋和关东煮,店主过来接班,我出门的时候,我才发现那辆SUV还没走。借着清晨微弱的天光,我看到徐梦正坐在驾驶位上睡觉。
不愧是富贵人家,真不怕烧油啊。我一边想着,一边上去敲她的车窗。她悠悠转醒,打开车内的灯,按下车窗,我看到她的眼眶很红,脸上有浅浅的泪痕。
“早上好。”我说。
“几点了?”她还有些迷离。
“六点半了。”我说,“你不回家吗?”
“不想回。”她靠在真皮椅背上,“你要不要进来说?可暖和了。”
座椅加热的灯亮着,她一定很舒适,我站在寒风中想。这样一想,寒冷忽然也变得色情起来。
“不用了。你接下来打算去哪?”
“你下班后一般去什么地方?”
“网吧。”我有点不好意思。
“走,我跟你去。”
“啊?不好吧?”我忽然有种捡到心碎女大学生的感觉。
“怎么了?”她从副驾的包里掏出DV。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
“没什么,就是里面抽烟的人很多。”我赶忙找了个借口。
“没事,我也抽烟的。”她说。
于是我带着她来到那家我常去的网吧,离便利店不远,也就有个二三十米的样子。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拍。
“来了哥。”一进门,网管就热情的招呼我。
“咱这儿还有富裕的证吗?”我给网管散了一根烟。
“有呢哥,今天带嫂子来玩啊?”网管接过烟,从抽屉里翻了张身份证出来。
“不是。充50吧。”我掏出手机扫码。
“啥不是啊,你看嫂子笑得多开心。”
我慌忙地扭头看她,却正对上DV镜头,心里的期待还没升起就已经破碎。
网吧里只有寥寥几个坚持通宵的人,临近考试周,很多学生都开始临时抱佛脚复习了。我在高配区的角落找了俩座位,清了下桌面上的垃圾,拉开小沙发让她坐下,然后打开机器。
“你一般玩什么游戏?”她透过镜头看我。
“激战2,或者warframe吧。”我看向镜头,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
“你不玩LOL或者CF吗?还有那个什么吃鸡,据说挺火的?”
“吃鸡以前玩,后来号被盗了,被封了,就没再玩。CF和LOL的环境不太好,怕被骂。”
“原来如此。”她挪开DV,“我想拍一些你打游戏的素材,你可以找一些你比较沉浸的游戏玩吗?”
“好的。”我说。
我打开warframe,在新纪之战和第二场梦之间犹豫了一下,最后选了新纪之战。然后我迅速沉浸了进去,直到我追着战甲被放逐到太空,无助地悬浮在茫茫宇宙中,听到中枢cy的那句“Tenno, on your six”时,才回过神来。
“你还挺沉浸的嘛~”她收起DV。
“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进去了。”我挠挠头。
“没事,这样的素材才好。”她说,“而且看到你玩的开心,我也开心。”
“谢谢。”我说,“你不打点什么吗?机器都开了。”
“我剪下片子算了。”她看向显示器,皱了皱眉,“怎么连PR都没有。”
“来网吧的都是来打游戏的。”
“你很喜欢玩游戏吗?”她问。
“还好啦,有些游戏很厉害的,‘第九艺术’可不是白叫的。”
“是吗?”她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
于是我带她打了一上午warframe的战役,她的评价是“故事结构很完整,很有趣”。然后她开车回家,我在网吧睡到晚上。
等到三天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了那副充满活力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chromaso发布于 2023-12-13 06:00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嚯,看起来又是年度大作预定了。文字功底和叙事技巧太强了。
人仿老师牛逼!
人仿老师牛逼!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3-12-13 11:50
Re: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3-12-13 11:52
Re: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11.14)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4-01-01 01:12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2024.1.1)
对于她被家里人要求和一个特定的男人结婚这件事后续,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我悄悄地观察她的眼睛,企图看出一些类似于小说中“眼底的阴霾”一类的东西,但是毫无所获。我不知道是我观察人的能力太差,还是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希望是后者。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祝愿她能够早日摆脱被家里摆布的境地。
真是可笑。一个男人,在自己想要保护的女孩子面前,能提供的唯一帮助,竟然只有在自己心中的默默祈祷。这让我心中那些颇为得寸进尺的美好妄想冷却了下来。无论幻想中,我能够如何地接近她,现实里我仍然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虽然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我们之间,借鲁迅的话讲,“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当然,这障壁对她而言既不可悲,也不厚重,可悲和厚重都只是单对我的。
“嘿!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徐梦从试衣间里跳出来,身上是一件米黄色的大衣。
“啊?”我慌忙从思绪中抬头,“我对时尚没什么了解……”
“ZARA这种快时尚品牌也论不上什么时尚啦,我是说对这件衣服的印象。”
“呃……很好看?”
“亏你还是写小说的创作者,就不能细致一点吗。”她笑着说。
“好吧。”我开动脑筋,“我觉得这件大衣很适合在明媚的阳光下,被一个满盈着活力的年轻女孩,向她的伙伴们带有微微炫耀意味地展示。我也会担心如果下雨,这件大衣会风光不再,它会变得又湿又冷,紧紧贴在穿着者的身上,没办法起到抵挡风雨的作用。”
“哇哦,这不是很不错嘛。”她拍拍手,“其实我是来替剧里的一个角色选衣服的,听你这么一说,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她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快速打了一些字。
“谢谢。”我说。
“那接下来我们该进行下一个项目了。”
“什么项目?”
“请你吃饭呀,前几天不是被那件事情打断了吗?”
“哦!”我想起来了,“怪不好意思的,要不还是我请你吧?”
“没关系,这个钱剧组出了。”她拍拍胸脯。
“剧组?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吗?”
“两个人也是剧组!”她兴致满满地说。
随后,她领着我来到商场内的一家餐厅,看起来很豪华。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冲锋衣,开始琢磨起自己被认为是外卖骑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过这么高档的餐厅,应该也不会做外卖业务吧?
“你吃西餐吗?”她回头问我。
“我都可以。”我说。
“那就这里吧,这里的鱼类做得还不错。”她似乎对这家餐厅很熟悉。
她放慢脚步,适应着我慢吞吞的、犹豫的脚步,和我并肩走进了餐厅的大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像电影里一样,抬起一只胳膊让她扶着。我用余光悄悄看了看四周,可惜并没有范例供我临时抱佛脚,餐厅里稀疏的客人都在用餐。
“我们想要一个靠窗的双人位。”我听到她对侍者说。
侍者领着我们来到了空位,往桌上放了两本菜单。我看到徐梦脱下大衣,交给侍者,也学着她的样子,脱掉冲锋衣外套。拉链拉开的声音让我感到很难堪,我把外套递给侍者,不敢去看他的神情。侍者拿着两件衣服离开了,周围没有其他食客,偌大的空间只剩下我和徐梦。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拉开椅子?”我半开玩笑地说。
“你如果这样做,我会很高兴的。”她用话术巧妙地照顾着我的尊严。
于是我费力地搬起沉重的椅子,好让它不像刚刚的拉链一样,在萦绕着优雅钢琴曲的豪华大厅里发出难听的声响。她走到座位上,却没有坐下去。
“推椅子也麻烦你啦。”她好心提醒道。
“抱歉。”我配合着她动作,搬动那张沉得过分的椅子,让她稳稳地落座。
“谢谢~”她说。
“我才该谢谢你提醒我。”我有些羞愧。
这时侍者送来了擦手的热毛巾,以及一件稍大一点的西装外套。我在《闻香识女人》上看到过,高档的餐厅会给衣着不是那么正式的人提供西装,来维持餐厅里的体面。我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迅速穿上那件宽松的外套,然后对侍者轻声道谢。
或许我应该做一个趴在橱窗外面,透过明净的玻璃羡慕地看着里面的食客的落魄的人,这样我会更加安心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立难安。
“你不会怪我领你到这里来吧。”徐梦看上去有些担心,“我没有想要羞辱你或者让你难堪的意思。”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我说。
“真的吗?”她狐疑地看着我。
“是有点……不过没关系啊,我不在意的。”我说。
因为在你面前,我更渴望尊严被狠狠践踏。我在心里悄悄补充道。
人在隐瞒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看向别处。我十分庆幸我也逃不过这个习惯,因为我在看向商场内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景星和她的闺蜜正从自动扶梯上来!
我立马用手遮住脸,扭过身子,背对着窗户。
“怎么了?”徐梦问。
“我……看到我母亲了。”
“啊?那你快到桌子下面躲一下。”
我来不及对徐梦表示感谢,掀开天鹅绒的桌布就钻了进去,好像钻进女人的裙摆。
桌下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几乎拖地的桌布把光线挡得严严实实,我什么都看不到。我摸摸兜,发现手机落在了桌子上。这时候,我听到手机在上面震动了两下,多半是什么广告短信。
这时候,我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侍者来送餐前面包,和徐梦点的一支酒,随后便离去了。
“你饿吗?要吃点面包吗?”她小声问。
我循着声音凑上去,小声回答:“谢谢。”
随后我听到布料摩擦的声音,她撩起桌布,递进来一片面包。亮光随着面包一起涌入,照亮了我身下的地面,以及她的靴子。
“看得到吗?”她抖了抖手腕,面包在她指尖一颠一颠的。
或许她没有意识到,但在我的视角里,这样的动作很像是在逗弄小狗。我忽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任何人能看到我的行为后,我以尽量小的动作挪动蹲着的双腿,跪在地上,双手撑地。冰凉的瓷砖地面迅速吸走了掌心的热量,膝盖和手掌被身体的重量压迫着,唤醒了身体中关于“屈辱”一词的自然记忆。
但是在徐梦面前自寻羞辱,又实在是令我兴奋的一件事。我伸长脖子,用嘴叼住那片面包,轻轻把它从徐梦的指尖之间叼了出来。我能看到光线照在她手指捏过的地方,在微微的凹陷里拉出阴影。
她的手撤了出去,桌布放下,周围重回黑暗。我把面包放在地上,像狗一样用鼻尖确认位置,然后叼着面包的一角,一口一口,跪在徐梦的面前,吃掉了她随手喂给我的食物。我感到一股热流从下身升腾起来,我舔舔嘴唇,心里生出了一种饥渴,我渴望更多,渴望更多徐梦无意识的羞辱。
“那个……”在性欲的推动下,我鲁莽地开口,“可以把桌布掀起来一点吗,下面好黑。”
“好。”她说着,往前坐了坐。我看到她黑色的皮靴率先伸入,平整的靴筒撩起桌布,掀开一个水滴形的口子,亮光再次涌入。她把桌布搭在膝盖上,随后自然地翘起腿,富有弹性的大腿将修身的牛仔裤绷紧,挤压成光滑的椭圆曲面。
“你还要面包吗?”她轻声问。
“可以的话请再给我一片。”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我面冲着她翘起的双腿,俯首请求。
“给。”她又递来一片面包。
“谢谢。”我叼起面包,把面包片对折,拿在手里,心里诞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我看着徐梦的靴子,在暖黄色灯光的照耀下,细密的皮革纹路泛着流光。我把鼻子凑上去,轻轻嗅了嗅,皮革的香气中夹杂着一点尘土的味道。我向上嗅着,后脑勺却顶到了桌子,我侧过头,把脸紧紧贴在桌子上,感觉脸颊都被压平了,才堪堪凑到靴口的边缘。我不敢靠的太近,怕不小心碰到会被发现。
淡淡的汗味传入鼻腔,钻透气管,顺着神经包裹住大脑。我死死压抑着脑海里那股把鼻子塞进徐梦靴筒的冲动,攥紧拳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仔细地嗅着那股味道,她用的香水有股淡淡的木质香味,点缀着青春女生那股说不清道不明,但确实缥缈地存在着的体香,以及长期穿着后的微微酸味和汗味。我仔细地嗅着,试图分辨出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再把它们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可是不巧,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她放开交叉的双腿,我赶忙往后躲,脑袋咚地一声磕在桌子上,震得餐盘和刀叉叮咣响。
“你没事吧?”徐梦问,“好像有人给你发消息,需要把手机给你拿下去吗?”
“没事,不用管。”我揉着脑袋,灼热的痛觉在磕到的地方燃烧起来。
徐梦没有回应。我伏低身子,虽然性欲因为这一吓而退却不少,但是我原本的计划还是打算继续实施。我拿起对折的面包片,用中心最柔软的部分抹在她的靴面上,借着她胯下透来的灯光,细细拭去她靴面上的浮灰。我不敢用力,怕被她发觉,因此靴子侧面所沾染的些许泥点,我只能一遍一遍地来回磨擦,一点点蹭掉它们。
脚步声再次传来,侍者开始上前菜了。徐梦稍稍往后坐了坐,让桌布自然垂下,放我独自跪在黑暗中,啃食为她擦过靴子的面包。
“开始上菜了,外面好像没有人了,你母亲应该是走了,要不然你出来吧?”徐梦等侍者走了之后说。
“好的。”我一把把面包塞进嘴里,从桌子下面钻出来。
我的身体重新回到了光明的世界中,灵魂却还留在黑暗的桌下,她的靴前。我不记得那顿饭都吃了些什么,是否有什么高级的味道。但我清晰地记得徐梦靴口那一抹幽幽的气味,以及为她擦过靴子的面包的味道。
手机上的消息是景星发的,两条都是,要我今晚早些去她家里。我没有回复,这种单方面的指令我已习以为常,但在今天,它让我格外地不想从徐梦身边离开。
我和徐梦在地下停车场分别。她坐上她的那辆SUV,我能想象她踩下油门踏板,命令车头那颗四缸引擎为她而转,输出动力的样子。她的车轮胎旋转着,狠狠碾在停车场的胶皮地面上,在地面尖锐的哀嚎声中,她在面前远去,把我抛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中。
我看向地面的轮胎印,在反光的胶皮上格外显眼,我想跪下去亲吻它们,就像亲吻徐梦走过的路面一样。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这里有摄像头。
真是可笑。一个男人,在自己想要保护的女孩子面前,能提供的唯一帮助,竟然只有在自己心中的默默祈祷。这让我心中那些颇为得寸进尺的美好妄想冷却了下来。无论幻想中,我能够如何地接近她,现实里我仍然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虽然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我们之间,借鲁迅的话讲,“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当然,这障壁对她而言既不可悲,也不厚重,可悲和厚重都只是单对我的。
“嘿!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徐梦从试衣间里跳出来,身上是一件米黄色的大衣。
“啊?”我慌忙从思绪中抬头,“我对时尚没什么了解……”
“ZARA这种快时尚品牌也论不上什么时尚啦,我是说对这件衣服的印象。”
“呃……很好看?”
“亏你还是写小说的创作者,就不能细致一点吗。”她笑着说。
“好吧。”我开动脑筋,“我觉得这件大衣很适合在明媚的阳光下,被一个满盈着活力的年轻女孩,向她的伙伴们带有微微炫耀意味地展示。我也会担心如果下雨,这件大衣会风光不再,它会变得又湿又冷,紧紧贴在穿着者的身上,没办法起到抵挡风雨的作用。”
“哇哦,这不是很不错嘛。”她拍拍手,“其实我是来替剧里的一个角色选衣服的,听你这么一说,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她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快速打了一些字。
“谢谢。”我说。
“那接下来我们该进行下一个项目了。”
“什么项目?”
“请你吃饭呀,前几天不是被那件事情打断了吗?”
“哦!”我想起来了,“怪不好意思的,要不还是我请你吧?”
“没关系,这个钱剧组出了。”她拍拍胸脯。
“剧组?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吗?”
“两个人也是剧组!”她兴致满满地说。
随后,她领着我来到商场内的一家餐厅,看起来很豪华。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冲锋衣,开始琢磨起自己被认为是外卖骑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过这么高档的餐厅,应该也不会做外卖业务吧?
“你吃西餐吗?”她回头问我。
“我都可以。”我说。
“那就这里吧,这里的鱼类做得还不错。”她似乎对这家餐厅很熟悉。
她放慢脚步,适应着我慢吞吞的、犹豫的脚步,和我并肩走进了餐厅的大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像电影里一样,抬起一只胳膊让她扶着。我用余光悄悄看了看四周,可惜并没有范例供我临时抱佛脚,餐厅里稀疏的客人都在用餐。
“我们想要一个靠窗的双人位。”我听到她对侍者说。
侍者领着我们来到了空位,往桌上放了两本菜单。我看到徐梦脱下大衣,交给侍者,也学着她的样子,脱掉冲锋衣外套。拉链拉开的声音让我感到很难堪,我把外套递给侍者,不敢去看他的神情。侍者拿着两件衣服离开了,周围没有其他食客,偌大的空间只剩下我和徐梦。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拉开椅子?”我半开玩笑地说。
“你如果这样做,我会很高兴的。”她用话术巧妙地照顾着我的尊严。
于是我费力地搬起沉重的椅子,好让它不像刚刚的拉链一样,在萦绕着优雅钢琴曲的豪华大厅里发出难听的声响。她走到座位上,却没有坐下去。
“推椅子也麻烦你啦。”她好心提醒道。
“抱歉。”我配合着她动作,搬动那张沉得过分的椅子,让她稳稳地落座。
“谢谢~”她说。
“我才该谢谢你提醒我。”我有些羞愧。
这时侍者送来了擦手的热毛巾,以及一件稍大一点的西装外套。我在《闻香识女人》上看到过,高档的餐厅会给衣着不是那么正式的人提供西装,来维持餐厅里的体面。我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迅速穿上那件宽松的外套,然后对侍者轻声道谢。
或许我应该做一个趴在橱窗外面,透过明净的玻璃羡慕地看着里面的食客的落魄的人,这样我会更加安心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立难安。
“你不会怪我领你到这里来吧。”徐梦看上去有些担心,“我没有想要羞辱你或者让你难堪的意思。”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我说。
“真的吗?”她狐疑地看着我。
“是有点……不过没关系啊,我不在意的。”我说。
因为在你面前,我更渴望尊严被狠狠践踏。我在心里悄悄补充道。
人在隐瞒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看向别处。我十分庆幸我也逃不过这个习惯,因为我在看向商场内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景星和她的闺蜜正从自动扶梯上来!
我立马用手遮住脸,扭过身子,背对着窗户。
“怎么了?”徐梦问。
“我……看到我母亲了。”
“啊?那你快到桌子下面躲一下。”
我来不及对徐梦表示感谢,掀开天鹅绒的桌布就钻了进去,好像钻进女人的裙摆。
桌下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几乎拖地的桌布把光线挡得严严实实,我什么都看不到。我摸摸兜,发现手机落在了桌子上。这时候,我听到手机在上面震动了两下,多半是什么广告短信。
这时候,我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侍者来送餐前面包,和徐梦点的一支酒,随后便离去了。
“你饿吗?要吃点面包吗?”她小声问。
我循着声音凑上去,小声回答:“谢谢。”
随后我听到布料摩擦的声音,她撩起桌布,递进来一片面包。亮光随着面包一起涌入,照亮了我身下的地面,以及她的靴子。
“看得到吗?”她抖了抖手腕,面包在她指尖一颠一颠的。
或许她没有意识到,但在我的视角里,这样的动作很像是在逗弄小狗。我忽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任何人能看到我的行为后,我以尽量小的动作挪动蹲着的双腿,跪在地上,双手撑地。冰凉的瓷砖地面迅速吸走了掌心的热量,膝盖和手掌被身体的重量压迫着,唤醒了身体中关于“屈辱”一词的自然记忆。
但是在徐梦面前自寻羞辱,又实在是令我兴奋的一件事。我伸长脖子,用嘴叼住那片面包,轻轻把它从徐梦的指尖之间叼了出来。我能看到光线照在她手指捏过的地方,在微微的凹陷里拉出阴影。
她的手撤了出去,桌布放下,周围重回黑暗。我把面包放在地上,像狗一样用鼻尖确认位置,然后叼着面包的一角,一口一口,跪在徐梦的面前,吃掉了她随手喂给我的食物。我感到一股热流从下身升腾起来,我舔舔嘴唇,心里生出了一种饥渴,我渴望更多,渴望更多徐梦无意识的羞辱。
“那个……”在性欲的推动下,我鲁莽地开口,“可以把桌布掀起来一点吗,下面好黑。”
“好。”她说着,往前坐了坐。我看到她黑色的皮靴率先伸入,平整的靴筒撩起桌布,掀开一个水滴形的口子,亮光再次涌入。她把桌布搭在膝盖上,随后自然地翘起腿,富有弹性的大腿将修身的牛仔裤绷紧,挤压成光滑的椭圆曲面。
“你还要面包吗?”她轻声问。
“可以的话请再给我一片。”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我面冲着她翘起的双腿,俯首请求。
“给。”她又递来一片面包。
“谢谢。”我叼起面包,把面包片对折,拿在手里,心里诞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我看着徐梦的靴子,在暖黄色灯光的照耀下,细密的皮革纹路泛着流光。我把鼻子凑上去,轻轻嗅了嗅,皮革的香气中夹杂着一点尘土的味道。我向上嗅着,后脑勺却顶到了桌子,我侧过头,把脸紧紧贴在桌子上,感觉脸颊都被压平了,才堪堪凑到靴口的边缘。我不敢靠的太近,怕不小心碰到会被发现。
淡淡的汗味传入鼻腔,钻透气管,顺着神经包裹住大脑。我死死压抑着脑海里那股把鼻子塞进徐梦靴筒的冲动,攥紧拳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仔细地嗅着那股味道,她用的香水有股淡淡的木质香味,点缀着青春女生那股说不清道不明,但确实缥缈地存在着的体香,以及长期穿着后的微微酸味和汗味。我仔细地嗅着,试图分辨出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再把它们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可是不巧,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她放开交叉的双腿,我赶忙往后躲,脑袋咚地一声磕在桌子上,震得餐盘和刀叉叮咣响。
“你没事吧?”徐梦问,“好像有人给你发消息,需要把手机给你拿下去吗?”
“没事,不用管。”我揉着脑袋,灼热的痛觉在磕到的地方燃烧起来。
徐梦没有回应。我伏低身子,虽然性欲因为这一吓而退却不少,但是我原本的计划还是打算继续实施。我拿起对折的面包片,用中心最柔软的部分抹在她的靴面上,借着她胯下透来的灯光,细细拭去她靴面上的浮灰。我不敢用力,怕被她发觉,因此靴子侧面所沾染的些许泥点,我只能一遍一遍地来回磨擦,一点点蹭掉它们。
脚步声再次传来,侍者开始上前菜了。徐梦稍稍往后坐了坐,让桌布自然垂下,放我独自跪在黑暗中,啃食为她擦过靴子的面包。
“开始上菜了,外面好像没有人了,你母亲应该是走了,要不然你出来吧?”徐梦等侍者走了之后说。
“好的。”我一把把面包塞进嘴里,从桌子下面钻出来。
我的身体重新回到了光明的世界中,灵魂却还留在黑暗的桌下,她的靴前。我不记得那顿饭都吃了些什么,是否有什么高级的味道。但我清晰地记得徐梦靴口那一抹幽幽的气味,以及为她擦过靴子的面包的味道。
手机上的消息是景星发的,两条都是,要我今晚早些去她家里。我没有回复,这种单方面的指令我已习以为常,但在今天,它让我格外地不想从徐梦身边离开。
我和徐梦在地下停车场分别。她坐上她的那辆SUV,我能想象她踩下油门踏板,命令车头那颗四缸引擎为她而转,输出动力的样子。她的车轮胎旋转着,狠狠碾在停车场的胶皮地面上,在地面尖锐的哀嚎声中,她在面前远去,把我抛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中。
我看向地面的轮胎印,在反光的胶皮上格外显眼,我想跪下去亲吻它们,就像亲吻徐梦走过的路面一样。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这里有摄像头。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4-01-01 01:12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2024.1.1)
酒后写的,水平可能有所下降,见谅
chromaso发布于 2024-01-01 03:16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2024.1.1)
牛子,很有感觉
猴面包🏆笔下封神发布于 2024-01-01 08:44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2024.1.1)
徐梦,我要徐梦,呜呜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4-01-01 15:16
Re: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2024.1.1)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4-01-08 21:55
Re: Re: 《羔羊在子宫中摇滚地麻木》(2024.1.1)